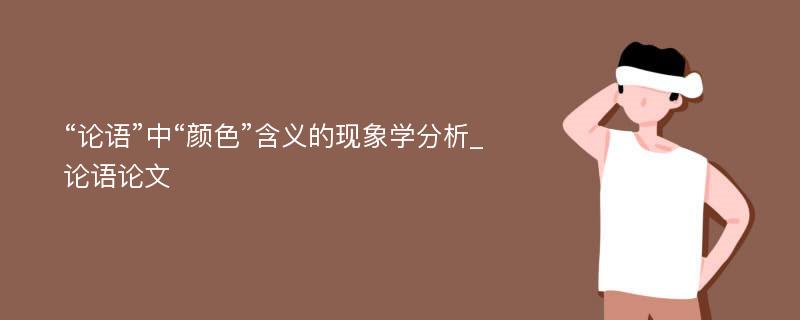
《论语》“色”的意义的现象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现象学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1)04-0047-09
一
《论语》“色”的意义,一直是人们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
《孔子研究》2000年第4期刊载的裴传永的文章《〈论语〉“色难”新解》,对“色难”一词作了重新解释。《论语》原文是: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
“色难”,传统上有两种解释。包咸认为,“色”指和颜悦色,“难”是困难的意思,“色难”,指弟子服侍父母的时候,保持和颜悦色很困难。郑玄则将“色”理解为“承顺父母的颜色”,“色难”指事奉父母时承望父母的脸色是件困难的事。裴传永以为包咸的说法是不对的。据《说文》和段玉裁的注,“色”是中性词,“和颜悦色”却是褒义词,而且从语义学的角度看,也是一种臆解。郑玄的注解也有问题。从语法学的角度讲,如果名词“色”被活用为动词,后应跟宾语,而“难”不可以作宾语。此外,从具体语境看,“难”也不可能是“困难”的意思。裴传永根据自己的统计分析,并且参考其他典籍资料,指出:“色”指面色、神情,“难”字相当于“戁”,“色难”应该指容色恭敬。
《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和1992年第1期分别刊登过《〈论语〉析疑三则》和《“贤贤易色”再析疑》,辨析“色”的意义。“贤贤易色”究竟是什么意思,前人说法颇多。朱熹《论语集注》注曰:“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杨伯峻《论语译注》却把“易色”译为“不重容貌”。两篇析疑作者的意见,又各不相同。一位坚称,“贤贤易色”应该指爱好贤人如同好色一样,另一位则理解为对待贤人时要轻视外貌。实际上除此以外,“贤贤易色”还可以有其他的解释,如皇侃在《论语疏》中就把“易色”理解作“改易平常之色”。钱穆的《论语新解》注解“色”时,直接指为“色貌”、“女色”。
如果细心考察,我们还可以发现《论语》其它章节中所谈及的“色”,同样也可以有多种理解。如:
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先进》)
朱熹《集注》解释说:“言但以其言论笃实而与之,则未知其为君子者乎,为色庄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色庄”就是神情上伪装庄重。“色庄者”就是伪君子。何晏《论语集解》的理解又完全不同:“色庄者,不恶而严,以远小人。”“色庄”就是自身矜庄,端庄严肃的意思。《集解》称“论笃”者、“君子”和“色庄”者“皆可以为善人”,按照《集解》的理解,“色庄者”却是正人君子。《论语》还有一章,与此相关:
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泰伯》)
朱熹《集注》注曰:“正颜色而近信,则非色庄也。”“非色庄”按他的理解就是“不伪装庄重”,人家便信任自己。郑玄却认为,“正颜色,能矜庄严栗,则人不敢欺诈之也。”“正颜色”并没有去掉伪装这样的一个环节,而是直接地表现出庄重严肃的模样。
《论语·子罕》和《卫灵公》重出的一句话也存在歧义: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有人把这一句话理解为“要象好色那样好德”。也有人认为是“不要好色,而要好德。”前者视好色为正面的、积极的,后者却视好色为消极的、应该否定的。前者注解“色”为“姣好的颜色”,后者却把“色”憎恶为“色欲”,一种万恶的欲望。更有人引“子见南子”及《史记·孔子世家》,试图用“史实”证明“色”确实指的是美色、色相。
此外,《宪问》有一章,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有人说“色”是“礼貌”(朱熹《集注》)。也有认为“辟色”是躲避“不好的脸色”(杨伯峻《论语译注》)。程树德《论语集释》考证说:高诱注引此文“辟色”作“辟人”。解“色”为“人”,是为了与“世”、“地”和“言”相一致。
至于《乡党篇》的末尾一章“色斯举矣”的意思,后人更是聚讼不已,莫衷一是。
其实,除了《乡党》记录“色”比较多,《论语》各篇出现“色”字的频率并不高。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人们对《论语》各章“色”的意义的理解如此不同,甚至出现完全相反的解释?是孔子谈论“色”时,本来就有歧义,所以后人解释起来特别困难?还是后人理解《论语》“色”的本意时,由于各自解释的依据和方法有所不同,从而出现不一致的结论?如果是后者,我们要进一步提问:能否找出一条合适的途径,真正领会和把握孔子《论语》中所谈论的“色”的意义,并且对前人的解释作出合理的评价?
二
同一章句的“色”,人们的理解却完全不同,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对解释者的分歧原因作出分析。裴传永说,“色”的意义,可以从语义学、语法学和具体语境等视角作不同的考察。当然这样的说法是比较现代的了。前人解释《论语》的“色”,可以作文字的考证、字源的探索,典籍之间的互相印证等等,解释者运用这些方法,可以各有侧重,有时候即使运用了同一种方法,例如字源上的考证,依据《说文》的定义与《礼记》的文本来解释,结论也可能会大不相同。
但是,真正影响“色”的不同理解,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当解释者把“色”的意义理解为特定语境中的实指含义时,就很可能出现歧见。例如“色难”一语,一般的解释者都特别注意到它是孔子回答弟子子夏问孝时的答语,解释者通过体会弟子服侍先生(父母)这样一种语境理解“色”究竟指什么:包咸、皇侃、司马光认为“色”指父母的颜色和志趣;而郑玄、朱熹以为“色”指承奉父母时弟子“自己的颜色”。很显然,当我们讨论“色”具体所指为何时,我们对单一语词本身的关注远胜于对这一语词所指示的实际生活的关心。“语境”一词如果强调语词意义的环境,那么我们就会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色”字的意义和作用上,进入我们眼帘的是作为语言现象的“色”,可以谈论的“色”,而不是真实的生活现象的“色”,不是可以直接观察的、并且体现着生活关联的“色”。因此如果我们停留在文本语词的意义上来谈“色”的意义,必然要会遇到“它实指什么”这样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不同的人自然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如果我们要想真正找到孔子所谈及的色的原意,就不能专注于“色”的语词意义,而应发现孔子所领会的色的生活意义。
第二,解释者对“色”的不同的情境体会,也可能会产生各种歧见。这里所说的“情境”,表示解释者理解具体章节“色”的意义时,不仅仅从实际生活的层次上去领会和把握它,而且这种领会和把握总是已经有情绪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反面的例子。《说文解字》对“色”这样定义:“色,颜气也。”段玉裁注解说:“颜者,两眉之间也。心达于气,气达于眉间,谓之色。”这一定义(包括段注)的陈述看上去很客观、很中性。除非我们另做特殊的说明,根据这一定义,“色”字本身并不负载任何自己与他人的社会关联信息,同时,它的规定性也不具有任何情境特征,即无论何种情境下,“色”总是指颜气。很多解释者声称,以《说文》定义为根据,完全能够理解《论语》各章“色”的意义,事实并非如此。无论解释者将“色难”理解为“承顺父母的颜色是困难的”,还是“弟子自己和颜悦色是困难的”,实际上总是已经表白了解释者对生活(即服侍父母)的领会的情绪意识(或恭敬、或谨慎)。“色”绝不是一种单纯的实体性对象物(“颜气”)。无论解释者把“色庄”理解为外表“伪装庄重”,还是“容色庄严”,解释者总是已经带有某种情绪的了(或嫌恶,或敬肃)。因此,《说文》的定义不可能是解释的最后根据,对“色”的解释首先有赖于对孔子谈及“色”的情境的领会。
当然,解释者可以采取冷漠的态度来解读孔子,他们可以毫不思考地按照流行的说法,把“好德如好色”解释为“喜好德性就象喜好女色一样”,把“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理解为戒除“性的冲动”(注:参看黎顺清《“戒之在德”传统注释质疑》,载《孔子研究》1989年第2期)。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态度,自己的喜好,来审度孔子谈及“色”时的情绪意向,于是对于同一个“色”字,尊孔者与贬孔者的理解便会大相径庭。但是就是在这种冷漠中、在不假思索中,或者在任由自己的情感驱遣中,解释者不可避免地离开了孔子的原意,同一个“色”的意义也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版本。
通过以上两点分析,我们不仅说明了《论语》“色”的意义的各种不同理解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们也触及了领会和把握《论语》“色”的原初意义的合适途径:离开单纯的语词意义,回到实际的生活层面;离开非真实的生活情境体会,回到真实的生活情境体会,从而让孔子所谈及的“色”的原象活生生地向我们显示出来。不过我们要沿着这条途径找到孔子的原意,还须费一番功夫。首先,我们要力图排除受各种成见的影响,克服解释的随意性;其次,我们要将孔子真实领会色这一现象的整体情境刻划出来,分析构成色这一现象的整体情境的各个要素和各个环节,展现出“色”的本来意义。这样的一项工作我们称之为现象学的分析。
三
一旦我们不从单纯的语词,而从生活表现上来考察,就会很自然、很容易地发现一个特殊现象:在《论语》的谈话中,“色”通常与“言”想伴随并且以对等的形式被表述,如“巧言令色”(《学而》、《公冶长》、《阳货》)、“察言而观色”(《颜渊》)、“正颜色…出辞气”(《泰伯》曾子语)、“…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宪问》)、“论笃是与…色庄者乎?”(《先进》)等等。这种表述形式上的一致性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仅仅是表面的,色与言的一致性更体现在生活功能方面:两者均为表达自己的方式,色通过表情显示自己,而言则通过言谈显示自己。言和色功能一致性,对于我们恰当地描述和分析色的情境特征,并进而理解孔子所谈“色”的原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色通过“逞颜色”(《乡党》)表现,就象言经由“出辞气”一样。不逞颜色,喜怒悲欢等情绪就无从表现。但是色的表现既不是一种生理学意义上的身体表现,也不是心理表现。色与逞颜色一致,情绪与情绪的表现一致。任何情绪都不可能内在于个人,色不可以孤芳自赏、顾影自怜,独语的言(即“隐居放言”)也没有任何意义。相反地,言的意义在于意识到有人接闻,色的意义在于意识到有人承望,言和色的表现不会象朱熹所说的那样“以自快足于己”(《大学章句》释“好好色”)。如果我们说色和言是己身的表现,那么己身总是行止在道上,总是已经处在与他人相关联的环境中。用现代的话说,色所表现的情绪不是单纯个人的情绪,而是己人之间的情绪关联,即社会情绪。
与自己发生关联的这个他人,不是抽象的社会他人,而是与自己有特定关系的他人(可能是君臣、父子、兄弟,也可能是师徒、朋友、乡人,甚至陌生人之间,或者与先辈之间的关系);自己总是已经立身于特定的“位”上(相对于他人而言的特定的社会地位),而且处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或在家或在邦;或在宗庙或在朝廷,或斋戒或祭祀,或为政或有事),与他人发生情绪上的关联。色这种情绪表现,就其作为真实的表现而言,应该展现出己人之间的一种情绪联系。从而使与自己有着特定关联的他人、自己的现实处境(“位”),以及自己的历史处境,直接构成色的真实情境。
色表现着我的情绪,我对自己的这一表现、对整体情境和各个相关环节又必定有所领会。这种领会就是情绪意识(孔子称之为“知”):对情境的察知和思虑。但是,色的表现,与言的表现一样,也可以摆脱对真实的生活情境的体会,摆脱与他人的真实的情绪关联,成为纯粹的表现。这种色的表现者,也会对他所处的环境有所察知,但是却基于虚假的情绪意识之上。《论语》中,孔子分别称以上两种色的表现为“达”和“闻”。
“…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颜渊》)
达者之察言观色,不是对言和色的对象性认识,而是对言和色的整体情境的领会,对相应的己人关联的真实体会,或者毋宁说,达者察知到,言和色的表现把真实的己人关系开放出来,把自己所处的环境恰当地刻划出来,也把自己的真实情绪表露出来。皇侃、马融,甚至今人钱穆、杨伯峻,均以“察言而观色”为观察他人之言、之色。实际上,将“察言而观色”与“色取仁而行伪”(“取”是取向,意向的意思)相对照,就可以发现,察言观色是对自身的言和色的情绪意向。
达者之察言观色,既要把自己的言和色的表现直接领会为自己的生活,而且还要在积极的思虑中把握真实的生活情境,把握己人之间的真实处境。孔子说,“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言思忠…色思温。”(《季氏》)“思虑”当然不是内省,而是通过对与他人共处的真实情境的领会,通过自己的情绪表现,使自己与他人的情绪关联保持在真实的情境中。实际上,色的真实情境,被领会为己身处于其间的道;色的表现者所拥有的己人之间这种真实的情绪关联,被领会为仁;而表现者自己持身于真实的情境、持身于真实的己人情绪关联,则被领会为德。达者之言和色的表现,能够把自己的情境恰如其分地、真实地予以展示,并且真实地加以领会。孔子说:
“辞达而已矣!”(《卫灵公》)
与“达”相对的是“闻”。我们上面说过,言有接闻,色有承望,不可以言、色为一己之事。但是,若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谨守其身,言、色的表现完全为了求取他人的闻见,就会失去其真实的为己的情绪表现。
求闻于人者,其心也易违仁。求闻于人者利用了言和色的显示功能、表现功能(“文”),但是忽略了、甚至有意掩盖了自己的真实情绪(“质”)。他们也许很明了自己所处的环境,很明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但是他无法持身于真实的己人情绪关联中,他的言和色的表现与他的真实生活也就割裂开来了。“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伪,居之不疑。”色取仁而行违者,其色的表现很容易为“克、伐、怨、欲”(《宪问》)等情绪意向所占据,很少顾及自身真实的生活情境和可能的行为表现。他会安于可以闻见的表面形式,以牺牲对生活情境的真实领会和持有为代价,己人关系也只能维持在虚假的情绪意向之上。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阳货》)
巧言令色者,务求致饰于外,表里之间、文质之间极不一致。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阳货》)
这里说的“表里”、“内外”,并不表明色只呈现于外表,而真实的情绪则藏于内里。实际上,无论是巧言令色者,还是色厉内荏者,他们努力回避的不是自己“内心”情感,而是己人之间最纯净的、最真实的情绪关联。这样的言和色,与其说表现自身的真实情绪,不如说掩盖真实的情绪。
色为什么又能够掩盖我自己的真实情绪呢?上面我们讲,色是情绪的表达,它不仅表达着我自己,而且表达着我和他人之间的关联,不过这都要基于对色的真实领会和真实表现。但是,色和言一样,很容易从表达的真实情境和情绪意向中解脱出来,很容易被看作自身具有独立意义的纯粹的表达形式和纯粹的交流方式,很容易在虚假的情绪意向(如上面提到的“克伐怨欲”)中表现。于是,色和言的表达者的真实情绪掩藏起来,原先只有在真实的情绪意向中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却可以在虚假情绪的掩护之下自身出场。
我们先来看《论语》的一个例子: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先进》)
子路的一番答话,就其自身来说没有错,就是孔子自己也可能会赞同这样的意见。但是他为什么还要斥责子路是个佞者?实际上子路的答话离开了自己“使子羔为费宰”这一实际生活情境,在拒绝对实际生活的真实领会之下,专就言谈本身的意义来狡辩。子路怀有好胜之心这样一种虚假的情绪,故而言不由衷,言不及义。《论语》中还有另外一章: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公冶长》)
求闻于人者无法真正察言观色,唯有口给捷便,放纵颜色,很容易成为一个佞者,孔子也称之为“便佞”(《季氏》)。佞者也考量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考量自己的处境,但是他不以实际的生活情境为根据,相反地,他恰恰要摆脱与他人之间真实的情绪关联,摆脱对实际生活情境的察知和思虑。“色取仁”的“取”字,很充分地表达出佞者以投机取巧的姿态,周旋于社会和他人的意向。
佞者摆脱己人真实情绪关联的方式,恰恰又与言、色的表现紧密联系在一起。本来我生活在言和色中,言和色将我自己与他人的关系通过情绪关联的方式实现出来。但是佞者却利用言和色,把它们视作与他人交流的手段、中介和工具,并且为实现自己的虚假的情绪意向和目的服务。语言和颜色一旦不表现真实的生活情境,真实的生活就无法发生,而佞者也只能苟且言笑而已。
求闻于人者,不仅其心易违仁,其意也不好德,其行也常无道。我们讲过,言和色是己身的表现,但是这种表现既不是心理活动,也不是生理活动,而是处于特定生活情境中、与他人有着特定生活关联的生活表现。若能够持身于真实生活情境中,则己身成德,否则无德可称。有德者,对实际的生活情境有真实的体会且能持身其间,言和色的表现也能够切合实际。相反,言和色若不顾及实际的生活情形,则自己就会难以立身。所以孔子说: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
“巧言乱德。”(《卫灵公》)
“乱德”就是乱身。巧言令色使人从真实生活情境中抽身出来。而离开真实的生活情境,也便失去立身之所。所以要想有德,就必须谨顺其身。孔子说,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卫灵公》)
好德者身据于德,好色者则志意于色的表现。好色者以求闻于人为鹄的,可以无所顾忌,而好德者其色的表现,必须依据对实际生活情境的真实体会,并且持身于真实的情绪意向。所以好言、好色往往多有过失,不仅小人如此,君子也会忘“形”失“色”。孔子说:
“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季氏》)
“言及之”,是言说完全依据对自身生活情境的真实领会,也就是达道的意思。“达”和“及”一方面指明言和色恰如其分地表达;另一方面,也指明自己真实的生活情境的充分显现。言和色的表现若不能谨顺其身,不仅言、色不以其道,其行也必远道矣。
四
《论语》中孔子谈及“色”的时候,并没有指出真实的情绪意向与虚假的情绪意向得以区分开来的形而上学或道德上的根据,但是,就色如何真实地表达情绪,即自己如何回到真实的情绪意向中来,回到真实的人生中来,孔子则多有述及。
首先,要有“耻”。佞者即使言、色和行相乖违,也不会反躬自省。孔子认为,要做一个质直的人,就要回到实际的生活情境中,从而获得对真实情绪关联的体会,这就必须有耻。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宪问》)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
廉耻、愧怍,能够使我们能够联系自己的行来察言观色,在自己真实的情境体会中立身,远离便佞,远离鄙倍。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宪问》)
“辟世”、“辟地”是远避无道之君、无道之国。“辟色”、“辟言”是身避佞人,也可以说是“避身”。所以高诱引此文时不用“辟色”,而直接作“辟人”,不无道理,但是他也没有领会到“言”和“色”的一致性,不明白“辟言”也是避人。至于把“辟色”理解为避离美色,则实在无法与上下文照应。
其次,要有“谨”。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斯言也讱,其谓之仁矣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颜渊》)
“讱”,难也。“其言也讱”,是说话很难的样子,与“讷于言”(《里仁》)、“言之不出”的意思相同。言讱者不能象佞者那样口给捷便,善于机巧。孔子同样说明色的真实表现也不可以张扬。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肉,先生馔。”(《为政》)
“色难”,就是不轻易表露情绪,好像呈现颜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此处的“难”与“讱”意思相同。“色难”、“言讱”,并非真的因为表露颜色和言语本身很困难,而是在表现言、色时,依据对真实生活情境体会,而完全排斥虚假的情绪意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所以孔子说,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宪问》)
言讱、色难都是谨顺其身,从而有可能使自己持身于实际的情境中,并且对真实的情绪关联有真切的领会。如果弟子随意嬉笑怨怒,就无法敬事父母,因为他无法持守在对父母的真实情绪意向(“孝”)中。
孔子特别儆戒少年,因为他们年少轻狂,容色容易轻慢,或恣意倨傲,因此他说,
“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季氏》)
此外,还要有“信”。信,就是信实的意思。耻和谨使我自己远离便佞,谨守己身,但它们皆为消极的情绪。色和言的表现欲切近实际生活,还需要有一种积极的基本情绪,即“信”。“信”表明情绪意向是真实的,对实际生活情境的领会是恰当的。它与虚假的情绪意向根本对立。
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泰伯》)
曾子所说的“正颜色”与孔子的“正名”有相似之处。“正颜色”不只是要端肃自己的颜色,而且也指颜色的改变和保持须是对实际生活情境的真切领会和反应,杜绝受虚假情绪的支配。同样,正名并不在于名称的意义和运用是否恰当,相反,在讨论语言的意义和功用的普遍性之前,我必须观察到它在实际人生中的可能显现样式,必须将语言表达的实际情境先于语言自身的意义加以把握和领会。言和色的信实,不在于实指对象的存在与否的确证,也不在于它们的运用的实际功效和结果,而在于它们的表现是否已经将实际的人生展示出来了,把真实的生活情境表达出来了,在于情绪意向的真实与否。当然,“信”还必然要求言和色表现出己人关联的真实情绪,而且这样的情绪必定是相互关联的。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民无信不立。”(《颜渊》)“信,则民任也。”(《阳货》)。言、色的信实,不仅仅是自己的立身之本,也是立人之本。民若信之,则临其民时也会色庄言笃了。
正颜色,正名,就是正己身。如果说“耻”以避身便佞,“谨”以谨顺其身,那么“信”则以就有道。孔子说,“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学而》)这里说的“道”既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原则,也不是一种神秘的存在物,它就是我处身其间的实际的生活情境。
至此,我们对《论语》的“色”的意义考察也就告一段落。我们并没有给出所谓的“色”的实指意义。但是很显然,我们完全在生活意义的层面上,对《论语》的“色”的本质意义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色”不再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而是被还原为一种现实的生活表现。只有对实际的生活情境和己人之间的情绪关联获得真切的领会,也就是说,只有拥有真实不虚的情绪意识,色的表现,与言的表现一样,才真正具有立身行道的生活意义。当然,我们分析还很初步,随着我们对《论语》其他生活现象的分析的不断深入,“色”的意义必将更加具体地显示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