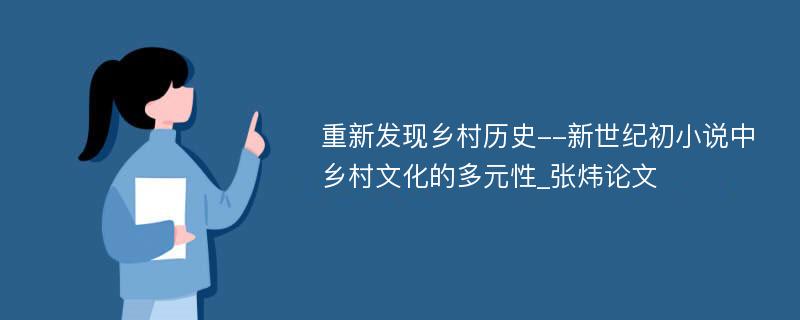
重新发现的乡村历史——本世纪初长篇小说中乡村文化的多重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村论文,本世纪论文,长篇小说论文,发现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仅为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所发现,在他们的表达中显得越来越急切和尖锐,而且它同样被文学家强烈地感知到了。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城市和乡村的巨大反差以形象的方式被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这种反差和不平衡,不只是 城乡的空间物理距离,或者是城乡现代化水平和物质生活的天然差距,而是说,在整体 上欠发达的中国,其乡村潜隐的文化问题可能仍然是中国最本质、最具文化意义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心城市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不断 缩小,发达国家和地区享受的物质、文化生活,在中心城市几乎已经无所不有,发达国 家的生活图景似乎指日可待。但是,中国最广大的乡村甚至还没有告别“前现代”的生 活,在极个别的地区,由于土地征用、环境恶化等因素的制约,生存境况甚至比现代化 的承诺之前还要恶劣。因此在当代中国,一直存在着两种文化时间:一种是都市快速奔 涌的现代化时间;一种是乡村相对稳定和变化缓慢的传统时间。这两种文化时间在表面 上是城乡之间的差别,但就近期小说创作表达出的文化精神来说,却是“前现代”与“ 现代”的矛盾或冲突。或者说,乡村对现代化的渴求,具有历史的合目的性,但乡村在 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危机、矛盾,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整体危机和 矛盾。这与中国还没有完全蜕尽乡村传统的文化形态现状有关,当然更与文化传统延续 、接受和导致的文化统治有关。因此,当下小说创作所揭示、表现的问题,也就具有了 民族精神史和文化史的意义。
一、乡村身份和精神危机
在现代中国,对乡村的表达一开始就是犹疑和不确定的。比如在鲁迅那里,阿Q、华老栓、祥林嫂等农民形象,他们是愚昧、病态和麻木的,这些“前现代”的人物形象蕴涵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诉求。但是,在鲁迅的社戏、少年闰土等作品的表达中,乡村的质朴、悠远和诗意又跃然纸上,它几乎就是一首韵味无穷的古老歌谣;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乡村生活几乎就是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那里既粗俗又纯净,既寂寞静穆又趣味盎然;到赵树理那里,由于第一次塑造了中国乡村健康、生动的农民形象,乡村的神话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叙述中进一步得到放大。因此,对乡村中国的颂歌几乎就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曲。特别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叙述中,由于农村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对农民、乡村的歌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道德化的。因此,中国乡村文化的全部复杂性,在近一个世纪文学历史叙述中得到部分揭示的同时,却也显得扑朔迷离。而由于时代的变故,中国乡村文化的多样性越发显示出了多重的功能和可能。
乡村身份在革命话语中是一个可以夸耀的身份,这个身份由于遮蔽了鲁迅曾经批判的劣根性,而只是抽取了它质朴、勤劳以及与革命的天然、本质联系的一面。当代文学经典作品中的形象几乎都是农民或者农民出身的军人。知识分子阶层被排斥的主要依据也是因为他们和农民巨大的心理和情感距离。但是,接近现代社会之后,乡村身份遭遇了危机。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初期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试图在精神和情感急于迈进“现代”而遭到压制的话,那么,三十多年过后,1982年路遥的《人生》的发表则适时地反映了乡村进入现代的精神危机。但是,遗憾的是,由于路遥把同情完全偏移于乡村姑娘巧珍一边,对高加林走进“现代”的要求诉诸批判,并明确告知只有乡村乌托邦才能拯救高加林,使他的小说仍然流于传统而未能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小说和电影与读者、观众见面之后,社会舆论几乎众口一词地偏向了巧珍而斥责高加林。如果说那一时代的美学原则还含有鲜明的道德意味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在表现乡村文化的作品中,却明确地感知了乡村文化的真正危机。
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使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大量地涌进了中心城市,他们成了城市强体力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或其他行业的“淘金者”。但是,走进城市的只是农民的身体,事实上城市并没有也不可能在精神上彻底接受他们。城市因“现代”的优越在需要他们的同时,却又以鄙视的方式拒绝着他们。因此,走进城市的乡村文化是小心翼翼甚至是胆怯的。城市的排斥和乡村的胆怯构成了一个相反的精神向度:乡村文化在遭遇城市屏蔽的同时,那些乡村文化的负载者似乎也准备了随时的逃离。
刘庆邦在近期的小说中,格外关注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到城里去》和《神木》表达的都是农民在与“现代”关系的焦虑、困苦和绝望中的坚忍与挣扎。《到城里去》甚至成了一种战斗的姿态,城里仿佛就是农民改变命运惟一的归宿,是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惟一途径,但是这个途径是那样漫长和遥远;《神木》还是一群“走窑汉”, 是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新的世风,对离开土地的底层人同样有观 念和心理上的影响,作家在凄楚的故事中,令人惊心动魄地展示了人与人之间具有的时 代特征的关系的变化,同一阶层的关系、与老板的关系以及与欲望之间的关系,都被作 者不动声色地表达出来。但其间流淌的那种沉重和无奈,表达了作者对底层生活深切的 理解和同情。特别是十五岁的孩子走出“小姐”房间后的号啕哭声,尖锐地揭示了乡村 文化危机的不可避免。
青年小说家吴玄的《发廊》和《西地》也是表现乡村危机的小说。西地本来没有故事,它千百年来就像停滞的钟表一样,物理时间的变化在西地没有任何痕迹。西地的变化是通过一个具体的家庭的变故得到表达的。如果按照通俗小说的方法解读,《西地》就是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但吴玄要表达的并不只是“父亲”的风流史,他要揭示的是“父亲”的欲望与“现代”的关系。“父亲”本来就风流,西地的风俗历来如此,风流的不只“父亲”一个。但“父亲”的离婚以及他的变本加厉,却具有鲜明的“现代”色彩:他偷卖了家里被命名为“老虎”的那头牛,换回了一只标志现代生活或文明的 手表,于是他在西地女性那里便身价百倍,女性的艳羡也招致了男人的嫉妒或怨恨,但 “父亲”并没有因此受到打击。他在外面做生意带回来一个女人。“带回来”这个说法 非常有趣,也就是说,“父亲”见了世面,和“现代”生活有了接触之后,他才会把一 个具有现代生活符码意义的女人“带回”到西地。这个女人事实上和“父亲”相好过的 女教师林红具有相似性。林红是个“知青”,是城里来的女人。“父亲”喜欢她,虽然 林红和“父亲”只开花未结果。林红和李小芳这两件风流韵事,从一个方面表达了“父亲”对“现代”的深刻向往。“现代”和欲望的关系,在“父亲”这里是通过两个女性具体表达的,但最终“父亲”仍然与现代无缘而死在欲望无边的渴求中。这个悲剧性的故事在《发廊》中以另外一种形式重演。故事仍然与本土“西地”有关。妹妹方圆从西 地出发,到了哥哥生活的城市开发廊。“发廊”这个词在今天具有非常暖昧的含义,它 不仅是个美容理发的场所,同时它和色情似乎总有秘而不宣的关系。妹妹和妹夫一起开 发廊用诚实劳动谋生本无可非议,但故事的发展却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发廊因为可以赚 钱,他们就义无返顾地开发廊,当做了妓女可以更快地赚钱的时候,方圆居然认为没有 什么不好。贫困已经不只是一种生存状态,同时它也成了一种生存哲学。妹夫李培林死 了之后,方圆曾回过西地,但西地这个贫困之地已经不能再让方圆留连,她还是去了广 州,还是开发廊。城市对乡村文化来说虽然对立,但“现代”的巨大诱惑和对其不能遏 止的渴望,是乡村文化悲剧的双重引力。
2004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作家邵丽的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在读过了许多“官场小说”之后,再读邵丽的《我的生活质量》,我相信有过官场经历和官员身份的人,既可能心情舒畅也可能忧心忡忡。原因是,在过去的官场小说中,官场几乎就是人性的墓场:尔虞我诈、欺下瞒上、鱼肉百姓、贪污腐败,最后,或者亡命天涯或者苦海余生。这些小说在“反腐败”的主流话语或生活的浅表层面,确实获得了固若金汤的依据。但它的文学性始终受到怀疑,总让人感到文学力量的欠缺。这与这些小说对官场生活追问的不彻底,对人性深处缺乏把握的能力是大有关系的。我们在这些小说中看到的还只是官场奇观,或者是夸大了的畸形黑暗的生活。邵丽的小说《我的生活质量》,也描摹或书写了官场人生,但这不是一部仅仅展示腐败和黑暗的小说,不是对官场异化人性的仇恨书写。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部充满了同情和悲悯的小说,是一部对人的文化记忆、文化遗忘以及自我救赎的绝望的写真和证词。
小说的主角王祈隆,是一个传统的农家子弟,他在奶奶的教导下艰难地成长,终于读完大学,并在偶然的机遇中走上仕途。他并不刻意为官之道,却一路顺风地当上了市长。在这个为世俗社会羡慕的角色的背后,却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人生苦衷和内心的煎熬。他恶劣的生活质量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和心灵的。一个人的生活幸福与否,不是来自外在世界的评价,外在的评价只能部分地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和成就感。特别是一个人的虚荣心和成就感已经获得满足的时候,其他方面的欠缺就会强烈地凸现出来。王祈隆的生活质量之所以成为问题,就在于他已经实现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与未能忘记的文化记忆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王祈隆先后遇到了几个青年女性:旧情人黄小凤、妓女戴小桃、大学生李青苹和名门之后安妮。如果小说只写了王祈隆与前三个女人的关系,那只能是并无惊人之处的平平之作。王祈隆的欲望和对欲望的克制,与常见的文学人物的心理活动并没有本质区别,但邵丽的过人之处恰恰是她处理了王祈隆与安妮的情感过程。
王祈隆与安妮都是当下的“成功人士”、社会精英,按照一般理解,他们的结合是皆大欢喜、情理之中。但面对安妮的时候,王祈隆有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他脚上的“拐”——那个“小王庄出身”的标记,是他深入骨髓的自传性记忆。这个来自底层的卑微的徽记,即便是在他当上市长之后仍然难以遗忘,难以从心理上实现他的自我救赎。他 见到安妮就丧失了男性功能,而面对相同出身的许彩霞他就勇武无比。文化记忆的支配 性在王祈隆这里根深蒂固。哈布瓦奇在《论集体记忆中》区别了“历史记忆”和“自传 记忆”两个不同的范畴。他说:历史记忆是社会文化成员通过文字或其他记载来获得的 ,历史记忆必须通过公众活动,如庆典、节假日纪念等等才能得以保持新鲜;自传记忆 则是个人对于自己经历过的往事的回忆。公众场所的个人记忆也有助于维系人与人的关 系,如亲朋、婚姻、同学会、俱乐部关系,等等。无论是历史记忆还是自传记忆,记忆 都必须依赖某种集体处所和公众论坛,通过人与人的相互接触才能得以保存。记忆的公 众处所大至社会、宗教活动,小至家庭相处、朋友聚会,共同的活动使得记忆成为一种 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记忆所涉及的不只是回忆的“能力”,而且更是回忆的公众权利 和社会作用。不与他人相关的记忆是经不起时间销蚀的,而且,它无法被社会所保存, 更无法表现为一种有社会文化意义的集体行为。哈布瓦奇的集体记忆理论强调记忆的当 下性。在他看来,人们头脑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 。回忆永远是在回忆的对象成为过去之后。不同的时代、时期的人们不可能对同一段“过去”形成同样的想法。人们如何建构和叙述过去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 、利益和期待。回忆是为现刻的需要服务的(注:徐贲:《文化批评的记忆和遗忘》, 载《文化研究》第一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回忆”当然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和争夺的对象。在过去的历史叙事中,农民因在革命历史中的巨大作用,这个身份就具有了神圣和崇高的意味。但在当下的语境中,在革命终结的时代,农民可能意味着贫困、打工、不体面和没有尊严、失去土地或流离失所,它过去拥有的意义正在向负面转化。这样,农民——尤其是带有“小王庄”标记的农民,在王祈隆这里就成为一种卑微和耻辱的象征。面对安妮,这个具有优越的文化历史和资本的欲望对象的时候,王祈隆就彻底地崩溃了,他不能遗忘自己小王庄的出身和历史。这是王市长的失败,也是传统的乡村文化在当下语境中的危机和失败。因此王祈隆/安妮就成为传统/现代冲突的表意符号,他们的两败俱伤是意味深长的。
二、蛮荒之地的精神史
当代小说对乡村文化的重新发现和表达,肇始于“寻根文学”。韩少功、郑万隆、阿城、贾平凹、王安忆等作家对乡村文化的重新书写,使我们发现了乡村文化的另一种历史。作为一种文学潮流或运动,“寻根文学”似乎早已过去,但“寻根文学”留下的思想遗产却仍在乡村文化的不断书写中发挥着影响。
200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林白的长篇小说《万物花开》,这是林白为数不多的乡村题材的长篇小说。林白似乎是在飞翔中写作这部长篇的,她独行侠般地天马行空如影随形。《万物花开》与她此前的作品相比,是一部变化极大的作品。这里没有了《说吧,房间》的现实主义风格,也没有了《玻璃虫》亦真亦幻的写实加虚构。这是一部怪异甚至是荒诞、完全虚构的作品。小说的人物也由过去我们熟悉的古怪、神秘、歇斯底里、自怨自爱、也性感、也优雅、也困惑的女人变成了一个脑袋里长着五个瘤子的古怪 男孩。窗帘掩映的女性故事或只在私秘领域上映的风花雪月,在这里置换为一个愚顽、 奇观似的生活片段,像碎片一样拼贴成一幅古怪的画图。瘤子大头既是一个被述对象, 也是一个奇观的当事人和窥视者。王榨这个地方似乎是一个地老天荒的处所,在瘤子大 头不连贯的叙述中勉强模糊地呈现出来。我们逐渐接触到了那些只会说出人的本能要求 的各式人物,他们是杀猪的人,是制造土铳的人,是没有被命名的在荒芜中杂乱生长出 的人。这些人物在原初的生活场景中或是粗俗地打情骂俏,或是人与兽共舞。那些难以 理喻毫无意义的生活在他们那里兴致盎然地过着。人的最原初的要求在这里成为最高正 义甚至是神话,他们的语言、行为方式乃至兴奋的焦点无不与这个要求发生关联,它既 是出发点也是归宿。这个类似飞翔的写作,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没有一 条清晰可辨的情节线索,它留给我们的恰似散落一地不能收复的石玉相间的珠串。
有趣的是,小说附录有“妇女闲聊录”及“补遗”。这个“闲聊录”以“仿真”的形式记录了王榨发生的真实事件。所谓事件同样是一些琐屑得不能再琐屑的生活片段,同样是细微得不能再细微的日常符号,但在小说中却有了“互文”的作用:正文发生的一切,在“闲聊”中获得了印证,王榨的人原本就是这样生活的。在我看来,这是林白一次有意的艺术实验和冒险。她与众不同的艺术追求需要走出常规,需要再次挑战人们的想象力和艺术感受力。在这种挑战中她获得的是飞翔和独来独往的快感,是观赏万物花开的虚拟实践,她面对的是乡村古老或亘古不变的精神史,是具像的模糊表达形上真实的一次有效实践,它可能更需要艺术勇气和胆识。
张炜是书写大地的当代圣手,也是这个时代最后的理想主义作家。在他以往的作品中,乡村乌托邦一直是他挥之不去的精神宿地,对乡村的诗意想象一直是他持久固守的文学观念。“张炜的方式”一方面延续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粹主义传统,一方面也可理解为他对现代性的某种警觉和夸张的抵抗。但是,从《能不忆蜀葵》开始,张炜似乎离开了过去城市/乡村、理想/世俗僵硬的对立立场,而回到了文学的人本主义。
他的长篇小说《丑行或浪漫》,是一部典型的人本主义的本文:一个美丽丰饶的乡村女子刘蜜蜡,经历重重磨难,浪迹天涯,最终与青年时代的情人不期而遇。但这不是一个大团圆的故事。在刘蜜蜡漫长的逃离苦难的经历中,她以自己的身体揭开了“隐藏的历史”。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当然也包括张炜过去的部分小说,中国乡村和农民都被赋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乡村是纤尘不染的纯净之地,农民是淳朴善良的天然群体。这一叙事的合法性如上所述,其依据已经隐含在20世纪激进主义的历史叙事之中。但《丑行或浪漫》对张炜来说是一次空前的超越。尽管此前已有许多作品质疑或颠覆了民粹主义的立场,但张炜的贡献在于:他不再从一个既定的理念出发,不是执意赞美或背离过去的乡村乌托邦,而是着意于文学本体,使文学在最大的可能性上展示与人相关的性和情。于是,小说就有了刘蜜蜡、雷丁、铜娃和老刘懵;就有了伍爷大河马、老獾和小油矬父子、“高干女”等人。这些人物用“人民”、“农民”、“群众”等复数概念已经难以概括,这些复数概念对这不同的人物已经失去了阐释效力。他们同为农民,但在和刘蜜蜡的关系上,特别是在与刘蜜蜡的“身体”的关系上,产生了本质性的差异。因此,小说超越了阶级和身份的划分方式,在乡村文化对女性“身体”欲望的差异上,区分了人性的善与恶。在小说的内部结构上,它不仅以刘蜜蜡的身体叙事推动情节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敞开了乡村文化难以察觉的隐秘历史。特别是对小油矬父子、伍爷大河马等形象的塑造,显示了张炜对乡村文化的另一种读解。他们同样是乡村文化的产物,但他们因野蛮、愚昧、无知和残暴,却成了刘蜜蜡凶残的追杀者。他们的精神和思想状态,仍然停留于蛮荒时代,人的最本能又没有道德伦理制约的欲望,就是他们生存的全部依据和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张炜在这里并没有将刘蜜蜡塑造成一个东方圣母的形象,她不再是一个大地和母亲的载意符号,她只是一个善良、多情、美丽的乡村女人。她可以爱两个男人,也可以以施与的方式委身于一个破落的光棍汉。这时的张炜自然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已不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者。他在坚持无产阶级文学批判性的同时,不只是对城市和现代性进行批判,而首先批判的是农民自身存在并难以超越的劣根性和 因愚昧而与生俱来的人性“恶”。对人性内在问题的关注,对性与情连根拔起式的挖掘 ,显示了张炜理解乡村文化和创造文学所能达到的深度。
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刚一出版,在批评界就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他以狂想的方式在当代背景下书写了乡村另一种蛮荒的精神史。《受活》的故事几乎是荒诞不经的,它像一个传说,也像一个寓言,但它更是一段我们熟悉并且亲历的过去:故事的发生地受活庄,是一个由残疾人构成的偏远村落,村民虽然过着听天由命的日子,但浑然不觉其乐融融。女红军茅枝婆战场负伤掉队流落到这里后,在她的带领下,村民几乎经历了农村革命的全过程。但在“圆全人”的盘剥下,受活庄仍然一贫如洗。茅枝婆最后的愿望就是坚决要求退社。小说另一条线索是总把自己和政治伟人联系在一起的柳鹰雀副县长带领受活庄人脱贫的当代故事。苏联解体的消息,让他萌生了一个极富想象力的致富门路——从俄罗斯买回列宁遗体,在家乡建立列宁纪念堂,通过门票收入致富。为筹措“购列款”,柳县长组成了残疾人“绝术团”巡回演出……这虽然是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却会让人联想到汤因比对《伊里亚特》的评价:如果把它当作历史来读,故事充满了虚构,如果把它当作文学来读,那里却充满了历史。在汤因比看来,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也一定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阎连科是一个文学家,但他却用文学的方式反映或表现了那段荒诞历史的某个方面。如果从故事本身来说,它仿佛是虚拟的、想象的,但那些亦真亦幻、虚实相间的叙述,对表现那段历史来说,却达到了“神似”的 效果,它比真实的历史还要“真实”,比纪实性的写作更给人以震撼。
对历史的书写,就是对记忆的回望。那段历史在时间的意义上是“现代”的,但在精神史上,它仍然是蛮荒和荒诞的,对这段荒诞的历史,阎连科似乎深怀惊恐。不只阎连科,包括我们自己,置身历史中间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察觉历史的残酷性,我们甚至兴致盎然并且真诚地推动它的发展。但是,当历史已经成为陈迹,我们有能力对它做出反省和检讨的时候,它的严酷和惨烈的一面才有可能被呈现出来。当它被呈现出来的时候,惊恐就化为神奇。这个神奇是杰出的艺术表现才能所致。我们发现,在小说中阎连科汪洋恣肆书写无碍,但他奔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语言方式,并不是为了求得语言狂欢的效果,恰恰相反的是,那些俗语俚语神形兼具地成为尚未开蒙的偏远和愚昧的外壳,这个独特性是中国特殊性的一个表意形式。尤其是中国广大的农村,在融入现代的过程中,它不可能顺理成章畅行无阻。因此,《受活》在表达那段历史残酷性的同时,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中国进入“现代”的复杂性和曲折性。阎连科对历史的惊恐感显然不只是 来自历史的苦难,同时也隐含了他对中国社会发展复杂性和曲折性的体悟与认识。
当然,阎连科不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作为一个文学家,在表现那段历史的时候,他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为我们提供的东西还要多。“茅枝婆”、“柳县长”、“绝术团”、“购列款”,可能不会发生在真实的历史和生活中,但它就像这本书夸张的印制一样,让我们心照不宣地回到了历史记忆的深处,同时也认识了我们曾经亲历的历史。阎连科曾经写过《耙耧山脉》、《耙耧天歌》、《日光流年》、《坚硬如水》等优秀作品,他的苦难感和悲剧感在当下的文学创作格局中独树一帜。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受活》因对乡村蛮荒精神史的逼真再现,从而使他走进了中国当代杰出作家的行列。
三、抵抗现代的权力意志
现代文明的诞生也是等级社会衰败的开始。现代文明所强调和追求的是赫尔德所称的“本真性”理想,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独特的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尺度。自己内心发出的召唤要求自己按照这种方式生活,而不是模仿别人的生活。如果我不这样做,我的生活就会失去意义。这种生活实现了真正属于我的潜能,这种实现,也就是个人尊严的实现。但是,当乡村文化遭遇了现代文化之后,它因家族宗法制度和等级观念培育的“权力意志”并没有妥协和再造。因此,乡村文化和家族宗法制度中的权力意志就和“现代”构成了对峙甚至抵抗关系,在本质上它是反现代的。
上世纪末,作家李佩甫发表了长篇小说《羊的门》,这部作品的发表在批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部小说是对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传统乡村文化重构后,对当下中国社会和世道人心深切关注和透视的作品,它是乡土中国政治文化的生动画图。呼家堡独特的生活形式和一体化性质的秩序,使呼家堡成了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块“飞地”,它既实现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化的过程,使农民过上了均等富庶的生活,又严格地区别于具有支配性和引导性的红尘滚滚的都市文明,它是一片“净土”,是尚未遭到现代文明浸染的“世外桃源”。从消灭剥削、不平等的物质形式来说,那里已经完成了解放的政治;但从权力与资源分配的差异性来说,从参与机会与民主状况来说,又没有从传统和习俗的僵化生活中解脱出来。它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它的井然有序是文 明的,而那里只有一个头脑,表明了它又是前现代的。呼家堡就是这样一个复杂、奇特 的不明之物,它是传统和社会生活遭遇了现代性之后,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生活 场景。但它的非寓言性显然又表达了作者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某种理解和洞察。
呼家堡的主人呼天成,是一个神秘的、神通广大和无所不能的人物,是一个隐于野又呼风唤雨式的人物。在社会生活结构中,他的公开和合法性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但他的作用又很像旧式中国的“乡绅”,他是呼家堡联系外部社会和地方统治的桥梁,但他又不是一个“乡绅”,呼家堡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是呼家堡的“主”,是合法化的当家人,是这块土地不能缺少的脊梁和灵魂,他所建立起来的权威为呼家堡的民众深深折服,他对秩序和理性的尊崇,使他个人的统治也绝对不容挑战和怀疑。呼家堡的生活方式是呼天成缔造的,在缔造呼家堡生活方式的同时,呼天成也完成了个人性格的塑造。这个复杂的、既有乡村传统、又有现代文明特征的中原农民形象,是小说取得的最大成就。
事实上,呼天成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特别是政治文化影响的产物,因此他是一个矛盾的复杂体。乡村文化在民间有隐形的流传,它不是系统的理论,它是在生活方式和人们的心理结构中得以表达的,其中实用理性、随机应变等文化品格在民间如影随形,呼天成的性格基调就是由这种文化品格培育出来的。它的土壤就是中原文化/乡村文化中盲从、愚昧、依附以及对私有利益的倚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原文化也就是中国乡村农民文化。呼天成的王朝统治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的。它的经典场景就是用一“贼”字对几百口人的震慑:
一个“贼”字使他们的面部全部颤动起来。一个“贼”字使他们的眼睛里全都蒙上了 一层畏惧。一个“贼”字使他们的头像大麦一样一个个勾下去了。一个“贼”字就使他 们互相偷眼望去,相互之间也突然产生了防范。那一层一层、看上去很坚硬的人脸在一 刹那间碎了,碎成了一种很散很无力的东西……
这个场景启示了呼天成,他对书上说的“人民”有了新的理解,也启发了他统治呼家 堡的策略,通过向孙布袋“借脸”、通过开“斗私”大会让妇女“举手”等政治行为, 呼家堡民众的尊严感、自主性、自信心就完全被剥夺了,呼天成不容挑战的权威也就在 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呼天成不是我们在一些作品中常见的腐败的村干 部,也不是横行乡里的恶霸,而恰恰是一个修身克己、以身作则的形象。他不仅在一个 欲望无边的时代,将激情逐出了“私化”领域,以自我阉割和超凡的毅力克制了他对秀 丫的占有,而且即便是他的亲娘,也不能改变他“地下新村”的统一安排,一个命定的 数字就是他亲娘的归宿。究竟是什么塑造了呼天成的“金刚不坏之身”?或者说我们究 竟应该如何评价呼天成“公”的观念、集体信仰和他的道德形象以及民众对他的信任亦 恐惧?在呼天成那里,他拥有的权力使他可以视统治对象为“贱民”,他在权力和“贱 民”的镜像关系中获得了统治的自信。这种权力意志使他难以走向以民主为表征的现代 而止步于遥远的乡村文化传统。
董立勃《白豆》的人物和故事,也许并不是发生在典型的乡村中国,但边陲军垦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中国乡村文化的另一种延伸和接续。那里的等级、权力关系是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白豆》的场景是在空旷贫瘠的“下野地”,人物是农工和被干部挑了几遍剩下的年轻女人。男人粗陋女人平常,精神和物质一无所有是“下野地”人的普遍特征,一如我们常见的乡村经典场景。主人公白豆因为不出众、不漂亮,便宿命般地被安排在这个群体中。男女比例失调,不出众的白豆也有追逐者。白豆的命运就在追逐者的搏斗中一波三折。值得注意的是,白豆在个人婚恋过程中,始终是个被动者,一方面与她的经历、出身、文化背景有关,一方面与男性强势力量的控制有关。白豆的自主要求,是在她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男人之后才觉醒的。但是,白豆的婚恋和恋人胡铁的悲剧,始终处在一种权力关系之中:吴大姐虽然是个媒妁角色,但她总是以“组织”的名义给年轻女性以胁迫和压力,她以最简单,也是最不负责任的方式处理了白豆和胡铁、杨来顺的关系。马营长死了老婆,马营长看上了白豆,就意味着白豆必须嫁给他。但当白豆遭到“匿名”的强暴之后,他就可以不再娶白豆而娶了另一个女性。
胡铁不是白豆的强暴者,但当他找到了真正的强暴者杨来顺之后,本来可以洗清冤屈还以清白,但一只眼的罗“首长”却宣布了他的新罪名。在《白豆》里,权力/支配关系是决定人物命运的本质关系。但是,如果把白豆、胡铁的悲剧仅仅理解为权力/支配关系是不够的。事实上,民间暴力是权力的合谋者。如果没有杨来顺图谋已久的“匿名”强奸,如果没有杨来顺欲擒故纵富于心计的阴谋,白豆和胡铁的悲剧同样不能发生, 或者不至于这样惨烈。因此,在《白豆》的故事里,权力和暴力,是人性的万恶之源。 在乡村文化的结构里蕴涵着权力意志和权力崇拜:“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 而优则仕”才是真正的目的。入朝做官“兼善天下”不仅是读书人的价值目标,而且也 是人生的最高目标。要兼善天下就要拥有权力。对于更多的不能兼善天下和入朝做官的 人来说,权力崇拜或者说权力畏惧,就是一种没有被言说的文化心理。这种政治文化是 一个事物的两面,它们之间的关系越是紧张,表达出的问题就越是严重。
在迈向“现代”的过程中,经过“祛魅”之后,乡村文化蕴涵的历史多重性再次被开掘出来。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机器隆隆的轰鸣打破了乡村的宁静,乡村文化对现代文明还怀有羡慕、憧憬和期待,乡村文化与现代的冲突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以后,有声和无声的现代“入侵”和诱惑,则使乡村文化遭遇了不曾料想的危机和困境。但是就在乡村文化风雨飘摇的时代,重返自然却成为“现代”新的意识形态。那么,在追随“现代”的过程中,乡村文化的永远滞后就是难以逃脱的宿命吗?这显然是我们尚未明了的文化困惑。
标签:张炜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我的生活质量论文; 读书论文; 受活论文; 阎连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