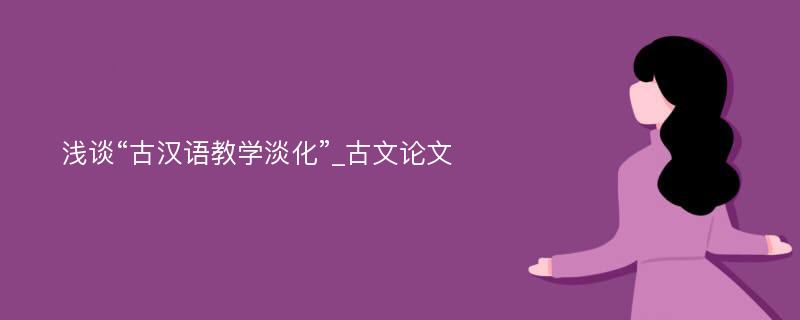
“淡化文言文教学”大家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言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段崇轩(文学评论家,陕西省作协副主席):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是用文言文的形式记载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借鉴国外优秀文化,这是做人的根本。五四时期那一代人的学习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那时候人们很重视学习四书五经。鲁迅和胡适等人小时候都对文言文不感兴趣,但如果没有少年时代艰苦的学习经历,没有那段时间的知识积累,也就没有他们后来的成就。对于世界文化的优秀遗产,中学时期如果不读的话,可能一生都不会再去读了,这对人生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丁帆(著名学者,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对于古典文学的教育,我们还是有一致共识的,认为古典文学和古汉语知识,那是中国文学和中国语言的立足之本,这个“本”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不了解汉语的发展过程,不了解古典文学的博大精深、浩如烟海的话,那么你对语文的掌握就不可能是一个高层次上的掌握,只能说是低层次的。所以凡是语文课标里要求的篇目我们全部都上,同时也换了一批选文选目。现在苏教版这些选文和人教版不同的是,我们采取的注释全部按照权威版本,全部重注一遍,所以古典文学这一块我们还是费了很大气力来搞的。除了规定的篇目,就是新课标里提到的篇目以外,我们还考虑了一些别的。古典文学占多少,外国文学占多少,现代文学占多少,各个层面的分析都有,总之就是一个分析报告。处理现代文和古代文,处理母语课文和外来翻译课文等问题,我们都做了认真的考虑,我们选的基本上是考虑到人文思想的经典性。
何永康(著名文学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言文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珍宝,最典型的有《古文观止》,还有古代散文、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这是母语写作作品中的最高点,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怎么能不用呢?很简单,背诵,从小学开始背诵,他不一定懂,但背得越多越好,先不要讲,背了之后,他慢慢就懂了。如果一个人没有古文素养,他的素质永远提不上来。什么是文言之分?什么叫粗细之分?什么叫高下之分?这是很关键的。当然现在花样很多,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一百首古诗、一百首古词、五十篇好的古代散文的学识储备,这个人肯定是不行的。现在有些人想把文言文取消是荒唐的,是他不懂古文。现在为什么一些人是草包,素质差,不上档次,就是因为肚子里缺少古文素养。一次我到镇江北崮山去旅游,一个企业家觉得没有什么好看的,但在那里有一个中学生,他对着风景就有感而发地吟诗,他这个人马上就显得不一样了。包括出去旅游,有诗文素养和没有诗文素养的他就是不一样。一百首古诗,一百首古词,五十篇好的古代散文,不管你懂不懂,从小学就开始背,背好了,长大以后,肯定就高人一筹,中国味道就出来了,就知书达理了,文言里面他就文了,粗细里面他就细了,高下里面他就高了,很自然的,所以不能取消。
很多政府官员,一些资深理论教育家弄错了,搞得不全面,他们有时候应该问问其他人,有时旁观者清。比如问问我们这些不搞教学理论的人,可能会有一些好的帮助。有些错误的理论是他们搞教学理论的提的,不是我们提的,有些人挖空心思地找些话,因为他要写文章、评职称,可能会写一些不负责任的话。但我们要为语文教学负责,为中国的下一代负责,为中国人的语文素养负责,还语文以自然的面貌。
鲁国尧(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言文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载体,学习文言文不只是为了了解几个字词、阅读几篇古文,更重要的是对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借鉴。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次我从南京坐火车去厦门大学,旅途上经历的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火车车厢里有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跟我聊天,他是一个做木材生意的台湾商人,闲谈中,他说话一会儿引用《论语》里的几个句子,一会儿又引用《孟子》中的一段话,而且能脱口而出,我感到很惊讶。我问他:“你对《论语》和《孟子》怎么这么熟悉呀?”他说,“这有什么,我们在中学课文里都学了,我们都背得滚瓜烂熟。”可见,台湾的中学教育是很注重文言文教学的。我又问他上过大学没有,他说:“我不想上大学,高中毕业之后就去做生意了。”他的文化程度不是很高,年龄也不大,但是对传统文化掌握得却比较好。学习传统文化里面的文言文,尤其是学习古诗词,对人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国大陆在这方面做的与台湾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里的精华是应该加以继承的。从小学、中学开始就应该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林焘(北京大学教授):文言文教学有传承文化的作用,不能把文言文看成纯粹的语言教育。它的重要性比过去的政治课还重要,它是影响整个学生思想的一门课程。我觉得文言文非但不应该减少,而且还应该增加。文言文是现代汉语发展演变的根基,我们现在之所以没有把传统文化割裂,也就仗着过去这些好的文言文,但有些学校和家长提倡甚至硬性要求小孩背诵大量古文,就有些过分了。要想把语文教育搞好,不重视文言文教学是不行的。没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就谈不上对新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如果语文教学把文言文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人文教育肯定是失败的,因为它把我们的文化割断了。现代白话文确实有许多有价值的文章,可是语文课本选的当代作品,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作品有多少能经得起检验?而李白、杜甫的诗歌,韩愈、柳宗元的散文,曹雪芹、蒲松龄的小说……这些文学史上的珠宝千百年来熠熠生辉。语文教材要精选经典篇章,语文教学应拒绝快餐文化,不能急功近利。
裴显生(南京大学教授):我不提倡学生写文言文,但我认为不但不能淡化,还有必要适当的加强,什么原因呢?我看到我们的古文功底越来越差了,普通话、现代话因为要讲,淡化不了,文言文却不是这样。像过去那些修养好的人,读过很多文言文的经典著作,一种是“五经”之类的经典著作,一种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小说,两种交叉在一起,文学素养就相当可观了。如果文言文教学削弱了,第一,会降低语文素质;第二,文言文素养差,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理解不了,对精华不了解,就无法弘扬文化传统。实际上读文言文并不影响现代汉语的运用。有人认为文言文读多了,现代汉语就不行了,实际上文言文读得多的人,现代汉语也好。现在我们的下一代把传统的东西都丢掉了,古文不读了,那不行,素养差了。所以我不主张削弱文言文。我们学语文并不全是从课本上学来的。我小时候读《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三侠五义》,统统是文言小说,看了觉得有趣,被迷进去,慢慢文章就会写了。我们应该坚持把文言文教学抓好,让大家体会到文言文的美。文言文确实很简练,内涵很丰富,文字很美,真正进去,受益无穷。
饶杰腾(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是不是增加文言文的比重就是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我以为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文言文没有必要增加这么多,我主张少学但是不能不学。学习的内容应该是到现在尚有生命力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文言文教学应弄清:学习目的是什么;学习的内容如何服务于这个目的;通过什么科学的教学方法在极有限的时间内达到目标。文言文的学习有利于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但这不是唯一的途径。而且文言文也是一把双刃剑,有的里边也掺有历史糟粕。
王宁(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我比较赞成读文言文,我觉得文言文要从初中开始读,因为语言的记忆高峰一般是在十岁到十四岁,这段时间很容易把一些语言的东西记住,虽然内容不一定懂,但不懂也没关系,可以先储存起来。应该说小时候读的东西我们现在记得非常清楚,到了高中读的东西印象就不是很深。中国的文言文对白话文的影响是很难割断的,因为中国历代不管口语怎么发展它的书面语是不变的,清朝蒲松龄的时代还在使用《史记》和《左传》的语言。对于历代的语言当时的口语都是横向影响,不是从先秦隔代传下来的。应该说我们现代汉语的语素基本上是在古代就已经成熟了;现代汉语的语法基本上是从古代发展下来的,变化也并不是很大。另外关于表达方式的很多精华还要从文言里面去学。所以我觉得对文言文阅读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读文言文的人被搞得很复古,脱离时代,离现实越来越远;另外一种就是真正地去读文言文来充实我们的现代汉语,使得文言文教学跟我们现在的白话教学结合起来。现代汉语的词汇没有文言文的基础是很难理解的,反过来说,如果借助于现代汉语来学习古代汉语,那么古代汉语也会比较容易学。
现在文言文教学有两种教法我是不太赞成的。一种是像学古汉语文选似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掰碎了,揉碎了,把它搞成古汉语去教学;还有一种就是拿了篇文章来,文章还没有看明白呢,就开始总结思想、分析形象。文言文阅读应该能够把一些东西读通,读得很顺畅,学生自己去感受。无论读文言文还是读白话文,在做文学形象的鉴赏时,就提高语文能力来讲,道理是一样的。不能把文言文当成外语来学,文言文毕竟是不同时代的汉语。另外也不能把文言文当成白话文阅读,因为毕竟它有语言障碍。所以教学文言文应该抓住一些跟主旨非常相关的东西,拿来做一些重点的解剖。尤其是阅读诗词,一定要从语言里出形象,不从语言里出形象,别人是没法把握的。初中语文教材中,文言文可以占50%的比例,高中就不一定把文言文和现代文那么截然分开了。高中文言文散文可以放在散文里面去教;文言文诗歌可以放在诗歌里面去教。高中的文言文主要是进行语文思维教育的,而不是去解决教学的问题,它主要是注音的问题,就是对一些生字难字的注音问题,这时必须要转到以汉字为中心而不是以拼音为中心。这有个转化过程。但是在一开始,拼音是很有用的,它把小孩子的汉字观念、字的概念,通过跟他的口语结合,这样他才会识字。什么是识字?识字就是把拼音跟口语结合起来,所以在初期的时候最有用的时候淡化了拼音,不是个聪明办法。
但是,我反对文言文写作,不能去推崇它,因为文言文毕竟还是跟口语不一致的。我们学习文言文是一种间接的借鉴,并不需要拿文言文当工具用。我也反对现在儿童读经,因为它带有复古性质。我们可以提倡读优秀的文言文,因为文言文是有文化底蕴的,但是如果现在还去使用文言文,我觉得就是复古得有点太离谱了。
温儒敏(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淡化文言文教学是脱离语文学习规律的。要学生学一些文言文主要是让他们对文化的根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对汉语有一个语感上的了解。所以有必要学习一些文言文,而且数量不能太少,这对他一生都是有好处的,这也是实践证明了的。文言文教学要占多少比重,需专家进行研究。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争论,主要因为我们缺少一种量化的社会调查,跟经济学似的,通过技术性的研究,调查不同类型的人对文言文的需求程度,以此来确定一个大致的要求。现在语文学界发表的文章很多,但都是经验性的,真正上升到研究层面的不多。只有做这种模式研究和调查,得出的结论才是有说服力的。
王希杰(著名语言学家,南京大学教授):我觉得文言文教学不能淡化。长期以来,我国港澳台地区非常重视传统文化、重视文言文教学,如果我们大陆地区一味地淡化文言文教学,淡化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教育,将不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也不利于民族的发展。如果忽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就谈不上民族文化的创新。众所周知,中文系学生只占大学生的少数,大学理工科学生基本上不学传统文化,一些理工科的知识分子、人才精英对传统文化懂得很少,从这个意义上讲,绝大多数社会民众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是在中学阶段,如果中学阶段淡化文言文教学将会导致教育的失误和人才综合素质的缺憾。
20世纪50年代的大中学校学生接受的人文教育比较全面,学校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很重视。从历史上看,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那是偏激的表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五四时期的许多问题都进行了反思,唯独在语言文字学习方面、在语文教育方面对五四时期的形而上学思想没有进行反思。文言文有几千年的历史,有优美的语言形式、有丰富的思想内容,现代白话文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不从文言文中吸收营养,白话文是没有发展前途的。现在随着文化交流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随着全民族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通过文言文学习来提高现代汉语水平是很有必要的。五四运动的一大功劳是把白话文作为书面语正式推广使用,但作为书面语的白话文,如何适应现代社会大众化的需要,这个问题我认为尚未完全解决。所以现代汉语书面语一定要积极吸收口语词汇,同时要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吸收营养。有的学者反对“不文不白,文白掺杂”,我却认为在特定的场合下,“不文不白”和“文白夹杂”是有必要的。金庸的小说语言是文白夹杂的,喜欢金庸文章的读者不但被作品的内容所吸引而且也被作者的优美语言所感染。金庸是华人写作的成功者,它对华人世界的影响是很大的。
谢冕(著名批评家,诗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我觉得这种观点有些偏颇,不能因为当代性、现代性或者时代性就忽视文言文。我相信说这些话的朋友,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学、古代文章也是阅读的。而我的人生经验也告诉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绝对不应该隔断中国文化、特别是优秀的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这是我们中国人引以自豪的、非常宝贵的历史财产,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并且古人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如此高超,我们后代子孙是自叹不如的,所以我不主张淡化,我觉得还应该非常重视它。有一些课本绝对排斥、断然排斥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字,这不是误人子弟吗?当然我也反对“唯古是尊”,一味认为古人的最好,那也不对,毕竟我们从新文学革命以后,新的文学出现了,用白话写作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杰出的乃至于伟大的作品和作家,它是另外一个方面的成就,所以也不该忽视。我不提倡以现代为主,也不提倡以古代为主,我希望得到一种综合的、合理的教学配制。
叶兆言(著名作家):这些人的看法总的来说有一定道理。如果连现代汉语都没掌握好,过多地考虑古文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无论是教现代汉语还是教文言文,让学生读写文言文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学生读好现代文,写好现代文,这应该是一个大前提。这中间的比例应该是非常恰当的、中和的,不能为了满足一部分人——比如有一部分人喜欢古文,这些人可以自己去读,他们以后可以去读中文系,甚至进行古汉语研究——而把中学语文教学就定位在他们身上。中学语文教学应该定位在所有中学生的身上,因为中学教育是普及型教育,如果普及教育中有太多文言文,我认为不合适,专家应该研究出一个恰当的比例。让年龄还小的初中学生读四书五经,我觉得有点过分。我也不赞成学生用文言文写作,因为已经到了今天这样的时代,我们应该用生动的、新鲜的、活泼的现代汉语写作,这是一个基本方向。至于说有人喜欢这么写,那是他的自由,在创作自由的前提下没有理由去反对,但从我个人来说,我不赞成文言文写作。
张伯伟(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当然反对。教材里所选入的都是名著名篇,这些名著名篇凝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即便仅仅从身为一名中国人来讲,了解本国的传统文化也是相当重要的。第二,现代语言也是从古典语言发展来的,一些成语仍然存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不去接触古典文献,那现实语言也就失去了根,不可能得到良性的发展。昨天我在中华书局的一位朋友那里还谈起,说应当要扫古文的盲,扫繁体字的盲。现在我们固然可以把古文译成现代汉语,用简化字来书写,但这样长久下去,人们都只会阅读现代汉语了,古籍又靠谁来研究、翻译呢?我们全民的古文阅读能力在下降,难道以后我们还要到韩国这些周边国家去留学我们的古典?这种情况已经是存在的了,日本人说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在日本,这让中国学者听起来还是很有刺激的,我们应该感到羞耻。同样,有一天如果说汉语在中国而汉学在日本,那我们又应当作何想,该如何汗颜与羞愧呢?中学教材里文言文本来就不多,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淡化那几乎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不合适。原来的选文有一个比例,维持那个比例就可以了,有的人中学以后可能一辈子也就不再会接触古典文学了。就像一个学理工的学生到外国去,听别人讲到中国古典的一个诗人都莫名其妙、不知道,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应该会很羞愧的。
赵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当前中学语文教材分成必读教材和参考材料,这种编法还是合适的。我认为必读教材在选文方面应该更精一些,应更多地听一听孩子们的意见,听一听儿童文学作者的意见。加重文言文的分量是一件好事。学生在中学阶段具备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将来即便学理工科也是非常有益的。通过阅读文言文可以较早地接触到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能有一个更加广阔的阅读面,有可能进入更大的文学世界。因为白话文阅读不会有太大的困难,而文言文的阅读现在越来越成为一种特殊的能力。另外,现当代文学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占30%的比例就可以了,因为还要有20%留给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可选择的余地很大,应该尽可能地让学生多学习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现代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是有定评的,在必修教材中应该多一些。当代文学作品在选修教材里应多一些。
周正逵(语文教育专家):对于中国人来说,学语文的捷径是加强文言学习。文言文和现代文有内在的联系,现代文是由文言文发展过来的。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历史记载的材料大部分是用文言写下来的,要继承中国古代的文化,要从古代文化当中吸收营养。没有具备必要的文言阅读能力就等于是文盲或者是半文盲。学好文言文是学好现代文的必要条件,学文言文是提高作文水平的必要途径。过去鲁迅反对学文言文是限于当时的政治背景。现在许多学生甚至一些作家文言功底太差,作品写得多了,一年可以写几百万字的作品,但是从语言上来看,都不是传世之作,是应景的消遣性作品。真正的大作家古文功底深厚,写现代文也得心应手。有人曾经说农民作家赵树理没有读过文言文,翻一翻赵树理的传记可以知道,赵树理是私塾出身,文言文底子很好。他把文言里的一些精华吸收了,又融合民间语言,写出了深受老百姓欢迎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