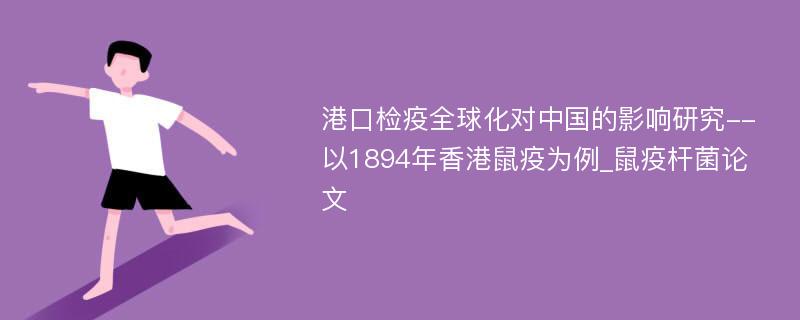
海港检疫全球化对华影响之研究——以1894年香港鼠疫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鼠疫论文,香港论文,为例论文,海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西方殖民扩展,人与物的流动日趋全球化,疾病成为此种潮流的附属品,亦开始全球范围的传播。西方殖民帝国不得不建立起保护网络,预防传染性疾病的蔓延。对欧美诸国来讲,这不仅仅意味着对抗疾病,保卫健康,而且意味着巩固帝国或政府统治,尤其重要的是在殖民地展现出他们控制疾病传播的能力,进而巩固欧洲文明的声望与信誉。19世纪中期,随着霍乱、鼠疫等疫情的扩散,海港检疫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来。其目的并非建立起全球卫生治理,而是旨在构建一种既可保护欧洲免受瘟疫侵袭又不影响贸易和扩张的保护网。中国自被动打开国门,海外贸易日增,大批劳动力前往美国、澳大利亚及南洋各国谋生,也被卷入海港检疫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按照各国惯例,清政府将海港检疫设定为一项海关业务,交由海关税务司处理。学界极少关注作为全球化产物的海港检疫是否对中国地方政府及社会防疫方式产生影响的问题。事实上,19世纪末,海港检疫在中国已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由于缺乏港口所在地中国官府和人民对检疫隔离方式的认同,仅靠医官和海关的力量,无法有效地控制疫情的蔓延。另一方面,海港检疫本身已无力对抗全球性疫情,必须基于医学文化共识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地方卫生治理,才能保证疫情得到有效的防控。1894年香港鼠疫期间①,香港、广州和上海三座港口城市颇受影响,本文拟通过比较三地如何应对鼠疫来袭,分析出海港检疫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及其遇到的困难。这三个城市颇具代表性,一个是殖民政府管理,一是中国政府管理,一个是兼有租界和中国政府管理,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出不同的影响方式。 一 海港检疫全球化 海港检疫始自15世纪欧洲对抗鼠疫的经历,后随着帝国殖民扩张推行到全球,其背后有一套西方医学文化理念。在基督教传统中,鼠疫是一种惩罚,不应被视作必然的,因为罪恶应当被确认和根除。因此,基督徒的态度倾向于人们采取下列行为:必须寻找替罪羊,给病人定罪,尤其是他们如果是穷人或不体面的人,而且要根除威胁身心健康的环境,例如大规模无序的公共聚会,或难控制的小旅馆、酒馆和肮脏的贫民窟。②瘟疫的可根除性成为西方各国发展海港检疫和公共卫生的基石。 15世纪以来,欧洲形成了一种长期有效的防疫措施,给船只发放健康证和建立隔离所。到17世纪,南欧的各港口互相合作监督来自黎凡特(时常是新疫情的来源地)的可疑船只。1720年,由于马赛未采取这些措施,结果导致一场严重瘟疫。西北欧各国开始关注防疫,政府监视来自被传染的地中海港口的船只,将它们隔离开,或拒绝它们进港。海港检疫措施控制商业和流动性,无论有效与否,使国家权力的扩张成为必须更多介入市政事务,更多文件、更多官员来收集信息和执行新的规则。③ 1825年,海港检疫隔离法案通过,适用于“鼠疫、黄热病、其他传染病、大瘟热等严重威胁人们健康的疾病”的船只。在港口执行这一法案的机构是海关。在船只离港或到港时,由政府发给一份健康证书(Bill of health),有三种形式:一是“干净”(Clean),表示完全没有传染病症;二是“疑似”(Suspected),表示有可能与传染病症接触过或来自“有疫”港口;三是“污染”(Foul),确定有传染病症。因此,隔离不仅适用于发现疾病的船只,而且适用于确信与疫病接触过的船只。由于海洋隔离法案扣留和隔离船只的理由在病人和健康者之间、在已有病情与疑似病情之间缺乏明确的区别,使两者都感到害怕与愤恨。害怕来自于健康的乘客被禁锢在船上与染疫病人待在一起;愤恨来自于船只被延误所带来的昂贵的贸易损失。再加之,海港检疫无力防止疫病扩散,且明显干扰海洋贸易,实际上在整个19世纪都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反对和质疑。19世纪早期,海港检疫隔离被视作英国海洋贸易的拦路石:给旅行增加了超过30天日程,不仅可能耽误另一次航行,而且易腐烂的货物若不毁掉的话可能烂掉,招致支付非常昂贵的隔离费用。海港检疫隔离政策的花费昂贵,且与英国自由主义信条冲突。因此,海港检疫隔离被人们指责为“野蛮的负担、干扰商业、妨碍国际交往、威胁生活以及浪费大量公帑”。④ 海港检疫隔离实际还是交织着诸多矛盾和斗争的公共卫生措施。澳大利亚政府用其作为阻止移民进入的策略。1881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命令对来自中国的所有船只进行隔离。同年,南威尔士政府提出对被认为搭载中国人的船只采取选择性隔离措施。梅恩研究认为,澳大利亚的隔离措施受到种族歧视的影响,成为一项重要的移民控制工具。⑤悉尼鼠疫防控的历史显示,“贸易利益团体、州政府和英联邦之间在卫生事务的竞争与互动使公共卫生成为一项困难的事业”。⑥此外,由于印度港口的巨大贸易利益,印度政府更多考虑经济利益,抵制英国要求对前往麦加朝拜的穆斯林进行隔离。孟买的公共卫生政策发展出一种复杂的网络,交织着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殖民当局与宗主国、殖民政府与当地人之间的时而冲突时而重合的利益关系。⑦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蒸汽轮船和铁路交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世界的联系。在这种背景下,瘟疫的传播亦相应地更加便利。欧洲各国因此发展出在卫生领域的国际主义,自1851开始就防治霍乱的传播召开了八次国际卫生大会,旨在建立起明确的边界。科学因此成为一种潜在的政治工具,既作为民族主义竞争的工具,也作为控制新危险的手段。最终国际卫生会议的代表促使世界各地越走越近,在“文明欧洲”和“东方”之间的文化鸿沟有了新的内涵。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新的脆弱性的经历遇到了新的边界模式以及偏离隔离和公共卫生警戒线等概念的边界保护的挑战。代表们设计的既不是一个无边界的世界,也不是完全边界的世界,而是一种即可保护欧洲又不会影响贸易和扩张的半透性的网络。他们的概念严重依赖于西方现代性,如国际主义、信息技术、现代科学以及现代行政机构的识别和分类设置。⑧这种现象正如学者们揭示的那样,海港检疫实际上代表的是以对抗疾病(Against Disease)的全球联合取代通过疾病(By Disease)的全球联合。⑨ 海港检疫受到诸多质疑,但并未停止其全球化的步伐,到19世纪末已经为世界大多数海港所接受。与此同时,热带医学发展出与帝国国内一致的卫生行政模式,是对海港检疫单调性的重要补充。在欧洲帝国的政治、军事和商业扩张过程中,医学不仅是帝国的“工具”,而且是欧洲殖民地的一种实践形式。无论是在热带还是在亚热带,医学使得欧洲人征服了世界遥远的角落,并在特定地方待下来。在热带,医学思想和实践往往源自军事占领和管理的需要;疾病控制的模式一直受到热带和地区特殊疾病的限制。但是,传播性疾病迫使帝国建立起更加系统的卫生和医学服务,殖民医学服务迫使“卫生秩序”成为他们保持的政治秩序之一。帝国主义需要运行一系列的技能和规则。殖民医学最初服务于帝国军事、政治和贸易利益,只在很低程度上满足当地人的需要。当医学服务成为一项政府永久性职能,殖民医学向宗主国寻求权威、训练和认可。在更温和地区,英联邦的白人地区帝国医学很快需要自己的殖民动力。⑩可以说,在海港检疫全球化的同时,西方开始了卫生治理的全球化预备工作,并已在若干殖民地开始试行,香港便是其中之一。 简言之,海港检疫全球化是为了保护帝国及殖民地侨民的免受疾病的影响,带有非常浓郁的帝国色彩,是备受质疑的一项防疫措施,且在执行中受到多方利益博弈的影响。虽得到国家强制力保障,成为世界主要港口普遍采纳的防疫措施,但在港口城市的卫生状况未改善的背景下,其局限性越来越凸显出来。仅仅依靠海港检疫对于对抗疾病来讲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起一套地方卫生体系,方能防止疫病的流行。1894年的香港鼠疫,香港、广州和上海的状况彰显了此种趋势,仅仅迫使东方社会接受海港检疫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促使它接受这套制度背后的文化认知,解决好嵌入性问题,方可有效对抗瘟疫。 二 海港检疫在中国 对中国来讲,海港检疫是帝国主义各国强加的一项海关业务。瘟疫一直被视作上天的惩罚,“凡疫疠之作,其起也无端,其止也亦无端,大抵天意使然”,故往往求神拜佛,打醮修斋或请神出巡游。反而对各种清洁措施,“断不计及,或通沟渠或除积秽,或浚井泉,或理河道,种种实在之事,视之绝不经心,惟祝上天之沛然下雨,殷然作雷,以除此一时之顽疾”(11)。 同治十二年(1873),因暹罗及马来半岛霍乱流行。外国领事要求中国实行海港检疫,清政府则完全交给海关办理。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有二:一是主权问题;二是经费问题。由于受条约限制,管理外国人船只颇为棘手,“许外人以领事裁判权,凡于处理外侨事务,诸多掣肘。非惟外侨之财产,即其寄港船只,亦享有领事裁判权,故登轮检验,处理染疫船只,及拘留隔离患病者等事,亦难于施行也”。此外,设立海港检疫机构及医院,施行隔离措施,需款甚巨,不易筹措,因此“入港船只之发现疫病者,均由轮船公司自行处理,我国政府向不与闻”。(12)这样,最初遇到洋人提出的海港检疫要求时,清政府基于上述两个原因,采取建立防护墙的策略,将检疫事务交给海关税务司负责,政府既免去了与外国就行使检疫权的交涉,也避免了外国借口检疫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结果,海关聘用医官专门负责海港检疫,地方政府与这套制度之间基本没有任何联系。 1862年,江海关税务司拟定检疫章程,呈请政府批准,并得各国驻华外交使团同意,公布施行,由海关延聘医官,办理检疫事务。翌年,复拟定较为详细章程,经领事团同意,由海关道公布施行。需检疫时,由海关当局与领事团随时商酌施行。伍连德对此描述道:“吾国海口检疫权,素归海关包办,以外人利益关系,只聘任在市悬壶之洋医,主持此重责,任其自有处断,使吾国海口检疫,不由自主。一切裁判办法,统由领事、税务司及洋医全权办理。吾国内地,发见传染症行时,彼则诸方取缔。除防范外延,或借口办理不善,故意阻拦,以致疫气常因此而大展。尚呼吾国为东方病夫,只求于外人无碍,吾民生命财产,无所计较,弊端百出。”(13) 1874年7月,江海关颁布《上海口各国洋船从有传染病症海口来沪章程》,规定由江海关监督及各国领事官随时规定何处为传染病症海口,确定后通知河泊司,由其传知驻吴淞管理灯塔、潮势之人。当有洋船驶至吴淞口,管灯塔、潮势之人赴船查问是否来自有传染病症的海口,若是,则令该船挂黄色旗号进口。河泊所看到挂黄旗船只,令其在浦江泊船,并派水巡捕看守,通知医生赴该船查验。停泊时间由医生和该船属国领事酌办。(14)这一规则显示出,上海的海港检疫由海关与外国领事官负责,他们决定是否需要检疫以及检疫时间的长短。此时的海港检疫仅仅负责出入港口船只的检疫工作,尚未建立起相关的医院和卫生站等基本设施。 由于海关聘用外国医生办理海港检疫,其代表的西方防疫理念很难对中国人产生直接影响,更罔论深层次的防疫观念。直到1894年香港鼠疫的爆发,中国人才真正开始面对以检疫、隔离和消毒为主要形式的海港检疫的挑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从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来理解。从文化层面来讲,人们仍沿袭传统对瘟疫和“隔离”的认知,对西方防疫方法既知之不多,且对其能否有效防止瘟疫缺乏认同。最重要的是,西方的检疫隔离措施与中国人习俗相背离,如将病人隔离和消毒、烧毁患者所住房屋等措施更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从政治层面来讲,人们尚未认识到对抗疫病是政府的职责,应采取措施将病者与社会隔离开来,在国与国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设置一个“健康”的安全阀。这使无论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对此次疫情的影响均集中于如何应对外国交涉和预防内乱,反而对防疫本身关注不足。可见,中国在形式上成为海港检疫全球化的一分子,但并未接受它所代表的西方防疫理念。应看到的是,西方无法在医学认知层面促使中国人接受海港检疫,但是通过清洁达到预防疫病的做法却为时人认可。 三 香港:厉行卫生行政 1894年5月10日,出现第一例鼠疫病例后,港英政府宣布香港为疫埠。11日,政府委派洁净局组织三人常设委员会主持防疫工作,并于当日制定了《香港治疫章程》,并获得港英当局的批准施行。该文件刊登在12日的《香港政府宪报》上,同月22日《申报》全文刊载。从该章程来看,其主要措施在于报告病例、隔离病人、埋葬疫死者、消毒患疫者住处和使用物品以及维护清洁卫生等内容。港英政府设立专门的医船和临时疫症医院收治、隔离鼠疫病人。停泊在港湾的“海吉亚号”作为医船,坚尼地城警署作为临时隔离医疗所,凡是感染鼠疫的病人须送到医船和医院隔离,接受西医治疗。由于华人大都不愿到西医院和医船接受西医治疗,洁净局又将西湾坚尼地城的旧琉璃厂改建为由中医师主治的隔离病院,归东华医院管理。后来九龙发生疫症流行,华人官员和绅士在九龙荔枝角辟地建院收治,“以致华人之疫者多入院就医,是以西医院中人数日少”(15)。入院病人受到严格控制,士兵日夜监守,未经医生许可,绝对不许外出,疑似病例则被隔离观察。 根据治疫章程,洁净局帮办谢文率人负责逐户查疫区房屋,转移患者去医船或医所,由高陆专门负责对疫区清洁消毒,“如室中有不洁之物,必令洗涤净尽,更以药水遍洒室中,使无污秽之气。各厕所每日洗涤,投以生灰,以辟秽恶”(16)。5月24日,随着疫情的扩大,消毒工作人手短缺,港府从驻港英军什罗浦郡第一团派出300名士兵,协助洁净局人员搜屋、查疫和消毒。这些工作人员,工作非常积极,“竟有终日奔走越十点钟之久或十五点钟之久,而未得稍息者”。为保障防疫人员的健康,当局做了分工调整,“每人查搜屋宇,日中分上下两班,各查搜三点钟,避免过于劳苦”(17)。但是,这些人手远远不够,“只能洒于有疫之街及屋,而不洒于未染时疫之处以预止疫气”(18),在太平山一处即有350间有疫之屋(19),而其“穷日之力,亦只薰洗屋宇三十间,而日中新患疫之家已有盈”(20)。 以检查、隔离和消毒为主要内容的防疫手段,未得到中国人的认同。当时,无论是报纸舆论,还是地方官员,都认为其残酷可笑。《申报》记载了时人对此的描述:“港中疫症之盛,与夫医治疫症之奇,实属可笑,凡染病者载至海船,先以白兰地酒十二两冲药水少许灌之,旋用雪水六磅重压头上,其胸前手足等处。又以雪水一磅压之。一经落船十人无一生者、另饬人入屋搜查,如白日偃仰者,疑是生病,牵至海船,照前法治之,死者不计其数。”(21)两广总督在给军机处的电报中亦指出,“香港以洋法将华人闭入船内,饮以药酒,洒冰块薰以硫磺”(22),“不许亲属往看,不许华医诊视,死后以灰验埋,不许亲属取回棺验,二三百人群聚屋内,席地而坐,来而待毙,以致死者甚多”(23)。挨家挨户喷洒消毒药水和粉剂,尤其是受到华人的抵制,妇女选出代表向港英当局请求变通,“虽系为卫生起见,究竟与我妇女廉耻有关”(24)。 严格的强制检疫隔离冲击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道德价值观念,迫使大量中国居民逃离香港,其中约有八万人逃往广州。(25)报载:“粤垣本月初一至初十日止,由港晋省者每日不下千余人,有携眷来者,有结伴来者,有肩挑负担来者,有拖男带女来者,老的、幼的、贵的、贱的,纷纷逃避,殊属可悯。”(26)两广总督李瀚章因“香港时疫洋官用洋法医,华人岂能不毙”,(27)饬善堂绅董用船前往香港接收病人回内地医治。(28)为此,军机处与英国驻华大使交涉,要其电港官变通办理,不要阻拦粤省派船接病人出口。英使为此致电港督,并得其复电照办。(29) 为掌握鼠疫流行的实际状况,港英政府设立疫情报告制度。由政府统计鼠疫病例,通过报刊及时公布每天的新增病例、疑似病例、死亡病例以及留院治疗病例。此举使得香港鼠疫死亡人数有了可信的统计数据,约2550人。(30)统计是现代卫生行政的重要手段,对了解病情、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人缺乏统计概念,对很多疫情都只有概括数字,缺乏精确统计。在此次鼠疫中,广州的死亡人数一直没有确定的数字,多为估计之数。有材料认为,“从可靠来源知道在阴历3月至6月间售出9万具棺木,其中75%是因鼠疫死亡的”(31)。俞抛在1894年到过广州,记载道“穗垣内外,死于是疫者十余万人”(32)。 此时,以细菌学说为基础的科学医学正蓬勃发展,香港的疫情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关注。为研究鼠疫病菌、传播状况及防治办法,有关国家向香港派遣了细菌学家和医学家。法属越南殖民地长官派探险家兼科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调查鼠疫及其控制。他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分离出鼠疫杆菌,并于抵达香港的第七个星期,就发表了提出详细治疗方法的论文。日本政府派遣由微生物学家北里柴三郎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在香港卫生局的支持下,发现了引起鼠疫的病菌。(33)这些病原学上的发现,只是鼠疫研究的起步,人们逐步加深对该病的认识,获得病菌状况、传播途径及治疗方法的知识。但在此期间,中西医生都认识到老鼠是此传染病的重要因素,却没有人真正知道老鼠的角色。 简言之,香港殖民政府对抗鼠疫的重心已非海港检疫,而是地方卫生治理,执行现代民族国家卫生行政职能:颁布防疫章程,设立专门的防疫机构,严格执行搜屋、隔离、检疫、消毒和清洁;政府设立隔离医院,收治患疫者;严格进行统计患病人数,获取准确的疫病信息等。 四 广州:无为而治 作为最早开放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广州的海港检疫却建立得很晚,直到宣统三年(1911)东三省肺疫流行时,“粤海关鉴于轮船有由华北传布疫病之虞,乃根据上海办法,编订检疫章程,经海关道核准,及领事团同意,于该年春季公布”(34)。可见,广州长时期置身于海港检疫全球化之外。 清代,瘟疫很少作为灾荒上报。浙江人袁一相曾指出地方官员不报疫灾的积习:“查疾之作,外不由于六气之所感,内不由七情之所伤,系天灾流行,疹病为祟,沿乡传染,阖门同疾……谨案入告之章,言灾异不言祥瑞,止于地震、涝等类,而不及瘟疫。”(35)就实际状况而言,当时并无治疫良方,朝廷所能做的不过蠲免或赈济而已,并无控制或消灭疾病流行的措施。在面对瘟疫时,地方官员会采取若干措施,为灾民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地方官府虽无卫生方面的职责,但地方官可能出于个人意愿,象征性地参与防疫,设局治疗病患。《申报》曾总结过华人防疫的方法:“或在城厢市镇分设施医局,以便患病者就近诊治,或选上等药料,制备红灵丹、行军散、辟瘟丹、蝉酥丸等,施送与人。其所以为治疫,计者如是焉而已。倘药饵无灵,传染不已,则惟有乞灵于神祇。官府在城隍庙设坛祈祷,为民请命,而地方士庶或更举土偶出巡,幡幢夹道,鼓乐喧天,藉以驱逐疫鬼,或扎成龙灯、狮灯、象灯,昼夜出巡,或听方士、巫觋之言,为祈福、镇压之举,徒事张皇,毫无实际。”(36) “粤俗按鬼”的传统由来已久,据清人记载:“《汉书》谓越人信巫鬼,重淫祀;武帝平南粤以后,尝令立越祝祠,祠天神百鬼,而以鸡卜,至今粤俗尤然,无论朱门、悬簿、中堂皆供神像,朔望必礼拜。市肆则燃香烛于门首,晨起见之,有如火城。遇有疾病,不事医而事祷,贫者至弃产揭债,曾不顾惜。”(37)人们认为,瘟疫的发生是由鬼神掌握的,因此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一些特殊的仪式,如“击鼓鸣金,合吹牛角,呜呜作鬼声,书符咒水”,“异神像出游,焚檀香、放鞭炮”,(38)以保平安。在这种鬼神司疫风俗之下,广州地方官吏常建醮祈禳,以驱避疫气。疫情爆发后,广州府张润生太守督同南海、番禺两邑宰,“设坛城隍庙,建醮七日,祈禳瘟疫,为民请命”,甚至连日常的政务也不管,“致斋三日,不理刑名,并示谕各各屠户不许宰杀,以近祥和”。(39)南海、番禺两县令参拜三次,广州府太守偕同南海、番禺县令参拜两次。甚有好事者提出“度岁之说”,以四月初一为元旦,方可拔除不祥。于是在三月二十三四日举行祀社之典,为此纸店、灶疏为之售罄,“从前每张不过一二文者,今则出至十余文而不可得”,“各家门首均洗刮洁净,贴换宜春闾阎,气象忽又一新矣”。(40)《申报》认为,这些迎神逐疫的行为都是无稽之谈,“曰当求之于人,而不当求之于神天道,远人道,迩何必循世俗之见,信巫觋之言,以有用之赁财作无谓之举动”。(41) 除建醮祈禳之外,某些地方官员请人备制药丸,分送患者,以资救济。时任臬宪的额玉如将治疫的药分给士民,病者一经服下,无不“立起沉菏”,以致“到署领取者应接不暇,户限为穿”。后因药物有限,便“将方抄出,发交爱育善堂,嘱其如发炮制,散给病者,藉以普救群生”,时人给予额玉如很高的评价,认为“臬宪此举,功德无量”。(42)此种宣传有夸大之嫌,若病者真能“立起沉菏”,又怎能遏止不住疫情呢? 士绅一直是此类地方事务的组织和领导者。他们不仅积极组织各种迎神驱疫的活动,而且组织各类善堂赠医施药。同治十年(1871),广州爱育善堂开办,吸引了士绅热情参与大规模兴办善堂,“自是而后,城乡各善堂接踵而起”。(43)广州周围各善堂都有赠医施药之举,如顺德寿仁善堂“赠医施药、施茶、施棺、赈饥诸善举”。(44)鼠疫期间,遍布各处的善堂还为疫死者施出棺材,“每日善堂施棺收殓,如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爱育善堂在3个月内共施出棺木数千具之多。(45) 鼠疫流行之时,士绅们一方面延医治病,另一方面宣传推广有效治疗方法。听闻李某医术高明,城西四庙赠医局的一些士绅,立即重金延请在局施医,“一时远近闻风而至”,更有救已毙命者之说,“李操术甚神,施以刀圭,其病若失”。油栏门外广济医院绅董,聘得名医二人,分在南关无字码头和西关媚州庙,设厂施医。此外,士绅开设“方便所”,为病人提供医疗,如刘学询在西关黄沙倡建施医养病所,受到官府嘉奖。(46)该医厂纵横数十丈,“本极宽广,奈就医者纷至沓来,大有人满之患”,故该绅见“时症未息,为日方长,恐后至者无地容留,或有为善不终之憾。又招雇之匠添构数十间,务使贫病之人咸欣得所”。(47)此外,士绅们重视医学知识,将治疗效果较好的“良方”集中起来,汇编成册,传播医学知识。罗芝园的《鼠疫汇编》是现存最早的专治鼠疫的医书,被证明有较好疗效,因此广为流传。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广州的士绅是对抗瘟疫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他们以设厂施药、施医等传统慈善方式参与防疫。由于没有统计材料,只能在报纸报道中窥见一二,实难对其有效性进行考证。 那么,广州的地方官们除了建醮祈禳外,还有别的措施吗?我们很难看到他们参与防疫的事务,以及表达自己的看法。直到香港防疫引起广州政治动荡时,才吸引到地方官的注意。两广总督电知北洋大臣,“港官焚民房逐疫,省城骚动,欲与洋人为难”。后者电告粤督留意防护外,另电告军机处。这些官员担心的并非疫情本身,而是“港疫不息,民心总不能清,惟加意预防保护”(48)。当广州城出现白贴,声称“如再烧香港民房,即焚省城、沙面以图报复”时,引起了两广总督的关注,密饬文武员弁严拿造谣之人,禁止白贴,并添派兵勇保护租界,以期无事。(49) 广州官员对卫生事务的基本无视还可从另一事例得以佐证。1894年年初,法国驻广州领事就沙面法租界附近停靠的粪船与两广总督进行交涉,要求其撤离沙面。两广总督认为,“沙面粪船系在浦外,并非租界,且湾泊已历多年,非始今日,其地距沙关房屋尚远,不致感受秽气”,仅饬县官命令“各船加做密盖,限时开行,不准久泊”。(50)如此作为,引起法国人不满,法国使馆翻译微席业亲自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递交节略,要求该署致电两广总督,速令停靠在沙面法租界附近的粪船立即驶离。(51)在得知粤督不愿照办后,法国公使施阿兰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其“即行速电粤督,转饬禁止该粪船在现泊以及附近沙面各处所,不许停泊”。(52)此事前后交涉若干次,历时几月,李瀚章一直以粪船向来湾泊沙面且涌外系中国水界为由,拒绝法国人的要求。(53)此事表明,有关卫生的事务即使上升到中央的外交交涉,洋人的施压也难以促使地方官干涉地方卫生事务。 从上述描述来看,广州地方政府未介入防疫事务中,没有采取控制瘟疫传染的措施,基本是无为而治。组织的几次祈神活动不过是求得心安而已,反倒是地方士绅聘医施治,设厂施药,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实际仍是传统的慈善救济。近在咫尺的香港殖民政府采用现代国家的卫生行政,带来了与广州不同的结果:香港死亡人数不到3000人,广州死亡人数达6万人。(54)这种情况在当时对广州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中国传统防疫方式,正视如何应对瘟疫来袭的问题,如费克光指出的那样:“中医业者已经证明自己无法有效的对抗此病。1894年启开了中国与瘟疫搏斗的新纪元。”(55)此外,少数乡村的士绅组织乡民隔离观察来自疫区的人,“附城西村乡,现恐瘟疫传染,遂在外隙地搭盖大棚厂一座,凡乡人由省中回者皆在厂中止宿,不许越雷池一步,即家人妇子亦不能与之相见”。(56)此举似可视作对西法的模仿。 五 上海:示范的作用 香港鼠疫爆发之前,上海公共租界已建立起卫生行政机构。1889年,工部局下设由专业医师史坦莱领导的卫生处,按照西方模式专职办理卫生事务。(57)不过,该处的职权范围仅限于公共租界,对界外的卫生事务无权插手。正是由于遵照西方医学原则进行卫生治理的只有租界当局,鼠疫来袭时它是最有危机感且最积极的。因为它明白,若无其他各方的配合,仅仅依靠自身,是无法有效进行防疫的。由于工部局对此事的高度重视,董事会会议反复进行讨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使我们能够对上海的海港检疫与地方卫生行政两种制度的实际运作有所了解。 1894年5月,上海领事团领袖领事接到香港发现黑死病瘟疫的通告。他要求上海道台发出指示,凡从香港来此的船舶一经发现其船上有疫情,务须严格遵照“港口章程”第16条规定行事。(58)为此,江海关延定杨树浦巴纪医生稽查香港来沪之船。(59)22日,工部局董事会致函领袖领事,建议所有来自广州、香港、汕头、厦门以及福州的船只到达吴淞时必须悬挂黄旗,泊船以备检查,一旦船上有流行病,按“港口章程”处理,并请求他要求道台,如该章程得到领事团的批准,就请其毫不迟疑地贯彻执行之。(60) 与此同时,工部局卫生官与海关医官商议决定:(1)凡广州或香港来船,无论曾否停靠中间口岸,均需接受检疫;(2)在港口范围之外至少两英里进行检查;(3)所有检疫官员认为有危险之华人行李、货物,一律卸于浦东岸边进行硫黄蒸汽消毒;(4)若船上无时疫患者,按第3号规定,卸下行李后,准发检疫通行证;(5)若船上有时疫患者,即按“港口章程”第16条处理。(61)虽然领事团领袖领事要求道台指示海关税务司立即执行医官所建议的措施,但道台拖延执行医官的建议。由于香港疫情正在蔓延,疫情传至上海的危险随之增加。所以领袖领事再次致函道台指出,目前不仅使当地侨民处于严旨危险中,且对本国国民来说尤为严重。若道台继续拖延答复,工部局建议征询领袖领事,可否请领事团致电北京,将此事提交总理衙门,请求立即指示道台执行医官建议。(62)到了6月,上海道台通知领袖领事,他已指示海关税务司执行医官卫生方面建议,发布检疫章程,在吴淞口外设立了崇宝沙卫生站,对来自疫区港口的船只及乘客进行检疫。(63) 在工部局看来,海港检疫所采取的措施仍不够严厉。上海外国侨民普遍认为,凡到达之船只必须在吴淞口外接受三天以上较长时间的时疫检查。而且一旦此地流行时疫,其对租界及此地贸易之影响将较香港更为严重。工部局认为欲确保租界安全,最好应命所有来自广州、香港及中间港口的船舶自其离港之日算起在吴淞口外共有八天检疫时间。(64)英国总领事致函工部局,他不能提出这样的停船检疫建议,除非所有国家,包括中国人,都准备执行。医官们认为,做好接收、隔离、治疗及对所有从受检疫之船上登岸的人与货物进行消毒的必要准备工作是必要的和行之有效的。除非医生、工部局及领事团都认为时疫传到上海的危险大到有必要对所有南方来的船只进行停船检疫的程度,否则无法执行。(65) 为了更有效地防疫,工部局卫生官还采取了两项措施。首先,开设临时性医院接收病人。对到达此地的西人病患者,在安全送往医院之前不得登岸,华人患者在送往浦东之前不得登岸,并在浦东接收他们。工部局当时在浦东筹建为华人时疫患者准备的是临时性医院,即两座隔离棚,它无意为时疫患者建造永久性医院。(66)消毒站及黄浦江两岸隔离棚竣工后,工部局任命拉尔卡卡及马修斯两位医师负责开办。(67)工部局还请道台选派两位他信任的本地医师,为愿意接受本地医师治疗的华人患者治病,并要求他发布布告,张贴于浦东消毒站。(68)6月19日,工部局要求中国当局接管消毒。(69)这一建议被中国官员拒绝,海关税务司以及道台都声明他们无权为所拟“卫生章程”拨付款项。(70) 其次,建议工部局要求华人当局准许安排运送时疫患者去医院,准许入户查找病人。因为,他认为一旦本地发现时疫,如无中国当局的协助要对华人中发现的病情进行实质上的控制是根本不可能的。董事局故此决定请领事团领袖领事要求道台发布告示,必须立即将华人患者从其住所送往医院。(71) 在租界之外,地方官采取的办法为“多制辟疫丸散,分送与人,各处善堂施医给药”,(72)并未注意清洁问题。当时的舆论已认识到防疫不能止于海港防疫,而要在整个地方社会厉行清洁才能有效防止疫情的蔓延。虽海港检疫将有疫或疑有疫者送往病院,但是人们担心这样的措施是不够的。有人指出,河南路马车常有数十辆之多,“矢溺熏蒸,行人皆掩鼻而过”,店铺诸人日受秽气势必生病,提议工部局“饬令清道役夫格外勤为洒扫,并责成御者随时打扫,不准矢溺漓淋,各铺户亦助之收拾洁清,庶免致蒸成疫疠”。(73)工部局已要求界内居民“勿再堆积污秽,以致臭气熏蒸”,注意屋宇、道路、食物和用物清洁,报界则希望这些措施能够在整个上海地区推行,“凡城厢以冀南市推而至于乡屯、市镇,次第依照,百密而无一疏”。(74) 此外,因租界贫民无力掩埋尸棺,往往弃之荒郊,而炎天毒日,秽气熏蒸,行人触之最易致疾,《申报》呼吁,“所期城厢内外各官实力施行,辅工部局之所不及,则民戴德益”。(75)租界有章程规定殡殓不得超过24小时,“人皆恪守,无敢或违”。但是,在租界外各处义冢停棺不葬,带来很大的卫生隐忧。上海东临黄浦,“西南北三面平畴旷野,一望无垠”,善堂购地以为义冢,“停棺丛丛”。善堂设义冢原为照顾那些客死他乡之人,“为方便计,准其暂时停柩于此,其有亲属者必函召前来,使之领棺归里早安,如查无亲属则即代为掩埋”。但是,棺材多由薄板钉成,“薰灸于烈日之中,飘摇于风雨之夕,板皆裂缝,尸骸不免暴露秽恶之气随风远送”,结果成为瘟疫之摇篮。这既是国人习俗所在,也是由于租界权力不能及的结果,“只能尽其心于租界中,未能施其租界外也”。(76)上海道台应工部局之请对各地运送棺材做了要求:镇江地方当局应立即妥为埋葬发往该地的棺材;发往上海的棺材应即交付其亲属,并在捕房督察长的监督之下埋葬于租界以外,且一年内不得迁动;不准华南运来的棺材在上海登岸。此外,道台要求工部局向各轮船公司发布命令,不许他们的船只从香港或广州载运时疫死者的尸体。(77) 在工部局的示范下,时人开始反思中西对待疫情的不同态度:一种相信是天命所为,自然采取的是求助于神灵;一种认为是人事未尽,想方设法地加以改进。“中国之人不甚畏疫,谓天行时疠,厥有定数,在数者难逃。其死焉者,不畏亦死,畏之亦死,其不死焉者,畏之不死,不畏亦未必死。惟自慎其起居饮食,寒暖而已矣。西人则以为疫之来,由于人事之不灭非可尽,委之于天平日居家不能清洁秽污之气,久而触发则致疫症传染亦多。由于秽气所致,避疫之法以洁除街道、居民为第一要义。”(78)对西人的做法,中国人并不认同,清廷官员认为海港检疫是无效的,“如西法封舱,禁人不许往来,势有不能止,可术医药饵以尽人力,别无他法”。(79)但是,人们已开始认识到此举的政治含义,西人将防疫之事作为爱民之举,租界较之非租界“一秽一洁,已有上下之别”,中国官员不应将爱民之名让于西人,而宜速设法严防。(80) 1894年,中国主要海港城市设有海关医官,办理海港检疫,但并未对中国社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在香港,殖民政府严苛办理地方卫生行政,颇有成效,却在当地造成极大恐慌,实际引起国人对检疫的反感和对抗;在广州,地方士绅作为主要领导者,采用传统方式对抗鼠疫,政府更多作为局外人旁观事态发展;在上海,工部局因担心影响到公共租界的卫生,非常在意防疫事务,以弥补海港检疫制度的缺陷。这些都表明,在1894年中国虽已成为海港检疫全球化的一分子,但并未真正接受西方的卫生观念,也未接受西方防疫和卫生治理的方式。 笔者以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西方的防疫方式要得到东方的认同和接受,必须建立在文化和政治认同基础之上,海港检疫无法达成此历史使命。海港检疫未让中国人信服其有效性,反而引起国人强烈反感,未能形成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感。海港检疫的全球化是帝国军事、政治和经济扩张的副产品,依靠的是军事霸权和政治强权。海港检疫的全球化所采取的隔离措施并非单纯的防疫措施,是各国为保护贸易和人口流动建立的一种保护网,交织着各种权力和利益网络的争斗。在这个过程中,前往外国淘金的中国劳工往往被视作瘟疫的载体,受到非常严苛的对待。中国人对海港检疫的直接感受不是西方医学文化的优长,而是一种不入道的强制性隔离和禁闭,带有种族歧视和帝国霸权的特色,引起国人强烈的反感,激发出民族主义情绪。清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对西方防疫感触最直接的不是其有效性,而是卫生事务交涉中的强权与霸道。再加之各级官员秉持防乱甚于防疫的理念,难以认识到卫生的重要性,根本未曾触及文化认同层面。 另一原因则是海港检疫已无力应对19世纪末期的疫情,必须建立起卫生治理的全球化才能应对瘟疫的传播。19世纪末,随着交通工具的改进和世界性市场的发展,全球范围的人和物的流动大大加快,仅靠海关办理海港检疫来防止疫情的蔓延,已是非常困难的。为此,英国于1872年将海港检疫纳入到公共卫生系统,以便对资源进行统合。我们看到,中国官员和百姓对于西方防疫持不认可的态度,造成海港检疫全球化影响甚微,也影响到对公共卫生的体认。此时,西方细菌学说兴起,医学界发生了一场科学革命,卫生治理有了严格的科学理论作为基础,为卫生治理的全球化提供了可能。科学的话语取代殖民话语,对于东方各国来讲也更易于接受。中国很快被卷入卫生治理全球化的大潮中,不得不接受新的医学话语和卫生行政模式。 ①1894年,香港、广州地区爆发的腺鼠疫,受到研究者关注,已有一系列成果问世。[澳]费克光:《中国历史上的鼠疫》,刘翠溶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下),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所1995年版,第673—739页;Carol Benedict,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彭海雄:《1894年香港鼠疫研究——基于19世纪香港社会变迁的考察》,硕士学位论文,华南师范大学,2005年;苏新华:《清末穗港鼠疫与社会应对措施(1894-1911)》,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6年。 ②Paul Slack,"Responses to Plague in Early Modern Europe:The Implications of Public Health," Social Research,Vol.55,No.3(Autumn,1988),p.438. ③Paul Slack,"Responses to Plague in Early Modern Europe:The Implications of Public Health",Social Research,Vol.55,No.3(Autumn,1988),pp.441-442. ④Krista Maglen,"'The First Line of Defence':British Quarantine and the Port Sanitary Author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Vol.15,No.3,2002,pp.413-428. ⑤A.Mayne,"'The Dreadful Scourge':Responses to Smallpox in Sydney and Melbourne,1881-82",in Roy MacLeod & Milton Lewis(eds),Disease,Medicine and Empire:Perspectives on West Medicine and The Experience of European Expans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8,pp.219-241. ⑥P.Curson & McCracken,Plague in Sydney.The Anatomy of an Epidemic,Kensington,N.S.W.:New South Wales University Press,1989. ⑦Mark Harrison,"Quarantine,Pilgrimage,and Colonial Trade:India 1866-1900,"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Vol.29,No.2,1992,pp.141-142. ⑧Valeska Huber,"The Unification of the Globe by Disease? The 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s on Cholera,1851-1894," 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49,No.2,2006,pp.453-476. ⑨Emmanuel Le Roy Ladurie,"A Concept:the Unification of the Globe by Disease," The Mind and Method of Historian,Brighton,1981,pp.28-91. ⑩Roy MacLeod,"Introduction",Disease,Medicine and Empire:Perspectives on West Medicine and The Experience of European Expans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8,pp.3-4. (11)《论防疫之禁令》,《新闻报》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日。 (12)宋志爱、金乃逸:《我国海港检疫事务沿革》,《中华医学杂志》1938年12月第25卷第12期。 (13)伍连德:《收回海口检疫权提议》,《德华医学杂志》1929年第1卷第11期。 (14)《关于海港检疫站向海关发放函件之事》,上海档案馆藏,U1-16-2877。 (15)《港电报疫》,《申报》光绪二十年五月初十日,第2张。 (16)《论中西治疫之不同》,《申报》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 (17)《香港疫耗》,《申报》光绪二十年五月初二日。 (18)《西报言疫》,《申报》光绪二十年五月初八日。 (19)《港报纪疫》,《申报》光绪二十年五月初十日。 (20)《西报言疫》,《申报》光绪二十年五月初八日。 (21)《述粤东香港疫疠近日情形》,《新闻报》光绪二十年五月初十日。 (22)《为广州瘟疫已减轻,香港改用中医治法以本土流行事》,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电报档,2-02-12-020-0287。 (23)《为香港瘟疫情形事》,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电报档,2-02-12-020-0384。 (24)杨思贤:《香港沧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50页。 (25)参见[澳]费克光《中国历史上的鼠疫》,第700—702页。 (26)《迁地避瘟》,《新闻报》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九日,第2张。 (27)《为香港瘟疫设法派船接回内地医治事》,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电报档,2-02-12-020-0377。 (28)《为香港瘟疫情形事》,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电报档,2-02-12-020-0384。 (29)《为香港瘟疫港官变通办理事》,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电报档,2-02-12-020-0404。 (30)香港政府公布鼠疫死亡病例共2550人。《九龙海关志》记录,1894年5月10日香港宣布为疫区,因疫病死亡的达2552人。苏新华在其题为《清末穗港鼠疫与社会应对措施(1894-1911)》的硕士论文中,根据1894年《申报》有关香港鼠疫新增病例、死亡病例、留院治疗病例、死亡总病例等指标统计,得出1894年香港鼠疫患者共死亡2378人。 (31)洗维逊:《鼠疫流行史》(内部资料),广东卫生防疫站,1989年印行,第204页。 (32)俞抛:《俞曲园笔记》,文明书局1922年石印本,“序”。 (33)参见[澳]费克光《中国历史上的鼠疫》,第702—704页。 (34)宋志爱、金乃逸:《我国海港检疫事务沿革》,《中华医学杂志》第25卷第12期,第107页。 (35)《救恤疫四条》,(清)贺长龄等编《清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卷45。 (36)《论中西防疫之不同》,《申报》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 (37)(清)张渠撰、程明校点:《粤东闻见录》,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9页。 (38)《西人言疫》,《申报》光绪二十年四月十三日。 (39)《时疫未已》,《申报》光绪二十年四月十七日。 (40)《过年却疫》,《申报》光绪二十年四月初五日。 (41)《论迎神逐疫之非》,《申报》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六日。 (42)转引自苏新华《清末穗港鼠疫与社会应对措施(1894-1911)》,第33页。笔者质疑对于此种施药效果,既然病者无不“立起沉菏”,怎么未能遏制住疫情呢? (43)(清)郑梦玉等修、梁绍献等纂:《同治南海县志》卷六《建置略》,《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 (44)《民国顺德县志》卷二《建置略》,《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 (45)《粤东患疫续纪》,《申报》光绪二十年四月十九日。 (46)《广行方便》,《申报》光绪二十年五月初四日。 (47)《五羊拾零》,《申报》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三日。 (48)《为香港瘟疫设法派船接回内地医治事》,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电报档,2-02-12-020-0377。 (49)《为香港瘟疫情形事》,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电报档,2-02-12-020-0384。 (50)《沙面粪船事抄送粤督回电由》,光绪二十年四月十九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01-18-065-01-006。 (51)《粤省沙面粪船由》,光绪二十年四月十三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01-18-065-01-001。 (52)《沙面粪船请再电达粤督禁止由》,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01-18-065-01-007。 (53)《沙面粪船并无窒碍由》,光绪二十年七月三十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01-18-065-01-015。 (54)陈继武:《鼠疫要览》,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第2页。 (55)[澳]费克光:《中国历史上的鼠疫》,第715页。 (56)《羊城疫信》,《申报》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57)阮笃成编:《租界制度与上海公共租界》,《民国丛书》第4编第24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124—125页。 (58)《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25页。 (59)《港电报疫》,《申报》光绪二十年五月初六日。 (60)《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11册,第625页。 (61)同上书,第626—627页。 (62)同上书,第628—629页。 (63)《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11册,第631页。 (64)同上。 (65)同上书,第633页。 (66)同上书,第629页。 (67)同上书,第633页。消毒站花费2432两,杨树浦隔离棚花费600两,浦东医院花费600两,加上家具、设备费用400两,共计4032两。 (68)同上书,第630页。 (69)同上书,第633页。 (70)同上书,第635页。 (71)《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629页。 (72)《论迎神逐疫之非》,《申报》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六日。 (73)《疫更难饵》,《申报》光绪二十年五月初三日。 (74)《防患未然说》,《申报》光绪二十年五月初一日。 (75)《上海防疫》,《申报》光绪二十年五月初四日。 (76)《论防疫宜先葬停棺》,《申报》光绪二十年五月初六日。 (77)《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11册,第660页。 (78)《去秽所以祛疫说》,《申报》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四日。 (79)《为广州瘟疫已减轻,香港改用中医治法以本土流行事》,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电报档,2-02-12-020-0287。 (80)《去秽所以祛疫说》,《申报》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