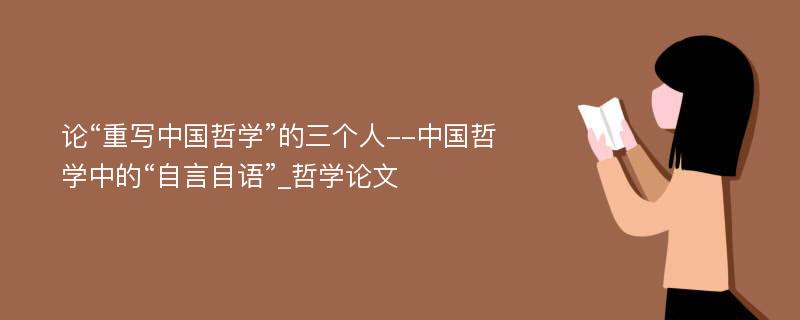
“重写中国哲学”三人谈——中国哲学“讲自己”的中国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哲学论文,重写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0511-4721(2005)03-0005-12
一
哲学是最要求概念的清晰性、确定性的,但哲学这个概念本身又是最不确定的。两千多年来,“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一直纠缠着哲学家。每个哲学家或哲学学派都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着这同一个问题,但答案却各异其趣。真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究竟是“哲学”本身就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抑或两千年来哲学家的智慧欠缺,不足以诠释?我想问题在于哲学所应指的领域的不确定性以及哲学家价值观念的差异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想确定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不仅力不从心,而且吃力不讨好。因此我主张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超越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我之所以这样主张,也有一点基于两千多年来“什么是哲学?”,至今仍然“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来解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似乎不太现实。首先,“什么是合法的”?两千多年来,像走马灯一样的形形色色的哲学中,哪一个是合乎“法”的?其次,这个“法”又是什么“法”?是古希腊之法,抑或古罗马之法?是理性主义之法,抑或非理性主义之法?是唯心主义之法,抑或唯物主义之法?是结构主义之法,抑或解构主义之法?等等。再次,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去合哪个“法”?是去合利玛窦(1552-1610)的“中国哲学”之法,抑或去合黑格尔(1770-1831)之法?是去合纪·鲍狄埃(Guillaume Pauthier)《中国哲学史大纲》(1844年)(注:见雅克·布罗斯《发现中国》,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页。)之法,抑或去合德里达“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之法?第四,“人为自然立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法”是人制定的,各家有各家的“法”,中国古代就有“家法”和“师法”,而各是其所是。“法”即使制定出来了,也可“与时偕行”,不断修改,而非铁板钉钉,永远不变。
鉴于此情,我曾提出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的中国方式。所谓“自己讲”、“讲自己”,首先,是怎样讲?是“照着”西方哲学讲,以西方哲学为真哲学,照着西方哲学讲中国哲学,抑或根据中国哲学的实际存在面貌讲中国自己的哲学?其次,是讲什么?要么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要么中国古有六艺,后有九流,大抵皆哲学范围所摄而讲之;要么讲述中国自己对“话题本身”的重新发现,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时代冲突的艺术化解,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时代危机的义理解决,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形而上者之谓道”的赤诚追求。再次,是如何讲?是“两耳不闻窗外事”,闭门只造中国车地讲,抑或放眼世界,海纳百川地汇聚千家之思想,而后融突和合为新中国哲学?这就是说,“自己讲”、“讲自己”大有学问,但必须依照“中国方式”讲。
二
古今中外,大凡新思维、新哲学的“转生”,都非“闭门造车”出来,而是“出入”古今中外各种哲学思想的结晶和凝练,是哲学家主体精神的超越和流行。在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文化、哲学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次外来文化、哲学的巨大冲击和洗礼。西历1世纪,印度佛教文化、哲学的传入;西历16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哲学的涌入,都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哲学产生里程碑式的作用和影响。
佛教入中土以后,经历依附、发展、鼎盛、消融时期。汉至魏晋时,佛教依附于汉之方术(道术)和魏晋玄学。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与本土的儒、道文化构成既冲突又融合的态势,在“弃亲”、“捐妻”、“不孝”、“无后”等问题上形成了紧张。然东晋般若学依玄学而开显为“六家七宗”,玄学的“有无本末”与般若学的“空”、“有”连类,故有僧肇的《肇论》依般若学而论玄学。玄佛合流,相互标榜。
南北朝时,佛教得以发展。虽有“沙门应否敬王”、“神灭不灭”、“夷夏”、“化胡”等问题的激烈论争,但名僧与命官进一步合流。如果说汉魏之际,安世高系小乘佛教所翻译的《安般守意经》、《阴持人经》,一以中国道家、神仙家的吐纳之术比附呼吸守意,一以“四大”连类“五行”、“五戒”连类“五常”,“元气”即“五行”即“五阴”(五蕴),那么支娄迦谶系大乘佛教把《般若波罗密经》译为《大明度无极经》(支谦译),则是依《老子》“知常曰明”格义“般若”为“大明”,“复归于无极”连类“波罗密”为“度无极”。到了南北朝时涅槃学流行,梁宝亮《涅槃集解》探讨“佛性”问题,有与中国传统儒家心性之学想连接之处。
隋唐时,佛教鼎盛,儒、释、道三教,佛教独占鳌头。佛教不仅在经济上“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注:《旧唐书·辛替否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158页。),而且在民间思想信仰上“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注:《隋书·经籍志四》,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99页。)。佛盛儒衰、道衰佛盛,外来印度佛教文化、哲学这时在中国成为强势文化、哲学,中国本土儒道文化、哲学,反沦为弱势文化、哲学。其实,梁武帝在天监三年(503)下诏宣布佛教为“正道”,儒、道二教为“邪”,开佛教“独尊”之先河,已取得强势地位。佛教愈是强势,愈要求融入中国本土文化、哲学,以便取而代之,于是天台、华严、禅宗不断中国化,从印度佛教转变为中国化的佛教,佛教得到了新发展、新繁荣。相反,佛教在其本土印度8、9世纪便逐渐衰败,到14世纪几乎湮灭。
在佛教强势文化、哲学的挤压下,本土传统的儒道文化、哲学确实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儒道文化危机凸显。虽然唐朝政府对儒、释、道三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用现代所说的“综合”,试图进行文化、哲学的整合,但由于兼容并蓄方法的文化、哲学整合方法,受其背后价值观的支配,就像一支无形的手制约着兼容并蓄方法的落实,因此终唐之世,兼容并蓄方法无大收效。
鉴于此情,一些具有儒家思想的知识精英,出于“匹夫有责”的担当感,要求改革时弊,振兴古道(韩愈作《原道》),出现了以复兴儒学之道为主旨的古文运动。韩愈与柳宗元虽在复兴儒学之道这一点上并无大的分歧,但在如何复兴儒学之道的方法和理路上却大异其趣。韩愈不仅仍着眼于佛教伦常、费财、夷狄、伤风败俗等说烂了的老问题,而且主张采取简单、粗暴、激烈的排斥方法。他说:“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注:《原道》,《韩昌黎集》卷十一,《基本国学丛书》本,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印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非常熟悉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破不立等话语,而且是不折不扣地按此去“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这种非此即彼的对立二分思维,便把人们的思想行为导向非理智的片面。韩愈为了破佛教,便要勒令所有僧侣还俗,焚烧一切佛教经论文本,把寺院都改为民居。这种偏激的活动,并没有挽儒学于将倒之狂澜,亦未能从形而上的层面斥佛教之弊病。朱熹分析说:“盖韩公之学见于《原道》者,虽有以识夫大用之流行,而于本然之全体,则疑其有所未睹。且于日用之间,亦未见其有以存养省察,而体之于身也,是以虽其所以自任者不为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至其好乐之私,则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于流俗,所与游者不过一时之文士,其于僧道则亦仅得毛千畅观灵惠之流耳。是其身心内外,所立所资,不超乎此,亦何所据以为息邪距诐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注:《与孟尚书》,《昌蔡先生集考异》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朱熹探究了韩愈反佛之所以在“本然之全体”上有所未睹的原因:一是只关注文字言语之工,而忽视形而上学理论的求索和日用之间的存养省察。二是没有自觉超越流俗的意识,在与文士、僧道交游中,不是去探讨佛教学说,人佛学之垒,而见其瑜瑕。他不研究佛学,自不能“息邪距波”。三是视阈狭窄,身心内外,不能包容佛道,吐纳佛道,而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超拔儒学于危机之中。朱熹的批评,可谓中其肯綮。
柳宗元复兴儒学的理论与韩愈迥异,他人佛而主张“统合儒释”。他在回答韩愈指责他“不斥浮图”时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注:《送僧浩初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73页。)柳宗元认为,韩愈谴责佛教只是“其迹”,而非其本,“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注:《送僧浩初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74页。)。这种只及外表皮毛而不涉内在本质的指斥,对于儒学的复兴重建确无太大的意义,它不能开出儒学的新生面。
三
宋明时期,是佛学被理学消融的时期。朱熹对韩愈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他在体验韩愈批佛的教训的时候,接受了柳宗元的“统合儒释”的主张,为自己设计了复兴儒学,重建儒学价值理想之路。其实,出入佛教,而后返诸《六经》,是有成就的理学家的共识,也是他们共同的心路历程。宋明理学的开山宗主周敦颐,一反宋初三先生和李觏简单化批佛的做法,而受道士陈抟的《无极图》于穆修,并受教于释教的寿涯、慧南等。理学的奠基者,他们并不是拒斥佛道二教,而是深入探究佛道思想。张载会见范仲淹时,范氏劝张载读《中庸》。张载“读其书,虽爱之,犹未以为足也,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注:《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81页。)。“尽究其说”,可见其对佛学、道学研究之深刻,而非一知半解。程颢亦“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注:《明道先生行状》,《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38页。)。出入老释几十年,而非一时一年,长期学习道、释,对道释思想学说的把握体认,而非只知其外而不知其里。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讲自己的治学历程:“熹天资鲁钝,自幼记问言语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而未得其处。盖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近岁以来,获亲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注:《答江元适》,《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四部丛刊初编》本。)绍兴十八年(1148),朱熹到临安(今杭州)去参加会试,他的行李中没有带一本《六经》和《语》《孟》,只带了一本宗杲和尚的《大慧语录》,竟中进士。
鉴于从唐到宋的这样的史实,我们可以追究体认:为什么唐到宋初几百年不能把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方法落实下来?为什么在唐代没有实现中国理论思维形态的转变?为什么韩愈不能建构起如苏辙所批评的“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为什么韩愈为护道而拒斥外来文化、哲学及与儒学相异的思想,却不能收“息邪距诐”之效?为什么张载、二程等实现了中国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开创了理学的新学风、新思维?为什么两宋学术成为中国学术的“造极期”?为什么出入释道累年,而后反诸《六经》为理学家所认同?等等。这些诘难,是试图把古今中外的文化、哲学和各家各派及其学者自我都放置在同一个平台上,以开展自由的、平等的对话。在这些诘难中,我们似乎可以体悟出这样几点:
第一,宋明理学家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弘大的气魄、宽广的心胸、久远的视野。为天地、为生民、为往圣、为万世,而不是为一人一时、一家一派,因此,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而不会只局限于儒教,对佛、道二教取绝对拒斥的态度;也不先在地在思想上存在对佛、道的偏见,抱着批佛、道的心态去研究出入佛、道,而是出于真诚的求知的需要,这样才能获得真知识。张载是读《中庸》而觉到犹未足,才去累年尽究佛、老之说的;程颢为求知而广泛地博览群书,出入释、老几十年;朱熹体识到为己之学有未得其处,而出入释、老。他们都是出于为满足强烈的求知欲望,而反复出入——尽究佛老学说的。“出入——尽究”四字,说明他们对佛老之学不是只知其外,而不知其理;只知其“石”,而不知其“韫玉”的。他们对佛、老之学都有很深造诣,而后反诸《六经》。这就是说,他们“出入——尽究”佛、老之学是在与“六经”等儒家学说作比较中,获得新体贴、新体验的。在比较、会通中,他们才深刻地体验到儒学的优缺,佛、老的短长。在儒、释、道三教平等自由地对话、互动中取长补短,融突和合,从而转生为新儒学的理学,实现了从隋唐以来儒、释、道三教之学向理学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并实实在在地落实了三教“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方法。
第二,两宋理学家、思想家在宋王朝“佑文”氛围中,喷发出儒学新生命智慧。他们破除了对《五经》的迷信,冲破了《五经》为圣人之言的种种神圣的光环和权威。质疑《五经》句句为真理的陈词滥调,推倒汉唐以来的“家法”和“师法”,把“疏不破注”、“讳言服、郑非”,转变为“舍传求经”、“疑经改经”。把汉唐的“六经注我”的章句训诂之学转换为“六经注我”的义理之学,使人们的思想从繁琐的、僵化的、教条化的经学桎梏下解放出来。欧阳修著《易童子问》,以《易传》非孔子圣人之言;朱熹以《周易》为卜筮之书,《诗经》三百篇非“思无邪”,而是讲男女之事,《尚书》为历史文诰等,还《五经》以历史本来面目。这不仅为重新诠释《五经》等经典文本开出了广阔的解释空间,而且为“六经注我”的义理之学荡涤了思想障碍,从而挽救了长期以来注疏训诂之学使儒学生命智慧枯萎的危机,并为理学核心话题理、气、心、性找到了新的解释文本的经典依据。他们从《礼记》中找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成《四书》,并抬高《四书》的地位,使之居于《五经》之上,而合称《四书五经》。这种依傍解释经典文本的重新选择,蕴涵着先前理论思维形态的终结,新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它说明先前理论思维形态所依傍解释的经典文本已不适合于新理论思维形态的需要。这就是说,随着理学新理论思维形态的“核心话题”的转变,它所依傍解释的经典文本也必随之而变易(注:为什么要变?请参见张立文主编《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这是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形态转生的具有标志性的两方面,缺一均很难构成新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
第三,理学家出入佛、道,是为了融突和合儒、释、道,落实从唐至宋初所倡导的“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方法,要“兼容并蓄”三教,必须出入三教,对三教有深入的研究和体悟,才能豁然贯通三教,于是程颢体认出:“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注:《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4页。)“天理”二字,其实《庄子》书中和《礼记·乐记》中均已有记载,程颢不会不知道,为什么程颢说是他“自家体贴出来”?显然是他对“天理”这个古老的传统范畴加以重新理解、诠释。这种重新理解、诠释,是一种文本的再创造,范畴的再发现,理论体系的新构建。所以,程颢敢于声称“天理”二宇是“自家体贴”出来的。这个“自家体贴”不仅落实了三百多年来的“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方法,而且实现了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开创了宋明理学的理论新时代。
“天理”(理)作为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融突和合的新哲学概念、范畴,它蕴涵了三家哲学精神。二程说:“释氏多言定,圣人便言止。”定与止有相通之处。《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儒释会通,以辨儒释同异。二程引《周易·艮卦》解止的意义:“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随其所止而止之。”(注:《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1页。)后来陆九渊用佛教的破“我执”、“无我”,破“法执”、“无物”的思想来解释《周易·艮卦》卦辞。据《语录》记载:“复斋看伊川《易传》解‘艮其背’,问某:‘伊川说得如何?’某云:‘说得鹘突。’遂命某说,某云:‘艮其背,不获其身,无我’;‘行其庭,不见其人,无物’。”(注:《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19页。)陆氏则儒释圆融,以佛释《易》。陆王心学和佛教禅宗都讲“本心”,顿悟和无我之境,虽话语一致或相似,但内涵仍异趣。
理学家吸收华严宗的“理事无碍”、“一多相摄”及佛教的“月印万川’’之喻,以阐述“理一分殊”思想。杜顺在解释事理圆融观说:“夫事理两门圆融一际者,复有二门: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心真如门者是理,心生灭门者是事,即谓空有二,自在圆融。”(注:《华严五教止观》,《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编第七函第五册。)朱熹说:“伊川说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注:《朱子语类》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理一”是总合天地万物之理的“一般道理”、“一般水”,分开来,每个事物都有一个理,其用不同。“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注:《朱子语类》卷十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9页。)也可说是朱熹窥得那释氏的道理。“理一”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无差别相,但能随事物而生,随缘而有。
宋明理学中无论是程朱道学(理学),陆王心学,抑或张(载)王(夫之)气学,胡宏性学,都受佛教的洗礼,都吸收佛、道哲学思想。佛教为理学的“核心话题”理、气、心、性的体用论、体认论、工夫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如果不是儒、释、道三教长期融突和合而营造了宽松的、平等的对话、互动的学术文化氛围,作为新儒学的理学是不可能转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佛道之学也就没有宋明理学(注:参见拙作《佛教与宋明理学的和合人文精神》,载《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417-429页。),或者说,没有佛道之学就没有宋明学术的“造极”。
四
佛教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不仅是思维观念上的、内心生活上的,而且是价值理想上的、行为方式上的,同时也是文体形式上的和概念分析上的。宋明哲学家、思想家仿照佛教“语录”体裁,使宋明理学“语录体”大肆流行。佛教对概念、范畴的深入剖析、细致分梳,也使中国固有概念、范畴解释学更趋发展。朱熹病中默诵《四书》,对《四书》中的概念、范畴以绝句的形式,加以解释,如天、学、心、意、致知、中庸、人心道心、命、性、道、情、谨独、静、体用、鬼神、仁、知天命、一贯、居敬、博约、克己、九思、求放心、存心、良知、闻知等。朱熹对“天”的解释是:“气体苍苍故曰天,其中有理是为乾。推原气禀由无极,只此一图传圣心。”(注:《训蒙绝句·天》,《朱熹外集》卷一,《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727页。)对“中庸”解释说:“过兼不及总非中,离却平常不是庸。二字莫将容易看,只斯为道用无穷。”(注:《训蒙绝句·天》,《朱熹外集》卷一,《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730页。)后朱子门人程端蒙(1143-1191)撰《性理字训》,就命、性、心、情等30个范畴作了简要解释,得到朱熹的赞扬。陈淳(1159-1223)继承朱熹之学,特别对朱子的概念、范畴,潜心研究。他对于经书中的要义,如身心性命之端,理义道德之旨,与夫阴阳鬼神之微妙,儒术异流之同异,纲举目张,条分缕析,因流溯源,从末探本,触类引伸,贯穿洞达,而撰成《北溪字义》(有称《北溪先生性理字义》、《北溪先生字义详讲》),把中国对于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推向高水平。
再者,佛教经典大量翻译和深入传播,众多佛教概念演变成汉语的概念,成为中国思想、哲学的常用概念:如实相、如实、觉悟、净土、彼岸、因缘、解脱、唯心、因果、本行、众生、公案等,充实与丰富了中国思想和哲学表述的内涵的意蕴。如“世界”,梵文loka,音译为“路迦”。《楞严经》(四)说:“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法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据此,世界是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后来作为空间观念,被汉语所接受。又如“大众”,梵语Mahasarngha,音译“摩诃僧伽”,意译为大众。《智度论》说:“大众者,除佛馀一切贤圣。”成为汉语习用词。汉语成语有不少出自佛经典故、教义、仪礼、寓言、传说等。如“三生有幸”,出自佛教生死轮回说;“神通广大”,出自对佛的法力的描述;“醍醐灌顶”,出自密教的入教仪式;“味同嚼蜡”、“五体投地”、“顶礼膜拜”等,出自《楞严经》。据有人统计,古汉语中的外来语,90%来自佛教。它融入汉语,但没有造成汉语的“失语症”。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同语言的交往、渗透、吸收、融合,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
五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与今日之鉴。今与古之唐宋,虽情境迥异,然面临重建中国哲学的历史重任则有相似之处。昔日之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转换为今日之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西方文化、哲学和马列文化、哲学的融突和合。古之哲学家,由于无细密的学科分类,因此,他们均兼通文史哲政经。今之学科分类过细;学人只知本学科,对其他学科完全外行;即使是本学科,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知中国哲学的,不知西方哲学、马列哲学;知西方哲学的不知中国哲学;知马列哲学的不知中国哲学等等。这离宋明理学家“出入尽究”佛、道之学的差距远矣,这样如何肩负重建中国哲学的重任?
履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覆辙对待外来文化、哲学,不是出路;走“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老路,是死路一条;唯一的金光大道是走宋明理学家“出入——尽究”释老之途。换言之,即要虔诚地、真心实意地、不抱任何偏见地去累年“尽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列哲学,理解中、西、马哲学的真涵义,把握其真精神。只有这样,中、西、马才能真正地、平等地互动、对话,在互动的融突和合中转生为新的中国新哲学。
隋唐时期,在外来佛教强势文化、哲学的冲击下,传统儒教也几乎陷于失语态势,但儒、释、道互动,并没有出现强势文化、哲学吃掉弱势的儒教文化、哲学,相反地,儒教文化、哲学在不断地吸收佛教文化、哲学的同时,既体认到儒教文化、哲学自身的不足,又明确了“统合儒释”的方向。儒教文化、哲学在佛教“话语霸权”情境中,像韩愈那样试图用卫护儒教话语和思想的纯洁性,挽救儒教主体精神的失落、缺位的危机,不仅收效甚微,甚至面临杀头的危险。相反,较为认同柳宗元开放的、“统合”的中国方式。虽然“统合”可能招致一些学者“阳儒阴释”的批评和讽刺,后来有的学者还把“阳儒阴释”这顶帽子扣在三教融突而转生的宋明理学和合体头上,但亦不能损害宋明理学是中国的儒学,只不过是新儒学而非旧儒学而已。它绍承孔孟的道统血脉,是中华民族传统生命智慧的延续和传统儒学的开新。
当今中国文化、哲学面临中、西、马的互动、对话,我们应该持开放的、平等的、自由的、真诚的、理解的心态,接纳各种文化、哲学,大可不必以强势文化、哲学的普适性来压抑弱势文化、哲学的特殊性,也不可以弱势文化、哲学的地域性、特殊性来拒斥强势文化、哲学的普适性,使古今中外文化、哲学,特别是中、西、马文化、哲学在融突和合中各展风姿,竞放异彩,而后获得中国化新转生。这新转生的和合体(如新生儿)可能被一些人指摘为“阳中阴西”、“不中不西”、“不西不马”的“四不像”,但只要这种转生的和合体,是有益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建设和发扬的,有益于中华民族现代的价值观念、理论思维、伦理道德、终极关怀的建构所需求的,有益于中华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繁荣发展的,有益于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文明之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的化解和协调的,有益于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网络普及化中,中华民族文化、哲学长久持续发展的,便是合理的、合法的,便是中国方式。若以这五个“有益于”为价值标准,我们便可以不去纠缠于中国哲学的失语或不失语,缺位或不缺位,以至于合法或不合法等问题;我们便可以解除种种历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包袱和重担;我们便可以消除与五个”有益于”相违的种种情结、偏见、教条和误解,营造一个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学术自由创新的空间。我所构建的“和合学”理论思维体系,是试图按这五个“有益于”去实现的。尽管“和合学”还是“在途中”,但可以“在途中”与各文化、哲学思想、体系互动、对话,并在融突和合中走向完善。
标签:哲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和合文化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文化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四书论文; 五经论文; 读书论文; 理学论文; 朱熹论文; 原道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中庸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