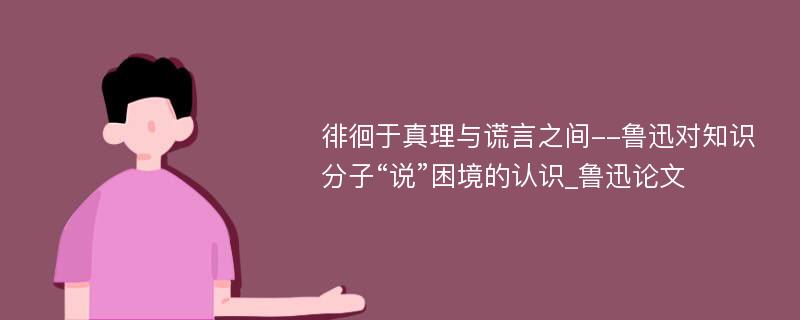
彷徨于真话与谎言之间——鲁迅对知识分子“言说”困境的体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体认论文,真话论文,知识分子论文,彷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以后,各行各业的分工日趋精细。在社会各行业中,知识分子扮演着“批判者”的角色。因之,“思考”和“言说”(形之于文字便成为著作)就成了他们参与社会实践的基本途径,同时,“思考”和“言说”也是知识分子赖以谋生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基本方式。
真正的知识分子总是力求无畏地抒发自我的心声,“任意而谈,无所顾忌”(注: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4卷,1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其“思考”和“言说”的动力都来自于对真理的虔信和忠贞。正如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一文中所言:“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果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注:《鲁迅全集》第8卷,1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鲁迅本人就是一位货真价实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以丰富而深邃的思想,犀利而冷峻无比的“言说”,显示了现代知识分子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强大能量,及其不可替代的社会地位。
鲁迅在他的创作中激烈地批判中国国民装模装样的做戏习性,和不敢正视现实、不敢直而人生的劣根性,激烈地抨击中国文学的“瞒和骗”的传统和自欺欺人的“大团圆”民族审美心理。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向现代文学艺术家发出倡议:“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直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注:《鲁迅全集》第1卷,2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鲁迅本人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新文场”上的闯将。终其一生,鲁迅都力图真诚地生活,真诚地思考,真诚地“言说”。他曾在《华盖集·题记》中这样描述自己的生存和写作状态:“……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注:《鲁迅全集》第3卷,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这是鲁迅真性情的完好写照,也表明鲁迅与虚伪、做作、善于做戏的中国文人传统毅然告别的绝决态度。
然而在现实生活和创作实践中,鲁迅却又经常要面对真话与谎言的二难抉择。他在去世前不久写了《我要骗人》一文,声称要借助“骗人”的方式来获得心灵“暂时的平安”。(注:《鲁迅全集》第6卷,4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可是,真正的骗子从不把自己的心思公之于众,像鲁迅这样公开亮出“骗人”旗号的实际上倒是真正的老实人。况且“我要骗人”本身就是一句大老实话,它对说谎行为具有双重的破坏和解构作用:其一,言说者一旦宣称“我要骗人”,那么他所说的谎话便不会再有人去相信;其二,“我要骗人”内在地包含了对自身具有颠覆力的涵义——既然你是要骗人的,那么你说“我要骗人”也可能是在说谎,其实,你并不骗什么人。
总之,“我要骗人”这句话充满着矛盾和悖论,它富有象征性概括了鲁迅一生的言说和写作状态,他经常在欲说真话与难以道出真话之间摇摆不定、犹豫彷徨;他的作品因之形成了欲言又止、欲说还休的晦涩含蓄的语言风格。而且他小说中的人物也时常陷入既不想说谎,又说不了真话的尴尬境地中。
鲁迅视野中的“谎话”与“假话”
首先,鲁迅认识到谎言具有抚慰苦难者心灵的功能。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对此进行了阐释:“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注:《鲁迅全集》第1卷,159~1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鲁迅发现宗教、哲学等文化形态从终极意义上看,只能起到制造梦境(谎言)、抚慰痛苦的功效。他在写给许广平的第一封信中说:“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沥诉困苦的半生,请他帮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之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注:《鲁迅全集》第11卷,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将来”和“死后”的命运是难以预测的,但人们听了牧师或圣人的劝慰后,便往往会忘却现世的苦难,渐渐步入一个虚幻的梦境。在此,鲁迅触及到了宗教、哲学等文化形态的本质:从某种程度上看,一切文化形态都在编织“谎话”,只不过这些“谎话”往往有利于世道人心,有利于缓解人们在现实中所遭受的痛苦罢了。
其次,在对敌斗争中,为了保护自己和团体的利益,说假话和说谎话也是在所难免的。鲁迅在杂文《半夏小集》(五)中从这一特殊的角度,对真话与谎话问题进行了饶有兴味的表现。这段文章由A和B两个人的对话构成:
A:B,我们当你是一个可靠的好人,所以几种关于革命的事情,都没有瞒了你。你怎么竟向敌人告密去了?
B:岂有此理!怎么是告密!我说出来,是他们问了我呀。
A:你不能推说不知道吗?
B:什么话!我一生没有说过谎,我不是这种靠不住的人。(注:《鲁迅全集》第6卷,5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在这段对白中,A和B两个人的主要分歧在他们对“可靠”这一人的品性有不同的看法,而这实际上涉及的是真话与谎言的问题,A认为一个“可靠”的人对同志、朋友是应该说真话的,但为革命事业着想,对敌人则不妨说假话、说谎话。B则狡辩道:一个“可靠”的人应该对所有人说真话,所以当敌人问他“关于革命的事情”时,他就一五一十地如实相告。
然而,这只是叛徒的逻辑。B对“可靠的人”的界定是有问题的。事实上,一个“可靠的人”不仅不说谎,而且也不应该出卖朋友和同志,不应该背叛自己的事业,否则,他怎么能算是“可靠的人”呢?
鲁迅设置这样一个具体情境,意在表明:在特殊的环境里(如对敌斗争),人是可以说假话和说谎话的。你的敌人根本无视诚实、可靠这些人类的美德,你若跟他们讲什么美德,他们就会利用你的弱点去破坏正义的事业,去屠杀你的同志、朋友。因此,从理论上说,人是应该说真话的,然而在现实中,还得看你的对手是否值得说真话。
再次,在日常生活领域,人们往往因感情、道德等因素的限制而说不了真话。就鲁迅本人而言,他对自己所关爱的亲人、朋友、青少年也并不总是讲真话。有时,他不愿说出自己的心理话,甚至也说点“假话”。
鲁迅在1924年9月24日写给青年友人李秉中的信中透露:“我不愿意使人失望,所以对于爱人和仇人,都愿意有以骗之,亦即所以慰之,然而仍然各处都弄不好。”(注:《鲁迅全集》第11卷,4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旧时代的老人大多希望自己死后能进入天堂,鲁迅的母亲大约也不例外。鲁迅在《我要骗人》一文中垣诚相告:“倘使我那八十岁的老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罢。”(注:《鲁迅全集》第6卷,4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作为一名深受西方现代科学熏染的启蒙主义者,鲁迅自然是不会相信有什么“天国”的存在。然而为了不给处于迟暮之年的老母亲增添精神压力,为了能让老母亲以轻松的心境走向死神,他只能违背自己的意愿,说了“谎话”。
儿童是天真无邪的。鲁迅最喜欢的对象是儿童和月亮。(注:参阅(日)增田涉《鲁迅的印象》,40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即使是对待自己的儿子,鲁迅也能平等相处,坦诚相见。然而,鲁迅也有过对儿童不说真话的经历。作于1936年2月的《我要骗人》一文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令鲁迅“难堪”的往事:有一天,鲁迅去看电影,在影院门口,一名鼻子冻得通红的小学生请求他给灾区的灾民捐款。鲁迅推说没有零钱,小姑娘眼中流露出了失望的神情。鲁迅只好捐了一块钱,小姑娘立刻高兴起来,并称赞他是“好人”。看完电影后,鲁迅又想起了募捐的事,进而联想到成人社会中贪污腐败的丑恶,联想到统治集团的对受灾民众的弹压,于是,他为那位小学生、为他自己而感到悲哀。他认识到自己捐的那一元钱“是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我明明知道着,却好像也相信款子真会到灾民的手里似的。付了一块钱,实则不过买了这天真烂漫的孩子的欢喜罢了。我不爱看人们的失望的样子。”鲁迅觉得自己不该骗那位小女孩,曾打算写一封公开信,说明自己捐钱的本意,向小女孩去消释误解,但因想到没什么地方能刊登这样的公开信,于是只好作罢。一直到深夜12点,鲁迅还被募捐的事搅得心绪不佳,心里像“嚼了肥皂或者什么一样”不舒服。(注:《鲁迅全集》第6卷,4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面对他创作的主要读者群的青年人,鲁迅说话更谨慎一些。他在《三闲集·通信》一文中对青年读者Y君说:“真话呢,我也不想公开,因为现在还是言行不大一致的好。”在信中,鲁迅还向Y君透露了自己不对青年人讲真话的苦衷:鲁迅原先是相信青年人胜于老头子,下等人胜于上等人的;后来经过事实的教育,他痛切地认识到青年人、下等人有时与老头子、上等人是没什么两样的。然而在创作中,鲁迅并没有真实地表现出存在于青年人和下等人身上的“黑暗”,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社会上毕竟是受压迫者,他本人不愿意加入到欺凌弱者的行列中去。(注:《鲁迅全集》第4卷,100、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可见,鲁迅没太多地去揭露青年人、下等人身上的“黑暗”,并不是他刻意要说谎,乃是出于对弱小者的同情。
1932年底,鲁迅在为《鲁迅自选集》所作的序言中重新提及自己在创作中说不得真话的苦处。他说自己在写小说时,一方面免不了要暴露“旧社会的病根”,目的是“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对旧社会的病态过多的暴露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失望情绪。因此,他在创作中总是努力地“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鲁迅把自己的创作称作“遵命文学”。接着他又辩解道:“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注:《鲁迅全集》第4卷,455~4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然而,既然是遵命而写作,就必然会有自我内在的欲求与他人的要求之间或者协调,或者冲突的问题。就难免有希望直抒胸臆与强迫自己不道出内心真实感受的冲突问题。在一些场合,鲁迅煞费苦心地处理自己那些真实地流露悲哀情绪的作品,以免给广大读者带来消极影响。他在1932年编选“自选集”的举措就颇为值得关注。
总之,从鲁迅编选“自选集”的情况看,他选择的作品并非都能代表他的创作成就,并非就是自己所喜爱的作品;他所舍弃的也并非都是他本人不欣赏的作品。他取舍的基本尺度是看这些作品是否有利于社会变革,是否会影响或“毒害”青年读者。看来,鲁迅的行为并不完全受支配于自己的意志。
鲁迅视野中的真话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恶灵》一文中叹息道:“人生中最困难的是不说谎而生活,同时不要相信自己本身的谎言。”高尔基也曾深有感慨地说,“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是为了能够说出和写出真情。然而说出真实情况是一切艺术中最困难的一门艺术”。(注: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真话为什么如此难得?换言之,说真话为什么那么不容易?
首先,真话往往不那么动听,动听的可能是假话、谎话;人们往往乐于接受动听的谎话,而排斥不那么动听的真话——这正是人性的弱点之一。《红楼梦》有诗云:“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言逆耳”揭示的正是真话不那么动听的事实。
鲁迅也曾深有感触地说:“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注:《鲁迅全集》第5卷,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鲁迅是从自身经历出发得出这一结论的,他的锐利无比的言说刺痛了中国社会的神经,因而被论敌称作“绍兴师爷”、“刀笔吏”。鲁迅还注意到了罗素、泰戈尔、萧伯纳、爱罗先珂四位外国著名作家、学者到中国访问、演讲时不同的遭遇:萧伯纳、爱罗先珂不会说客套话,只说真心话而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罗素、泰戈尔对中国文化大加赞美而到处受到礼待。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萧伯纳的遭遇。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乘船周游世界,2月17日来到中国的上海。中国社会各界出于某种心理惯性,期待着萧伯纳也像大多数来华访问的外国作家一样说些客套话和动听的话。然而,萧伯纳这位讽刺文学的大师让中国人的期望落空了,他只按自己的意志说话,他甚至厌恶中国人对他的过分殷勤的欢迎,因而激怒了中国人。大批文人、记者纷纷撰文攻击、指责萧伯纳,把他当作一名“可恶”的人看待。鲁迅的《谁的矛盾》一文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各界对萧伯纳的批评态度:对于这位只说真话而不说假话的英国作家,中国人觉得他“身子长也可恶,年纪大也可恶,须发白也可恶,不受欢迎也可恶,逃避访问也可恶,连和夫人的感情好也可恶。”(注:《鲁迅全集》第4卷,4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其次,真话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权力话语的压制。换句话说,在一个缺乏言论自由的社会里,说真话即是亵渎统治集团的权威,真诚的言说者与权力集团的冲突是必然的。萧伯纳说“一切伟大的真实都开始于冒犯神圣。”鲁迅在《漫谈“漫画”》中说漫画“因为真实,所以也有力”(注:《鲁迅全集》第6卷,2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同样,真话因为真实,所以充满力量,它必然会对权力集团的统治构成威胁。一个道理很浅显但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事实是:由于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不可改悔”的真话的言说者,因此,他们自然难以为权力集团所容,而成为四处碰壁、命运多舛的一个特殊群体。
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一文中揭示了历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他说:“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权力分散,在动物界有很显的例;猴子的社会是最专制的,猴王说一声走,猴子都走了。”鲁迅认为,在现代社会,知识阶级的“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他们必须在“发表倾向于民众的思想”和“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之间作选择;然而,“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注:《鲁迅全集》第8卷,189~1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0年代中期,鲁迅与周作人、林语堂、孙伏园等人一道创办《语丝》杂志,形成了著名的“语丝派”作家群。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中是这样来描述这一创作群体的基本倾向的:“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注: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4卷,167~1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这就是鲁迅所揭示的“语丝派”作家共同的言说和写作姿态。这种自由洒脱的言说方式必然会危及权力集团的利益而遭迫害。段祺瑞“执政”的威吓在前,张作霖“大帅”的封禁在后,《语丝》终于在1927年被查封。《语丝》的命运充分表明:在权力集团的高压之下,知识分子要想保持真诚的言说状态是多么的艰难。
再次,真话在传播和传达过程中很容易被歪曲、很容易走形,这是讲真话的三难。
现代社会是话语传播渠道非常复杂的信息社会,话语(信息)一旦说出,便很难保证它在传播过程中不变形、走样。鲁迅从萧伯纳身上看到了话语被扭曲的命运。他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一文中分析道:萧伯纳在上海发表讲演时,新闻记者们是带着各自的目的去的。萧伯纳“在同一的时候,同一的地方”,所说的“同一的话”在报纸上披露后却各不相同。譬如,在对中国政府的评价问题上,上海的英文报纸说萧伯纳认为“中国人应该挑选自己佩服的人,作为统治者”;日文报纸报道说萧伯纳以为“中国政府有好几个”;中文报纸则振振有词地说萧伯纳声称“凡是好政府,总不会得人民的欢心的”。(注:《鲁迅全集》第4卷,4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鲁迅在《〈萧伯纳在上海〉序》中进一步描述了中外各种利益集团对萧伯纳演讲的五花八门的心理期待:“蹩脚愿意他主张拿拐杖,癞子希望他赞成戴帽子,涂了脂粉的想他讽刺黄脸婆,民族主义文学者要靠他来压服了日本的军队。”(注:《鲁迅全集》第4卷,5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然而,萧伯纳只说自己想说的话,让各类听众的期待扑了个空,于是,他便成了各家报纸争相攻击的对象,他说的话受到费尽心思的“曲解”。鲁迅的《谁的矛盾》写道:萧伯纳在上海演讲时说的全是真话,人们偏要说他是在讲笑话;“他说的是直话,偏要说他是讽刺,对他哈哈的笑,还要怪他自以为聪明;他本来是来玩玩的,偏要逼他讲道理,讲了几句,听的又不高兴了,说他是来‘宣传赤化’了。”(注:《鲁迅全集》第4卷,4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面对这类冥顽不化而且极其无赖的听众,演讲者真诚的言说是根本打动不了他们的。没有合格的听众(读者),言说者(作家)说真话与说假话似乎都没什么区别,这恐怕就是真诚的言说者的悲剧之所在。
更值得注意的是,言说者内心的真实想法在被自我述说(被传达)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着被歪曲的可能,这是“言说”对“思想”的歪曲,是言说者的自我歪曲。“言为心声”揭示的是语言不折不扣地传达内在思想情感的理想的言说状态。而“词不达意”是言说过程中更常见的现象,它表明,语词和意义之间、能指与所指之间横亘的那条鸿沟是难以跨越的。
鲁迅也注意到言说过程中语言对思想的歪曲现象,他的杂文《听说梦》举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自己所做的梦的叙述来说明问题,1933年春节,鲁迅在《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上读到了题为“新年的梦想”的一组征文作品。参加这次征文活动的读者达140多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畅谈了各自的梦想。梦是人们潜在意识的自然流露,它是可信的;而人们对自己的梦境的叙述也应该是可靠的,但是,鲁迅却发觉了梦在被叙述过程中受篡改和歪曲的可能,他在文中分析道:“文章是醒着的时候写的,问题又近于‘心理测验’,遂致对答者不能不做出各各适宜于目下自己的职业,地位,身分的梦来。”鲁迅总结道:“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注:《鲁迅全集》第4卷,476~4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再者,真话可能“毒害”听者、读者,这是说真话之四难。鲁迅多次指出他的作品中所流露的一些真实的思想可能会“危害”读者(尤其是青年人)的可怕后果(如《写在〈坟〉后面》、《华盖集·北京通信》等文章);他甚至觉得自己无意中充当了统治者戕害青年人的“帮手”。他在《答有恒先生》一文中把自己的文学创作与江浙一带的人烧制“醉虾”这道菜的工艺进行比较,认为自己像是那烹制醉虾的厨师,“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注:《鲁迅全集》第3卷,4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在这里,鲁迅对自己真诚的言说之效果进行了深刻的质疑,也把关于启蒙运动之负面价值的思考推向别的思想家难以企及的高度。
在真话与谎言之间进退维谷的“失语”状态
作为一名现代社会诚实的言说者,说假话、说谎话自然是鲁迅所不愿意做的事。然而,说真话又有这么多的困难,于是,他陷入了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他往往以沉默的方式来面对真话与谎言之间的二难选择。可是,沉默长久了,他便可能丧失言说的能力,这又是他所不愿接受的结局。鲁迅正是这样一位不断在真话与谎言之间作二难抉择,时常为“失语”的痛苦所煎熬的言说者,而且他在创作中也经常表现着“言说之难”的主题。
小说《头发的故事》的主人公N年轻时曾到国外留学,为了行动的方便,他剪掉了辫子。回国后,他因没有辫子而饱受同胞们的嘲笑和欺辱。清朝末年,N先生在一所中学担任“监学”,有一天,几位受革命思想影响的学生来到他家,向他征求是否剪去辫子的意见。
从理论上说,N先生应当持“没有辫子好”的观点;然而,他本人过去的经历却促使他不赞成学生剪辫子。这样,N先生在逻辑上便走进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困境,面对纯洁、真诚的青年学子,他最终不知该说什么为好。
其实,小说主人公N先生这番遭遇正是鲁迅本人曾亲身经历过的。鲁迅晚年写的杂文《病后杂谈之余》比小说《头发的故事》更详细地表现了他本人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既不愿说谎,又不能轻易说真话的痛苦:1910年,鲁迅在绍兴中学提任“学监”一职,他因为在日本留学时剪去辫子而被故乡绍兴的民众看成“假洋鬼子”,受尽各种嘲骂。这一年,绍兴学生中兴起了剪辫风潮,鲁迅劝阻学生,学生们就推举出代表来同他论辩。学生代表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鲁迅不假思索地答道:“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注:《鲁迅全集》第6卷,188~1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部份学生认为鲁迅自己不留辫子,却又反对学生剪去那根“猪尾巴”,是一个“言行不一致”的人,并因此而有些看不起他。
像小说中的那位N先生那样,鲁迅掉进了自己设立的逻辑陷阱里。从剪辫子事件发生的1910年,到写作《头发的故事》的1920年,再到写作《病后杂谈之余》的1935年,鲁迅在25年中一直为自己的“言行不一致”而难以抹去心灵中的一道阴影。这个剪辫子事件也是鲁迅一生言说状态的集中写照:他总是难以摆脱真话与谎话互相纠缠给他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折磨。
鲁迅在小说《伤逝》、《祝福》等作品中艺术地揭示了现代知识者言说的困顿局面。
《伤逝》以大量的篇幅展现了涓生所面对的二难选择:由于情感的变化,涓生已不爱子君,他想把真情坦言相告,但每当看见子君“孩子一般的眼色”,便只好装出一副很愉快的样子。此时的涓生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涓生想说出自己已经不爱子君的真心话,不过,他怕真话一说出来便会驱使子君走向死路;另一方面,不说出心里话,涓生又觉得自己是个虚伪、怯懦的人,这与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是相悖离的。最后,涓生还是说出了真话,果真导致了子君的死亡,于是他谴责自己“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了子君,他认定自己是一个“卑怯者”。从此,涓生决心“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作他的“前导”。(注:《鲁迅全集》第2卷,127、1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在小说《祝福》中叙述者“我”与祥林嫂在鲁镇大街上的那番对答,同样显示了现代知识分子在真话与谎言之间游移不定的精神状态。已经沦落为乞丐的祥林嫂问“我”:“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这一问题问得很突兀,令“我”十分惶然,“我”只好告之曰:“也许有罢。”祥林嫂接着便问:“那么,也就有地狱了?”这又令“我”猝不及防,只好吱吱唔唔说:“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祥林嫂追问道:“那么,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的?”至此,“我”已经知道自己根本无法解决祥林嫂的疑惑,只好用“我也说不清”来搪塞,并匆匆逃离现场。(注:《鲁迅全集》第2卷,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我”本来是不会相信“灵魂”、“地狱”之说的,然而为了给祥林嫂一点精神安慰,只好说假话,说也许有灵魂和地狱。当祥林嫂透露了她想到地狱里与死去的亲人见面的心思后,“我”开始担心自己所说的安慰话会有害于她。因为祥林嫂除了想去地狱见她可爱的儿子阿毛外,还害怕自己会被锯成两半分给两个丈夫。于是,“我”便用“说不清”来摆脱自己与祥林嫂的干系。在一位目不识丁的女乞丐的盘问下,这位现代知识分子“我”竟然丧失了说话的勇气,只好落荒而逃。这是非常具有象征意味的一幕,它揭示了知识分子言说的自相矛盾和软弱无力,揭示了启蒙运动的局限和困顿。
鲁迅自己就像《祝福》里的“我”那样害怕自己的言说“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他坦率地说道:“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有时,他甚至认为,“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注:《鲁迅全集》第2卷,2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这就是说,当他不能说真话而又不愿以假话、谎话骗人时,只好选择沉默。
沉默有时令鲁迅更加自在一些。在沉默状态下,他至少不必在真与假之间作出抉择。因而,鲁迅在《野草·题辞》开首写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可是,沉默终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言说毕竟是知识分子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除非选择死亡,否则,只要还活在世上,一位现代知识者便不可能永远保持沉默状态;换言之,如果真正得了“失语症”,知识分子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于是,鲁迅的《立论》就有了解决真与假矛盾的新办法,这就是“打哈哈”的方法。这篇精致的散文诗为我们设定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境:“我”梦见自己正坐在小学课堂上写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老师认为立论很难,他举例说:有一家人生了一个男孩,全家都高兴坏了。满月时,家长把孩子抱出来给贺喜的客人看。一位客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另一位则说这孩子将来要当官。他们的祝福令家长很感激。第三位客人发话了,他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话音刚落,他就遭到众人的一顿毒打。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是真话,说他将来会富贵却可能是不真实的,可能是客套的谎话。说谎的人得到感谢,说真话的却遭毒打。那么“我”既不想说谎,也不愿挨打,该怎么办呢?老师毕竟是老于世故的,他告诉给“我”一个“良策”:“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He He!he,he he he he !”(注:《鲁迅全集》第2卷,2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这位先生口授的立论“秘诀”简单而实用,归结起来说,就是在立论时不要明确地表态,要学会打哈哈,要掌握骑墙的本领。简而言之,要学会世故。
然而,正如沉默不能彻底解决真话与谎话的二元对立一样,老于世故的打哈哈方法同样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直话与谎话的矛盾,它只能使真诚的言说者沉陷于真与假之间的言语沼泽而不能自拔。像大多数现代知识分子一样,鲁迅还必须在真话与假话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而选择就意味着知识分子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为自己的言说承担一切后果,更意味着他们将面对接踵而来的无数新的选择,将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真话与谎话之间的两难境地中。
标签:鲁迅论文; 萧伯纳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文学论文; 头发的故事论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论文; 读书论文; 祝福论文; 鲁迅中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