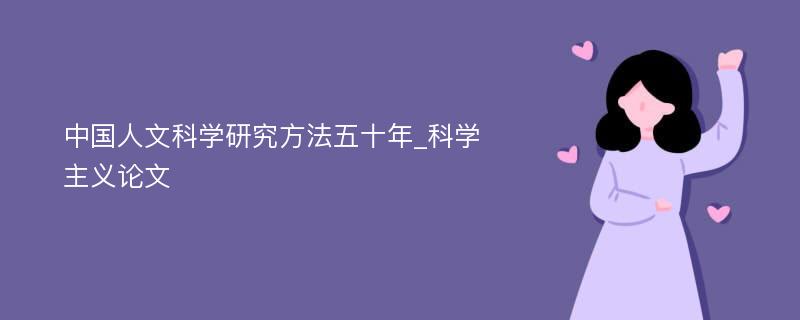
中国人文科学研究方法五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科学论文,中国论文,五十年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后五十年,中国人文科学研究方法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为限,这个阶段主要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方法成为研究人文学科的唯一、至上的方法;第二个阶段以70年代末至90年代为限,这个阶段主要特征是对50—70年代错误否定其它研究方法、歪曲运用马克思主义行为的检讨,并逐步建立起健康、理性、宽容的人文科学研究方法。五十年来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演变不仅反映出中国人文科学本身的发展状况,更显现出人文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为此,通过对五十年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回顾,对于正迈向21世纪的中国人文科学研究言,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50至70年代: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应用及其向教条的转化
20世纪50—70年代,马克思主义方法演变为一切方法的代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方法如物质决定意识、阶级分析、一分为二等被人文社会科学界当作研究学问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而其它方法却遭到了排斥。
1951年,红学家俞平伯出版了《红楼梦研究》一书,1953年,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但由于俞平伯的研究方法仍然是以考证为主的方法,着眼于对《红楼梦》赏析性分析。这种方法与当时以阶级分析为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大异其趣。因此,俞平伯文艺观受到批判。批判者认为,俞氏主要错误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则方法,抹杀了《红楼梦》中的阶级意识,注重写生主义而忽视了现实主义。质言之,俞平伯的方法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方法、科学主义方法。50年代初,胡风的文艺观也受到了批评。胡风的主要观点是:强调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和关怀精神、强调文学艺术中心环节是实践,认为只有投身实践,才可创造好作品,强调艺术的个性在创作中的地位。但这些思想被认为是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资产阶级唯心论,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否定作家到人民群众中去的必要性,否认小资产阶级改造的必要性,否认民族文艺的差异性。因此,胡风的现实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其研究方法是唯心主义的、超阶级的。这些批判,从人文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看,是30年代以来对科学主义方法批判的继续,马克思主义方法由此在人文科学研究上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和应用,但马克思主义方法从此被人弄得渐显出霸气来。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到60年代上半期,又形成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学术批判。即将马克思主义方法停留在表面的继承和对非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绝对排斥。在哲学领域,冯定认为,“人的认识本来是有相对性的;因而对已往的、现存的理论多少抱些怀疑是必要的。”这种观点被认为是陷入了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普遍性也形成了否定。在文艺领域,这个时期受到批判的是巴人。1957年,巴人的《论人情》一发表,便受到批判。1959年,巴人《文学论稿》再版,集中表述了巴氏文艺观。巴人被批评的观点主要有:其一,巴人认为对一个作家有吸引的东西,除了作家所处的历史社会环境及其阶级地位外,还有人类一般的共同性。这种观点被认为是宣扬抽象的人性,用人的自然本性代替其阶级性。其二,巴人认为,文艺作品之所以能激励人,传之久远,就在于它的人情,因为人情是人人相通的基础。这种观点被认为抹杀了文艺的阶级性,因为在当时的批评者观念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根本就没有相通的人情。在历史学领域受到批判的是周谷城。周谷城1962年发表了《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文中提出“时代精神”问题。主要观点是:各个时代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成为每个时代的时代精神;阶级社会则由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等各个“不同阶级”的“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成为当时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是“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的思想。这种观点被认为是“把时代精神抽象成为超阶级的各种意识的汇合,是违反科学分析,违反事实的,属于脱离阶级的历史唯心主义”,在方法上,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代替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因而是赤裸裸的阶级调和论、阶级合作论。
20世纪50年代下半叶至60年代上半叶,从巴人的“人情文艺”到冯定的“对现有理论存疑是必要的”,再到周谷城的“精神大汇合”,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看,这些观点事实上体现了科学主义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合流。注重事实的分析,注重个别的细节,注重普遍情感,注重非阶级因素,正是科学主义方法的主张,也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疏忽。这些科学主义方法特征无不体现于巴人、周谷城、冯定的思想中,因而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能够超越当时仅停留在字句上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所谓“人情文艺”是建立在人的经济生活基础之上的,而关于“历史精神的汇合”,恩格斯不是有过平行四边形合力论吗?冯定关于真理的相对性表述,本质上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理论的“真传”。难怪,他们没有一个人不为自己受到无理批判而反驳和叫屈的。实际上,这一系列批判,反映出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理解把握的教条化。在此,我们有必要对科学主义方法自马克思主义方法进入中国后,便受到一些人持续批判的原因作一概括性分析:科学主义方法提倡怀疑、主张实证,反对盲从,这与一开始便显独断倾向,到以后终于成为一霸的伪马克思主义方法在精神上是对立的;当然,它本身固有的某些局限,如对政治、主义不太关心,也是被批判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在50年代至60年代中叶科学主义方法、传统方法受到批判的氛围中,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还有相对独立的地位,那么到了“文革”时期,人文科学研究方法则基本上丧失了它的地位,即便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也受到歪曲。在哲学上,将“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改造为“主观第一、客观第二”的唯心主义、唯意志主义,认为办事情就是从主观到客观、从思想到实际,因而所谓学问研究可以随意创造观点、随意编造结论;鼓吹打倒一切的“斗争哲学”,否认事物的同一性、统一性,因而学术研究就是寻找阶级敌人,然后批倒批臭。在文艺上,所有文学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大搞两条路线斗争,文艺完全成为政治的助手。在历史学领域,大搞影射史学,研究历史纯粹为了现实政治需要,为着现实政治需要的目的,历史可以随意更改、篡改;鼓吹英雄史观,别有用心地鼓吹英雄,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显见,“文革”时期的人文科学研究完全陷于停顿状态,马克思主义方法被随意歪曲、夸大,没有起到推动人文科学研究的作用。而之所以成此局面,政治对学术的彻底渗透是根本原因。从研究方法本身角度讲,马克思主义方法已经完全走向异化;从政治与方法关系言,则是政治对方法的全方位彻底的控制。哲学在西方中世纪成了宗教的婢女,而马克思主义方法在“文革”十年成了政治的婢女。
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国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全面复苏
自70年代末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逐渐展开,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随着社会发展的任务从革命转向建设,从政治转向经济,政治斗争、阶级意识出现了淡化的趋向。在这种背景下,人文科学研究逐渐找到了自我,对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限制、约束也逐渐松懈,从而使这个时期人文科学研究方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些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50—70年代扼杀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之检讨。在50—70年代,科学主义方法受到批判,传统方法被赶出人文科学领域。这些方法有实验法、历史法、存疑法、比较法以及整理、考证和鉴别方法等。进入80年代之后,学界重新肯定了上述方法的价值。如1983年出版的《历史研究理论与方法》中,作者们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基础上,肯定整理、考订、鉴别等方法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性。张岱年在1983年出版《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对于校勘、辨伪、调查、训估、考证、诠次等包括中国传统研究方法和科学主义方法在哲学史研究中的作用做了肯定。1991年出版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对实验方法、数学方法在人文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作了明确的肯定:“不能把社会科学方法看成单一结构,即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而排斥其它具有社会科学方法特色的纯方法。如实验方法、数学方法、系统方法等纯方法,也完全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表明这个时期的中国学术界对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认识、理解日趋合理。
(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被歪曲使用的反省。通过对50—70年代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考察,我们大致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走向教条化的线路作这样的描述:50年代初是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否定、批判科学主义方法和传统方法的时期;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较稳定应用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则是马克思主义方法教条化、歪曲化颠峰期。对于马克思主义方法在50—70年代的应用状况,70年代末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界已开始反思。学者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方法必须与具体学科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方法不应该取代其它研究方法在人文科学研究的价值。如,陈涌认为,“文艺学的方法论,需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文艺的特殊本质结合起来。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把文艺的特殊本质规律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形成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理论和方法。”李达顺等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是高度抽象、应用于所有领域的方法,但它却不能取代各门科学方法论和具体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特点,仅仅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它既不能代替其它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关系,也不能概括西方其它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关系。”如上反思表明,80—90年代的人文科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位置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歪曲、教条化使用作了较为彻底的反省。陈传之认为,50—70年代的“文学理论研究,常常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指导与文学的本体研究及其价值评析相分离,习惯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原理或个别观点、结论,进行简单、机械地演绎推论,以致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对于人们深入探索文学的奥秘与规律的指导作用,甚至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运用的简单化和庸俗化。”如上对马克思主义方法教条化、歪曲化应用的反思是深刻的,它为马克思主义方法在将来的人文科学研究中的正确应用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确立起健康、理性、宽容的人文科学研究方法态度。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文社会科学界在接收、吸收新的科学方法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容性和灵活性。这首先表现为对一切有价值的方法吸收接纳的态度。1991年出版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已包含选题方法、社会观察方法、实验方法、统计方法、系统科学方法、预测方法和决策方法等。可见,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对研究方法有了一个理性、健康的态度。第二表现在对各种研究方法关系的正确理解上。如有人指出,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应该适合研究对象的特点。因此,不能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照搬过来硬套。第三,表现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使用。如在哲学研究上,有用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方法研究哲学思想体系、哲学范畴的;也有用协同学、耗散结构理论研究哲学思想的。在文艺学研究方面,研究方法也日趋多样化,有心理学的,接受学的,直觉主义的,结构主义的,有诠释文艺学,也有系统论的文艺学研究等等。在历史学领域,不仅有社会学、人类学等实证性很强的方法,也有数学、计算机等工具性方法。
总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人文科学研究方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概括表现为:第一,对马克思主义方法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通过对50—70年代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化、歪曲化使用的反省,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方法已经有了较准确、客观的评判,这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本身还是对中国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未来发展都将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第二,对马克思主义方法与具体学科研究方法关系理解的理性化。认为马克思主义方法是一种宏观的方法论,对具体学科研究有指导意义,但却不能取代具体的学科研究方法,二者应相互补充。第三,注意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差别。指出要谨慎使用自然科学方法,不能随便地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强加在人文科学研究上。第四,在主张大力吸收现代西方新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指出了使用这些方法时要注意的问题。
五十年中国人文科学研究方法嬗变的启示
对于正迈向21世纪的中国人文科学研究,20世纪50—90年代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演变似有如下启示:(1 )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繁荣与科学技术发展有着密切关系。20世纪初的科学主义方法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物,其方法特征也体现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特征:归纳、分析、实证、怀疑;而70年代以来,一些新的方法,如精神心理学、系统论、信息论、协同学、耗散结构理论等,则是20世纪中后期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因此,如果要繁荣人文科学方法,我们必须努力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并时刻关注自然科学成果。(2 )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兴衰与政治理性的干预有着密切关联。20 世纪中国人文科学研究方法, 之所以出现50—70年代衰落状况,就在于方法的意识形态化。20世纪初至40年代,马克思主义方法尽管也是一种“主义”,但仍属“方法”性质。50年代以后,传统方法、科学主义方法被排斥与批判,以及“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方法被教条化和歪曲化从而导致了人文科学研究的空白。因而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将是21世纪中国人文科学繁荣的关键。(3 )人文科学研究方法具有“价值中立性”。方法是“中立”的,是超越的,它对任何人、任何阶级的态度是一样的。正所谓“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在发展与繁荣人文社会科学时我们必须时刻意识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