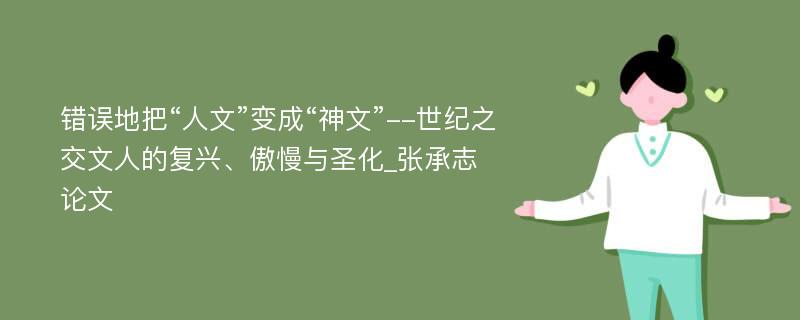
错把“人文”作“神文”——世纪末文人的自新、自大与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末论文,自大论文,文人论文,人文论文,神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新篇
故事从闹了个满城风雨的贾平凹开始。
真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废都》所引起的愤怒可以称之为“公愤”。谁也没想到那么个老实巴脚的陕西娃子贾平凹一改“文化精英”之本色,写起了那到处是“□□□□□□”,后面又跟着些“……”的小说,而且直言不讳地告诉人家“此处删去××字”;谁也没有想到一向温文尔雅、藏而不露、与人为善、暗送秋波乃至相互抚摸的文人们陡然一改和颜悦色之面目,板起脸来都成了道德家、宗教家(如果也有这一“家”的话)和热爱社会伦理工作的什么什么家。总之,文人们在贾平凹的面前摆起了谱,端起了架,声色俱厉地开展了一场文化批判暨道德自新运动,在批评贾平凹之余,也对自己进行了伦理、道德、艺术、宗教的洗礼活动,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之后,指着贾平凹和那百读不厌的《废都》说:“看,丑陋的艺术家,丑陋的中国人。”瞬间自己的形象高大起来,俨然成了民众的代言人、真理的传教士、文化的守灵者。
文人们之所以能够借助于《废都》“自新”,那是因为《废都》是面照妖镜,每个人往它前面一站,就立刻现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兽性、人性与神性(如果也有人性与神性的话);意识里的光明和潜意识里的黑暗;平时见得人的和说得出口的,见不得人的说不出口的……于是乎,该掩饰自己的快快地掩饰,该显示的快快显示……
这些文人自称或被称为“人文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英雄主义者”、“精英分子”……他们的自我高尚化、圣洁化是始于对贾平凹的批判,在这场纯粹的民间文化批判运动中,差不多每一个批判者都不失时机巧妙地表现了自己的纯洁、高尚、精英的美好一面,都表达了精英分子对于大众文化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同时捎带着也进行了灵魂的自我反省。凭心而论,贾平凹的《废都》无论站在什么立场上,从什么角度看,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现在看来,小说本身存在的问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那些精英们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他们通过这部小说的批判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精英们把贾平凹当成了“魔鬼的辩护士”,他们通过对“魔鬼的辩护士”的讽刺挖苦,达到一次心灵的洗礼。这是一种宗教活动,道德洗礼活动,而不再仅仅是一种文化批判和文学批判。
人们哀叹贾平凹已经义无反顾地“堕落”了,由一个举世公认的“精英作家”“蜕变”成一个通俗作家,他的精英“心灵业已死亡”,阅读《废都》“是一次令心情黯淡的凭吊”。他“径直投合了大众文化阴暗而卑微的心理”,因为他没有“对生命的正视、对人生的尊重”,没有“对历史真义的体味与敬畏”,“人、性爱、情感与斗争都变成了一种肮脏的玩弄”。“为什么几年间贾平凹就由一个纯粹而敏感的严肃作家变成了一个趣味低级的通俗作家?……我们看到的是文人阶层英雄主义和理想的丧失,当民族面临着巨大危险的时刻没有文人表现出对民族命运深切的关怀与体察,当需要声音的时候没有先知在旷野呼叫;我们看到的是文人们个体生命的苍白,没有执著的信仰,没有卓立独行的个性,没有对人间万事万物的多情、容纳与超越,他们失去了探寻真谛的勇气,甚至失去了周密而新鲜地叙述一个故事的耐心和能力。文人们陷了一种可耻的麻木之中,鲁迅所代表的现代文人的人格成就已经忘却:既没有那种体现社会责任感的呐喊,也没有那种体现个人丰富性的彷徨。文人们的情感、意象和语言已经失去了对人们的感召力和感染力,只能在没有光荣的、小市民的市场上卖个好价钱。《废都》及其作者的状态使我们如此强烈地印证了这一切认识,唤起了我们作为一个文人的羞耻和愤怒;如果我和我的批评界同仁对贾平凹使用了比较激烈的言辞,那也不是针对贾平凹个人的,这种谴责之中就包含着我们对自己的谴责,包含着我们对文人阶层命运的深刻恐慌”①。
不仅如此,还有把《废都》直接了当地看作是“一部”‘嫖妓小说’”的②。论者以为《废都》“对于东方奇观的展示完全是以一种欣赏的,甚至是得意的轻松的姿态对待的”,谴责它没有好好地保守“性”的秘密,无所顾忌地把它昭示于天下。“低俗的‘性文化’屡禁不止,发行量惊人,说明了我们赤裸裸的‘性描写’,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大概是空前的。‘性’的隐秘性和其它涵义在这里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人生理需求上的放纵和刺激,从这个层面上说,它仅仅具备了商业的品格。”因为展示了东方的神秘文化,这“使这本称为‘城市小说’的作品充满了陵墓的阴森气息”。“时至今日,卖淫嫖娼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贾平凹正是在这样的世俗风气下赤裸裸地描述性的行为,只能说是在怂恿张扬大众俗欲的享乐倾向”。“在《废都》中,男女双方都仅仅是作为性的对象存在,其过程太简化了。既没有维特式的青春冲动,也没有罗米欧与朱丽叶式的浪漫,所剩仅仅是为了欲望而直奔‘主题’。在这里小说和它的主人公都明显地存在着“嫖妓意识’。”
说得最有文彩的是扎西多。“这《废都》却看得人有些心惊,一水的县城流氓、省城遗老,一杆子的男盗女娼、名流野客、贪官污吏,一街的死猫烂狗、乌烟瘴气,又还有用黄汤儿淫水洇出来的桃花坞。”“反应是炸了锅。有人觉得它老气横秋、空虚无聊,有人说它春秋笔法,是当下人欲横流的大陆社会的一面照妖镜。淑女们为性描写的猥亵下流而愤怒,女性主义者为大老爷们小贱胎的陈腐观念而震惊。通达的说它是大陆文化多元局面下的一绝,感伤的说是大陆书生末路的悲歌;有人为那一串卖关子的床上戏‘天窗’而想入非非,还有人读出了大量的政治影射……把所有这些搅拌到一起,这书的味道也就出来了。”③不难看出,人文主义者和精英主义者从《废都》事件中所获得的最大的一个教益是“严精英与通俗之大防”,并自觉地强化自己的精英意识和贵族意识,这种贵族意识和精英意识是在与大众的比较中凸现出来的,或者说是在给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泼了许多脏水之后才凸现出来的。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无论在古代文学史上(想一想冯梦龙)还是现当代文学史上(想一想王朔),都不乏精彩绝伦之笔,无论在消解正统意识还是在拓展审美空间方面都功不可没,这是有目共睹的。不过,很不幸的是,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成了人文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假想敌,正是在对这样的假想敌仇视中,发泄自己被社会孤立之后的愤恨,表现自己的失落之后的惆怅,优雅地净化自己的灵魂,进而坚定自己的斗志。不过假想敌永远是假想敌,通过对假想敌丑化而做出的一切也永远是虚幻的,如通过一系列假想在精英与大众文化制造了一连串的二元对立:低俗与高尚、污浊与纯洁、蜕变与升华、阴暗与光明、卑微与崇高、正视生命与无视生命、尊重人生与污蔑人生、体味敬畏历史与游戏亵渎历史、情感的高尚处理与性爱的肮脏玩弄、麻木与敏感、低极趣味与高雅品质、痞子阶层与文人阶层、英雄主义与狗熊主义、理想主义与物欲主义、关怀民族命运与对于民族命运麻木不仁、先知与群盲、执着的信仰与生命的苍白、独立的个性与混然的无知、高尚的觉醒与可耻的麻木……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在这场为人文精神、理想主义“召魂”的过程中,精英分子们总是搬出鲁迅来为自己壮胆,请出鲁迅的亡灵来为自己寻求合法性。鲁迅固然有体现社会责任感的呐喊,也有体现个人丰富性的彷徨,但他又何尝动辄以精英分子自居,特别是在晚年他不乏为大众文化献身的道德与热情。大众文化是他们的假想敌,而鲁迅则是他们的“假想友”。
可以说,作为新时期以来第一场大规模的民间文化批判运动,对贾平凹及其《废都》进行近似于“墙倒众人推,鼓破乱人捶”式的批判,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冲撞、拷打、侮辱、施虐,它不仅是针对着贾平凹的,也不仅是针对着一般的大众文化的,更是针对着每个批判者自己的。这是一场精神的自新运动,顿时成了一种时尚、标志、信仰、仪式。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尝到做为一个批判者的快感、虚荣和自我幻想,能够证明自己的非同寻常,证明自己有理想、有道德、有信仰、英雄主义、大公无私、勇于奉献……;每个人都把自己对于社会文化的不满巧妙地转移到了贾平凹这里,把贾平凹及其《废都》当成了社会文化罪恶的替罪羊。
可爱之至。
自大篇
然后是理想主义、人文主义、英雄主义、精英主义……的大肆自我美化。
理想主义者有两义,一是与实利主义即物质主义相对立的,专注于精神生活的价值,视精神生活的满足为人生真正幸福之所在;二是与虚无主义相对立,指信仰某种绝对精神之价值并对其有执着的追求。凭心而论,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向有美名为人称道,但问题还是无法回避:这“理想”、那“英雄”是否要经过理性的过滤?如何证明理想、英雄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如何证明它的唯一正确性?
至于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那总是对于一定的社会环境的具体回应。相对于西方的基督教来说,它指的是人的世俗生活;相对于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来说,它指的是人的情感精神活动的丰富性、多样性与不可化约性;相对于物欲主义来说,它是精神的纯洁与高尚……这里所谓的“人文”只是文人们臆想中的理想的文化环境或生存状态。至于什么才是理想的文化环境和生存状态,那可就是人言言殊了。或曰人文精神是对于人的存在状态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或曰人文精神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即一场人文精神与反人文精神的较量,传统儒学、宋明理学即非人文精神的代表与象征;或曰人文精神就是人性完善;或曰人文精神是一种生命的承诺和道德操守。④
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张承志的理想主义。
张承志自谓“都市的牧人,无马骑手,公开的教徒、自由的作家”⑤。
——作为一个“都市的牧人”,张具有浓得化不开的都市情结。他说自己“肉身置于闹市,灵魂却追逐自然。”⑥北京是“人粥”稠密、腐臭卑鄙、他落草为寇的边远地带。他向往的是“自然”,就是他寄寓灵魂的圣城,那就是蒙古大草原、新疆、北方的大河、回民世代居住的黄土高原。这是他的家园,即他的“黄泥小屋”。都市与自然是截然对立的,闹市是一个符号,它代表的是完全的制度、繁华的世俗文明、实证主义的学问、孔孟之道的迂腐。自由也是一种符号,代表的是苦难美、牺牲美、异端美、艺术美,草原是母亲,大河是父亲,西海固农民的质、神秘的哲合忍耶,苏菲主义。他憎恶物化的现实,抵御文学的商业化、世俗化潮流,自诩为良知、正义、理想、世道、人心的保护神。
——作为一个“自由的作家”,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天马行空的艺术家,一个都市、现行制度、文化权威和物质主义的叛逆者,一个充满了侠肝义胆的血性汉子。不过这倒有些“假冒伪劣”之嫌。其实他是一个哲合忍耶的教徒,象《水浒》里的好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一样,他反对的权威只是现代的都市文明和汉族人的孔孟之道,并不怀疑自己的信仰。他说:“对于追求精神充实,绝对正义和心灵自由的一切人,对于一切宗教和理想,对于一切纯洁来说,中国文明的核心即孔孟之道是最强大的敌人”,他“否认孔孟中庸的人生形式和艺术”,认为“中国需要公元前后那大时代的、刚刚混血所以新鲜的‘士’;需要侠气、热血、极致。”⑦说到底,只有哲合忍耶才是济世的良方,才是人生的指南,才是价值的源泉。
——作为一个“公开的教徒”,他不遗余力为自己制造超凡脱俗的圣者、救世主的形象。他自认自己面对的形势极其险峻:大众文化勃兴、英雄道路荒芜、理想主义终结,……他坚信自己是世道人心的唯一拯救者,是物质主义世界中的最后的英雄,而不仅仅是文学上的朝圣者。他“关注生命存在的处境问题,特别是关于生命、处境与美的问题”⑧。在哲学上,他是一个彻底的反知主义者,赞扬“知识的终点,是主的认知”。他对于世界的体认,对于真理的把握,凭借的是直觉,即非功利、非理性的审美体验,强调当下达到审美体验、生命、处境、宗教、美的境界。他所谓有哲合忍耶的灵魂也不过是生命、处境与美的浑融一致。他不仅强调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唯美主义者、一个浪人、一个虔诚的圣徒,还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教主,一个宗教领袖,承担着阐发哲合忍耶教义的天职,要宣扬哲合忍耶派真主的“口唤”。他以教主的口吻说:“不应该认为我描写的只是宗教。我一直描写的都只是你们一直追求的理想。是的,就是理想、希望、追求——这些被世界冷落而被我们热爱的东西。”“……到文化崩溃的时候,今天的知识分子都将被追究罪责,我希望我不成为罪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将自己从他们这中划出。”这就是最后的审判,也是文化危机论、中国危机论的最为宗教化的表现。总是有人在玩那“狼来了”的老把戏,八番十次高吼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崩溃,但谁也没有张承志的这一喊“震聋发聩”。可实际上,所谓的文化危机,实际上就是精英文化的危机,就是在文化舞台上找不到自己的危机,喊一声狼来了,无非是希望有人把自己再请回到那个舞台上,让时代大众的聚光灯再一次照到自己身上而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策略呢?
不说也罢。
圣化篇
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是孪生兄弟,理想主义的极致是理想的宗教化,英雄主义的极致是英雄的神圣化。
理想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在得到了从“理想”与“人文”的真传以后,并不想秘之独享,他们不仅要“独善其身”,而且还要“兼济天下”,以那“理想”与“人文”普度众生过苦海。这就有了所谓的“文人操守”问题。
可当一个文人把自己置于可以大谈文人“操守”问题的位置上时,他本人的操守可能就很成问题:是谁赋予他这样的权力对于别人的操守问题加以评论的?
好在张承志决不是以一个一般的文人身份说话的,他在《以笔为旗》的文章里说:
“我没有兴趣为解释文学的字典加词条。用不着论来论去关于文学的多样性、通俗性、先锋性、善性及恶性、哲理性和裤裆性。我只是一个富饶文化的儿子,我不愿无视文化的低潮和堕落,我只是一个流行时代的异端,我不爱随波逐流。
“那怕他们炮制一亿种文学,我也只相信这种文学的意味,这种文学并不 叫什么纯文学或严肃文学或精英现代派,也不叫阳春白雪。它具有的不是消遣性、玩性、审美性或艺术性——它具有的,是信仰。”⑨
张自信自己是一个“富饶文化的儿子”,“不愿意无视文化的低潮与堕落”,“是一个流行时代的异端”,“不爱随波逐流”,以神的法眼看待这个末世,以圣的口吻来谈论这个末世,真让我们这些个芸芸众生无地自容。有信仰当然好,可信仰什么?你所信仰的真值得大众都信仰吗?
张承志说:“我之所以拼了命写《心灵史》,是因为我发现在中国这片国土上,居然有这样一群哪怕是死光了也要追求心灵信仰的人,这对中国文化的意义实在太大了。中国人现在最可怕的就是没有信仰,我不是要求每个人都信仰宗教,但人总要信一点什么,哪怕搞甲骨文的信仰甲骨文,搞语言实验信仰语言,都要纯一点,不能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像旧衣服一样随时可以扔掉。”⑩
在我们这些芸芸众生看来,中国是否存在那样一个为了信仰而死光的一群固然暂时还是一个疑问,但没有疑问的是中国现在最可怕的肯定不是没有信仰,而是总是处于盲信的境地,搞甲骨文的信仰甲骨文,搞文字的人信仰文字,已经不在少数,而这一切是否值得信仰都成问题,正象张承志已经承认的那样,现在一切都是假的,我们为什么要信仰假的东西?一个事物是否值得信仰,这要借助于自己的理性来判断。明知是假,明知有诈,还催促大家赶快信仰,不知这是一种什么用心?这是不是在搞某种形式的蒙昧主义?
在我们这些草芥之辈看来,我们目前最大危险正是蒙昧主义而不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固然没有建设性,但它也没有欺骗性,它不会故作姿态装腔作势,也不会在信仰的名目之下把人群糊里糊涂地引入死地。而这一切,蒙昧主义都能轻而易举地做到,它要把人的理性遮蔽起来,让人人都来做奴隶,做某些人的思想和信仰的奴隶。我们现在最需要健康的怀疑精神和深刻的批判理性,不要说信仰,就是一般的学术研究,一切也都要打上一个问号,一切都要再三地追问“为什么”?以为只有随便信仰点什么才是清“洁”,恐怕失之于简单。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张承志对于知识分子的指责是武断的:“现在的知识分子太脏了,甚至以清洁为可耻,以肮脏为光荣,以庸俗为时髦,‘洁’这个字只有在公共厕所、垃圾站才能见到。然而在古代中国,它却是关于一个该怎样活着的重要观念。”(11)这是在历史中重建为我所用的乌托邦,在乌托邦或回民文化传统中重温自己的旧梦,从中寻找非理性的力量为自己的信仰作理论辩护。用一个“洁”字来概括过去士大夫阶级的特征,试图“着一”‘洁’字便境界全出”,实在是过于天真。
但天真的并非张承志一人,在这点上,他“吾道不孤”。那个号称“农业文明的歌者”的张炜也决不甘寂寞。与张承志的满腹牢骚却又有板又有眼地娓娓道来不同,张炜以山东汉子特有的气质和大江东去式的豪迈,厉声大问:“诗人为什么不愤怒!你还要忍受多久!快放开喉咙,快领受原来属于你的那一份光荣!”(12)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使理想主义、人文主义、英雄主义……的真面目一下子暴露无遗。原来不过是因为大众文化挤占了自己原来的地盘,使自己原来的“那份光荣”作了社会再分配而已。因此他要做一个磨刀霍霍的“复辟派”,这就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所谓的人文主义者也不过是一批复辟狂而已,颇有些《艳阳天》里一味变天的马小辫们的气味。但如果头脑清醒的话,就应该看到,过去精英地位的维持是靠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撑,从而构成对于大众文化的打压之势,随着主流意识形态控制力的减弱和市民社会的初始形成,过去精英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联合执政的美好时光已告结束,现在是三分天下之局。梦想再一次与主流意识形态一统天下,使天下定于二分之一尊,不仅只是梦想,而且是僭妄。所谓“原本属于你的那一份光荣”。也只能是“原本属于你的”了。真是“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其实这里面掩藏着一种深深的失望感,这种失望感又孕育了浓浓的恨世情结。“张承志们”对于文化界的一切都不满意。
——不满意于新闻界和批评界没有信仰,随波逐流,苍凉孱弱,蝇蝇苟苟;因此社会上缺乏真正犀利、充满良知和信仰的批评,批评家们只是一味地跟在通俗文学的“大腕”(而不是当年的精英“大腕”)后面且分些残杯剩羹,真是“朝扣富儿门,幕随肥马尘”。
——不满意于文学创作由一种神圣的精神活动变成了机械的操作,虽然不少精英分子对于电脑写作也是情有独衷。这时文学创作与制作、操作成了同义语,它已经专业化、技术化、匠人化了,产量固然大得惊人却又是赝品,因为里面没精英们所珍惜的“血泪心汁”,于是人文精神枯萎了。(这时“人文精神”可悲地成了失去了乐园的代名词,失去了名与利的代名词,失去了社会轰动效应的代名词。)于是大众所喜爱的大腕们所制作的作品也都成了产品,接着又成了赝品,然后又成了垃圾,最后成了人类不耻的狗屎堆。(这里有一种“正义的逻辑”,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逻辑”,凡是自己所不喜欢的就是没有价值的,凡是不能昭示自身地位不能使其领会“原本属于你的那一份光荣”的一切,都是狗屎一堆)。
——不满意于大众文化不含理想和缺乏热情,没有震撼人心之作,人人都是眼前主义者,都是物质至上主义者,都是金钱万能主义者,不去思考生活的意义,也不关心自己的灵魂,轻视知识文化(就是轻视精英),居然把审美追求、生存价值视若无物。煮鹤焚琴,斯文扫地呀。张嘴就是“他妈的”,闭嘴就是象“丫挺的”,无耻堕落呀。都在追求时尚,都在追赶流行,都在东张西望,都在匆匆忙忙,都在人云亦云,“小说家们曾经虔诚捍卫的竭力唤醒的大众,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庸众,忘恩负义,人阔脸就变,他们无情地抛弃了小说家。居然转过脸去朝搔首弄姿的三、四流歌星热烈鼓掌。不仅大众变了,而且一夜之间作家们连同时代一样,变得越来越不可信。”“我们身处在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一个不相信灵魂的时代。耻言理想、蔑视道德。到处可见浮躁不宁面容紧张的精神流氓。”(韩少功语)
——不满意于一个小报记者的名望大于一个顶尖级的大作家,不满于大大小小的贾平凹们写“性”,不满意于大众文化淹没掉了精英文化……
很多很多,好恨好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丑化通俗文学的同时,是不遗余力地为自己唱动听的赞歌,为“严肃文学”、“精英文化”制造一个又一个神话。创作严肃文学的作家才是“真正的作家”,他们的眼睛、灵魂、每一根血脉生来就是为了一种“追求”而存在,他们完全超越于个人,为了人类的进步,为了人类日臻完美,他们妙笔生花般地奔泻出一札札关于正义的苦恼和沉思,一札札促使人类发生根本变化的人文思想……他们无私无畏,成败利害不系于心,得失存亡不牵挂于怀,功名利禄如过眼烟云,荣华富贵似路边粪土。他们拥有一种永恒的爱,爱自然,爱社会,爱英雄,爱苍生,爱祖国,爱人民,爱……,总之,他们是人类的救星,是精英中的精英,人类中的极品,社会的良心,大众的眼睛……
妙不可言。
废话篇
人文精神首先是一种宽容的识时务的人生态度而不是狂人式的自吹自擂,更不是充满了杀气、乖张、暴戾之气的自以为是、自尊自大、走火入魔和不知廉耻;人文精神是一种理性精神而不是非理性主义的自我标榜;人文精神是一种以自省为核心的启蒙主义而不是蒙昧主义;人文精神对于社会的批判永远始于自己,不能把一切教条和好听的东西当成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不是贵族至上主义;人文精神是人间的人文精神而不是天上的神文精神,它排斥大众文化但却是出于公心而且是以理性的方式进行的。
人文主义者追求真理却永远不独占真理,不能动不动就以拯救天下为己任;人文主义者支持己见却从不固执己见;人文主义者做不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是时刻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自己行为的根本准则;人文主义抵制物欲主义,却从不敢说也不必说自己不食人间烟火;人文主义者可以以精英自任自励,但这是以承认大众文化的存在的合理性的前提基础上,否则依仗着政治权势而自保地人文精神最好是去掉才好;人文主义者关心人类的命运,而不能强迫大家都按着他的那个模式来关心,否则就斥其为大逆不道;人文主义者有自己的终极关怀,但不强调每个人都得具有他那个样子的终极关怀,而且只能那么关怀;人文主义者可以是一个道德至上主义者或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或一个精英主义者,但不能是一个唯道德主义者,一个唯艺术主义者,一个唯精英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可以是一个以批判为己任的人,但第一那批判必须是始于自己,而终于自己的,第二是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批判的有限性,第三是批判必须建立在必要的理解基础之上的;人文主义者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不能自命为上帝、救世主、真主、最后的审判者、真理的裁定者、道德的仲裁者,不能将一已的标准当成是全社会的共同要求和共同愿望,而要时时刻刻考虑自己的要求是否合乎一个多元化共生时代的多种要求。他不是一个卫道者,不能以道杀人;人文主义者是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但从不断定只有自己才得了“道”的真传,别人手里拿的永远是垃圾和粪土。
与此相反,伪人文主义者正是站在道德和宗教的立场上对于社会上的是非曲直作出自认为是唯一正确判断,才不容别人分辨地发出愤怒的咆啸,才因为一己之失而把这个世界称之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末世,才发出先知一般的、神一样的谴责和诅咒。伪人文主义者有精英意识和济世雄心,但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想做民众的思想领袖和精神导师。他们自信自己超人一等,先知先觉,把自己所不喜欢的一切打成“小市民情调”,“市侩哲学”、“痞子文化的代言人”、“打着反文化、反价值、反意义这类堂而皇之的旗帜去干从俗、媚俗、庸俗的勾当”,“没有灵魂、没有灵智、不求意义、不相信永恒,追求感官的刺激及审美的程式化、电子化、流行色”。
当把“人文”作“神文”时,“人文”是极容易变成“兽文”的。
简单之至。
注释:
①李书磊:《现代人格的沦丧》,《学习》1993年第12期。
②孟繁华:《一部“嫖妓小说”》,《学习》1993年第12期。
③扎西多:《正襟危坐说〈废都〉》,《读书》1993年第12期。
④参见高瑞泉等四人:《人文精神寻踪》,《读书》1994年第4期。
⑤张承志:《荒芜英雄路》,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
⑥《小阿克利亚》,引自张承志《错开的花》。
⑦张承志:《荒芜英雄路》,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第98页。
⑧张承志:《荒芜英雄路》,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⑨(11)转引自《新华文摘》1994年第11期,第123-126页。
(12)张炜:《抵抗的习惯》,《文汇报·文艺百家》,1993年3月20日。
标签:张承志论文; 人文精神论文; 大众文化论文; 废都论文; 贾平凹论文; 人文主义论文; 精英文化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荒芜英雄路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文学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