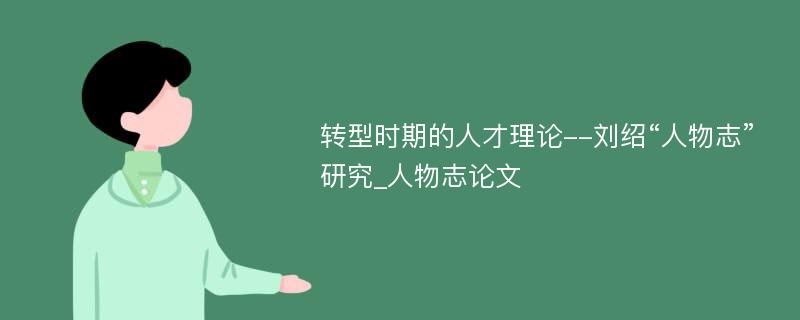
转型时期的才性理论——刘劭《人物志》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期论文,理论论文,人物志论文,刘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以“才性理论”为核心的人论与文论,于汉魏之际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此时期思想界对人之关注与研究,其理论重心逐渐由“伦理”转向“心理”,由对正统儒家整体性道德规范的恪守,转向对个体气质、性情、才藻、智能的崇尚。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刘劭《人物志》具有精典意义及丰碑价值。
关键词 人物志 才性 转型
2—3世纪的汉魏之际,是中国思想史的转型期,思想界对人的研究与关注,其重心逐渐由“伦理”转向“心理”,由“德性”转向“才性”,由对正统儒家整体性道德规范的恪守,转向对个体之气质、性情、才藻、智能的崇尚。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刘劭《人物志》具有精典意义及丰碑价值。这一点,并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本文拟在中国思想史的上下文中,重新确认刘劭《人物志》的理论价值,确认刘劭其弘阔而精致、灵动而严整的才性理论,对中国古代“人论”与“文论”的独特贡献。支撑这一宏观性理论评估的,是本文对刘劭《人物志》才性理论的细读,是对刘劭“才性类型说”与“才性识鉴说”的阐释。
1 刘劭,字孔才,三国魏广平邯郸(今河北邯郸)人。建安中,御史大夫郗虑辟劭,拜太子舍人,迁秘书郎。魏文帝黄初年间,为尚书郎、散骑侍郎。明帝即位,出为陈留太守,迁散骑常侍。正始年间卒,追赠光禄勋。《三国志·魏志》有传。
刘劭《人物志》三卷十二篇,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才性理论专著。《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论辨人才,以外见之符,验内藏之器,分别流品,研析疑似”。后魏敦煌从刘延明为之作注,刘注“惟疏通大意,而文词简古,犹有魏晋之遗。”(同上)《人物志》有《龙溪精舍丛书》本和《四库丛刊》本。
中国古代的才性理论,在汉魏之际,有一次大的转型。建安十五年(210)春,曹操在邺城下《求贤令》, 呼唤“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两年前曹操有赤壁之败,“今天下之不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不仅欲求“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甚至也愿接纳“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见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此中所传达的信息,不仅仅是思贤若渴,更有对传统之才性观,对儒家之正统礼教的抛弃与悖逆。曹孟德之才性思想,实乃“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之大变革”,使得“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据矣。”(见《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147页)
曹操之后的魏国君主,也颇为重视对人才的选拔,重视对人才理论的研究。黄初元年(220),曹丕立九品官人法, 由各州郡县的大小中正,考察选拔并举荐本地人才,第分九品,亦可根据其表现而酌情升降。曹丕的才性品评,重新承认门第的作用,与乃父之才性思想相比,已是一种倒退,但在具体操作中,并不乏灵活性。比如,九品官人法虽明文规定“郡口十万以上岁察一人”,却又表示“其有秀异,不拘户口”(见杜佑《通典》卷十《选举》)。到了魏明帝太和年间,九品官人法在大小中正们的手中,衍为彼此间的递相标目,人才品鉴的客观标准已退居其次。于是,刘劭上疏明帝,请求“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后因明帝驾崩,刘劭的《都官考课》未能执行。(事见《三国志·魏志·刘劭传》)
自先秦至魏晋,关于人才的考察、选拔与品评、识鉴,方法有别,准则各异,但大体上是分为两个方面:才与性。前者指才干能力专长,后者指德性个性人品。正统儒家的才性标准,更强调德性,强调整体性的伦理规范。而从曹操开始,魏国的几代君主,更强调才能,强调治国用兵之术与文章诗赋之才。刘劭本是曹魏政治集团中人,且颇受重用,其才性思想,与诸曹大体一致。读《人物志》可知,刘劭论“才性”,并未提及“忠教仁义”等儒家才性要义。《人物志》谈得最多的,是各类人才在性格、能力方面的特征,以及考察、辩析人才的各种方法。“才性”之中,刘劭更看重才;而论及“性”,刘劭主要地是讨论性格、气质、人格。刘劭的才性理论,主要是心理学而非伦理学。
才性理论在建安时代的转型,其开创者当然是曹操。但曹操的才性理论,虽宏阔却失之简略粗糙。而刘劭《人物志》的理论建构正好弥补了曹氏理论之不足。刘劭之论才性,有着精致的理论形态、严谨的逻辑结构、细密的思辩层次。比如,关于才性的分类,就有多种角度与多种层次:按“才能”之特征,逐层分为“三度”、“八材”、“十二流业”;按“性格”,又逐层分为“二体”、“九理”。又比如,关于品鉴才性的方法,既有动态性考察的“八观”,也有静态辨析的“五观”;既有以气质性格考察为核心的“九征”,还有以动机情绪把握为主旨的“六机”。而这些多层次多角度的“类型说”与“识鉴说”,又整体性地统驭于“才性”这一中心范畴之下。
作为改朝换代的君主,曹操的人才理论与实践,主要限于经世致用、治国用兵。而刘劭的才性理论,将实用与审美融为一体。他的“十二流业”中,专门讨论了三种审美创造之才:文章、儒学与口辩。此外,刘劭对各种性格气质的辨析,对各种“才性识鉴”方法的阐述,都有着文学的审美的意味。刘劭本人也有过文学创作经历,他作过《赵都赋》、《许都赋》和《洛都赋》,还著有《乐论》。后来南北朝的文论家,对创作才能的分类学研究(如钟嵘之“三品”),对文学品鉴的方法论探讨(如刘勰之“六观”),都可以看到刘劭才性理论的影响。
刘劭本人也是一位难得的人才。据《三国志·魏志·刘劭传》,青龙二年(234),魏明帝诏书博求众贤,散骑侍郎夏侯惠向明帝推荐刘劭,说是“群才大小”,皆视劭为楷模,“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性实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静之士慕其玄虚退让,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数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笃固,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制度之士贵其化略较要,策谋之士赞其明思通微……”这段称荐之辞,固然有溢美之处,但称荐者的品鉴之方,以及对各种人材的分类,岂不正是《人物志》才性理论之要义?
2 “才性”一词,最早见于《荀子·修身》:“彼人之才性之相悬也,岂跛鳖之与六骥足哉?”虽说荀子之言“才性”偏于“才能禀赋”一端,但他关于“才性之相悬”即才性之差异性的思想,却成为后来才性分类学的理论基础。才性之分类,其必要性与可行性,正存在于其差异性之中。刘劭论“才性”,很是强调其差异,以至于他最终将“才”分为“十二流业”,将“性”分为“十二类型”。
才性之差异是如何形成的?《人物志·九征》:“盖人物之本,出于性情;性情之理,甚微而玄。……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为性。”人之血气,其本质是“元一”即元气,元气有阴阳两体;人之禀阴、阳二气,有兼有偏,有多有少,这种“禀气”之别,便形成“性情”之异。比如,“明白之土”,禀阳气多,故“达动之机而暗于玄虑”;反之,“玄虑之人”禀阴气多,故“识静之源而困于速捷”。若是阴阳清和,则动静适宜;若是阴阳失调,则性分拘抗,“拘抗违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人物志·体别》,下引《人物志》只标篇名)刘劭还以“英雄”为例为说明阴阳之别。英者,草之精秀;雄者,兽之特群。英是智者,多玄虑之静;雄为勇士,多速捷之动。或“英”或“雄”,只是偏至之性;只有那些集“英”与“雄”之气于一身者,方为性之至境。(《英雄》)
“禀气阴阳,性有刚柔;拘抗文质,体越各别。”(《体别》之刘延明注,以下简称“刘注”)《人物志·体别》以“气”论性,在阴阳二体的基础上,划分为十二种不同的性格类型,并概括出每一种性格类型的总体特征与长短得失:
1,强毅之人:狠刚不和;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许。2,柔顺之人:缓心宽断;柔顺安恕,每在宽容,失在少许。3, 雄悍之人:气奋勇决;雄悍杰健,任在胆烈,失在多忌。4, 惧慎之人:畏患多忌;精良畏惧,善在恭谨,失在多疑。5,凌楷之人:秉意劲特; 强楷坚劲,用在桢干,失在专固。6,辩博之人:论理赡给;论辨理绎, 能在释结,失在流宕。7,弘普之人:意爱周洽;普博周给,弘在覆裕,失在溷浊。8,狷介之人:砭清激浊;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肩。9,休动之人:志慕超越;休动磊落,业在攀跻,失在疏越。10,沉静之人:道思回复;沉静机密,精在玄傲,失在迟缓。11,朴露之人:申疑实谄;朴露劲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12,韬谲之人:原度取容;多智韬情,权在谲略,失在依违。
十二种性格类型,每两种为一组:前阳后阴,前刚后柔。比如“强毅”与“柔顺”,一“狠刚”一“宽缓”,前者有“矫正”之材,却有“激许”之抗;后者有“宽容”之德,却有“少许”之拘。
“才性”之“性”,在汉魏之前,多指伦理道德之性,如孟子论“性善”,荀子论“性恶”,管子论“性有善有恶”。才性理论发展到汉魏之际,其道德意识逐渐淡化,心理学意味逐渐增强。刘劭论“才性”之“性”,以“元气”为根柢,以“阴阳刚柔”为体别,以秉气之“偏兼多寡”为依据,细致周祥地辨析各类性格气质之特征。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严格意义上心理学,但并不妨碍理论家在他们的论著中表述心理学思想。刘劭对十二种性格气质的描述,从观念到用语,均不乏心理学意味。与刘劭同时的曹丕,以“气”论文和文人,亦表现出心理学倾向,只是曹丕的才性论,远没有刘劭的那种弘阔而精致的形态,以及清晰而细密的描述。才性理论在汉魏之际的转型,曹氏父子当然有其开创之功;但论及这一转型的理论标志,当首推刘劭《人物志》。
才性理论之转型有两项重要内容,一是淡化“性”的伦理道德意味,而赋予心理思想特色;二是对才能才干(尤其是治国用兵、赋诗作文等专门之才)的格外看重。《人物志·流业》将才能分为十二种类型,除了“清节之家”以外,其余的十一种都是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他们各有着属于自己的特殊才能,因而能胜任或某种级别或某个部门或某种职业的专门性工作。根据《人物志》“流业”、“材能”等篇的论述,我们将十二种人才的主要特征分述如下,每一种类型依次分为四项内容:名称,“才”之特征,“能”之范围,举例。
1,清节;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有自任之能;如延陵、晏婴。2,法家: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有立法之能;如管仲、商鞅。3,术家: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有计策之能;如范蠡、张良。4, 国体:法正天下,术谋庙胜;三材兼备;如伊尹、吕望。5,器能:法正乡邑, 术权事宜;三材皆微;如子产、西门豹。6,臧否:好尚讥诃, 分别是非:有司察之能;如子夏。7,伎俩:受一官之任,措意施巧; 有权奇之才;如张敞、赵广汉。8,智意:能遭变用权,权智有余;有人事之才;如陈平、韩安国。9,文章:能属文著述;如司马迁、班固。10, 儒学:能传圣人之业;如毛公、贯公。11,口辩:辩不入道,而应对资给;如乐毅、曹丘生。12,骁雄:胆为绝众,材略过人;有威猛之能;如白起、韩信。
《人物志》对才能的分类,如此全面而系统,足以见出作为“才能品鉴者”的刘劭,自己也是颇有才能的,说到底,品鉴才性,本身就是一种才能,它对品鉴者的才性同样有着很高的要求。
3 才性品鉴,实际上是一件很难的事,所谓“知音其难哉”,知音之难,在客体(品鉴之对象)是材理难察,在主体(品鉴者)是才性有限。“材既殊途,理亦异趣”(《材理》之刘注),品才者,若通晓某一方面的材理,便是获得了一种品鉴之才能。《人物志·材理》将“品鉴之才”分为八类;
1,名物之才,聪能听序;2,构架之才,思能造端;3, 达识之才,明能见机;4,赡给之才,辞能辩意;5,权捷之才,捷能摄失;6,持论之才,守能待攻;7,推彻之才,攻能夺守;8,贸说之才,夺能易予。
偏于一类者,则专有“一能”,谓之“偏才”;若八类皆通,则“兼有八美”,谓之“通才”。通才品人,则能“同解而心喻”。(同上)
才性识鉴者,不仅其才能有偏至小大之分,其性格气质也是因人而异。《材理》对识鉴者的分类研究,除了依“才”之异而一分为八,还察“性”之殊而一分为四:
1,质性平淡,思心玄妙,能通自然,道理之家;2,质同警彻,权略机捷,能理烦速,事理之家;3,质性和平,能论礼教,辩其得失,义理之家;4,质性机解,推情原意,能适其变,情理之家。将“八才”与“四家”联系起来看,便不难明了刘劭对才性识鉴志之“才性”要求颇多理想色彩。且不说“八美”兼有、“四家”俱备的“全才”如凤毛麟角;即便是通晓“一才”、自成“一家”者,也并不多见。才性品鉴者,受着自身的局限,在品才实践中往往失误。
“四家”之分已表明:品才者因其质性之异,对材理的把握不尽相同。“四家之明既异,而有九偏之情。”(同上)良好的素质与情性,导致对材理的准确把握;相反,品才者质性的偏颇与拘抗,则难免酿成品鉴之失。《材理》在“四家”之说之后,又指出了因品鉴者之“性”而导致的“九偏”:
1,刚略之人,不能理微;2,抗厉之人,不能迥挠;3,坚劲之人,好攻其事实;4,辩给之人,辞繁意锐;5,浮沉之人,不能沉思;6,浅解之人,不能深难;7,宽恕之人,不能速捷;8,温柔之人,力不休强;9,好奇之人,横逸而求异。
才性品鉴者,不仅有自身气质、性格方面的偏颇,还有操作上的失误,比如角度的选择、方式的运用,等等。刘劭将后者概括为“七缪”:
1,察誉有偏颇之缪;2,接物有爱恶之惑;3,度心有小大之误;4,品质有早晚之疑;5,变类有同体之嫌;6,论材有申厌之诡;7,观奇有二尤之失。
《人物志》才性品鉴说,既强调品鉴主体的才性,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法。刘劭论才性品鉴之方,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征神见貌的整体性感知,二是察情辨志的动机性把握,三是观通否而明格度的动态性考察,四是视行止而知效验的静态性效荐。四者既是不同的方法系统,分别适应于对品鉴对象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的识鉴;同时也是识鉴过程的各种步骤,适用于识鉴过程的不同阶段。
刘劭认为,人物的才性,其质内充,其精外彰,无论多么复杂的“质”,总是会通过各种途径显露于外,使得才性品鉴成为可能。而才性识鉴的第一步,便是对这些外部特征的感知,《人物志》将这种方法或过程称为“征”。征之对象有九,每种内潜之质,各有一相关的外显部位:
神——平陂之质;精——明暗之实;筋——勇怯之势;骨——强弱之植;气——躁静之决;色——惨怿之情;仪——衰正之形;容——态度之动;言——缓急之状。
对这九个方面的品鉴,不可孤立地进行,而是要相互联系,以作整体性感知,所谓“九征皆至”(《九征》)。
“九征”之法,尚是对识鉴对象之外征的感知。品鉴者还须由外入内,去把握对象复杂的内心世界。这种内在的识鉴从何处入手?刘劭有“察情辨志”之法。《八观》指出,人之“情机”,有六种类型:
抒其所欲则喜,不抒其所能则怨;以自伐历之则恶,以廉损下之则悦;犯其所乏则姻(忿),以恶犯姻则妒。
欲,用心理学的术语说,是人的心理需求;而抒其所欲,则是一种行为动机。个体的人,在动机的驱使下,借助特定的行为,满足(或未能满足)一己之心理需求,便酿成相应的情绪反映。在这一“需求—满足”的心理过程中,不同的动机,会导致不同的情绪,这便是刘劭所说的“情机”。“观其情机,而贤鄙之志,可得而知。”只有细致而准确地把握了对象的动机与情绪,才能知其“志”,知其人格的与精神的真实状况。在任何一种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之中,“动机”与“情绪”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词”;刘劭的“六机”,以“情机”为理论核心,在才性理论的建设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刘劭是一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才性理论家,他所创建的才性品鉴之法,有着较强的可操作性。其“八观”与“五视”,分别从动态与静态两个侧面,为才性品鉴者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八观”是:
1,观其夺救,以明间杂;2,观其感变,以审常度;3, 观其志质,以知其名;4,观其所由,以辨依似;5,观其爱敬,以知通塞;6,观其情机,以辨恕惑;7,观其所短,以知所长;8,观其聪明,以知所达。
“八观”的内容,包括了性情与才干,人格与智力,行为与心态,动机与情绪等诸多方面,是对被品者才性的全方位考察。
个体的人,处于不同的境遇或状态之中,会有不同的行为与心态。如何在不同的情境中识鉴才性?刘劭又有“五视”之法:
1,居,视其所安;2,达,视其所举;3,富,视其所与;4,穷,视其所为;5,贫,视其所取。
如果说“八观”是一般状态下的才性识鉴,那么“五视”则为特殊境遇中的才性效验。“八观”与“五视”相结合,便可得被品者才性之全貌。两百多年后,刘勰《文心雕龙》论作家、作品之识鉴,有“三准”、“六观”、“八体”之说,其心理学观念与方法,与刘劭《人物志》有诸多相似之处。此刘受彼刘之影响是很有可能的。
刘劭论才性品鉴,无论是关于品鉴主体的“八才”、“四家”之分,“七缪”、“九偏”之别,还是关于品鉴方法的“八观”、“五视”之法,“九征”、“六机”之术,不仅有着极为丰富的心理学内涵,而且还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审美意味。才性品鉴的才能与方法,其实质是审美鉴赏的才能与方法,她标识着鉴赏者的才藻、情性、胸襟、气局、境界、趣味等等。肇始于东京,兴盛于曹魏的人物品藻,渐渐地丢弃了世用之功能,而衍为玄学之风习,成为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行为。曹丕《典论·论文》之品藻性情,已是纯粹的审美批评;而溯其滥觞,应是始于刘劭之《人物志》。中国古代以“才性理论”为核心的人论与文论,转型并重铸于魏晋南北朝,其理论丰碑,非刘劭《人物志》莫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