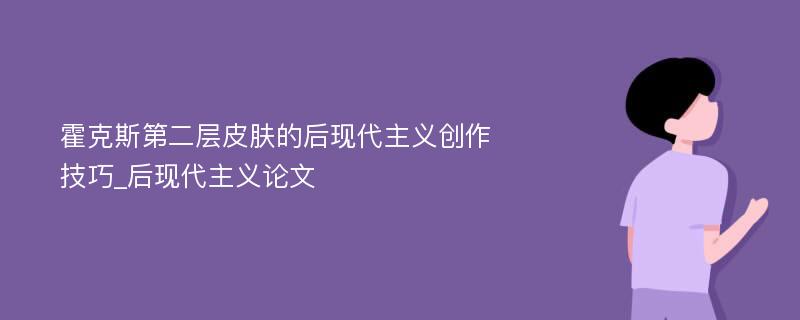
霍克斯《第二层皮》的后现代主义创作技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第二层论文,霍克论文,技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表于1964年的《第二层皮》是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约翰·霍克斯重要代表作之一。小说以一位在二战中退役的美国海军军官斯基泼(外号“船长”)自述的形式,回忆了自己“毫无掩饰的历史”(注:John Hawkes:Second Skin,New York: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64,p.9.以下引语均译自此版本。):父母相继自杀;妻子由于精神空虚绝望,在汽车旅馆和他的部下酗酒调情,最后在旅馆自杀;女婿费尔南德斯也被残酷杀害;自己千方百计地想保护女儿卡桑德拉,但无力使她免遭同样的厄运,结果却促使她被人引诱后跳塔自杀。他本人是美国“海星”号兵变的受害者,之后又无端地受到接二连三的挑衅和袭击,最后终于在飘流岛上从为母牛人工授精的工作中感受到了生活乐趣,并从当地黑人姑娘卡塔丽娜·凯特身上找到了自己爱情的归宿。小说中黑暗与光明、死亡与新生、虚幻与现实相互交织,堪称一部梦魇漫游史。尤其是霍克斯在这部小说中,实验性地运用了多种后现代主义创作方法,颇受评论界的重视。本文拟就这部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创作技巧加以探讨。
梦魇般的叙述文本
霍克斯的小说创作主张是对传统小说形式的反叛,他曾在一次谈话中宣称,“我在写小说时,就假设小说的真正敌人是情节、人物、背景和主题,一旦放弃关于小说的这些熟悉的想法之后,实际上只剩下想象力的总合或者结构。而结构——文字上和心理上的紧凑——乃是我作为作家的最大的关怀。”(注:董衡巽、朱虹、施咸荣、李文俊:《美国文学简史》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15~416页。)《第二层皮》正是他实行这种主张的典型文本。在这部小说中,毫不相连的回忆碎片代替了情节;梦魇般的心理叙述代替了人物刻画;背景常常游离于虚幻和现实之间;而主题却深深地编织在貌似漫不经心的叙述当中。值得注意的是,霍克斯在这部小说中改变了他早期小说的叙述方法,通篇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者本身也是小说的主人公。看来此时他已不满足于像以往那样用全知式的叙述方法来表现强大、黑暗的世界,而他这种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更能表现现代人对这个梦魇世界的心理反映,更能自由地发挥他的创作想象力,从而任意组合他的叙述结构。
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斯基泼在叙述时自始至终保持一种超然性,几乎对人物和事件不作任何评论,这样就最大程度地调动了读者的参与。小说第一章的开局很奇特:“我来简单地告诉你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爱那只蜂鸟,它一下子就飞落在我搭脚的旧窗台外面的那朵花上;我爱老奶奶们灵活的手指和针尖儿,她们正弯着腰,聚精会神地绣着可爱但又蹩脚的图案;我爱那种软布阳伞,年轻女孩儿们的衬裤也是用这种布料做成的;我也爱那艘小舰艇,不管怎样,我在她的甲板上或操舵室里渡过了不幸的岁月;我也爱妻子、孩子和我那既可亲又可怜的黑人餐厅勤务兵桑尼,桑尼是我的难友和知己。但我最爱善良乐观的自己。”这种开头尽管文字流畅,结构工整,但语义断裂,语境混乱。接下来,叙述者便像电影开始前在银幕一一掠过的片头一样开始了人物介绍,因为他认为人物介绍必须先于他那“牵动人心并且有时间、地点和情节的切实经历”。叙述者在这一章似乎以传统的叙述方式讲故事,实际上在回忆,中间还夹杂着一些“有点儿浪漫色彩的幻觉”,梦魇般的回忆碎片杂乱无章,时而跳跃、中断,时而交叉、平行,使读者难以轻易地分辨虚幻和现实,从而创造出一个霍克斯式的现代神话。
对斯基泼来说,他来到漂流岛之前所经历的一系列事件就像是一场恶梦,尽管虚实难辨,但无非都是现实社会在他内心世界中的反映,是他心理王国的漫游史。霍克斯这种让主人公作虚幻叙述的方法和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的主张相同,他认为小说家“绝对需要根据自己的想象来创造出一个全新而且必要的虚构环境或幻觉世界”(注:John Hawkes: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ed.Carolyn RiIey,Detroit:Gale Research Company,Vol.3,p.223.)。他曾于1964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我的目的是通常绝不让读者(或者我自己)脱离这个陷井,也就是说,绝不让读者想到现实中还有什么比这更黑暗的景象,或认为还能从人类存在的梦魇中轻易地找到什么出路。”(注:John Hawkes:"John Hawkes:An Interview",with John Enck,Wisconsin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6,1995,p.145.)因此在阅读霍克斯的《第二层皮》时,读者会心不由己地进入主人公的心理王国,从而产生更强烈的心理共鸣。
纷乱的时空
时空的跳跃和颠倒是现代小说家经常使用的创作技巧。例如,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的时空次序是非常复杂的,但读者仍能从叙述者的心理叙述以及凯蒂的经历中找到时间的次序和空间的关联。而作为后现代主义小说家,霍克斯在《第二层皮》中把这种技巧运用得更为奇特,简直到了“错乱”的地步。小说中没有传统小说式的情节,斯基泼的心理漫游是“沿着蜂岛飘忽不定的轨迹”进行的。他叙述中的地点如“战时的首都”、“美国西南部大沙漠”、“平和岛”、以及“飘流岛”等都是他臆想出来的地理位置,“在时空中无处可寻”,而且他表述的“现在”、“今天”和“昨天”在时间概念上也都是极不确定的,是“无法用时间计算的时间”,串联性的时间消失了,历史性的内容深度开始消解。因此,这部小说中的时空关系无非都是叙述者心理上的时空关系。
斯基泼是在漂流岛住所的窗前作回忆叙述的,从他的心理流动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他以几个不同的时点为中心向前、向后作时空跳跃。第一个基本时点自然是在小说的开始,叙述者躺在华丽的吊床上,把脚搭在破旧的窗台,回忆起他自从来到漂流岛之前的历史以及它像风、像船一样的主题、回忆起死去的家人,而时间对他记忆的影响就像“流水对旧绳结的作用”一样难以使它磨灭;第二个时点是第四章卡塔丽娜·凯特怀孕三个月、女儿卡桑德拉自杀已有七年的时候;第三个时点是卡塔丽娜·凯特怀孕六个月的时候;第四个时点是在第十章她怀孕八个月的第二天;第五个时点是在最后一章,也就是她分娩后的第二天深夜,叙述者回忆了为新生儿庆典、向亡者吊唁的情景。叙述者望着“残夜的太阳、黎明的月亮”,他回忆的碎片在万籁寂静中逝去了。
以上几个叙述时点还是有一些联系的,但叙述的事件都是印象式的碎片,分散在全书的各个章节,在时空上的排列几乎是无序的,完全按照梦魇回忆的需要。例如“海星”号兵变事件是在好几个章节里叙述的,兵变头目特雷姆洛的名字可以说贯穿于小说的始终,这说明战争和动乱给叙述者留下的心理创伤是非常严重的,尽管岁月流失,但他心灵上的旧伤疤仍在隐隐作痛。对于女婿费尔南德斯因搞同性恋而惨遭杀害,读者也是从斯基泼回忆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的。他不愿意再给女儿制造心理创伤,但又因为没向女儿吐露真情而感到内疚,骚乱矛盾的心理跃然纸上。在叙述者回忆黑暗荒诞的“昨天”的同时,又不时地将视角拉回到田园牧歌式的“今天”。所有这些叙述的事件都是斯基泼骚乱心理的外在表现。就在这纷乱的时空中,霍克斯通过斯基泼之口创作了一个万花筒般的现代神话,这里有炼狱般的世界,也有伊甸园式的幻境。他之所以在《第二层皮》中运用这种技巧,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揭露、嘲弄、抨击暴力和荒诞,同时也常常可以唤起和更新我们对暴力、荒诞和美好事物的潜在意识”(注:John Hawkes:"John Hawkes:An Interview",with John Enck,Wisconsin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6,1995,p.144.),恰到好处地表现了现代人纷乱的内心世界。
不确定的象征意象
一般来讲,成功的小说往往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象征成份,然而霍克斯在《第二层皮》中所运用的象征主义手法极为不同,他似乎并不刻意表现历史的厚度和现实的深度,而注重的是现代人在荒诞的世界中对生与死、光明与黑暗的心灵体验和感受。因此在这部小说中,象征意象转换不定,象征寓意具有强烈的主观和虚幻色彩,常表现为多元性和不确定性。而这种寓意的不确定性往往是后现代主义小说形成与发展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霍克斯很擅长自然景物的描写,这可能和他的经历有关。他在青少年时曾在阿拉斯加居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他领略了“黑暗、暴雨、狂风、山脉、冰山断层、北极熊、野草莓、一条腿的印第安人、可怕的矿工区废墟等梦魇般的异地景物”(注:John Hawkes: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ed.Daniel G.Marowski and Goger Matuz,Detroit:Gale Research Company,Vol.49,p.154.),这些都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二战期间,他中断了在哈佛的学习生活,参加了美国战地服务团,在意大利和德国当一名救护车司机,战争的恐怖和荒诞使他形成了对生活和世界的冷漠态度,也强烈地体现在他的作品中。
风,在这部小说中的象征寓意极不确定。斯基泼在开篇就讲到他的历史的真正主题很可能只是一阵风,他的内心和皮肤对此尤为敏感:“它变幻莫测,时而狂暴肆虐,时而喃喃细语,它将世上的苦辣酸甜都揉进了阵阵的热浪或寒流,改变着我们在内心中回忆欢乐或痛苦的滋味。”在这部小说中,风含混地代表着主宰世界的各种力量,在不同的环境下,人的内心对风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例如斯基泼和卡桑德拉前往平和岛途经美国西南部大沙漠时,深夜中的热风“使皮肤感到温暖,却使肉体感到寒冷,令人发抖……风刮得长长的仙人掌干刺沙沙作响,低矮的荆棘、死甲虫、游蛇蜕弃的半透明的蛇皮、蜥蜴胚胎的腐肉、干死的蝗虫堆,沙漠中所有的残骸都发出刺耳的声音。”但是在漂流岛上,风转变成慰藉之物,它尽管有时猛烈,却使斯基泼感到阵阵惬意,“风像手臂一样搭在我的肩头,缠绕在我裸露的腿上,以它那变幻不定的重量、附着力和张力,拍打、冷却、抚摸着我的皮肤。”在漂流岛上他远离战争和邪恶势力的伤害,远离美国西南部大沙漠令人心悸的寒风,无需再担惊受怕,可以全身赤裸地在岛上漫游,承受大自然的风光,和桑尼共同分享着卡塔丽娜原始的人类之爱。
小说中“第二层皮”(second skin)的象征寓意怕是最不确切的了。斯基泼出于对女儿卡桑德拉的疼爱接受了她的要求,自残似地在自己的胸上刺上了女婿费尔南德斯的名字,直到长期在漂流岛上裸露身体后才逐渐隐没在胸毛下面。在漂流岛沼泽地,一条绿色的巨蜥死死地吸附在已怀孕三个月的凯特的裸背上,斯基泼每拉一次它的前腿,它就陷得更深,此时斯基泼感到“自己的皮肤正快速地变为爬行动物的皮肤”。在平和岛上,斯基泼带着卡桑德拉随里德父子乘船去钩指礁,由于风大浪急,每个人都要穿上雨衣。斯基泼把它看成是自己的“第二层皮”。也正是在这次出海中,卡桑德拉脱下了雨衣,和里德发生了性关系。对于“第二层皮”的象征寓意,有的评论家认为它指的是“小说的书皮,即掩盖斯基泼悲惨、真实历史的语言防护层”(注:Patrick O'Donnell:John Hawkes,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82,p.92.)也有人认为它指的是“传统概念上人们所穿的衣服,或者暗示人们原裸、天真的回复”(注:Patrick O'Donnell:John Hawkes,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82,p.92.)。笔者认为这里的“皮肤”是斯基泼内心对外部世界的感觉,是他对“昨天”和“今天”所经历的世界的心理折射。由于小说中象征寓意的不确定性,小说的深层意义极为复杂而又不稳定,读者只能凭自己的想象对小说进行再度创作,从而做出各种不同的判断和解释。
自嘲和戏仿
在解读这部小说的过程中,读者常常发现斯基泼的叙述话语中充满了自我嘲讽和对传统喜剧小说形式的戏仿,这正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本质特点之一。他明明多次声称讲述的是毫无掩饰的历史,但却掺杂着大量的虚幻成分;他自称是“勇敢的男人”,但在人生重大事件面前常常束手无策,对多次受到的挑衅和袭击不能采用任何必要的反抗。例如,他的父亲在浴室准备开枪自杀时,他不知所措,却荒诞地拿起了大提琴,为父亲演奏勃拉姆斯的乐曲;特雷姆洛在兵变中无端地袭击了他之后,带着他的同伙乘救生艇逃离军舰,当时他满可以架起那门口径三英寸的炮,下令把他们击沉,但却放过了他们,只是强笑说“让他继续跳舞吧”;他在平和岛上的十个月中一直受到战乱寡妇米兰达的挑衅和迫害,但他事后回忆时却认为“创伤也是甜蜜的”。他就像一个有自虐狂的小丑,一侧脸挨了打,又把另一侧脸伸了过去,似乎只有在这种不断的受虐中他才能感到心理的平衡。这有悖于读者正常的心理认同,甚至令读者感到震惊,殊不知这正是霍克斯创作《第二层皮》的创作意图。霍克斯曾对别人讲过,“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个跌跌撞撞的行路人,一个荒诞的人,有时应受到指责,有时制造一些麻烦,自己陷了进去,但结果却有一种内在的勇气使自己生存下去。”(注:John Hawkes:in Comic Terror:The Novels of John Hawkes by Donald J.Greiner,Memphis:Memphis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8,p.161.)看来,霍克斯就是要塑造这样一个历尽人生坎坷、作了社会的牺牲品还天真地表示宽容一切、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存下去的小人物。他似乎意识到“昨天”的历史是“一场已经完结并且毁灭了的梦”,社会是荒诞的,抗争是徒劳的,自己的问题不是如何采取行动来对待这个世界,而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中生存下来,因此他的生存方式只能是自我嘲讽。
小说中人物的自嘲是通过对传统小说喜剧形式的戏仿来完成的。传统的喜剧场面在这部小说中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荒诞不经、令人苦笑的叙述碎片。霍克斯笔下的主人公形象已经不带有传统的喜剧英雄的性格特点,却表现为与自己的年龄和经历极不相称的天真。如果小说中还残留一些喜剧成分,那就是他滑稽地嘲弄了自己似乎有受虐狂的小丑性格;如果他自身还存有传统喜剧人物的英雄特征,那就是他勇敢地拒绝和荒诞的势力进行抗争,拒绝当传统式的英雄。从这一点来看,霍克斯并不是某些评论家所说的专门以写暴力、恐怖、荒诞为宗旨而不注重思想内容的小说家,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职责。他认为小说家“应该面对我们自身和周围环境的丑恶以及潜在缺陷等重大问题”(注:John Hawkes: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ed.Carolyn RiIey,Detroit:Gale Research Company,Vol.3,p.223.)。通过对自嘲和戏仿的运用,霍克斯不但拓宽了现代小说的形式,而且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可笑可鄙而又可怜可爱的现代受难者的形象,他的弱点也是现代人普遍的人性弱点,他的自嘲也是对荒诞的现代社会的讽刺,忽视这一点,也就忽视了《第二层皮》的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作为小说家和学者,霍克斯凭着他对现代生活的深刻洞察力,从反传统的视角,用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技巧,奇特地创造了一个与真实世界相异的梦魇世界,深刻地表现了现代人的困惑和无奈。但在嘲弄现代社会的荒诞和人性普遍弱点的同时,他也通过小说中的主人公揭示了“美德终究会获胜”这一信念,表达了对未来和光明的向往。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后,这位七十二岁的老人于一九九八年五月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小说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