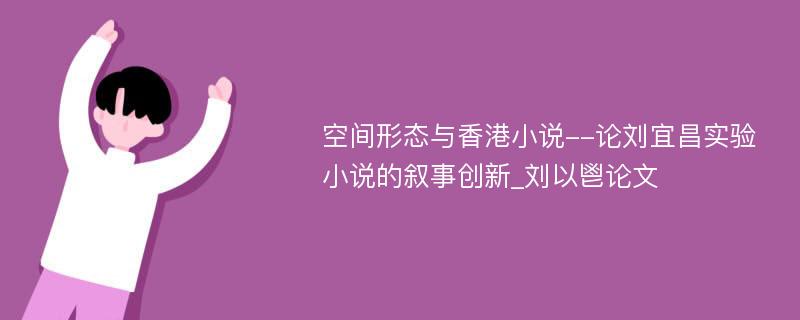
空间形式与香港虚构——试论刘以鬯实验小说的叙事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试论论文,形式论文,空间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坛,刘以鬯的特立独行,无疑凸现了其异数和另类本色。时 至今日,刘氏自然已是香港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重镇,如黄继持 所言,“不写近三四十年的香港文学史则已,要写便须要先着力写好刘以鬯这一笔。” ①(注:刘以鬯编《刘以鬯卷》,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90页。)不难看出上述 话语的重心所在,它一方面明断了刘氏之于香港文学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另一面却又 暗示了为刘氏撰史的艰巨性。显然,意识形态有色眼镜的无形遮蔽及对传统现实主义的 顽固坚守之下的对刘氏的解读,往往都会衍化成误读和偏执的指摘②(注:袁良骏著《 香港小说史》,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353页等处皆有相关偏激论述。) 。笔者曾在《清洗独角兽的尾巴》一文中对此予以批评,同时却又不自量力地预支了并 不成熟的研究计划③(注:朱崇科:《清洗独角兽的尾巴?浅论香港文学批评的一种偏离 》,香港:《纯文学》,复刊第30期,2000年10月31日,第26—37页。),如今只好自 食其果,不得不接受挑战,从空间形式角度解读刘以鬯具有香港特色的虚构?实验小说 的叙事创新。
何谓实验小说?应当指出,实验小说并非是不言自明的固定的文体,它是这样一种小说 :它更多指向了创作者的叙述姿态,即探索小说创新的无限的可能性,“同占主导地位 的文学传统的常规俗套分道扬镳,探索新的观察和反映人生及社会的方法和技巧。”④ (注:李今编《刘以鬯实验小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1页。) 对刘氏而言,实验小说不仅是他标新立异,凸显香港性的猎猎旗帜,而且也是他用以“ 娱乐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在香港恶劣的文学夹缝中,为维护文学尊严挣扎奋斗确立其 文学地位的结晶。尽管刘氏的文本大多都有相当的实验性,而本文所依据的文本(指严 肃文学)主要是《刘以鬯卷》(香港:三联书店,1991)和《刘以鬯实验小说》(李今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两本代表性著作及其散作若干。
一、空间形式与刘氏实验理论
作为与时间问题相对立的空间问题,其实是艺术理论中的一个历史悠久的论题。莱辛 在《拉奥孔》中就曾指出:“时间上的先后承续属于诗人的领域”,“空间则属于画家 的领域。”然而步入20世纪后,这种壁垒分明的划分(界定)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尤其 是现代主义小说创作中,各种创作实践的尝试和反小说理论的兴起发展,时空交叉、倒 置、错乱,打破了以往相对单一的时间秩序,转而显出追求空间形式的态势。
所谓空间形式理论,一般认为,是由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约瑟夫·弗兰克1945年首次 提出并进行系统阐述的。“形式空间化”,“就场景的持续来说,叙述的时间流至少是 被中止了:注意力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被固定在诸种联系的交互作用之中。这些联系游 离叙述过程之外而被并置着;该场景的全部意味都仅仅由各个意义单位之间的反应联系 所赋予。”①(注: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见秦林芳编译《现 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第8页,第71页。)而正是 这种使对象得以生存的空间关系,催发了空间形式。
弗兰克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了他的深入阐释。首先,从创作主体角度看,20世纪作家显 出了对空间与结构的浓厚兴趣和偏嗜,而往往对时间顺序表示了反抗乃至弃绝,他们往 往在同一时间里展开不同层次,通过来回切断,取消了时间顺序,更强调各种相关的情 节在不同舞台层次上发生的同时性和统一性。弗兰克曾提出一个重要的批评概念“并置 ”,简言之,并置即为“词的组合”,“就是对意象和短语的空间编织”。当然,现代 主义小说中空间形式的获得还有很多手法:如主题重复,章节交替,夸大的反讽等等。 其次,从接受主体来看,为了更好地理解空间形式,读者应把此类小说当作一个整体进 行观照和解读。“反应参照”这个重要概念是弗兰克对从接受批评角度阅读的强调。他 认为的“乔伊斯是不能被读的?他只能够被重读。”②(注: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 说中的空间形式》,见秦林芳编译《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版,第3页,第8页,第71页。)更是对在互动结构与关系中反复阅读必要性的深刻说明 ,将独立时间顺序之外而又彼此关联的参照片段拼接起来,并以此实现对小说背景的重 构。当然,弗兰克对空间形式的论述不是抽象的,他还结合诸多文本,如《夜间的丛林 》等进行精辟分析,并借此展示了他的理论范式的可操作性和独特价值。
弗兰克之后,许多批评家各显其能从不同角度对其理论进行了应用、发展和补充。如 杰罗姆·科林柯维支的《作为人造物的小说:当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主要论述自弗 兰克论文发表以来美国空间形式小说的发展情况,并以空间形式理论进行了审视和评析 ,他的这一做法无疑与弗兰克的研究交相辉映,可谓惺惺相惜,互为补充。詹姆斯·M ·柯蒂斯《现代主义美学关联域中的空间形式》主要从“现代思想、特别是在科学和哲 学上的空间和时间的讨论的关联域中”③(注: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 形式》,见秦林芳编译《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第8页,第71页。),进行解释和考察空间形式理论的流变,确认了弗兰克在现代美学 背景中的位置,并把结构主义语言学与弗兰克理论的相似之处进行中肯而深邃的比较。 《空间形式与情节》(埃里克·S·雷比肯)从结构、情节这一核心开掘了空间形式理论 ,而安·达吉斯托尼等人合著的《夸大的反讽、空间形式与乔伊斯的<尤里西斯>》则论 述了夸大的反讽在空间形式创造中的功能,并以《尤里西斯》进行例证④(注:上述批 评家及相关著述皆可参《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一书。)。
显而易见,要想阐明空间形式与刘以鬯香港虚构之间的关系,考察刘氏的实验小说理 论应当不可或缺。尽管刘氏虽然是一个学者型小说家,但其实验小说理论却并不系统和 具有独创性。但是,刘氏却在借鉴、吸收众声喧哗的现代小说基础上,经过艰苦的摸索 ,从而形成了具有个人特色的实验小说理论。
实验小说(Experimental Fiction),顾名思义,其核心特征则为其实验性和创新性。 当然这不应只是形式的重塑,它应该包含了文学观念和文本叙述(Narration)的更新。
(一)创新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兼容性
刘以鬯倡导作者要具备实验精神和创新意识,他曾多次谈到“从事小说创作的人,要 是没有创新精神与尝试的勇气,一定写不出好作品。”⑤(注:刘以鬯著《短绠集》,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P101。)他同时强调作家创作意识要具有时代性,“‘ 多试验才能走出新路来’这句话的真实性,是不能否定的。历史是一个轮子,时间推动 它前进,作家要是故步自封、墨守成规的话,一定跟不上历史的轮子。”⑥(注:梅子 、易明善编《刘以鬯研究专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9—50页。)同时他又 号召,“作为一个现代小说家,必须有勇气创造并试验新的技巧和表现方法,以期追上 时代,甚至超越时代。”①(注:《刘以鬯研究专集》,第63页,第57—58页,第92页 ,第63页。)尽管刘氏承认继承各位小说大师时受其影响的不可避免性,但他仍力主革 新与融会贯通,独树一帜。“我们不能再停留在摹仿和借鉴的水准上,要想法超越国际 文学的水准,要拿文学‘奥运’的金牌”。②(注:《刘以鬯研究专集》,第63页,第5 7—58页,第92页,第63页。) 面对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体对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冲击,刘以鬯在鼓吹创新与实验的同 时,也论及其可能性,“小说死去的时候,也可能是小说再生的时候。”③(注:《刘 以鬯研究专集》,第63页,第57—58页,第92页,第63页。)当然,这种可能性的实现 ,更要依靠创新所要遵循和历经的兼容性。刘氏曾有个通俗的比喻,“比方钢琴是种西 方的乐器,由一个中国人来演奏却不因乐器是西方的而失去本国风格,尤其是演奏中国 作品的时候。同样道理,我并不反对用芭蕾舞的形式来表演《聊斋志异》或《白蛇传》 这样富于中国风土特色的故事。现在更有人用中国乐器演奏西方作品,我看也无不可。 在文学上,这类试验也应该可行。”④(注:《八方》编辑部:《知不可为而为——刘 以鬯先生谈严肃文学》。)又言,“我们可以吸收西洋文学的精髓,加以消化,然后设 法从传统中跳出,创造一个独特的个性。”⑤(注:《刘以鬯实验小说》,第87页。)从 中不难读出刘氏对兼容性的推崇。当然,这一切的最终的目的都指向创新。
(二)文本叙述的探寻
刘以鬯对小说的林林总总的叙述模式可谓谙熟于心,“有的脱离现实进入幻想,如鲍 赫士(Borges);有的将幻想与历史结合在一起,如加西亚·马盖斯(Garcia Marquez); 有的将小说与寓言结合在一起,如葛拉斯(Grass);有的用小说探求内在真实,如史托 雷(Storey);有的用不规则的叙述法作为一种实验,如褒格(Berger);有的用两种方法 写一部小说:一方面是有规则的叙述,一方面是不规则的叙述,如葛蒂莎(Cortazar); 有的将小说和诗结合在一起,如贝克特(Beckett);有的透过哈哈镜来表现现实,如巴 莎姆(Barthelme);有的甚至要求更真的真实,剔除了小说的虚构成分,如目前颇为普 遍的‘非虚构小说’或‘非小说小说’(Nonfiction Novel)”⑥(注:《刘以鬯选集》 ,第15页。)。
熟悉刘氏实验小说的人不难发现刘氏对上述现代小说模式的借鉴和弘扬。如探求内在 真实,诗体小说等等。然而如前所述,刘氏的借用往往也在探索中打下了自己的烙印, 那就是他对“横断面”、“形式”、“格局”等概念的强调和剖析。
“只有用横断面的方法去探求个人心灵的飘忽、心理的幻变并捕捉思想的意象,才能 真切地、完全地、确实地表现这个社会环境及时代精神。”⑦(注:《刘以鬯研究专集 》,第63页,第57—58页,第92页,第63页。)横断面手法的被借用成为现代小说区别 传统小说的主要标志之一。面对芜杂、荒诞、断裂的现世社会,传统的时间序列叙述, 往往要让位于空间形式叙述。“没有格局的叙述是故事。有格局的叙述才是小说。”⑧ (注:《短绠集》。)而格局无疑是指作家对叙述结构与空间的悉心营造。
形式也是刘氏不遗余力宣扬的,要“探索一种现代中国作品还没有人尝试过的形式” ⑨(注:《八方》编辑部:《知不可为而为——刘以鬯先生谈严肃文学》。),创作出与 众不同的文本来。应当指出,刘氏所指的形式并非只是形式内容两分法(Binary Classi fication)中简单的形式内涵,更应该是凝结了创新理念与意义指向的叙述实验,这不 仅可以从刘氏的实验理论中窥豹一斑,更关键的是其小说创作中所体现的这种锐意创新 ,勇于实验的精神。这恰是本文下面所要着力论述的重点。
二、空间形式之一:外在空间
饶有意味的是,刘氏在屡屡强调追求内在真实的同时并未忘记对外在空间的开发。表 面上看来,外在空间似乎更多指向直观、形象、通俗,而缺乏深沉的意义沉淀,如人所 述:“它们缺少震撼人心的力度,它们太过纤巧。”⑩(注:袁良骏《香港小说史》第3 48页。)其实不尽然。我们不妨看看刘氏外在空间形式探索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一)平面直视。显然这种手法会带来明晰形象的视觉效果,绘画或是电影技巧的镶嵌 ,使得原本白纸黑字的小说同样也可以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小说《盘古与黑》①(注 :刘以鬯《盘古与黑》,香港:《香港文学》,1993年8月号。)在描述盘古开天前无尽 的昏黑时,可谓穷形尽相,极尽渲染之能事。首先是文字上反反复复地铺陈,从声音、 色泽、质地等多方观察,仍是黑,到了最后刘氏用了摇镜头手法将许多大小不一、方向 各异、深浅不同的“黑”字,杂乱无章又秩序井然地排到了一起,而这种描述则鲜活泼 辣地体现了铺天盖地的黑对人的巨大压抑。
同样,《黑色里的白色 白色里的黑色》中黑纸白字、白纸黑字,黑白相间的杂陈似 乎有哗众取宠之嫌。然则实际上这种强烈的视觉刺激却让读者在新奇中读出作者的良苦 用心,“原来作者并非玩弄形式,而是充分利用和发挥形式的魅力,使印刷编排本身也 成为‘内容’的一部分。”②(注:温儒敏《<香港文学>小说短评》,香港:《香港文 学》,1992年4月号,P14。)代表罪恶、黑暗、痛苦、贫困描写的黑底白字和代表善良 、快乐、富足、光明的白底黑字,采用异类并置的手法构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而 这种平面直视恰恰映衬了现代都市的迷乱与芜杂,最后的空白(黑)则又暗喻了这种光怪 陆离的无限性和多变性。
(二)立体观照。这种手法无疑凸显了空间形式的多维化和立体性,从而更好地审视描 写对象。《链》是一篇结构奇特的小说,如篇名所示,整篇小说也恰是一个开放的链式 结构,而这种结构也恰恰暗合了某一香港性。首先构成链的每一环扣之间关系并不紧密 ,显出片段化和断裂的趋势,无中心、无情节,显出零散化的解构意识,但同时,这一 结构又有“严谨的内在结构与外在结构:内在结构表现在每个人物的生活片段,都反映 了香港某一阶层的生活,他们共同组成体现了香港的整个社会面貌,不可或缺;外在结 构主要表现在每个人物离场时,都以不同的方式,巧妙地引出了另一个人物出场。”③ (注:《刘以鬯卷》,第418页。)陈可期、姬莉丝汀娜、欧阳展明、霍伟、史杏佛、陶 爱南、孔林、高佬李、单眼鑫、何彩珍……他们可以“躲进小楼”自成一体,但又若即 若离保持适当的联系与距离,而开放的链式结构的采纳无疑恰到好处地反映出林林总总 生龙活虎的香港众生相。我们不难看出刘以鬯“自己是空间和结构而不是时间和序列的 支持者。”④(注:《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第77页,第307页。)
(三)重复与交替。重复与交替的采用往往在浩大的气势中,呈现出相当的哲理性抑或 感情宣泄。《打错了》就采用了一种复式的叙述方式。全文共分两个部分,其中第一、 二部分的前3/5篇幅文字重复。对于读者来讲,如此大的重复显然对他们的耐心是个考 验,当然同时又激发了他们对小说本身的关注。反复阅读后才豁然开朗:重复的部分恰 恰反映了平常人生中的平常故事。而只是在小小的结尾中更映衬出偶然因素影响下人生 的无常。一个打错了的电话,使陈熙“形成了他到巴士站尚有‘不足五十码’的空间距 离。”⑤(注:《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第77页,第307页。)从而使他由车祸的罹 难者变成车祸的目击者。而刘以鬯恰恰借文本篇幅的构成与变化,暗示时空错位中人生 命运的偶然性。
《寺内》中,重复与交替的使用可谓比比皆是。重复的使用往往是对于情感、欲望和 思想的一种造势和推动,如“那墙并不高,他为什么不跳过来?她想。”三次连绵的重 复无疑在滚滚而来的文字中,夹杂了崔莺莺对张君瑞的渴望和欲望的气息。而更加典型 的是第七卷中,“墙是一把刀,将一个甜梦切成两份忧郁”的15次连续重复与交替使用 。这一句话幻化成中国古典戏剧表演中无形的道具?墙(或者门),将张崔二人分隔却又 可以让观众共同鉴赏他们的心灵对话或独白。仅此而已,也只算是刘氏的借用,而“墙 是一把刀”文本中的文字幻化成一把无形的刀,慢慢削薄乃至切除他们的隔阂,直到最 后,刘氏写道:“墙是一把刀,将一个甜梦切成两份忧郁。她哭了。”“墙是一把刀, 将一个甜梦切成两份忧郁。他也哭了。”可以看出,刘氏借此实现了文本篇幅和人物情 感发展上的对称与合拍。同样《对倒》也是采用了人物场景交替的手法。
三、空间形式之二:心理空间
毋庸讳言,探求内在真实与内心独白是刘以鬯实验小说的重头戏,也是他自身创作的 主要指南。无疑,刘氏在这方面的成就最丰,声誉亦最隆。“刘以鬯是一个心理空间感 很强的小说家,他善于利用心理空间的进退、疏离和线性流动来统摄人性与文本虚构。 ”①(注:朱崇科:《故事新编中的叙事范式?以鲁迅、刘以鬯、李碧华、西西的相关文 本为个案进行分析》,中山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5月,第20页。)我们不妨考察一下他 的蹊径独辟。
(一)内省的外露。刘以鬯注意内在心灵探索的特色之一,就是将原本隐藏的东西从潜 意识抑或隐晦中剥离出来,使其走向外露,甚至透明化。《蜘蛛精》的出现,显然呈现 了作者对《西游记》中,唐僧凡性(心)勾勒模糊的不满与质疑,他将唐僧放在人性的拷 问台上进行残酷的讯问。“小说采用作者叙述和角色内心活动跳接的手法,使整个场面 更富戏剧性。”②(注:《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第208页。)它用一种极具逼迫感 、文字密度极大的语言,展示了唐僧在面对蜘蛛精步步进逼时思绪的纷繁芜杂徒劳挣扎 ,直至最后防线被步步瓦解的思绪转换。唐僧内心的紧张、纷乱、甚至窒闷,令人想到 心电图中起起落落的波状显示。而黑体字阿弥陀佛等的频频闪现,又表明了唐僧脆弱人 性逐步崩溃的密度。
刘氏的《寺内》,是他大刀阔斧重写《西厢记》的结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性 爱理论与精神分析在文中隐隐可显。所以《寺内》成了“突出其性爱定义的文本”③( 注:容世诚:《“本文互涉”和背景:细读两篇香港小说》,见陈炳良编《香港文学探 赏》,香港:三联书店,1991,P289。)。作为《寺内》源头的《西厢记》,尽管在文 明的历程中并没有抹煞其性爱色彩,但刘氏的改写却更充斥欲望的当下性。《寺内》中 ,几乎所有的女人都迷恋张生,几乎所有的男人都禁不住莺莺的诱惑,无疑说明了性意 识蓬蓬勃勃的流动和它对《西厢记》的镶嵌。当然有人对这种改写存有疑惑,认为这样 写诸多“性意识、潜在性意识、病态性意识”,对1000多年前的古人来讲是否符合古人 古事,是否太离谱?“一切都赤裸化、性化甚至原始化、动物化”,是否对经典著作的 亵渎?④(注:袁良骏:《香港小说史》,第358页。)不管人们对改写结果反应如何,有 一点非常清楚,内省的透明化已成为刘氏心理空间探索的重要技巧。
(二)隐喻与“诗化意识流”⑤(注:周伟民、唐玲玲著《论东方诗化意识流小说》,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刘氏心理空间的开创手法的复杂性,还反映在他 其实非常强调的开拓内心真实的诗化做法与隐喻特征里。这尤其以《酒徒》和《寺内》 为代表。
严格说来,《酒徒》的故事性很弱,它的并不曲折离奇却足以让出版人一版再版,个 中原因耐人寻味。作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刘氏对结构的营造可谓煞费苦心。作者 主要以“现时的理想和现实之间,通过醒与醉的转换展开作品。”⑥(注:王毅:《眼 睛的撤退?刘以鬯的<酒徒>与西方意识流小说之比较》,见黄维梁编《纷繁活泼的香港 文学》(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新亚书院2000,第512页。)酒徒的醉与醒既刻划 了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同时这种空间结构又推动了小说的发展。鉴于他人对于《酒徒》 的相关评论较多⑦(注:主要著述有香港获益出版公司的《<酒徒>评论选》。),笔者在 此不赘。
而这种手法在刘氏的另一代表作《寺内》中,也是发挥得淋漓尽致。首先是意象的灵 活运用,最为经典的则是小飞虫,在张崔二人的爱恋中,小飞虫意象频频以不同面貌展 现活跃异常,它如同一把锋利的小刀挑开了层层被掩盖的真实。同样鹦鹉之于莺莺,麻 雀之于老夫人等,都是她们内心阴晴变化的目击者,起到了揭示真实人性的作用。其次 是诗性话语的妙用。诗性话语的潜入,一方面扩大了小说意义的张力空间,另一方面又 对历史时间作了隐性处理。《除夕》中刘氏对于曹雪芹肆意挥洒青春的青少年时代、中 年以及凄惨的晚年进行的历史接驳,也采用了类似手法。
(三)梦幻。梦幻本身可能寓含了另外一种真实。如人所论,“梦幻与场景的关系,更 多的是梦幻对场景的凌驾与导引,这是物质与精神层面的作用与反作用……但梦幻与场 景的关系还不仅于此,它的更深的内涵包含着梦幻对场景的颠覆,或说梦幻对现实的颠 覆。”①(注:张世君:《红楼梦的空间叙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 —104页。)
《寺内》中“额角还没有皱纹”的老夫人,背叛了相国门楣里的道德传统:在梦中“ 她见到了自己与那个年轻的男人睡在一起。而那个年轻人竟是张君瑞。”原本作为相国 府道德伦理的捍卫者和执行者,在梦中却颠覆了自己的现实角色。而莺莺在孙飞虎包围 普救寺时也做了两个梦,她希望是张生而不是孙飞虎直面自己的胴体,因为她想看看读 书人可以“使孔夫子流泪”的床上的疯狂。
《蛇》中许仙的梦更是别有意味,刘以鬯为了将神话故事变成实实在在的人间故事, 白蛇昆仑山盗灵芝草这个家喻户晓的神话退缩成许仙病中的一场梦。当他“从梦中醒转 ,睁开惺忪的眼,见白素贞依旧坐在床边,疑窦顿起,用痰塞的声调问:‘你是谁?’ ”白蛇是千年蛇精的传说也渐次被颠覆,“白素贞已经变成一位勇于追求幸福生活的实 实在在的人。”②(注:《刘以鬯实验小说》,第204页。)
四、结语:什么在隐退
对空间形式的侧重势必会引起诸多传统手法的隐退。先可能是时间顺序、因果关系, 而具体到小说自身的构成,情节、人物、故事似乎都可以成为挑战的对象,至少对刘以 鬯来说是这样。
《追鱼》是一个极短篇小说(全文300来字),但情节隐蔽。刘氏采用了电影速写手法, 第一日至第六日事件的发展采用了如下结构:A1—A2—A3—B—C1—C2—C3(其中A1,A2 ,A3与C1,C2,C3系列是指它们的语句有重复之处),异常简单的架构却显出了空间的 功用,“象外之义”恰从此而生。如人所评,“《追鱼》巧妙运用了空白艺术,使作品 清简俊逸,空灵秀拔,墨光四射,无字处皆有字。作品时空的界限大大突破了,作家将 读者的眼光和神思从有限引向无限。”③(注:谢福铨:《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论 刘以鬯小小说<追鱼>》,香港:《文汇报·文艺周刊》1999年4月19日,第725期。)
而《吵架》似乎走得更远,不仅没有情节、没有中心人物,甚至连人物都没有。作家 将笔墨全集中在写物的场景上,由物及人。因吵架而被打碎的物品和房间内在“战争” 后的一片狼藉与凌乱不堪,暗示了男女主人吵架的激烈与矛盾的尖锐程度。而这一切, 需要通过对作者创造的物的空间场景间接推及,我们不难看出刘氏的匠心独具和利用空 间形式所作的创新。
总而言之,空间形式与刘以鬯实验小说的契合,既奠定了他在香港文学史上的地位, 同时又彰显了他文本中不可遏抑的香港性,正所谓香港虚构。如杨义所言,“如果这样 谈论刘以鬯,说他承受着香港商品经济浪潮铺天盖地的冲击,以始终不懈的艺术真诚, 在南天一隅出奇制胜,率先使华文小说与世界新锐的现代主义文学接轨。那么,他在香 港,甚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凸现出来了。”④(注:杨义:《刘以鬯小说 艺术综论》,北京:《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第139页。)当然,从空间形式角度 论述刘以鬯的实验小说只是一种视角,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希望借此机会抛砖引玉, 从而激起更多更新更深视点的立体综合观照。
标签:刘以鬯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香港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现代小说论文; 酒徒论文; 西厢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