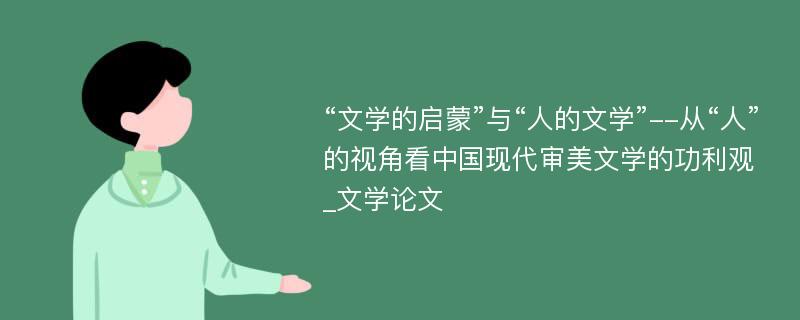
“文学的启蒙”与“人的文学”——从“人”的角度看中国现代审美性文学的功利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功利论文,角度看论文,中国论文,性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824(2006)03-0051-04
五四新文学开辟的启蒙传统不仅是思想的启蒙,同时也是文学的启蒙。陈思和先生分别称之为“启蒙的文学”和“文学的启蒙”。他指出:这两种新文学的启蒙在性质、宗旨、任务上都有很大差别。“启蒙的文学”是传播新思想的载体,目的在于为新文化的思想启蒙服务,因此它所承担的是一种非文学的任务;而“文学的启蒙”则是以新文体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它的旨意在于建设20世纪的美感形式与审美精神,启发读者对美的敏感与重新发现,进而提高和更新民族的审美素质。[1] (P31-33)这两种启蒙意识指导下的文学构成了现代文学发展的两个主要方面。尽管二者在不同时期产生过分歧甚至严重的对立,但它们一直同时并存且作为五四新文学的两种传统贯穿于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以前,我们总是把现代文学置入文学/非文学(政治)的二元对立中加以确认。认为“启蒙的文学”就是工具化、政治化文学,“文学的启蒙”就是纯文学、审美性文学,且二者水火不相容。好像前者只有功用而没美感,后者只求美感而不屑于功用。尤其是对于“文学的启蒙”,只强调其纯粹的审美性,而忽视其审美特质隐藏下的特殊的功用性和价值观。本文拟从“人的文学”的角度观照这种审美性文学内在的功利观。
文学即人学,文学的存在方式最终取决于人的存在方式。五四新文学正是在高扬“人的解放”的大旗下摧毁旧的文学观念,开始了新的文学历程。“文学的启蒙”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把个人的发现、人性的净化、人的审美素质的提高等作为其启蒙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而表现出与侧重从社会领域、思想领域等外部进行启蒙的“启蒙的文学”不同的功利观。在现代文学发展的三个十年中,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其中,20世纪20年代的周作人、30年代的沈从文、40年代的徐訐分别是各个阶段的突出代表。
五四时期,为了配合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先驱们以摧枯拉朽之势颠覆了旧的陈腐的文学观念,一种新的现代性的整体文学观应运而生。受当时斗争现实的影响,新文学的倡导者们虽然矛头直指“文以载道”的旧文学观念,反对文学的功利性,强调文学的主观精神和审美特质。但由于他们本身就是以文学作为斗争的手段和工具,所以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反封建的战斗色彩和积极进步的社会功利性。文学革命的先驱们也都自觉地把文学的社会功用作为新文学的重要特征而加以标榜。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就明确说:“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的文学才能“成真正的文学”。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更是从政治革命的高度来思考文学的革命。他们虽然反对旧文学的文以载道,但好像更多的是反对载“旧道”,而并不排斥文学传“新理”。很明显,胡适、陈独秀等注重的还是从外部社会特征来阐述文学的,走的自然是“启蒙的文学”的路子。
周作人则有所不同。早年留学日本时他就曾以锐利深刻的目光关注并探讨文学的性质问题。与他人不同的是,他特别强调文学在表现人生过程中的三大要素:“具神思,能感兴,有美致。”既把文学从传统的被众多外部社会作用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强调其内在的美的特质;又未完全抛弃文学的功能价值,把文学和人结合起来,从人的角度阐述文学的独特价值。周作人的这些观点,是对文学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独立性观念的较早触及,是五四新文学整体观念确立的理论先导。到五四时,虽然同处于一个革命的时代,作为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不可能完全抛开功利去谈文学,但与陈独秀等人从社会的角度探讨文学的作用不同,周作人更多地是从“人”的角度去观照文学,把现代人的改造作为文学的核心命题。第一次大张旗鼓的在文学里谈人和人性,并把它作为文学的本质特征和独特价值。在这点上,较之胡适、陈独秀的文学改革明显深入得多,也在理论上完成了新文学的嬗变。
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集中地阐述了他的新文学的理论主张,正式打起了“人的文学”的大旗。他把新文学的本质内涵高度概括为“人的文学”四个大字。即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崇尚自然的灵肉一致论。他认为,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故“兽性和神性结合起来的便是人性”。所谓兽性就是人的自然本能性,人既然是生物,那么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应得到完全满足,凡是违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所谓神性就是“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尚和平的境地”。其二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周作人把人道主义解释为:“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就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2] (P194-195)可见,周作人所强调的人道主义,就是要以个人为本位,充分肯定人自然本性和自身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而以这种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人的文学”也必然是呼唤人的发现和觉醒、尊重人的自然本性与独立尊严的文学。对于这种“人的文学”的价值观,周作人进行了深入地辨析:“艺术派的主张,是说艺术有独立的价值,不必与实用有关,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但在文艺上,重技工而轻情思,妨碍自己表达的目的,甚至于以人生为艺术而存在,所以觉得不甚妥当。”否定了远离实际人生的艺术派。对于盛行的人生派他也并不苟同:“人生派说文学要与人生相关,不承认有与人生脱离关系的艺术。这派的流弊,是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坛上的说教。”两派均有偏颇。那么周作人认为自己理想的“人的文学”:“正当的解说是仍以文艺为终极目的。但这文艺应当通过了著者的情思,与人生有接触。换一句话说,便是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到艺术的享乐与人生的解释。这样说来,我们所要求的当然是人生的艺术派文学。”[3] (P141)看来,这种“人生的艺术派文学”既不是实用的功利性文学,也不是完全不讲功利的“纯文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超现实的功利观。那就是通过文学对人的影响而实现文学的独特价值。它表明,周作人从人的角度而谈文学,是注重文学的内部规律性和文学性的。文学即人学,“文学性是与人类生存的本体域紧紧相连,或者说,它就是人类的经验存在和人性本身的体现。”[4] 人和人性是文学的本质内涵。因此,周作人最初提倡的“人的文学”,既是从文学的内在特质谈文学,显示了他与陈独秀等不同,走的是“文学的启蒙”的路子;又是从人的角度来界定文学的功用,表现了他与众不同的文学功利观。
当然,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唤起国民的任务远远大于文学性的追求。为了斗争的需要,周作人在他的“人的文学”中,自然对“人生的”的一方面突出较多,可文学性、审美性始终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可实际上人们一般都是从周作人后来创办“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这个角度来理解“人的文学”这一主张的现实功利性,而大多忽视了其前期包含的“文学性”内涵。有人就认为:“正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开了为人生的艺术大门,无异给新文学写了一张卖身契,被人辗转贩卖,直到今天还没有恢复自由之身。”[5] (P118)固然周作人在文学研究会的宣言中过多强调了为人生的艺术。但从他早期“人的文学”的本意来看,似乎并不完全如此。如果新文学确实被贴上了卖身契,那么这张卖身契大抵更多是后人贴上去的,似乎并不完全出自周氏的本义。
但周作人自己也很快就对“人的文学”后来被赋予越来越明显的现实功利感到不满和厌倦,在1923年出版的《自己的园地》中表明了自己的文学再认识。人们认为这是他由此前新文学主潮的带头人变为自由的思想者的转折,由为人生而艺术转向自娱自乐、完全不考虑价值功用的纯文学,并长期被人们所不齿。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自己的园地”这个提法并不一定要照字面理解为非功利,周作人在此反对的是浅薄的外在功利,他的意思是“不为而为”。一部文学作品只要“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虽然本意不是“为福利他人而作”的,不是功利的,也能使他人引起共鸣而得到“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周作人称之为“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对于文艺和人的关系,他说:“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人们为作用,是个人的而亦为人类的。”[6] (P8-10)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和当初人的文学含义的一致性,还是注重文学对人和人性的作用,从人的角度来探求文学的功用,这是内在的功用,亦是无形的功用。此时的周作人想剥离掉附在人的文学身上太多的社会功利,还其以本来面目,重返他的以人为核心的“文学的启蒙”,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可惜后来却矫枉过正,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他强调“讲闲话”与“玩古董”,日益自囿于草木虫鱼,鬼神古董,彻底地沉沦在“自己”封闭的王国里。这样,既背离了“人的文学”主张,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学的启蒙”。这同时也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对于人的文学,无论是社会功利膨胀过了度,还是自由独立强调过了头,都将是一根藤上的苦果。
周作人虽然提出了人的文学,但由于当时斗争的需要和他后来的沉沦变节,他本人其实并没能很好的在创作中体现。真正落实这一主张的,还是后来的一些作家。20世纪30年代的沈从文、40年代的徐訐是突出的代表,他们分别从“人的文学”内涵的两个方面实践和丰富了周作人的文学主张。
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构成了特殊的文学氛围,文学和社会现实的联系日益紧密,文学发展在整体上呈政治化趋势,“启蒙的文学”占据了主流地位且排挤“文学的启蒙”。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却能安于他的湘西世界,坚守“文学的启蒙”,创造了独特的文学天地。
一般认为,以沈从文为代表的20世纪30年代的审美性文学(即文学的启蒙)是反功利的。的确,沈从文曾反对将文学纳入商业和政治的功利圈,主张“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的独立文艺观,并因此与当时强调现实批判和社会功利的左翼文学主潮相对立而沦于长时间的寂寞。后来人们也正是以超功利和独立性的文学审美眼光重估他的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实际上,沈从文也不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有着不同于左翼文学的文学功利观。即通过文学揭示、祛除丑陋的人性,表现、重塑美好的人性和生命形式,在他的人性王国里实现文学的独特价值和功用。沈从文曾明确表示文学要使读者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和生命作出更深一层的理解。通过文学达到对“生命的明悟”,“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欲望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我认为推动或执行这个工作,文学作品实在比别的东西更其相宜。”[7] (P114-115)他同时希望作家努力制作“真的对于大多数人有益,引导人向健康、勇敢、集群合作而去追求人类光明的经典”,努力制作“那类增加人类智慧,增加人类的爱,提高这个民族精神,富饶这个民族感情的作品。”他希望作家应该有“对于一切人性的认识或了解——这认识或了解不特是社会、经济的,还应当是生理、心理的”。[8] (P191)重视人的自然本性,强调文学提升人生品格,再造民族灵魂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与“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文学启蒙思想有某些承传之处。在他们的文学观念中,同样具有一种特殊的功利性。
在创作上,沈从文主要是从自然性这一翼实践和丰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五四文学中还备受压抑扭曲的自然性,到了沈从文笔下已经成为人性中不可剥夺的一部分。他通过家乡奇异的自然风物、人情世态,展示湘西普通人自然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及其在时代的大力挤压下的扭曲和变形,在与都市人生的比照中,讴歌了湘西底层人民身上朴素自然的人性美和恒久的生命形式。通过两种不同的人性和生命形式,体现作者对美好的自然本性的追求与向往。在《绅士的太太》、《八骏图》、《有学问的人》等一系列表现都市人道德堕落和人性沦丧的作品中。那些“高等人”“文明人”在种种绳索中捆绑住自己,拘束人的自然本性,跨入更加不文明的轮回圈中。作者以毫不留情的犀利之笔,撕下了文明人的道德面纱,揭示出都市人生变异人性的荒唐和可笑。但他的这种讽刺暴露与同时期以讽刺文学著称的张天翼、沙汀等所取的角度有明显的不同。他不是从社会历史角度暴露上流社会的腐朽、庸俗、自私,而是从人性道德角度切入都市人生,切入到人性最深处,揭示上流社会人的本质的失落与自然本性的扭曲。与此相对,沈从文心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对人的美好自然本性的追求。他把民族出路的探索和变革现实的希望寄托在完美人性的再造上,他要在世风日下的现实中用文学重塑美好的人性王国,以期对现实中日趋污浊的人性有所净化。沈从文在谈及《边城》时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9] (P78)作者目的不在于描绘一幅与现实隔绝的世外桃源,而是从人性道德视角去透视一个民族可能的生存状态及未来走向。在这个湘西世界里,那古风犹存的乡野村落,那未被浸染的自然本性,沈从文于此寄托了他对美好人性的深情回味和向往,并含蓄地表明了他独特的文学价值观。
京派研究学者吴福辉认为:“京派在对民族进行过去和当前对照时,他们仍然采取以城市代表当前,以乡村代表过去的模式,肯定乡村的文化和下层的人性,否定上层的文化和城市的人性,认定前者是人性和自然的契合,后者是违背自然的人性扭曲。”[10] (P14)从人的自然本性这个意义上讲,到沈从文这里,周作人的人性学说得到具体落实,同时代的梁实秋虽然也提倡人性说,但他更多是强调理性节制,较注重社会性对人性的某种控制。而沈从文才是从自然性方面典型地消化了周作人“人的文学”理论。
20世纪40年代,抗战是时代的重中之重,“启蒙的文学”理所应当地成了以民主和抗战为主旋律的“抗战文学”,并几乎占据了整个文坛。而“文学的启蒙”因在战火纷飞的时代不合时宜而少有人问津。但在这众口一词中,仍有独特的异响,徐訐就是其中的一位。
与时AI写作作——抗战文学不同,徐訐的创作是一种审美主义的个人性写作,它使在极端环境下被时代话语海洋所吞没的个人性话语再一次浮出海面。在文学功利性很强的40年代,徐訐因追求文学性、通俗性而卓然独立,同时也长期被主流文学所排斥。但徐訐的创作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非功利。和时AI写作作直接、实用的功利观不同,在其文学性、通俗性下有着内在的独特的功利观。即通过人性的挖掘与塑造、从人的视角来实现文学独特的功用。它与时代的关系不像时AI写作作那样直接、明确地将时代的要求与文学的要求合而为一,而是将时代作为个人生存的一种维度,从个人的视角对时代作出一种回应和对话。与现实主义文学将现实主义理解为社会政治现实不同,它所关注的现实主要是个人性的精神现实。在此非政治性、现实性的立场下,实现其更为深远的超民族、超时代的价值关怀。徐訐的成功虽缘于文学性和通俗性的结合满足了由八股气日重的时AI写作作所轻视的大众审美需求;但更主要的是其于趣味性、传奇性的情节框架下还有着对人性、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作形而上的哲学追问。去掉其传奇性外衣,我们发现徐訐与20世纪20年代的周作人、30年代的沈从文在“文学的启蒙”与“人的文学”的关系上有着某些一致的地方。
所以,徐訐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虽都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展开,但它不从社会现实角度直接响应抗战;而重在从个人的视角挖掘更为深沉的人生哲学。“爱”和“浪漫”是其创作的常见主题,他既有通过个人视角来表现爱的哲学,又有对极端个性主义的揭露探究,更有对人性洞察幽微:《风萧萧》不是从正面写社会抗战的,而是从个人的角度以爱和美为核心去观照时代和社会。小说的主人公徐,在沦为孤岛的上海从事一项学术研究工作,“这是关于道德学说、美学的一项研究,想从美与善寻求一个哲学渊源作为一个根据去写一部书。”这句话是理解这部小说的一个钥匙。虽然后来时局的动荡使他无法安坐书桌进行这项研究,但他走出书斋投入时代的漩涡之后,仍然用行动为这种善与美寻到了同一个哲学渊源,那就是“爱”。作家正是从个人的角度,用爱串起人性的美与善,使这部小说在当时战火纷飞的抗战文学大潮中富有个性之美、闪耀着人性之光。剧本《生与死》探讨了个人主义走向极端后的危害,也即“爱”的哲学的反面——一种个人主义的怨恨、复仇心理。由于社会的不公和欺骗,主人公产生复仇情绪而错杀无辜。但经过良心的煎熬,最后作为人的良知复活了,认识到自己选择的是一条背弃人性的不归之路,并为此作出了沉痛的忏悔,主动去承担自己的罪责进而获得心灵的平安。“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周作人的观点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在徐訐看来,“恶”并非完全由社会造成的,它还源于人性自身的残缺。因此,单靠反社会的个人复仇和对社会这一外部环境的改造并不能真正消灭恶,必须从人性的深处着手,剔除人性的痼疾才能去恶。小说《灯》用非英雄化的方式剖析了一位平凡的抗日“英雄”复杂的内心世界。抗战文学中英雄人物的行为都是出自先进阶级和集体的高尚品德的影响,而这篇小说主人公的“壮举”只是出于个人的没有理由的本能,一个奇怪的道德的本能。它类似于良知,是一种宗教性道德而不是社会性道德。主人公成为“英雄”抑或“罪人”,好像都具有某种偶然性,其不是没有内心的斗争和妥协的可能。抗战文学强调的多是社会性因素,而徐訐则关注的是个人的人性本能。
就这样,徐訐在20世纪40年代“启蒙的文学”为了时代而忘掉个人性和文学性的时候,把文学和人联系起来,以个人性的审美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文学的启蒙”。就这点来讲,其实质是和周作人、沈从文一脉相承的。如果说沈从文是从自然性一翼落实周作人的“人的文学”,那么徐訐主要从“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个角度实践之。但徐訐又加上了通俗性、传奇性的外衣,其影响之广也就可想而知了。
审美和功利本来就是文学始终纠缠不清的问题,在中国现代这些主张文学审美性的作家身上尤其如此。如果我们把人、人性放入其中一起考察,似乎可以廓清一些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功利追求本身就是一种人性的表现,但过分沉溺于功利又是一种人性的危险,于是就要有审美价值的强调。周作人、沈从文、徐訐正是从人的文学的角度来看待审美性文学的功利,试图把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构筑他们独特的文学殿堂。由于种种原因,后人难以避免地对他们有些误读。今天,当历史的烟雾渐渐散开,我们从文学的多种功能的角度平等地看待他们及其文学观念,追寻他们探索的足迹,是耐人寻味的。
标签:文学论文; 人的文学论文; 艺术价值论文; 人性观论文; 艺术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沈从文论文; 周作人论文; 人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