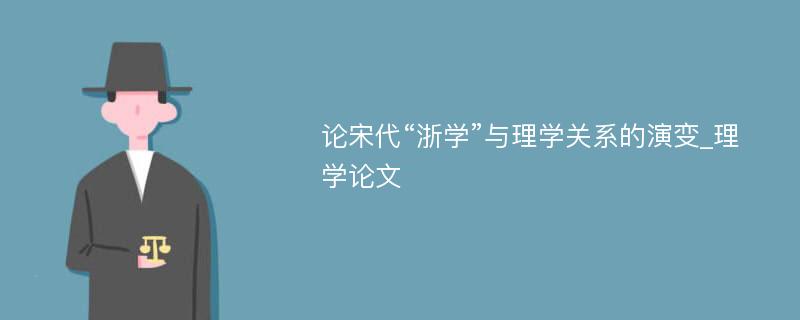
论宋代“浙学”与理学关系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宋代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0)02—0067—10
两宋时期,浙江地区文化发达,学术繁荣,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其中许多学者和流派与理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有的以积极传播理学为己任;有的在传播过程中注重对理学的修正和发展;有的则最终走上了反理学的道路。这使得“浙学”在深受理学思潮影响的同时,也对理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试就“浙学”与理学关系的演变过程作一番历史性的具体考察与分析。
一、北宋时期的“浙学”与理学
宋代“浙学”与理学的关系最早可追溯到北宋中期的庆历(1041—1048)、皇祐(1049—1054)年间。此期浙江地区先有以明州(今浙江宁波)“杨杜五子”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与理学先驱之一的胡瑗及其“湖学”在学术和教育上互相呼应,继有永嘉(今浙江温州市)学者林石等人对“湖学”的积极追随和传播。
“杨杜五子”是指庆历前后活动于浙东地区的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五位学者,故又称“庆历五先生”。他们虽与胡瑗并无直接交往,但在许多方面明显表现出受到“湖学”的影响。如五位学者一生都安贫乐道,淡泊名利,唯对教育和学术活动孜孜不倦,这与“湖学”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以及把学术研究与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风格极为相似。而在学术思想和教育方法上,史称杨适“治经不守章句”,注重“究历代治乱之原”;楼郁“志操高厉,学以穷理为先”;王致、王说“讲贯经史,倡为有用之学,学者宗之”(《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这更与胡瑗所积极倡导的既重经义(注重对儒学经典的重新解释)又讲实用(讲求学术研究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合拍。诚如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所指出的:“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吴师仁,皆与安定湖学相应。”(同上)
与杨杜五子相比,号称永嘉“皇祐三先生”之一的林石与“湖学”的关系更为直接。林石(1004—1101),字介夫,永嘉瑞安县人,学者尊称塘岙先生。作为胡瑗的再传弟子(他是胡瑗高足管师常的学生),他一生笃奉“湖学”,不仅“以明经笃行著称当世”,而且广收生徒,“以其说窃教授诸乡生”(《止斋集》卷四十八《新归墓表》),长期坚持不懈地进行传播“湖学”的活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为稍后“洛学”、“关学”在永嘉地区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
不过,“湖学”毕竟不是正式的理学流派,真正把理学思潮全面引入浙江并对“浙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是继林石等人而起的“永嘉九先生”,亦即生活于北宋中后期的周行己、许景衡、沈躬行、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宵、张煇、蒋元中九位学者,他们是“洛学”、“关学”在浙江的主要传播者。其中,周行己等六人曾直接师事程颐,并一度问学于关学的主要传人吕大临;赵宵等三人则是私淑洛学。南宋永嘉学者陈傅良在《重修瑞安县学记》中说:元丰、元祐年间,“许公景衡与沈公躬行、谢公佃偕同郡诸儒,又尝越数千里外,窃从程(颐)、吕(大临)二氏问学”(《止斋集》卷三十九)。《宋元学案》亦云:“(洛学)其入浙也,以永嘉周、刘、许、鲍(若雨)数君。”(卷二十九《震泽学案》)又云:“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也,不知其兼传关学。考所谓‘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门,其三人则私淑也。而周浮沚(行己)、沈彬老(躬行)又尝从蓝田吕氏游,非横渠(张载)之再传乎?”(卷三十二《周许诸儒学案》)其实,“九先生”中最为年长的周行己不仅兼传关学,而且其早年还一度学习过王安石的“新学”。他是元丰六年(1083)开始进入太学学习的,而此时王氏“新学”仍是太学的主要教学内容,直到元祐二年(1087),宋廷才正式规定科举和太学“毋得专取王氏”(《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吕公著传》),行己亦由此转向洛学。对此,周行己后来在回忆自己的求学经过时也承认:“是时(指元丰六年)一心学科举文(即王安石的《三经新义》等书),编缀事类,剽窃语言,凡所见则问而学焉。”(《浮沚集》卷五《上祭酒书》)
正因为“九先生”在接受洛学的同时,又受到关学、新学等诸多学派的影响,而浙江地区十分浓厚的求实致用学风也使得他们并不满足于对师说的简单因袭和传递,故在一些方面呈现出与正统洛学的不少差异。特别是作为九先生代表的周行己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在政治思想上,二程对王安石变法及其新学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却是介甫(即王安石)之学”(《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而周行己却对新学颇为尊重,以至将王安石的得意门生龚原与程颐、吕大临并称为“能传古道”的“当世儒宗”。与此相似,对于与洛党在政治上尖锐对立的蜀党领袖苏轼等人,周行己也一再给予称赞。故四库馆臣评论说:“行己之学,虽出程氏,而绝不立洛、蜀门户之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五五)为此,周行己不仅受到程颐的批评,也为后世诸多正统理学家所抨击。如朱熹公开指责说:“周行己学问靠不住。”(《宋元学案》卷三十二《周许诸儒学案》)在哲学思想上,周行己一方面继承了二程的“理”、“道”本体说,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关学的“气”说,认为气的阴阳相荡,升降沉浮,是由“道”成物必不可少的动力(《浮沚集》卷二《经解》);一方面强调为学要“去其养心之害,而导夫至正之路”,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各因其仁智之见,而成其才”,亦即人的成才要靠后天的学习(《浮沚集》卷三《孔门四科两汉孰可比》);一方面坚持洛学所宣扬的由二程承孟子而续儒学正统的“道统”说,另一方面又大胆地指出,从孟子到二程之间的汉唐时期,“圣人之道”并非一片空白,“若两汉数百载间,岂无豪杰特出之士能传圣人之学于千百载不传之后?”(《同上》)在学风上,正统洛学专重修心养性,“涵泳义理”,而周行己却强调注重实际、学以致用,认为“学病乎无实,不病乎无名”(《浮沚集》卷四《送强应物序》)。为此,他身体力行,不仅研究经学,也注意结合社会实际探讨诸如天文历法、兵家要略、财政经济、政治刑律乃至医学等方面的有关问题。周行己等人的这种继承师说而又不拘泥于师说、传播一学而又不局限于一说的思想和学风,对后世浙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南宋时期浙江地区各种流派的风涌而起,以至同一流派之中也是派别纷云,支流繁杂,亦正是由此出现的。
除九先生外,在北宋后期,永嘉地区的洛学传人还有鲍若雨、陈经邦、陈经正等一批学者。据《程氏外书》卷十二记载:“温州鲍若雨商霖,与乡人十辈久从伊川。”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也说:“鲍敬亭辈七人,其五人及程门。”(卷三十二《周许诸儒学案》)这当中,陈经邦、陈经正兄弟算得上是程颐晚年较有名的学生,现存《程氏遗书》和《程氏外书》中尚有他们与程颐的20多条问答。就永嘉学术发展而言,二陈对南宋中期以徐谊为代表的温州“平阳之学”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影响。史称:“平阳学统,始于先生兄弟,成于徐忠文公宏父(即徐谊)。”(同上)
总的说来,北宋中后期是宋代浙学的崛兴阶段,也是理学思潮开始传入浙江并对浙学产生很大影响的时期。但由于浙江学者多以灵活求实的态度和积极开拓的精神来接受和传播理学思想,使得他们在不少方面呈现出与理学主流派有所不同的特点。
二、南宋中期的“浙学”和理学
经过北宋时期的发展,到南宋中期,浙学进入全盛阶段。在短短几十年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形成了诸多各具特色的流派。如温州地区有“郑氏之学”、“平阳之学”“永嘉事功之学”;婺州(今浙江金华市)地区有“吕学”、“永康之学”、唐氏“经制之学”;明州地区有“四明之学”等。这些流派与理学的关系形态互异,各不相同,有的是在理学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有的成为理学的主要流派;有的则以强烈的反理学倾向闻名于世。这使得此期浙学与理学之间呈现出既全面融合又互相冲突的关系。
“郑氏之学”是北宋时周行己等人所传洛学进一步发展演变的产物。其代表郑伯熊(1124—1181),字景望,学者称敷文先生,温州永嘉县人。史称:“永嘉诸先生从伊川者,其学多无传,独先生(指周行己)尚有绪言。南渡后,郑景望私淑之,遂以重光。”(同上)确实,从思想上看,郑伯熊继承了周行己所传洛学的诸多观点,如主张性善论,认为“万善本吾性之固有,学至于圣贤,于性无所加焉,而缺一则不足以为尽性”,故人人都应“省己修德”,“存天理,克人欲”(《敷文书说》)。不过,与此同时,他也继承了周氏的学以致用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对洛学作了进一步的改造,结果招徕了朱熹等人诸多责难,认为他表面看“气象虽好”,其实是“昏了正意”(《朱子语类》卷七十九)。也正因为如此,在郑伯熊之后,继其而起的郑伯英、郑伯谦等人越来越远离正统的洛学思想,最终转向了具有强烈反理学倾向的“事功之学”。故清人孙诒让说:“敷文之学,没而无传”(《浪语集·序》)。
“平阳之学”从渊源上看属于北宋后期温州洛学的另一支绪余。其代表徐谊(1144—1208),字子宜,又字宏父,温州平阳县人。徐氏之学主要承接前文提到的陈经正、陈经邦兄弟所传的洛学。与周行己等人有所不同的是,陈氏昆仲侧重于发展洛学中的“心”“性”之论,强调“盈天地间皆我之性”(《二程集·程氏外书》卷一一),而徐谊将这种倾向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对此,与其同时的另一位永嘉学者叶适曾评论说:“公以悟为宗,县解昭彻,近取日用之内,为学者开示。修正所缘,至于形废心死,神视气听,如静中雷霆,冥外朗月,无不洗然自以为有得也。”(《水心文集》卷二十一《徐谊墓志铭》)可见,徐氏之学实际上已逐渐向“心学”靠拢。不过,徐谊的这种学术倾向到其学生彭仲刚、黄中等人那里又发生很大的变化。史称黄中主张“论学应实地用功,不徒托之空言”;彭仲刚“其材为实材,德为实德,此先生之学之大致也。”(同上卷一五《彭子复墓志铭》)。这与当时永嘉事功学者的观点和学风颇为相似,表明“平阳之学”也同“郑氏之学”一样,最终与事功之学合流了。
以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婺州金华县人)为代表的“吕学”向被人们视为南宋中期与朱学、陆学相提并论的三大理学流派之一,在宋代理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宋元学案》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陆学也;吕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卷五十一《东莱学案》)从渊源上看,吕学的兴起与北宋中期以来延续不断的吕氏家学密切相关,而吕氏家学与洛学的关系又非同一般。如吕祖谦的六世祖吕公著“自少讲学,即以治心养性为本”,与二程交谊深厚,引为同调(同上卷九《范吕诸儒学案》);公著之子希哲“归宿于程氏,集益之功,至广且大”(同上卷二十三《荥阳学案》);希哲之子好问也“贤临一时”,与北宋末著名洛学学者杨时齐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吕学乃是在洛学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吕氏家学在治学风格上又具有“不名一师,不主一说,兼取众长”的特点,如吕公著在推崇洛学的同时,对王安石的“新学”、邵雍的“象数学”等也很是赞赏;吕希哲虽最终“心服伊川学问”,但也吸收了焦千之、孙复、石介等人部分思想;至于希哲之子本中则更是公开倡言:“既自作主张,则诸子百家之长皆为吾用。”(同上卷三十六《紫微学案》)受此家学学风的影响,吕祖谦对诸家之说也采取了“兼容并包,委曲拥护”的态度,不仅力图将各个理学流派、特别是朱学和陆学统一起来,由此导致其理学思想具有浓厚的折衷与调和色彩;而且还积极吸取了诸家事功之学的不少观点和主张,如在理欲观上,认为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性异行”(《吕东莱文集》卷四《与朱元晦》),亦即在一定条件下天理和人欲是统一的;在义利观上,主张“利者,义之和也”,“义之和处,即是利也”(同上卷十二《易说·乾》),这实际上是承认义与利的一致性。在历史观上,提出“有因有革”的历史变革论和“天下之事向前则有功”的历史发展论,反对“言必称圣人,行必效贤哲”的复古守旧思想。在学风上,强调“大抵为学,不可令虚声多,实意少”(同上卷二十《杂说》),力求学以致用,等等。这些观点和主张实际上也正是浙东事功学者在与朱熹等人的激烈争论中所一再强调的。为此,朱熹曾多次对吕祖谦提出批评,以至将其视为与事功学者同类,认为“伯恭之学合陈君举(傅良)、陈同甫(亮)二人之学问而一之。永嘉之学理会制度,偏考其小小者;……同甫则谈论古今,说王说霸;伯恭则兼君举、同甫所长”(《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
以明州学者舒璘、沈焕、袁燮、杨简(即所谓的“甬上四先生)为代表的“四明之学”按《宋史》所言是“得陆子之学统”,亦即是陆九渊“心学”在浙江的主要流派。其实,四先生都有各自深厚的家学传统,并与金华、永嘉诸流派学者交往甚密,彼此多有切磋影响。如沈焕之父沈铢曾受学于焦千之,以传程氏之学为主;舒璘之父舒黻也曾与洛学学者童大定“讲学相睦”;袁燮、舒璘还一度师事吕祖谦。对此,全祖望在《四先生祠堂碑阴文》中曾作过具体的探讨,并得出结论说:“四先生自其始志学之时,早得门内之圭臬而由之,况又亲师取友,遍讲习于乾、淳诸大儒而取短集长,积有层累。及其抠衣陆子之门,遂登首座,固其所也。”不仅如此,即便对于“心学”的承接,四先生的具体师从情况也有所不同。其中,杨简直接求学于陆九渊;袁燮、舒璘先师从陆九龄,后随陆九渊;沈焕则主要接受陆九龄的思想。因此,四先生的学术思想虽总体上都属于心学范畴,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学术性质,诚如黄宗羲所说的:“杨简、舒璘、袁燮、沈焕,所谓明州四先生也。慈湖(即杨简)每提‘心之精神是谓之圣’一语,而挈斋(即袁燮)之告君,亦曰‘古者大有为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此心之精神而已’,可以观四先生学术之同矣。”(《宋元学案》卷七十六《广平定川学案》)但另一方面,四先生对于心学的理解和发挥又有不少差异,具体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杨简公开引进佛家思想,并把心学进一步推向极端化的“唯我论”道路;袁燮积极吸收婺州、温州等地诸家事功之学的部分思想,着重在政治和伦理思想方面把心学向“笃实”的方向修正;舒璘在努力调和朱、陆两学的同时,将玄虚的心学移向平凡的日常生活;沈焕“辨古论今”,力求心学能开物成务。。故文天祥在《郡学祠四先生文》中评论说:“舒、沈、杨、袁,人皆名称。广平(即舒璘)之学,春风和平;……定川(即沈焕)之学,秋霜肃凝;瞻彼慈湖,云间月澄;瞻彼挈斋,玉泽冰莹。”从心学演变的历史来看,四先生不仅从不同角度对其作了颇具影响的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来明代王阳明对心学的全面改造奠定了基础。
与上述诸家流派的情况很不相同,以陈亮(1143—1194,字同甫,学者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县人)为代表的“永康之学”和由薛季宣(1134—1173,字士龙,一作士隆,号艮斋)奠基、至叶适(1150—1223,字正则,学者称水心先生,温州永嘉县人)时蔚为大观的“永嘉事功之学”以对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公开批判而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作为南宋浙江事功思潮的两大典型流派,它们之间虽也存在不少分歧和差异,但彼此关系密切,不仅许多基本观点相近或相同,而且在学术风格上俱以讲实事、究实理、求实效、谋实功为特色,特别是在对理学的批判上,更是互为呼应,迭相唱和,共同成为南宋反理学思潮的主流。如陈亮于淳熙年间(1174—1189)一度与朱熹展开长达三年之久的大辩论;而叶适晚年更是对理学加以全面、系统的否定。关于这两个学派对理学的批判,笔者在另文中曾有专门的分析,(注:参见拙作《论南宋事功学派的反理学思想》,载《安徽史学》1998年第3期。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其一,事功之学与理学的分歧不仅仅只是某些观点上的不同,而是从理论基础到社会思想上的尖锐对立。如在哲学观上,表现为朴素唯物论与主观、客观唯心论的对立;在历史观上,表现为进化的历史观与复古倒退观的对立;在价值观上,表现为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与动机决定论的对立;在伦理观上,表现为“义利合一”观与“崇义斥利”观的对立;在人生观上,表现为英雄化的理想人格与“学为成儒”的人生目标的对立;在学术观上,表现为强烈的求实致用倾向与空谈义理的疏阔学风的对立。其二,事功之学虽到南宋后期便很快走向衰落,但它对理学思潮、特别是浙江地区的各理学流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便得它们与正统理学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距离,对此,笔者在前文的有关分析中已多次提到。
三、南宋后期的“浙学”与理学
与南宋中期的情况相比,到南宋后期,浙学与理学的关系显得较为简单。由于此期浙江地区的学术发展趋于平稳,特别是不少一度与理学分庭抗礼的学派走向衰落,加上程朱理学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开始确立起统治地位,使得浙学在总体上呈现出向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全面回归的特点,以至在众多朱熹后学中,不少所谓“醇正”的支流都出现在浙江地区。《宋元学案》说:“晦翁(朱熹)生平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诸弟子支离、舛戾、固陋无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师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卷八十六《东发学案》)所谓“北山一支”是指南宋后期至元初兴起于婺州地区的“金华朱学”,它因较多地保留了正统朱学的色彩,而被后世封建学者推崇为朱学嫡脉、理学正宗。所谓“东发一支”是指明州学者黄震,他既是宋末朱学在浙东地区的主要传人之一,也是著名的程朱理学的修正者。
“金华朱学”以号称“北山四先生”(又称“金华四先生”)的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为代表,他们对朱学的承接虽并不直接来自朱熹,而是朱熹高足黄幹,但在一基本观点和思想风格上却较其它朱熹后学更接近正统朱学。如“道统说”是宋代理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征,几乎所有理学家无一不言道统,无一不以克绍道统自任。特别是朱熹,不仅全面论述了所谓“自上古圣贤”以来的道统传授心法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至孔、曾、思、孟的道统传授世系,而且将自己列为二程道统的嫡脉。四先生也是如此。他们一方面以很大的精力来清理理学的道统体系,如王柏作有《拟道统志》20卷,其族侄王敬岩和门人车玉峰也先后编有《道统录》等书;另一方面,他们又以朱学嫡传自居。如金履祥在其所作的《濂洛风雅》中,尊周敦颐为理学开山祖,以二程——杨时——罗从颜——李侗——朱熹——黄幹——何基——王柏为理学传递的正统世系,其余则皆为旁支,从中表现出浓厚的宗法色彩。这种强烈的宗派性道统观使得金华朱学象正统朱学那样对其它流派持激烈的排斥态度,“经义一本朱子,排斥异论,有抵朱子者,恶绝弗与言”(《吴礼部集》附录宋濂《吴先生碑》)。又如“理一分殊”说是程朱理学基于“太极”说提出的有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理论,四先生全面承袭了这一理论,并进一步趋于极端化,以至于因过分强调“分殊而理一”的认识方法和“格物致知”的求理功夫而最终走上了“昧却本体,而求之一事一物间,零星补凑”的屑细烦琐道路,黄宗羲喻之为“因药生病”(《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再如在学术风格上,四先生明显表现出“由传以求经”的特色。在他们看来,要巩固朱学的正统地位,就必须不断完善朱熹等人的传注,维护理学的道统,故何基即以发挥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为旨趣,王、金二人也大体如此,而许谦更是明确提出了“由传以求经、由经以知道”的主张,认为:“道固无所不在,圣人修之以为教。故后欲闻道者,必求诸经。然经非道也,而道以经存。传非经也,而经以传显。由传以求经,由经以知道,蕴而为德行,发之为文章事业,皆不倍乎圣人,则所谓行道也。”(《白云集》卷三《与赵伯器书》)正因为四先生刻意承袭程朱之学,故时人把何基比作守师说最醇的洛学传人伊焞;把王柏比作洛学之魁的蔡良佐(《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
当然,也应指出,金华朱学在承袭程朱之说的同时,又有不少自身的特点,特别是:第一,不专注性理空谈,比较重视实际,这显然是受浙学求实致用的传统学风影响的结果。如王柏反对一味咀嚼儒家教条,强调为学要研究现实社会问题。他一生研究内容极为广泛,对腐败的社会现实批评至为激烈,并提出了一系列如何富国强兵的具体主张。金履祥也是如此。清人陆心源评价说:“其学以由博返约为主,不为性理之空谈,经史皆有撰述,《尚书》则用功尤深。”(《重刊金仁先生〈尚书注〉序》)第二,具有较强烈的疑经思想,尤以王柏、金履祥两人最为突出。他们认为,“大抵有探讨之实者不能无所疑,有是非之见者不容无所辩。苟轻于改而不知存古以阙疑,固学者之可罪;狃于旧而不知按理以复古,岂先儒所望于后之学者!”(《诗疑》卷二《诗辨序》)由此,两人不仅对一些传统儒家经典提出疑论,而且对朱熹所注《四书》亦有不少异议。如王柏曾感叹地说:“恨不及质正朱子,既不敢自以为然,又不敢自欺曰无疑”(同上卷十《中庸论下》)。第三,在与陆学的关系上,虽不象同期以吴澄为代表的江西朱学那样主张“和会朱陆”,但在一些方面也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心学的影响。如王柏说“孟子激发人说‘放心’、‘良心’诸处都流汗”(《金华王鲁斋先生正学编》下卷《朱子读书法》);金履祥强调“事物之理本具于吾心之知,惟夫不能格事物之理,则不能充吾心之知”(《大学疏义》),这些都表现出某种心学倾向。
黄震(1213—?),字东发,庆元慈溪人,学者称于越先生。作为朱熹的四传弟子,黄震始终以弘扬朱学、辟除“异端”为己任,但其为学不恃门户之见,“反复发明,务求其是”(《四库全书·黄氏日抄提要》),故于程朱理学又多有修正。如在世界观方面,他在继承朱熹“理”(“道”)本体论和“天理流行”观点的同时,对程朱关于“道”的解释有所修正,认为“道”并非超乎天地人事之外的抽象精神本体,而是于“日用常行”的实在之物。“谓理为道,而凡粲然天地间,人之所常行者皆道矣。……若以道为别有一物,超出天地之外,使人谢绝生理,离形去智,终其身以求之而终无所得焉。吁,可怪也!”(《黄氏日抄》卷九十五《读抱朴子》)这实际上是对朱熹“理”在事先说的某种否定。在人性论方面,他在继承程、朱“性即理”观点的同时,又主张以孔子的人性说统一各种人性说,反对程、朱将性善说和“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说与孔子的人性说对立起来的倾向,认为:“孔子言性,包举大体;孟子之说,特指本源而已。性无出于孔子者矣。”(同上卷二《读论语》)而“伊、洛说出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亦不过为孟子解性善之说”(同上卷八十五《回陈总领》)。在认识论方面,他在继承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的同时,又批评程、朱的“圣人生而有知”的说法,认为“诸儒议论叠出,皆因待圣人过高,谓圣人不待学故也。然圣人亦与从同耳”(同上卷二《读论语》);在继承程、朱“主敬”说的同时,又不同意他们的“静坐”主张,认为“心者,所以治事,而非治于事。惟随事谨省则心自存,正不待治之而后齐一也”(同上卷八十六《省斋记》)。针对因朱熹强调“先知后行”所带来的其后学“摄拾绪余,增衍浮说,徒有终身之议论,竟无一日之躬行”的流弊,他特别强调了“躬行”的重要性,认为“言之非艰,行之为艰”,“其行于言也,常恐行有不类,惕然愧耻,而不敢轻于言;其见于行也,常恐不副所言,惕然愧耻,而不敢不勉于行。则言日以精,行日以修,庶几君子之归”(同上卷八十二《余姚县学讲义》)。在道统论方面,他在尊奉二程、朱熹为“道统”传递者的同时,又对“道统”作了不同的解释,认为所谓道统之“传”和“道”并非如程、朱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转相授受的密传心诀和神秘之物,而是前后次第相承之名和圣人所行之治道,把道统说成是“若有一物亲相授受”的观点,实乃与“释氏以衣钵为传”无异(同上卷四十二《读陆象山语录》)。由此,他还进而对朱熹所宣扬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道统心传之要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对《尚书·大禹谟》的断章取义,它与陆学的“心即道”一样,都源于佛学禅宗的影响(同上卷五《读尚书·人心惟危章》)。正因为黄震在继承程朱理学的同时又多有修正,故《宋元学案》一方面认为“四明之传,宗朱氏者,东发为最”,另一方面又指出黄氏“折衷诸儒,即于考亭亦不肯苟同,其所自得者深也”(卷八十六《东发学案》)。
除了金华朱学和东发之学外,到南宋后期,永嘉地区的学者也逐渐背离了叶适的事功之学,走上了追随程朱理学的道路。如此期永嘉最著名的两位学者叶味道和陈埴都先后接受了朱学,并以积极传播朱学为己任。全祖望在谈到宋末永嘉学术的变化时说:“永嘉为朱子之学者,自叶修文(味道)与潜室(陈埴)始。修文之书不可考,《木钟集》犹存焉。自是永嘉学者渐祧艮斋一派矣。”(《宋元学案》卷六十五《木钟学案》)
四、余论
通过上面的考察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
其一,宋代浙学与理学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形态和特点。大致说来,北宋中后期理学思潮开始传入浙江,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浙学的兴起;南宋中期具有浙学特色的各种理学流派和反理学流派相继形成,使得浙学与理学的关系显得特别醒目;南宋后期则浙学向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全面回归,从中反映出一度异常兴盛的儒学改造运动的结束和程朱理学一统天下局面的逐步形成。因此,浙学与理学关系的演变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宋学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
其二,在浙学与理学的关系中,既包含了理学对浙学的巨大影响,也包含了浙学对理学的影响。就前者而言,在湖学、洛学、关学影响下相继崛起的明州杨杜五子和永嘉九先生等人是宋代浙学的早期代表,他们在许多方面为后来浙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如五先生被后世浙江学者视为宋代浙学的开山祖;九先生则是永嘉学术的奠基者。而南宋中期伴随着浙学与理学的全面融合和冲突,吕学、四明之学、永康之学、永嘉事功之学、郑氏之学、平阳之学等众多学术流派纷纷兴起,彼此争鸣,把浙学推向空前的兴盛。及至南宋后期,“理学化”更成为浙学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不仅如此,在学术内容和学派分流上,由于理学的影响,浙学也始终不外乎表现为追随和发展理学、或反对和批判理学两种倾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理学派和反理学派两个基本阵营。就后者而言,一方面,各理学流派传入浙江后,都不同程度地被赋予传统浙学的一些特点,特别是求实求真、经世致用的精神,从而呈现出与其正统理学有所不同的发展趋向和特点;另一方面,更为突出的是,由于浙学的不少学派或直接成为理学思潮中自成一体的著名流派,或对理学的发展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从而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如吕学与朱学、陆学并为南宋三大理学流派,全祖望曾评论说:“明招学者,自成公(吕祖谦)下世,忠公(吕祖俭)继之,由是递传不替,其与岳麓之泽(指朱熹一支)并称克世。”(《宋元学案》卷七十三《丽泽诸儒学案》)而金华朱学上承程朱之学,下启元明理学,并在元时理学的北传过程中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宋元学案》说:“鲁斋(王柏)以下,开门授徒,惟仁山、导江为最盛。仁山在南,其门多隐逸;导江在北,其门多贵仕。”又说:“导江学行于北方,故鲁斋之名因导江而益著。”(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
总之,正如笔者在另文中所指出的,“在宋代浙学的发展过程中,即便是最‘醇正’的理学派,亦与理学主流有很大的不同;即便是态度最激烈的反理学派,亦与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句话,由于整个宋代学术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理学化的特征,因而作为宋学一部分的浙学自然也不可能完全游离于理学思潮之外,尽管它有着鲜明的地域个性。”(注:参见拙作《论宋代“浙学”的特点》,载《社会科学论坛》1995年第3期。)
标签:理学论文; 朱熹论文; 心学论文; 儒家论文; 永嘉学派论文; 读书论文; 南宋论文; 周行己论文; 国学论文; 宋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