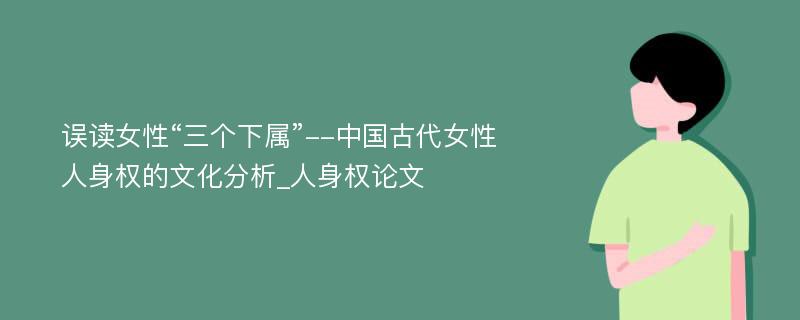
被误读的妇女“三从”——中国古代妇女人身权的文化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身权论文,妇女论文,文化学论文,误读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 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6)010-0078-07
“三从四德”是一个老调重弹的话题,人们似乎已经不屑于对此再置一辞,不就是说男尊女卑吗?例如有学者指出:“作为古代妇女基本道德准则的‘三从’之道为:从父、从夫、从子。它们严格规定了妇女在人生各个阶段和扮演各种家庭角色时的卑下、服从地位。”由于以卑下服从地位论“三从”,所以在历史上人们会发现存在很多与之矛盾的现象,这种矛盾被认为反映了“妇女社会地位的两重性”。“一面是广大妇女的卑下屈辱,一面是女皇、女主人的至尊至贵;一面是‘三从’观念与夫权至上,一面是全社会的尊母、孝母风气与史不绝书的‘悍妇’、‘畏妻’现象;一面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与前仆后继的节妇烈女,一面是绵延不绝的再嫁与私情。”作者继而指出:“妇女在家庭中并不是永远的卑下者、服从者,男女之间尊卑、主从地位颠倒的现象在古代绝非罕见。事实上,‘三从’之中只有做女儿时的从父是最不打折扣的,此后,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力则随着年龄的增长、辈分的提高、角色的变化呈逐渐上升的趋势。”① 这种认为妇女地位存在矛盾性的认识非常具有普遍性,因此本文就以这篇文章为参照重新审视妇女“三从”的含义。在这一点上我受到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研究成果的启示,因此在谈“三从”前,让我们先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一、“三从”——妇女的人身权归属
考察任何一个民族的两性关系,必须先弄清楚男女成员与其所在群体之间的关系,因为两性关系是受制于这种关系的。根据布朗对西澳洲父系的卡列拉部落的研究,一个社群(他以“队群”为例)是指一个共同拥有、占领和开发某一地域的一群人。他指出,社群作为一个法人团体拥有对本社群成员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既包括对其成员的对人权,即成年男性成员对社群负有一定的义务,又包括对其成员的对物权,即如果他们中的某个人受到伤害,社群有权进行报复或要求赔偿。但有一点需要牢记的是,妇女和儿童永远不是与成年男性同等意义上的社群成员。妇女直接归丈夫所有,由丈夫行使对她的对人权和对物权。作为对人权,他有权要求她履行一定的义务;作为对物权,如果有人杀伤了自己的妻子或未经自己同意与妻子通奸,就是对他的伤害,作为个人他有权要求赔偿,并对妻子进行惩处,群体并不干预,这是通奸法的基础。然而,她也间接属于社群,当其丈夫去世后,她将依照习俗改嫁给队群内而不是队群外的某个成员,这种婚俗通常称为夫兄弟婚。儿童归父母所有,当男孩到了青春期或行成人礼后,则由父母所有转归群体所有,这就是某些部落的成年仪式所表达的象征含义。此时作为群体的一个成员,他对其他成员、群体领地和财产都拥有一定的权利。女孩则由婚前归父兄所有,婚后转归丈夫及其社群所有。② 如果我们对上述这段话进行归纳的话,是说男子掌握着妇女的人身权,妇女在出嫁前归父兄所有,出嫁后归丈夫所有,丈夫死后归丈夫的某个男亲属所有,总之妇女在身份上也在生活上必须从属于一个男人并受到这个男人的保护。这种所有与从属的关系在父系制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如果我们把握了父系社会下两性关系的这个“纲”,两性关系的表现形式即使再复杂,仍然不难驾驭。
中国自夏商周以来一直是父权制社会,以中国历史之悠久、民族之众多、疆土之广大,两性关系之复杂当可想见,但无论怎样,妇女在身份从属上与其他民族并无不同。自周兴以来,一切折衷于礼,以礼对原始习俗进行梳理、改造。礼讲究男女有别,凡是与此不合的习俗如夫兄弟婚被喻为“父子聚麀”遭到贬斥,而妇女的所属身份不但被礼确认为两性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在宗法家族组织下被制度化;战国秦汉以后渐又辅之以律,从魏晋隋唐的“以礼入律”到明朝的“明刑弼教”,两性所有与从属的关系在国家权力的形式下被法律化;名门望族的族法家规也在不断维护和实践着两性的这种身份制度,这就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三从”,两性关系的许多方面都是建立在这一身份制度之上的。
“三从”的提法最早见于《仪礼·丧服》出嫁女为父服章:“为父何以期也?妇人不二斩也。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妇人不二斩者,犹曰不二天也”③ 这段话是对出嫁女为什么要为父亲服一年丧(期),而不服三年丧的解释。服制是根据服丧者与死者的身份关系制定的,出嫁女为父服期依据的是她与父亲的关系,《丧服》就此对妇女的身份作了进一步说明,这就是“三从”。用现代术语来表示就是妇女没有自己的人身权,出嫁前从属于父兄,出嫁后从属于丈夫,丈夫死后从属于儿子。古人以天为比,是对“三从”制度合法性的哲学表达。因此“三从”首先是通过丧服表现出来的身份制度,女子未嫁时从属于父亲,故为父服最重的斩衰三年;出嫁后从属于丈夫,故为夫服斩,为父则降服期;如果被出返回父母家中,所有权又变更为父,故为父仍服斩,即“子嫁,反在父之室,为父三年。”④ 在身份上一女不能有二统,所以《左传》僖公元年鲁国人“以齐人之杀哀姜也为已甚矣,女子,从人者也”。⑤ 春秋时鲁庄公夫人哀姜因私通庆父乱鲁被自己的母国齐国所杀,哀姜既已嫁鲁,有过错就应由鲁国处分,齐国却越俎代庖显然违反了“女子从人之义”。《丧服》中子为父、妻为夫、臣为君都服斩,这是“三纲”的由来,三纲首先强调的是父子、君臣、夫妇的身份关系。那么丧服是如何表现“夫死从子”的呢?丧服中,父母为子正服当期,但如果死去的是嫡长子,父亲要为其服最重的斩衰三年,母亲服齐衰三年。嫡长子服制如此之重,是因为作为祖祢之正体,他是家族未来的继承人和代表,因此服制甚至超过为母。母死,子为母服丧要视父在世与否,父在服齐衰杖期;父卒才得以服齐衰三年。如果庶子为父后,成为家族的继承人,其生身之母因是父妾,死后,儿子只服缌麻三月。这说明丈夫死后儿子成为家庭的继任人和代表,是一家之主,即使是母亲也要从子。儿子如果年幼,家庭事务当然要由母亲全权打理,儿子成年以后母亲需要交出权力,母亲的权威很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这就像老皇帝死了小皇帝尚年幼,由皇太后暂行摄政,日后要还政于子一样,象武则天那样另立门户就有悖于从子的原则。《列女传·邹孟轲母》记载孟子因担心母老而无法离齐远游时,孟母的一番话很可以说明母与子的这种关系:“妇人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也。故年少则从乎父母,出嫁则从乎夫,夫死则从乎子,礼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义,吾行乎吾礼。”君子因此称孟母“知妇道也”。由于继承的父系相传,男子始终是家庭的法人代表,妇女的人身权归男人所有也就意味着归家族所有,这也是从制度上维护父系家族,防止妇女侵夺丈夫及其家庭的权力。
礼书反复强调的“妇人从人者也”都是就妇女的从属身份而言的,《礼记·郊特牲》:“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⑥《大戴礼·本命》《白虎通·嫁娶》《谷梁传》隐公二年都有类似的表述,在身份从属这一点上贵族妇女和平民妇女没有两样。她们的区别属于阶级范畴,不属于性别范畴,不能混为一谈。《左传》成公十一年鲁国声伯嫁妹又夺之是妇女从属身份的一个典型例子,“(声伯)嫁其外妹于施孝叔。郤犨来聘,求妇于声伯。声伯夺施氏妇以与之。妇人曰:‘鸟兽犹不失俪,子将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妇人遂行。生二子于郤氏。郤氏亡,晋人归之施氏。施氏逆诸河,沈其二子。妇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俪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杀之,将何以终。’”⑦《左传》不书声伯夺其妹,而书夺“施氏妇”表明其妹的所有者已经是其丈夫施孝叔,虽然慑于郤犨的强权他把妻子送了出去,但从郤氏被灭,晋人将其妇送回来看,他最终仍保有其妻的人身权。声伯之妹则由于没有自己的人身权,不但要听凭兄长、丈夫的安排,甚至连孩子都无法保护。
二、聘娶婚——妇女人身权的转移方式
世界各地的婚俗之多样足以让人眼花缭乱,旧婚姻史往往以描述这类复杂的制度形式为己任,下面我以聘娶婚为例谈谈婚姻是如何实现妇女人身权的转换的。这种转换通常是两个家庭通过缔结婚姻,女子的男性亲属把对她所拥有的大部分权利交给了她丈夫及其男性亲属。这种所有权(有时并非全部)的转移往往以经济补偿的方式完成,这种补偿由娶妻者及其家庭提供,他们或出钱或交付一定的物品即聘礼给女方家庭,或到女家服一定期限的劳役,有的干脆直接以自己的姐妹作为交换,这些婚姻方式习惯上称为聘娶婚、劳役婚和交换婚。
聘娶婚是世界上较普通、流行较广泛的婚姻方式,聘礼含义也因民族而异。聘礼有时很重,相当于一个买卖的价格,有时要向女方家送上猎物以表示自己具有养活妻子的能力,有时只是为了表示尊敬和好意,而有时聘礼仅具有象征性。亚麻逊河流域西北部印第安人的聘礼少至一罐淡巴菰、一罐可加叶。但无论聘礼的含义如何多样,却必不可少,因为它是妇女人身权转移的标志,即使是盛行嫁妆的民族也不例外。中国自西周以来聘娶婚一直是社会承认的正式的婚姻形式。大部分婚姻由父母安排,他们对可能的婚姻配偶进行评估从而选择合适人选。这种安排表现为缔结婚姻的两个要件,一个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另一个是纳幣。《诗经·国风》虽然有许多民间自由恋爱的诗句,但也不是没有规则,《南山》:“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⑧ 可见即使男女相悦最终也要明媒正娶,这是获得家庭认可的必要手续,所以《诗经·郑风·将仲子》才有“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⑨ 纳幣是指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交纳聘礼,通常是两张白鹿皮(俪皮)和玄纁束帛,至此婚约正式成立。父母之命和纳幣之所以重要,在于以此表明只有家庭有权转让妇女的人身权,纳幣就是这种转让的证明,虽然它并不构成一个买卖的价格;而未经家庭允许的自由恋爱也正因其个人之“私”违背了家庭之“公”而不被认可。这类事情并不少见,战国时莒大史之女与齐闵王之子私通即是一例。据《战国策·齐策》记载,齐闵王之遇杀,其子变易姓名为莒大史家庸夫。大史女“与私焉”,大史曰:“女无媒而嫁,非吾种也,污吾世矣。”于是终身不见女儿。⑩ 其实即使在原始部族中,一对青年不顾长者反对和习俗压力,毅然以私情相许的事例也常有,但同样无法与正式婚相提并论,有时甚至被视为无效。一个澳洲男子如果和一个已经订婚的姑娘私奔,她的兄弟们会约定那个男子来殴斗,直到流血为止,那个女孩交给母亲和姊妹们痛打一顿。(11) 有人以“私奔”或《诗经》中的男女恋爱为依据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表示怀疑,其实这就好比今天我们以登记结婚为法定的婚姻形式,可是总会有人不登记而同居一样,但同居并不能否定婚姻登记的效力。
三、丈夫对妻子的人身权
1.夫主妇从。结婚后,丈夫取得了这个嫁过来的女子的人身权。《仪礼·丧服》将妻子的身份归属说得很清楚:“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12) 妻子完全根据丈夫确立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这种名分的依附从制度上规定了夫妇间的主从关系。它不是人们表面理解的妻子服从丈夫的意思,而是指夫妻间身份上的所有与从属关系,俗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正是这个含义。这种主从关系始于婚礼亲迎时的一个象征性仪式,《礼记·郊特牲》“出乎大门而先,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13) 从此以后,妻子的尊卑荣辱完全取决于丈夫,这便是婚礼夫妻共牢而食、合卺而酳的意义,《礼记·昏义》:“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郊特牲》“故妇人无爵,从夫之爵,坐以夫之齿”(14)。妇人无受爵命之法,她们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丈夫爵位的高低。妻爵从夫爵,夫为天子,妻为后,夫为诸侯,妻为夫人,夫为大夫,妻为命妇;妻齿从夫齿,兄弟之妻,其娣姒之序,不以己年而以夫年,夫为兄,妻为嫂,夫为弟,妻为妇。《周礼·小司寇》有“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之说,(15) 命夫不躬坐狱讼是恐狱吏亵其尊有悖贵贵之义,而命妇因夫贵得与夫享有同等的特权。汉以后妇人因夫、子之贵常有封号,并随同享有种种特权。这是同尊。何谓共辱?是指丈夫犯罪,妻子受到牵连。这既是为惩戒于人,也是因为妻子的从属身份。《国语·吴语》勾践誓师曰:“谓二三子归而不归,处而不处,……身斩,妻子鬻。”(16) 这是就军法从重而言。秦汉以后,妻子连坐扩大化,或从死、流放,或配给士兵为妻,或被没入官奴婢等等。曹魏令“既醮之妇从夫家之戮”,进一步明确了妻子的从属身份在实际生活中的操作。直到元代文宗即位,才下诏罪人妻子勿役,止及一身。但明清妻妾入官或随夫发配之例仍然常有。(17) 而妻子犯罪一般“只坐其身”,即使有时“坐其夫”也是因为丈夫对妻子管教不力,没有尽到监护人的责任,这还是因为丈夫拥有妻子人身权的缘故。
2.夫妇齐体。常有人以夫妇齐体来说明妇女与丈夫具有同等的家庭地位,应该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应该明白古人是在何种语境下谈夫妇齐体的。《礼记·内则》“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下郑注云:“妻之言齐也,以礼聘问,则得与夫敌体。妾之言接也,闻彼有礼,走而往焉,以得接见于君子也。”(18)《白虎通·嫁娶》:“妻妾者,何谓也?妻者,齐也,与夫齐体。自天子至于庶人,其义一也。妾者,接也,以时接见也。”(19) 可见妻齐是因妾生义,对于妾来说只有妻子才是丈夫的体敌对应之人。《左传》一书屡屡出现表示妻子的用语如伉俪、妃耦都是体敌之义。古人在行文中也是妻妾对言,毫不含糊,如《左传》襄公十三年:“天子求后于诸侯,诸侯对曰:夫妇所生若而人,妾妇之子若而人。”(20) 因此夫妇齐体实际是在妻妾制下强调一夫一妻的法律关系,而妾无论贵贱都要以夫为君,以嫡妻为女君。春秋时晋国赵盾虽贵为父后并继为正卿,仍称嫡母为君姬氏,就是以父之嫡妻为女君。妻所以被称为女君,不是因为妻与夫是平等关系,而是因为只有妻才是夫的体敌对应之人,这也正是上文同尊之义。夫妇一体、夫妇半合虽然强调妻子尊于妾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夫妻间是平等关系;正相反,它从人身权角度说明当妻子与丈夫合卺共牢之后,妻子的人身权已转归丈夫所有,被丈夫所吸收,是妇合于夫的夫妇一体。换言之,就是通过婚姻,夫妻在法律上合为一人,妇女的存在被吸收、并入到丈夫的存在之中。所以有人说女子出嫁是“辞父母而言归,奉君子之清尘,如悬萝之附松,似浮萍之托津。”其喻确矣!(21)
四、丈夫家庭对妻子的所有权
1.夫兄弟婚与夫死从子。婚姻把妇女的人身权由自己的男性亲属转交给了丈夫及其男性亲属手里,他们对这个嫁过来的妇女次第享有对人权和对物权。丈夫死后,依习俗其妻被兄弟、继子或外甥继承,这是夫家行使对寡妇的对人权,这些婚姻形式统称夫兄弟婚。夫兄弟婚在原始民族中非常流行,要找到不实行这种婚姻制度的民族实非易事。以多妻的南非通加人为例,倘若死者有五个妻,第一个妻大抵属于继兄为家主的弟弟,第二第三两妻或许属于其他两位弟弟,即叔嫂婚,第四个归于一位外甥,即继舅母,第五个归于其他妻所生的儿子,即继庶母。也就是说,凡是分得一份遗产的,就有继承一个寡妇的权利。(22) 如果别家的人要娶她,后夫要向前夫家送礼,以完成所有权的转移。如在新几内亚的阿拉佩什人中,正常情况下如果前夫死了,寡妇理应与丈夫的兄弟结婚。如果她嫁给了外人,后夫绝对不能把聘礼送给她的娘家而一定要送给她原来的婆家。(23) 这是夫家行使对寡妇的对物权。
夫兄弟婚向来也在匈奴、西域各国、东夷、蒙古、女真等中国边疆各族流行。华夏上古时期是否通行这一婚制已经不得而知,但夫兄弟婚的例子倒是不时出现。《孟子·万章上》的舜弟象欲“二嫂使治朕栖”可算是未得逞的一例;(24)《左传》中妻婶母庶母的烝、报就更多了;又《淮南子·氾论训》:“昔苍吾绕娶妻而美以让兄,……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25) 他们一个是孔子时人,一个是战国时齐人。陈顾远在《中国婚姻史》上也说此类婚俗“迄今仍所不免。今日,各地所谓叔接嫂、接续婚、转房、升房、接面、上舍……等称,即系指其事而言者。”(26) 这里我无意探究中国古代是否曾有这种婚制,不过有一点可以确信,那就是只有丈夫家庭掌握了妇女的人身权,收庶母、叔接嫂、兄弟共妻才能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而非仅仅是个人行为。
礼既然否定夫兄弟婚,父亡收庶母更被喻为父子聚麀,禽兽之行,那么对于死了丈夫的妇女应该怎么办呢?中国的办法是“夫死从子”,儿子是继父之后家庭的法人代表,母亲在身份上从属于家庭的这个新任继承人。与夫兄弟婚相比,夫死从子不仅使叔接嫂成为非法,也是从身份角度对有子寡妇外嫁的限制。所以秦始皇会稽刻石说“有子而嫁,倍死不贞。”(27) 董仲舒“春秋决狱”中有一个夫丧妻嫁案例,有人议曰当弃市,董仲舒曰:“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28) 但是对于无所凭靠的孤儿寡母来说,改嫁常常是不得已的出路。为此礼制也有权变,《仪礼·丧服》为“继父服”章就说明礼制有条件地允许寡妇再嫁,但前提是“妻稚,子幼,子无大功之亲。”(29) 也就是说妻稚子幼,三代以内又没有男性亲属守养弱嗣的情况下,寡妇可以再嫁。在其他民族中,夫兄弟婚在夫死之后把保护寡妇的责任交给了丈夫的兄弟、继子等;中国则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儿孙。宋代有个叫袁采的人,他的一席话很有助于我们认识妇女在从属身份下的处境:“妇人依人而立,其未嫁之前,有好祖不如有好父,有好父不如有好兄弟,有好兄弟不如有好侄。其既嫁之后,有好翁不如有好夫,有好夫不如有好子,有好子不如有好孙。故妇人多有少壮富贵而暮年无聊者,盖由此也。(30)
2.从一而终。夫死不嫁、从一而终恐怕是妇女归丈夫及夫家所有的最完全彻底的表现了,这是礼书极力强调,也是极易引起误解的问题,因为现实生活中寡妇再嫁很常见。常有人因此怀疑从一而终对妇女的影响或者说只是在宋元以后才对妇女有较大影响。其实从一而终、夫死不嫁应该从两个方面理解,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它对所有妇女都有意义,在制度层面上则表现在宗法制度对宗妇提出的特别要求。对于宗法家族来说,作为家族的继承人和代表,只有嫡长子夫妇有祭祀祖先的权利。而经过聘娶仪式嫁过来的主妇,成为丈夫的体敌之人,与丈夫共同成为祖先的继体承重之人,除非被出,否则她永久属于丈夫宗族所有,这种身份永远不变,即使丈夫死了,她也不能改嫁。所谓“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31) 因此夫死不嫁不仅是道德的要求,更是宗法制决定的。据《左传》春秋时妇人再嫁并不少见,但诸侯夫人和卿大夫嫡妻守寡少有再嫁者,大家族的维持需要她们从一而终,但这样做的副产品却是礼的制订者意料不到的,那就是通奸,我想这应该是春秋时贵族寡妇多有通奸的根本原因。降至后世,隋、唐、辽、元、明、清都以法令的形式禁止命妇改嫁。(32) 因此夫死不嫁虽然具有普遍意义,但作为制度要求,它的主要对象是命妇们,她们具有夫死不嫁的经济条件,而普通妇女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迫于经济压力改嫁很常见。
国家也根据人口形势的需要鼓励再嫁或提倡守节。在战争、瘟疫等大难造成人口锐减的情况下,政府通常通过促成婚姻以增加人口,这就是《周礼·大司徒》十二荒政之一“多昏”的意义。《管子·入国》:“凡国都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之谓合独。”(33) 又如唐太宗贞观元年二月下诏:“其庶人男女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贫窭之徒,将迎匮乏,仰于亲近乡里富有之家,衰多益寡,使得资送。”(34) 明清以后政府提倡妇女守节与愈益增加的的人口形势也是相适应的。北宋时人口突破了1亿,明清时人口继续倍增。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没有必要充分利用寡妇的生育能力了。(35) 可见从一而终与夫死再嫁是经与权变的关系,无论是鼓励改嫁还是用经济政治手段限制、禁止妇女改嫁甚至逼迫妇女自尽者都是对妇女设法,是以妇女没有人身权为前提的。
妇女没有自己的人身权,这使她们在法律上属于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丈夫负有管教妻子的责任。《易》家人卦“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36) 就是强调丈夫的治家之责。降至后世,妻子犯罪由其夫责罚,如明清律规定:“凡妇女犯罪,除奸及死罪收禁外,其余杂犯责付本夫收管;如无夫者责付有服亲属邻里保管,随衙听候,不许一概尽禁”。这虽然是对妇女的照顾,但妇女的法律权利也因身份(当然也有别的原因)受到限制,如离婚权、子女抚养权、财产继承权等。妇女凡涉及民事纠纷,不许出官,告状必须代告,如夫亡无子,方许出官理对。在法律上妇女必有所从,有夫从夫,无夫从子。(37) 而与“三从”相伴随的“四德”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并甚嚣尘上也正是基于妇女的从属身份。作为一种身份制度,它告诉人们妇女属于家庭所有。因此,“三从”之重要不仅在于它是私人领域两性关系的准则,更在于妇女因此丧失了进入公共领域的权利,它与影响两性关系的其他因素一道,共同构建了性别的等级结构。这也是新中国建立后首先颁布《婚姻法》的原因。研究妇女史如果脱离妇女的从属身份去谈妇女地位,很可能会矫枉过正。
我想在我们清楚了“三从”的真实含义后会发现妇女社会地位存在两重性的提法并不准确。“三从”首先也主要是一种身份制度,强调的是妇女没有人身自主权的从属身份,作为妇女的道德规范及其所反映的卑下地位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惧内”、“畏妻”、“河东狮吼”之类的社会现象并非如上文作者所言是“妻为夫纲”、“妻主夫从”。历史上的妒妇、悍妇不仅不是妇女地位高的表现,相反正反映了她们在社会生活中无足轻重,只能靠在家庭中争一己之短长以维持自身利益。这种现象今天仍然以“怕老婆”、“妻管严”等名义程度不同地体现于现实社会中,这不仅不是妇女解放,正是女性缺乏事业和社会地位,只能在家庭中找回失落,是女性不自信、男女社会不平等的表现。关于从子,上文作者指出:“与从父、从夫相比,从子在三从中是最没有意义的一项。自古虽有此说,但只是作为规范女性总体地位的大原则笼统言之,除了特殊情况下,既没有人特别强调这一礼法并以之要求作为母亲的女性,在古人家庭生活中也极少见有这一原则行事者。相反,尊重母亲是古代社会贯彻始终的统治观念与普遍风气。”“母亲在人伦之序中位尊于子及孝亲的敬顺之道与母亲要从子这两种理论是有所抵牾的。而考诸史实,可以发现,人们实际遵奉和执行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这里作者将分属于不同范畴的两类现象混为一谈。儿子孝母属于长辈与晚辈的关系,从子则属于性别范畴,二者并不矛盾。妇女地位之所以会产生诸如此类的两重性问题源于对妇女“三从”的误读。
注释:
①《中国古代妇女社会地位的两重性》,载周积明:《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92-624页。
②A·R·拉德克里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③④(12)(29)胡培翬.仪礼正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7页、第1378页、第1496页、第1430页。
⑤⑦(2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81.第279页、第853页、第997页。
⑥(13)(14)(18)(31)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09页、第709页、第710页、第773页、第707页。
⑧⑨朱熹:《经集传》,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41页、26页、第33页。
⑩文远:《战国策新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463页。
(11)罗维:《初民社会》,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92页
(13)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09页。
(15)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69页。
(16)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60页。
(17)(21)(26)(32)(37)转引自陈顾远:《中国婚姻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79页、第185页、第107页、第178页、第232页、第186页。
(19)陈立:《白虎通疏证·嫁娶》,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90页。
(22)罗维:《初民社会》,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2页。
(23)米德:《性别与气质》,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
(25)高诱:《淮南子注》,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222,226页。
(27)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2页。
(28)成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62页。
(30)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50页。
(33)《管子》,第300,124页。
(34)《唐会要》,卷13。
(35)周积明:《中国社会史论》,第280页。
(36)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