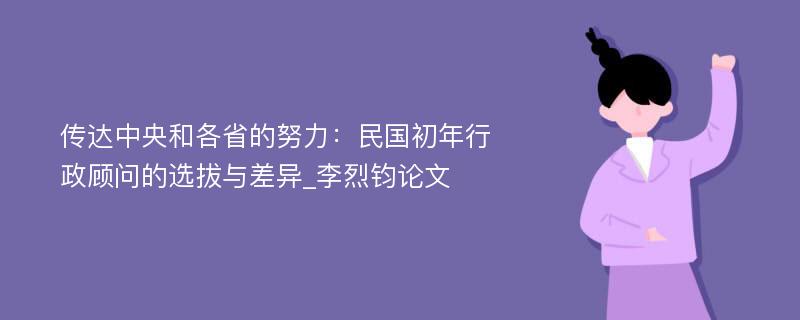
沟通中央与各省的努力:民国元年行政咨询员选派及分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年论文,分歧论文,民国论文,努力论文,中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4)03-0117-10 南北通过和议实现统一后,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并遵照《临时约法》规定,组建统一的临时政府,形成临时参议院、总统府、国务院并峙的格局。同时,因为《临时约法》除规定临时参议院由各省临时省议会选派代表组成外,未及规定中央与各省权限的划分以及省制,各省都督与总统府、国务院以及各省省议会与都督关系微妙。 袁世凯上台伊始,不顾自己尚无实力控驭南方光复省份的事实,积极推行集权措施,触及辛亥革命期间壮大起来的各省都督利益。同时,袁又通过频频更换总理,加强对内阁的控制,政府与临时参议院关系趋于紧张。列强也在等待袁政府加强对各省的控制,确信政局已完全被其掌握才予以正式承认。面对内外两面的压力,为了打破僵局,袁世凯援引前清督抚派员参与外官改制之例,通令各都督派员赴京参与中央内政、军政、财政决策。与此同时,政体构建方案尚在酝酿,古今、中外各种学说、宗旨均有不同市场与受众,包括革命党人在内,对于新政体的形式均未有成熟且形成共识的方案。在新制尚未形成定谳,需要集思广益、征求各方意见时,各种政治力量均希望确立对其有利的主张。对于各省都督而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的各省都督府代表,正可为其提供更多机会。在中央政府与各省都督共同要求下,各省选派代表赴京。1912年9月,政府正式将其定名为“行政咨询员”。由于袁世凯政府与各省都督各怀不同目的,在代表权限的问题上主张分歧,此举最终未能改变民初纷乱政局。 以往研究主要强调袁世凯及政府与各省都督,尤其是同盟会籍都督间的对立。本文通过考察行政咨询员,①意在说明,当时中央与各省在斗争的同时,彼此间也曾努力调和与沟通。 一、缘起 众所周知,中华民国是由独立各省都督府派遣代表,经过协议组建而成的。这些代表在临时政府成立后,一度代行临时参议院议员职权,继续影响南京临时政府的重大决策。南北统一后,在各省临时省议会力争下,临时参议员改由临时省议会选举。至参议院北迁后,由各省都督府派员暂代参议员已不及总数的2/10。[1]同时,虽然在辛亥革命期间,各省都督府取得对外代表全省的资格,各省临时省议会也在士绅的努力下,由准立法机构一变而为代表全省民意的立法机关,但由于各省官制尚未统一,各省都督与省议会关系十分微妙,在各省临时省议会纷纷选派代表赴京组织临时参议院的同时,却很难让都督将这些选举产生的参议员视为都督府代表,与中央政府接洽。如何沟通各省都督府与中央政府间的意见,随之凸显出来。这一探索在北京临时政府建立不久即已开始。1912年4月20日,东三省都督赵尔巽因东北夹处日、俄两强间,局势紧张,仿前清资政院特派员例,派潘鸿宾、傅疆顾问员,赴北京陈述意见。[2]此举遭到奉天临时省议会反对,认为民国已建,“奉省政见如何,自宜公诸舆论,非一二顾问员所能代表”,而且此举未得中央命令,“今置自东省,尤与各省参差”,电请袁世凯下令取消。袁氏虽电令顾问暂留,赵氏却深为气愤,直称“参议员不咨询,能禁大总统及政府亦不咨询”。[3] 中央政府在推行集权措施受到各省掣肘后,亦感到有必要考虑各省意见。在山东、河南、直隶等省因发生都督选任问题,出现直接用民间团体、个人的名义迭电政府各部院,就用人行政发表意见,袁世凯虽以有碍统一为由置之不理,终感有必要加以根本解决。[4]同时,袁世凯与唐绍仪及各国务员本计划派人前往各省,调查军政和财政真实情况,再会同各都督筹商解散军队、清理财政的办法,不过均感到此类人员不可多得。而且各处军队人数诸多虚冒,不仅拥兵者不愿人前往调查,深知其情者也担心担任此项调查,招来意外恶感。[5]隶籍同盟会并因府院权限与袁世凯矛盾重重的唐绍仪,鉴于军民分治问题发生后,袁氏及政府与各都督间、各都督间的分歧日益凸显,在接到胡汉民电请政府公示外官制方案后,更加意识到中央独断省官制厘订实不足取,在法制局厘订外省官制草案的同时,以“各省情形分歧不一”为由,提议仿清季督抚派员参与外官制厘订之例,电令各都督迅派委员来京参议此事。[6] 同盟会籍都督在反对中央集权的同时,也提出由各省派员参与中央决策的要求。南北统一后,同盟会并未甘心附袁,一直在寻求机会予以制衡。而袁世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积极推行军政、财政、内政统一政策,触及各省都督的权力,引起各都督不满,正好提供了一个藉口。1912年6月6日,粤督胡汉民针对袁积极推行中央集权,通电主张“有限制的集权制”,在谈及各省受协额与协助额、各省军队数确定时,主张应由中央政府召集各省都督特派员开会决定。[7]此外,赣督李烈钧针对“近来一二人或私团不明行政系统,辄向中央各部要求地方一部分权利,中央或有时偏信遽予批准,或直接往返电商”的情况,也致电袁世凯,建议“自后个人或私团迳赴中央请愿事件,由中央主管之部先行电咨各省查询商复,再行核办”。[8]唐绍仪内阁因府、院权限冲突垮台后,袁氏与同盟会间失去缓冲的桥梁,关系紧张。不仅同盟会领导及议员主张政党内阁,致使陆征祥组阁受阻,胡汉民、李烈钧等同盟会籍都督亦力主地方分权制,在他们策划和疏通下,各都督抵制政府军民分治政策。在都督内部,也因所处坏境、政治立场等原因,在军民分治问题上明显分为两派。与此同时,省议会亦在极力力争民选省总监,又为政府与各省都督彼此走向合作提供了客观条件。 袁世凯在通过软硬兼施的办法暂时平息内阁风潮后,随即转向解决省官制。1912年7月24日,国务院致电各省都督,遴选“熟于军事及内政各门”代表3人,“以阅历甚深、素有经验而为各都督所信任者为合格,选定之后即由各都督加给委任状,迅即来京以备咨询”。[9]可见,在当时,中央政府与各省都督都有由各省派员赴京,以便疏通中央与各省意见,解决军政、财政、内政等方面问题的诉求,但因双方基于不同的目的,对于代表在沟通中充当什么角色,具有哪些职权,不无分歧。这不仅涉及中央与各省都督在政治权势格局中地位的确认,并影响各省代表的最终命运。 二、代表职权与条件 对于这些代表,各省都督与政府都非常重视。在政府一方面看,每省各派3名确能代表都督资格的代表,可以帮助解决政府深感棘手的军政、财政及内政方面的诸多问题。[10]而在各省都督一面看,各省代表乃“传述都督意见,敷陈地方利弊,藉通内外之邮而确收联络之效”,但为避免重蹈前清外官改制时选派陈述员的故习,藉政府电令并未明确这些代表究竟有哪些职责及应具备哪些条件,试图拟订代表权限并求政府制为专条。[11] 赣督李烈钧首先发起这场讨论。他在得悉政府命令各省派代表赴京电后,于1912年7月27日致电各省,要求各都督协商后联电中央,订明代表在京职务,并开列四条征求意见:(1)各省派代表一人出席国务会议并陈述意见;(2)各省代表可奉都督指令,就本省要政请求开国务会议;(3)大总统提出的法制、预算案在交参议院以前,应由代表转达各省,征集各省意见;(4)中央对各省的政务命令,应先期咨询该省代表,对地方情形是否有窒碍。对于代表应对都督负何种责任,李烈钧主张参酌各省情形,在不违越都督意旨而在中央运动服官、放弃代表职务的前提下,另订遵守条件。[12]从李开列代表职权看,各省代表类近南京临时政府时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表明素主地方分权的李氏想趁此机会,将各省代表定位为都督私人代表,代表各省参与中央决策。此举代表了部分都督心声。此电一出,广东、山西、奉天等都督表示赞同。[13]不过,当时内外形势皆趋向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同持反对军民分治主张的一些都督,考虑到各省都督府代表与联邦制特征间的关系可能引起政府及各方不满,对李所开列条件进行商榷。 7月29日,苏督程德全发表通电,指出代表的作用“在疏通隔阂,供备咨询”,既非地方代表,亦非联邦委员,对都督亦“以力图统一、无背意旨为原则”,为一种意思机关,而非法定职务。基于此,除第三条外,程德全对李烈钧所拟条件均作修改:易第一条为“凡国务会议各省政务时,应先期咨询各省代表员”;删去第二条;第四条意思已包括于第一条内,不必另定专条;增加“国务会议关于某省事件,得由某省代表附座旁听”一条。另外,程还力主在三名代表中须有一或二人来往中央与各省间,不必拘定常驻机关,并表示,应该从各都督平时所信任的人当中,选派道德高尚、顾全大局的人充当代表。[14]经程修改,各省代表权限较李所拟大大缩小,更像是都督的私人代表,并充当中央政府决策时的顾问,在当时趋向建立统一、强有力政府的大势下更易为各方接受。8月3日,粤督胡汉民通电赞同程德全的意见,不过对程氏“国务会议关于某省事件,得由本省代表附座”条有所保留,主张改为“出席陈述意见,但不加于表决之数”。[15]此外,同隶同盟会的湘督谭延闿、皖督柏文蔚也发表意见。与程一样,谭担心国务会议骤增议员“不毋妨碍”,并认为第四条已包括在第一条范围内。[16]柏则更关心充任代表的条件,主张删除李所拟“不得违越都督意旨暨在中央运动服官”条,增加“各代表与职务实有不宜之处,得由各都督随时另选改派”、“各代表与服务期内不得充当中央官职”二条。[17] 李烈钧非常重视程、谭、胡等人意见,8月4日藉向各都督通报各省代表权限及条件商讨结果,逐条回应:关于第一条,李仍坚持原有主张;对于旁听一条,接受胡意见,改为“得出席陈述意见,但不加于表决之数”;关于第二条,亦照程意见,“拟照删”;关于第四条,表示改为“凡关各省政务之命令,如与各省有特别关系时,应先期咨询该省代表,于地方情形有无窒碍”。此外,李赞同程所主“代表三人,须以一二来往内外”的建议。并考虑“现在各省或已派代表赴京,或急待选派”,要求程主稿领衔会电中央订定。[18] 程德全在同意李对第四条修改的同时,对于胡、李对自己所增条的修改仍存意见。在程看来,中国本非联邦制度,胡、李的修改与政体不协,且妨碍中央政权,与其待各代表到京后由中央改削,不如先行妥酌。此外,程赞同胡建议由李主稿、其本人领衔联署入告的方式,要求各都督在8月12日以前电知。[19]由于李对各省代表职权、条件的修改,已“相当斟酌适中”,特别是他基于各省在省官制案上的共同利益诉求,秘密联络,并促成各都督结成同盟,发表九督联电反对军民分治,不仅迫使政府决议都督与总监暂可兼任,[20]此议先后得到粤、晋、湘、豫、桂、黔、奉、吉、直、鲁、皖、闽、陇等13省都督赞同。同时也让袁世凯感到,要解决军民分治问题,“当俟各省都督代表到京后再行讨论”。[21]程虽仍有顾虑,但见多省赞同也只得表示同意,同时在代表附座旁听问题上态度也趋于调和,将其改为“国务会议关于某省事件,由某省代表附座旁听,如国务院咨询时得出席陈述意见,不加表决之数”。[22]与此同时,胡汉民为消除上述改动可能引起有碍于中央政权的顾虑,更是引欧美各国之例,说明改动的合理性,并认为“许其陈述,能收面询之益;不许陈述,必殆退有后延之诮”,“似仍照酌稿为宜”。[23] 李烈钧按照各都督往返电商的意见,草拟代表职权及条件,电交程德全。8月21日,程德全等17省都督联衔发表通电,要求袁世凯及国务院:一、国务会议在各省政务时,应事先咨询各省代表;二、国务会议某省事件,应由某省代表列席旁听,如当场经国务员咨询,或事前奉有都督指令时,得出席陈述意见,不加入表决;三、大总统提出法制、预算案交参议院以前,应请征集各省都督意见,由代表传达;四、凡关各省政务之命令,如与某省有特别关系时,应先咨询该省代表,于地方情形有无窒碍。同时,各省代表须选择经验闳深、道德高尚、关怀大局者充任。[24]很明显,所公示的代表职权和条件,集中代表了李烈钧、程德全、胡汉民、谭延闿等人的意见。具体而言,在代表职权方面,除第一条、第三条分别为程、李所拟没有变更外,第二、第四条融合了上述各人的意见:第四条主要是李在程、谭意见的基础上所作的修改,第二条则更多体现李、胡、程三人的意见。在代表条件方面,李基本上放弃自己的主张,接受程意见。这些条款抹去李烈钧最初所提条件带有的联邦制特征,在迎合当时时势的同时,加重了各省对中央政府行政决策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李烈钧、胡汉民、程德全等人,正是反对军民分治政策的要角。他们热衷于代表职权及条件的商榷,反映出他们试图在中央与各省间的沟通上掌握主动。 三、各省派员与权限变更 由于当时内外形势趋向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且中央与各省均有沟通意见的诉求,当政府饬令各省特派代表来京电文发出后,浙江、山西、湖南、湖北等省相继响应,并陆续派定人员赴京。 当时省官制案被提交参议院讨论,各省与中央在军民分治与否、省长选任方式等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政府于7月31日将其撤回修正。同时,政府就对外借款与四国银行团谈判破裂,引起财政短绌,如何解决中央行政经费成为一个难题。政府更加急待各省派员来京商讨这些问题。8月1日,袁世凯再度交饬秘书厅,电催各省速选派代表,在8月15日以前到齐,同时要求各省先行电告所拟派各员衔名。[25]4日,总统府再电各都督速派代表来京商定省制及省官制,[26]奉、直、豫随后表示派遣代表。[27]随着多省表示派员,总统府、国务院在由谁主导政府与各省代表间接洽的问题上发生分歧。8月8日,袁世凯与总理陆征祥商讨各省代表会议场所,表示将来所议各政均关系统一大局,届时自己当随时出席,主张将总统府前楼右偏修缮作为议场。[28]不过,12日陆在总统府召开国务会议后,与袁谈及各省代表来京后预备办法时,认为将来开议时,诸国务员均当于第一次开会全体出席,且应令派临时会议专员与会坐办,主张以煤渣胡同陆军军需学堂为会议所。[29]但是袁世凯仍坚持将总统府第一层北大楼作为临时会议厅。[30]至8月中旬,除赣、苏、粤等省尚未派出代表外,已派定代表赴京的省份不断增多,[31]据悉“西北各省代表已经到京,加上东南各省已电京派员者,总共约有十二三省之多”。[32]这让早已被军政、财政、民政上的种种困难弄得焦头烂额的袁世凯看到希望,计划在代表来京后先行接见一次,告以中央种种情形,借以疏通意见。而此时参议院因张振武、方维在8月15日被杀,与政府关系再次出现紧张,尤让袁感到疏通各省意见的迫切。8月16日,袁饬国务院将各省所派代表已到京人数查明开单呈报。[33] 袁世凯原本以为各省代表在8月15日以前即可到齐并择期开议,实际上届时到京的代表仍不多。为此,袁一面将省制省官制修正案提交参议院审议,一面再饬国务院秘书厅电催各省代表务须赶速来京,并修改前定全部到齐即开议的声明,表示只要代表人数足总数的6/10即开议。[34]由于都督代表职权商榷在8月下旬已结束,及至9月中旬,包括赣、粤、苏在内的多省亦陆续派遣代表赴京。在当时的22行省中,除新疆外,有21省陆续向政府提供了代表名单,但截止10月上旬,实际到京的有19省共计59人。[35]而且各省都督在选派代表时,大体按照中央政府要求及各省都督商榷各省代表条件选定,并尽量避免党派门户之见。[36] 随着各省代表陆续到京,政府对于代表应担任何种职权的规定不容回避。8月22日,袁世凯会见先期到京的十余位代表,其本意想藉此联络感情,并商讨要件。[37]然而,多数代表却趁机向袁表示,不愿为单纯顾问机关,认为既会议当有议决权。[38]这一要求侵犯了国务院权限而遭国务院反对。而且袁世凯在接到该电后也极感不满。因为他知道,果照各都督意见办理,中央行政将受制于各省。为此,他饬令国务院在8月28日电复各省都督,指出此项代表纯属行政上的作用,并非立法机关,并表示第一、三、四条在事实上虽不妨酌量实行,在法律上则万不能一一规定,而第二条与国务院规制颇有冲突,担心牵动立法问题,几乎全部否决都督们协商所得的代表职权。[39]随后,袁世凯又饬令国务院根据各都督联衔所提各条,本诸运作简要为主的原则,酌订代表办事规则。[40]国务院接令后,曾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商讨。不过,大多数国务员认为各都督代表所提的这种议决权,在性质上既不同于参议院,又有异于国务院,实兼有立法、行政两种效力,任何国家都不应有,如予代表以此种议决权,就与国务院会议相冲突,决计不予承认。当时国务院不可过拒,原因在于:政府一方面因为张振武、方维被杀倍受参议院攻击,另一方面又希望在围绕省制省官制案与参议院展开的争执中获得各都督的支持。于是,工商总长刘揆一和教育总长范源濂的调和意见占据上风:各省所派代表均是一人担任一事,宜视其所担任何事,以归于该事主管部,代表既各隶于行政部,不妨予以议决权。[41]据此国务会议决议对代表的议决权变通办理,即“在非国务常会期另开特别会议,关于何省何部分之事,该省代表即有参与会议之权”。[42] 尽管政府和各省都督因为参议院法制委员会在审议省制省官制案时,删去总统解散议会权和削弱省尹的权力,在立场取得暂时一致,政府在代表职权上的态度强硬,使李烈钧在各省代表权限问题上又回到原来的立场。李本在8月31日根据各都督协商结果,命令各机关将临时省议会自光复后至当时议决的法律案件、军事行政各机关拟定的各种编制规则、举办的各项要政纲要手续及政务会议议决各案,全部抄录交存代表,以备到京陈述、备问时参考。这些资料中,“有关系全省通案并纯属于省行政,也有虽为省行政,但其性质则与国家有关,将来中央当全部收归直接管理或变更一部”,[43]但大体尚属省内事件。李得悉政府不满各都督联电所定各省代表权限并力主另定的通电后,态度大变。9月9日,在欢送江西代表赴京所举行的欢送会上,他又提出15个问题,指示代表转达政府。这些问题涉及如何筹划满蒙藏国防、军民分治与合治的选择、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调处以及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的入手办法等。[44]虽尽是当时亟应解决的问题,却超出本省范围。此举表明,李烈钧又回到此前坚持仅视各省代表为传达各省都督意见者的立场。这自然不为政府所接受。加之孙中山、黄兴在8月底9月初先后入京,极大地改善了袁世凯与国民党的关系。袁正寄望借助孙中山和黄兴的力量,疏通政府与参议院、中央与同盟会省份间的矛盾,对于各省代表不甚关心。在孙中山、黄兴影响下,国民党在9月16日开会,决“取稳健态度,与袁总统提携”。[45]国民党与政府、参议院与政府关系趋于稳定。袁还与孙、黄就中央与各省权限划分,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下达成共识,正式确认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等集权中央,其余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46]暂时平息国民党籍都督主导的、各省都督对省官制案的抵制。政府转而致力改善与各都督间的关系。 政府正式将各省代表定名为行政咨询员,设立总务处,并由总统府派朱家宝、沈秉堃等10人、财政内务陆军三部各派4人为特派员,②接待各省代表会议一切要政。[47]同时,由总统府起草行政咨询员简章,不仅规定各省代表在性质与顾问相同,如有关于某省要政时,由大总统和国务总理延请某省咨询员讨论一切,只有关于全国要政才随时召集各代表开特别会议,而且不按时开议。[48]该简章草案后经国务会议修正议决通过。简章共10条,包括:行政咨询事件分民政、财政、军政三种,由主管各部按照情形办理;主管各部派特派员与各省特派员接洽,并就主任事件随时建白或答复意见;各部及各省特派员对于主任事件,如得3人以上同意即可开议;议决及陈述事项应呈候主管各部总长裁夺,大总统亦得派员加入会议,遇事咨询;并设立总务处,为各省特派员会集机关。此外,对各省特派员回省及谒见大总统、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等均有规定。[49]这是政府首次对行政咨询员职权的明确规定,极大缩小了代表权限,且由相关各部直接接洽,隐然有将咨询员隶于各部之下,这与前此都督商议代表职权不符。简章一出,赣代表徐秀钧极不满意,认为咨询员隶于各部之下,如此代表不如解散,藉袁世凯召见代表之机,积极运动,并函约鄂代表孙武出面协调。[50]徐氏显然视咨询员为各省都督代表。中央与各省都督间在各省代表职权问题上的这一分歧,在行政咨询员正式履行职责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四、职责发挥与不解而散 因各省代表迟迟未能到齐,会期一变再变,从8月中旬一变而为9月2日。至9月中旬,好不容易有14省代表到京,又因政府招待员主管朱家宝尚未到京,再次稽延。当时正值都督反对参议院审议会限制行政长官职权及政府苦于省长简任、民选争持不决,政府再度撤回省制省官制案,后经法制局长施愚主导,采用普鲁士制,将省级行政划分为官治与自治两部分,激起各方反对。袁世凯再次意识各省代表的重要性,于是通知各代表于9月25日按省份次序谒见。不过,由于人数过多,袁氏在接见时只能与各省代表略谈数语。[51]随后,不断有报纸报道政府频频向各省代表咨询解决问题的消息。 10月2日,袁世凯召集各省代表在总统府讨论军民分治、财政统一规划、大总统有无解散省议会权,以及省长由中央简任抑由民选等问题。[52]同时,袁也就一些省份内部发生的事件就近咨询该省代表。10月7日晚袁世凯为了解该省所拟遣散军队的办法及程德全对省制案所持的政见,交谕国务院,通知苏省代表陈陶怡、雷奋、赵正平3人,8日到总统府听候传见。[53]10月13日,行政咨询员在总统府会议维持财政办法,决议:盐斤加价,由各省都督、民政长自行核办;借运盐斤以报效银两接济中央;协济中央,各省量力认解;整理税务,由财政部拟具问题交议。[54]此时政府已决采纳虚三级制,并本诸此意将省制省官制修正案核定脱稿,经国务会议通过后,为减少各都督抵制新省官制案,在电告各省都督的同时,再次求助行政咨询员。10月14日,政府与各省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宣布省制案修正情形及变通实行军民分治各办法等。[55]同日,赵秉钧在国务会议结束后往谒袁世凯,据说二人议及实行省制办法及省官制与各省统一政令的问题,并一致决定,17日在总统府召集国务员及各省特派代表等开讨论会,一次性取决统一实行法。[56]会议因故未能按时召开。 10月18日,行政咨询处召开第一次会议。[57]会议刚开始,各咨询员就对政府颇多微词,嗣因财政部特派员报告三议案大要后,又提出应采何种办法编制明年预算案及应据何种标准分别国家税、地方税,要求咨询员答复。[58]此举激怒了各咨询员,他们纷纷发言表达对政府羁滞各省代表数月及不明咨询员职权的不满。后因总统府特派员沈秉堃劝解,方才散会。[59]此时各方在省制问题的僵持,使得政府束手无策,袁世凯等向各省代表求助。10月20日,法制局因省制案虽在数日前就提议,但迄无正当解决,具呈向袁请示办法。据悉,袁世凯一面将梁士诒等在当月12日会后所拟关于省官制案的说帖交由国务院核议,[60]同时命秘书厅分函各省代表,依据本省情势各就省制如何规定,在三日内拟具说帖。[61]次日,袁世凯又派梁士诒、沈秉堃召集各省咨询员,讨议省官制案及其余各省要政事宜。由于各省谘议员反对法制局所拟的虚三级省制办法,[62]结果因人数不齐没能开会。[63] 由于各省所派代表参差不齐,除“三五名宿稍明共和大政”外,其他多碌碌无所表现,或终日在北京八大胡同花天酒地,事事仰承政府鼻息为主,或在各部运动佥事、科长,或趋炎附势,在会议政府提交的军政、民政、财政各项议案时“又互相攻击,意见不一”。袁世凯本就对这些代表非常失望,“悔从前不应召集代表”,[64]但因各省代表到京时间前后不一,又不便解散。于是,所派招待员则秉承袁意,大事殷勤,避谈国事。[65]本来肩负重要使命而来的各省代表见此情形,不满情绪更为加剧。出于激愤,湘代表周震鳞、邹代藩随即留函回湘。各省代表的出走引起政府的重视,连忙寻求补救办法。赵秉钧内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面请袁世凯出面,致电湘督谭延闿申明理由,[66]一面在10月21日与财政总长周学熙、陆军总长段祺瑞,在东厂胡同俱乐部设宴款待各省代表,试图加以笼络。由于政府极力迎合,当日较为融洽。[67]此外,袁世凯也择要开示民政、财政、军政三项方面共15个问题,交各省代表讨论。这些问题与前述李烈钧9月9日所提问题比较,财政和军政两方面多有重合,在民政方面,到底该拿出哪些交由各省代表讨论,歧异仍然存在,但明显超出政府最初的设想,[68]表现出向各省都督妥协的意向。 与此同时,总理赵秉钧意识到,亟需对前拟行政咨询处简章进行修改。10月23日,赵在国务院提议咨询员权限:大总统交议行政事项、国务院交议军政及财政事项,凡属于立法和司法者,不得与议;凡关于地方财政收入及其他有利益于该省者,得呈报政府核议;关于实业事项,迳由咨询员与农林、工商等部会议。对此,各总长“均以为然”。[69]咨询员权限规定一出,国务院即积极遵循施行。时正着手整理各省财政的财政总长周学熙,即在10月24日拟就国税厅设置、中央调查财政的意旨以及划分税项的暂定办法等,求商于各省咨询员。然而,各省咨询员均表示自己不负其责,此举仍须先商于本省都督。[70]此外,总理赵秉钧还面告各部长,各省代表业已来京,宜各就本部范围应行咨询事件在27日汇送到国务院,以便28日复议后再交由行政咨询处会议。[71] 10月26日,袁世凯与赵秉钧商讨省制修正案时,决定28日在总统府召开国务会议,并表示在29日或30日将召集各省代表开会,宣明修定省制的政见并讨论。[72]但由于袁不认可国务院所议决咨询员权限,为此专门在10月29日与秘书阮忠枢等人商议,拟定代表权限:各代表专备政府咨询事件;咨询事件以民政、财政、军政为限;政府与各都督发生疑难问题时,由各代表疏通两方,使内外一致,不得强制执行;由各主管部决定咨询事件,各代表不得干涉;咨询事件但求简明。[73]很明显,国务院与总统府均对各都督商榷所得代表权限不甚满意,且二者议定行政咨询员的权限,基本上是在袁、孙等人9月在中央与各省权力划分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基础上草拟而成的,并比较明确规定各省代表仅限于作为政府的顾问,只能与议行政、军政、财政三项。当然,国务院与总统府因为所处立场,彼此间亦存在不同。相较而言,前者注重代表权限的范围,后者则更强调代表在中央与省关系间的作用。 因大借款未能签字,政府财政更感支绌,积极寻求解决对策。但中央政府与各省立场不同,主张各异。当各省咨询员晋谒赵秉钧,代表各省都督要求政府在民国二年不行酌免税厘时,赵却只是敷衍,表示民力、国币必须兼顾,待国务会议后再定办法。[74]袁世凯只好亲自出面,在11月2日召集各省代表咨询解决财政困难的对策。[75]结果无果而终,反激起代表们的不满。各省代表在当日开茶话会,纷纷表示:各代表奉总统命令来京,理应陈述对于本省利病情形的意见;政府在关于各行省直接设施的政略也必须咨询代表,但是代表应以何种手续与政府相接洽,政府并未规定范围,决定呈函大总统,历叙代表来京理由与其应尽职务,请求政府明示接洽办法。[76]袁接到呈文后,连忙召集各国务员、政府特派员会商对策,最后决议将政府特派员名单概行送交各省代表参阅,并分定日期安排代表轮流晋谒大总统。[77] 俄蒙问题因俄蒙密约的签订更加紧张之后,政府无心继续讨论省制省官制案,将其暂为搁置的同时,因筹措财政和应对边疆局势需要,更加重视各省代表的作用。11月12日,陆军部设宴款待各省代表。当日该部总、次长及司长均列席,且态度极其殷勤。[78]同日,总统府要求各省代表就规定解散军队日期、编配水巡、本年田赋征解,及各省都督条陈拟划分军区等案进行讨论。[79]13日,袁世凯又令秘书厅致函各省咨询员,定于14日在总统府召集讨论会,征集对蒙俄政见。[80]在外患的压力下,各省代表更为活跃,举止超出政府对其权限的规定。11月10日,各省代表联电阎锡山,要求他急电政府向俄抗拒;[81]13日,又决议上书,要求与闻并参加政府对蒙事务的决策;[82]14日,各代表遵约赴总统府,详述对于俄蒙协约意见,一致主张武力解决,[83]会后又以全体代表名义提出四项征蒙理由分电各省都督,要求联合一致对付俄蒙。[84]此外,各代表还计划联合临时参议院,一起鼓动全国舆论,作为政府后援。[85] 政府还来不及应对各省代表的诉求,各督纷纷提出类似要求。袁世凯只好让步,允准各省咨询员参与密会。[86]本此原则,赵秉钧连与各国务员会商变通办法,决计“凡开关于蒙藏之军政、外交密议,准各咨询员旁听,惟不得发言”。[87]政府这一变通,本希望藉此缓和与各都督的关系,缓解因俄蒙协约签订所起的紧张局面。袁世凯在蒙事发生后,将密约原文分电各省都督,征求意见。然而,各都督意见不同,或主平和解决,或主先抚后伐,或主武力解决。[88]在内外压力下,政府态度难免乖戾,覆电各都督时颇为含糊,引起各都督对政府的因循行为极为不满,甚至计划再派专员赴京质询政府。[89]同时,行政咨询员逐渐丧失其存在基础。行政咨询员本为解决中央与各省在内政、财政、军政上存在的分歧而来,而这一诉求因形势变化或在丧失或被取代:一是经中央政府与各省都督彼此妥协,财政调查及税务整理初见成效;二是蒙库事件发生后,各都督都表示拥护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应对外来危机;[90]三是总统府军事处也以征库事宜关系重要,呈请袁世凯电饬各省迅派参谋二人来京会议军事上种种计划。[91]见此情形,夹在中央政府和各省都督之间的行政咨询员自知难以发挥作用。恰在此时,正式国会选举即将开始,在京各省代表因须返回本省参加选举,纷纷以回省筹划军备为由,呈请辞职,对此政府也乐得允准。[92]随着多数咨询员离京,行政咨询处不解而散。 五、结语 民国元年行政咨询员从出现到不解而散的历史过程表明,在民初政体变革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各省都督间除因利益纠葛出现对立,彼此间亦曾有过意见沟通的尝试,只因民初的特殊政情,这一尝试一开始便成为中央与各省力量较量的延续。 行政咨询员的出现是必要的。自晚清以来,“省”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各省更在辛亥革命中取得事实上的“自治”地位,并在联邦制下结合组建中华民国,继续通过各省都督府代表,代行参议员职权,左右南京临时政府的重大决策。南北统一后,袁世凯依据《临时约法》组织统一临时政府,但势力尚不能控驭全国,东南光复各省,尤其同盟会(国民党)籍都督仍拥有强大的力量。主张集权和统一的袁氏及政府与要求自治与分权的各督间,通过一个管道进行意见沟通是极其必要的。正如时人所言,“在革命起于地方,中央旧有权力一一分夺于各都督之手后,如欲由各都督之手一一奉归于中央,非中央与地方开诚布公,各捐猜忌,斟酌利害、是非而一一商定之不可。”[93]因此,各省代表到京后,“大可各自就各省行政得失、利害以及民生、国计的因革损益陈说政府,匡补中央行政缺略,并借以疏通中央与各省两方面意见而收统一实效”,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对待,“善用之则于政治及感情上收完好之效果,否则必至中央与地方滋生恶感情,因之政治上亦现睽离之状态。”[94] 然而,中央政府与各省都督、袁世凯与国务院之间,在对行政咨询员的认知上存在分歧。在中央政府看来,咨询员只是政府仿效清季各抚督派员参与外官改制先例,由各省都督派出的个人代表,以备中央行政决策时咨询,借以疏通与各都督的关系。而在各都督看来,咨询员不仅为自己私人代表,更试图将咨询员回归到创建南京临时政府时各省都督府代表的角色,成为自己左右中央行政决策的管道。由于时势亟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使得这一诉求苍白无力。而且由于知识背景、党派归属、所处的内外环境以及利益考量等因素影响,各都督间也难以一致。即使在政府内部,袁世凯与国务院间意见也不一致:陆征祥内阁时,由谁主导与各省代表的接洽,国务院与袁世凯存在分歧;赵秉钧则力图在袁世凯所允许的范围发挥作用,即使在袁、赵之间因府院职责不同亦存有分歧。正是中央与各省以及府院间的这一分歧,直接致使行政咨询员履行职责受到限制,虽因形势变化有所逾越政府的限定,并最终无疾而终。在经受此次失败的尝试后,中央与各省依据彼此实力进行较量。随着自身权势增强和对内阁的控制,以及当时对建立强有力政府的渴望,袁世凯又回到“独断乾坤”的立场,以命令代替法律,颁布暂行省官制。 注释: ①在当时,“行政咨询员”又被称为“各省都督代表”。日本学者曾田三郎曾略提及这群人物,见《立宪国家中国への始动——明治宪政と近代中国》,京都:思文阁,2009年,第334页。李学智对此亦有注意,但对代表性质及解散原因,与事实有一定距离,见《民元省制之争》,《民国研究》总第17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18页。 ②政府派员并未严格按此标准,总统府、内务部各派5人,陆军部7人,财政部11人。《行政咨询员特派员名单》,《神州日报》1912年11月16日第4版。标签:李烈钧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民国论文; 袁世凯论文; 历史论文; 程德全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