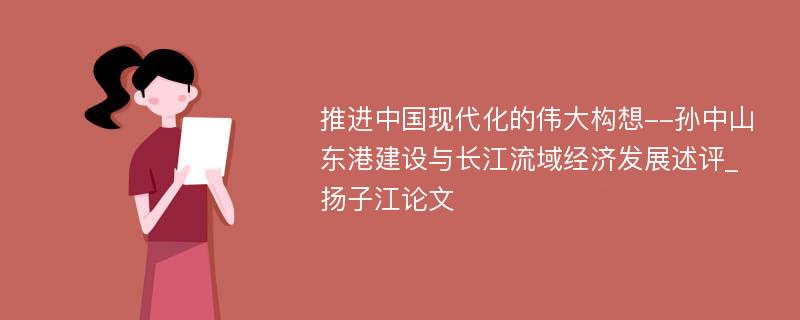
一个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设想——孙中山建立东方大港和开发扬子江流域经济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扬子江论文,大港论文,述评论文,流域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以来,中国许多志士仁人,为振兴中华,竭尽思虑,提出种种建议设想,规划未来宏伟蓝图。孙中山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18年5月,护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被迫避居上海法租界寓所(今香山路中山故居),“闭门著书,不理外事”,检讨革命失败之教训,规划未来建设之宏图。1919年写成《实业计划》。时值“欧战甫完之夕”,孙中山为大战期间及稍后一段时间里中国民族工业长足发展而欢欣鼓舞,又为北洋政府倒行逆施,使中国经济与世界先进国家拉大差距而忧心忡忡,他主张抓住战后“各交战国家军需工业必须转化资金另谋出路”之机会,利用欧美“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①]
一
《实业计划》又名“国际共同开发中国实业计划书”,是一个开放型的规划。开始时系英文撰写,意在“希望国际决策之制定者,或对此巨大决策有影响之人士能同意此种观点”,并便于在欧美各国传播发行,“以利于计划之实施与完成”。[②]1921年《实业计划》由朱执信等人译成中文首次出版。《计划》除“篇首”和“结论”外,共分六个计划,设想在中国东部沿海建立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以三大港为起点,建筑五个系统的铁路网,伸向内地四面八方,配以公路航运等,以交通,特别是铁路为龙头,开发中国内地经济。在第二计划中,孙中山提出在长江口附近建立东方大港,改造上海旧港,并开发扬子江流域的具体设想。
与北方、南方大港相比,东方大港拟在中国东部中间,筑成与美国纽约港相匹敌的世界大商港。当时上海已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又在中国东部中央,当可现成利用。然而上海港受长江淤泥填塞,航道日浅,“无以适合于将来世界商港之需要与要求”。如加改造,“所费甚巨”[③],同时港区地区狭窄,又被列强租界分割,地价昂贵,扩建改造,困难甚多。为避免这些牵制、纠葛,孙中山主张一面规划改良上海旧港,一面另觅新址,建筑东方大港。
为选择港址与规划建港,孙中山作了长期的酝酿与准备。他参照了世界各国港口建设与管理方面的名著,查阅了大量沿海的地质、水文、气候等资料,亲自或派人进行实地勘察。早在1916年9月15日(农历8月18日观潮节),适逢袁世凯死后不久,孙中山心情舒畅,精神振奋。这天雨后天晴,孙中山和叶楚伧、朱执信、蒋介石等一行七人,从上海乘火车前往浙江海宁钱塘江观潮。钱江潮水惊涛拍岸,奔腾起伏。孙中山深有感慨地留下了“当今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著名题词。当夜留宿海宁商业学校,又为该校师生题写“猛进如潮”的匾额。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正以他那吞吐风云的气慨,思考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篇章。回沪后孙中山始终惦记着钱塘江弯弯曲曲的堤岸。不久着手撰写《实业计划》时又派机要秘书邵元冲专赴乍浦等钱塘江沿岸,搜集海塘资料,并嘱咐调查乍浦澉浦一带之海塘,弄清是石塘抑系土塘,谓“如无书可查,宜亲询该处士人,以期确实”。后来邵元冲将“查得浙江水陆道路记等书,图说颇详,乃举以相告”。孙中山“遂据以为规划东方大港之资”。[④]期间,孙中山还亲自去过海宁作实地调查。据1966年宋庆龄在纪念孙中山诞辰百周年回忆此事时说,“他只要有一点空,就在书屋里把大地图铺在地上,手里拿着深色的铅笔和橡皮,在上面标绘铁路、河道、海港等。有次他乘巡洋舰视察海宁时,告诉大副航道水浅,把船靠外行驶,但这位大副自以为他更熟悉情况,结果船搁浅。”可见孙中山掌握沿江水文资料之具体。
在选择港址的标准上,孙中山认为有四个原则必当遵循的:(一)必选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资;(二)必应国民之所最需要;(三)必期抵抗之至少(即避免因征地等引起群众抵抗者—引者);(四)必择地位之适宜。根据上述四条原则,孙中山确定东方大港最良好之位置“当在杭州湾中乍浦正南之地。”即杭州湾北岸乍浦角和澉浦角之间。
翻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杭州湾乍浦与澉浦之间,海岸呈弧线凹形,两突角相距约15英里(21.4公里)。港区建筑规划将作这样安排:在两角之间的凹形海岸,分成五段,每段3英里(4.8公里),分期分段建筑一条水泥石筑海堤。而在乍浦角突入海面数百尺处开一个缺口,作为港区的正门。为何选在伸出海面的地角上开口作港区的大门呢?因地角深入海中,受海浪冲刷,附近不积泥沙,水位较深。据测平均低潮时深12米至14米。港身长约20公里,宽2.4公里,港面水深最浅处为11米,平均水深达15米。完全符合世界大港12米水深的标准,最大的航船可以自由出入港口。
孙中山认为东方大港“作为中国中部一等海港”是“远胜上海旧港”的。第一,“此港一经作成,永无须为将来浚渫之计”。因为港区附近没有夹带泥沙的江河,加之杭州湾潮汐的冲刷,不会造成港口及航道的淤塞,今后不存在疏浚问题。第二,乍浦澉浦附近,有大量未被开发的土地,在此地“规划城市,发展实业,皆有绝对自由”,“一切公共营造及交通计划,均可采用最新最有利的方法建造”;第三,从资金上考虑,建设一个港口,需要巨额资金,购买土地。乍浦澉浦一带的普通农地价格要比上海地价低得多。当时每亩地仅50元至100元。为建筑港口,可以根据平均地权的原则,以政府名义购为国有。为建筑港身及街市之用地,约需200平方英里(合76.8万亩),按每亩最高价100元计,也只需款7600万元。这笔款项在当时虽不算小,“但政府可以先将地价照现时之额限定,而仅买取所须用之地”,其余暂时不用之地则作为国有土地,未给价者留于原主手中,只许使用,不许转卖,国家一旦需用时,随时可以以不变之地价向原主收取。这就是说,根据城市发展进展,分期征用土地。港口一旦建成,“地价急速腾贵”,每亩自千元至10万元之高价。这样,政府可以将土地自身产生的利润,收买以后所需的土地。“以地养地”,“以地征地”,逐步扩大,建设资金何愁源源不绝而来。
在原来荒僻的地方建造港口和港口大城市,完全可以采用最新的方法,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市内按照生产、流通和消费的需要,分设港口作业区、工业区、商业区、金融区和行政、教育文化区、居民住宅区等等。各区之间配以公共交通,连成一体,构成最佳的布局。这种新型大城市出现后,原来的上海则留“作为内地市场与制造中心”,这样并不会如有些人担心上海会衰落。孙中山举了英国孟遮斯打(曼彻斯特)旁边的利物浦港、日本大阪西侧的神户港,以及东京附近的横滨港为例,指出后者都是筑海港后新兴的大城市,而前者的老城市并未因为港口新城的兴起而失去繁荣的地位。孙中山放眼世界,满怀信心地认为东方大港,一定能建成象美国纽约港那样规模的现代化世界大商港和大城市。
二
孙中山在规划杭州湾新建东方大港的同时,对上海港的作用仍倾注了极大的注意力,主张通过一系列的改造,充分利用上海港的现有设施,使其保持“在全国经济中居有的特殊地位”。
我国北方沿海一些港口,如牛庄、营口等港,冬季有结冰之患,且港身腹地河北、山东地区,地质上都属冲积区,土质疏松,入海河流夹带泥沙。故港口附近沙洲满布,水位很低,港口一般不深。而南方沿海港口,大都为花岗岩层,近海暗礁丛生,只能停泊较小船只,为海军停泊军舰或地方性进出口贸易之用,且南方入夏以后,台风频繁,急浪袭击,不利船只通行。而地处我国中部沿海的上海港,地理位置极为优越。它扼万里长江入海口的咽喉,沟通江、河、海、陆的交通运输。并以物产富庶,盛产出口丝茶的江南水乡作为它的广阔腹地。这样的港口,既无北方港之结冰之患,终年通畅;又无南方台风急浪之害,潮水落差较小。同时河底泥土细软,便于船只抛锚停泊,两岸地势平坦,适合码头仓库之建造等等。上海港这些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在全国经济的发展中显示了优势的地位。早在明中叶以后,上海已是海上贸易的发达县城。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启航港口就在上海附近的太仓刘家港,随船而去的不少水手是上海本地人。1684年,清康熙年间解除海禁后,开放海上运输,在上海华亭设江海关,先后建立了北洋、南洋、长江、内河和国外五条航线。鸦片战争以后,上海最早被列入开放口岸,迅速取代了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特别是杭嘉湖一带盛产的著名丝绸以及棉花、桐油、药材、猪鬃、羊毛、皮革等大宗物资,全都源源不断汇集上海,运销海外。日益发达的对外贸易不仅推动了上海工商金融业的发展,更直接促进了上海港口的不断扩展。开埠之初,租界当局在外滩已建成十多座驳船码头。六十年代以后,随着进出口航船的增多又建造了一批固定码头和堆栈仓库。甲午战争以后,外国列强在华获得设厂特权,浦江两岸码头更是鳞次栉比,见缝插针,接连建立。到本世纪二十年代,黄浦江已是汽笛之声不绝,船只穿梭往来,呈现一片繁忙景象。
然而上海港在日益发达的工商经济和进出口贸易面前,显得力不从心,疲惫乏力,潜在的危机不断显露出来。这主要是由于潮水之涨落速度不同,浦江航道随涨潮带进来的泥沙积沉下来,造成河床堵塞日趋严重。一些浅滩阻挡了吨位较重、吃水较深的巨轮驶入。上海开埠初期,船舶吨位小,吃水浅,进出船只尚能自由通航。随着贸易的扩展和造船技术的提高,船舶吨位不断增加。1850年至1860年的十年间,进出船只平均吨位为1000吨,吃水3至4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平均吨位达到2300吨,吃水增至5米至6米。到1880年平均吨位增加到4000吨,吃水7米以上。三十年间,船舶吨位增加4倍,吃水深度增加2至3倍,船舶吨位的增加与浦江航道的淤塞矛盾愈来愈突出。一些装载货物的巨轮,往往需要等候潮水,方能进港。有的船只,只好停在吴淞口外或改装驳船、或卸除部分货物再行驶入。这样就大大减低了港口吞吐能力,增加了运输费用,严重地削弱了上海对外经济的交往,特别是影响了在华外商的利益。为此,上海租界当局曾多次向清政府致函,要求疏浚黄浦江航道。驻沪英国领事惊呼“上海商埠不久将为海洋巨船所不能达……或竟沦为无足轻重之内地市场。”[⑤]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则巧妙地说:“浚浦之事之是否核准,将直接关系到当地人士之利益”,不然的话“上海及宁波的丝茶,皆于镇江装运,镇江必取上海而代之”。[⑥]尽管外商把航道问题说得如何严重,清政府却一贯彻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某些昏庸无能的官吏起初“企图利用吴淞浅沙阻挡侵略者”,“防止兵舰进入港内”。同时由于疏浚浦江,需要大笔经费,当时清政府对外借款,对内镇压人民,财政早已枯竭,自然不肯在航道上化钱,因而长期拒绝疏浚。然而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毕竟都要仰赖外国侵略者,在外商一再敦促下,1882年清政府才第一次向英国格拉斯哥购买了一艘“安定”号挖泥船,于1883年3月10日开挖,前后六年,因船身过小,成效甚微。1889年5月,又造“开通”号拖轮铁壳泥驳3艘,重新开挖。至1891年9月,二年多时间挖泥24万吨。这种小规模的疏浚“不可能取得什么真正的好处。”[⑦]1901年,八国联军之后,中国失败,列强各国强迫清政府订立《辛丑条约》,在条约末尾写上了与义和团事件毫不相干的浦江航道疏浚问题。清政府明知这是出让主权,但为了维持其日益动摇的统治,不得不同意成立黄浦河道局,计划用20年时间,每年费银46万两来整治黄浦航道。当时吴淞口内水深只有3.3米,吴淞口外也只有4.5米。首期工程到1910年完。黄浦江口至高桥一段的主航道,最浅处水深增至6米,涨潮时可达7米左右,一些较大的轮船,勉强可以驶入。1912年4月,辛亥革命后,河道局改名浚浦局,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聘用荷兰人奈格为总工程师(后调瑞典人海登斯丹),继续进行整治。经过多年的疏浚,浦江航道的淤泥虽有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奔流不息的滔滔长江,带来了巨量泥沙,航道淤积问题仍然无法根治。据此,从1914年至1919年,中外专家就浦江航道的疏浚问题,提出过许多调查报告和整治计划方案。这些报告和方案自然为正在制订规划的孙中山所重视。与众多的中外专家一样共识,孙中山认为上海港问题的症结在于“扬子江之泥沙”。根据浚浦局技师长方希典斯坦的推算,扬子江每年夹带的泥沙约有一万万吨,“足以铺积满40英方里之地面至10英尺之厚”。这些泥沙填塞航道异常迅速。所以,“由此审度”,“必首先解决此泥沙问题,然后才可视上海能永成为一世界商港者也。”
怎样整治长江航道、改造上海港呢?孙中山参酌诸家建议,较比种种方案,其设想大致可分四个部分。
其一,重挖一条新黄浦江,以替代老的浦江航道。当时有一种议论,主张将河道局花了12年时间、1100万两银子之代价疏浚改造之工程(从黄浦江口至吴淞江心沙上游高桥一段)“尽行毁弃”。孙中山反对此举,认为应该保留这段工程的成果,但“必须延长河道局所已开成之水道”,“又扩张黄浦江右岸之弯曲部,由高桥河合流点开条新河,横贯浦东。在龙华铁路接轨处上段第二转弯处复与黄浦江合流。这就是说在浦东地区,自北向南,重开一条黄浦江。其南北两端仍与老黄浦江汇合。新黄浦江计划水深12米,自南端汇合之处至杨树浦的河段,“直儿如绳”,再往北至吴淞,略有弯曲。
其二,因开河而新圈的浦东11万亩土地,一部分作为新市宅中心,一部分辟为新黄浦外滩。而老的黄浦江水道,则填塞成陆地,作为国有土地,用以拓宽马路和建造新的商业街市。这些新街市和新外滩将成为新的黄金地带,地价昂贵,其增加的地价用来补偿新圈土地的价值,“以地养地”解决了资金来源。
其三,自杨树角起北至吴淞口江心沙上游(高桥河)转弯处,横跨老黄浦江(此段不填塞),和新开浦江接通,建立一个大泊船坞。面积约有6平方英里(合4000余亩),水深与新浦江相同,为12米,作为停泊来往巨轮之用。
其四,整治长江淤泥。这是改造上海港的关键。孙中山根据“航道阻塞必自河口始”的自然水文规律,把治沙主攻方向放在扬子江入海口。原来扬子江有三条入海水道,即北水道、中水道和南水道。崇明岛介于北水道和中水道之间。河道口之所以易被沙泥淤塞,盖因河道入海口过于宽阔,江水入海,流速大大减慢,泥沙因此而沉积。故“救之者,收窄其河口”,加强水之流速,使其与上游湍流一般。这样水流湍急“沙泥被水裹挟,直抵深海,”泥沙自然不再沉积。
那么怎样收窄扬子江入海口呢?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书中设想堵塞原入海口中的北水道和南水道,留下一个中水道。方法是在中水道两侧,建筑石坝,高度与海水低潮时相平。这样,当三股水道之流汇聚一处时,流速骤然加急,如此急流冲刷河床,泥沙为水所混,可以“直冲到深海广阔之处”。当潮水同落时,泥沙则向石坝两侧扩散,正好填平中水道两边的低洼地。这样利用潮水涨落正反方向流动的自然力,“遂使河口常无淤泥”。上海港因此可保持畅通无阻。利用泥沙,填海为田,变害为利。经二三十年之后,估计可填平1000英方里面积。这些土地耕作收益可补偿投资之费。通过这样的改造,上海港才能成为“世界港得一永久之通路”,而保持其原有的繁荣地位。
三
扬子江下游(芜湖以下)及江南地区,自明清以来,经济发展就在全国处领先地位。孙中山在规划全国实业建设的宏图时,始终将这一地区作为全国的中心,以此带动和促进内地经济的开发;而各地产业的发展又反过来加强扬子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实力。通过这种横向联系、互补互助,使全国经济波浪式地向前推进。与全国性规划一样,孙中山是以交通特别是铁路为龙头来部署扬子江下游地区实业开发的。孙中山认为实业范围甚广、门类繁多,“助之而必行者”,必须首先发展铁路交通。“苟无铁道,转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之可图?”故“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⑧]孙中山不仅从发展实业上重视铁路建设,而且还从保障国家主权独立和统一的高度告诫人们,认清修筑铁路的重要,强调“今日我国,如欲立足于世界,惟有速修铁路,以立富强之基”,否则,“一旦铁道为人所夺,国即为人瓜分”。[⑨]
早在1912年6月25日,孙中山在上海与《民立报》记者谈话时,便提出了在10年内建设全国三大铁路干线的设想。其中之一就是起自扬子江口的中路铁路大动脉。它经过扬子江流域的江苏、安徽,转入河南、陕西、甘肃,越新疆而迄于伊犁,横贯中国东西诸多省份,计程数千公里。
1919年,孙中山在制订《实业计划》时,又在第四计划中,进一步使三大铁路干线计划周密化和系统化,并将起自东方大港的铁路分别列入中央铁路系统和东南铁路系统,在全国五大铁路系统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其四通八达的铁道修筑计划,包括有:
第一,东方大港塔城线,为西北走向。此线沿太湖至南京过江后经安徽、河南、陕西,循渭河西行,横绝沙漠,经新疆哈密,直至中苏边境的塔城。全程4800公里。
第二,东方大港库伦线。自安徽定县起,经河南、山东,两渡黄河,折行入陕西、绥远,直抵内蒙库伦。全长2100公里。
第三,东方大港乌里雅苏台线。从库伦线的定远起,经河南郑州,过黄河入陕西,循长城南侧至宁夏,达至终点乌里雅苏台,全程2900公里。
第四,东方大港重庆线。自东方大港起至杭州,西行安徽、江西,循扬子江右岸穿两湖,入四川,沿扬子江而西上,直至重庆。全程1900公里。
第五,东方大港广州线。自杭州折西南行,沿钱塘江左岸至江西,越赣粤界岭,直达广州,全长1400公里。
除以上五条贯通全国的铁路大干线外,还有扬子江下游地区性的若干条短线铁路。如苏嘉、芜霍等。总之中央铁路系统中24条铁路中有15条线路直接与扬子江上游东方大港相联接。上述铁路干线修筑的走向,明显地体现了孙中山以扬子江下游流域为中心向腹地扩散、推动和开发内地及边远落后地区经济的总体构想,而将对外开放的东方大港作为实现这一庞大计划系统的总枢纽。
除铁路以外,孙中山也十分重视公路建设和内河航道的疏通改造,以建立铁路为主体,水陆配套的交通网络。与铁路建设和运输相比,公路建设造价低,汽车运输灵活、简便,而内河航运更是量大、运费低,可以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而且有些地区,限于种种条件,无法修建铁路,更应注意公路的扩展。1912年10月19日,孙中山在考察长江下游途经江苏江阴县时发表演讲,在宣传铁路建设的重要时,又结合当地实际情形,申述公路建设的必要。他认为“有了马路(即公路)火车方能发达”。当时江阴有人呈函要求孙中山支持从江阴县至沪宁线横林(无锡西)筑一条铁路的主张,孙中山当即表示,江阴县距沪宁线不远“不过四、五十里,来往的人又不很多。”“若是通了火车,每天开车两次,那火车公司就要赔本”。所以在此修筑铁路“是很不值得的”。[⑩]他劝导地方官绅与百姓,注重公路的建设。
在改造上海旧港、疏通黄浦江航道计划中,孙中山还细密地设计了长江中下游的河道疏浚和内河商埠的建设。在《整治扬子江》为标题的计划中,自吴淞口溯江而上至汉口,分为五段,即由黄浦江合流点至江阴,由江阴至芜湖,由芜湖至东流,由东流至武穴,最后由武穴至汉口。该计划对每段江岸的特点,从起止里程到水位深度、江面宽窄、堤岸曲直,以至泥沙流量、沙滩位置等水文情况都作了详尽的记述,并在自制的地图上用英汉两种文字标出沿江重要城镇地名等。以这些数据为根据,提出了每段江岸的整治方案。在这个详尽的计划中,孙中山十分重视河道修治后的经济效益,因此对每段河道疏浚和筑堤工程所需的经费,都一一作了估算。从表面上看来,除部分“新填之地”,可以开垦种植“补其所费”外,大部分在短期内“不能发现不亏本之方法”,但河道疏浚后,保护了两岸陆地,防止了将来洪水为患,同时又能在沿江建立商埠,有利于航运和经济开发,从长远看是“必为有益”的。(11)孙中山举苏伊士、巴拿马两条著名运河工程相比,认为长江航道疏浚后,“容航洋巨船驶至住居2万万人口之大陆中心”,经济上“更可获利”。此外,孙中山还对长江以外的内河、内湖例如运河、淮河、汉水以及太湖、鄱阳湖、洞庭湖等江南内河水系的整治,或疏浚筑堤,或开河分洪,或设闸蓄水,无不因地制宜,各作细致的规划。在这里,我们透过计划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的孙中山,为开发实业、振兴中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和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这种精神和态度永远为我们后人所敬慕。
扬子江上游的江南地区,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星罗棋布的中小城镇。城镇经济成为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孙中山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重视。在《实业计划》中,专节规划了“内河商埠”的建设。认为这是“发展计划中最有利之部分”。计划指出,这一地区城镇经济之所以特别发达,主要原因在于该地区农矿物产丰富、居民极为稠密、水陆交通方便、附近大城市的辐射影响等。这可从江南中小城镇几乎都座落在水陆交通交叉口上以作引证。孙中山认为整治长江和内河工程完成之后,“水路运送所费极廉。则此水路通衢两旁,定成为实业荟萃之点”。加上“两岸之廉价劳工”,所以沿江河两岸,东起海边,西达汉口”,“转瞬之间,变为两行相连之市镇”。(12)孙中山看准了这一发展趋势,主张“选最适宜者数点”,进行积极的建设和开发,在小城镇上做大文章。
在计划中,孙中山对镇江、南京、浦口、芜湖、安庆等沿江原有的大中城市,分别列举它们的简要历史沿革、地理位置和传统产业等情况,根据这些情况提出了今后城市适宜发展的产业和街市基本设施的改造与建设。在这里,孙中山特别要求人们注意历史上形成的两岸对肘城市的兴起,将它称为“双联市”。例如镇江与对江的扬州、南京与浦口,以及武汉三镇等。认为在江南地区,江河交错地区“建此双联市,必为大有利益”。他以安庆为例,建议将安庆对岸“突出的地角应行削去,使江流曲度更为和缓而全河之广,亦得一律,新市街即当在此处建造”。(13)这样,皖南浙西所产茶叶、稻米等大宗物产都将在此新市集散。对新城镇的选点、建筑以及各城镇开发何种产业等这些具体的设想,孙中山认为应由专家们另行设计,因此计划中没有作更多的议论。但是他建议在扬子江下游城镇积极发展水泥工业,认为这是适宜的。因为这些地区盛产水泥原料石灰石、煤等,且水陆交通方便。在孙中山看来,“钢铁与士敏土,为现代建筑之基,且为今后物质文明之最重要分子”,无论是国际国内,“筑港建市街,起河堤岸诸大工程同时并举”,水泥是必不可少的。如斯巨大市场,“不足供此所求”。(14)所以孙中山提议“投资一二万元资本”,兴“建无数士敏土工厂”,必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孙中山建立东方大港和开发扬子江流域经济的伟大构想,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经济现代化的趋势,代表了国家民族的利益。然而在当时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帝国主义步步入侵,大小军阀连年混战,国民经济日趋衰败,人民生活贫困颠沛,根本不具备有计划进行大规模建设的条件。时光荏苒,70年过去了,只有改革开放的今天,孙中山的伟大设想才能逐步变为人间的现实。
注释:
① ③ (11) (12) (13) (14)《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6、231、221、227、231、238页。
② ⑧ ⑨ ⑩《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86页,第2卷第383、435、526页。
④邵元冲《总理学记》,《孙中山生平事迹追忆录》第695页。
⑤《上海港史话》第113页。
⑥岑德彰编译《上海租界略史》第138~139页。
⑦《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22页。
标签:扬子江论文; 黄浦江论文; 孙中山论文; 上海铁路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实业计划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港口论文; 长江论文; 铁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