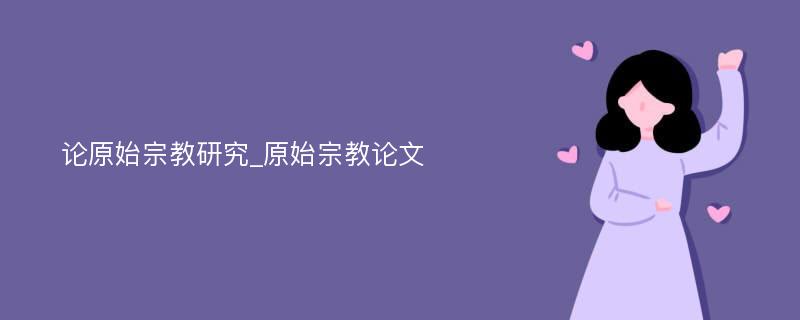
试论原始宗教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原始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原始宗教曾经是原始社会里的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意识形态,它是民族学和宗教人类学传统的基础性研究项目之一。原始宗教在人类历史上跨越的时间最长,即使进入了阶级社会,它也没有全然消亡,仍然在某些僻远闭塞的地区和民族当中,程度不同地找见它的踪迹。原始宗教包涵的内容极广,几乎囊括了它所存在的社会的整个生活面,而这方面的研究通常主要包括了宗教的起源及最早或最原始的宗教形式;各种观念、信仰的形成与本质特征;诸崇拜形式的内在联系及其转换或演变;仪式和仪俗中的象征含义;“原始思维”的特点;原始宗教和原始艺术、医术、神话、民俗、道德、法律及语言等共生现象之间的关系;多神教和一神教的关系;原始宗教和族群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及社会制度之关系;原始宗教的历史作用以及当代人应该怎样看待原始宗教。
19世纪以来,在西方人类学的研究中,有关原始社会的历史和文化方面,原始宗教问题常有专门的著述相继问世,在不断的学术批判与激烈争论当中,均有多种不同的理论流派涌现出来。可以认为,在上述列举的众多问题中,不可能存在着一种固定不变的解析模式。我认为运用不同的理论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材料研究原始宗教,充其量只能说明局部的现象,解释部分问题,对于原始宗教这个跨越时空极长涉及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生活面极广的异常复杂的精神世界问题,欲用一种概念化或公式化的方式看待它和处理它,实为不可能的。
我们能够见到的原始宗教信仰活动多属于民族志和宗教志的范畴,绝非是往昔历史上的实际情状或全貌。考古学提供的实物资料原本有限,仅是零星的片断,而且经常夹杂了不少并非确凿的推测成分;语言学留下来的多属并不连贯且发生了不少变异的残迹;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不是语焉不详就是充斥着混乱和矛盾,特别是渗透着后人的观念,远非原型原装。需要讲明,此处我并不是否定上述学科资料的价值,仅仅是指出其中的明显的局限性或不足处。
研究当代残存的原始宗教,必须立足于实地调查。倘若不具备实地调查的足够的经验,不全面了解人们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不熟悉他们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化习俗及心理状态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只满足于从文献资料到文献资料,从理论到理论的归纳推导式的做法,那确实是很难深入和创新的。至于实地调查,当然存在着方法和技术上的甚至是不可回避的心理上的许多问题。需要提出的是无神论者去到有神论的群体当中直面了解其信仰活动,首先必须充分地尊重对方,至少要让他们理解你的调查工作,不会对他们造成危害。
原始宗教研究的经验往往显示:试图通过局部的资料就想推论和概括全部宗教的原理和本质,那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欲证实一个看法或假设而列举若干事项时,继而会发现一些相反的例证。E·杜尔干的经典研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5 )一书提出宗教起源于图腾崇拜,并且对“仪式”(ritual)提出了一个颇著名的功能性理论,认为宗教仪式在本质上视为用来表达和加强集团的感情和团结的一种主要途径。然而这位“书斋式学者”并不明白在澳大利亚的部落里,村落居地的群体和氏族群体之间有明显的差别。村落群体始终是从事于共同经济活动的单位,而氏族群体主要是在定期的图腾崇拜地点上共同举行仪式时才汇合,仪式结束复又分散。为此有人指问,那些除了仪式之外没有任何联合行动的社会群体究竟是通过什么来保持他们的团结一致的呢?此外,那些没有图腾崇拜的如安达曼人和爱斯基摩人等,尽管他们对于某些动植物保持着一种仪式的态度,却始终缺少共同的有关缘关系的图腾崇拜的观念和仪式,试问他们的宗教起源是什么呢?当然不是图腾崇拜。再如,我们惯常以为那些奉行图腾崇拜的群体或民族,其选择作为图腾物的物种曾是同他们的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或重要的利用价值。但是民族志的资料表明,非洲的一些民族所选定的图腾物,多数都没有什么利用的价值,相反地,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被利用的动植物、自然物或人造物,可谓关系至为密切,却从来没有被选入图腾之列,这又当如何解释呢?拉德克利夫—布朗曾对澳大利亚部落做过实地调查,他认为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这两种宗教崇拜的形式和社会结构形式之间有一种密切的一致性,他提出祖先崇拜仪式往往和社会中的世袭结构有关联。可是伊凡斯—普里查引证了不少的氏族部落社会不存在世袭制度,却盛行祖先崇拜的事实。〔1 〕可见对宗教现象的理解或解释,常常难以用特殊来概括归纳出一般。我觉得重要的是要阐释清楚宗教中的观念信仰和行为是怎样同一个特定地区群体的社会结构形式及现实生活发生关系的。事实上,原始宗教并不总是直接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宗教形式同社会生活的联系是复杂多样的,多层次的,更是曲折的。我倾向于宗教的起源在不同的自然生态条件下不同的人群当中可能采取不同的原始的形式的说法,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巫术等都可能是属于宗教起源的形式,而且原始宗教的各种崇拜形式的发展演递,也不可能是万般一律的直线推进。因此,对于原始宗教中的每项问题,我们只能将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一定的自然的社会的条件下,置于一定的文化环境或背景中,坚持具体问题作具体的分析。
在原始宗教的调查研究中,最感困难的是具体了解和把握属于信仰系统中的各种观念之内涵,以及它们的形成与演变。信仰是一种信念,看起来似乎很抽象,但它们是一切宗教行为的基础或核心,支配着各种崇拜的仪式、仪俗的行为,倘若不注重探究构成信仰系列的各种内在的观念和思维的特点,仅仅限于仪式仪俗行为的外在表现,则这种研究最终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深掘不出有理论价值的东西,也找不准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容易导致研究上的迷津。西方的一些专搞象征人类学的人,一味强调宗教仪式的行为研究,每每忽略仪式背后的种种观念内函的特征分析,是不可取的。围绕对观念的探讨,应是宗教研究深层次的东西,值得重视。
此外,在原始宗教的调查研究中,我们还必须意识到调查研究者和被调查研究者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着的巨大差距,特别是表现在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种种差异。如果忽视甚或无视这类历史的文化的差异因素,就有可能把原始宗教简单化或现代化,即用我们的认识或理解来取代原始人的思想,用今人的概念强加在原始人的头上,或用汉族的习惯看法框套少数民族宗教活动中的独特观念,这是最易出现的弊病,应引起我们高度的警觉。
近十余年来,我国原始宗教的研究陆续出现了一批可喜的成果,其中包括有价值的调查报告和资料汇编,以及具有较好质量的学术论著等。但是,这一领域的研究毕竟还处在初步阶段。从民族学和宗教人类学的宗教人类学的角度观之,有关民族志和宗教志的原始信仰活动第一手材料尚不全面系统,不少术语缺乏统一和规范,田野专项调查向来开展不够,译介国外有较高学术水准的论著的工作也颇为缺乏。对于迄今保存原始宗教较多的边疆民族地区,随着这些地区的开发和社会的进步,有关资料消失较快,抢救资料的工作始终是一项很紧迫的任务。总的讲来,鉴于主客观的多种原因,我国原始宗教研究领域中积累的资料还不丰厚,也不齐全,研究人员自身所具备的学科条件及研究手段比较单一,综合性比较研究不多,理论和方法的探讨更显薄弱,学术评介和争论也不够等等,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原始宗教研究水准的不断提高。
二
在原始宗教的调查研究中,“精灵”、“鬼”、“神”这三个术语是最为常见和使用最频繁的。世界各民族在自己的宗教信仰系统和神话系统里对这三个术语都有一套专门的称谓,具有独特的内涵和解释。在我们运用汉语语言文字记载、报告、著述或翻译其他民族有关原始信仰时,须明瞭汉语中的精灵、鬼、神的内容, 它们并不全然等同于其他民族的解释。比如“精灵”一词,在古代汉语里有时同“鬼神”或“神仙”混用,《文选·左思〈吴都赋〉》:“精灵留其山阿。”吕向注:“精灵,神仙之类。”但是,作为学术用语,当将这三个术语予以区别,作出比较准确的解释和规范的界说,否则势必会造成这类术语在使用上的混乱状况。
首先需要提及的是同这三个术语有直接关系的“灵魂”这个术语。灵魂这个词古今中外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称谓和传说,比较共同的说法是人的灵魂居于人的体内,人死后其灵魂可以脱离其躯体而单独存在,并构想出一套有关灵魂的属性、功能和生活方式,进而认为存在着“灵魂不灭”或“灵魂转世”等复杂的情况,形成一系列以灵魂为中心的崇拜活动。灵魂观念虽是一切宗教信仰活动的基石,但是,处在不同社会里的各民族对灵魂的解释却不尽相同。据我的实地调查,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家族公社的独龙族比较普遍地相信一个人有两个灵魂,即活魂(“卜拉”)和亡魂(“阿细”)。人的死亡总是活魂先死,不久其躯体才会死亡,紧接着亡魂出现。亡魂总是舍不得离开家宅亲人,经常从亡魂们聚居的地方“阿西默里”跑回家中要吃要喝。独龙族从不认为亡魂就是鬼。亡魂存在的年限同亡人生前的寿命一般长,年限一到,亡魂逐化作蝴蝶飞向人间。蝴蝶的生命短暂,蝴蝶死了,对于该亡人来说就不存在任何的灵魂了,所以独龙族没有灵魂不灭或灵魂投胎转世的传说和观念,在他们的宗教活动中,没有祭祀祖灵和祖先崇拜的仪式,这是独龙族灵魂观念和宗教信仰方面的独特之处,和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相比是很不相同。〔2 〕如果我们不加解释地用汉族于发达的封建社会里形成的一套观念和术语来表述后进民族的事物,特别是曾经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宗教信仰的观念活动,则我们的描述性研究,不一定就是该民族自身的观念,而同实际情形大相径庭。另一方面,我们在如实地、准确地反映出各民族宗教信仰中的各种观念的同时,也应该科学地鉴别有关术语的内涵,审慎地使用它们。我认为至少首先应对精灵、鬼、神这三个被运用得最多最广的术语,指出它们之间的本质特征和差别是必要的。唯此,拟作一个大体上的探讨,以求教于识者。
“精灵”:是信奉原始宗教的各民族当中最普遍、最盛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更是原始宗教研究中最常见的一个术语。精灵是灵魂观念的具体延伸。一般地讲,精灵大都是指世间存在着的各类事物的灵魂,属于“万物有灵”或“泛灵论”的范畴,这些事物可以是有生命的,也可以是无生命的。须注意的是原始宗教的信奉者所说的某某精灵,常是十分具体地指某个单一事物的灵魂而言,或者是某类事物的单个灵魂。原始民族的精灵观念多具备物质的属性,少有甚或没有抽象概括的纯精神因素,因为处在原始社会里的人对客观事物的直觉性联想是其思维的一大特点,表现在精灵观念上亦颇突出。至于精灵的属性,原始民族多是理解成某类事物的个别的具体的性能,而不一定是这类事物的整体的抽象的性能。比如山精灵、水精灵或树精灵等,他们总习惯指的是某座山、某片水或某棵树的精灵。云南布朗山地区的布朗族认为,山林中有一种树的精灵叫“色家枯”,进山伐木者若闯着了它就会生病,须请巫师占卜,断明是碰上了那一棵树的精灵,遂携病人衣物和祭品向这株树的精灵作请罪的祭祀,病人可望禳解康复。如果祭祀后患者仍不见好转,则认为非该树精灵作崇,须再卜,直到找准作崇的那棵树的精灵为止。而精灵崇人,被认为是崇其健康的灵魂。所以精灵这个概念,常是指世间存在着的万物的灵魂,是那些信奉万物有灵为主的民族或人群普遍的也是主要的崇拜对象。至于精灵的各种名称、来源、传说、形象、居处、属性、作用和祭祀中的特殊方式等,属于原始信仰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需要我们用心探知的。如果把精灵称作是鬼,这就混淆了这两个术语的概念,因为鬼这一术语,有自己的内涵。
“鬼”:这个字在汉语言文字中是很古老的。有些意见认为,鬼字的出现比神字要早。甲骨文和金文中有不少鬼字。有人认为甲骨文鬼字的某些写法像是在死人的脸上盖着件东西。卜辞中也曾将鬼字作为一个方位来称呼不同族群的所在地域,如“鬼方”等。对鬼字的释文,《礼·祭仪》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说文》:“人所归为鬼。”《易·系辞上》郑玄注释:“精气谓之神,游魂谓之鬼。”可见在汉族的观念中,鬼常是和死人联系在一起的,许多民族也持此观念。鬼作为一种亡魂,经常连用,“鬼魂”被视为可以脱离其物质的躯体而单独存在,即人死其灵魂尚在,死人的亡魂多被说成是鬼,鬼有自己的性能和生活方式,并对活人产生多种影响。汉族具有发达且复杂的鬼的系统观念,更具有完备的祖先崇拜的系列仪式。《辞源》对鬼的释文有二,“迷信称人死魂灵为鬼”,这是比较符合该词本意的,又说鬼是“指万物的精灵”,如是作为一个术语,这似乎又混淆了鬼与精灵的本质差异。因为鬼一般总是指死者的亡魂,精灵则多系指除了人之外的万物的灵魂而言。实际上在许多民族中,对死者的亡魂(有时不一定是鬼)有专门的称谓,而对万物的灵魂(多为活魂、生魂之类)则另有称谓,二者的称谓区分得较为清楚,在其观念上和使用时并不混淆,只是在将它们译成汉语言文字时,找不到相应的词,往往干脆用鬼字表示,如独龙族指精灵称“卜郎”,傈僳族指精灵称“尼”,但我们曾误认为是鬼,一律用“鬼”字来取代它们,我想,这是造成这类术语不断混淆的主要原因。再者,鬼这个词在人们的心目中多有贬意,而精灵一词却少有贬意。但是,在灵魂观念的作用下,精灵和鬼这两个词又有相通、相似之处,它们主要的都是指灵魂而言,是灵魂观念下的产物,都属于看不见、模不着的虚幻之物,皆被说成能对人世间的事物施加各种坏的或好的影响,故而往往不加区别地使用这两个词语,很少深究它们的基本差异。至于所谓的精怪、仙魔和妖孽等,一般多是在精灵和鬼魂观念的基础上演伸出来的。有人曾将它们列为“鬼的旁系”(张劲松:《中国鬼信仰》)。
“神”:汉字神是殷周时期出现于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说文》:“申,神也”,“申,雷也”。于省吾在《寿县蔡墓铜器铭文考释》中认为,申字“本象电光回曲闪烁之形,即‘电’之初文。”又说:“古人见电光闪烁于天,认为神所显示,故金文又以‘申’为神。”清人桂馥在《说文解字议证》中说:“申、神相音近”,并引《风俗通》:“神者,申也”。汉字“神”无论在形、音、意上都表示同天际雷电的“申”字有密切关联,而神的观念和信仰,可能是从雷电这种自然现象中形成的。
在汉族的传统信仰中,存在着十分发达的鬼的系统和神的系统,这两个系统反映在道教和佛教的民间信仰活动中,比较清楚,鬼和神这两个词在上述各自的宗教经典里,也区分明确。鬼和神两个词在许多民族民间信仰中的传统使用方面,有一种现象颇值得研究,在中国长江以北特别是黄河以北地区,对于所崇拜的对象,多数较为习惯地称呼为“神”,而在长江以南和秦岭以南地区,对于所崇拜的对象,多数较为习惯地称呼为“鬼”。在许多民族的传统观念里,神总被视为比鬼具备更为强大、更为积极的力量或传统道德因素,而且在时空的跨度上,神似乎具有更广泛和更持久的作用。各民族的神话常描述了这样的情节,即神与鬼(魔)相斗争,总是以神大获全胜而告终。此外,鬼通常被认为居于地面或地下,而神则多来自于天际,在广垠的天空中驾云乘风,自由驰骋往来。
神的观念最初可能形成于天际,天际的神很可能是人类崇拜的最早的神灵。神的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扩张的概念。当这个独特的观念慢慢地从天上移向地面,根据一定的条件蔓延和渗透时,就将原先被崇拜的精灵、鬼魂一类逐步地予以转化、改造成为地上的神灵,如山神、水神、火神或草神等等,及至后来,神的观念由自然界伸向人的本身。“萨满教”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白族的“本主”信仰亦然。在神的观念和信仰由天及地的过程中,有一个值得考虑的现象,就是对山的崇拜。在世界许多山地民族中间,比较普通的一种看法是对高耸入云的山峰视为天的一部分,把与天际相连的山巅当作神灵来崇拜和祭祀,故而“山神”有可能是地面上众多精灵当中较早升华为神的一种。据上述分析,我认为神的观念和“万物有灵”的观念不是同一个观念系统,二者是有明显差别的。万物有灵观念主要是精灵的观念,不是鬼的观念,更不是神的观念,而神的观念主要是始于天的观念,或者天神的观念系统,甚至是具有创世和原始的道德伦理力量的“原始至上神”(Primitive supreme being)的观念。〔3〕
综上所言,在原始宗教的调查研究中,我们亟需要充分地注意吸收前人和今人研究的优良成果,逐步建立起一套适用于中国原始宗教研究的较严密系统的、概念精确界说清楚的术语,以提供一种科学的参照系统的叙述单位,利于操作,俾使调查研究者能够将观察了解和思考到的现象、事实和问题,作出较为精当规范的描述和论述,这无疑对整体提高我国原始宗教调查研究的水准是十分必要的。当然,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E ·利奇说过:“要把文化事实区别为能用术语加以精确叙述的基本单位并非易事。”〔4 〕这是有待于同仁们进一步作不懈的努力的。
三
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迅猛推进,一些于50年代刚刚走出漫长的原始社会的边疆民族,其原始宗教的信仰活动都处在快速的消亡当中。这是必然的。但是,原始宗教作为一种民族的传统文化观念,一种原始的哲学思想或宇宙观,仍然比较牢固地扎根在旧有的生活方式的土壤里,起着不容忽视的潜在影响。
现今,从外部世界输入的现代化的种种观念,不可避免地要同这些民族旧有的传统观念发生对立和冲突,其中原始宗教的观念往往是首当其冲。每提及原始宗教,一般总认为是十足的迷信、稚昧和荒诞。如果我们对原始宗教中的观念细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的有些观念与行为在客观上包涵有某种积极的方面或合理的因素,亟待用心发掘,并作出审慎的分析。
在中国深厚的本土文化之中,最见其长的是被称为“东方文化的哲学精髓”(季羡林)——“天人合一”的思想,人们常用它来指导和规范世事或行为。如果从宗教观念的角度上看“天人合一”,即万物、人类及其文化是大自然界神灵的恩赐,自然界被视为是超自然力的、人格化的、神性与万能的、有感知有意志的东西,人类只有拜倒在它的脚下,通过各种宗教仪式的崇拜活动和立下众多的人为禁忌,顺乎其意志,才得以生存繁衍下来。原始宗教中的一些观念与活动,证实了这一点。
信奉“萨满教”(原始宗教的一大类型)的鄂伦春族猎民,从不猎杀正在交配中的野兽,认为她们在办好事;一些老人也禁猎怀孕中的母兽,否则被以为会触犯山神“白那恰”,于狩猎不利。往昔他们世代游猎在东北大小兴安岭的原始密林里,森林是他们唯一能赖以生存的地方。他们爱护森林的观念要比其他民族尤为突出。除了不滥砍乱伐外,对于在林区用火,有许多宗教上的禁忌,破坏这些禁忌,就得罪了火神“欧透博如坎”,永远得不到火。例如:平素燃火,严禁用迸炸出火星的木柴;睡觉前必将火堆附近的木柴堆拾整齐,绝不任意丢弃;每当迁移宿营地,首要工作是将各处火堆中的余火彻底熄灭,方才离去。云南的独龙族也有类似做法。正因为如此,50年代以来,鄂伦春族出色地执行了国家交给他们的护林防火的重任。云南边疆地区具有原始宗教观念的民族,出于对神灵的企佑,从不在村落居地附近砍伐林木或破坏水土,几乎每一处聚落地周围的林木和水源都很畅茂,对于不具备这类观念和行为的村寨聚落,周围大片光秃,水土流失严重,每每形成明显的反差。凡此,都可以视为是“天人合一”思想通过原始宗教或其它宗教的观念活动的一种表现。如果我们拨开上述宗教观念中的神秘迷雾和宿命论的观点,就可以窥见其中合理的内核,即是: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和文化是不断适应客观世界的结果,人类和自然界应该“整合”融通成一体,不要把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当作人类生存发展的对立面,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敌对的关系,应是和谐相处的。我们既然向大自然不断索取所需要的一切,那么,人类就必须充分地热爱它、保护它,尊重并顺应自然界的规律,不要干出违反自然规律的蠢事来。
“天人合一”的思想,本乎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具有的一种传统观念,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于客观上都具有不容否定的价值。今天的世界,人口急速猛增,人类生存的空间和环境由于长期过度地、无序地向自然界作掠夺性的索取而变得愈发的满目疮痍和危机四伏了,人类已经落入难以摆脱大自然无情惩罚的困境。唯此,“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格外地显示出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了。我们对原始宗教的功能于这方面的发掘研究还很不够,还未能比较全面系统和客观地总结出内中的一套哲理来。当然,原始宗教于文化上的积极因素并不止于“天人合一”这类思想观念。至少我们在具体评估现代化事业和传统观念相碰撞一类的问题时,不能无视原始宗教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反映出来的合理性一面。我们的研究就是要充分挖掘出我们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的那部分,力图用来为现代化事业服务。
〔1〕参见B·莫利斯著、周国黎译:《宗教人类学》,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273、161~172页。
〔2〕蔡家麒:《独龙族社会历史综合考察报告》, 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印《民族调查研究》专刊第一集,1983年,第74~75页。
〔3〕关于“原始至上神”问题,本人已另有专文论述。
〔4〕E·利奇著、周庆明译:《人类学中的比较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民族学译文集》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1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