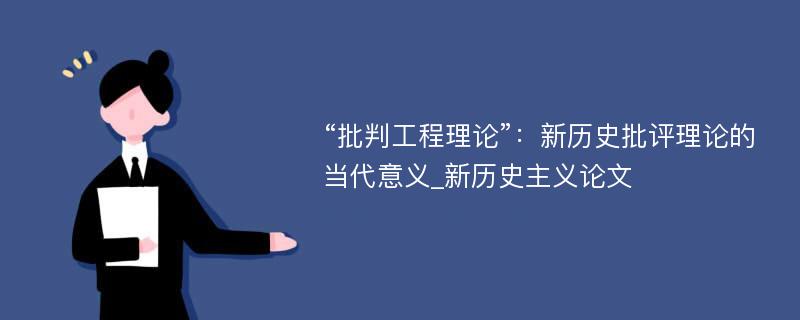
“批评工程论”——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的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主义论文,批评论文,当代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文学批评实践都不免要预设一个关于文学批评的基本观念(尽管并非总是意识到这一点),“批评为何?”以及“批评何为?”的问题恰恰是文学批评应该首先澄清的理论命题。对此缺乏反思而导致的后果是,文学批评自古以来都被想当然地看成文学事业从属的、次要的附加部分,寄生于作品分析,而不具有自己的独立价值;同时还设定,文学批评阐发的是关于作品的“客观知识”,是一些不受质询的、具有普遍性的一般言说。20世纪后半叶以降,文学事业的发展基本打消了这种观念。文学的聚光灯从此不再专注于文学作品而是追逐着各种竞相登场并占据前台的理论批评学说,读者及读者的阅读批评成了文学活动的真正主角,这造成了阅读统驭创作、批评理论代替作品分析的文艺现实。不但文学批评多于文学作品创作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且关于某种批评的批评多于该批评自身的批评实践的情况也并不鲜见。人们意识到,理论批评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批评家才是“知识的开拓者和文化传统的铸造者”,“批评可以讲话,而所有的艺术都是沉默的”(注: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理论”是不可回避的,即使那些拒斥理论的人,“不过是处在较为陈旧的理论的掌握之中”(注: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Preface,Basil Blackwell,1985.),“其实也在采用某一种理论”(注: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3页,三联书店,1988。)。这使得文学批评者再也不能以作品分析为由而拒绝理论批评及对理论批评自身的反思,而必须对自己在批评中的理论立场和所充当的角色进行反省;即使是从事单纯的作品分析的实证批评,也必须对其批评的功能做出重新阐释。
这正是当代“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的一般特点。人们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特征和价值,虽也涉及对文本的哲学思考和对批评本身的某些反思,但这种反思仍然不会脱离文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进行。而批评理论“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由于批评可以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文本,所以批评理论不限于文学,而是一个新的跨学科的领域。”(注:詹姆逊:《文化转向》“总序”,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按照卡勒的总结,这种当代理论也是“分析的话语”,是“对常识的批评”,“具有反思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注: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1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这种批评大致相当于托多罗夫所说的“对话批评”,它“不是谈论作品而是面对作品谈,或者说,与作品一起谈,它拒绝排除两个对立声音中的任何一个。”(注: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175-176页,三联书店,1988。)这种批评在面对作品时,不是亦步亦趋地随着作品节拍“跳舞”并因而“沉醉”于作品之中,而是调整阅读步调,改“快板”(allegro)为“慢板”(lento),变“随舞”为“慢步”,走走停停、左顾右盼、怀疑质询,防止作品将任何现成的东西塞给我们,关注作品以何种方式开启了一个世界而非作品已然开启的世界。(注:J.Hillis Miller,On Literature,p.122,Routledge,2002.)这种批评阅读不是单向涉入对象,而是突然“反身自问”——批评的历史性依据是什么?批评在何种立场上言说?批评与它处身其中的文化机制是一种什么关系?
批评理论的兴起,是后工业社会知识分子将对社会文化的批判审视态度扩展到“批评”自身而出现的现象;也是人们对“历史性”的思考进一步深化而意识到批评自身的“历史性”并对之进行盘诘的结果。换言之,批评理论追求对所有研究对象的“历史化”,而在历史化的两条不同路线——客体的路线和主体的路线,事物本身的历史根源和我们试图借以理解那些事物的概念和范畴的更加难以捉摸的历史性——中,它选择后者。它强调“我们对过去的阅读主要取决于有时所称的消费社会的结构”,即“形象或景象社会”。(注:詹姆逊:《政治无意识》,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因而它关注的焦点已不是作品的一般审美特点和形式构成,而是批评如何参与社会历史进程、如何在这个进程中发挥作用的问题。新历史主义历史诗学的批评观,即出现在这种批评理论背景上。当然,新历史主义批评也还关注作为批评对象的文本,但它在文本批评中总是对批评自身进行反思,即在批评中渗透了对批评自身的“自我意识”——“我们揭露、批判和树立对立面时所使用的方法往往都是采用对方的手段,因此有可能沦陷为自己所揭露的实践的牺牲品。”“我们批判和分析文化时所使用的方法和语言分享和参与该文化机制的运转。”(注:Aram Veeser,ed.,New Historicism,p.10,New York:Routledge,1989.)
新历史主义有关批评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的观点,集中体现在蒙特洛斯所使用的“批评工程”(critical project)概念上。“工程”一词使人想到社会建设中的铺路搭桥、修屋筑居,或是战场上的堡垒、战壕或掩体等攻防设施。这一概念与他们通常使用的“文本工程”(the project of text)和“意识形态工程”(the project of ideology)等概念是相通的,它们共同强调,批评不仅仅是表达个人兴趣爱好的一般言说,而且是实际的综合而复杂的社会文化工程。批评既是主流意识形态“巩固”自身权威的事业,也是被统治阶层和受压抑群体“颠覆”这种权威的事业;或者说,它是这些阶级之间“包容”与“反包容”的意识形态战场。(注:王一川:《后结构历史主义诗学》,《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批评是支配性意识形态的“表征”,它虽被竭力掩饰、“自然化”和“中性化”,但其意识形态性仍然从它所删除、排抑和凸显的东西上表露出来。批评也不只是对于文学文本单纯客观的形式分析,而是一项复杂浩大的社会文化工程。
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工程”观念主要体现在它对“批评语境”合法性的盘诘和对批评本身的“事件化”、对批评“划界”活动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反思和对批评参与社会能量流通过程的强调、以及对“历史重构”的再认识和对“横向超越”思维方式的追求上。
一、盘诘“批评语境”的合法性与批评的“事件化”
新历史主义批评工程理论,源于它对“批评的语境”的合法性的深刻质疑。传统的“历史诗学”在与各种形式主义对抗时,总是强调“语境”对文本的制约作用,而其语境则主要指“写作的语境”和“接受的语境”。前者强调的是作者意图、传记、社会文化、政治境遇及其意识形态与话语;后者注重的是文本如何被不同的社会组织、社会机构、读者大众所阅读、利用或滥用的问题。在20世纪,人们通过对“语境”的强调,将文学活动的诸要素,特别是作品和读者的“历史性”凸显出来,并分别基于这些要素建立了新型的批评理论,“读者的语境”也因此得到了强调。但批评者作为特殊读者,其自身的“历史性”却未能得到全面而系统的反思。这一点表现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变体接受理论之中。这些理论虽都强调解释者语境的“历史性”,但一般并不怀疑这个语境的合法性,而是将它归为源于传统的“前理解”或“期待视域”,进而将它“合法化”了。因此,相应的阅读理论,主张阅读者带着自己无法摆脱的“视域”进行共鸣性的、投入式和陶醉式的对话阅读,而并不强凋对这种视域作批判性审视,也不考虑“对话”是否会蜕变为权势者“独白”的问题。因此,“历史在伽达默尔那里并不是一个斗争、断裂和排斥的场所,而是一条‘连续之链’,一条永恒之流。”(注: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p.73,Oxford:Basil Btackwell,1985.)尽管哈贝马斯和利科尔等解释学家的“批判的解释学”强调了批判在解释中的重要性,但这种认识并未全面进入一般接受理论。
那么,一旦我们认识到批评者语境的历史具体性并对它进行批判性考察,情况又当如何呢?这会引起批评理论重心的转移,即从对“写作的语境”、“作品的语境”和“读者的语境”的一般性专注,转向对“批评的语境”的合法性的关注、质疑和盘诘。其实,批评的语境自身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批评者带着某种特定的期待视域去阅读,这并不是一桩不受质询的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是一个涉及批评者如何选择其批评立场,如何对待其阅读在当代批评场景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如何对待社会文化加于自身之上的历史性等等的问题。对批评语境自身合法性的怀疑批判会导致人们对“写作的语境”、“接受的语境”、“批评的语境”及其间关系的重新定位:写作的语境与接受的语境并不是由客观中立的档案材料堆集起来的,而是由各种力量“选择”和“涂抹”而成的,它们以何种面目出现以及具有哪些本质特征,这恰恰是与批评语境息息相关,甚至是受后者制约的。
因此,一般性地强调语境本身的重要性也还存在着问题。任何语境都不是现成既定的、单一同质的和自然而然的,而是复杂交叠、多重互渗和多声部的,因而是充满矛盾、断裂和疑问的。那么,人们是依据何种价值观念和思维背景来决定某一语境优先于其它语境的呢?这个价值观念和思维背景本身是否也是一个应该盘诘的对象呢?新历史主义就是带着这些疑问,“结合历史背景、理论方法、政治参与、作品分析,去解释作品与社会相互推动的过程。”(注:廖炳惠:《形式与意识形态》,211页,台北联经,1990。)这种阅渎解释通常是“怀疑的、谨慎的、祛魅的、批判的、甚至是逆向的。”(注:Gallagher,C.& Greenblatt,S.,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p.9,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自由人文主义者(liberal humanist)宣称,文学经典(包括批评经典)体现了人类经验和表达方式的全部本质。女权主义和妇女运动向这种观念发起了挑战,其学术研究探索了妇女的声音如何在各种文学戏剧作品及以前的作品评论中被压抑、被利用和被边缘化和“口技化”的过程。这种学术研究通过公开将批评实践与学术政策和社会政治实践领域联系起来的方式,揭开了自由人文主义理论宣言的神秘面纱——学术研究绝非远离或凌驾于利害关系、偏见成见和物质生存斗争之上的纯粹的客观知识,而是与知识分子职业的和社会的利害关系相互纠缠在一起。这种洞见及其所采用的一系列细致入微的批评方法都与新历史主义之间具有同气相求彼此发明的效用,它们共同强调:作为学术研究的文学批评,尽管以客观公正的面目表现出来,但它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并不是一个中性角色,而是以某种特殊方式参与了历史进程;批评及批评者的主体位置和具体语境是一个值得盘诘和质询的问题。
在盘诘批评语境的合法性的过程中,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不但将批评对象看成一个“事件”(event),而且将自己的批评活动本身作为“事件”来批评和反思,将其自身的批评活动“事件化”(eventualization)。“Event”相当于海德格尔哲学中的“Ereignis”,表示“缘构发生”,是一种居有且揭蔽的发生。(注:约翰逊:《海德格尔》,89页,中华书局,2002。)在他那里,真理、艺术作品都可以成为一个事件,按照伽达默尔的解释,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的存在不在于去成为一次体验,而在于通过自己特有的‘此在’使自己成为一个事件,一次冲撞,即一次根本改变习以为常和平淡麻木的冲撞”。因此作品“不仅仅是某一真理的敞明,它本身也就是一个事件”。(注:伽达默尔:《美的现实性》,107页,三联书店,1991。)这样event(事件)就是发生之中、时间之中的fact(事实),或者说是fact的动词形态。从视艺术作品为fact走向视艺术作品为event,也就将作品放置在时间和发生之中。(注:叶秀山:《美的哲学》,145页,东方出版社,1997。)这样一种“事件”观念被引申到各种知识领域,利科尔将其引入话语领域,认为“话语是作为事件而被给予的:当某人说话时某事发生了。”“事件”意味着,话语是一种说话的事件,它是瞬时和当下发生的。(注: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13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福柯将事件观念运用在“知识”上,认为“知识不是由某个普遍性的法则和价值标准所构成,而只是具有逆转偶然性的‘事件’”。(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1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看待一个事件不是凭它的内在意义和重要性,而是凭外在于它的,它与各种社会性制约力量的关系。事件的意义不是永恒的意义,它随时有可能遭到偶然性的逆转。在此基础上,新历史主义坚定地认为文学文本是一个事件,“小说是一种话语事件。它不反映历史;它就是历史”。(注:Claire Colebrook,New Literary Histories,p.38,Manchester University Oress,1997.)承认文本作为一个事件,这被认为是新历史主义最重要的成就。文本作为事件的观念让人们承认文本的暂时的具体性,也承认文本是历史变迁过程的组成部分,它本身可以构成历史变化。
以这种观念去解析文学批评活动,即是文学批评的“事件化”方法。这个概念首先指与“自明性”(理所当然、无可置疑)的决裂。“自明性”往往借助“永恒性”和“普遍性”的神话,掩盖事物的独特性和具体性。福柯发现,有总体普遍化癖好的历史学家常常热衷于寻找普遍的真理或绝对的知识,而实际上,任何所谓普遍绝对的知识或真理最初都只是作为一个“事件”而出现的,而事件又总是历史的、具体的。(注:The Foucault Effect:Studies in Govermental Rationality,p.76,Harvester Wheatsesf,1991.)就文学批评而言,事件化即意味着把有关批评的所谓普遍“理论”、“真理”还原为一个个特殊的“事件”,看成特定批评者在特定时期、出于特定需要与目的而从事的一个“事件”,因此它必然与许多具体条件存在内在关联。因此,任何批评理论的结论都不是必然的、无条件的、自明的与普遍的。通过“事件化”,就达到了对批评理论自身的“反思”,即研究者对于自己研究活动的自觉,达到一种对作为文化生产者的文学批评家的自我分析,达到对有关文学的“科学之所以可能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反思”。(注:布尔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4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总之,新历史主义对批评丧失自我意识保持着极高的警惕。研究者发现,“像许多处于后现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新历史主义者高度敏感,时时质疑和检验自己在批评运作中所起的作用与扮演的角色。在批评理论中进行自我反思,从理论上探讨自己的假定和论据,表明自己话语的立场,是新历史主义者作为批评团体的一种姿态。”(注: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需要补充的是,新历史主义者的敏感并非无缘无故,而源于他们对批评自身历史性的意识;也不能将之归入批评者个人的“敏感气质”,而应该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去理解。
二、重划“界线”与“社会能量流通”
批评作为工程是一个充满竞争的领域,是意识形态主导因素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场所。人们在阅读、讲授和修订文学经典的过程中,有一些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但人们对之或习焉不察、熟视无睹,或以为无关大局、小不足称。人们并未意识到自己是被某些文化体制因素授权做着批评工作,因而并未认识到自己必须选择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使用这些“权力”。但新历史主义则强调,“文化诗学”的研究和教学都深陷在更大的“学术政治学”(academic politics)之中,没有无关利害的学术团体,没有客观中正的学术立场,也没有不受质疑的批评语境。人们阅读什么以及如何阅读,都绝非与“政治”无关,也无法摆脱权力结构的影响;我们应清醒认识自己的历史性,意识到我们处在抚育我们又限制我们的权力知识之中;意识到我们批判和分析文化时所使用的方法和语言分享和参与该文化机制的运作,以免“沦陷为自己所揭露的实践的牺牲品(注:Aram Veeser,ed.,New Historicism,P.10,New York:Routledge,1989.)。蒙特洛斯指出,“任何一种集体的批评工程都应该牢记,社会实践也参与到批评工程试图分析的利益与观点的相互作用之中。所有学术文本都有选择地建构其文学—历史知识的对象,而且通常是在未经检验和反复无常的基础之上这样做的。”(注:Louis Montrose,New Historicism,see Greenblatt,S.& Gunn,G.ed.,Redrawing the Boundaries,p.415,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92.)这说明,批评家所面对的“对象”,恰恰是无法充分“对象化”的,因为对象本身已被批评活动所“建构”。这里所涉及的是广阔的“政治无意识”领域。批评工程的观念就是要将对无意识领域的“意识”贯彻到文学批评的每一个层面和环节。
从其显在层面看,文学批评所从事的事业就是“划界”和“重新划界”(redrawing boundaries),也就是将某些文本、作家、流派、风格、体裁、方法等划归文学或文学经典而将另外的排除出去,从而保证“文学”的完整性和纯洁性。这样就在“文学”与“非文学”之间做了分割并确立了界线。后来者对这个界线或赞同或反对,但一般认为这个界线关乎文学的“知识”,而并未意识到这是特定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共同作用而成的“权力知识”,因而将之视为“自然的”“客观真理”。这样也就未经批判地接受了文学与非文学之间存在界线的假设。布尔迪厄指出,“事实上,发生在文学或艺术场的斗争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对场的局限性的定义,即对斗争牛的合法参与性的定义。”(注: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比如,人们在争论文学问题时常常会说,“这根本不是文学”或“这不是诗”等等,这种做法就是对对象的合法参与性的定义,也是对“文学”或“诗”的边界的划定或重划。因此,划界和重新划界的过程,也正是将某些文本纳入界线之内或排除在界线之外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本质上是一项意识形态工程。
针对这一情况,新历史主义拈出了另一个假设以作为理解批评的出发点,威瑟教授将之概括为,“文学与非文学‘文本’之间没有界线,彼此不问断地流通往来。”(注:Aram Veeser,ed.,New Historicism,p.10,New York:Routledge,1989.)这个假设当然并不是要否认或抹杀历史上赫然存在着的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限,而是用来说明,他们对既往“界线”的合法性和自然性的怀疑恰恰是“合法的和自然的”,从而为他们的重新划界活动提供一个理论依据。新历史主义的这一认识显然与福柯有关“话语控制”的学说有关,主要与其“学科原则”的思想相联系:“任何学科的话语都不纯粹是由真理性陈述所组成……但一个陈述是否能被接纳入一个学科,却首先不看它是真陈述还是伪陈述,而是要看它符合不符合某些条件,这些条件比单纯的真理性条件要严格和复杂得多。”(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14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沿着这一思路,新历史主义的批评着力寻求文学“划界”过程中“复杂的”条件。
其实,一旦着手批评,就不免要进行划界和重新划界,但界线往往并非一目了然,而通常是隐而不彰、纷纭交错的,因而界线所涉及的范围是非常宽泛的。按照格林布拉特的理解,文学研究试图重划的界线涉及“从国家的、语言的、历史的、代际的、地理的界线到种族的、人种的、社会的、性别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宗教的界线。而且,文学研究还有许多并不明显但具有同样决定性的界线,它将阅读与写作、印刷文化与口述文化、经典性传统与异端传统、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区分开来。”(注:Greenblatt,S.& Gunn,G.ed.,Redrawing the Boundaries,P.4,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92.)这些或隐或显的界线都是文学研究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划定的,具有自身的历史相对性,因而并不是自然的和当然的,也不是一般的和“普适的”。因此,这些界线可以被跨越、混合、合并或瓦解,也可以被重订、构想、设计和置换。界线划定以及对既有界线的侵越是一项批评工程,它是文学批评始终从事的工作,新历史主义的批评观念强调了这一学术事实。
文学批评总是通过排斥打击某部分而包容吸纳其它部分,对既定界线进行修订和重划。新历史主义认为,对界线的破坏是在最深层的“喻说”(trope)层面发生的,也就是说,这种破坏是在一个先于批评的、潜在的语言结构深层发生的。但人们对这个层面所发生的一切通常浑然不觉,因而总是容易相信界线是在学科层面被跨越的,所以常常将“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与“批评划界”看成同一回事。这就是混淆了从同一界线的不同侧面来研究对象的问题与重新构想不同界线之间关系的问题。新历史主义是要重新构想不同界线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从同一界线的不同侧面来研究对象。因此,在新历史主义看来,界线是历史性地划定的,也应该在历史性中被重划;界线不是自然的,应该受到质询和商讨,而一般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则并不对学科之间界线的自然性或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国内有研究者以“‘跨学科研究’性”(注: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17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来泛论新历史主义的特点,就有可能造成对新历史主义的划界观念的肤浅理解。新历史主义的跨学科研究与一般所说的跨学科研究之间的区别,即在于前者不承认已有学科界线的合法性,或者说在进行跨学科研究时连同学科界线也一并质疑批判而不是认可放行。
界线问题的提出让人们意识到,文学并不是某种一劳永逸地“给出的”东西,而是某种建构和重建出来的过程和结果。不仅文学经典作品是在界线的徘徊不定和对界线的超越中塑造出来的,而且文学观念本身也处在不断的重新商讨过程中。因此文学研究必然或隐或显地对想象中的界线进行质询。旧历史主义(思辨历史诗学和大部分批判历史诗学)在描述文学语境时,大多采用“时代精神”(黑格尔)、“历史背景”(丹纳)以及“世界图景”(蒂利亚德)等概念,把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化为某种同质的、连贯的和稳定的文化“背景”或“图景”,认为非一致性、矛盾性和张力因素都是一些无力撼动这个和谐基础的东西而对之存而不论。这些假设在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前驱那里即已受到挑战。威廉斯在70年代就将文化划分为“残存的”、“主导的”和“新兴的”三个方面,认为不仅这三个方面之间的界线是动态的,而且基于不同方面的批评之间的界线也是不稳定的,因而由这种批评划出的界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注: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p.122,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而辛费尔德有关“faultlines”的理论则认为,批评常常以抹杀矛盾冲突的方式,将文化中的复杂关系表述成和谐一致的和统一连贯的,这是一项意识形态工程(the project of ideology);而文化唯物主义的批评就是要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这些久被忽视的方面。(注:Alan Sinfield,Faultlines:Cultural Materi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sident Reading,p.9,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也就是说,批评在文化中所划的界线是各种批评基于自身的历史性而做出的,这些界线在历史过程中必然会得到修订或重划。
批评在从事划界和重新划界工作时,它就同时勾画出文学批评自身的“旅行”(travel)轨迹,从中可以呈现出已往的文学批评话语、流派、观念和理论从此时向彼时、从一种情境向另一个情境、从一个领域向另一领域、从一种语言向另一语言的旅行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释放的“社会能量”(social energy)和社会能量在流通过程中所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过去的理论批评是这样,我们所从事的理论批评未尝不是这样。赛义德认为,“文化和知识生活经常从这种观念流通中得到养分,而且往往因此而得以维系。”(注: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1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换言之,我们作为当代批评家,也加入了类似的理论旅行而使批评得以延续。当批评家考察研究对象的流通过程时,也加入、推进或改变了这一流通进程。因此,有关批评对象之间界线的动态性的研究,同时也就成了对批评理论自身存在状态的反思。
新历史主义认为,在历史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有一种普遍的社会能量在往返流通,从具体的社会事件到笼统的社会现实都具有一种能量,它“具有产生、塑造和组织集体身心经验的力量”。(注:Stephen Greenblatt,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p.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文艺就是这种社会能量流通的一部分:一方面,社会能量通过编码进入文艺作品;另一方面,文艺作品又不断释放发挥着这种能量,对读者观众产生影响,进而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文艺既是社会能量的载体和流通场所,也是社会能量增殖的重要环节。社会能量在“流入”和“流出”文学作品的“流通”过程中实现其意识形态功能。流通中卷入了多种社会历史因素并引起了社会上各种利益、势力和观念之间的互动,因此,这种流通必然是各种社会历史因素之间的“协商”和“交换”。
这样,新历史主义批评就采取了一条与传统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同的比较方法:它并不像影响研究那样注重对“起源”的纵向追溯,而是更注重对“流通”的横向描述;它也不像平行研究那样注重比较对象之间的“相同性”,而是更重理论批评在旅行中所经历的不可避免的“变异”和“转化”。它考察各种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追问集体信念和经验如何形成,如何从一种媒介转移到其他媒介,如何凝结于可操作的审美形式以供人消费,等等。(注:Stephen Greenblatt,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P.5,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这种研究突出了能量流通中的“非连续性”和“断裂”,从而也加强了这种理论研究的自我反思力度。
总之,界线划定和重划是一项社会文化工程,是批评工程得以开展的一个基本手段,同时也是我们将历史和现实建构成一个意义世界的基本途径。蒙特洛斯说,“通过将‘文学’重建在不稳定的和论战性的词语和社会实践领域——通过重划文学研究的界线而后又超越这些界线,我们可以将人文学科表达为在知识性和社会性上于历史性的现在有意义的工作的场所。”(注:Greenblatt,S.& Gunn,G.ed.,Redrawing the Boundaries,p.145,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92.)也就是说,如果想让人文学科于我们当下的历史性存在有意义,就必须不断重新划分文学研究的界线;因而划界也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存在方式。
三、构设不同版本“历史”与“横向超越”
界线重划看似寻常,但它也与不同寻常的历史理解问题紧密关联。界线的摇摆甚至会营造出历史的另一副景观,另一个版本。可以说,批评划界活动在自觉不自觉地构造并体验着不同版本的“历史”。
文学批评总是处在与过去和当下的社会历史文化的互动关联之中,因此批评家要对这种关联网络的复杂性有清晰的意识。蒙特洛斯认为,任何一种集体的批评工程都应该牢记,“所有的学术文本都有选择地建构其文学—历史知识的对象,而且通常是在未经检验和反复无常的基础之上这样做的。对于任何真正新历史主义的工程不可或缺的是,必须认识并且承认,我们的分析必然是由我们自己的历史性、社会性和体制性地形成的一些优先考虑的问题所推动的,而且同时,我们所建构的过去是批评家的文本建构,而这些批评家也是历史性的主体。”(注:Greenblatt,S.& Gunn,G.ed.,Redrawing the Boundaries,p.145,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92.)即是说,“过去”尽管作为“知识对象”和“客观历史”出现,但它是身处“现在”的人们选择和建构的结果;反过来,“现在”亦然。这就要求文学批评要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在“话语讲述的时代”与“讲述话语的时代”之间展开一种双向辩证对话,从中把握历史和历史意义。我们对过去的文本的理解和表述,既是疏离的过程,也是占为己有的过程。过去的话语与我们有关过去的话语是互为条件的。诚如怀特所言,“‘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某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注:Hayden White,Figural Realism,p.1,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因此,我们有必要既将过去“历史化”,也将现在“历史化”,同时还要将过去与现在相互建构的辩证关系“历史化”。这样一种批评实践既构成了“文化诗学”与“文化政治学”之间的对话。这也正如中国古人所说,“相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从划界的社会文化工程功能看,文学理沦批评的写作与“历史书写”(historical writing)之间并无明晰的界线,其间的学科界线也是人为划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文学理论批评像新历史主义一样主要涉及历史题材时,它就与历史书写在做着大致相同的工作,二者之间就“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关系”。(注:海登·怀特:《“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见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4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因此,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功能就可以参照“历史书写”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得以说明。举例来说,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的记载,孔子“删《诗》”与“作《春秋》”,前者“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后者则“约其文辞”,使“乱臣贼子惧”。这两种写作都是当时批评工程的一部分,在社会文化功能上可以互相参证和阐发。巴尔特认为,“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注:巴尔特:《符号学原理》,59页,三联书店,1988。)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亦然。历史写作突出的意识形态性,有助于人们对文学批评的社会文化工程特点的把握。
文学理论批评及批评的每次划界,都不只是对既定界线的修订或侵越,它实质上是在建构一个不同版本的“历史”,让某些处于边缘或被压抑的“历史”浮出历史地表,让那些久已湮没的历史档案发出声音,从而营构出各种“小写历史”(histories),使它们与其它“历史”进行对话和竞争;同时,它也是在解构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必然的、连续发展的、唯一真实的“大写历史”(History),阻断大写历史的连续性之流,“把一个特定的时代从连续统一的历史过程中爆破出来,把一个特定的人的生平事迹从一个时代中爆破出来,把一件特定的事情从他的整个生平事迹中爆破出来。”(注:本雅明:《本雅明文选》,4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这种被“爆破”出来的东西可组成另一版本的“历史”,让人们意识到“历史”的相对性和可逆转性。蒙特洛斯强调,“在文学研究中,新历史文化批评的工程,就是分析具体文化话语实践,包括那些文化经典得以构成和重新构成的话语实践。通过这种话语手段,不同版本的真实和历史得到体验、扩展和再生产,而且通过这种话语手段,不同版本的真实和历史也可以得到征用、竞争和转换。”(注:Greenblatt,S.& Gunn,G.ed.,Redrawing the Boundaries,p.415,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92.)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工程,并不是以某种客观中正的面目去呈现“唯一的”真实或历史,而是要揭示不同版本的历史或真实形成并被利用的过程,而这种揭示活动本身也参与到文化话语的流通之中。
自古以来,理论批评总是承诺其“超越价值”。新历史主义有关批评的承诺也不例外。但是,这种源源不断地构想而出的另一版本“历史”,能否满足人们的期待视野呢?很显然这种理论无意于所谓终极真理,但它也不是没有追求“超越”,只是它采用不同的超越途径,即“横向超越”(horizontal transcendence)而非“纵向超越”(vertical transcendence)。后者指“西方传统的概念哲学所采用的由感性中的东西到理解中的东西的追问”,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追问方式,最终导致从表面的直接的感性存在超越到非时间性的永恒普遍概念中去。而“横向超越”是强调任何当前在场的东西都是同其背后未出场的天地万物融合为一、息息相通的,从前者超越到后者不是超越到抽象的概念王国,而是超越到同样现实的事物中去。(注:张世英:《哲学导论》,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这样的超越是“无底的”,因此它不追求终极的“历史”;这样的超越不求相同而求“相通”,不强调外在的认识而追求内在的体验,因此它强调与古人“对话”而“不舍己从人”或定于一尊地独白。在这里,批评对象、批评者自我批评过程本身,这一切都是“历史化”、“事件化”和“地方化”,是处于时间之中的具体历史过程。
总之,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工程论,在当代批评理论背景上对文学批评在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文化功能和政治意识形态功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对理解我国转型时期文学批评的功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它将批评过分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做法也是应该警惕的。
标签:新历史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