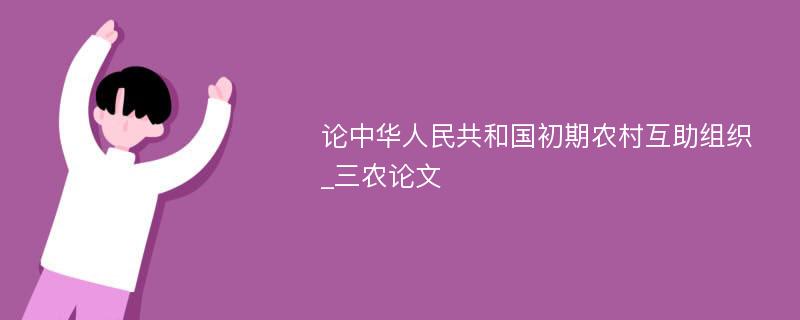
论建国初期的农村互助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助组论文,农村论文,建国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4)03-0054-10 新中国成立后,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广大农村,为解决劳力、耕畜及农具缺乏等困难,陆续推广建立互助组,以促进农业生产。中国农村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社会,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互助组要贯彻互助两利原则,需要对劳力、耕畜、农具的互助共用进行评工计分。确立合理的评工计分制对互助组的组成和巩固有着重要影响。以往相关研究只把互助组作为农业合作化的初级形式,作为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一部分来提及①,对互助组本身缺乏细致考察,有些问题尚未明确。如:互助组是如何组成的?有着怎样的规模?它又是怎样实现互助两利的?它到底是怎样的组织?对入组农户是否有益?对农业生产是否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存在哪些问题?等等。本文试图探究这些疑问,以便对建国初期的农村互助组有具体而清晰的认识,全面了解当时的农业政策与农村社会。 一、组织起来:互助组的组成与规模 中共自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时起,就开始号召组织变工队等互助组织,以解决农家生产中遇到的劳力、耕畜、农具缺乏等困难。因此,在老解放区,互助组并非新鲜事物。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农民渴望休养生息,发展生产。顺应这一要求,政府要求在农村继续组织起来的工作,并根据不同情况增加新的内容。提出“在农业生产恢复较差的地区,组织起来应着重克服劳力、畜力和农具缺乏的困难;在农业生产已恢复到战前水平或已超过战前水平的地区,应在组织起来的基础上着重改良技术,加强经济领导,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②。由此,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农村,作为组织起来的具体表现形式,农村互助组开始陆续建立推广,组织过程可谓披荆斩棘。 因为解放后分得土地的农民对互助合作顾虑重重,思想情况非常复杂。如江苏省宜兴县闸口乡北沙滩村,1951年3月该村劳动模范邓槐银响应政府号召,开会反复说明组织互助组的好处时,全村只有3人赞成,大多数人直摇头,村民赵云秀说:“一人一条心,十人十条心,互助组人多手杂,把我的牛用伤了怎么办?”王根宝说:“我有我的打算,不要互助”③。农民对互助合作最根本的思想问题是怕吃亏。如河北省大名四区小湖村村民,对参加互助组,劳力多的怕“白给别人帮工”,劳力少的怕“出工米不上算”,不愿参加;一部分老中农和富裕户这种思想更严重,他们说:“自干自吃,自由自在;够吃够穿,就是安乐神仙”。另外,有些农民怕参加互助组“合不来”,说“亲哥们还闹分家呢,张王李赵的咋能互助得好?”还有些人因为该村几年前曾用“大编组”的强制办法组织过互助组,怕这回互助起来闹不好又“散伙”,对互助合作政策抱怀疑态度④。各地反映,贫农是迫切要求互助的,但怕组织起来后,出卖劳动力不自由,怕做了活拿不到现钱,怕自己的活做得晚,怕大家有私心,把人家的活做坏,因而产量降低。中农的顾虑比贫农更多,怕贫农白使耕牛农具,或不爱护耕牛农具,出劲用,用坏了;怕人多合在一起活做不好,不如自己单干来得好;怕组织起来好处不多,反要向外找工钱。劳动力不强的农民则怕互助以后,拖不了,吃不消⑤。可见,农民对互助合作有各种各样的顾虑,这直接影响互助组的组成。 怎样解除农民的顾虑,打通思想,使农民自觉自愿地参加互助组,是中共在基层农村组织互助合作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村干和劳动模范在宣传发动方面费了不少心思。他们从新旧生活对比、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最头疼的家庭矛盾等问题入手,对村民反复劝说组织起来的好处。安徽省阜阳县口孜区的劳动模范焦天凤,为启发农民响应政府组织起来的号召,参加互助组,提出七想:“一想黄水滔天,二想逃荒要饭,三想有田难种,四想少吃没穿,五想地主万恶,六想妻离子散,七想过去妇女关在阎王殿,现在打断了铁锁链。”让大家对比过去的苦难,珍惜如今翻身得解放的新生活,响应政府号召组织起来。这种忆苦教育很奏效,焦天凤互助组在1951年春一度解散后又重新组织起来,到麦收时,参加互助组的户数由7户增加到11户⑥。河北大名四区小湖村宣传员根据不同对象,“对症下药”。该村农民仝福,原来是个保守自私思想很严重的富裕户,怕互助起来劳力多吃亏。宣传员仝聪就首先给他解说自愿互利,拿计工清工的具体办法帮助他算细账,拿本村仝俊峰互助组和他家对比,拿张希顺互助组过富、使新式农具等事实说明组织起来的好处,讲将来使用机器种地和社会远景等,这样,仝福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感动地说:“互助就是比单干强百倍啊!”自愿参加了仝万亮互助组。宣传员李栋、李德才动员富裕中农李三元时,先帮助他家开家庭会,解决了家庭不和的问题,李三元很受感动;他俩就顺势说服他参加了互助组,并帮助他家把参加互助组保证增产添到爱国公约里去。该村组织起来的宣传工作,获得了显著成绩。全村原有常年互助组6个,到1952年已发展到21个(包括145户,666人),另有1个互助组转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包括16户,54口人),全村单干农民只剩2家,共6口人⑦。 陕西省兴平县自1951年春土改完成后,县领导大力领导生产工作,抽派70%的干部下乡,普遍成立乡、村生产机构;结合镇反、抗美援朝等运动,广泛深入宣传各项农业生产政策,打破群众对生产工作的顾虑,召开各种会议,教育干部,明确认识“组织起来是搞好生产”的关键。为取得有效领导经验,特选定了五个重点——两个乡、两个村、一个互助组,指定专人负责。并在新政重点乡架设电话,开始在重点乡村组织起互助变工组,具体帮助、订立生产计划,建立民主管理、记工算账等制度,订报学习,解决生产变工上的困难。张明亮互助组就是这样在县领导亲自扶持培养下,壮大起来的⑧。通过重点领导,树立核心,组织爱国生产竞赛,互助组得到迅速发展。1950年全县只有209个组,1951年增加到1854组,参加劳动力占全县总劳动力的23%⑨。 从陕西兴平县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共基层乡村干部推动互助合作,在重视宣传工作的同时,注重党员发挥带头作用,树立典型,推动一般。这很具有普遍性。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农村工作委员会调查组对山东莒县吕家庄调查,该村组织互助组,也是首先以中共村支部为核心,在党内外充分酝酿。劳动模范吕鸿宾主动与吕安吉进行互助,做出样子,在农民中扩大宣传。因而,全村32户在自愿的原则下,先后建立了4个变工组,实行人牛换工,解决了生产困难,做到耕种及时⑩。江苏宜兴县闸口乡北沙滩村劳动模范邓槐银在村里组织互助组,劝说大家无效时,就决定先把容易打通思想的几家组织起来,做出榜样,使单干户看到互助组做活又快又好,并能认真记工算账,就陆续要求参加互助组了。对少数不想入组的,也不强求,不孤立,当其生产遇到困难时,互助组又派人力、牛工相助。亲自体验到互助的好处后,比较顽固的单干户也要求参加互助组,到1951年秋,互助组已扩大至35家(11)。该村共有40余户,可见近九成的农户加入了互助组。 组织参观模范互助组与互助模范报告经验,是新区典型推动一般的成功方法。如陕西长安杜曲区请王蟒村村长孟纪东在全体区、乡干部会议上介绍经验,各乡、村又派代表到该村参观学习,因此全区很快发展了195个互助组,并有不少的临时变工组提高为长期定型组。河南鲁山马楼乡劳动模范苏殿选到外村报告互助经验,带动全乡组织起102个互助组(12)。 从生产需要出发,从群众旧有互助基础做起,组织互助,是新区群众比较乐于接受的方法。中国农村原有的互助习惯普遍而且多样,同时与生产需要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组织互助的有利条件。苏南松江专区就是从解决群众当前生产困难着手,大量恢复旧有的修渠、筑圩、罱河泥等互助组织,然后在春耕中总结前段优点和成绩,指出不合理部分,加以改进,并调整领导,选出组长作为骨干,进一步组织起来。有的地方是运用群众原有的“合犋”、“和伙”等组织扩大成员,改进互助办法,或在农民共同使用政府贷放的耕牛和大农具,解决生产困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13)。由于各地条件不同,在组织互助组时,提出了不同的互助内容。如河南、皖北、苏北沿海各专区、县就组织治淮与农业生产结合的互助;在特产区组织特产品生产与加工的互助,如河南许昌专区以烟炕为中心的烤烟组,江浙一带的蚕业小组、茶叶生产小组等;在有水利灌溉条件地区,则提倡互助打井、开渠,合购水车等(14)。 发起挑战竞赛、评比等活动,也被一些地方运用到互助组的宣传推广中。如陕西兴平县,1951年春模范互助组张明亮、许敬章等宣布响应山西省全国劳模李顺达互助组的挑战,并以此向全县互助组挑战,开始在全县掀起爱国生产热潮。春耕生产结束之后,张明亮等47个互助组又发起向全国小麦产区提出夏收夏选爱国挑战竞赛,立即获得全国各地8300多个互助组热烈应战;在全县范围内有990多个互助组、4个乡、83个村起来参加竞赛,掀起了全县区与区、乡与乡、村与村、组与组的连环竞赛,有力地提高了群众生产劲头和生产情绪,推动了全县互助组数量和质量的增多与提高。为了更多地发展和巩固互助组,在张明亮等互助组发起夏收夏选、保棉种麦、冬季生产等挑战之后,曾先后召开全县麦收夏选,秋收秋选及冬季生产等三次评比大会,在比组织领导、比产量、比收成、比爱国表现等热烈讨论中,具体教育了互助组,提出改进与提高的办法,再推广到所有互助组中去,使已经组织起来的互助组明确认识组织起来的好处,使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积极组织起来,发展生产(15)。 互助组的发展步骤一般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点到面,由老组带新组,由克服生产困难到提高生产。如湖北黄冈浠水县的河东乡、望城乡,蓟春县的新铺乡,参加互助组的户数到1952年已发展到全乡户数一半左右,一般老互助组的周围,都新成立了三五个互助组(16)。由于各地认真贯彻中央“组织起来”的政策,互助组很快在农村大量组成,但并不普遍,程度不一,无论老区或新区都是如此。如黑龙江富裕、克山等县组织起来的户数达百分之95%左右,而洮南、瞻榆、泰安等县仅组织30%左右的农户;互助基础较好的山西老区,有的村(如左权七里店)还没有一个互助组;河南许昌专区较好的县区组织起来的户数达70~80%,但有些区村还是空白的;而不少的新区互助组织还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17)。1952年年初,就连山西长治革命老区,“互助组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已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18)。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1952年农业生产的决定颁布后,互助组的发展速度开始加快。决定要求:在老解放区今明两年把农村中的80%或90%的劳动力组织起来,新解放区要争取3年左右完成这一任务。并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应普遍大量发展简单的、季节性的劳动互助组;在互助有基础的地区应推广常年定型的、农副业结合的互助组;在群众互助经验丰富而又有较强骨干的地区,应当有领导、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为此,推广召开互助组代表会议和举办互助组训练班,扩大宣传,培养骨干。1952年,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区、县普遍地召开了互助组代表会或举办互助组骨干训练班。据山西、辽西、湖南、宁夏四省统计,1951年冬和1952年春与会受训的互助组长和积极分子达50余万名。河北定县专区所属各县1952年春连续召开互助组代表会议后,全区组织起来的劳力迅速达到70%以上。另外,政府出台了针对互助合作组织的经济和技术上的融资优惠扶持等举措。1952年国家发放农业贷款3万余亿元,以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要贷放对象,新式农具、优良品种、农用药械等也以互助合作组织为主要推广对象。如华北区推广二万八千套新式步犁,绝大部分是贷给或卖给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国营农场对互助组、生产合作社的技术帮助逐渐在加强,与组、社订立“技术合同”,有些地区的国家银行和互助组、生产合作社开始订立“信贷合同”。各地供销合作社也和互助组、生产合作社订立“结合合同”,密切联系,这些对帮助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作用很大(20)。 1952年上半年,组织起来的劳动力,西北区为60%,比1951年增加一倍以上;华北区65%,比1951年增加20%;华东区33%,比1951年增加60%;内蒙古达70%;东北区组织起来的农户达80%以上。据不完全统计,中南区组织互助组100万个,西南区55万个,各占该区总农户数18%以上。总计全国共有互助组600余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近4000个,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3500余万个,约占全国总农户40%左右。全国常年互助组占互助组织的比率,在1951年占10%,1952年增加到20%(21)。 随着全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截至1953年11月份,全国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约有4790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43%,比1952年增加了20%以上。参加常年互助组的农户,约占组织起来农户总数的24%强,比1952年增加了21%强。其他各种临时性互助组占组织起来的农户总数的70%以上。按地区分别来看,组织起来的农户在各大行政区占农户总数的比例是:东北区75%,华北区50%多,华东区50%左右,西北区45%,中南区30%,西南区40%。在各大行政区组织起来的农户中,参加常年互助组的户数比例是:东北区33%(加上三大季组即占70%),华北区33%,华东区35%强,西北区10%,中南区14%,西南区10%。其他都为临时互助组与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有了质的提高,突出地表现在有名无实的形式主义的互助组(即名义上是互助而实际上是单干的组)已大大减少,常年互助组大大增加。华北、西北、西南等地区的互助组,在1952年中,估计约有10~20%是有名无实的,1953年这种互助组就大大减少了(22)。 总体看来,建国初期农村组织起来的工作,只是在局部先进地区和部分先进村庄达到相当的发展,在一般地区还甚为薄弱。以组织起来的农户比例居中的华北为例,华北农村互助组发展不普遍不平衡的状况并无多大改变。截至1953年11月,全区组织起来的农户(包括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内),山西、河北达全体农户的45%左右。蒙绥东部和陕坝专区达70%左右,绥东在30%左右。河北、山西以专区计,一般发展较平衡,只山西长治专区较突出,达75%;但专区内县与县、村与村之间悬殊。山西的平顺、武乡、左权、榆社等县组织起来的农户在80%以上;怀仁、忻县、稷山等县只及30%;崞县、神池、代县只及15%,河北定县专区785个村中,组织起来的农户达到40%的,占半数村庄;达到60%和仅在20%以下的村,各占25%。此外,各地都还有些空白村庄。如山西阳曲、崞县、神池三县,发现有133个自然村还没有互助组。在组织起来的农户中,参加常年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般地区除先进村庄外,均不到三分之一,互助合作基础最好的长治专区只达一半,大多数仍是临时的季节性互助组。因此,组织起来后,互助组碰到的主要问题是时聚时散,愈忙愈散,苦于不能常年坚持(23)。 二、互助两利:互助组的运行与评工算账制 中共组织互助组的原则是自愿两利,在互助组的具体运行过程中,能否贯彻互利政策,在组员之间解决好耕作的先后次序,劳力强弱、技术高低和做活多少好坏的计算及耕畜农具的使用与报酬问题,则关系到能否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和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直接影响到互助组的发展与巩固。以上问题是每个互助组都存在的必须解决的问题,是贯彻互利的重要环节(24)。 耕作次序的先后,是临时性季节互助组和常年组都会遇到的问题。华北各地对收割、下种、锄苗等耕作事项,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解决:(1)按生产需要采取利益均沾的原则。如锄苗先锄苗大草多的地,后锄苗小草少的地,并让每户都能享受先锄,自报公议,民主排队。(2)适当分散使用劳力,并充分发挥辅助劳力的力量。(3)对某些由于耕作先后引起用工多少的悬殊,如抗旱担水点种,中间落了雨,种同样多同样好的地,先担水点种的用工多,后趁墒播种的用工少,一工换一工,谁都不愿先种,可采用先种和后种拉平的办法(25)。 常年互助组内的评工算账等问题,解决起来则要复杂棘手得多。 互助组内劳动力的交换使用首当其冲。中国是小农经济占主体的国家,各地素有“换工”或“伴工”传统,福建省的互助组就部分利用了传统的“换工”形式。据调查,该省互助生产中的劳动力交换,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工换工”。就是不分劳力强弱、技术高低及实际效率如何,只要做一天,就算一天工,彼此以工抵工。这种办法是被大部分临时性季节性的互助组和一些刚成立的常年互助组所普遍采用的,实行起来简单、方便,但也有缺点。二是“按劳定分”。按照劳动强度、技术高低、劳动性质采用自报公议的办法,民主评定每个组员的劳动工分,农忙时劳动力的调配也都由大家开会决定。这种“按劳定分”的办法是一部分常年互助组及少数临时性季节性互助组采用的。它的优点是简单易行,较公平合理,比第一种办法更进了一步。它的缺点是每个劳动力所定的分都是死的,这就给发挥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和提高农业技术一个限制,认为反正“分”已经定好,做好做坏都是这些“分”,因而不能有效调动农民劳动积极性和提高劳动效率。三是一些较好的常年互助组在“按劳定分”的基础上实行的“死分活评”。这种办法,除按劳动力强弱、技术高低、劳动性质评出固定的工分外,每天再按各人实际表现和劳动效率评议,适当增减工分。这种办法可以直接鼓励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避免偷懒。四是“按件论成计工”。它的特点,是不管男女老少,能做多少活儿就算多少工(活要规定一定的质量),这是接近“按件计资”制的较先进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比较精细复杂,一般基础较差的互助组不容易采用(26)。 根据劳动力的强弱等评工计分的“按劳定分”、“死分活评”等方法比较普遍,山东、江苏等省的互助组也较多地采用这种方法。山东莒县吕家庄在劳力评定方面,不论男女均按劳动效率评定“工分”,男劳力从3分、5分到12分;女劳力从3分到10分不等,每天开个短会,除检查与计划生产外,还找清当天工账,交清工牌。必要时召开组长会议,听取群众反映,解决问题。为保证劳动效率,并订出劳动纪律,迟到者自动退分(27)。江苏兴化县永丰区周家村刘长山领导的互助组,1949年春刚成立时,日工抵日工,没什么问题。转为常年互助组后,死工死记,时间长了,导致生产效率下降,甚至有做活快的觉得吃亏而退组。后改为按件计工,即按活计估工,按人评分,按分计账;超额加分,差额减分,真正做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样评工计分合理后,组员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已退组的又请求回到互助组(28)。 其次是对耕畜的评工计分。耕牛是中国农村普遍使用的畜力。在对牛工的评定上,福建省主要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按日计分”,另一种是“按亩计分”。前者是不管做多少活,一律按既定的工分算;工分的高低一般是根据牛的强弱事先评定,有的是1头牛做1天活顶2个人工,有的顶1个半人工,有的还不及1个半人工。“按亩计分”就是以牛所耕作的亩数多少评定分数。闽侯林淑英互助组用牛犁1亩田评5分,犁多多计,犁少少计。为解决缺耕畜农户的困难,还实行人牛换工,即:一般是按牛力的实际耕作效果,评出1天多少工分,折为人工多少(29)。 最后是农具的使用问题。农具缺乏一直是困扰旧中国农民生产的一大难题,新中国成立之初,这种状况仍然持续。互助组内农具公用成为必然要求。福建省的互助组里使用农具,一般小农具是私有自用自修,大农具有三种情况:一是公有农具,一般都是公买公用公修(有的把私人的大型农具作价归公),用费有的按田亩,有的按使用多少分摊,这种办法较简便易行。二是私有的农具借给全组公用,不评工分,或只给一些折旧费,坏了公修。三是私有公用,按成本计算折旧费评出工分(30)。湖北黄冈在农具的使用上,各地互助组都感到记分麻烦,许多组虽确定了计分办法,也没认真贯彻,结果有农具的农民,感到吃了亏,甚至要退组。后来经过讨论,根据已有几个组的经验,都认为可以把农具分为大小两种,大农具如水车、犁、耙等,采用伙用公整,私有权不变,年终酌量予以报酬。公整费与报酬费(多少由组内自议)按耕作面积均摊,小农具如锄头、铁扒等,基本是各用各的,没有的在组内互相调剂(争取每人一套),年终按耕作面积出修整费,不取报酬,互助组在增加生产或搞好副业生产的情况下,经过组员自愿,提取一部分公积金,购买新农具,以补原来的不足(31)。山东互助组内使用农具的情况是:大农具(如犁、耙、水车等)按地亩出钱,公买、公用、公修。私人农具,或放在组内伙用“打成色”(即偿付折旧费),用坏了公修,或临时借用顶工(32)。有些地方互助组的农具,陆续折价归公。陕西省王蟒村互助组的农具,1952年时已差不多把农具都折价成为公共财产,由联组统一调配使用(33)。 对劳力、畜力的互助使用评工记工后,如何算账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关于记工算账的方法,福建省有的是记账,有的是使用工票。算账的时间,有的10天一次,有的半个月,也有1月甚至几个月算一次的。当时农民的文化水平还很低,使用工票的记账办法简单易行。工票一般分1分、2分、5分、10分四种,这样可以计算成任何数字,简单方便。有的互助组只有5分、10分的工票,做工3分或7分就无法算。工票有的用纸做,有的用竹、木签等。至于如何使用工票的问题,有的是“票换票”,每个组员都先分得同等数目的工票。如300分或500分,我给你做,你给我票;你给我做,我给你票。定时评出工资,按期(通常是一个节令)算账(34)。 在有副业生产的互助组里,如何在副业生产中以及农副业之间贯彻等价交换?这个问题包括:一是农业和副业如何结合,如何记工算账实现互利的原则;二是副业生产中劳力与资金如何分益。在农、副业结合和记工算账方面,福建省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谁去搞副业生产,收入归谁所有;他家里的田由组内耕种,由搞副业生产的人按工付给工资。(2)搞副业生产的人也计工得工资,副业生产收入除必需的开支及工资外,按资金分红。(3)农、副业统一记工,按件评分、按劳分红(35)。 建立合理的评工记工算账制度,解决好耕作的先后次序,对于互助组的正常发展与巩固非常重要。但1952年多数的互助组仍未建立评工记工制度,如宁夏盐池县738个组没有一个评工记工的(36)。华北各地对一般等价互利是重视的,但不全面,只抓计工制度以解决劳动用工的多少问题,而对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如种地先后的矛盾等,则不甚重视,而且常用些琐碎的制度去斤斤计较表面上的“等价”,忽略实际上的互利。还有,在互助基础薄弱地区的干部和农民中间,不知耕作先后这种矛盾怎样解决,不知劳动用工怎样计算,则是普遍的现象(37)。有些已经坚持常年的组,则苦于“死分死记”不合理,“死分活计”太麻烦,评工、记工不合理,使许多组员感到互助时间越长苦乐越不均。因此常在次年发生跳组、退组或重新另组的现象,有些互助组便涣散解体(38)。 三、积极作用:互助组对农业生产的促进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完成土改的广大农村,通过建立互助组等组织起来的努力,给参加者的生产与生活带来了实际的帮助。资料显示,建国初期农村互助组的组成,在土地私有的基础上把农民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39)。 首先是组织起来提高耕作水平、改进生产技术、改良生产条件,增加了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许多互助组不仅在深耕多锄增施肥料上有显著成绩,而且集体研究改进耕作方法,按技术专长实行了生产分工。不少互助组设立了“小农场”进行选育良种与防治病虫害实验,划出“丰产地”进行改良耕作法,增施肥料,创造丰产纪录的实验。有的互助组和省、县农场密切联系起来(如山西榆社、平原濮县、辽东盖平等地)成为传播新的生产技术的核心。组织起来改良土壤、修梯田、修滩、打井、开渠的更普遍。据1951年统计,山西省榆社、武乡、左权三县互助组已改良土壤15万余亩;黑龙江镇赉县农民互助改良土壤1900垧;河北省蠡县、安国两县群众组织起来合伙打井,使2万余亩旱地变成水地;陕西长安王蟒村20余年来未修的旧堰,由于组织起来修好了,增加水地130亩。河南襄城、郏县、确山、孟津等的典型村,较好的互助组比一般生产较好的单干户每亩多收小麦一成至二成,黑龙江讷河马庆福互助组比一般单干农民每垧地多收小麦二石至三石,陕西兴平许敬章互助组每亩产麦比一般单干户高出30斤以上。 其次,互助组大量引用新农具。1951年东北区又有104个互助组使用全套苏联马拉农具,有5000余个互助组贷购综合号铲蹚机;华北区同年推广6000余部解放步犁,6万6000余架管式水车,5万余架喷雾器,山东省推广的2万余架水车,绝大部分是组织起来的农民购买的。组织起来便于发挥新农具的效能,给新农具的推广使用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新农具的使用也巩固与发展了互助组。 第三,互助组广泛结合副业生产,合理使用劳力从多方面增加财富。1951年,山西武乡255个互助组统计,上半年副业收入小米1244石,大部分又投资于农业生产。陕西长安王蟒村22个互助组制扫帚赚1亿3000万元,以此款购买耕畜18头。 第四,在新区组织起来克服了生产生活中的困难。河南省潢川县栗岗乡很多贫雇农缺乏耕畜和农具,由于组织起来人牛换工,不但及时种上地,并合伙购了一架水车,组员黄天明领会到组织起来的好处说:“要不是参加互助组,俺也没牛,今年种田又要落人后,借牛时还得求人情说好话”。同时由于组织起来,克服农民播种季节大吃大喝的浪费现象,不少地区在互助组内展开互助共济,解决了贫苦户的口粮、种子困难。甘肃省皋兰县庄子萍乡在互助组内开展互助互济,共借出粮食、籽种二十六石,解决了贫苦户的困难,保证了播种及时(40)。 第五,在春耕防旱及防治病虫害上取得了很大成效(41)。1952年全国兴修及整修小型水渠74300条,塘坝圩堤等166万处,打砖井40万5000眼,共扩大灌溉面积2290万亩,这些水利工程,绝大多数是由于组织起来合作兴建的。同年入春以来全国范围内麦蚜、蝗虫、棉蚜等病虫灾害为害面积很广,由于各地群众组织起来,在“打早、打小、打了”的方针下,基本上消灭了虫害,如热河、辽东两省曾组织起来51万多群众,编成防虫队,划分防虫区进行防虫灭虫的斗争。 同时,能否把农民组织起来,以及组织的好坏,是影响农村经济上升快慢及发展平衡与否的一个主要因素。据建国初期调查,东北松江省集贤县二区保安屯经济上升快而发展又平衡。土改前,该村是当地人人皆知的“穷棒子屯”,土改后,还有好多的二流子。组织起来后,情况有了很大改变。贫农张国卿两口子抽大烟,打“吗啡”,该屯把他组织在互助组后,已上升为中农的水平:自家养着一匹马,还买了一台车;1950年又盖了两间新房子;家里有了余粮,添置了新衣被等。全屯过去的二流子王玉堂、潘惠麟等6户、7户,也都像张国卿这样了。全屯43户中,无马户只有4家,中农已占总户数的83.7%。该屯经济的发展与农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改善,与组织起来,实行了合理分工、等价两利以及充分发挥妇女儿童的劳动能力等是分不开的。而同县的陶斌屯,组织起来只停留在种上地的程度,结果经济发展就慢(42)。 上述事实表明,在私有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劳动互助组,既能保持自耕的小农经济的优点,又能弥补其缺点。因此,互助组的成立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和解决了各地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保证了耕作及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四、消极影响:互助组建立与运行中的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在互助组的建立与运行过程中,有些地方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如西南地区,“自愿、互利和民主管理的原则,在许多互助合作组织中没有充分实现,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的现象很严重”,因此,“组织起来的数字虽然不少,但质量不高基础很不巩固,还有不少的(据计算一般达30%左右)互助组不起作用或很少起作用”(43)。东北地区也较为严重。据《东北日报》1950年5月19日报道,在辽西、辽东两省新区和吉林、松江两省某些老区,采取各种方法排斥限制单干,如单干户出门不给开路条,开荒时不准先占场子。松江有的区提出对单干户“三不贷”、“一不卖”(即不给贷款、贷粮、贷农具,合作社不卖给任何东西)。有的甚至提出:单干户没有公民权,不和他来往,使单干农民“不仅在生产上步步感到困难,而且在人权上受到歧视”。报道还说,对“把互助组织提高一步”,不少地方追求数量,忽视质量,有的地区采用挑战竞赛办法,要求组织起来的农户越多越好,有的连续开会,对单干户进行“说服”,说了不服就不散会,直逼到农民怕耽误生产不得不答应入组为止。据吉林省调查了解,依靠这种强迫命令方式组织起来的互助组占七到八成。也有一些干部把“提高一步”理解成互助组越大越好,辽西兴城县一下子就搞了1125个大型联组。有的地方规定,组员要退组,第一次给予批评,批评后仍然要退,就只能“净身出组,车马留互助组”,而且不准组员和退组户来往。有的还规定,哪个互助组散了,罚款100万元(旧币),给军属代耕一垧地(44)。 华东区在发展互助组方面,不仅有强迫命令和打击单干户的偏向,在盲目“奔社会”、“争光荣”的推动下,还先后出现了不少“明组暗社”的混乱现象,群众讽刺这些组是“描金箱子白铜锁,外面好看内面空”,是“败家组”(45),出现了严重的急躁冒进倾向。 新区在开始组织劳动互助时,比较普遍的方式是领导号召,区乡干部按居民组挨户编组,登门造册。这种方式,由于没有事先细致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往往流于形式主义。如皖北、苏南、山东和浙江的个别地区,都发生过“挨户编组,敲钟起床,吹哨集合,站队分工,红旗一插,大家劳动”的形式主义偏向(46)。 即使是互助组织建立较早的山西省,也有违背自愿原则的现象存在。据1953年4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山西省农村党员中有15%到20%的人存在强迫命令作风。如,有的村支书在群众大会上宣布:“现在我命令大家参加互助组,谁不参加,谁就不爱国”。这种为完成计划任务强迫命令的做法,显然视农民的意愿于不顾,不加入互助组,就给扣上政治帽子,使人不得不入,绝非“自愿”。 另一方面,为实现互助组内的“两利”原则,而实行的评工算账制等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有: 第一,记工算账方面,存在平均主义思想,有的按出工时间,有的根据劳力年龄评分记工,没有坚持“按劳计酬”原则。如陕西长安县的王蟒村,就按“劳动日”计分,一个“劳动日”分早晨、上午、下午三段,不管你劳动强弱,也不管你技术高低,只要是一个全劳动力,做一个“劳动日”都是计10分(早晨2分,上午和下午各4分)(47)。评工计分上的平均主义,实际上把农民的收入与劳动的质量脱节,造成有的农民给别人耕种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出工时间,而庄稼的长势与收成的好坏与己无关,往往出工不出力。 第二,男女劳动力不是同工同酬。陕西长安县的王蟒村对于妇女参加劳动,起初是一个女全劳力,做一天活,得男劳动力一半的工资,引起妇女不满,她们认为自己和男子不平等,被当“半个人”看待。后来在会上提出,才提高到男劳力工资的60%(48)。福建不少地区也有对妇女评分过低现象,有的不管劳动能力如何,硬性规定男的一工抵女的两工,引起妇女很大不满(49)。 第三,记工算账办法复杂,开会太多,严重影响农民及村干部的健康和劳动效率。比较极端的例子是陕西长安县的王蟒村。这个村几乎天天晚上开会,大会开完后,各互助组又要分别开各组的会,特别是春耕季节,会议就更多了。会议往往准备不够充分,一开会就到夜里12点左右,第二天早晨五六点钟便要起床,开始一整天的劳动(50),农民很难休息好,劳动效率势必降低。华东区不顾群众的习惯和经验,不顾生产需要,盲目推行复杂的记工算账办法(如“四定”、“标准工”等),结果形成“活好干,账难算,互助组太麻烦”,“评工记分就是不让睡觉”,更有群众说:“苦,苦,参加了互助组,自己做不了主”(51)。福建省有的组也是天天开会算账;有的评分办法很复杂,多至11种(52)。互助组要讨论评工计分方法及生产计划等,会议多注定是普遍现象,如此则严重影响农民休息,妨碍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互助组是在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的前提下,为解决劳力、耕畜及农具缺乏等困难而组成的一种生产协作组织。它顺应了刚获得土地的农民发展生产的热情,对于生产有困难的农家,特别是贫雇农,组织其参加互助组,确实能解决困难,增加生产,改善生活。据建国之初河南省调查:“现在已经证明了翻身的贫农活干比单干强,如果将来进一步做到活干比单干的中农也强的话,则更会证明组织起来的优越性”(53)。前述大量事实和数据已说明,互助组在建国之初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增长,对有互助需求的贫雇农,互助组的作用尤为显著。作为一种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应充分肯定它的积极作用。当然,互助组运作过程中一些问题的存在,又说明互助组在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存在违背自愿两利原则、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妨碍农业生产的现象,而且比较普遍与严重。一向重视调查研究、讲究实事求是的中共,已经了解这些问题的存在,1953年3月8日中央给各大区的指示中,即曾试图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左倾”冒进倾向(54)。但随着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放弃“新民主主义”(55),中国开始快速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以土地私有为基础,既体现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讲话“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引导”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发展要求(56),也符合建国之初国家施政方针《共同纲领》第27条“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规定(57)的农村互助组,很快被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所取代。 ①主要研究成果有: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邢乐勤:《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叶杨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刘庆旻:《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及其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 ②《华北局关于农村生产情况与劳动互助问题向毛主席的报告》(1950年7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6页。 ③邓槐银:《我是怎样领导互助组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3页。 ④⑦《中共大名四区小湖村支部在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宣传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政司:《农业生产互助组参考资料》第一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1952年版,第61-62页,第60-64页。 ⑤中共中央华东局农村工作委员会农业互助研究组:《华东区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1952年3月9日),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 ⑥胡巨海、春江:《我是怎样领导互助组的?——劳动模范焦天凤的自我介绍》,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政司:《农业生产互助组参考资料》第二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1953年版,第43-44页。 ⑧兴平县人民政府:《陕西省兴平县的互助合作运动是怎样开展起来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参考资料》第一集,第23-25页。 ⑨(12)(13)(14)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政司:《发展新区农业生产互助的一般经验》(1952年4月25日),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58页,第59页,第58页,第59页。 ⑩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农村工作委员会调查组:《莒县吕家庄劳动互助组调查报告》,《农业生产互助组参考资料》第一集,第67-68页。 (11)邓槐银:《我是怎样领导互助组的》,第4-7页。 (15)兴平县人民政府:《陕西省兴平县的互助合作运动是怎样开展起来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参考资料》第一集,第25页。 (16)赵辛初:《湖北省黄冈专区巩固和发展互助组的几点经验》,《农业生产互助组参考资料》第一集,第45页。 (17)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政司:《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49页。 (18)山西省长治专署王良玉:《关于一般村与较差村互助问题的商榷》,《农业生产互助组参考资料》第一集,第5页。 (19)《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1952年农业生产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54页。 (20)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政司:《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农业生产互助组参考资料》第二集,1953年版,第9-11页。 (21)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政司:《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农业生产互助组参考资料》第二集,第5-6页。 (22)《一九五三年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1954年1月14日),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177页。 (23)(24)《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关于农业互助组的总结》(1953年11月20日),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157页,第158-159页。 (25)《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关于农业互助组的总结》(1953年11月20日),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159页。 (26)中共福建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农业生产科:《当前福建农业生产互助运动中等价交换问题的初步研究》,《农业生产互助组参考资料》第一集,第30-33页。 (27)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农村工作委员会调查组:《莒县吕家庄劳动互助组调查报告》,《农业生产互助组参考资料》第一集,第71页。 (28)刘长山说、黎华记:《我领导互助组的几点经验》,邓槐银:《我是怎样领导互助组的》,第28-35页。 (29)(30)中共福建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农业生产科:《当前福建农业生产互助运动中等价交换问题的初步研究》,《农业生产互助组参考资料》第一集,第33-34页,第34-35页。 (31)赵辛初:《湖北省黄冈专区巩固和发展互助组的几点经验》,《农业生产互助组参考资料》第一集,第43页。 (32)中共中央华东局农村工作委员会农业互助研究组:《华东区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1952年3月9日),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73页。 (33)华而实:《全面丰产模范王蟒村互助联组》,《农业生产互助组参考资料》第一集,第80页。 (34)中共福建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农业生产科:《当前福建农业生产互助运动中等价交换问题的初步研究》,《农业生产互助组参考资料》第一集,第35-36页。 (35)中共福建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农业生产科:《当前福建农业生产互助运动中等价交换问题的初步研究》,《农业生产互助组参考资料》第一集,第36-37页。 (36)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政司:《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85页。 (37)(38)《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关于农业互助组的总结》(1953年11月20日),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158页,第157页。 (39)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政司:《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47-48页。 (40)(41)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政司:《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80-81页,第80页。 (42)中央农业部计划司编:《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52年版,第42-43页。 (43)张际春:《关于西南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1952年12月),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66页。 (4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9-200页。 (45)《华东局农村工作部关于互助合作运动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及初步整顿情况的报告》(1953年9月7日),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147页。 (46)中共中央华东局农村工作委员会农业互助研究组:《华东区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1952年3月9日),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72页。 (47)(48)华而实:《全面丰产模范王蟒村互助联组》,《农业生产互助组参考资料》第一集,第86页,第86页。 (49)中共福建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农业生产科:《当前福建农业生产互助运动中等价交换问题的初步研究》,《农业生产互助组参考资料》第一集,第40页。 (50)华而实:《全面丰产模范王蟒村互助联组》,《农业生产互助组参考资料》第一集,第86-87页。 (51)《华东局农村工作部关于互助合作运动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及初步整顿情况的报告》(1953年9月7日),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147页。 (52)中共福建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农业生产科:《当前福建农业生产互助运动中等价交换问题的初步研究》,《农业生产互助组参考资料》第一集,第40页。 (53)《河南省农业调查报告》,《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汇编》,第251页。 (54)《中央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给各大区的指示》(1953年3月8日),《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104-105页。 (55)杨奎松:《毛泽东为何放弃新民主主义——俄国模式影响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观》,《读史求实》,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7页。 (56)(57)《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第2-3页,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