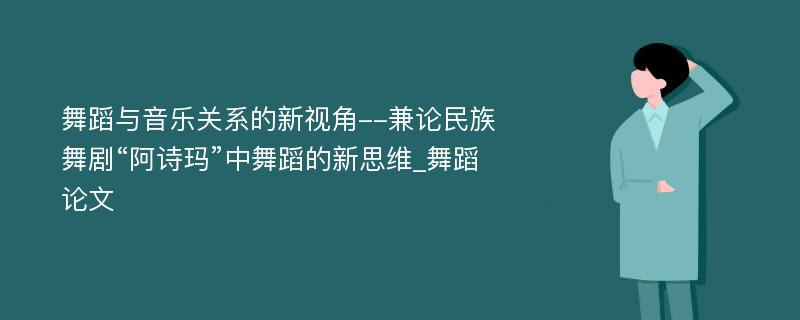
对舞蹈与音乐关系的新透视——兼论民族舞剧《阿诗玛》的舞蹈新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诗玛论文,新思维论文,舞蹈论文,舞剧论文,透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漫长的人类文化艺术进程中,舞蹈与音乐按照各自的本性独立发展。音乐是时间艺 术,而舞蹈既是时间艺术也是空间艺术,连续的、有节律的人体动作及舞蹈队形的流动 组合,都不可能离开空间而存在。舞蹈艺术的这一时空特点,决定了它与音乐这种单纯 的时间艺术,有着互不相同的发展道路。当然,这种发展不可能有纯粹意义上的“独立 ”,两者都会受到对方的影响,但它不可能使两者的发展呈现出某种对应或同步,更不 可能出现艺术轨迹的完全重合。
让人感兴趣的问题不是轨迹是否完全重合,而是两者之间的矛盾。矛盾是由于关系密 切而产生的。如果舞蹈与音乐真正独立发展,各走各路,矛盾也就不会有了。但这是不 可能的。一方面,舞蹈与音乐很难分离;另一方面,艺术的演变和进化又不能不使它们 有所分离。美国舞蹈理论家约翰·马丁明确地指出:“当舞与歌的统一体分解成各自的 一半时,每一半都各行其道,而不再顾及最初的相互关系了,它们各自的进一步发展变 得彼此遥不可及,难得重归旧好了。”(注:[美]约翰·马丁:《舞蹈理论》,文化艺 术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第54、184、185页。)
约翰·马丁说的“舞与歌的统一体”,指世界各民族的民间歌舞,在这个民间歌舞海 洋里,舞与歌的确是个艺术的统一体,或者说是连体艺术吧。而所谓“分解”,其实也 就是音乐与舞蹈的分工,当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这种艺术功能分流 发展的要求才会出现,实现这种分流发展的物质基础也只有到这个历史阶段才能具备。 简单地说,音乐与舞蹈的分流发展是人类艺术进化的必然结果。如果两者始终捆绑在一 起,我们实在无法想象它们的演进与发展,将比文学和戏剧、美术等艺术门类滞后多少 个历史阶段。事实也正是这样,分流促进了两者各自的发展,而音乐的发展尤其是这样 。古今中外,特别是近、现代,音乐在远离舞蹈的条件下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客观地 说,两者的发展不但不同步,而且应该承认,音乐是大大地走到舞蹈前面去了。
舞蹈的落伍主要是在舞蹈创作上的落伍。拿中国来说,虽然舞蹈艺术有着极为悠久的 历史,但在学术意义上讲的舞蹈创作,舞蹈界认为也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在此之前 ,包括漫长的古代和近代,中国舞蹈艺术的延续,一直依靠艺人间对动作形式本身的世 代传承。欧美的情形要不同一些,他们比较早就形成了舞蹈的编导法,这种编导法是与 芭蕾舞剧同步形成的,至今已有五百年的历史。但编导法过于注重传统,墨守成规。中 国新舞蹈的开拓者吴晓邦先生曾经如此分析编导法的局限:
芭蕾舞中的《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等古典舞剧均属编导法的成就, 基本上都是根据音乐的乐想及芭蕾编舞的模式而作的。编导遵循编导法原则,设计出独 舞、双人舞、三人舞以及群舞(插舞)的舞段,组合成全剧。正由于有了这种程式的编舞 法,不免给芭蕾舞剧的题材带来了一定的局限,它使芭蕾舞长期禁于狭窄的领域里。( 注:吴晓邦:《编导法与创作法》,《舞蹈》1986年第10期。)
正因看到舞蹈编导法的致命弱点,所以吴晓邦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倡导富于创新精神的 舞蹈创作法。但他指出,“舞蹈创作法的形成在世界上也只有五十年的历史”,虽然早 在二十世纪初已经有革新的舞蹈家进行了探索性的实践,并取得一定的创作成果,但以 理论形态出现的舞蹈创作法,历史其实不算长。(注:吴晓邦是1986年说“五十年”的 ,算到今天则有六十多年了。)
这很正常。人类的艺术也早以证明,艺术的各个门类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快,有 的慢,不可能齐步走。
对“生长在同一条根上”(注:[美]约翰·马丁:《舞蹈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 94年7月第1版,第54、184、185页。)的音乐、舞蹈这两种艺术来说,它们之间的矛盾 就是因为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而产生的。音乐可以不顾及掉队的舞蹈而独自朝前走,而 舞蹈不能这样,它需要音乐的助力,做到尽可能的结合。问题就这样出现了。约翰·马 丁对此看得十分透彻,他说:
当把它们重新搁在一块去完成某种联合性的功能时,有必要使二者都回到当初分离时 共同的起源点附近去。既然音乐已在自身领域里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它与舞蹈再 次结盟就必须在纯粹音乐形式上,牺牲相当大的进展。(注:[美]约翰·马丁:《舞蹈 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第54、184、185页。)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许多有才华的作曲家是不愿意为了与舞蹈结盟而使音乐作“牺牲 ”的。所以在1986年,终于有人尖锐地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在创作一部舞蹈(舞剧) 作品的过程中,舞蹈创作和音乐创作的关系应该怎样摆?谁先谁后?谁轻谁重?应该是为 舞蹈‘配乐’呢,还是为音乐‘编舞’?”(注:舒泽池:《舞蹈与音乐关系的探讨》, 《舞蹈论丛》1986年第1辑。)
如果就事论事,应该承认,作曲家为舞蹈“配乐”,舞蹈家(编导)为音乐“编舞”, 两种情况都存在,并且都有成功的例证。但无可否认的实际情况是,作曲家为舞蹈“配 乐”是主要的合作模式。舞蹈编导先有一个基本构思,然后向作曲家提出自己的要求, 规定基本的节奏型,比如要几个8拍,几个4拍,总共多少小节,或者进一步提出情绪类 型上的要求。在这种合作模式中,音乐变成了舞蹈的附庸,舞蹈家只要求音乐为舞蹈提 供一个音响的躯壳。这样做,作曲家当然是不甘心的。怎么办?要么干脆不介入舞蹈, 去创作与舞蹈无关、不受舞蹈限制的音乐,如歌曲、歌剧、交响乐等。但如果由于某种 原因(比如在歌舞团担任专业作曲)而不能不搞舞蹈音乐的创作呢?可以设想,作曲家会 在服从总的舞蹈要求的前提下,力求保持自己作品的独立完整性,“追求最合宜的曲式 ,最具自己特性的风格与作品。也力争让舞蹈家追随自己的乐思去编舞”。(注:叶纯 之:《冲突·调和——从舞蹈音乐看作曲家与舞蹈家的关系》,《舞蹈论丛》1987年第 1辑。)双方的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相互让步,彼此调整,但 在具体实践中,一般是作曲家被迫作出较大的让步。例外的情况当然也是有的。《天鹅 湖》是芭蕾舞剧的经典,但首演(1877年)未获成功,原因是舞蹈编导没有吃透柴可夫斯 基的音乐,按古板的程式编舞。几年以后,另一位编导根据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重新构思 ,这才创作出成为经典的舞剧版本。从那以后,一些舞蹈家才对音乐的重要性有了新的 理解。不过话又说回来,也许这是因为柴可夫斯基的名气太大了。
二
如果我们讨论的范围不局限于舞蹈音乐这个专门领域,就宽泛的范围来谈舞蹈与音乐 这两者的相互关系,那么可以说,在人类渡过了歌舞一体的原始阶段以后,音乐发展的 自由度是比较大的,它可以完全离开舞蹈而单独存在;而舞蹈则继续保留着对音乐的依 赖性,我们无法想象不需要音乐作伴的舞蹈。(个别而言,也有一种无音乐伴奏的舞蹈 ,但演员有节奏的动作仍然体现出一种“无声的音乐”。)即使是像伊莎多拉·邓肯那 样反传统的舞蹈家也无法离开音乐。据国外一些舞蹈理论家的研究,这位现代舞的先躯 者对音乐采取一种单纯利用的态度,她利用音乐大师的作品来激发、点燃自己的创作灵 感,但她不是用自己的动作和造型去表现音乐,而是自由发挥。一方面,“她对音乐的 依赖几乎就像对毒品一样”,“当她在巴赫、贝多芬和瓦格纳的音乐中听到大地那‘吸 引与排斥、抵抗与屈从’的节奏时,心里才有创造性的基本力量”;另一方面,她又绝 不是去“解释”这些作曲家的作品,“她从未竭力用舞蹈形式去与他们所表现的思想和 信信念相对应”,“她甚至不用音乐去创作过舞句和完整的舞蹈”,“也没有以他们的 重音和装饰音为模式,来用自己的地面图(即场记)和空中旋转加以重复”。尽管这样, 这位“现代舞之母”仍然不得不“屈从于音乐,这使她绝对无法完全将自己从音乐的统 治下解脱出来”。(注:[美]约翰·马丁:《舞蹈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7月 第1版,第54、184、185页。)
用不着再举例了,舞蹈不可能摆脱对音乐的依赖。
正确的做法是,舞蹈家应该深刻认识舞蹈与音乐两者间的辩证依存关系,借助音乐文 化(而不仅仅是包括舞蹈音乐在内的音乐作品)来提升舞蹈的艺术品位。在这方面,云南 省歌舞团创作的民族舞剧《阿诗玛》,音乐优美而富于民族色彩(本文不多作讨论),舞 蹈编创更是大获成功,它所体现出的新的舞蹈思维和新的舞蹈文化,很值得我们探讨、 研究。
在我近年读过的舞蹈理论著作中,于平博士的《风姿流韵——舞蹈文化与舞蹈审美》 是很有学术价值的一部。作者在叙述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舞剧创作历程的时候,从分析舞 剧形态的角度,对《阿诗玛》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从《小刀会》、《鱼美人》、《 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到《丝路花雨》,中国舞剧偏重于戏剧性的叙述结构,受苏 联芭蕾舞剧的传统模式(主要是《天鹅湖》)影响较深。而《阿诗玛》的诞生代表着中国 舞剧形态的新倾向,即淡化戏剧性的“诗化”倾向,具体说,《阿诗玛》以“乐章式” 结构取代了既往的戏剧结构,它的乐章式的“情感色调”重于戏剧性的“情节线索”, 因此,它被类称为“交响舞剧”(注:见于平《风姿流韵——舞蹈文化与舞蹈审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第244—245页。)。由于运用了“交响编舞法 ”,作品达到了舞蹈与音乐的深度融合。
交响编舞法是借鉴交响音乐的思维逻辑的编舞方法(也有人称之为“舞蹈交响化”)。 我国著名舞蹈教育家肖苏华曾发表《交响芭蕾初析》(注:载《舞蹈》1992年第3期。) 一文,据此文介绍,早在十九世纪初意大利就有人进行过创作交响芭蕾的尝试。柴可夫 斯基首次把交响乐的写作手法运用到舞剧音乐的创作中,为芭蕾交响化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以后,俄罗斯的几位编舞大师成功地进行了交响芭蕾的创作实践,但只是体现在舞 剧的某一幕或某个大型场面中,交响芭蕾还未能从古典芭蕾舞剧中完全独立出来。二十 世纪初在俄国出现的舞剧《仙女们》(又名《肖邦组曲》)是交响芭蕾发展道路上的重要 里程碑,它标志着独立的交响芭蕾艺术的诞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完全抛弃交 响芭蕾而开始步入戏剧芭蕾时,美籍俄裔芭蕾大师巴兰钦在西方又树起了交响芭蕾的旗 帜。进入五十年代,苏联开始为交响芭蕾“恢复名誉”,并随之出现一系列佳作。1968 年,编舞大师格里戈罗维奇采用著名作曲家哈恰图良的舞剧音乐创作的芭蕾舞剧《斯巴 达克》,被认为是交响芭蕾的典范。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舞剧编导对《斯巴达克 》的舞剧形态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可以说,《阿诗玛》就是在这个舞蹈文化大背 景下产生的一个艺术硕果。
在一般舞剧中,故事情节占有重要的地位。与此相关,舞剧中的哑剧成分很大,因为 要靠哑剧成分来推动情节的发展。《阿诗玛》别开生面,编导们聪明地利用人们对阿诗 玛故事的熟悉(从同名长诗到电影的广泛影响),摆脱其叙事框架,用七段组舞来结构作 品。编导打破时空限制,以阿诗玛这个主要人物“诞生于石林又回归石林”为情节线, 以她的情感世界的起伏变化为主旋律,精心安排了黑、绿、红、灰、金、蓝、白七个色 彩舞段,即:生之黑色舞段(序幕《诞生》)、长之绿色舞段、爱之红色舞段、愁之灰色 舞段、哀之金色舞段、恨之蓝色舞段、死之白色舞段(尾声《化石》)。在以往的一般舞 剧中,群舞可有可无,实际上多游离于主题之外。交响编舞则十分强调群舞的重要性, 它与主人公舞(独舞、双人舞和三人舞)相交织,形成类似音乐多声部织体那样的“多舞 群织体”(注:于平博士对“舞蹈织体的组合关系”有独到的分析,见《风姿流韵》。 本文据此。)。例如在序幕的黑色舞段里,石林深处虎啸声声,一群彝族汉子裹挟着高 原奇观的苍莽之气,开天辟地般走来,踏步狂舞。突然一块巨石崩裂,汉子们众星拱月 般地托起一个伏卧大地的红衣少女阿诗玛。在这里,独舞与群舞这两个“声部”交织呼 应,寓意天地裂变,一个民族从远古走来。汉子的石头群舞既象征石林,也象征民族, 阿诗玛既是石林的女儿,也是民族的女儿。独舞与群舞这两个“声部”合二为一。这种 手法在绿、红、灰等几个色彩舞段中也有极佳的表现,例如在绿色舞段中,阿诗玛轻盈 的舞姿好比独唱,而那身着绿衣的女子群舞好像女声合唱,为她作呼应、烘托式的“帮 腔”。在表现阿诗玛与阿黑火热恋情的红色舞段之后,接着是灰色舞段。与女子独舞为 伴的是一群身着灰白色纱衣的女子群舞,她们频频变换队形,迂回流动。古人说“青云 徘徊”、“愁云浮沉”,编导着眼于一个“愁”字,以独舞、群舞两个“声部”合力表 现阿诗玛面临财主儿子阿支逼婚的压力。这样的编排,既是阿诗玛忧愁、愤懑心理的形 象外化,同时借助由“红”变“灰”的色调落差推动了戏剧情节的进展,十分巧妙。
在交响音乐中,“二元性”是一条相当重要的原则,作曲家十分注意各声部间、各乐 章间以及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之间的戏剧性对比。在贝多芬的作品里,尤其是在《第三 交响曲》(“英雄”)里,交响音乐的二元性矛盾对立体现得最为充分、典型。交响舞剧 不能完全照般这些,但二元性的原则也应受到重视。《阿诗玛》正是这样做的,在金色 、蓝色两个舞段里,独舞与群舞的关系就很好地体现了交响音乐的二元性特点。比如金 色舞段,阿诗玛拒绝了阿支金项圈的诱惑、笼络后被关进由若干根金色长杆象征性构成 的金色牢笼,这牢笼就是由手持棍棒的家丁们的群舞来表现的。棍棒或直立,或交叉斜 立,或横拉高抬,这些不断变幻的群舞构图,与阿诗玛或被囚,或奋飞的独舞交织,完 全把戏剧变成了舞蹈,“化戏为舞”,与那种靠哑剧方式推进情节的传统编导手法相比 ,可以说是独辟蹊径,另开天地。在蓝色舞段里,阿黑与阿诗玛在洪水中相互寻找、摸 索、挣扎,那洪水是由一队汉子的蓝裙舞(也有人称之为“大裤脚舞”)来表现的。汉子 们动作凶悍蛮野,大幅度翻卷彝族的男式百折裙,不断变换队形,这段极为精彩的群舞 与阿黑、阿诗玛的生死恋双人舞交织,强烈的二元对比终于将剧情推向高潮。
《阿诗玛》的交响编舞不仅仅体现在主人公舞段与群舞的织体关系中,它的主人公舞 段本身也体现出编导的交响思维。比如双人舞,它在传统芭蕾舞剧中历来占有重要地位 ,但其功能主要在于展示两位首席舞者(男女主角)的技艺,构成华彩舞段,而戏剧情节 的进展却在那里停顿。《阿诗玛》不同,它的双人舞具有推动情节的功能。比如表现阿 诗玛与阿黑、阿支三角关系的一女两男三人舞,利用变换人物组合,一会儿是阿诗玛与 阿黑的亲密对话,一会儿是阿诗玛对阿支纠缠的婉拒,这就使三人舞在不断交替的双人 舞“变奏”中传递出丰富的戏剧信息,既有独白,又有对话与“交响”。
总之,交响编舞法借鉴交响曲的音乐思维逻辑,提升了舞剧中的舞蹈表现力,使舞蹈 与音乐的关系达到深度融合。在这方面,《阿诗玛》的编舞取得了突破性成功。至于这 部舞剧的音乐,总体上讲也是相当成功的。由于这部舞剧在总体构思上淡化情节,以乐 章式的“色块结构”代替重情节、分场次的传统结构,它的音乐自然也相应地一改传统 舞剧音乐的结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全敞开的,无明显分场界限的,甚至没有 确定贯串主题的、是松散状态的自由式结构”(注:《色彩缤纷的乐章——浅析民族舞 剧<阿诗玛>的配乐》,《民族艺术研究》1993年第4期。)。不仅在总体结构上,而且在 作曲技法和音乐的民族风格等方面,《阿诗玛》的音乐也都作了有益的探索。但正如何 予先生所指出的,“《阿诗玛》配乐还不能说是前后贯通、完整无缺的。前后两个主要 部分无论在创作思维上,写作技法上,风格和格调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与两位 作曲家在艺术上未能取得更多共识有关。何先生还指出,《阿诗玛》的“配乐”在有些 地方存在较明显的“断裂”现象,而据了解,“这种‘断裂’是在编舞的过程中给‘砍 ’出来的”(注:《色彩缤纷的乐章——浅析民族舞剧<阿诗玛>的配乐》,《民族艺术 研究》1993年第4期。)。为舞蹈“配乐”而出现“断裂”,这又回到前面讨论过的舞蹈 与音乐、舞蹈家(编导)与作曲家的关系问题上去了。但我们还是再回到编舞问题上去。 毕竟,作为“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的舞剧《阿诗玛》,它的里程碑价值不在音 乐而在舞蹈,在它对“交响编舞”的创造性运用。也许可以说,《阿诗玛》编舞的交响 性大大弥补了舞剧音乐在“交响”上的欠缺。从这部交响舞剧的成功实践中,我们看到 了一种新的舞蹈思维与新的舞蹈文化的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