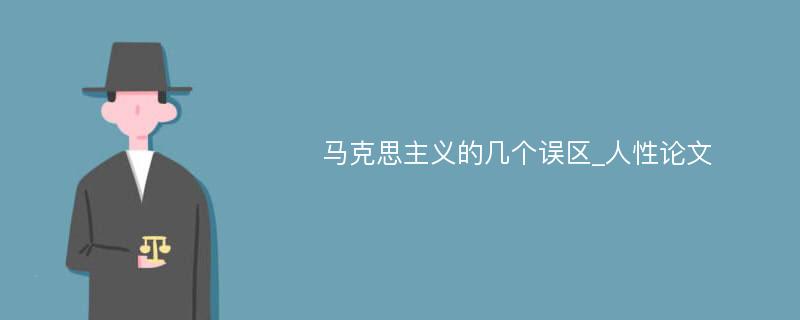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误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误读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马克思对自由的承诺是乌托邦吗?
在今天的不少人看来,马克思对自由的承诺(人的全面发展、共产主义)虽然令人“高山仰止”,却是很值得怀疑的。比如,有学者说:“(马克思认为)只有当物质变得极大丰富,也就是相当于世界的无限扩大,世界大到人人能够拥有足够自己伸展的世界,才能有足够条件做自己想做的事,才不会去压迫、剥削和掠夺他人,每个人才能够有自由。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一个世界不可能丰富到相当于包含无数个属于个人的足够大的可能世界的地步。一个有限的世界不可能变成一个无穷大的世界,这就是自由所以是个难题的真正底牌”,“至少在现实世界是不可能的。当然,在理论世界中或许是可能的”。因为“事实上人的需要和欲望总是水涨船高”,“欲望往往增长得比物质增长更快”。(赵汀阳,第57-65页)
从“资源有限”和“欲望无限”的假定出发,断定马克思关于自由的承诺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可以说,这种看法能引起不少人的共鸣,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如果“资源有限”和“欲望无限”这两个假定是确定无疑的,那么上述结论当然成立。然而在我看来,这两个假定并不是“确定无疑”的。从资源的绝对量看,如果人的欲望无限,则资源就是有限的;问题在于,如果人的欲望有限,那么资源即使在绝对量上是有限的,但在相对意义上(与有限的欲望相比)却是无限的。换言之,资源是否有限,关键要看欲望是否无限。于是,对上面两个假定的分析就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人的欲望是否无限?
众所周知,欲望展示的总是某种欠缺,欲望的本质是匮乏。因此,匮乏既是欲望的源泉,又是欲望的边界,匮乏的消除也就意味着欲望的消解。从这个层面来看,人类的欲望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在我看来,人们通常所说的“无限欲望”其实并不是物欲,而是精神方面的欲求。人对精神的欲望的确是无限的,但人对物质的欲望却是有限的。“物质欲望的有限性和精神欲望的无限性”不仅是马克思对自由承诺的出发点,也是人类社会演进的真实的历史逻辑:
其一,物欲在技术上的边界
在当代,不断升级的计算机、越来越快捷的电信网络、拟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机器人以及信息时代的各种相关技术,正在每个领域和行业迅速取代人类的位置。科技的惊人发展促使许多学者敏锐地提出了“工作的终结”、“无劳动社会”的大胆预测:“在将来更加自动化的全球经济中,上亿人的劳动将不再必要,或根本不必要”。“在无劳动社会中,人们不再有为了生计而劳动的压力”,人们“可能追求从新闻和写作、艺术欣赏和创作、做游戏中获取更大快乐。他们可能追求更多的更高尚的活动——为了学习的乐趣而进行学习,为了更健康而锻炼身体,以及为了更大的个人满足而培养其心智”,“人们掌握了这一切闲暇时间,就有可能大规模地帮助他人。这将使他们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者”。(迈克尔)据美国电脑专家库茨魏尔预测:“2025年之后,机器人将迅速代替人在工厂和农场中工作,而且它们将为所有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转引自波特)
闲暇时间的增加和劳动时间的缩短,为上述预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休闲时间的增加和休闲活动的扩张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第三产业的重要内容,从而使得娱乐预算在家庭开支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足以证明,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物质生存的满足对于人类已经越来越不是问题。在18世纪末,这个时间是72小时;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个时间已经缩减到不足40小时。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缩减”还远未终结:只要科技的发展不停止,工作时间的缩减就将“进行到底”。不难推测,随着工作时间在人的生命中所占有的比例越来越小,人的发展的时空将极大地得到延展,旧的分工界限将越来越模糊,人类为了生计而劳动的压力将越来越小,劳动的目的将越来越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生命的意义”,劳动将越来越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自然力替代人力”的发展过程中得到实现的。
问题在于,如果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人类会不会因无所事事而堕落呢?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一旦劳动不再成为价值的尺度,“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8-219页)。因此马克思说:“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这种“自由时间”由“闲暇时间”和“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构成。(同上,第225-226页)可见,闲暇并不是“什么都不干”、“无所事事”,而是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愿意的活动。
然而,人们可能会问,如果劳动不再是财富的源泉,那么劳动不就成了一个历史范畴了吗?那么我们又怎样解读马克思的以下论述:“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同上,第208-209页)?我认为,对以上论述应当辩证理解。马克思把被自然力替代的劳动称为“直接形式的劳动”,这意味着人类在“直接形式的劳动”消亡之后,还将存在着“间接形式的劳动”,后者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艺术和科学”等较高级的活动。因此,虽然那种需要用价值来计量的“直接形式的劳动”消亡了,但是,那种无须价值计量的“间接形式的劳动”——个人在“艺术和科学”领域的自由发展,却构成了人类乐生的手段和存在的意义。我认为,正是在“间接形式”的意义上,马克思才把劳动看作是永恒的范畴。而在“直接形式”的意义上,劳动则是历史的范畴。
其二,物欲在心理上的边界
在现代经济学的经典教义中,“人类的物质欲求与物质产品的数量成反比关系”是公认的结论。这个被称为“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是物欲有限性在经济学上的最好证明。它表明,人类的物欲在生理上存在着边界,不可能无限膨胀。如果说,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积累是可以确定的必然趋势,那么,伴随着这一必然趋势的必然是物欲膨胀速度的下降乃至最终趋于“停滞”。诚然,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的现实,似乎对上述趋势蒙上了阴影,并且表明科技发展要受到生态和社会各种关系日益失衡的制约,其前景可忧可叹。这是马克思的承诺无法回避的事实——比如俞吾今先生强调:“无论是地球上的资源,还是社会生产,都存在着自己的界限”,因此,“必须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前提”。但这也正好从反面说明,原有的以物欲膨胀为导向的社会关系恐怕将越来越难以适应和容纳科技的发展和新的生产力水平;这种导向必须改变,也一定会改变。否则,物欲的“无限膨胀”必将导致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
按现代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人类的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永远没完没了。毫无疑问,“物质动机”是人类“利己”行为的出发点,现代经济学把“物质动机”视为经济人“利己”行为的出发点,这是正确的。在物质匮乏的背景下,个别人的“利他”行为(如雷锋)之所以彰显出高尚、伟大和不平凡,是因为“利他”行为往往是物质层面的“利他”,缺乏必要的物质支撑,“利他”行为就很难“普世化”。但现代经济学却不愿正视,不仅“物质动机”只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一个层面,而且“物质动机”在人类心理活动中的主角地位也并非是不可动摇的。美国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分层理论”证明:物质财富与人类心理活动中的“物质动机”成反比,与“非物质动机”成正比。也就是说,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人的物欲将趋于递减——这个道理在今天并不是什么乌托邦的理论猜测,而是越来越鲜活的现实。随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类心理活动的“物质动机”将趋于递减,而“非物质动机”(比如对精神的追求)会越来越凸显。对此,只要看一看当代绿色和平运动、志愿者行动、环保潮流的强劲势头就清楚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一旦群体中多数人的行为不再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将失去解释力。这一趋势在后工业社会里看得非常清楚(西欧、北欧和北美的部分地区)”。(汪丁丁)
学术界有不少高人总是以“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来嘲讽马克思对自由的承诺。其实,这种嘲讽多半来自现代经济学不断重复的小商小贩式疑虑:马克思的承诺固然值得尊重,但这种承诺岂不是在与“经济人”的本性对着干吗?这个疑虑涉及两个基本问题:(1)人性是否永恒不变的范畴?这个问题我将在下一节分析;(2)劳动作为谋生的手段是否永恒不变的范畴?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经作出了回答。在这里,我想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与学术界的同仁共勉:“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取决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革命与进化,而这种改造却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纯粹的空想。他们的眼光超不出当前时代的经济界限,因而不懂得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80页)
二、马克思的人性假定是“利他论”吗?
利己且理性的“经济人”假定,不仅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也是市场经济得以确立的基本前提。那么马克思是怎么看待人性的呢?把马克思有关人性的假定判断为“利他论”,这是当下经济学界最常见的解读(有趣的是,不仅非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不少马克思主义者也持这种看法)。然而我认为,这种解读严重曲解了马克思有关人性的看法。
马克思对人性有多种表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两个:一是把人性归结为“社会关系”。比如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二是把人性归结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或实践,比如马克思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在如何评价马克思这两种有关人性的论述的问题上,学术界见仁见智(强调前者的被称为“社会关系本质论”,强调后者的被称为“劳动本质论”或“实践本质论”)。我认为,有一种看法值得认真对待,这种看法认为:“上述两种不同的表述是马克思从不同层面上对人的本质所做出的科学揭示。劳动本质论着眼于人的本质的内在根据的层面,强调人之为人的根据就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社会关系本质论则着眼于人的本质的现实性表现的层面,认为人的本质的现实性表现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孙熙国)
社会关系仅仅是人性的表现形式,而劳动(实践)才是人性的更深层次的内容——这种认识正是马克思人性观的精髓所在。在我看来,不论马克思关于人性的表述的具体内容有何不同,马克思对人性的认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实践”。从实践的角度来把握人性,是马克思“人性论”的真谛。由此可见,那种断定马克思对人性的假定是“利他论”的说法,实在是对马克思的重大误读。马克思在人性问题上从不去纠缠什么“利己”还是“利他”。在马克思看来,不论是用“利己”还是“利他”来框定人性,都会失之肤浅和皮相。质而言之,在马克思看来,“利己”和“利他”都只是人性的外在表现,而不是人性的本质内容。对于人性而言,还有比“利己”和“利他”更为根本、更为本原性的东西,这就是“社会关系”,而比“社会关系”还要本原性的东西就是“实践”。这种人性论显然比什么“利己”和“利他”之类的人性假定,其内涵要深刻得多,其境界也要高得多。在人性问题上,马克思的深刻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人性是第二性的
历史上的人性观一般都是“本质先于存在”的人性观(从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到弗洛依德的“人是非理性的动物”等等,均如此)。这种人性论自古典经济学以来,一直是主流经济学不证自明的公理,比如在现代经济学的教义中,“利己”之心是人性的根本特征,也是人的天性使然(由此可见人性是与身俱来的、不可变更的)。“利己”具体表现为人的本能要求——食欲和性欲。马克思却是一个另类。从“存在先于本质”的立场出发,马克思认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任何动物都有活动,但人这种动物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就在于,人的活动是“自由”和“自觉”的。正是这种“自由”和“自觉”,决定了现实的人性都是人自己劳动的产物。所以马克思说: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把“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同上,第95页)。劳动不仅改造着自然界,而且也改造着人本身。马克思坚信:不是人性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人性。因此,人性之谜寓于社会存在之中,要揭示人性之谜就必须揭示社会存在之谜。
其二,人性不是人的自然属性,而是人的社会属性
马克思并不否定人具有自然属性(食欲和性欲),但他反对把人的自然属性当作人的本质。他认为,人的生理性(本能)是天赋的,而人的社会性(人之所以是人的依据)则是既定社会存在的结果。如果“利己”指的是对食欲和性欲的本能要求,那么所谓的“利己”仅仅是人的动物性特征,而不是人性的本质规定。因为人性的本质规定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物性。如果“利己”指的是市场中商人的斤斤计较,那么所谓的“利己”就不过是人的存在(环境、历史等)使然。当然,这个“存在”并不是抽象的个体的存在,而是有着社会结构规定的现实的存在。从古典经济学开始直到现在,主流经济学总是把人看作是非历史的和抽象了具体社会关系的人,眼睛里永远只有孤岛上的鲁滨逊先生——马克思说:“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8页)其实,个体总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个体:“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马克思,第12页)因此,对社会存在的解读也就是对既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剖析。
其三,人性是历史范畴,而不是永恒范畴
由于“经济人”假设是市场经济中斤斤计较的小市民或讨价还价的小商小贩的真实写照,所以现代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对于市场经济中的人性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把人性永恒地锁定在小市民的身上,实在是大谬不然。马克思坚决反对把人性看作永恒范畴,他在讥笑耶利米·边沁把人性视为不可改变的看法时说:“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同上,第669页)。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观点与马克思比较接近,他说:“如果人性是不变的,那么,就根本不要教育了,一切教育的努力就注定要失败。”(杜威,第155页)从“经济人”假设出发,现代经济学期望的“理想人物”也就是那种吃得好、穿得好然而却“没有灵魂的人”。其实,我们所面对的人,是从事着实践活动的现实的并且发展变化着的人,而绝不是从来如此、永远如此的抽象的人。按照辩证思维,事物的本质不是先定的、先在的、永恒不变的、已经成型的,而是不断生成的、向未来开放的。人的本性也是如此。既然“存在”随着实践会不断发生变化,那么人的“利己心”也就必然会发生变化。正因为马克思将实践看成是人性的深层次的内容,所以他才能把人性理解成历史的、不断生成的和发展变化的,而不是理解成先验的和永恒不变的。
三、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在于对公平和正义的关注吗?
面对当下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公平和正义的诉求正在成为社会的主流呼声。强调公平和正义,说明人们对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现状有了清醒认识,比起“效率惟一,不顾公平”的认识水平毕竟是一大进步。然而,仅仅让公平和正义获得并不可靠的“话语权”是远远不够的。古往今来,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外,有知识有良心的学者们往往坚信:公平和正义是“超越社会和历史”的永恒范畴,是一切社会变迁的基础和动力。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仅靠几句动听的口号,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获得过真正的公平和正义吗?那种“超越社会和历史”的公平和正义真正光顾过弱势群体吗?
有人或许会反问:难道人类社会就没有超越一切阶级之上的公平和正义吗?马克思的回答是:很不幸,在阶级社会中的确没有。即使诸如“杀人偿命”这种看上去任何社会都认可的公平和正义,在许多人看来在特定条件下或许并不公平。由此可见,一旦超时空的公平和正义落入具体的社会之中以及具体的个人身上,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从来就没有什么抽象的公平和正义。在公平和正义的华丽辞藻下,其实有着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当人们谈到公平时,一定绕不开“谁是公平的所有者”的问题,说白了也就是“谁有资格为公平买单”的问题。在一个私有制大行其道的社会,真正能够属于各色人等、各个阶级平等共有的东西恐怕已不多矣。物质财富是这样,作为精神财富的“公平”和“正义”当然也是这样。
说到公平和正义,人们免不了要拿马克思来说事。马克思是怎么看待公平和正义的呢?在一个只知道“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久已不知公平为何物,甚至已经习惯于把公平诉求一概斥之为“平均主义”的丛林世界中,大概是为了在围剿马克思的时尚中表现得稍微公允一些,一些人终于良心发现,开始大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就在于其对公平和正义的呼吁和关注。
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定位于对公平和正义的关注,实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大误读。不错,马克思一生都在为公平和正义奋斗,可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公平和正义并不是其诉求的对象。不仅如此,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公平”、“正义”往往成为这位一生都在追求公平和正义的伟人讥讽、拒斥和批判的对象。以至于波普尔认为:由于心怀正义但又苦于“正义”被人所滥用,马克思才忌讳使用“正义”的(参见波普尔,第310、319页)。马克思的确对公平和正义的滥用多次表示过不满,但这还不是马克思拒谈公平和正义的真正原因。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公平和正义并不是一个超越历史的范畴,而是一个历史范畴:奴隶社会有奴隶社会的公平,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公平,资本主义社会有资本主义的公平。此公平并不等于彼公平,更何况主子的公平岂能等价于奴隶的公平?“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保护民、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指广义而言),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么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3页)其实,善变的公平就如同经济上不能独立的女人,离开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的支撑,就注定会成为无家可归的娜拉:一旦离家出走,必然面临“娜拉走后怎么办”的困惑。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清醒地看到:社会变迁的动力并非抽象的公平和正义,而是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生产力的发展。公平和正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实质上是物质生产及其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与那些空喊公平和正义的人不同,马克思“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际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因此,马克思坚信“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不公平、不正义的社会绝不可能用公平和正义的观念来摧毁。这也正是马克思对空谈“公平”、“正义”始终不以为然的原因所在。马克思说:“‘宗教’和‘政治’只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同上,第44页)。那么“时代的现实动因”是什么呢?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时代的动因不应当从“意识”(宗教、政治、观念)中去寻找。同理,社会变迁的动因并不在于对“公平”和‘“正义”这些观念的诉求之中——公平和正义仅仅是社会变迁的现实动因的表现形式。
我注意到,在今天的学术界,某些人正在把抽象的公平和正义当作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他们看来,要推动社会进步就必须改变人们的公平和正义观念。其实,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同上,第45页)。公平和正义是崇高的,是值得人们追求的,但是如果把公平和正义当作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把观念看作先于存在的第一性的东西),则是荒谬的。遗憾的是,这种荒谬恰恰是当今极为普遍的认识。当许多饱学之士动辄以“公平和正义”的名义为自己的主张提供依据时,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如果不是心虚的矫饰,就是冬烘的迂腐。
马克思说:“什么东西你们认为是公道和公平的,这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什么东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81页)于是我们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从来不纠缠于公平和正义的空洞说辞,而是始终关注决定公平和正义的物质基础是如何存在、如何发展的。
公平和正义在本质上不过是某种社会制度、某个阶级或集团利益的“辩护词”,它是不可能“超然于社会”之上和之外的。也就是说,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公平和正义。以为这世界真的存在“普适的”、“人类社会共有的”公平和正义,只不过是在自欺欺人;如果不想成为学院派的自娱自乐,那么关注“谁的公平”、“谁的正义”,才是在关注有意义的“真问题”。而有关这个真问题的答案,大概只能到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
标签:人性论文; 社会公平正义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社会公平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