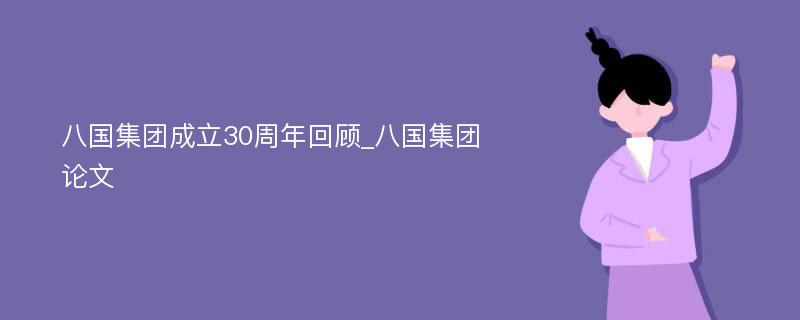
八国集团30周年发展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八国论文,周年论文,集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国集团(以下简称G8)是当前国际体系中占据优势的一种权力与利益组合。在经济上,G8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占全球GDP的70%左右;(注:根据世界银行资料库中2004年世界GDP数据统计所得:http://devdata.worldbank.org/data-query/。) 政治上,在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中,就有4个属于G8;军事上,八国集团内有4个核大国,军费开支占全球军费总额的一半以上。(注:2005年6月8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公布的全球军费支出新数据:http://www.sipri.org/contents/milap/milex/mex_database1.html。) 近年来,该集团逐渐将自身的定位从“西方大国内部协调”转为“全球治理中心”,通过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等重大国际组织的话语基调,很大程度上操纵着全球规则的制定。伴随着中国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国际体系,如何处理与G8的关系已成为中国外交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一、G8的演变和发展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国际金融市场陷于混乱,世界经济形势动荡不安。西方主要国家的领导人意识到,西方大国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协调各自的经济与金融政策,从而引导自身和世界经济平稳运行。
1975年11月,在法国总统德斯坦的提议下,法、美、英、日、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六国在法国的朗布依埃第一次举行了六国首脑会议。1976年加拿大加入,七国集团(以下简称G7)正式形成。1997年俄罗斯加入G7的峰会讨论,会后的政治公报开始以G8的名义发布。2002年俄罗斯取得了在2006年担任峰会轮值主席国的权利,这标志着G7正式演变成为G8。
纵观G7/G8的30年发展历程,G8在成员组成、运行机制、职能范围和对外政策等方面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在成员组成上,G7/G8对吸纳新的成员国极其谨慎。从1976年G7形成至1997年正式接纳俄罗斯加入首脑政治会议的近20多年的时间内,G7没有接纳任何新的成员国。根据G7成立时的声明,成员国应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成员国必须是实行市场经济和西方民主政治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二,成员国在全球范围内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强国,二者缺一不可。这个准入标准基本上将希望加入该集团的其他国家挡在了门外。
其次,在运行机制上,G8的组织架构逐渐从虚到实,并且坚持实效优先。在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该集团从最初的少数西方领导人的“炉边谈话”,逐步形成以首脑会议为核心的一套较为完整的组织架构,就众多具体问题设立了一系列政策协调和实用机制。除一年一度的首脑会议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每年还举行独立的外长会议以及3~4次的财长会议。20世纪90年代开始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贸易、环境、劳工、内政、司法、能源等部长会议,近年来又创建了十余个专家工作组。组织机制逐渐覆盖了经济、政治、安全、社会等各领域,并且在不停地分化和细化。
再次,在职能范围上,G8从最初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向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等领域拓展。G8最初的议题集中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1978年以后开始讨论政治、安全问题。近年来首脑会议的涉及面越来越广,包括地区冲突、军控、反恐、环境、卫生、打击跨国犯罪、信息技术等诸多领域。议题的增多和议题领域的扩大使得G8的职能范围随之扩张。对内,成员国越来越多的国内政策受制于G8的集体讨论;对外,越来越多的国际规则由G8制定,或者在G8的影响或操纵下制定。
最后,在对外关系上,G8从封闭的内部协调转向与外部对话。成立之初,G7的政策协调局限于西方内部。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的不断加剧,G8为了缓和来自发展中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压力,开始进行政策调整,注意与发展中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开展对话,以寻求国际社会更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二、G8的结构机制与功能
(一)G8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
经过30年的发展,G8已经形成以首脑会议为核心的一套较为完整的协调机制,其组织架构大致可分为4个层次:首脑会议、部长级会议、领导人私人助理会议和专家小组与工作小组。
G8决策的形成有4条途径:其一是由部长会议提出议题和建议,交由首脑会议讨论通过,然后交付部长会议或者专家工作组执行;其二是首脑私人助理向首脑会议提出议题和建议,在首脑会议通过后,由部长会议或者专家工作组执行;其三是专家工作组直接向首脑会议提出建议方案,首脑会议通过后,由部长会议或者专家工作组执行;其四是部长会议自身选择议程并代表G8做出决议,目前使用此项决策权限主要是财长会议。
G8的首脑会议—部长会议—专家工作组决策机制,保证了信息交流的开放和决策的封闭,从而兼顾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效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专门机构不同,G8的架构涵盖多个不同的问题领域,这使得各国在进行谈判时能够全面考虑各领域的关联性,综合考量本国在不同领域内的得失,进行平衡协调。
(二)G8的功能与作用
G8不仅为成员国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与高层次的交流平台,具备了促进成员国之间进行合作并且履行协议,商议、决策和执行等功能,同时还具备一定的导向功能。纵观G8近30年的发展历程,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呈上升的趋势。G8影响的领域从最初的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安全和其他社会各领域。同时,G8在各领域的影响程度也在逐渐加深,这使G8对重大国际事务的研究和把握能领先一步,进一步加强对国际局势的掌控能力。
为了科学判断G8在不同功能领域内的影响力,笔者选取了公报中的承诺、相关部长会议的数量(定期和不定期的)、成员国的遵从性、可掌控的国际组织、新发起的国际制度以及专家工作组等6个指标作为分析变量,得出的统计如下表所示:
G7/G8在不同功能领域的比较(注:根据多伦多大学G8研究中心的数据计算而得," Commitments Produced at Selected Summits,1975-2001," Prepared by Professor John Kirton and Dr.Ella Kokotsis,http://www.g7.utoronto.ca/evaluations/committment-assessments.htm。)
项目领域
经济 政治安全
社会
承诺(项)1975~2001年
357151 142
部长会议1993~2003年77 35
35
遵从性1975~2001年 37%
24% 59%
可掌控的重要组织IMF/WTO/WBNATO 无
新发起机制(个) 5
35
专家工作组(个) 5
53
注:经济领域囊括世界经济、金融体制、贸易、援助、减债、就业、教育、人口老龄化、信息技术等方面;政治安全领域包括联合国改革、反恐怖主义、军控和不扩散、地区冲突、预防冲突和危机等;社会领域包括卫生、能源、环境、食品安全、文化多样性、难民问题、人权等等。
由下表可见:国际经济领域是G8首要的核心功能领域,该集团涉及经济领域的议题最多,相关的机制化程度最高,而且基本上可以掌控最重要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这使得G8确立了在国际经济领域内的主导地位。
其次,G8的功能表现在社会领域,虽然涉及的议题相对较少(这主要是由于G8涉足社会领域的时间较晚),但成员的遵从性却最高,机制化程度在较短时期内即与政治安全领域不相上下。
最后,在政治安全领域,G8虽然涉及的议题不少,但是成员的遵从性却很低,这降低了该集团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影响力,这说明G8在政治安全领域内的影响力最弱。
三、G8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G8面临的机遇
从产生到现在,G8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是因为其既能仰仗外部客观条件,又能获得该集团独特的内部条件支撑。结合G8发展的外部客观环境和自身内部条件,G8发展面临着三大历史机遇。
首先,随着全球化的高速发展,全球治理的需求增强,这为G8提供了历史契机和舞台。过去30年中,全球化的高速发展催生出许多新的问题。这些新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先就存在的、伴随着全球化在更大范围内扩展开来的问题,如环境污染、毒品走私、各种传染病扩散等等。另一类是在发展过程中新领域内出现的问题,如利用因特网犯罪、各种金融衍生品市场管理等等。各种各样的全球问题,迫切需要建立各种相应的治理机制来应对,召唤着一个全球治理新时代的来临,这些都为G8提供了历史机遇和舞台
其次,现有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极端不均衡,大部分权力和财富集中于少数的发达国家手中,这为G8实行全球治理提供了有利环境。G8成员国无可辩驳的实力优势是该集团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力的坚实后盾。在经济上,除俄罗斯外,另外七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70%左右,贸易量占全球总量的52%;政治上,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中有4个属于G8;军事上,有6个是北约成员国,4个核大国,军费开支占全球军费总额的一半以上;科技上,几乎所有的世界科技强国全汇集在该集团之中。正如一位加拿大学者所说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因素——全球权力的集中,是G8具备的最大优势。”(注:加拿大学者Alison Bailin的讲稿," From Traditional to Institutionalized Hegemony," February 2001,http://www.G8.utoronto.ca/scholar/bailin/bailin2000.pdf。)
最后,高度的利益认同和灵活的运行机制保障了G8的决策效率。G8清一色是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占优势地位的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相近的地位决定了它们的国家利益有着相当程度的重合和交汇;同时,由于各国的政体类似,相互之间已形成较高程度的集体认同,而这种集体认同进一步重塑和巩固了成员国的共同利益,有利于各国在此基础上进行积极的政策协调。此外,与其他大多数国际组织相比,G8成员国数量少,且能充分发挥灵活机制和首脑外交的优势,因此能保障其决策和执行的效率。
(二)G8面临的挑战
同时也应看到,G8亦面临着外部的压力和其内部因素的局限,制约着G8影响力的发挥。实质上,G8的成立基于这样一种设想:最强大的少数几个西方大国实现联合,共同主导国际事务。这个设想的成功实现必须依赖两个内部的前提条件:其一是集团的成员国必须囊括世界上实力领先的大国;其二是成员国都有维持现有国际秩序的意愿。当然,机制的稳定运行还依赖于一个外部条件:集团外的认同。而目前,这几个条件都遭受到了程度不一的挑战。
首先,由于大国实力发展的不平衡,G8的成员设置已逐渐不能对应世界政治中现实的权力格局,这削弱了该集团发挥影响的实力基础。自集团成立30年以来,各大国发展速度很不平衡,世界力量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集团之外新兴大国的崛起。即使单就经济实力而言,目前中国的GDP超过若干个G8的成员国。这种状况导致了一种局面:尽管集团依然保持着整体的绝对力量优势,但由于没有囊括新兴的实力领先大国,该集团无法有效控制世界局势。因此,从2004年春天开始,G7的财长会议邀请中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讨论。
其次,近年来集团内部矛盾和碰撞的增加制约了G8的协调能力。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在外交上单边主义恶性膨胀,与其他成员国在安全观、秩序观、格局观等问题上分歧日深。美国为了建立单极霸权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现有国际秩序的破坏者。集团内部的矛盾,实质上是维持现有的西方集体霸权模式和建立美国单极霸权之间的矛盾。2003年伊拉克战争充分暴露了美欧深刻的观念与利益分歧,表明西方战略同盟裂痕已经公开化。如果美国坚持独霸和单边主义,德法两国就不会让步。这将严重制约G8协调一致对外行动的能力。正如一位学者所估计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出现在实力上足以对G8构成挑战的新兴国家,导致该集团解体的因素最有可能来自于其内部的利益分歧。”(注:加拿大学者Alison Bailin的讲稿," From Traditional to Institutionalized Hegemony" ,February 2001,http://www.G8.utoronto.ca/scholar/bailin/bailin2000.pdf。)
最后,近年来自集团外的对G8缺乏代表性和合法性的批评和指责声也越来越大,动摇了国际社会支持G8的民意基础,削弱了G8的政策号召力和影响力。对G8提出反对和质疑的力量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二是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国际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发展中国家对G8的批评从该集团成立之初就开始出现,并长期存在。发展中国家认为该集团的组成缺乏普遍性,是发达国家的机构,因此在政治领域反对由G8主导国际事务,在经济领域内要求该集团更多地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减免穷国的巨额债务等等。近年来国际市民社会对G8的质疑和责难之声越来越高。这些非政府组织认为由G8主导推动下的全球化导致了全球环境恶化、贫富分化加剧等一系列恶果,同时也认为G8并不是由民众所选举出来的机构,因此无法代表各国民众,不具有合法性。因而非政府组织近年来不断掀起反全球化的运动,G8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目标。
总之,全球化的继续发展,对全球治理的需求进一步增强,为G8提供了一个长期发挥作用的空间。与目前国际上其他的国际组织相比,G8具备实力优势和机制灵活的两大长处,似乎更能适应新时期全球治理的需求。但同时,G8也面临着来自外部压力和内部因素的诸多限制,其功能和效率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G8能否成为未来全球治理的中心,关键在于其是否能完成自身重大改革,如根据形势的发展吸纳新兴的大国、增强成员国之间政策的协调,加强与集团外的对话以增强民意支持等等。
四、G8的对华政策
(一)G7/G8对华政策的演变
自1975年成立以来,随着国际格局、G7/G8自身以及中国实力的变化,G7/G8的对华政策经历了3个阶段。笔者将其分为对华漠视阶段(1975~1986年)、干涉阶段(1987~1996年)和寻求建立联系与对话阶段(1997年至今)。在G7/G8对华漠视阶段,它与中国没有任何接触与往来,双方处于相对隔绝状态。在G7/G8对华干涉阶段,G7/G8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关注中国,如1987年的G7首脑会议公报首次简短地提到中国:“在亚洲,我们同意应该特别关注中国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注:John Kirton," The G7/G8 and China:Toward a Closer Association," in John Kirton ed.,Guiding Global Order:G7/G8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0,p.197.) 但是在1989年,G7对华态度发生逆转。1989年的巴黎峰会发布了一份专门的《中国问题声明》,指责中国政府“违反人权”,并由此发起了一项全面制裁中国的提案,包括暂停双边高层政治接触,终止对华军售和世界银行对华贷款等等。此后几年,G7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进程,将中国视为主要潜在问题,一方面鼓励中国经济改革和参与国际裁军进程,另一方面在政治改革、人权、香港回归、南海问题上企图干涉中国内政。G7/G8对华寻求建立联系和对话阶段从1997年开始,由于香港回归和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国际舆论呼吁中国加入G7。1999年,G8邀请中国参加“金融稳定论坛(FSF)”和成立新的二十国集团(G20)。2000年G8冲绳峰会时,日本通过各种渠道邀请中国、印度、印尼和韩国4个主要亚洲国家领导人参加峰会对话,但被中国婉拒。此后,G8越来越频繁地邀请中国参与其各种机制。2003年6月,在法国总统希拉克的邀请下,中国领导人参加八国峰会举行前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2004年10月,七国集团财长会议首次邀请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参加对话会议,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表明,G8正式承认了中国在解决全球经济和金融问题中不可回避的作用,将中国视为处理重大国际事务必须借重的伙伴。
(二)G8对华政策的争论
吸纳新的“对系统有重要影响的(systematically important)”大国加入G8已经成为大多数成员国的共识,目前的讨论主要是吸纳哪些国家以及吸纳的具体步骤。中国是最热门的候选成员国,也是讨论的焦点所在。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核心问题上,即吸纳中国是否有助于增强G8总体实力,是否有助于提高G8在国际上的声望与合法性,是否有助于增强对中国的影响?
1.在吸纳中国是否有助于增强G8的实力这一问题上,一种观点是:G8必须接受中国,没有中国的加入,G8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力将大打折扣。这种观点在西方经济学界相当普遍,美国格拉汗教授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指出,“在美国,大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G7并没有充分代表亚洲的经济力量。比较合理的选择是吸收中国,它已经是亚洲第二大的经济体,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强国”。(注:《G7财长会议鸿门宴?》,转引自《21世纪世界经济报道》,2004年10月1日。)
另一种观点却认为:如果G8吸收中国加入,成员国数量的扩大将降低决策的效率,反而将损害G8的行动能力。这派观点担心由于中国采取的政治制度和西方国家相“对立”,而且一向又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自居,与西方发达国家在诸多领域都存在原则性的政策分歧,因而如果接受中国加入,很可能使得G8达成协议的效率大为降低。因此,这派观点坚决反对G8接受中国。
2.在吸纳中国是否有利于提高G8的合法性的问题上,一种观点认为:取得和增大合法性的主要途径在于扩大成员国代表性。国际舆论在批评G8缺乏合法性时,主要是指G8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只考虑少数发达国家的利益,而置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于不顾。因此,加拿大学者彼得·哈纳尔(Peter Hajnal)认为:“G8必须考虑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和沟通,才能增强全球民众对G8的政治认同。”(注:Peter Hajnal,The G7/G8 System:Evolution,Role,Documentation,Ashgate:Aldershot,1999.) 而中国的国际形象长期以来定位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吸收中国入内显然有利于增进G8的代表性,从而增强G8在全球治理中的合法性地位。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取得和增大合法性的主要途径在于尽可能增加公民的共识和政治认同感,“民主”形象是维系民众政治认同感的最有效方式。加拿大的约翰·凯尔顿(John Kirton)教授是维护G8“民主”形象的坚定支持者。他指出:“如果G8吸收非民主国家加入,那么就违反了当初G8创建时的基本原则,背弃了G8的民主性质,使G8丧失基于民主政体之上的道德优势,损害G8的国际声誉,并且动摇G8在全球治理中的合法性基础。”(注:John Kirton,Joseph Daniels,and Andreas Freytag," The G8' s Contribution to Twenty-Firsrt Century Governance" ,in John Kirton,ed.,Guiding Global Order:G7/G8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0,p.283) 因此持这派观点的人坚决反对吸纳中国。
3.在吸纳中国是否有助于增强G8对中国的政策控制力问题上,亦存在两种相反的判断。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以及世界经济未来发展趋势决定了G8必须要面对中国,而让中国加入G8有利于利用G8已有的各种灵活机制加强与中国的沟通,增进与中国在各具体领域的协调。美国学者威廉·海曼(William Whyman)虽然不赞成让中国直接加入G8,但却赞成G8加强与中国的接触和联系。他指出:“如果把中国等国家置之门外,这些国家所贯彻的开放、多边的贸易体系以及其国内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可能不会保持。”(注:何帆:《中国与G7的双向选择——在接触和参与之间》,载《国际经济评论》,2004年9~10月刊。)
另一派观点则认为,吸纳中国加入G8无助于增强对中国的控制力,因为中国崛起过程中在诸多领域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不可调和,中国注定要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和西方的权威力量。(注:持这派观点的多为支持“中国威胁论”的西方人士,虽然公开发表此观点的文章较少,但是在笔者与西方学者的交流中可以明显察觉到此类观点还是具有一定的市场。) 因此,应该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尽可能地阻止和延缓中国挑战西方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如果让中国加入G8,反而将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其在游戏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因此坚决反对G8吸纳中国。
(三)G8成员国对于是否吸纳中国的不同立场
从G8内部分析,笔者认为其成员国对G8是否应该吸纳中国这个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也大相径庭,具体来说如下:
美国:美国对G8吸纳中国持消极否定的态度。美国一方面担心中国加入G8会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加快中国的崛起步伐;另一方面也顾虑中国加入G8后会与法、德、俄罗斯等国联合,削弱美国对G8的控制力。因此,在2000年德国和日本提出邀请中国参加G8的意向之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冲绳会前、会后多次谈到在G8扩大的问题上,应以“民主国家”和“市场经济”作为加入条件,表明了对中国加入G8的否定态度。同时,迫于国际金融形势和欧洲盟友的压力,美国不得不支持让中国部分地加入八国机制,例如利用七国财长会议与中国开展对话,协调汇率问题。
法国与德国:法国和德国一方面出于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平衡美国单边主义的战略考虑,另一方面也认为中国加入G8有助于推动中国和平地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因此对G8吸纳中国抱着非常积极的态度。法国早在1997年就提出要建立G8和中国之间的定期会晤机制。2003年,希拉克总统热情邀请中国领导人参加埃维昂会晤。德国的态度也非常明确而积极。据海外媒体报道,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埃维昂峰会期间公开表态说,如果八国集团要增加成员,中国应该是首选国家。
日本:日本将G8当做其提升国际地位的最重要平台,无论是出于与中国竞争还是从政治上紧跟美国的战略考虑,日本对让中国正式加入G8持消极否定态度。在2000年G8冲绳峰会时,日本曾以东道主身份再三邀请中国领导人参加八国峰会最后一天与亚洲国家的对话会议。同年11月,日本亦曾邀请中国出席八国峰会上成立的“数码机遇工作组(DOT FORCE)”。但这主要是出于扩大当年的峰会成果,凸显其作为“亚洲代言人”形象的需要。根据海外媒体报道,2004年G8海岛城峰会时,日本的代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考虑G8吸纳中国的时机并不成熟。可见,日本人内心深处不愿意看到中国加入G8。但是在另一方面,日本又想通过G8的机制来控制和约束日渐强大的中国,因此在某些领域内支持中国加入G8的一些工作机制,利用G8对中国进行控制和约束。
俄罗斯:俄罗斯对G8吸纳中国抱着积极推动的态度。作为经济实力较弱的新成员,俄罗斯在G8这个俱乐部中有一种人微言轻的感觉,而中国的参加可使俄罗斯多一个“伙伴”,有利于相互借重,增强其发言地位。俄罗斯曾邀请中国加入G8的“打击高科技犯罪24小时联络站网络”和“反恐工作组”,并且表示,无论中国是最终加入G8,还是以某种形式参与G8的活动,俄罗斯都将尽力协助,予以支持。(注:John Kirton," The G7/G8 and China:Toward a Closer Association" ,in John Kirton ed.,Guiding Global Order:G7/G8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189.) 从俄罗斯致力于推动“俄中印”三角关系的策略看,俄罗斯支持中国和印度同时加入G8的想法也未必完全是空穴来风。
英国、加拿大、意大利:它们对于G8吸纳中国抱着被动和谨慎的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立场。如果美国支持中国加入G8,它们也不会反对;反之,如果美国持反对意见,那么这三国基本上也不太可能支持中国加入G8。另一方面,即使不考虑美国的意见,这三个国家对G8吸纳中国本身也抱着犹豫和怀疑的态度,它们既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认为中国的加入有助于提高G8的整体实力,但又担心中国的加入会导致G8的决策和执行效率降低,反而损害G8和它们自身的利益。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G8内部成员对吸纳中国的态度分为三派:最积极的是法国、德国和俄罗斯,最消极的是美国和日本,而英国、加拿大、意大利介于前两派之间。由于美国在G8内具有最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因此是否吸纳中国加入G8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五、结束语
通过从历史的维度纵向分析G8的演变规律和发展前景,从横向角度分析G8的结构、运行机制和功能,我们可以得出结论:G8是当前国际体系中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机制,它隐藏在诸多专门性的国际机制的幕后,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全球规则的制定。同时,G8凭借其优势实力和灵活机制,在塑造未来的全球治理中亦占有先机。因此,如何发展与G8的关系已经成为崛起进程中的中国所面临的必然课题。近年来G8开始主动寻求并积极推动与中国的对话,为双方关系发展带来契机,我国应抓住有利时机,更积极、务实地探索应对G8的各种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