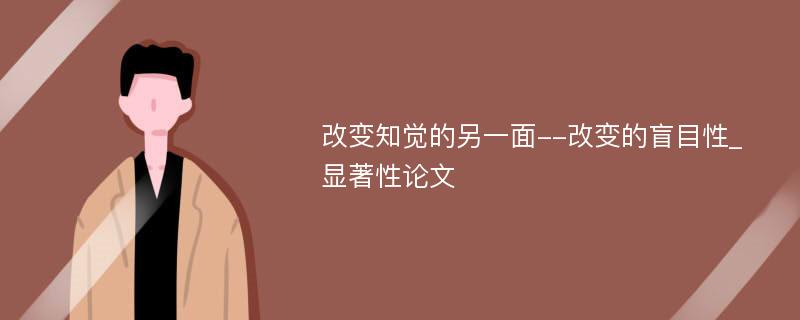
变化知觉的另一面——变化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2
1 前言
生活中有很多变化盲(也称为变化盲视change blindness)的例子,例如“找出图片差异”的游戏需要反复对比才能发现;看电影时我们很难察觉人物在转换镜头前后装束的变化;父母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变化熟视无睹等。与变化盲相反的是变化觉察(change detection),变化盲和变化觉察都是我们对变化的知觉,二者产生于同一过程中,像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Rensink,2002)。
对变化的意识觉察是一个古老的命题,许多哲学家也为此展开过讨论,上世纪50年代以来心理学对于变化盲的研究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已从零散的现象验证发展到真实场景的信息整合研究(Rensink,2002)。早期,图片识别、圆点辨认、面部变化判断等研究中已经提到变化觉察和盲视的现象(French,1953)。几十年来,有关变化盲研究已经对注意、视觉加工、记忆过程等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有研究者运用变化盲的闪烁范式(原始图片A和变化后图片A′之间插入白屏,三者循环往复出现直至被试觉察到变化或一个trial结束,这一范式能够最大地排除被试的猜测作用)来检测司机在“十字路口”的决策准确性,以此了解注意捕获失败现象探索无意注意对视觉的影响(Caird,Edwards,& Creaser,2005);Hollingworth(2003)通过眼睛扫描和渐进变化实验来探究视觉记忆机制,并依此提出了视觉记忆模型。
变化盲的普遍性及理论价值使得它几十年来受到关注,成为研究的热点。近几年关于变化盲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变化盲产生原因的新解释、变化盲的影响因素研究、内隐变化觉察以及变化盲的多通道和错误元认知研究等方面。
2 变化盲现象原因辨析
上世纪80、90年代,许多研究认为变化盲的出现是人们很少或根本没有对事物进行视觉表征,如果有也仅仅是对那些处于中心注视点的事物进行表征(Irwin,1991)。后来的许多研究则发现即使在非常详尽租完整的视觉表征情况下变化盲也会发生(Hollingworth,2003)。Simons和Rensink(2005a)对10年来的研究进行总结,认为由于变化盲现象的存在而把视觉表征看成是稀少的、全无的观点是不经推敲的,在以下四种情况下,即使是有着丰富而细致的视觉表征仍可能发生变化盲,即“原有表征衰退或覆盖”、“连接失败”(变化前后的表征没能进入比较通道)、“变化前后的表征格式不匹配”及“未对原有表征进行合适加工”。Rensink等人和Landman等人的实验结果支持了表征衰退和覆盖说(Rensink & O'Regan,2000; Landman,Spekreijse,& Lamme,2003);Silverman的实验支持了第二种情况(Silverman & Mack,2006);Mitroff,Varakin等人的研究支持了第四种情况(Mitroff,Simons,& Levin,2004; Varakin,Levin,& Collins,2007);第三种情况目前还未得到强有力的支持。综上所述,目前比较统一的观点是变化前事物的视觉表征是存在的,变化盲现象只能说明表征在促进有意识的变化知觉方面有局限。
Simons等认为成功地觉察变化取决于是否能够完成全部三个步骤,否则即会出现变化盲。首先,所看到的事物要能够被表征,并且这些表征被保留以用来作出觉察与否的判断,否则就会出现变化盲;其次,变化前后的事物表征需进行比较;除此之外,要成功地报告出变化,还需要在前后表征比较之后被主体意识到,因此以变化盲来推断变化前刺激表征为“无”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并且如果变化前刺激没有被表征,那么就不可能有“有意识”的变化觉察(Simons & Rensink,2005b)。
针对事物变化前表征信息状态和变化盲产生的原因,有研究者相继提出“易变干扰”、“覆盖”、“比较失败”等假设。Rensink和O'Regan(2000)通过连续闪烁范式证明了早期对于事物的视觉表征是丰富的,但是易变的。无论早期阶段的表征如何详细,由于注意容量是有限的,随着新表征的形成、时间的推移和间隔物的干扰,原本的完整的表征变得不稳定并且渐渐消退,以至于不能为变化觉察提供足够连续统一的像,所以觉察失败。为了验证事物变化前信息表征被“覆盖”的假设Landman等人(2003)在实验中要求被试判断矩形的方向是否变化,中间插入持续1600ms的灰屏间隔,被试判断准确率由于变化位置上线索信号的出现有所提高,而且只在插入间隔前提示是有效的,间隔后则无效的,说明原始的表征已经被变化后的物体表征所覆盖,不能与之比较从而导致对变化的盲视。Silverman等则认为前表征被覆盖是不可信的,他们运用Sperling部分报告法探索变化觉察和变化盲情况下信息表征的情况,实验结果表明字母列变化前后的信息都得到编码,变化盲发生的原因在于前后表征不能进行比较(Silverman & Mack,2006),“比较失败”假设同样也得到了验证(Simons,Chabris,Schnur & Levin,2002; Rodway,Gillies,& Schepman,2006)。另外,Hollingworth和Henderson(2004)的研究也证明了那些受过关注的事物在长时记忆中保留了丰富的表征信息,只是对这些信息的编码、提取和比较过程受到了限制才会出现变化盲。比如,渐进式变化更容易出现变化盲是因为视觉短时记忆总是在更新以反映环境的变化,逐渐发展着的变化对应着更快的更新,变化前后的表征太过相似,比较更可能失败,而一步到位的方位变化就容易被觉察,Beck等的研究也验证了变化盲现象是由于所储存的信息不能被很好地提取(Beck,Levin,& Angelone,2007a)。
3 变化盲的影响因素研究
3.1 刺激属性与注意广度
明确各刺激属性及注意广度对变化盲的影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各视觉属性在场景知觉中的作用,并将之推广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比如,对于旅行路线中不同方位、界标的变化盲研究对航海、飞行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提高对方位、界标、方向的变化觉察能力更可能避免各种意外事故的发生。
刺激属性对视觉的影响研究由来已久,其中著名的研究是Simons和Levin(1997)的“问路情景”实验。研究发现,当实验者(问路者)与被试年纪相仿,被试的变化觉察率有所提高;但当实验者被打扮成与被试非同一个群体时,觉察率又下降了,证明了问路者(刺激)的群体属性影响了被试的变化觉察能力。Rensink等人(1997)的实验研究也揭示了觉察率受到刺激意义的影响,比如,处于兴趣中心事物的变化能更快地为被试所觉察,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兴趣中心的事物更可能通过高水平的加工捕获到注意。然而,Pringle和Irwin(2001)的实验结果却与此相反,他们发现刺激显著性(包括方向、颜色、明度、移动)作用强于意义性。他们对此的解释是:他们的研究是“刺激显著性”,而Rensink等所谓的兴趣中心并不完全是刺激意义属性,也包含着其他的显著性。
Aginsky等发现刺激的颜色、位置、呈现方式三个属性,只有颜色变化显现出线索效应,并且不管是否改变场景构型,都有线索效应(Aginsky & Tarr,2000)。他们认为刺激的位置和呈现方式都得到自动的编码,而颜色没有,代表性特征(位置和呈现方式)比表面性质(颜色)因素得到更好的编码,才有以上的差异,这一结论得到David等人(2006)研究的支持:面部表情比无表情刺激的单纯颜色变化觉察率来得更高一些,Bahrami(2003)也证明了在多刺激觉察任务中对于颜色的变化需要投予更多的注意才能被观察者意识到,对听力损伤者与正常被试变化击中率的比较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观点(Bottari,Turatto,Bonfioli,Abbadessa,Selmi,Beltrame et al.,2008)。此外,还有研究证明了物体的明度也影响变化盲(Arrington,Levin,& Varakin,2006),场景结构性好的图片觉察率高于混乱的图片(Varakin & Levin,2008)。
在注意广度与变化盲的关系方面,Pringle等人(2001)结合刺激的三个特性(角度特异性、显著性、意义性)及注意广度考察年轻人与老年人对交通场景的变化觉察能力。FFOV(functional field of view功能视野范围)任务用来检测被试的注意广度,80张以驾驶员在车内的视角拍摄的照片作为材料,让被试判断照片场景是否发生变化,记录反应时。结果显示FFOV范围小(注意广度窄)的个体变化觉察反应就更慢,这验证了注意与变化觉察效率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注意广度与刺激角度变化的关系时,Pringle等发现注意广度范围与边缘变化觉察的相关程度高于中心变化(相关系数为分别为-0.66和0.54),即对边缘变化的觉察更多地依赖于注意广度。遗憾的是他们并未将注意广度和刺激显著性、意义性结合起来解释,注意广度对于这三种刺激特性变化觉察能力的影响是否一致需后续研究者来解答。
3.2 知识经验
视觉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对人们对世界认识的影响?这个问题历来都是视觉和意识研究的重心,并且通过了解知识经验在变化盲中的地位是探究“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加工方式在知觉过程中作用的一个有效途径,因此将知识经验作为一个单独的影响因素加以表述是有必要的。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尚未达成共识,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知识经验对于变化知觉中起何作用以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加工孰轻孰重两个问题。
在知识经验的作用方面,“问路情景”实验中被试就是依据实验者的外表特征来表征信息,这种对群体的归纳就是自上而下的加工过程,同时说明变化知觉是一个包含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向的加工,是不单纯依赖于某一个场景视觉特征而更可能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认知过程(Stirk & Uunderwood,2007)。Beck和Peterson(2007b)的研究发现更可能在现实中发生的变化(probable change)的觉察好于不可能发生的(improbable change),并且在长时记忆任务中两种材料的成绩无明显差异,这证明了虽然两种材料都得到了编码,但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有助于对变化前事物信息的提取,致使觉察准确率不同。与此一致,Epstein等人(2007)的研究也证明了熟悉性对变化觉察有主效应,被试对于自己所在校园场景的变化判断会更准确。然而,Rosielle等人的研究结果却显示对于熟悉场景的变化判断和难度估计都未有更好的表现。他们认为对熟悉场景(长时记忆)的表征往往是“大纲式”的并非是详尽而细节化的,即使是得到详尽的编码在对变化前后信息的进行比较时反倒会因为信息太过繁多而导致比较失败(Rosielle & Scaggs,2007)。
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加工的重要性来看,Pringle等人(2001)的实验发现刺激显著性比意义更能捕获注意,说明高水平加工(意义)并不比低水平加工(显著性)更强有力,由此推论在变化的知觉过程中自下而上加工优于自上而下加工。但是,这一结论却与其他研究有所出入。Hollingworth等人(1998)为考察知识对物体识别的作用,运用了不同语义联系的材料,重复Biederman等人1982年的实验发现刺激的语义属性影响了被试的变化觉察表现,场景语义一致比不一致的更容易被觉察,但他认为这一结果是由于被试的反应偏差所导致的,排除这一干扰之后,无论是对与场景语义一致还是不一致的变化的觉察都未出现优势(Hollingworth & Henderson,1998)。Stirk和Uunderwood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冲突可能是由于未把刺激显著性和语义显著性区分开,他们将刺激变化的显著性和与场景的语义关系作为自变量(与场景不一致的变化被称为“语义显著性”),采用2×2组间实验设计,结果证明刺激变化无论是高还是低显著性,对与场景语义不一致变化的觉察相对于一致的显得“更快更好”。基于这一结果,Stirk等得出知识背景的作用优于刺激显著性的结论,这也支持了Kelley等人的研究(2003)。他们为此做出的解释是:可能语义显著性更容易捕获注意,得到更多的加工,客体表征更持久;又或者刺激显著性更早地受到关注,但是由于语义上不一致引起的理解不通畅致使被试花更多的时间来加工(Stirk & Underwood,2007)。不论是哪种可能性,都意味着稳固而丰富的表征有利于变化被觉察。
3.3 个体差异
变化盲的另一个作用在于它能够用来进一步研究不同个体之间的信息处理和注意偏差。比如,有研究者用变化盲来揭示酒精和大麻吸食者的信息处理偏差性,少量吸食者或不吸食者比大量吸食者更容易对图片中酒精和药物的变化出现盲视;反过来,大量吸食者对与酒精和药物无关的变化更容易出现盲视(Jones,Jones,Simth,& Copley,2003)。Mayer等人(2006)对蜘蛛恐惧症和非恐惧症被试的研究发现:蜘蛛恐惧症患者比非恐惧症组对蜘蛛变化的觉察率更高,与其他事物比较,他们能更好地觉察出蜘蛛的变化。另外,变化盲也被用于考察读写障碍儿童的视觉信息处理机制(Rutkowski,Crewther,& Crewther,2003)。
各专业领域专家与熟手对于信息的不同处理方式也体现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校对工作需要将注意分配到整个句子才能觉察不规则的词,他们能够更好地控制注意的分配,这是否可以迁移到其他特定任务中?Asano等人(2008)为了检验这个问题,他们选择无变化提示的觉察任务与视觉搜索任务,将专业校对工作者与新手进行了比较,发现专业者能够更合理地把注意投向各部分,更容易觉察到变化,与此相反的是新手则会把注意集中在视觉场景的上半部,觉察成绩也更差。Steffen等人(2000)的研究中以足球教练与足球新手为考察对象,以连续交替出现的足球场景照片为实验材料,发现美国足球教练比那些新手更能认出足球现场那些与足球关联的变化,从而推论对特定领域内图像的变化,专家比新手更具有敏感性。此外,从年龄角度来看,老年人更容易出现变化盲,刺激意义性对老年人的影响小于年轻组(Pringle & Irwin,2001)。
3.4 文化背景
视觉与认知的研究都倾向于认为东方人是整体地观察这个世界,注意整个全局和各事物之间的关系,西方人是分析性地注意那些显著的物体,借助变化盲研究也可以验证不同文化群体的注意分配特点。Nisbett等在场景注意的跨文化研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看完一副静态图片后要求被试报告他们所看到的事物,美国被试最先和最频繁提到的是显著的物体(比如鱼缸里的大鱼),而报告出背景事物(比如鱼缸中的水草和小青蛙)的日本被试是美国被试的两倍。对场景事物的注意及记忆存在着这样的文化差异,变化盲也难免打上文化的烙印,他们由此将跨文化研究推广至变化盲研究领域:美国被试更容易觉察显著事物的变化,相反的,日本被试更可能报告出背景的改变(Nisbett & Masuda,2003)。随后的研究中他们给被试呈现各种生动动画和静态图片,美国被试对焦点事物的变化更敏感,而亚洲人对背景事物的变化更敏感(Masuda & Nisbett,2006)。这两项研究只是揭示了变化盲的跨文化现象,为了证明变化盲的跨文化性来源于不同的文化视角模式,Chua,Boland和Nisbett对各种自然状态场景(无文化色彩的中立图片)进行处理,将一部分背景进行改变,新旧图片混合呈现,先记录眼动情况,过后让被试评判对各图的喜爱程度,判断刺激是否看过;美国被试视线更多停留在显著的物体上,说明他们对这些物体进行了详细的编码,中国被试在背景与物体之间视线分配则更均衡,中西方不同复杂程度的社会网络使得他们的注意分配指向不同(Chua,Boland,& Nisbett,2005)。
4 内隐变化觉察研究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发现部分报告觉察失败的被试却对变化有一定的敏感性,这被称为“内隐变化觉察”(Thornton & Fernandez-Duque,2001),换言之内隐变化觉察就是“变化没有被个体的意识所觉察,但却对个体的行为产生了影响”。依据Rensink(2002)的观点变化要为观察者所意识到才是对变化的成功觉察,那么就可把内隐变化觉察视为变化盲的一种特殊类型。内隐变化觉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人们的视觉表征是丰富而完整的,只是对变化的觉察未被意识到。从静态到动态实验材料,从间隔技术到注意持续技术,变化盲研究的实验范式已经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而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认为这种外显的报告方式会致使研究忽略内隐的变化觉察,应兼用反应时和观察时间等判断标准来验证内隐变化觉察的存在和作用。
Fernandez等人(2000)采用二择一迫选(2AFC)范式对内隐变化觉察进行研究:16个简单矩形矩阵式呈现在屏幕上,特定位置的矩形方向发生垂直或水平变化,让被试对随后出现的选择项进行选择反应,被试虽然未能意识到变化,但是他们对于变化的判断成绩却高于随机水平,Fernandez认为是因为对变化的内隐定位促使他们的判断成绩更好,这结论与Smilek等人(2000)的研究一致。Mitroff(2002)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被试之所以对变化刺激与未变化刺激的反应与观察时间不同,原因在于被试一般采用保守的评判标准,更倾向于对“相同”作出反应,而对作出“不同”的判断则比较谨慎,因此这并不能说明内隐变化登记过程的存在,对于变化仍需通过外显的比较才能觉察。Fernandez和Thornton对Mitroff的挑战进行回应:如果是迫选方式使得被试用排除法对“非变化”项进行排除,那么就意味着被试对“非变化”项的信息有更好的保留,而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反倒意味着对“非变化”判断应该好于“变化项”了(Fernandez & Thornton,2003)。面对是否存在对变化的内隐加工过程这一争论,Laloyaux等人(2006)认为以上两项研究结论冲突在于方法不一致,为此再次重复Fernandez等2003年的研究,肯定内隐变化觉察确实影响着被试的表现,人们对方向的有意识判断受到实验过程中对方位无意识觉察的影响,其后,面部表情的渐进变化研究,同样证明了被试对面部表情的辨认受到了变化信息的影响(Laloyaux,Devue,Doyen,David,& Cleeremans,2008)。
5 变化盲研究新动向——多通道与元认知研究
5.1 变化盲的跨(多)通道研究
变化盲研究主要在于探索对变化“视而不见”的各种机制,集中在视觉领域,然而多通道整合发展已经成为心理学发展取向之一,变化“盲”也不再局限于“视”,也可以是“盲听”(Eramudugolla,Irvine,McAnally,Martin,& Mattingley,2005; Demany,Trost,Serman,& Semal,2008; Haroush,Hochstein,& Deouell,2007)、“盲触”(Gallace,Tan,& Spence,2006),近几年来又出现了一些混合通道的综合研究(Auvray,Gallace,& Tan,2007; Auvray,Gallace,Hartcher-O'Brien,Tan,& Spence,2008; Gallace,Auvray,Tan,& Spence,2006),不管何通道形态,都是对“未能探测事物所发生的变化”,都可称之为“变化盲”,
在听觉通道方面,Eramudugolla等人(2005)验证了混音状态下注意指向可以消除变化盲听:在四种以上自然音混合情况下,被试几乎觉察不到其中一种声音的消失,而如果让被试注意指向某一种声音,他们的觉察表现几乎完美。这与视觉通道“注意对于变化觉察是必要非充分条件”的结论不太吻合,可能是因为注意指向条件不同,在视觉研究中,即使是焦点事物也有不同的特征属性,而听觉研究的声音刺激则非常纯粹。触觉通道的研究通常运用震动器对人体产生触觉作为刺激,运用变化盲经典范式进行。Gallace等人(2006)的研究发现,人们对于触觉形态的震动依然存在变化盲。
对于听觉、触觉的单通道研究更多地是为了验证变化盲在这些形态下是否也存在,而视、听、触的多通道研究则可以探究各通道之间是否相互干扰,也更符合现实生活条件。Smith(2008)将变化盲视与变化盲听(change deafness)进行了比较。实验主要任务是让被试数出字母表中搭配不当的字母数,同时向被试呈现搭配好的声音与图片(比如蜜蜂的图片与声音),中间出现空白屏,随后出现变化或者没变化的图片与声音(其中一半的图片与声音有变化),最后让被试再认或回忆是否变化,结果是更多的被试出现变化盲听。Smith对此的解释是因为人们在生活中更多的是依靠视觉系统而非听觉系统,听觉更可能被忽略,Auvray等人(2008)的研究部分支持了这一结论。他们将触觉作为变化刺激,实验条件为前后触觉连续出现、中间间隔空隙、触觉掩盖、声音掩盖、视觉掩盖5种,有间隔的情况下变化盲增强,触觉、视觉掩盖都削弱了变化觉察,而听觉掩盖则没有对被试产生影响。
5.2 变化盲的错误元认知研究(CBB研究)
人们总是对自己的变化觉察能力很自信,但是实际上又经常出现变化盲,人们的这种错误的认知被称为变化盲误(change blindness blindness,CBB)。Levin等人(2000)为了证明CBB的普遍存在将他们在1997年研究中的那些实验电影材料(披肩、碟子变化)进行描述转换成问卷形式,让被试评估他们自己对这些变化的觉察情况,结果发现大多数被试都高估了自己的变化觉察能力,为了排除被试的个体差异(比如人格倾向、自信度等),他们又进一步采取为他人评估的方式,结果还是如此。后来,他们又开展对于CBB的机制研究,认为个体对自己知觉经验的自信并不能说明人们的CBB现象,而低估目的性及场景复杂性在变化觉察中的作用才是解释CBB的因素之一(Beck,Levin,& Angelone,2007a)。
6 研究展望
变化盲为探讨注意、意识、知觉及视觉记忆提供了非常好的方法和视角。通过变化盲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注意的本质、机制和功能。然而,国内的研究者只在某些研究领域涉及变化盲(梁风华,曹立人,2004),很少有人对它进行专门的研究。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变化盲研究中存在着许多的争论,这些争论既可为我们研究变化盲提供借鉴,也是以后研究发展的动力所在。
(1)表征机制的争论。目前比较一致认可变化前事物信息是被编码和储存的(Rensink & O'Regan,2000; Landman,Spekreijse,& Lamme,2003; Silverman,& Mack,2006),哪个环节导致变化盲(提取还是比较)?信息是被覆盖还是易变被干扰?视觉信息是否需要以某些方式被保护起来以免变化盲的发生?如果表征是存在的只是未到达意识层面,那么这些表征虽然没有得益于集中注意,它们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另外,需要考察是否存在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考察变化盲、变化觉察的神经机制,探索选择性注意和内隐信息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都是未来研究所需要努力的。
(2)变化知觉的“上下加工”的问题。对“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加工的地位目前许多细节还没有弄清,它们孰轻孰重?是否如同认知心理研究领域中所广为认可的“这两种加工各有侧重,在良好的知觉条件下,知觉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加工,而随着条件恶化,自上而下加工的参与也将逐渐增多”(王甦,汪安圣,1992),或者在知觉早期阶段自下而上起主要作用后期则自上而下起主要作用,又或者两种加工同时进行?这也是以后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
(3)内隐变化觉察。“观察者虽不能外显报告看到变化,但变化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判断”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这个问题得到了更多的肯定回答,但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许多额外因素还没被完全排除,比如在内隐变化觉察实验中个体的差异还未得到很严格的控制(Mitroff,Simons,& Franconeri,2002);还有内隐变化觉察与内隐学习及“暴露效应”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
(4)变化盲的错误元认知研究。作为信息接收者,人们有许多的知觉经验,但是还会存在对视觉的一些误解,对变化知觉的过度自信就是其中的一种,主要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使人们形成了这种对变化觉察能力的错误认识?这种错误的认识是否是变化盲现象的影响因素或者原因之一?
(5)变化盲的认知神经心理研究与应用。变化盲的脑损伤认知神经心理研究还不多见,这会是运用变化盲探索视觉和注意偏差的有效途径。另外,变化盲在实际生活中也有广泛的运用前景,对于它的实质探索及实际运用(比如视觉治疗方案和仪器的设计)是我们进行研究的最终目的之一。
收稿日期:2008-1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