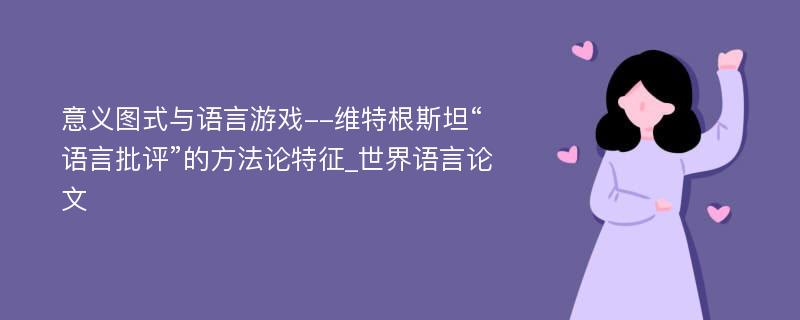
意义图式与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语言批判”的方法论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特根斯坦论文,方法论论文,语言论文,图式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1)04-0051-09
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在西方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因为他完成了或者说实现了“语言的转折”。这就是把认识论考察的主体从私有的“自我”扩展为公共的作为人类总体的“形而上学的我”或“世界灵魂”,从传统的个人经验和思维推进到人类语言的水平和层面上,提出了认识的界限就是语言的界限,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就是关于语言的意义以及怎样可能的问题。从哲学观上说,他把哲学归结为语言分析活动,主张“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1]。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活动以1933年为界,先后建立了人工语言哲学和自然语言哲学。前者以《逻辑哲学论》(Logisch-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1922)为代表,后者从《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1936-1949)为代表。这两种语言哲学对西方语言哲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维特根斯坦先后建立这两种语言哲学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方法,也不无独到之处和启发意义。笔者仅就这个问题作一点评述。
一、意义图式说:通过逻辑分析把握语言的本质
对语言问题的哲学考察,西方学者一直是在“思维-语言-世界”的三维参照系的框架中展开的。但以往的语言哲学家都只是从“三元关系”中的“二元关系”来研究语言,如弗雷格、罗素就是分别侧重于“语言-思维”和“语言-世界”的二元关系来考察语言的。维特根斯坦则从“三元关系”来全方位地考察语言问题,并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建立人工语言哲学。他前斯提出的“意义图式说”就是这一方法的核心内容。
(一)“逻辑图画”与“思想投影”
从“三元关系”来考察语言问题,首先要找到三者共同的东西。维特根斯坦在吸收逻辑原子论的基础上把“逻辑形式”作为思想、语言和世界三者共同的前提。他承认“逻辑形式”具有原子性,世界的原子是原子事实,语言的原子是基本语句(原子命题)。但是,语言与世界是彼此分离的两个领域。人们不能从语言本身中获得原子事实,也不能在经验中直接得到基本语句。这样,他用“逻辑图画说”来改造逻辑原子论,用“图画”的观点来看待逻辑形式,特别是刻画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他认为,语言和世界的逻辑对应关系,完全可以用图画和描绘对象之间的符合关系来形象地加以表述。人们用以表述世界事物及情景的象征性符号,同画家勾勒一幅图画所运用的线条、色彩等具有相似的意义,不仅可以对事物作结构性摹写,而且能够创造出它的图式。
维特根斯坦通过一个交通事故模型(或图解)来说明语句表达事实与图画表示事件之间的这种相似性。该模型由汽车、马路、行人、篱笆等组成,所有相关个体都被安置在特定的位置并以一定方式联系在一起,由此它们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一件事实。通过这个启示,他确信:一个语句表达一件事实与一幅图画表示一件事情不仅可以等同看待,而且两者可以相互转换。在图画中出现的各种个体可在语句中以相关语词(名称)来代表,在图画中个体之间的特定关联也可在语句中以特定方式把诸名称联系在一起。
语言与世界之间所以能够形成这种图式关系正是思想“投影”(Projektion)的结果。他认为,语言与世界虽彼此分离,但思想与事实、思想与语言之间却存在着直接联系。一方面,人们借助语言思考世界及其事物,世界通过思想“投影”以逻辑图画的形式在语言中表现出来,思想的过程就是通过语言推论世界的过程;另一方面,人们思考语言的意义,是通过“投影”把关于世界的逻辑图画传递给语言,从而使语言成为可能。这样一来,维特根斯坦就以“思想投影”这一概念填补了先天的基本语句与经验的原子事实之间的理论空隙,并从三元关系中确定了语言的本质:“语句传达给我们事态,因此,它必定本质上同事态相联系。而实际上这种联系就在于,它是事实的逻辑图画。”[1](4.03)
那么,思想存在于什么之中?思想是否由语词、记号来表达?罗素就这个问题向维特根斯坦提问:“一个Gedank (思想)是一个Tatsache(事实):它由什么组成,它的组成部分同被图示的事实的组成部分有什么样的关系?”对此,维特根斯坦回答道:“我不知道思想由什么组成,但我知道它一定有同语言中的语词对应的组成部分。其次,思想的组成部分同被图示的事实的组成部分的关系如何是个枝节问题。而查明这种关系是心理学的事……思想由语词组成吗?不是的!它是由心理成分组成的。这种心理成分同实在的关系和语词同实在的关系是同一种关系。”[2]
语言的本质与语言的意义是一致的,当断定一个语句是事实的图画时,指的就是一个有意义的语句。这就是说,在涉及事实的条件下,一个语句是否有意义,根本上取决于它是否成为一件事实的逻辑图画,亦即是否符合人工语言的标准。维特根斯坦据此来分析语言意义,就集中表现在对语句意义的条件进行考察,从而为“可说的”语句和“不可说的”语句之间、语句与非语句之间划分一条明确的界限。
(二)意义分析与证实方法
依据图式说的观点,维特根斯坦把语言表达式划分为名称和语句,名称代表个体事物,语句表达事态。这种划分不同于罗素的划分。罗素是将语言区分为名词、摹状词、主词、谓词、关系词、原子语句、真值函项等表达式。但是,“罗素在制定他的符号规则时,不得不谈及他的记号所指谓的事物”[1](3.331)。这有悖于人工语言的语形规则。而维特根斯坦将语言表达式仅仅区分出名词和语句,是因为他注意到,对于语言作为表达式的形式方面应同语言作为意义(包括指谓)的内容方面分别开来考虑。他的意义理论正是在“意义-指谓”和“名称-语句”这两组区分的框架上建立起来的。
关于名称这一表达式,维特根斯坦认为,名称只有指谓没有意义。而名称的指谓,只有当它处于语句中才是可能的。但是,罗素、弗雷格认定名称在语句中是有意义的,而语句的意义又取决于其构分即名称的意义。这就造成了一种错误循环。维特根斯坦通过“指谓与意义”的划分,就可以克服这一困难。名称对语句只是指谓上的联系,而语句在意义上与名称没有关系。他把名称比喻为“点”,把语句比喻为“箭矢”。“点”是没有方向的,因而没有正负之分。名称也是如此,它只有在语句中指谓对象,在语句之外既无意义又无所谓真假,它只是单纯的符号而已。由名称组成的语句具有正负方向,名称才获得指谓。
这样说来,有关意义的标准问题,就只存在于语句这种表达式中。语句具有意义,是因为语句和事实才具有图式关系。但语句没有指谓,是因为“事态可以描述,但不可命名”[1](3.144)。“语句记号”对事态不是命名关系,而是描述关系。语句是否具有意义,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形式方面的,二是内容方面的。
从形式方面来说,合乎逻辑是语句具有意义的先决条件。他说:“我们不能思想任何不合逻辑的东西,除非我们必须不合逻辑地思想。”[1](3.03)为了能够思考和表达合乎逻辑的东西,必须合乎逻辑地使用语言,因为只有在合乎逻辑的东西与合乎逻辑的语言之间才具有共通性,这个共通性就是逻辑形式。语句的逻辑形式是由构成语句的名称、单词以及它们按照逻辑语法-逻辑句法的应用所规定的。在他看来,有意义的语句必须满足的逻辑要求主要有以下两条:
一是语句的构分(名称)必须有明确规定。如前所述,语句的意义与名称的意义无关(名称无意义),但与名称的指谓有联系。只有当语句所由组成的名称有指谓,命题中的记号有具体规定,语句和命题才有意义。日常语言往往发生这种情形:同一个词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标记,因而它属于不同的符号;或者用不同方式标记的两个词,在语句中却是同样地使用的。这就违背了语句的构分必须有明确规定的逻辑要求。例如:“苏格拉底是同一”,这个句子中的“同一”一词没有一定规定,它作为形容词与它作为等号是不同的,把“苏格拉底”与“同一”结合在一起,就违反了逻辑法规。如果把“同一”当作等号,那么,“说两个事物是同一的,这是无意义的;而说一个事物与自身是同一的,就是什么也没有说”[1](5.5303)。因此,语句的构分有无明确规定,是语句有无意义的必要条件。
二是语句构分的结合必须合乎逻辑语法-逻辑句法。他指出:“语句记号在于这样的事实:它的元素即语词是以确定的方式结合在其中的。”[1](3.14)例如,表示“点”的字与表示颜色的字结合起来,在逻辑上是许可的。表示声音的字与表示“高”、“低”的字相结合也是符合逻辑规则的。像“这个点是红的”、“这种声音很响亮”等句子中的词的结合就是如此。但是,如果把“点”和“响亮”、“声音”和“红色”连结在一起,就出现对事实似是而非的叙述。这里,由于他把事物的物理特性和其他自然特性都归结为逻辑特性,就决定了“点”不能有声响,声响也不能存在于“颜色空间”中。
可见,从逻辑上确定语句有无意义,不外两种情形:一种是因为不合句法地把一堆词排列起来而产生无意义的语句;另一种是因为使用不当的词而导致了语句不具有意义。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形而上学命题就是由于把本来无意义的词组合在一起而出现的似是而非的命题。此外,一个词在某个语句中是有意义的,而当其出现在别的语句中,如果将其省去并无损于该语句,则它必定是无意义的,因此,他主张用“奥卡姆剃刀”即“记号经济原则”将其清除。
从内容方面来看,语句意义的根据在于可证实性。依据逻辑条件可以确定语句有无意义,但要表明语句意义的根据所在,只有从语句与事实的联系中去解决。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图式说的直接引申。语句因其代表事态才成其为语句,因而也才具有真假。
1.语句的意义与语句的真值。意义概念与事态概念如此紧密相关,决定了具有一种正意义的语句所表达的事实是存在的,具有负意义的语句所表达的事实不存在。这样,他把语句意义问题和真值问题等同了起来:一个语句如果是真的,它就把某些事态的存在传达给人们,因而它具有正意义;如果它是假的,它就告诉人们某些事态不存在,所以它具有负意义。意义不论正负,都表示语句有意义,只不过表示的方向不同罢了。但是,如果肯定或否定一个语句(命题),一点也不能把事态传达给我们,那么,当我们无论肯定还是否定语句时,等于什么也没有肯定或否定。这样的语句无所谓叙述,无任何意义可言。语句的意义在于指出事实的存在和不存在。
2.意义标准与证实方法。揭示了语句意义的根据所在,语句意义的标准也就呼之欲出了。维特根斯坦与罗素都同意把“可证实性”作为语句的意义标准:一个语句,不论真假,必须有可能被证实为真的或被证实为假的。具有这种可能性的语句就是有意义的语句。反之,如果一个语句既没有可能被证实为真的也没有可能被证实为假的,它必定是无意义的。进而言之,怎样证实一个语句的真假,就是要找到证实这个语句的方法。例如,爱因斯坦在建立广义相对论时,从理论上判断恒星光线经过太阳近旁,由于太阳引力的作用,会出现弯曲现象。对此他提出在日蚀时可以使用照相的方法给予证实。因此,爱因斯坦关于光线弯曲效应的结论具有可证实性,是有意义的语句(论断)。由此表明,可证实性作为意义标准,就是指语句(命题)必须有其证实方法。
语句的逻辑标准与证实问题被并列为语句意义性的两个基本条件,也是进行意义分析的两个基本方法。按照这两种方法,在人类语言中就只有自然科学的语句兼备这两个条件,符合人工语言的意义标准。而形而上学的语句无真假可言,是无意义的,因而是不可说的。
(三)意义标准与“重言式”
维特根斯坦运用上述条件考察了逻辑语句和数学语句。与此相关的是真值函项理论的建立。他把语句划分为符合语句和基本语句(原子语句),认为一切有意义的语句的真值都可以根据基本语句的真值来确定,即复合语句是基本语句的真值函项;基本语句的真值条件在于它与事实的一致或不一致,或者说基本语句就是它本身的真值函项。按照这一理论,将各种可能的真值条件整理成一套“真值表”,他注意到有两种极端的情形。一种情形是:对于基本语句的真值的一切可能性,语句是永真的;另一种情形是:对于基本语句的真值的一切可能性,语句是永假的。在前一种情形下,语句是“重言式”;在后一种情形下,语句是“矛盾式”。这样,真值函项就包含了三种类型:语句(命题)、重言式和矛盾式。语句作为综合命题含有经验内容,在某些真值组合下为真,在另一些真值组合下为假。重言式和矛盾式是分析命题,对于这个世界无所叙说,没有任何经验内容。“重言式和矛盾式不是实在的图像,它们不表述任何可能的情况。”[1](4.464)据此,维特根斯坦就把一切逻辑和数学的语句都归于重言式,以确保它们的先天必然的真理性。
维特根斯坦认为,逻辑语句和数学语句作为分析命题,它们的记号无指谓,语句本身与经验事实无关,因而不带有意义(sinnlos),但它们具有真值,所以又不是无意义的(unsinnig)。这就是说,逻辑和数学的语句符合语形学,语形学只涉及形式语言中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不涉及符号与世界的关系。这两种语句的真值就是与语形学进行比较而来的。“逻辑语句的特殊标志是,它的真值是从符号本身得知的,这个事实包括一切逻辑哲学。非逻辑语句的真值或假值是不能单从这些语句认出的,这也是极其重要的事实之一”[1](6.113)。逻辑语句和数学语句作为符号体系的一部分,可用于作证明的形式,这正如"0"是算数符号体系的一部分一样,是不可或缺的。逻辑语句和数学语句表示世界的脚手架。这个事实显示了语言和世界的形式的逻辑性质。
由此可见,维特根斯坦比罗素和弗雷格进一步表明了逻辑和数学在形式语言中的地位和性质。这一观点也成为后来逻辑实证主义发展人工语言哲学的一个直接而重要的来源。
二、语言游戏论:从语言的应用中展示语言的多样性
当《逻辑哲学论》的观点正发生影响时,维特根斯坦因不能回答这样一个要害问题而感到困惑。这个问题是:如果语句都可以分析为彼此独立的基本命题,那么,两种颜色在视觉空间的同一点出现为何是逻辑上不可能的?比如:“这是绿的”与“这是红的”两个语句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说“这是绿的”,意味着同时指出,“这不是红的”、“这不是蓝的”等等,这实际上进入了有关颜色的语句(命题)系统。由此他开始怀疑:选择一种“僵硬的、形式的语言”并把它投影到世界上是否合适,进而走出《逻辑哲学论》的思想框架,进入自然语言哲学的研究领域。
(一)语言游戏与描述功能
维特根斯坦开辟这一新的研究方向,据说也是受到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研究方式的启发。爱因斯坦在建立狭义相对论时所采取的决定性步骤是,利用时钟并按照一定的规则在理想实验中对时间进行测量,从而确定“同时性”概念的意义。由此显示出来的方法论轨迹是:
(1)怀疑“同时性”概念的传统解释;
(2)把“同时性”概念放到世俗经验中去;
(3)通过经验考察来确定“同时性”的意义。
在这种方法的启发下,维特根斯坦对语言问题的考察,不再强调逻辑分析和建立人工语言,而是描述直接经验的语言,即从人的日常生活和经验中来研究人们实际使用的语言。这种经验性研究的结果,就是语言因其使用而成为可能。
自然语言就是我们实际应用的语言。维特根斯坦把“应用”区分为两个层次:“工具”和“活动”。首先,他对语言作为工具这一层次赋予了“语词”这种表达式。他说:“试想工具箱中的工具,有锤子、钳子、锯子、螺丝钻、戒尺、锅、胶、钉子和螺丝钉。词的功能正如这些物品的功能一样多种多样。”[3]这里,他用“语词”取代前期的“名称”,以区别于图式论中的“命名”,就是要表明:“一个语词的指谓是它在语言中的应用。”[3](I,43)但是工具只是代表履行某种功能的“能力”,语言的真正应用在于进行一定的活动。因此,他对“活动”这一层次赋予了“语句”这一表达式,并将语句的应用比作“游戏”这种活动,因为在他看来,游戏是一种完整的活动,它把“近乎只是目的”的工具的功能付诸实现。语言的意义就是在语言游戏的整体中表现出来的。语言游戏具有“第一性”的地位。
维特根斯坦提出“应用”概念来取代前期的“思想投影”,是为了要驱逐语言的“心理根源”,真正回到“语言唯我论”的基点上。但“应用”出自何处?是“意向”。他认为“意向”并不是超语言的心理过程,而是语言固有的内在机制。这里,他把意向完全归诸于语言,意向又可以通过语言的“阐释”表现出来。
“语言游戏”概念的引入,表明语言的意义不在于它同实在的关系,而在于它本身就是语言的实际应用,这正是应用说与图式说的根本不同之处。他举例说:让某人去买东西,交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5个红苹果”。店主看过纸条,就拉开标有“苹果”字样的抽屉,逐一找出5个红苹果,这就以行动“应用”了这些语词。“'5'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这里没有这种东西,只有'5'这个词的应用方法”[3](I,1)。语言的每一次应用就是一次语言游戏,语言的意义就只能通过对语言游戏的整体揭示出来。
对语言作动态性的考察,突出了哲学的描述性功能。他说:“哲学决不能干涉语言的实际应用;哲学只能终止于描述语言本身。因为,它不可能给语言任何基础。它对一切都顺其自然。”[3](I,124)作为描述的自然语言哲学不是提出某种理论,“哲学只是把一切摆在我们面前,既不作解释,也不提出什么”。[3](I,127)因此,哲学是描述的,不是说明的。
哲学的描述不同于经验科学的描述。这好比对“房间”一词的使用不同于客观地描写和说明一间房屋,它意味着以细致和琐碎的方式去表现语言的日常用法是怎么回事,显示出我们实际上怎样来使用语词和词组。哲学描述自然语言的用法,并不是追求一般性的“根本”规则,而是提供语言日常使用的个例,并对语言游戏的情景进行描绘和整理。从具体方法上说,一是“汇集提示”(Zusammentrage von Erinnergen)即搜集语言游戏的典型事例;二是“重新排列”(Ordnen)即对“坦然可见”的语言应用的范例进行分类整理。
维特根斯坦列举了他精心挑选的15种范例:“下命令和服从命令;描述一个对象的现象,或对它进行测量;根据一段描述,构造一个对象;报道一个事件;思考一个事件;形成和检验一个假说;用图表表示一个实验结果;虚构一个故事,阅读它;演戏;唱歌;猜谜;开玩笑,说笑话;解一道应用题;把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提问,思考,诅咒,问候,祈求。”[3](I,23)这15种情形,既是日常语言应用的范例,而且可以据此建立一切其余的游戏。
(二)“家族相似”与“生活形式”
“语言游戏”的概念意味着理解一个语句必须置身于一种语言活动的整体中,因而将语言分析为彼此独立的基本语句及其真值函项是不合适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本身既不存在共同的“逻辑形式”,也不存在相互独立的基本语句和复合语句。语言应用于特定的活动之中,各种应用之间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语言的意义不能脱离各种应用和上下文的关系而存在。语言的“这些现象以许多不同方式相互关联。而正是因为这关系或这些关系,我们把它们全称为‘语言’”[3](I,65)。
语言活动中的这些关系不能用“逻辑形式”来统摄,但可以用“相似性”来描述。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的本质不是“应用”、“活动”或“游戏”这类“共同性东西”,而是各种“应用”、“活动”或“游戏”之间具有相似关系,他称之为“家族相似”。因为正如在一个家族中,各成员之间不存在共同本质,但他们具有相似性,如:体型、像貌、气质等等以种种方式重叠和交叉。通过对各种语言的相似关系的考察,“我们看到各种相似关系通过交迭和交叉组成一个复杂网络;有时总体上相似,有时细节上相似”[3](I,65)。总之,“游戏形成一个家族”[3](I,67)。多种多样的“家庭相似”反映了语言的真实面貌。
与语言的相似性相关的是语法的不确定性。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游戏正如下棋、打牌一样,也有一定的机制并按一定的规则才能进行,语言游戏的机制和规则就是语法。语言的“本质是由语法表达的[3](I,371)”。但这里所说的“语法规则”同前期的“逻辑规则”不同,“规则”不是超语言的,而是语言活动的方式,它只能以实际使用语言的例子描述,对于“深层语法”的任何解释和说明都是多余的。他说:“语法不告诉我们语言应当怎样构造,以便履行其目的,对人类产生某种作用。它只是描述而决不是解释符号的应用。”[3](I496)在他看来,语法给出语言用法的多样性;语法确定我们使用语言的自由度。
大致说来,维特根斯坦关于语法规则的观点有三:第一,一种语言游戏是有规则的,但规则并不决定语言(语词和语句)的具体的实际的应用;第二,语法规则是约定的,有其相对稳定性,但不是刻板的,它又具有随意性,甚至在游戏过程中调整;第三,服从一条规则是“纯粹实践的”活动,就是说,即使不懂一种游戏规则,也可以进行这种游戏,人们可以在进行语言游戏的过程中了解语法规则。
(三)“哲学疾病”与治疗方法
通过对语言的实际应用进行的描述性考察,维特根斯坦仍然将传统哲学划出有意义的范围。只不过这种划分有着不同的意义罢了。前期他提出,哲学家不懂得“我们语言的逻辑”。后期他认为,哲学问题本身就不存在,哲学问题的提出,就意味着哲学本身出了毛病。因此,现在哲学的任务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消解问题。
他自称是哲学疾病的“医生”,密切注视着古今各种哲学问题的提出,而对哲学问题的提出及解决的方式更是特别留意。在他看来,哲学疾病产生于“语言闲置的时候”。“当语言休息时哲学问题就产生了”[3](I,38]。这是因为语言作为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就一定要在生活中显示出对生活的重要作用。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语言的休息或闲置。语言不发生作用或“空转”就没有效用,而这时就要导致对语言的误用。
误用语言首先在于忽视了语言用法的多样性。语言的效用是通过这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如果不注意这种多样性,而被表面上的“一致”所迷惑,就会在不同的语言习惯之间作出不恰当的类比。例如,有关物理对象的语言和有关心理对象的语言之间有着虚假的雷同。有些人混淆了这两种语言的用法,在两者之间作出错误的类比,硬是按照“指称说”来看待心理学的概念和术语,把诸如“思考”、“理解”这样的词与“桌子”、“石头”这样的词相类比而忽略它们的差异,以物理对象语言去解释心理经验语言,使心理学语词实体化,从而造成了哲学上的混乱。进而说来,对语言用法的误解来源于对语言形式的误解。因为日常语言有着不同的种类。就语词而言,就有名词与动词之分,如:“桌子”、“知识”、“感觉”等是名词,它们之间存在着“家族相似”;像“看见”、“期望”、“请求”等构成了动词的家族。语句中的家族相似也是如此。维特根斯坦指出,由于没有恰当地把握语言形式的这种“家族相似”就导致了对语言用法的误解。
形而上学的根源在于误用了科学语言。他说:“哲学家们常常在他们眼前注意一种科学方法,并不可避免地试图照搬科学所运用的方法来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这一倾向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来源,并且导致哲学家陷入黑暗之中。”[4]他认为,哲学家往往不满足于观看,总要去思索出“为什么”来,总是焦急地在哲学中寻找因果关系。这就不得不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而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就是使用自然科学的语言。以“心灵的理论模型说明心灵的活动”为例,“这方面可提出的问题是心理学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如果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因果联系,那么心灵的活动就会展示在我们面前。当我们对思想的性质感到焦虑时,我们错误地认为是关于一种媒介物的困惑,乃是由于莫名其妙地运用了我们的语言而引起的困惑”[4](p.19)。因此,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当作哲学的方法,把自然科学的语言当作哲学的语言来使用,就掩盖了问题的本来面貌。
哲学疾病究竟是如何从我们语言的使用中产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是由于我们使用的语言符号总是以各种方式(符号的纯粹中介、对逻辑的崇高化、特定的幻象等等)挡在我们面前,使我们脱离语词的实际使用,离开语言游戏的老家,走向了形而上学。对此,他开出的药方是:把语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日常的使用上来,也可设想或找到一种语言游戏来解除哲学家的精神负担。比如有人提出“什么是思想”的问题时,他忠告说,做一个关于“思想”的游戏吧!描写出有关“思想”活动经过的情况,看一看在怎样的情况下使用“思想”一词的。一旦这么做了,就会发现看看就够了,而不必发问什么是“思想”了。
又如,“私有感觉”一直是困扰哲学家的重要问题。笛卡儿以来的许多哲学家认为,描写感觉的语词所表达的只是说话人自己的私人感觉,别人不可能懂得这种语言,因而私有语言是存在的。维特根斯坦通过对心理语词的语法研究,认为哲学对“私人知觉”的谈论是犯了把语词的用法与非语言的事实相混淆的错误。他指出,像“我知道我疼痛”这句话,只是代替了疼痛行为,并非指称了私有感觉。首先,这里的“知道”只是意味着:我不怀疑我的疼痛,我的痛感是确定无疑的。其次,这种代替不可能是私下的代替,而只能是公共的代替。例如某人用记号"E"记下自己的某种感觉,这似乎表明私有语言的存在,但维特根斯坦反驳道:如果没有公共的标准,一个人如何能知道在不同时刻用"E"记下的感觉是同一种感觉呢?如果记录感觉的记号"E"或别的语词是可理解的,那么这些记号或语词作为语言的一部分就与个人的感觉没有关系。
为了彻底摆脱哲学问题的干扰,维特根斯坦反对拘泥于一种用法,特别反对用一种方式看事物和用一种定义确定语词的做法。他指出,即使有人认为他所采取的是一个语词的“单一”用法,仍会发现存在着许多边缘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一种用法会不知不觉地并入别种用法,以至用任何定义的方式来确定语词的适用范围都无济于事,从而导致新的悖谬。进而言之,对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和知识论来说,也可以发现有关“本体”、“认识”的一系列依赖于上下文的含义。这些含义之间存在着家族相似,找不到共同的东西,亦即不存在对于“本体”、“认识”的通用释义。因此,一切有关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判断都是无意义的和多余的。有意义的,只是它们在具体情境下的特定使用。
综观维特根斯坦的全部哲学活动,他作为“语言转折”的实现者,尽管在其前后期分别作出了两种不同的回答,但也不难看出作为贯穿于前后期的一般语言哲学的方法。
首先,“语言批判”既是哲学的本质,也是哲学的方法。他说:“哲学的正确方法是这样的。除了能说的之外,什么也不要说……这种方法大概是别人所不满意的,他们会感到,我们是在教他哲学。但是,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1](6.53)当然,在不同时期他采取的批判方法各有侧重,大致说来,前期注重“逻辑分析”,后期倾向“自然描述”。但无论前后期,他都一贯强调“哲学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种活动。一件哲学工作基本上是由阐释构成的。哲学的结果不是一些‘哲学命题’,而是使命题清晰”[1](4.112)。这种观点不免有失偏颇,他的语言哲学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论。问题是他从这一观点出发,就使语言哲学带上了浓厚的方法论色彩。特别是他的后期哲学为西方语言哲学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按照它,语言哲学就成了用来重新考察传统哲学问题,进而寻求新的哲学的方法论。
其次,从“语言-思想-世界”三元关系的构架来看,前期他对“思想”这一要素的理解是“活动”,而活动就是对语言意义的思考,它具有“投影”的功能,是使语言与世界得以连接的媒介。而三者的共同根源和形态是逻辑形式。但是,作为“语言唯我论者”,维特根斯坦不能容忍“思想”作为超语言的基础的存在,所以后期他一方面改用“应用”来替换“投影”,另一方面又引入了“意向”,并把“意向”归诸语言,认为“意向”是语言的内在行为,并通过语言的“阐释”表现出来。这里,不难看出他对“语言唯我论”的辩护非常勉强的一面,不过他以“意向-应用”来替换“思想-投影”,也有其拓展“思维”内涵的一面,客观上为发展自然语言哲学提供了生长点。在他以后的一些语言哲学家(如塞尔)就是将“意向”视为语言意义的一个重要机制的。
最后,维特根斯坦后期为了寻求各种语言用法的“家族相似性”,特别强调哲学研究应是一种“观光漫游”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哲学研究的多样性。应当看到,并不是所有哲学家都对他的“哲学漫游”感到满意,许多人宁愿严守界限分明的精确定义,擅长奇异的思辨,以及对专门术语和用法的嗜好。然而,也不可否认维特根斯坦试图突破传统哲学教条的樊篱,促使固守古老田园的学究们翻然醒悟。打开新的视野显然比沿用专一词汇所能看到的要多得多。他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我们不反对从各自的窗口去看事物,但切不可把丰富多彩的世界同某种单调的语法虚构相混同。
[收稿日期]2000-11-13
标签:世界语言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逻辑符号论文; 语言描述论文; 逻辑哲学论论文; 哲学家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