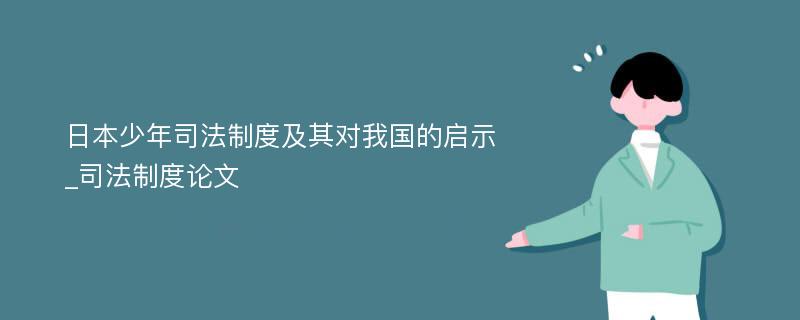
日本少年司法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启示论文,司法论文,少年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邻国日本的少年司法制度,从1922年制定第一部《少年法》(旧少年法)算起,①至今为止已经经过了整整九十年的实践和发展,相对而言比较成熟、完善。其中有不少地方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本文将从日本少年司法的历史发展、少年法的基本理念、少年司法基本特征这几个方面对日本的少年司法制度进行介绍,并在分析日本少年非行现状的基础上探讨日本少年司法制度对我国的启发,以期能够为我国在实践中适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提供参考,提高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水平。
一、日本少年司法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在日本除了面向成年人的刑事审判制度(刑事程序)之外,还存在少年审判制度(少年保护程序)和儿童福祉制度(儿童福祉程序)。因此,处理少年的非行与问题行为,②会同时涉及刑事程序、少年保护程序及儿童福祉程序。但如后所述,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少年司法实践,少年非行事件一般都是在少年法的框架之下优先适用少年保护程序。
日本第一部《少年法》制定于1922年。依据该《少年法》,未满18岁的人为少年,少年违法犯罪时,对其是适合处以刑事处分还是保护处分,检察官必须做出决定(检察官先议),被定为适合处以保护处分的少年将会被送往“少年审判所”这一行政机关接受审判。相对而言,刑事司法的色彩较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宪法的全面修正,日本在参照当时美国标准少年裁判所制度的基础上,在1948年对旧《少年法》进行了全面修正,制定并公布了新《少年法》,这就是日本的现行《少年法》。③新《少年法》分为总则、少年保护事件、成人刑事事件、少年刑事事件、杂则、附则六个部分。除附则外,正文共有61个条文。新《少年法》从实体处分和程序两个方面设计了一套完全区别于成年人的制度。因此,可以认为日本的少年法是日本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特别法。
根据日本的官方统计,日本少年刑法犯的被立案调查人数,在1951年为166,433人达到第一个高峰,随后在1964年达到238,830人形成第二个高峰,之后在1983达到317,438人形成第三个高峰。从1984年起一直到1995年,逐年下降,之后是有增有减。从2004年起继续呈递减状态,至2010年为127,188人,比2008年减少了4.1%。从人口比看来,从2004年到2010年也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④出现第一个高峰的时代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经济困窘、秩序紊乱,整个社会还处于混乱之中。第二个高峰的背景是,十多岁的人口激增,经济处于高度增长期,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代表的巨大社会变革加剧了各类社会矛盾。第三个高峰的背景是,日本进入经济发达社会,价值观出现多元化,家庭与地域社会的保护、教育机能变得低下,增加了各类犯罪机会。⑤
二、日本现行少年法的基本特征
(一)少年法基本理念
日本现行《少年法》第1条规定:“本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少年的健全发展,对实施了非行行为的少年,处以矫正性格和调整环境为内容的保护处分,同时对侵害少年以及少年福祉的成人刑事事件采取特别措施。”这是日本少年法的基本理念。因为少年的人格尚处于未成形阶段,其非行行为既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家庭和社会的原因,其自身也是受害者,而且少年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比起成年人更容易被教育和改善。因此,对少年的基本刑事政策不应该是科处作为报应的刑事处罚,而应该主要是科处以教育为目的的保护处分。国家的介入是出于对少年的保护,所以这一理念也被称为“保护主义”理念。该理念的理论基础是“国亲思想”,即少年走上非行道路的主要原因是其所在家庭未能正常发挥监督和教育职能,所以,国家就代替少年的家长行使亲权,为促进少年健全发展而采取一定的措施。
日本现行《少年法》所指的少年为未满20岁之人(《少年法》第2条第1款)。在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年龄的判断基准时间为作出处分的时间,而不是指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日本《少年法》的规制对象为少年非行,包括犯罪少年、触法少年和虞犯少年这三类少年的非行(《少年法》第3条)。其中犯罪少年是指14岁以上20岁未满,有犯罪行为的少年。触法少年是指14岁以下触犯了刑罚法令的少年。因为日本《刑法》规定未满14岁的人为完全无责任能力,⑥所以14岁以下的少年即使触犯了刑法,也不会被定为犯罪行为,于是这类行为就成为少年法的规制对象。虞犯少年是指14岁以上20岁未满,根据少年的目前表现,虽然还没有犯罪或非行行为,但是存在《少年法》第3条第1款第3项所规定的四个事由的其中之一,而且根据其性格和生活环境,在将来有可能犯罪的少年。这四个事由是:有不服从亲权者正当监护的习性;无正当理由不回家;与有犯罪习性之人或道德低下之人交往,或者经常进出猥亵场所;有伤害自己或他人的倾向。这其中每一种行为本身都没有触犯刑罚法令。可以看出,日本少年法的管辖范围,不仅包括犯罪少年的犯罪行为,也包括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未构成犯罪的触法行为,还包括连犯罪构成要件还都没有符合的虞犯行为。显然其规制范围比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要宽泛得多。这应该是与重在面向未来,教育改善失足少年,防止非行再犯,而不是针对过去,对非行行为进行惩罚这一日本少年法的根本宗旨有关。⑦
(二)少年司法程序概要
1.搜查、移送。犯罪少年事件一般通常都是首先由司法警察发现,经过搜查和调查,能够被处以罚金刑以下的事件都会被直接移送到家庭裁判所(《少年法》第41条)。能够被处以自由刑以上刑罚的事件会被移送至检察院。检察官在结束搜查和调查之后,认为有犯罪嫌疑的,与成人事件不同,不允许其行使裁量权,全部都要移送至家庭裁判所。这一制度被称为“全案移送主义”。除此之外,家庭裁判所的调查官和一般人也有义务直接向家庭裁判所报告或通报少年刑事事件(《少年法》第6条第1款、第7条),但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人发现了少年犯罪事件几乎都是通报给警察的。
触法少年事件首先适用《儿童福祉法》。警察接到通报后,发现该少年没有监护人或监护人的监护方式不恰当时,有义务向儿童相谈所或福祉事务所通报(《儿童福祉法》第25条)。只有在儿童相谈所或福祉事务所认为该事件适合接受家庭裁判所审判的情况下,该事件才会被移送至家庭裁判所接受审判(《儿童福祉法》第27条第1款第4项、《少年法》第6条第3款)。
虞犯少年事件的处理方式因年龄而异。如果该少年14岁未满,处理程序与触法少年几乎一样。如果该少年14岁以上18岁未满,发现者(几乎都是警察)可以选择移送给家庭裁判所或儿童相谈所(《少年法》第6条第2款)。如果该少年18岁以上、未满20岁,则全部移送给家庭裁判所。
可以看出,家庭裁判所在日本少年司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日本《少年法》之所以规定“家裁先议主义”,其目的就是要在程序上,尽量发挥家庭裁判所的作用,切实落实“保护优先”的原则。因为尽管大多数的少年事件从客观方面看来确实很轻微,但是这可能已经显现出少年较深的犯罪性,因此,有必要在详细调查之后,采取适当措施来预防。这时,最适合来做调查和判断的机关就是家庭裁判所,而不是检察院或其他搜查机关。因为日本的家庭裁判所除了裁判官之外还专门安排了职业调查官,由两者合作,共同处理少年事件。大部分的调查官,都拥有心理学、教育学或社会学的专业背景,可以从不同于裁判官的角度去发现非行少年的问题,有利于作出最适合少年改善、更生的处分。
2.受理与调查。经过上述程序,如果该少年事件符合审判要件,家庭裁判所就会受理。与成年人案件不同,少年事件即使被家庭裁判所受理,也不会立即开庭审理。家庭裁判所受理案件后,首先要做的就是“调查”。这被称为“调查前置主义”。调查分为法律调查和社会调查两种。前者先于后者,前者由裁判官自己来实施,主要是根据搜查机关送来的证据资料来判断审判条件和非行事实存在的盖然性。而后者则是由少年鉴别所和调查官来实行。如果少年事件是连同本人(在拘留状态下)一起被移送来的,家庭裁判所就会作出采取“观护措施”的决定,将少年送往少年鉴别所(《少年法》第17条第1款第2项)。少年鉴别所在对其进行收容的同时,运用专门的科学技术对少年的身心进行鉴定,之后将会把鉴别结果提交给家庭裁判所。如果少年事件仅仅是通过文件形式被移送过来,那么家庭裁判所就会命令调查官对该少年展开科学调查(也被称为社会调查)(《少年法》第8条、第9条)。调查官通过与少年及其监护人进行面谈、走访学校等方式对其性格和家庭环境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最终向裁判官提出调查报告书。社会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合适的改善措施,所以其乃是关于非行少年的犯罪危险性、矫正可能性及保护相当性等因素的调查。
裁判官参照调查官的报告和少年鉴别所的鉴别结果,综合考虑决定审判是否需要开始。少年审判的内容不仅包括该少年是否实行了非行事实(相当于刑事事件中的犯罪事实),还包括该少年是否具有在将来再次实施非行的危险性,为了预防再犯是否有必要对其处以保护处分。这一因素被称为“要保护性”。换言之,要保护性是对非行少年处以保护处分的实体法要件之一。因此,即使认定少年确实实行了非行事实,如果该少年不具有再犯的危险性,那么对该少年就不能处以保护处分。这也是少年法“保护主义”理念的体现。
其实在因不存在要保护性而决定不开始审判的事件中,有很多是因为在调查的过程中要保护性消失的缘故。为何会这样?因为调查官在调查过程中,不仅仅局限于调查,而且还会采取各种保护措施,例如在谈话中对少年进行训诫,通过与监护人、教师的接触和交流对少年的学习与生活的环境进行调整。由此可以看出,调查官的调查本身已是一种对非行少年进行教育和改善的一种积极手段。这也体现了少年法的“促进少年健全发展”这一目的。
当家庭裁判所认定,少年实行了非行事实具有较大的盖然性,而且经过上述的调查,发现有必要对少年处以保护处分时,就会做出开始审判的决定。至此,少年非行事件进入审判程序。
3.审判。家庭裁判所的少年审判由裁判官主持,出席的人员有少年、少年的监护人、付添人(相当于刑事事件中的被告方律师),以及裁判所的书记官。此外,一般家庭裁判所的调查官也会出席。根据需要,有时保护观察官、保护司、少年鉴别所的技官、少年的亲戚或老师也会出席。裁判官一般是一个人,如果案件比较复杂,就会由三名裁判官组成合议庭审理。关于付添人,虽然没有规定一定要是律师,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的付添人都是律师。在一些重大事件中,当少年的人身自由已经被限制时,如果少年没有具有律师资格的付添人,那么家庭裁判所必须为其安排律师付添人(国选付添人制度)。另外,《少年法》在2000年修订之后,关于重大事件,家庭裁判所认为有必要的话,检察官可以出席少年审判,以认定非行事实为限度,检察官可以阅读案件记录、证据,可以向少年以及证人提问题,可以陈述自己的意见(《少年法》第22条之二)。但这并不意味着检察官具有出席权。
少年审判与成年人审判不同,一般不公开(《少年法》第22条第2款),这是为了保护少年及其家属的名誉,以利于其日后回归社会。但这一制度现在已经出现例外,《少年法》在2008年通过修正已经导入被害者和遗族旁听制度。根据该制度,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经过裁判所的允许,被害者或被害者的遗族可以旁听少年审判(《少年法》第22条之四)。
审判的内容以非行事实的存否和要保护性的有无为主。少年审判应该是在亲切、温和的气氛中进行(《少年法》第22条第1款)。与日本的成年刑事审判所采用的当事者主义构造不同,少年法采用的是职权主义构造。这是因为少年审判的目的并不在于追究少年的责任,而是为了查明少年所存在的性格和环境上的问题,以决定能够改善和更生少年的最为合适的处分。因此,与采用当事人之间的对立程序相比,采用能够促使当事人之间进行合作的职权主义构造更为稳妥。
虽然《少年法》针对证据调查手续、证据法则没有作任何规定。但是,对于少年而言,即使是保护处分,仍然也是一种不利益处分,所以日本司法界普遍认为,少年审判也受到来自于宪法的正当程序保障(日本《宪法》第31条)。因此,裁判官在告知少年沉默权之后,宣读非行事实,充分听取少年的辩解,对非行事实的存否进行审理。当少年对非行事实的认定有异议时,可以通过传证人出庭等方式进行证据调查。这种证据调查由家庭裁判所依据职权开展,至于其具体方法和范围,则完全取决于家庭裁判所的合理裁量。⑧在日本,这被称为“非形式性”,主要是因为考虑到为了发现每个非行少年所特有的问题,制定出对其最为有效的改善更生处分,有必要灵活对待每个少年事件,规定过于严格的程序则不利于发挥少年审判的教育机能。关于证据调查,在司法实践中的一般做法是,在不违背少年法理念的范围内,大致参照刑事诉讼法。
如果家庭裁判所经过审判发现确实难以决定对少年应该处以何种处分之时,作为中间处分,可判处少年接受“试验观察”(《少年法》第25条)。试验观察,是指先保留最终处理程序,家庭裁判所的调查官将少年安置在其家庭或适当的社会机构里,在一定的期间内对少年的日常行为进行观察,并随时给予建议和指导,以便找出最为合适的终局决定的一种制度。家庭裁判所在实施试验观察的同时,还可以采取以下的一种或多种措施:制定遵守事项并命令少年履行;附条件地将少年交给监护人;委托相关合适的机构、团体或个人对少年进行辅导。试验观察的目的在于为审判收集资料。因为作为主要审判结果的终局决定——保护处分在原则上决定后是不可以再取消或变更的,所以要求家庭裁判所在作出终局决定时必须慎重,只有在充分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才能作出终局决定。
4.终局决定。经过审判,家庭裁判所对少年作出的处分决定可分为三类:不处分决定、保护处分决定、移送决定。
(1)不处分决定。当少年审判的结果显示,不能处以保护处分或没有必要处以保护处分时,家庭裁判所必须要对少年作出不处分的决定(《少年法》第23条第2款)。该处分决定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不能准确认定非行事实;二是虽然存在非行事实,但不存在要保护性。其决定要件与上述的审判不开始决定几乎相同。其不同之处在于,不开始决定是针对调查结果而言,而不处分决定是相对于审判结果而言的。
(2)保护处分决定。经过上述的调查和审判,结果显示适合判处保护处分时,家庭裁判所则必须作出保护处分决定。少年法共规定了三种保护处分:由保护观察所实施保护观察;移送儿童自立支援机构或儿童养护机构;移送少年院(《少年法》第24条)。
保护观察是指将少年放在社会内,由保护观察所的保护观察官对其进行指导、监督和帮助,从而促使少年更生的一种处分。由于保护观察并没有将少年关押于特定设施内,少年的自由没有被剥夺而只是被限制而已,因而这是一种社会内矫正措施。保护观察的期限一般是从家庭裁判所作出决定时起一直执行到少年满20岁时为止。如果执行到20岁还未满2年的,则执行2年(《犯罪者预防更生法》第33条第3款)。
儿童自立支援机构是对实行了不良行为或者有实行不良行为倾向的儿童根据其个性特征进行教育保护,以帮助儿童不再实行不良行为的机构(《儿童福祉法》第44条)。而儿童养护设施则是以没有父母或受虐待等原因而有待保护的儿童为对象,主要是出于生长环境的理由而为儿童提供养育保护的机构(《儿童福祉法》第41条)。少年(儿童)被移送至这两种机构后,将会由这两个机构依据《儿童福祉法》的相关规定来对其执行保护处分。《儿童福祉法》所规定的措施一般有:对儿童或其监护人进行训诫,或者让其提出保证书;让儿童或其监护人接受儿童福祉司的指导;帮助儿童认养父母或者让儿童进入儿童自立支援机构生活(《儿童福祉法》第26条、第27条)。
少年院是由法务省管理的对少年实施矫正教育的国立机构(日本《少年院法》第1条、第3条)。少年院有四类:一是初等少年院,用来收容大约12岁(特殊情况下可以包括11岁)以上16岁未满,没有明显身心障碍的少年;二是中等少年院,用来收容大约16岁以上20岁未满,没有明显身心障碍的少年;三是特别少年院,用来收容大约16岁以上23岁未满,虽然没有明显身心障碍,但是具有犯罪倾向的少年;四是医疗少年院,用来收容大约12岁(特殊情况下可以包括11岁)以上未满26岁,有明显身心障碍的少年。在少年院,主要以接受教育改造为主,不像在监狱一样要从事劳动。少年院的收容期限,原则上是到满20岁时为止。如果在作出移送决定时少年已经超过19岁,那么收容时间一般是1年。作为例外,如果存在特殊事由,家庭裁判所可以提出继续收容的申请,特别少年院可以收容至满23岁,医疗少年院可以收容至满26岁的青年(日本《少年院法》第11条)。
保护观察所和少年院属日本法务省(类似于中国的司法部)管辖范围。儿童自立支援机构和儿童养护机构归日本厚生劳动省(类似于中国的民政部)管辖,所以其福利性色彩较浓。少年院主要是收容并教育改善非行少年,关押期间要剥夺其人身自由。所以移送少年院乃是一种设施内矫正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对非行少年所判处的保护处分主要是保护观察和移送少年院,而移送儿童自立支援机构或儿童养护设施的情况则并不多。
(3)移送检察院。经过审判,当家庭裁判所认为该少年事件适合处以刑事处分时,则要将案件返送给检察院(《少年法》第19条第2款、第20条)。这一般被称为“逆送”。如上述,因为日本少年法采用的是“全案送致主义”,家庭裁判所对少年事件拥有先议权,检察院一般都是把少年事件移送给家庭裁判所。所以,家庭裁判所将案件反过来移送给检察院则被称为“逆送”。可以决定移送检察院的情形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经过调查和审判,发现少年本人超过了20岁,即超过了少年法的管辖范围,这时家庭裁判所必须要将该案件移送检察院(《少年法》第19条第2款)。
第二,家庭裁判所经过审判发现,该少年事件相当于死刑或自由刑事件,而且依据调查的结果,根据罪质和情节认为应该判处刑事处罚的必须要将该事件移送检察院(《少年法》第20条第1款)。在2000年以前,未满16岁在“逆送”范围之外,但在2000年《少年法》修订之后,所有的犯罪少年只要满足条件都可以被“逆送”。其具体条件为:该案件能判处自由刑或自由刑以上的刑罚;能够证实存在非行事实;具有刑事处分相当性。
关于刑事处分相当性,根据少年法的基本理念,应该说是尽量寻找处以保护处分的可能性,必要时才使用刑事处分。但是,在实际司法实践中,事件的社会影响比较重大、被害者的情感反应比较激烈的情况,也会被认为不适合保护处分,从而被移交给检察院。⑨
第三,《少年法》在2000年修订的时候,增加了一个新制度,即“原则逆送制度”。依据该制度,在行为时已满16岁的少年,因故意犯罪行为导致被害者死亡的,家庭裁判所必须要作出“逆送”决定。但是,依据调查的结果,综合考虑犯罪动机、形态,犯罪后的表现,少年的性格、年龄、一贯表现以及环境等因素,认为确实适合处以刑罚之外的处分时,作为例外可以不进行“逆送”(《少年法》第20条第2款)。创设该制度的旨趣在于,通过规定重大事件原则上属于刑事处分的对象,来促使少年学会自觉与自制。⑩
当少年事件被送到检察院后,检察院必须要对该事件进行起诉,进入公判审理程序。与中国的新《刑事诉讼法》不同,日本的《刑事诉讼法》中不存在未成年人犯罪特别程序,所以进入公判审理程序的少年事件会同成人的刑事事件一样,在程序上完全依照《刑事诉讼法》来进行。虽然程序相同,但在判刑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依据《少年法》,犯罪时未满18岁的,应该判死刑的处以无期自由刑(《少年法》第51条第1款);应该判无期自由刑的处以10年以上15年以下的有期自由刑(《少年法》第51条第2款);应该判处3年以上有期自由刑的,除缓刑之外,在其刑期的范围之内判处不定期刑,且短期年限不得超过5年,长期年限不得超过10年(《少年法》第52条)。另外,被判了自由刑而又未满16岁的,在满16岁之前可以暂不去监狱服刑,可以在少年院接受矫正教育(《少年法》第56条第3款)。
(4)终局决定的附加措施。家庭裁判所在作出终局决定的同时,还会作出调整环境命令或没取这两项附加措施决定。当家庭裁判所作出保护观察决定或移送少年院决定时,可以对保护观察所下达命令,让其对处于保护观察中或因附条件退院而接受保护观察的少年,采取各类调整环境的措施(《少年法》第24条第2款)。没取是指家庭裁判所在作出终局决定的同时,针对与犯罪或触法事实有关联的物品,可以剥夺少年的所有权,将其收归国库的一种附加措施。(11)没取的对象主要为非行行为的工具或因非行行为所得之物。
根据日本政府统计的最新数据,在2010年,家庭裁判所的终局处理人员为14万4985人。其中审判不开始的为8万3440人(占57.6%);不处分的为2万5723人(占17.7%)。被处以保护处分的为2万9515人(占20.4%),其中被处以保护观察的为2万9408人(占20.3%),被移送儿童自立支援机构的有299人(占0.2%),被移送儿童养护设施的有245人(占0.2%),被移送少年院的有3619人(占2.5%)。被移送检察院的为6062人(占4.2%)。(12)
5.上诉。针对家庭裁判所的保护处分决定,少年及其法定代理人或付添人以存在违反法令、重大事实误认或处分显著不当为由,在2周之内,可以向高等裁判所提出上诉(《少年法》第32条)。在2000年《少年法》修正之后,检察官针对自己出席审判的事件,以在非行事实认定中,存在违反法令或重大失误为由也可以向高等裁判所提出将该事件作为上诉事件来受理的申诉(《少年法》第32条之四)。上诉只能针对保护决定,关于家庭裁判所的其他决定,一般不可以上诉。
三、日本少年司法的最新动向
日本新《少年法》自制定以来,在20世纪的五十多年的时间内一直都没有进行过实质性的修正。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因出现多起重大恶性少年非行事件,在舆论的推动之下,日本国会分别在2000年、2007年、2008年对《少年法》进行了三次大的修正。
第一次修正是在2000年,这次修正的主要内容为:(1)加重了对少年事件的处分,例如降低了逆送年龄,由16岁降为14岁;规定了原则性逆送,针对重大案件将逆送的例外与原则关系颠倒了过来;针对无期刑,由强制性减刑改为裁量性减刑等;(2)加强了少年审判的正当程序,例如导入合议制,允许检察官参与审理,增加了保护处分终了后的救济程序等;(3)加强了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例如允许被害人阅读和誊写办案记录等。
第二次修正是在2007年,该次修正的主要内容为:赋予警察对触法少年行使强制权;将移送少年院的下限年龄由14岁改为大约12岁(大约是指可以包括11岁);增加新措施,接受保护观察的少年不遵守规定时可移送儿童自立支援机构、儿童养护机构或少年院;针对重大事件,导入公费为少年聘请律师制度。
第三次修正是在2008年,其主要内容是:将成人的福祉犯罪的审判权从家庭裁判所中划分出去;扩大犯罪被害者等预览、誊写办案记录的范围,扩大听取被害者等意见的范围;针对一定的重大事件,允许被害者或被害者遗族旁听少年审判。
以降低逆送年龄、创设原则性逆送制度、降低移送少年院的下限年龄为代表,这三次改正显然都具有处分严厉化的倾向。另一方面,以允许被害人阅读和誊写办案记录、旁听少年审判为代表,这三次改正还具有加强保护被害者权益的特点。这几次修改的直接原因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相继发生重大少年恶性事件,日本社会普遍认为,现行少年法对于少年过于宽大,对恶性少年犯罪应予以严惩。引发修正的间接原因可以归纳为:刑事司法整体出现严厉化倾向,强调保护被害者权益的运动蓬勃发展。
这三次修正虽然在很多地方都加重了少年法刑事化的色彩,但与此同时也对这些制度的适用范围和运作方式作了严格限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出现少年司法严厉化现象。据日本官方统计,从2001年4月1日至2010年年末期间,因故意犯罪致人死亡的属于原则逆送的案件的对象人员共有512人,其中最终有328人(64.1%)被逆送至检察院。(13)少年被送往监狱服刑的人员在1966年曾超过1000人,之后大幅减少,到1988年降至100人未满,2010年比2009年减少25人,降至29人。(14)这表明司法实践已经证明,尽管2000年以来的三次修正有严厉化的意图,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少年法的基本理念仍然被忠实贯彻,司法机关对少年适用刑罚仍然相当谨慎。
四、日本少年司法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以上简要地介绍了日本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特征以及近年来的最新动向。中日两国的相同之处在于,尽量通过教育、改善措施来促进少年犯罪者更生,与成人犯罪者相比增加了不少保护和教育的措施。但是,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则存在众多不同。日本的少年司法一如既往地秉承着“教育、改善”这一基本理念,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始终贯彻着保护优先主义,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刑事政策效果。借鉴日本的少年司法制度,有利于正确执行和完善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笔者认为,我国至少在三个方面应该向日本的少年司法制度学习。
第一,完善未成年人调查制度。日本《少年法》的最大亮点在于其调查官制度。家庭裁判所受理少年事件后,一般首先就会命令专业调查官对该少年展开科学调查。如上所述,调查官不仅要通过多种途径对非行少年的犯罪危险性、矫正可能性及保护相当性等要保护性进行调查,而且调查官在调查过程中还会采取多种保护措施,对少年的学习与生活的环境进行调整。可以说,调查本身也是一种教育和改善非行少年的途径和方法。调查制度顺应了现代刑罚的个别化原则,有利于实现个别预防目标,已被多数发达国家所采用。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由此可见,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调查制度贯穿于整个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同样也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还未能对此调查的主体、调查的内容、目标以及调查的规范形式作出明确规定。因此,今后可以借鉴日本《少年法》中的调查制度,通过司法解释等来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调查制度。
第二,增加非刑罚处分。除“逆送”检察院之外,日本《少年法》所规定的处分都是非刑罚处分。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66条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可以看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方针和原则与日本《少年法》的基本理念基本相同。而且这一原则在近年的《刑法》修正中也有所体现。2011年5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多种针对未成年人的宽大制度。例如:修改《刑法》第65条,将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排除出累犯适用范围;修改《刑法》第72条,扩大未成年人的缓刑适用范围;修改《刑法》第100条,免除了部分未成年犯罪者的报告义务。但遗憾的是,虽然我国对未成年人减轻了刑罚,但我国对符合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仍然基本都是适用刑罚,而并未在实体法中规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非刑罚处分措施。少年司法的目的应该以特殊预防而不是一般预防为主。德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针对未成年犯罪设立了实证研究项目,最后所得出的结论是:谦抑性、教育性的社会内处遇更有利于防止再犯。(15)因此,对未成年人有必要考虑设计符合其身心特点的类似于日本“保护观察”、“移送少年院”那样的非刑罚处分。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地促进未成年人改善和更生,减少再犯,从而实现特殊预防的刑事政策效果。
第三,完善非刑罚处分的程序正当性。在日本,保护处分等非刑罚处分由家庭裁判所根据少年审判的结果而判处,受《少年法》所规定的正当程序保护。目前我国虽然存在如“工读教育”、“劳动教养”等非刑罚处分。但是,其运用程序并不完善。由于这些处分往往被冠以“保护、教育”的名称,因而更容易掩盖其剥夺或限制少年人身自由的性质。所以我国在完善这些已有的非刑罚处分,或者是引进新的非刑罚处分时,应该树立正当程序的观念,加强探讨如何设计针对该处分的适用程序。但是,程序如果过度诉讼化,也会不利于教育、改善非行少年。对少年的程序权利保障到何种程度,这要和未成年人保护的目的以及实体处分所具有的限制自由程度相适应。(16)
注释:
①日本旧《少年法》内容参见田宮裕、廣瀬健二編:《注釈少年法》(改定版),有斐閣2003年,493頁以下。
②非行行为包括犯罪行为、触法行为和虞犯行为。
③日本现行《少年法》的内容可参见日本法务省网站http://law.e-gov.go.jp/htmldata/S23/S23HO168.html。
④参见日本法務省法務総合研究所編:《2011年犯罪白書》,http://hakusyo1.moj.go.jp/jp/58/nfm/n_58_2_7_2_1_1.html,2012年10月30日访问。
⑤参见日本法務省法務総合研究所編:《1998年犯罪白書》,http://hakusyo1.moj.go.jp/jp/38/nfm/n_38_2_1_5_1_1.html,2012年10月30日访问。
⑥日本《刑法》第41条规定:“不处罚未满14岁的人的行为。”
⑦参见川出敏裕:“非行少年に対する法的対応システムの現状と課題”,载石川正興編《犯罪学へのアプローチ》,成文堂2010年,200頁。
⑧日本最高裁1983年10月26日判决,刑集37卷8号1260页。
⑨菊田幸一编:《少年法》,北樹出版2003年,98頁。
⑩菊田幸一编:《少年法》,北樹出版2003年,99頁。
(11)没取不同于刑法上的没收。因为没取的对象还包括知情第三者所有之物(日本《少年法》第24条之二第2款)。
(12)参见日本法務省法務総合研究所編:《2011年犯罪白書》,http://hakusyo1.moj.go.jp/jp/58/nfm/images/full/h3-1-1-01.jpg,2012年10月30日访问。
(13)参见日本法務省法務総合研究所編:《2011年犯罪白書》,http://hakusyo1.moj.go.jp/jp/58/nfm/n_58_2_3_1_2_2.html
#h3-1-2-04,2012年10月30日访问。
(14)参见日本法務省法務総合研究所編:《2011年犯罪白書》,http://hakusyo1.moj.go.jp/jp/58/nfm/n_58_2_3_2_3_0.htm
l#h3-2-3-01,2012年10月30日访问。
(15)武藤謙治:“少年法研究の動向”载《犯罪社会学研究》第35号(2010年)167页。
(16)参见金光旭:《日本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最近的动向》,http://crimina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1853,2012年10月30日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