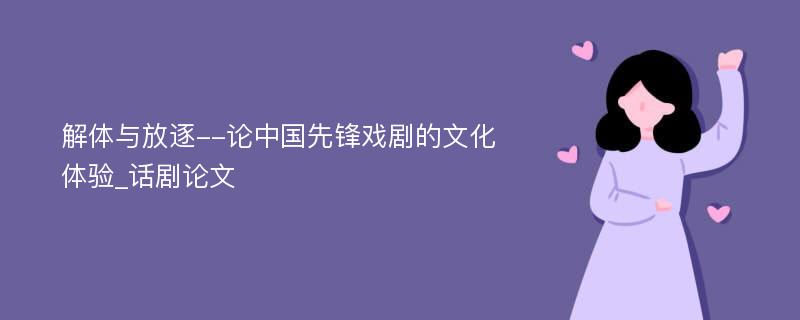
拆解与放逐——论中国前卫话剧的文化体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卫论文,话剧论文,中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某种意义而论,艺术人文与修辞的每一次调整,都具有前卫的倾向,但学术层面上的前卫艺术,则应该是指企图在艺术的整体上进行颠覆和革命的艺术实践,以非正统与背离传统为标的,实现前瞻式的操作话语实践。由此,论述中国新时期的前卫话剧,一般经验的艺术批评方式,显然难以阐释其中的核心问题,必须进行某种策略性的转换,而重新获得批判的话语权力。虽然话剧不同于其它个体性劳动较强的艺术门类,例如文学、音乐、美术,它是集体性的艺术,而且在形式与语言方面有较大的稳定性质,但这种前卫性,依然是显著且具有主体意识的。
中国话剧作为一种外来艺术,在不断民族化的同时,也体现了它的政治色彩。建国以来,中国话剧构成了大一统的组织系统,全国各大中城市都建立了演剧院团和相应的教育基地,在创作上遵循一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以现实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创作方法,演剧思想则独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由于将话剧纳入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观众大多抱着接受思想洗礼的态度,进入神圣的剧场。此时,演出者与接受者有着共同一致的目标,而处于相对和谐的政治文化氛围。但是,文革以后,中国政治经济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阵痛,文化领域也进行了重新调整以及组合,受此大背景制约下的中国话剧,也面临着一个崭新的命题:在娱乐分流的情景之下,话剧受众日益减少,话剧原先的运行机制的各种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在演剧指导思想上的僵化与单一,限制了话剧艺术的发展;加上外来现代派戏剧的不断传播,许多话剧工作者产生了激切难耐的现代焦虑感,他们以解放思想为旗帜,以内在获得释放之后的极度快感,进行了话剧艺术的大突围,对传统的主体话语权力发出挑战。
自80年《屋外有热流》开始,这种具有前卫激情的话剧冲动,一直贯穿到八十年代末期,才在极度逍遥与无尽补天的文化狂放之后,处于茫然失措状态。话剧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自觉理性批判精神,扫荡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及其流毒,继而以“精英意识”为标榜,站在文化批判的前沿,对中国社会的文化机制与国民性格,进行了颠覆性的价值批判与重估,甚至发展成为极端性的艺术势力,即文化激进主义,企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进行拆解,重新建构中国话剧的文化秩序,以及当代人文思想的“精神乌托邦。”
社会体制的大变革,给话剧艺术以外在的推动力量,也在总体上规范了它的发展方向,从某种意义上承载了历史转型期带给它的命运。和这种社会开放运动相适应,前卫话剧也开始了它的激进历程:
首先,是文体与修辞的艺术革命。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现代派,例如理论上的“心理分析”、“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符号学”、“原型批评”、“间隔理论”,流派上的“象征主义”、“存在主义”、“表现主义”、“荒诞派”、“贪困戏剧”、“偶发戏剧”、“残缺戏剧”、“环境戏剧”、“全景戏剧”、“即兴戏剧”,象一个巨大的自选商场,前卫话剧用短短的十来年把它演示一遍。象征、隐喻、荒喻、变形、无实物表演、意识流等修辞的大量运用,对舞台假定性与非幻觉因素的高度重视,对综合美学的追求,对人物心理空间多层次表现,诸如人的内心世界的外化,舞台时空的自由转换,灯光技术的广泛采用,对舞台造型的多媒介综合,观演关系的空间建构,这些崭新的艺术语言,汪洋恣肆地表达了自由的艺术观念,对中国话剧历史中的一元体系的基调和格局,进行了无情的艺术拆解,体验了文体与修辞革命的多元诱惑。例如高行健的《车站》,对传统的写实的叙事模式进行了瓦解,场面的异形化,同期独白,“公共汽车”、“等车的人”与“沉默的人”的符号式存在,滑稽、反讽、希望和厌弃等的言语性动作,都产生了一种叙事性的变异。又如《W·M》,对事件经过的极度淡化,采取散文化风格,作灵魂的内心独白,模拟音响、无实物表演及演出的整体化象征,都充分突出了假定性的舞台功能。这些对传统话剧文本与修辞美学的解构,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野人》、《魔方》等剧目中,以至到了八十年代后期,《狗儿爷涅》与《桑树坪纪事》同样承续了这种叙事体系的前卫性。《狗儿爷涅縏》对意识流、精神分析、隐喻、怪诞、象征、内心独白等现代手法的舞台化处理,以人物的心理活动作为结构手法;《桑树坪纪事》对戏曲表演艺术的借鉴,转台几乎成为舞台表现的灵魂,对舞台综合性的和谐运用,都是对沿用过久的单一的写实舞台的一种扬弃,也是对前卫性话剧美学的自我性确认。
其次,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正面逆动。前卫话剧以一种崇高的价值理性与美学中的精神启蒙话语,展开了热烈的政治社会批判,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具有意识形态批评性质的权力规范。人类的最初文化与最后文化,从终极关怀的角度,其实都是对人类生命尊严的捍卫与承诺,是对人性的一种自恋与升华,因此,前卫话剧对与其人性理想不相适应的主流意识形态部分,进行挤压与排斥形式的抗争,甚至将其贬为亚文化,或者反文化,用带有朦胧象征意义的调侃与黑色幽默的讥讽,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正面的拆解,例如《W·M》中,深刻地表达了人在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愤怒的呐喊”,由于内心空虚与失落所产生的愤懑与反抗情绪。在“冬”景里,大风雪把门刮倒了,知青们又冷又饿,唱起了“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和“天上布满星”,此外,“偷鸡”,用刊有社论的报纸当月经纸,对“不须放屁”的议论,都是对主流性意识形态的进一步瓦解。前卫话剧对政治社会话语中心的直接切入,进行煽动性的权力拆解,既表明了它的激进批判热情,努力造就新的政治社会素质,也说明了它高举的“精英意识”,具有某种程度的非现实性,与国情相脱离。
新时期的前卫话剧,作为当代人文叙事的一种抒情方式,与总体人文生态与语境是密切相关的,从主体上受到它的限制。从文化的角度而论,由于历史断裂与文化转型,从现代向后现代与人文化向自然的人文化的转换,人本身经历了从现代人向后现代人人格位移所带来的巨大灵魂震颤,于是,众声喧哗,急切表达对于社会和人生的各种宣言,认识世界和情感传达的角度发生了变化。“人文化”的全面泛化,必然导致单元意义的主导文化为多元化的边缘文化所替代,而且发生周期性的类型转换。与此总体性的文化生态与语境相适应,中国前卫话剧表现了完全不同的文化姿态。中国话剧原有的三种“文化母语”系统,一是本位话语系统,即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后殖民方式的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以及国人在现代意识中对传统的漠视,它的影响力已完全今不如昔,仅局限于行为话语系统之中;二是非本位话语系统的西方传统文化,在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进入中国的,由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现代派艺术大面积的闯入,而退避到次要的位置,只表现在操作话语系统;三是曾经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理论,也因为受到先锋思潮的排挤,削弱了它的观念影响力量。由此,八十年代的中国前卫话剧,实际上处于某种程度的母语断裂状况,即话语系统失语,无法确认母语,各种文化背景话语没有规则;意识形态失语,本位话语系统和国家意识形态没有成为文化的主体指导思想,而外来的现代派艺术却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心,因而非位;叙事结构空语,面对多种人文和修辞迷惑,艺术选择十分艰难,似乎什么都会又什么都不会,故而叙事表达失范。新时期的前卫话剧,在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母语文化的时空汇点上,既有了多方选择的可能,又有了多方选择的困惑,而且急于求成和出新,缺乏真正独立的艺术思考,从布莱希特、梅耶荷德到格罗托夫斯基、阿尔托等二十世纪以来的演剧理论模仿和照搬了一个遍,缺乏浑厚的现实底气和充足的吸纳功力,使前卫话剧在光怪陆离的舞台呈示中,失却一些学术意义上的艺术创新,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难免出现逐奇而不能真正创新,探索而缺乏胆识的现象。
其实,中国前卫话剧在艺术革命的狂放热情中,仍有某些折衷主义的形态,在言词与文本之间有所保留,即使是“艺术极端势力”的被称为“野孩子”的,声称要打破艺术与技术界限的行为艺术家也是如此。因为前卫只是相对的,在边缘文化频繁性的更替中,前卫很快就会变成古典。另一方面,新时期的前卫话剧“母语”无序,致使艺术行为有些错乱,甚至处于失控状态,人们传统的经验方式被消解,因而造成了历史时序、文化约定与抒情对象的非本位化与文化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权威地位受到了动摇,但在这一切的背后,其深层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母语”的潜移默化的死死纠缠,前卫话剧表面上可以对之不屑一顾,绝不领求传统文化认同的体面,但在心理深处仍维系着传统价值体系的人伦指向,渴望得到社会公众理解的传统理想,他们的激进主义态度,实质上是一种对“乌托邦”冲动的自恋或者“利比多渲泄”,对中国传统文化“母语”仍有所依赖。此外,中国前卫话剧与西方先锋文化存在着一个“时差”,中国前卫话剧所模仿与照搬的所谓西方前卫艺术,其实在西方早已成为古典,或者正在走向古典,这样就必然使中国前卫话剧的先锋锋芒有所减弱。从实际情形来看,新时期的前卫话剧更多地是针对沿袭已久的戏剧文化环境的观念与认识意义,而较少真正的风格与形式意义。在这其间,前卫话剧也出现了变奏的现象,即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某种融合,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现实主义的回潮,但实质上是中国前卫话剧一次质的升华,从单纯的文化批判激情上升到文化反思的高度,例如《桑树坪纪事》、《荒原与人》、《大雪地》、《中国梦》等,也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与国际通则的艺术接轨。
二
八十年代末期,中国前卫话剧产生了一条严重的裂痕。由于前卫话剧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正面拆解,它的非现实性,对政治社会的价值批判和重估,遭到了国家主体意识的反抗而导致毁灭性的打击,但它在短暂的沉默以后,又以一种新的文化姿态重新粉墨登场,其中突出的表现是,前卫话剧不再以非叙事性的抽象艺术语言,达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性主题进行极端的政治反拨,而是以一种近似于日常生活的大众化态度,放弃对个体生存意义的观念性理解与自我英雄主义的崇拜,开始填平激进主义的沟壑,以构筑新保守主义的艺术城邦,从政治社会批判的前沿向文化的后卫撤退。如果说八十年代的前卫话剧更多的是对异己的否定,那么,九十年代的前卫话剧则成为自我的诘问,以中国大众文化意识为自身的精神价值建构的对象,体现了特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这一阶段的前卫话剧,其艺术关注的重心从现代与后现代的冲突,转移到了中心与边缘的冲突,而且从中心对边缘的控制,走向了边缘对中心的消解,对主流意识形态采取逃避的态度,使深度人文叙事模式出现平面化,正如美学家贝尼尔·贝尔所说的:“碎片或部分代替了整体。人们发现新的美学存在于残损的躯干、断离的手臂、原始人的微笑和被方框切割的形象之中,而不在界限明确的概念,以及在不同类型应有不同表现原则的概念,均在风格的融和与竞争中被放弃了,可以说,这种美学的灾难本身实际上倒已成了一种美学”(引自《资本主义文化矛盾》95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前卫话剧实现对自我的放逐,成为与其所指断裂的一种能指游戏与世俗化的自由嬉戏,不再严格遵循使真理与秩序合法化的那个绝对支点,只是前卫艺术家的一种日常感受与实际行为,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绝对的间隔距离,体现为大众生活化的自由兴趣,其艺术本文注重事件的描述,而不直接表达内容的意识形态企图,呈现为平民化的游戏状态,例如林兆华在《浮士德》说明书中写的:“对我们来说,最辉煌的演出无非只是一场焰火,一场光和热的游戏罢了,而且转眼就会云消烟灭。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观众能加入我们的游戏,与我们一起动动脑子,与我们一起共享快乐。”其内容可以是任意选择,如果是名著大多加以重新组合,容纳一些现代的意识和情节,也许就是我们目前所经历的此刻“活着”本身,表现为先锋锐气的弱化与对日常生活的亲近。例如《鸟人》,通过对北京一群养鸟人的生命众相的具有荒诞意味的描写,呈现了一幅都市世俗社会的人的存在状况。动物保护学家是个残杀珍稀动物的“刽子手”,研究心理变态学的学者是个心理变态者,而一群追求悠闲的人们,为了某种利益自愿地住进了实验病院,成了一群“鸟人”,在轻松可笑的具有游戏性的叙事中,感受到普通人生的喜怒哀乐。再如《情感操练》一对年轻夫妇在深更半夜操练情感,生发出“贫贱夫妻百事哀”的苦涩;《同船过渡》也传达了难言的人生况味,老水手的骤然离世,产生出一种人生的悲凉感。其他剧目《旮旯胡同》、《OK、股票》、《泥巴人》、《疯狂过年车》,都不再与主流意识形态过于密切,而注重发掘世俗生活中的平凡真理,使九十年代的前卫话剧在重拾写实主义艺术话语的过程中,经过对艺术文本叙事性的再度变异,体现了文化保守主义的言路策略。
如果说八十年代的前卫话剧,艺术当事人是一种热切的情感投入,甚至是声嘶力竭地发表自己的政治与艺术批判企图,九十年代的前卫话剧,则普遍具有一种理性的态度,对于人的现实生活的一种冷静审视,在不动声色的客观叙事中,使描写的世俗人生具有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崭新体验,这说明了九十年代的前卫话剧,在变革八十年代前卫话剧政治社会批判热情的情景中,不再纠缠沉重的生命感和历史感,已然放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控制,开始进入了主流文化的边缘部位。
这种放逐,与其说是一种无奈,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策略,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悄悄疏离,前卫话剧不再以先锋姿态为荣耀,而是对平凡人生作公众认同的任意选择,而不作观念形态的评判,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漠视中,更不采取正面反抗的政策,甚至许多前卫话剧当事人直接搬演外国戏剧,以避免国内题材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涉,例如北京“蛙”实验剧团的《犀牛》,中央戏剧学院“鸿鹄”创作集体的《秃头歌女》、《风景》、《等待戈多》、《阳台》等。九十年代的前卫话剧,艺术的力量不来自于激烈的批评冲动,而是大多依据个人最平凡的生活经验,以及个体对这一种最平凡经验的直觉性敏感,主流意识形态反而成了一种边缘之物,无法切入直感性的生活本身。这在94年度演出的许多剧目中,就清晰地表现出来,例如《极光》、《离婚了,就不要来找我》、《古塔街》、《热线电话》,既不是去树立英雄偶象,也不对处于转型时期的现实生活作肯定与否定的评判,而只是对复杂的现实人生作一种多元而真实的审美观照,让观众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去补充和发展它的生命况味。
九十年代前卫话剧的放逐态度,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疏离,使自己处于一种较为主动的艺术位置。前卫话剧不必小心翼翼地去逼近主流意识形态,而可以实现在文化“后卫”座位上的自由抒情,确立自我主体与世俗生活的对应关系,也沟通了与观众的前所未有的感应通道,表明了九十年代前卫话剧的一种新的文化心态与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放逐策略更具有社会文化的话语颠覆性质,它不是赤裸裸地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正面性的冲撞,而是以退为攻,对主流意识形态抱着冷淡的情绪,艺术本文通过叙事结构变异、世俗化的审美主义原则,将主流意识形态形容为完全是人为造成的、无法还原为生活本身的东西,而难能进入九十年代前卫话剧的话语体系,更不可能扮演观念主角的角色,更大能量地瓦解主流文化的话语霸权地位。在前卫话剧轻松愉快的自由嬉戏中,甚至如孟京辉的《思凡》碎片式的拼凑,剧中和尚和尼姑爱意缠绵时,前面打出一横幅“此处删去365字”,这种黑色幽默式的能指游戏,使人们意识到主流文化并不是前卫话剧的必要之物,也并不是只有主流文化才能提供唯一的真理,世俗生活的自由情趣远比主流政治社会思潮来得亲切可爱,而且扎实牢靠。在这种放逐中,信仰本身表现得是如此的飘忽不定与幼稚软弱,所谓深刻的价值还不如自身正在经历的庸碌生活更有意义。这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瓦解,确实是极具有挑战性的。与此同时,九十年代的前卫话剧,为了弥补主流意识形态流失的空白,又向大众制造了一个个极富人情味的与新的人格力量的世俗偶象,来满足人们各种感官形式的审美需要,如《留守女士》里的乃川,《美国来的妻子》里的元明清,尤其是后者,既是古老的又是传统的,既有些清高又有些落魄,这些文本形象本身并不深刻,其实也无须深刻,但是却拥有迷人的感性渲染力;它不对社会人生的各种价值观念作评判,只是在对历史的轻轻呓语,或者对现实的冷冷描写中,充满了温馨的吸引力,令观众再次经历日常生活中难以言传的微妙情感体验,达到一种对人们现实人生中精神创伤的疗治作用,以及调整现实意识形态的功能。这种世俗偶象的确立,使前卫话剧具有了一种新的艺术气象,能够在文化的边缘位置,愉快地切入大众的精神兴奋焦点,从而取得了一种艺术话语的主动权,成为人们自我慰藉与自我寄托的情感力量,在与主流意识的放逐情景中,重新获得了自我生存的自觉。由此,九十年代的前卫话剧,放逐了主流意识形态与历史,却建构了新的世俗化的生活模式,重新成为大众认同的对象,从“后卫”与“边缘”的部位回归到大众日常意识的关注重心。
九十年代的前卫话剧,由于放逐主流意识形态而实现了自身的文化策略,出现了一个艺术现象,即舞台技术手段的高度发达,诸如声、光技术,使技术逻辑形态优先跨入主体意识的前沿,在舞台时空获得合理化与合理化地位的前提下,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技术手段主体化、技术现象本位化、技术局部合体化的总体倾向,使前卫话剧更具有舞台化的魅力,例如徐晓钟导演的契诃夫名剧《樱桃园》,一会儿在小剧场,一会儿在花园,一会儿在走廓,舞美、灯光、音响、化妆等都作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处理,采用多空间演出形式,增强了观众对戏剧活动的心理参与,寻求戏剧技术空间的新因素和新美质。灯光、音响等不仅仅是一种话剧演出的辅助手段,而且成为一种艺术抒情符号,有独立的表情达意作用,在有些前卫剧目中甚至成为叙事主题。技术手段的高能化,使前卫话剧在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激情批判之后,在不断创造出世俗偶像的同时,使舞台意象更具有惑人的感官体验。
新时期的前卫话剧,在经历了与主流文化的拆解与放逐以后,从大突围到守“后卫”,从营构激进主义到消解批评热情,似乎又回到了原地,进入了被某种人格预设了的“文化宿命”。自然,这种循环怪圈,不是一种历史倒退,而是更符合国情的质的成熟。但同时也说明了当代人文知识分子把握历史文化叙事话语权力的艰难。从某种意义而论,由于东方政治与东方文化的特殊性质,人文知识分子一直没有很好地获得对意识形态的主动支配权,由此,有必要建构前卫话剧当事人的人格话语,有比较强的独立意识,具有自我精神调节的机制,完善自身素质结构,作好进行文化叙事作业前的人生观、美学观的人格准备,建设一种足以对自身进行正常统制的观念意识形态运作话语,同时,建构一系列专门的型态操作话语,即在确立新的叙事模式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新的观念话语表述系统的意思结构与新的术语概念演示系统的赋诗语境,不断调整的叙事结构与话语系统,以适应历史文化的新的变化。人文知识分子要把握意识形态的体验权力与表达权力,成为它的发言代表,更好地传达历史文化的真正声音,前卫话剧还必须摆脱经济基础上的“后殖民文化自身心理”,以较强的民族自信力去对待西方外来的戏剧文化,不至于崇洋媚外而迷失发展的方向,纠正西方强势文化与东方弱势文化的倾斜度,以达到相对的平衡,也才能在世界总体人文构成中真正确立自己应有的位置,使前卫话剧不但成为话剧形态的先导试验,而且更成为体现民族性格的精品艺术,从而获得人文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