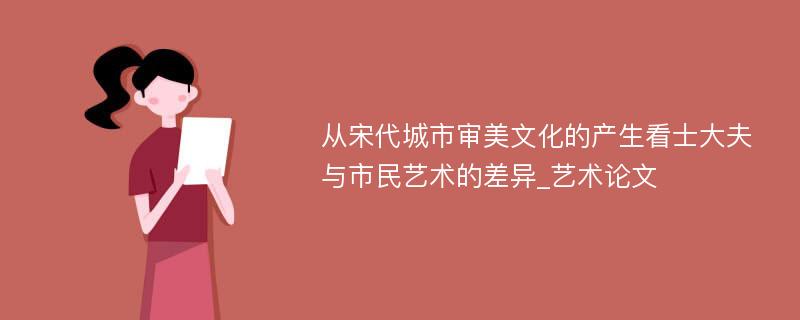
从宋代城市审美文化的产生看士大夫与市民艺术的不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大夫论文,宋代论文,市民论文,艺术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城市虽然产生很早,但是,代表城市文化的市民阶层却是直到宋代才真正得以萌生。因而,中国城市审美文化的真正发生也是在宋代。宋代由于农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促进了工商业的发达,加上大力兴修水利,水、陆两种交通比以往更为通达,促使粮、盐、茶、绢帛、铁器、香料、药材、瓷器等农产品、日用品的流通交易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各地以镇为中心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墟市、草市、集市、庙会等方便交易的场所。这种商品流通和定期的集市贸易,激发了不少新兴市镇的产生和旧有市镇的不断兴旺,使宋的大地上出现了星罗棋布的大小城市。同时,由于严重的土地兼并、自由土地买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封建社会中期社会阶级组成的分化,打破了以往封建地主和农民之间的较为单一的阶级关系,出现了自耕农、小商贩等新的社会人口组成,他们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并陆续由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一只城市市民的大军诞生了。他们过着与以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生活完全不同的五彩缤纷的城市生活。伴着清晨早市的各种叫卖声醒来,又在灯红酒绿、丝竹管弦的夜市中结束一天的生活。酒楼茶肆、勾栏瓦舍、花街柳巷、坊院池苑,处处芸集着新生的城市居民,他们交易买卖、饮酒品茶、听曲观舞、赏景游玩、狎妓嫖娼、斗鸡赌博。如果遇到年节时令、婚丧育子等大事,则应时而乐、依礼而行。一年四季时物不重,风景各殊。生活丰富多彩,繁杂中蕴含着滋味,忙乱中体现着情趣,追求中包孕着满足,失望中燃起新的希望,笑声中饱含着甜酸苦辣,不知不觉中送走匆匆岁月。虽然他们只是普通百姓,但城市却因他们的存在而日益繁荣。诸色杂卖、百戏伎艺、三教九流、阡陌市井,构成了宋代市镇生活的风景画。那热闹的场面、喧嚣的人群、婉转的音乐、飞舞的彩幡、斑斓的服饰、诱人的美食、紧张的关扑、优游的戏耍,一切都是崭新的,既不同于平淡、单调、纯朴、机械的农民生活,也不同于刻板、冷清、奢侈、放纵的皇亲贵族生活,也与风雅、飘逸、闲散、清淡的文人士大夫的生活迥然相异。因而,它所表现出来的是另一种前所未有的审美文化风尚,这种审美文化风尚当然不是空中楼阁,它是与当时的社会大文化背景,与当时理学的发达、艺术的兴盛、工艺的杰出和日常生活中丰富的审美情趣密切相关的。
宋代在中国封建史上虽不是一个最为强盛的朝代,但却是一个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皆有巨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当时文明的主要创造者就是新兴的城市市民,这些原来只靠自己灵巧的双手默默无闻地创造着物质文明的人,到了此时不仅已经开始拿起纸笔,记下自己的先进的科学经验,写下了《木经》、《喻浩》、《营造法式》(李诫)、《农书》(陈旉)《蚕书》(秦湛)、《水利图经》(毕功绩)、《新仪象法要》(苏颂)、《数书九章》(秦韶九)等一批我国最早的科技著作,而且也开始在文学艺术和日常生活领域中创造出一些源于这个阶层的社会生活、符合他们的审美理想与情趣的独特的审美对象,形成了代表宋代城市审美文化的审美物化产品。文学领域,与当时异军突起的文人士大夫的词同时发展起来的有大量的反映城市市民生活的话本、南戏、曲子词、诸宫调等生动活泼的新形式。绘画领域,在李成、范宽、李唐、马远、夏珪这些独步一时的画家以他们的苍劲淋漓的笔墨为中国文人画开创新天地的同时,以《清明上河图》为代表的描摹世情的民间风俗画也创举性地登上画坛,其纯朴生动的内容、细腻写实的手法,不仅是宋代城市生活的艺术再现,而且是宋代城市审美文化物化产品的典型。在造型艺术领域,另一颇能反映宋代市民审美品味的门类是雕塑艺术。雕塑艺术在宋代已不再为士流所重视,但却仍然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不少名垂青史的杰作,它们的作者是当时市民阶层成员中的艺术工匠。这些人虽然没有文人士大夫那么系统的艺术指导思想,但却以自己真挚的情感,独特的视角,塑造了体现时代风貌的一尊尊栩栩如生的雕像,山东长清灵岩寺中那些生动传神、将内心世界与外在容貌、刚劲的骨架与纤柔的衣褶完美结合的罗汉雕像,反映了当时工匠艺术水平和审美概括力的高超;同样,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中那43尊体态修长、娴雅端秀的侍女彩塑,也表现了宋人对女性不同于唐人丰满肥胖的审美风尚;这种新时代的审美精神也忠实地出现在四川大足石刻的观音雕像上,那里的尊尊身段窈窕、情态柔媚、衣饰富丽的观音塑像,与其说是神圣的宗教人物,不如说是现实中的美女化身,无怪人们会称之为“媚态观音”了。音乐舞蹈等艺术领域中,虽然宫廷与士大夫都在试图进一步以“道统”规范其内容与形式并将其理论化,但市民阶层却把它几乎作为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蓬蓬勃勃地发展起各种自由轻松的形式。尽管那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唱赚、小曲、杂剧、舞队与正统的艺术相比显得俗气,并被认为缺乏艺术性,但它却是广大市民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是他们对于生活热爱与投入的自发表现,因而也是他们快乐舒心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工艺领域,宋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成果,除了官方的手工业机构外,大量的精美产品是出自那些心灵手巧的百工艺匠。在大小城市的大小货行中,绫罗绸缎等纺织品、金银铜漆等器物、竹石玉雕等装饰物以及名满天下的各色瓷器琳琅满目,其高超的工艺水准、独具一格的审美特色,反映出宋代市民日益成熟的新的审美观念体系。在宋人的日常生活中也无时无刻不充满着对于美的追求,他们力图在其穿着、饮食、居住、行游、玩赏等各个领域都表现得更为完美,在详细记载宋代都市生活的《东京梦华录》、《梦粱录》、《都城记胜》、《西湖老人繁胜录》和《武林旧事》中,随处可见这方面的描绘。
上述各类审美文化的物化成果已经体现了宋代城市人审美文化的特点,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对当时这一新生的社会阶层正在成熟并形成特色的审美观念体系有一定的把握。如果说传统艺术可以分为雅艺术与俗艺术的话,士大夫阶层与市民阶层则可以说是这两种不同风格的艺术的代表。从二者的区别中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出市民艺术及其审美文化的特点。大体上讲,二者的区别有以下几方面:
1.在艺术创作的目的上,士大夫注重的是自我表现和陶冶性情,市民阶层追求的则是自我娱乐和欢快喜庆。所谓自我表现,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言志”,即将文艺作品当成作者言情表志的结果。《尚书》中“诗言志,歌永言”的说法几乎尽人皆知,自司马迁起,更把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名作看成作者抒发心声之所为,从孔子的《春秋》、屈原的《离骚》到韩非的《孤愤》乃至《诗》三百,均为“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1]。以《离骚》为例,是由于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2]。西汉扬雄已明确指出:“言,心声也;书,心画也。”[3]此后的士大夫文艺理论家在谈到艺术创作的目的时,大都一再强调其自我表现的功能。如东汉王充的“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4],唐韩愈的“不平则鸣”,宋张戒的“言志乃诗人之本意”[5],明汤显祖的“因情成梦,因梦成戏”[6],清叶燮的“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7]等。所谓陶冶性情,是与自我表现相辅相成的,艺术家通过作品表达自己的心志,欣赏者则通过对这些作品的鉴赏而获得情感的陶冶和心灵的升华。这一点古代美学家也曾多次谈到过,如管子的“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8];荀子的“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9],“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10];北周颜之推的“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11]等。与这种基本上属于个人艺术创造、主要表现个人心志情感的个体性的士大夫艺术不同,宋代兴起的市民艺术是一种集体性的艺术,广泛流行的文学、戏剧中的主角,不是某一人物的再现,而是市民阶层人物的化身,他们的身上凝聚着该阶层成员所具备的普遍性特征,人物形象的包容性、随意性也很大,演员们在每一次演出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加入新的东西。再如以《清明上河图》为代表的绘画,没有突出的个人角色,而是繁盛的城市生活众生相的写照。士大夫的词曲、书画等艺术的创造与欣赏,一般是单独进行的,这样便于将创作者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市民艺术的特点是,创造与欣赏往往同时进行,如说话、杂剧、鼓子词、诸宫调、傀儡戏、影戏、歌舞等艺术均是创作演出与观看欣赏同时进行的,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随时可以彼此交流沟通,悲哀喜乐、笑语欢歌融汇在一起,台上台下同时沉浸在对那些既是艺术人物、又在现实中似曾相识的人的故事的感动之中。无论对于创造者还是欣赏者来说,通过艺术所要达到的是一种自娱自乐。可见,市民艺术与审美文化的主要功能是把人从日常生活的常轨故辙中解放出来,消除城市生活的紧张与约束,使人在娱乐之余重新振奋起精神,全力去负担新的生活,因而它重在消闲,而非升华。
2.在艺术创作内容与生活的关系上,士大夫的作品往往与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讲究远离凡尘;市民阶层的艺术作品则紧密地贴近生活,随时取材于生活。士大夫艺术家在谈到艺术创造的来源时,并不反对艺术取材于现实,然而却非常强调艺术与现实的不同,这种不同有两方面,一是艺术要高于现实,而非对现实的简单再现,如刘勰的“称名也小,取类也大”[12],荆浩的“删拨大要,搜妙创真”[13],郭熙的“千里之山,不能尽奇;万里之水,岂能尽秀?……一概画之,版图何异?”[14],徐渭的“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栽”[15],郑板桥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之别等。二是现实中没有的事物,艺术家通过想象可以创造出来,即通过艺术家的神思、灵感得到富有独创性的艺术形象,如虞世南所云“书道玄妙,必资神遇”[16],严羽所谓“诗有别材”、“诗有别趣”[17],李渔主张的“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耳”[18]等。与之相比,市民艺术是现实中市井生活的一种投影,同现实生活的联系非常紧密,不仅其题材选取大多来源于日常生活中最平庸、琐碎的细节,而且它所描写的也多是小商贩(茶坊、酒肆、杂货行的小老板)、落魄书生、市井小民(诸如艺人、伙计、小工、测卦先生等)乃至娼妓、小偷、无赖、强盗等不起眼的小人物,正是因为来自于这些身份、地位卑微而情感、欲望又较比粗俗、本能的小人物的小事,几乎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相差无二,故更容易打动人心,产生强烈的反响。也正因为许多市民艺术就诞生于勾栏、瓦舍、酒楼、茶肆之中,它不可避免地带着大众现实生活中那些粗俗、愚昧、调笑甚至荒唐的东西。并且由于新兴的市民对于人类生命中许多盲点(如贪婪、偏执、迷信、滥情等)还没有自觉的认识,将其真实地带到了其艺术之中,所以使刚刚产生的市民艺术缺乏士大夫艺术的高雅,然而它也很少有士大夫艺术的那种无病呻吟。
3.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士大夫大多强调写意,主张为求意境而得意忘象;市民阶层的艺术作品则大多采用写实手法,将现实生活忠实地再现于作品之中。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与上述两点紧密相关的,正由于士大夫强调艺术的自我表现和超凡脱俗,所以在表现手法上特别注重写意,注重寻求和表现艺术形象以外的东西,以至于言与意、象与意、实与虚的问题成为中国古代艺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且得意忘象、以形写神、避实就虚、寻求韵外之致则成为士大夫在艺术表现上的共识。而市民艺术不仅内容上忠实生活,表现手法也多是朴素的写实方法,话本中的人物语言、绘画中的生活场景、舞蹈中的动作姿势等,几乎没有多少艺术提炼,而是原汁原味地用到艺术作品之中,因而市民艺术缺少士大夫艺术的那种耐人寻味、回味无穷的特点,重在现场的娱乐效果。
4.在艺术创作的态度上,士大夫认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必须标新立异,具有独创精神和个性;市民艺术则尊重传统,不习惯打破先制且非常大众化。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都有如何面对传统、尤其是前人的优秀成果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士大夫艺术家大多认为,只有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打破传统,独创一格,才能达到最高的艺术境界。从陆机的“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19]、刘勰的“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定古法”[20],到叶燮的“人未尝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与闻其言者,诚可悦可永也”[21]、石涛的“我自用我法”[22],倡导独创精神,始终是士大夫艺术创作中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与之相反,市民艺术则注重继承传统,这并非说市民艺术不注重创新,只是它不习惯于将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也不会因为一些小的改变而彻底打破传统。这主要是因为市民艺术在产生、演变过程中,经过长年的实践、许多人的积累,已经形成一定的程式。以戏曲艺术为例,它是在民间说唱、歌舞、伎艺的基础上,吸取了诗词等艺术的优点逐渐形成的,是一种把歌唱、舞蹈、念白、音乐伴奏、人物造型、砌末道具等各个方面有机巧妙地结合起来的艺术形式,每一出戏曲,根据其情节的需要,其中角色的唱、念、动作,与之相配合的音乐旋律、节奏,所相应的服装、道具乃至脸谱勾勒,都是相互联系,有一定名堂的,因而即使是著名的演员,在对其进行改革时,也必须有通盘考虑,不能擅自妄为,否则便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哗众取宠。因为市民艺术大多是集体性的,所以个人意志对它的影响比较微弱,形成独特的风格比士大夫艺术更为困难。
5.在对于艺术规律的总结和把握上,士大夫有一定的艺术理论,并能自觉地对各种艺术规律进行总结,有不少艺术品评、艺术批评和艺术鉴赏的著作传世。因而,今天我们关于古代艺术和美学研究的工作大多是在其基础上进行的。与之不同,由于市民阶层对于艺术作用的理解和他们在文化知识、自觉意识等方面的欠缺,因而对其艺术进行系统的理论概括、整理的很少。当然,他们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也注意把握和遵循一定的艺术规律——即程式,但却未能对这些程式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以戏曲音乐中宫调的“声情”为例,经过宋杂剧、元曲的多年发展,每一宫调均形成了其特殊的“声情”,如仙吕宫:清新绵邈;南吕宫:感叹悲伤;中吕宫:高下闪赚;黄钟宫:富贵缠绵;正宫:惆怅雄壮;道宫:飘逸清幽;大石调:风流蕴藉;小石调:旖旎妩媚;高平调:条畅滉漾;般涉调:拾掇坑堑;歇指调:急并虚歇;商角调:悲伤婉转;双调;健捷激袅;商调:凄怆怨慕;角调:呜咽悠扬;宫调:典雅沉重;越调:陶写冷笑,等等。市民艺术家不仅懂得准确地使用各宫调,而且强调将“声情”与“辞情”相统一,烘托剧情,渲染气氛,绝不会以悲痛哀伤之曲用于欢快喜庆之辞。但对于这些宫调为什么会具有该种声情,其历史渊源和音乐特性的研究却很少。
6.在艺术欣赏和品评上,士大夫的态度大多比较审慎、挑剔;市民阶层则比较宽和、包容。曹丕《典论·论文》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文人对他人艺术品的欣赏评价上,纵观历代文学、艺术批评,多数批评家不仅对于同代艺术家的态度非常挑剔甚至苛刻,就是对前人的艺术成果也采取审慎的评点,不仅将艺术品分为三六九等,而且能进入神品、得到共赞的作品少得可怜。市民阶层对于自己的艺术所表现出的却是包容与热情,对于他们来说,艺术是他们休闲娱乐的一种手段,是他们反观自身生活、寄托未来期望的一种形式,只要能表现其真实的喜怒哀乐、安慰其枯燥乏味的悲苦生活,即使内容上有缺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他们也并不特别在乎;尽管形式上比较粗糙,他们也照样可以接受。
7.在艺术风格上,士大夫的艺术风格趋于简洁、高远、疏淡、清雅,没有很强的地域性差异;市民阶层的艺术风格则繁缛、通俗、娇艳、浓丽,地域性差异很大。李白作诗崇尚“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司空图的《诗品二十四则》中,“冲淡”、“高古”、“典雅”、“洗炼”、“自然”、“含蓄”、“疏野”、“清奇”、“造诣”、“飘逸”、“旷达”、“流动”等一半都是讲的这种风格,而宋、元以后,特别是明代,这种风格更得到高扬。尽管如梁启超等人指出的,士大夫艺术也有南北差异,但其地域性特点远不如市民艺术突出。市民艺术的各类艺术品、工艺品都有强烈的地方特色。以陶器为例,不仅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瓷窑的风格不同,而且北方、南方地区内各个瓷窑也因其独特的釉色、款式、纹样、质地,而显示出百花齐放的多样风格,河北定窑的胎质坚细、花纹精美,河南钧窑的色斑窑变、形式优美,陕西耀州窑的刚劲有力,刀锋犀利的刻花、剔花、镂空等是其特有的装饰手法,河北磁州窑黑白对比鲜明、富于层次感的特点,江西景德镇窑类玉似冰、极富盛名的“影青”,至今未发现窑址的哥窑的如鱼子纹的“开片”的绝世之作,浙江龙泉窑的苍翠色泽和独特的“出筋”手法,福建建窑的细如毫毛或呈羽毛状的美丽的褐色斑纹,江西吉州窑独创的木叶、剪纸粘贴技巧等等,都形成了一方独有、别具一格的风格。此外,不同地域的戏曲和曲艺活动也是各具特色。因而,从这一点上讲,士大夫艺术的审美风格虽有一家的个性特征,但却缺少地域差别;而市民艺术的审美风格却因不同的地域特征而显得更为丰富多彩。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2]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3]扬雄《法言·问神》。
[4]王充《论衡·超奇篇》。
[5]张戒《岁寒堂诗话》。
[6]汤显祖《玉茗堂尺牍之四·复甘义麓》。
[7]叶燮《原诗·内篇上》。
[8]管仲《管子·内业》。
[9]荀况《荀子·大略》。
[10]荀况《荀子·乐论》。
[11]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
[12]刘勰《文心雕龙·比兴》。
[13]荆浩《笔法记》。
[14]郭熙《林泉高致·山川训》。
[15]徐渭《画百花卷与史甥,题曰漱老谑墨》。
[16]虞世南《笔髓论·契妙》。
[17]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18]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
[19]陆机《文赋》。
[20]刘勰《文心雕龙·通变》。
[21]叶燮《原诗·内篇上》。
[22]石涛《大涤子题画诗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