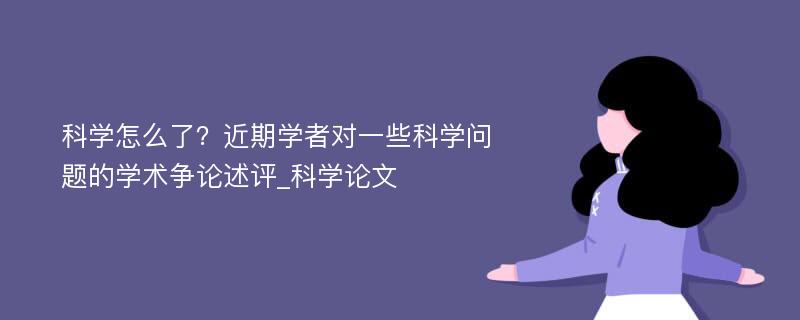
科学到底怎么了?——综观近期学者有关科学一些问题引发的学术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学者论文,近期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一篇《宣言》引出的
陶世龙
一个被称为“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的“学术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近日引起了一番议论,找来读了一下,发现确实颇有些令人费解之处,譬如:
“近年来,科学文化领域主要的矛盾表现形式,已经从保守势力与改革开放的对立,开始向单纯的科学立场与新兴的人文立场之间的张力转变。”
这个“科学文化领域”具体内容是什么?广而言之,科学研究、教育、新闻媒介乃至其他许多工作均可囊括在内,因为如《宣言》所说,“科学的技术已经渗入到人类生存的所有方面”。其“主要矛盾表现形式”的转变,则应是针对社会实体的行为而言,从宣言的口气来看,所指当是中国大陆社会(其他论断也是如此),不知这个研讨会对中国大陆社会的有关情况作了那些调查研究,而能作出如此高度概括的结论?
像“单纯的科学立场”,“新兴的人文立场”,“张力转变”这类用语,《宣言》作者心里应该是明白的,但没有明白的表达出来,使人不知所云,从而各人可以各有自己的理解。《宣言》中类似的用语颇多,怪不得别人议论。
“科学的技术已经带来了不可逆的社会后果,继续坚持僵硬的科学主义立场不利于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从上下文来看,这里的“后果”只能理解为负面影响,也就是说科学的技术本身(不是科学主义)出了问题,而何为“僵硬的科学主义立场”,《宣言》的制定者也无界定,平常对大家已有共同标准的事物,理解尚可有不同,何况《宣言》中不少用语的涵义,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有人认为《宣言》在反科学也不足怪,重要是需要用自己的言与行来证明自己真的是出于对科学的维护。(略)
关于反科学与反科学主义
无名氏
在中国,五四以后我们试图循着西方的道路完一个强国梦,我们试图离弃自己的传统,远远地跟在西方的屁股后面,在西方文化的垃圾堆中寻拣着破烂,试图从中发现一些至尊宝,用来完我们的强国梦。就象每一个垃圾拣拾者都梦想着拣到金镏子一样,当我们发现了黄色的东西就会兴奋不已,以致于我们把驴粪球也当做是金旦旦。于是,德先生、赛先生就这样被中国发现并当作至尊宝被供奉在殿堂上了!
陶世龙
如果说反对科学主义是反对把科学当成宗教,当然有道理,但许多所谓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其实是针对科学,于是什么“科学的技术已经造成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科学技术使战争变得残酷”,”科学技术正在颠覆人类的道德伦常”之声,甚嚣尘上,乃至说科学造成了“20世纪中国人文精神的萎缩与专制主义的横行”。有人回顾了”(中国)90年代几次最有影响力的学术争鸣,如关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问题、关于人文精神问题、关于儒学的复兴问题、关于学术与思想的关系问题以及学术史的规范问题等等讨论,这些会上的主流意见,给人的印象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失误与教训,都是由于科学越出了自己的范围。”(如何解读“唯科学主义”?)科学,可谓罪莫大焉!
批所谓“科学主义”,实际上是转移了目标,真正应该追究的是导致这些问题发生的社会人文因素。这一点,那些对科学和文化的历史有研究的学者,应该是很清楚的。
按专家的查证,科学主义本不过是指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一种与人本主义对立的思潮或运动,有过争论,不过多是在哲学界或学术界内进行,一般人并无此概念。为什么现在却似乎是“科学主义”满中华,甚至到了关系着国运的兴衰,需要群众性围剿呢?
美国科学史家杰拉尔德·霍尔顿
分析了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如此辉煌的美国,反科学现象仍如此普遍、反科学势力仍如此强大的多种原因:如美国成年人中绝大多数人仍不了解科学;宗教势力强大;有些人害怕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不良后果,如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科学家在美国的社会地位的上升,引起另一部分人的不满;如此等等。在反对科学的队伍中,还有一些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他们认为科学同神话和小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因为科学变得日益深奥、复杂、抽象、难以理解,而对科学产生反感;有些浪漫主义的人文主义者认为现代科学强调理性、客观性、非人格化,使人生失去了魅力;有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甚至主张取消男性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科学,代之以女性主义的或东方神秘主义的类科学、边缘科学。
方舟子
(“反科学”文化人)他们一方面享受着现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另一方面却出于一己的私利或者无知与恐惧妄图阻碍科学的发展。如果把他们置于他们所喜欢的远古洪荒时代,他们的死亡只是瞬间的事。人类之所以能生存至今,全赖知识的积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自然的了解与控制的增强。这一过程不可停止,因为无数已知和未知的灾难还在等待着人类。人类的发展不会因一些疯子的呓语而终止。科学的研究方法给予我们的是一个可预测可控制的世界,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除此之外只有冥想与祈祷,而那些部是无效的。
谁能给公众带来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是他们这些反科学文化人,还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研究工作者?我想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决策权可能被掌握在无知的人手中,从而导致科学技术的停滞。而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落后就意味着一切的落后。要预防这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科学的普及,包括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科学研究方法与思想的普及,要让公众知道科学研究的结果是怎样得到的,一些看起来神秘的东西是怎么回事。要用知识去消除无知所带来的恐惧,要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去驱除神秘主义。
科学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正是促使无数科学研究者投身其中的原因之一。虽然多数人也许只能做出微不足道的贡献,但也是科学长河的一朵浪花。我们不容任何人阻止或者玷污她,为了我们的信仰和价值。
关于“反科学”的含义
方舟子
“反科学”在现在的两个最常见含义:一、否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否定科学研究可以揭示客观规律,而把科学知识当成主观的“社会建构”;二、与科学界为敌,正如反科学文化人的上海宣言所说的那样,把广大科技工作者当成敌占区。正是在这两个含义上,我们认为他们的思想、言论是反科学的。
coconut
我觉得“反科学”在当前至少有如下含义,各位也可以另外多补充可能的含义。
1.反对科学定律,认为那是假的。(评论:这种“反科学”当然可笑,科学定律确实可错,科学也在试错中前进,但像牛顿定律、相对论、量子力学理论都有可靠的经验基础和逻辑论证(不完全),它们是最优秀的理论。但也不是没有人持这种“反科学”的观点,比如江湖科学爱好者,就想轻易地突破。还有人提出“反引力”的理论,有的是在认真探索,有的是胡闹,要区别对待。)
2.反对科学的后果,如技术的某些应用,认为它们有时不利于个人或者社会的某些发展。如用高科技研制大规模杀人武器。
3.反对科学家的行为,认为他们行为不轨。(评论:如反对科学界的骗子,认为他们败坏了科学的声誉,又因为他们掌握话语权,于是这种声音被对方称作“反科学”,即“反对我就是反科学”,就像“反对我就是反党、反国家、反人民、反革命”。这种“反科学”是呼吁科学界保持纯洁,有利于科学的发展。李森科案是一个典型。)
4.反对(唯)科学主义,被一类人简称(有意地或者无意地)为“反科学”。(评论:唯科主义把合理的科学思想无限延伸到其他领域,问题不在于这种扩充是否合理,而在于声称者把未来的事情当作已经完成的事情来对待,把它们作为理由。更要命的在于,他站在科学一方,他是解释者,他唯一地占有真理。唯科学主义者不承认现实的科学从其他学术或者文化中曾经或者将要吸收任何营养。唯科学主义者把人类取得的一切进步都装进自己的腰包,声称全是科学的功劳。并声称或者隐含着声称未来人类如果取得什么进步,也要把功劳全计在科学自己的身上,与其他任何事物都没有关系。唯科学主义的逻辑是,真理都属于科学,科学都是真,我代表着科学,我代表着真理,与我争论就是与真理过不去。当然,唯科学主义者从没有说得如此清晰。)
5.反对现有科学的某些形而上的假设,或者反对现有科学的若干政策,目的是呼唤一种可能的新科学,引导科学向更人性的方向发展。(评论:这种声音被保守派称为“反科学”。科学是要发展的,科学观也要变化。)
6.反对科学的方法及其他形而上学假设,但不反对具体的科学知识。(评论:如一些宗教国家和团体,不接受无神论的主张,但他们却接受一般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教育,也能搞出科学发明,在理论科学上也有建树。科学家可以信神。)
7.与科学本来无关的互相吵架,把对方称作“反科学”,目的是夺取话语权。
关于科学的局限性与科学思想方法
宫敬才
人类源于斯、长于斯的自然被无情摧残,生态环境遭到致命性破坏,苟活于其中的人,就其生存的质量而言,可能无法与生存于自然状态中的野兔子相比。
我们用已知的科学知识干预自然,征服自然,在干预和征服过程中,科学知识马上暴露出自己的局限性,因为当自然未被知晓的习性或层面发挥作用,对人得寸进尺的干预和征服进行报复时,科学显得无能为力和无所适从。科学的职责是认知自然,它确实尽力而为且成就卓著,但相对于未被知晓的自然的习性或层面而言,它并没有尽到职责。科学在这里应负的责任是揭去自然未被知晓的习性或层面的神秘面纱,变未知为已知。实际上,这是强人所难,因为,从时间结构上看,变未知为已知是未来的事情,而科学只能说明过去和现在。从这个意义细心思量可知,当面对有限对象中的有限层面或有限习性时,科学本身并没有过错,因为它已尽到了说明的责任。但是,科学的思维方式、科学为自己承揽的总体职责和科学发挥的作用告诉我们,它把自己的有限性移植到对象的有限性(实际情况是,对象的习性和层面是无限的),并把移植的有限性固定下来,把现在与未来拼结在一起,抹煞了现在与未来的时间差,把已知和未知搅揉在一起,未知在假象的意义上变成“已知”(真把未知变为已知有待未来时日),实践以这样的“已知”支配行为,在达到预期目的的同时出现生态危机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生态危机不是与人道主义思想整体有关系,而是与其中的科学部分有关系。生态危机不是与科学的所有部分有关系,而是与科学中隐含的一系列内在矛盾有关系,说生态危机“挑战”人道主义,不是说要抛弃人道主义,而是说生态危机给人道主义提出了应该反思的问题;说生态危机与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中的科学部分有内在关联,不是说科学没有功绩和存在价值,而是说科学也有自己未能涉足的地方,科学应当在自己的反思过程中讲明这一点,因为这同样是科学的职责,生态危机正是从应讲明又未讲明的陷阱里产生出来的。
陶世龙
其实环境污染乃人类活动的结果,在科学未出现以前,即已发生,近一二百年来污染的加剧,有人类发展工业生产的影响,但科学和技术不等于工业,而且治理环境,包括环境质量下降的察觉,还都亏有了科学和现代技术。环境问题的出现和战争的发生,以及道德的沦丧,都应从人类社会自身或者说“人文”去检讨,而不是对科学横加指责。
赵南元
自从生命在地球上诞生以来,生命就在不断创造和改变着生态,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也时时光顾,原始的藻类把地球上还原性的大气变成了氧化性的大气,这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造成恐龙灭绝的巨大生态灾变恰恰开辟了哺乳类的新纪元,使人类的诞生成为可能,这些都是在地球上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发生的。
人类很多民族的传说中都有关于大洪水的记载,但是对于这场生态灾难的原因却有不同的说法。西方的圣经认为,是由于人类的堕落使得上帝发了怒,降下洪水淹死了所有人,只留下相信上帝的诺亚一家。中国的大洪水却是自然发生的,靠着自己的力量两代人不断试错,最后由大禹找出正确的方案,成功治理了洪水。远在“人道主义”出现之前,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存在东西方不同的看法。这种区别可以称之为“诺亚观念”和“大禹观念”的区别。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生态的变化也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以气温变化为例,商朝时河南有象,南宋时太湖结冰可以行人,这些也不是用人的行为或思想可以解释的。近时(2003年1月20日)澳大利亚森林大火逼近堪培拉,也是天干物燥,雷电引起,与人类活动无关。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恩格斯的这段话经常被引用,以至于耳熟能详。但是“报复”这种说法,的确含有“诺亚观念”的影子。爱因斯坦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因此认为“上帝深奥莫测,但他并无恶意”,“上帝”不是那种“每一次”都要“报复”的爱记仇的小肚鸡肠的家伙。改造自然的人类活动是一个“试错”的认识过程,重要的是从失败中总结经验,达到成功。大禹就是在前人遭到“报复”时不低头、不气馁,总结经验才取得成功的。后世李冰父子设计的都江堰,让川西平原富庶了两千年,至今还在发挥作用,并没有遭到“自然界”的“报复”。哈尼族变荒山为梯田,也已经用了一千多年,至今完好如初。
强加给科学的“局限性”很难自圆其说。当自然显示其“未被知晓的习性或层面”时,正是科学(及一切人类认识)的用武之地,而不是像宫文所说的那样“无能为力和无所适从”。大禹的事例就说明了这一点,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科学真像宫文所说的那样一出现“未知”就“无能为力和无所适从”,早就被人们扔到垃圾堆里去了,何需宫先生在这里诋毁?
时间永是流逝,没有一刻停歇。现在就是过去的未来,也是未来的过去。科学追求对未来越来越精确的预测能力,如果“科学只能说明过去和现在”,这种“科学”就根本不是科学,而是史学。如果牛顿定律不预测未来的日蚀和月蚀,我们要他何用?
如果谁认为“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就请他明示那个“限度”在哪里,或者掏出他的“无限”的法宝(例如神的认知能力),实际试试看。
方舟子
在认识论上,(“反科学”的人文学者)他们竭力向不明真相的公众宣扬科学的“局限性”和“危险性”,然而对用什么方法来取代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避而不谈,实际上,他们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取代科学的方法,他们所谓的对“自然”的“敬畏”,只不过是对“上帝”的“敬畏”的另一种说法。任何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只能依靠事实与逻辑,在科学方法中,更明确为数据与逻辑。而这些家伙们却要抛开这一唯一有效的方法,而诉诸“信仰”,走向神秘主义与迷信的泥潭!
他们并不真正理解自然科学的一些基本常识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科学力量的强大,但他们出于无知而对科学产生恐惧。更可悲的是,他们不是通过增加自己的知识来消除自己的恐惧,而是求助于“对自然的畏惧”这样一种毫无根据并且毫无用处的信仰,而且要把这种垃圾强加于公众!
陶世龙
由于我们许多知道或不知道的原因,我感到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科学与文化似乎离得远了,封建迷信又在沉渣泛起,不讲科学的愚昧行为,更是常有出现,乃至在知识分子中也存在着不讲科学的问题,譬如用主观臆想代替事实,用笼统的概念代替科学的分析,甚至给迷信披上科学的外衣等等。如果用科学的眼光来审视一下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新闻报道等等精神产品,恐怕值得推敲的地方就更多了。当然,我们不能用科学的尺子来量度文学,但文学艺术要求真善美,并把真放在首位,这与科学精神是一致的。文学对传播科学精神,创造一个适于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可以起重要的作用。而科学对各种研究或创作,也是有用的,当然这不是把科学仅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来对待,如用电子计算机来研究小说之类,而是说应在研究或创作中体现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方法。
关于理性主义
宫敬才
去除神性,贬低和蔑视自然,彰显和夸张人的理性能力是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传统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问题的基本态度。我们不要忘记,没有神性,人便摆脱了终极价值的内在约束,他可以肆意妄行而无所顾及,结果是人把自己降低到了穿衣饰的动物的水平,除了有时是病态的欲望和满足之外,他什么也不知道敬畏,敬畏之中的神妙感、崇高感和安全感,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这对于他来说等于不存在。实际情况是,没有敬畏就没有谦虚和深沉,没有谦虚和深沉的极端化是狂妄和轻浮,这种狂妄和轻浮把自然作为发泄对象,这时的自然便失去人的天然依托的地位,成了人恣意妄为地征服、掠夺、践踏和摧残的可怜虫。借助对自然界的影响和干涉,人确实可以满足消费、破坏等各种各样、有时是可恶至极有时是愚蠢至极的欲望,但在自然界的正当报复面前,人又是表现得那么渺小、无力和狭愚。
至于人的理性能力,一旦把它与幸福、进步、发展、效率、竞争取胜、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等这些价值性、规则性和目标性的东西纠合在一起,自身的工具性质和作用便会充分地展现出来,其社会历史作用客观存在,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帮助功不可没,但人的精神世界除了工具理性以外就没有其他构成要素了吗?人对精神的需求,仅仅工具理性能满足吗?真实的情况是,工具理性有包打天下的想法(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就是典型)但没有这个能力,最简单的理由是:人不是机器人,更不是机器。概括地说,工具理性的具体化就是科学知识,培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知识就是力量。我们实在应该再补充一句:丢弃人类终极价值的约束,知识有可能就是罪恶。客观的社会历史事实昭示给我们的是,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传统充分发展和肆意张扬的,首先是这种知识。
赵南元
“终极价值”是“文化人”经常挥舞的幌子,但奇怪的是,他们从来不肯明确说出他们的“终极价值”是什么。从全文的文脉可以推测,所谓“终极价值”就是“神性”,但世界上神灵众多,如果不直接指明他们尊的是哪路神明,岂不又让人“无所适从”?
据说“敬畏”是个好东西,知道了“敬畏”,就可以得到“神妙感、崇高感和安全感”。但是是否追求某种感觉也像是否爱吃臭豆腐一样,是各人自由选择的事,如果因为不信神就被说成是“穿衣饰的动物”,是否又要仿效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的体制?只是某些人有“神妙感、崇高感和安全感”并不意味着真的安全,是不是人人“敬畏”就可以防止“生态危机”了呢?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早有答案。两千多年前,人心纯朴,断然没有受过“人道主义”或是“科学”的污染,对大自然“敬畏”有之,河水泛滥,就有几位女士出来张罗着给“河伯”娶媳妇,但“河伯”好像并不太领情,依然断不了发脾气。后来西门豹是怎样化解“生态危机”的,地球人都知道,无需赘述。如今只要见到有人提倡“敬畏”,就会想起那几位女士。
刘华杰
正如人们利用着科技带来的好处,同时也对科技担心一样,或者说得清楚点,如人们喜欢使用木制家具,同时也担心森林减少一样。反思或者批评一种东西,并不自动承诺可以不使用它。现实中,人们就处于种种矛盾之中。科学理性主义似乎矛盾少一些,但科学理性主义在哪里,它在哪里完全实现了?把一种理想的东西当作现实的东西,是可以的,但不是必须的。对科学的本性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声称的理性主义解释只是其中的一种,它有存在的权利,但同样其他并列的解释也有存在的权利。对声称的理性主义的反驳,并不承诺不使用逻辑和理性,相反,这暗示着“声称的理性”并不真正代表人们“心目中的理性”。既然都是一种理想化的东西,凭什么他的心目中的东西在有的人看来仅仅是胡说?如果理性还是个可以继续使用的术语的话,对目前声称的理性主义的批判,就是对一种新的更完善的理性的追求。
事实上,历史上理性有不同的所指,在中世纪和近代差别很大,现在声称理性主义者的人也不过坚持了历史上诸多理解中的一种罢了。没有证据声明,在未来理性概念不会扩充。因此,在论战中,理性和非理性的牌子挂到谁身上,并不等于自动判定了好与坏、正确与错误。“理性”并不能代替论证。说到底,我们是站在地上生活与说话,我们是在社会中生存,我们是社会的动物。一定意义上我们能够做到一点超越,但完全的超社会、超人类甚至消去人类(僭临上帝)的超越,是做不到的,骗人的。那与声称的理性主义者所反对的什么教有什么区别?费耶阿本德有《告别理性》一书,他并非真的不相信理性,只是不相信自称理性主义者的人所阐述的那种干瘪而霸道的理性,他何尝不是在憧憬一种新的理性!如果理性只如你们所说的,还真不如告别理性。
赵南元
我早已声称没有任何信仰,所以自然也不信仰什么“理性主义”或是“逻辑实证主义”,我只是喜欢摆事实,讲道理,对争夺话语权或话语霸权不感兴趣,如果有人认为科幻小说或神话比科学的事实更有说服力,那我也没法子。但是我如果认为谁在胡说,决不是因为他“心目中”如何,而是看他说了什么,我的反驳必定就具体问题举出证据,按照逻辑进行,迄今为止这些反驳没有被再反驳回来,我只好理解为他们认账了。关于“上帝”的事我不感兴趣。我只知道拿上帝来骗人的不少。
附:另外两种观点
“真由美”
科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毒瘤,成为严重危害人类自的生存的一个现代邪教,科学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僭越,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玷污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圣洁,造成了人性的沦丧,道德的堕落,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枯渴,使20世纪人类陷入空前的危机。对科学理性的不加限制的推崇,给本世纪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造就了凶残的法西斯主义和反共反人民的西方自由主义,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现代专制。所以,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家开始着手对科学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于是,在西方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神学以及各种新宗教得到复兴,人文主义得到标举。
当西方已经完成了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反思,我们还在高喊着要现代化,用现代主义的鸦片麻醉着人民,把科学当成最摩登的宗教,鼓吹科学主义。
群言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形成,特别是随着中国成功加入贸易组织,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交融将在所难免。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的渗透将变得更为直接、迅捷、全面,并对我们已有的价值体系进行最大挑战和最大考验。新世纪或新时代运动所宣扬的恰恰是“反科学、反理性”,这种思潮已影响到我国,而且宣传这些思想的组织和膜拜团体有的已经发展成为邪教,成为一股反社会的逆流。而在我国,从所谓“神功异能”的兴风作浪到“法轮功”作大成势,恐怕与那一时期的“非理性”、“伪科学”的宣传有关。而现在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似乎又在形成一股思潮,在概念或定义不清的情况下,让公众去接受“反科学主义”的宣传,会不会影响公众对科学价值的判断,导致新一轮思想意识风波,成为新“邪教”制造的理论先导和利用的工具?因为价值观念中,科学已经成为破坏人类的罪魁祸首,崇尚科学的社会主流被谩骂打击科学替代。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这20多年来,迷信、伪科学、邪教“法轮功”给我们的教训太深了,我们总不该重犯“历史的健忘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