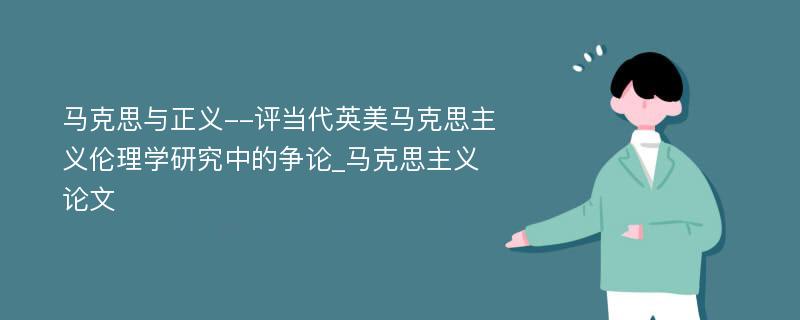
马克思与正义——评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的一场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伦理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英美论文,正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0)03-0138-07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美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马克思学说的热潮。站在潮头的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第一波来潮则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主题,而处在风口浪尖的正是一场有关“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①。
争论的导火索是美国斯坦福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伍德的一篇文章。在1972年的《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一文中,他认为:不能错误地把“正义”概念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推崇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评价标准。在伍德看来,“正义”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根本就不是一个“道德”概念,而是一种“司法的”或“合法的”概念。这种概念主要涉及“人们身居其中的法律和权利”。由于唯物史观指明,法的或权利的形式只能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以,“正义”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就是“被决定的”、“只能维护和体现一定生产方式”的“保守的力量”。因此,尽管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推崇共产主义,但并不是依据所谓的“正义”概念,而是以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在满足一些非道德善(诸如“需要”、“利益”等)上的优劣程度为根本标准。由于资本主义的“正义”概念只能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产物,只能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以马克思是不可能用资本主义的“正义”概念去谴责资本主义社会的。据此,伍德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正义的社会。”[1]
伍德的结论引起了轩然大波。文章发表不久,众多学者在“马克思与正义”的主题下发表评论、互相辩驳,从而引发了一场持续近三十年之久的大规模论战。可以说,凡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英美学者,几乎都在这场争论中发表过自己的看法。
一、“马克思反对正义”与“马克思赞成正义”
英国《新左派评论》前编委会成员诺曼·杰拉斯(Norman Geras)曾于1985年和1992年推出了两篇前后相继的综述文章《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和《把马克思带入正义:答疑与补续》,涉及论文百余篇,著作二十余部。在文章中,杰拉斯指出了所谓的“两个战略性问题”(也就是争论的焦点)②。简单地说,这两个战略性问题的实质是:
(1)马克思是否在用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正义原则批判并衡量资本主义社会?
(2)如果马克思的确用了这一正义原则,那么该原则从何而来?是来自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还是来自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或是来自“超历史的”(trans-historical)正义标准?围绕上述两个争议焦点,我们可以把各方观点都归到“马克思反对正义”(Marx against Justice)与“马克思赞成正义”(Marx for Justice)的两大立场中。下文所列则是双方针锋相对的代表性观点。③
1.“马克思反对正义”(Marx against Justice)
(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作为劳动力的所有者的工人与作为资本所有者的资本家之间进行的工资交易是“等价”交易。工人与资本家都是各自商品的所有者,都在依据工资合同进行公正交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人并没有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2)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表达了对正义原则的批判态度,反对那些社会主义者把“公平分配”或“权利”当作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合法武器。
(3)在马克思看来,“正义”和“权利”的标准不可能超越它们的经济基础。它们受制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因而是受动地、被决定地、历史地相对于一定生产方式的。
(4)马克思认为,道德的本质是意识形态,它是非独立性的、易变的,因而是虚假的上层建筑。
(5)如果把正义原则带入马克思的思想,就会把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意义限制在分配领域(如收入差别、工资水平等)。这是一种改良主义。而马克思本人更加基础、更加革命的意图显然是要变革一定社会的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
(6)把马克思的批判武器归结到正义原则上,势必会改变他意在揭示历史真实力量的努力方向,即导致资本主义社会覆灭的根源。而马克思本人无疑会把这类具有“伦理启蒙”性质的原则看作是唯心主义的产物。
(7)无论如何,“司法性的”正义原则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根本就没有国家层面与法律层面上的司法工具。
(8)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排除了那些使“正义的环境”(如资源的稀缺和不可避免的冲突)成为必要的社会条件。因此,所谓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根本就不是一种有关正义的分配原则,而恰恰是超越了正义原则的某种结果。
(9)马克思的确在谴责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但并不是根据正义原则,而是根据自由、自我实现等其他价值。
2.“马克思赞成正义”(Marx for Justice)
(1)即使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资关系是“公平交易”,那也只是表面的暂时现象。相反,马克思在生产领域揭示了这种公平背后隐藏着的真实的剥削关系。“公平交易”根本就不是真实的交易,它是资本家对工人无偿劳动的占有。
(2)尽管马克思反对“道德化的批判”,但他本人经常把“剥削”说成是错误的和不公正的,并称它是“掠夺”和“盗窃”。这表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必然存在某种正义原则。由于马克思同时又认为正义原则不可能超越一定的社会制度,因此,这种正义原则只能是“超历史”的标准(即适用于各种社会形态的正义标准)。
(3)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到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分配规则,按由低到高的价值层级排列,分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原则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按需分配”原则。这表明,在马克思那里有一套等级分明的有关分配正义的道德价值序列。正是这些正义原则构成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依据。
(4)即使马克思用了道德相对主义的表达方式(即道德总是相对于特定社会的特定生产方式而言,不具有对他类社会或生产方式进行评价的合法性),也不应该把它们理解为相对主义的,因为那是道德现实主义的态度。马克思拒绝“超历史”的伦理判断,他的道德现实主义的宗旨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公平标准,必须创建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
(5)马克思强调分配正义原则从本质上讲并不是一种改良主义。对正义原则的考量应具备一种广义视角。该视角不仅体现在分配领域,它是一种对社会中的好与坏最基本的分配,甚至包括对生产资料的分配。
(6)马克思并不认为道德批判本身是充分的,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历史变革的一个补充,正义原则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是有地位的。它不仅可以结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还可以化作社会革命的有效中介。
(7)用“司法正义”限定正义原则是一种狭隘的理解。作为伦理原则,正义价值是可以独立于任何专制体制的工具,继而评价和决定如何分配社会收益与社会负担。
(8)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按需分配”就是一种分配正义的原则。它旨在追求“自我实现”的平等权利。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国家机器消亡之后才能获得这种权利。
(9)正义原则可以被自由、自我实现等其他道德价值容纳,即使正义原则是有限的、相对的,它的有限性和相对性也可以在其他价值中得到补充说明。
上述18种观点基本上涵盖了争论的全貌。在后面的评述中,本文将依据这些观点内在的理论关节和逻辑理路把它们串起来,让它们相互对话。同时,为指明线索并简化起见,下文将以观点前的数字符号作为标识,如(1),(2),(3)……(9),以“F”(for)和“A”(against)区分相同数字标号的不同立场④。
二、正义原则的价值来源
从F(1)和A(1)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来看,它们把目光分别聚焦在流通领域与生产领域,前者偏重流通领域,后者偏重生产领域。A(1)观点的代表人物伍德提出此观点时大量引用了《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中有关劳动力的买与卖的部分。在他看来,该部分似乎说明,在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它“随着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即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的改变而改变”[2]。同时,“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劳动力的承担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2](201)。相应地,货币占有者,即资本家,通过工资形式的劳动契约合同从劳动力的所有者那里购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于是,“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的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惟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2](204-205)。伍德据此认为,在流通领域内的工资关系中,工人与资本家的交易符合契约关系,因而是公正的。在那里,并没有所谓的非正义,工人也并没有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244-282)
作为观点F(1)的代表人物,胡萨米认为伍德在理解马克思的原话时忘记了马克思在写作中的“反讽式”风格。在胡萨米看来,伍德是把资本主义形式上的“公正”当成了真实的社会关系写照。但恰恰相反,资本家先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工人先是“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品出卖”,“公平”交易才是可能的。因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事先决定了这种表面上看似“公正”的交易关系的实质。马克思在这里正是用资本主义自己所鼓吹的形式“正义”刻画资本主义本身的虚伪与欺诈。一旦形式上的“正义”被劳动合同固定下来,资本家在生产领域对劳动者无偿剩余价值的剥削看上去就顺理成章了。所以,胡萨米认为,“从劳动契约的自由、平等、等价交换转变为不自由、不平等和非等价交换只是因为资本家和工人在经济地位上不平等。资本主义的劳动契约和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掩盖了工资关系的真实本质,好似资本主义在把劳动(而不是劳动力)当作商品并告诉工人他们的劳动已经得到了足额的回报”。相反,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契约权利只是‘形式上的’,这种表面现象与真实关系是直接对立的”。事实是“工资只是支付了劳动力的价格而并未支付足额的劳动贡献”。真正的公平在于:“要根据工人的劳动所得(而不是根据劳动力的商品价格)支付工人的工资。”胡萨米继而把这种“劳动贡献原则”联系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到的“按劳分配”,认为这就是马克思在谴责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所用的社会主义正义原则。马克思正是通过把“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正义原则“引申”为无产阶级正义原则的方式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正义的。这是观点F(3)。[3]
正是上文提到的“引申”一词,在杰拉斯那里似乎是说不过去的。尽管他承认马克思的思想中确有某种分配正义原则,但却不是来自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他问道,既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原则可以用来批判和谴责资本主义社会,那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本身的价值优先性从何而来?也就是说:“如果马克思是通过潜在的控诉(使用偷窃、盗用等字眼)谴责资本主义的剥削是非正义的,而标准来自社会主义。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更热衷于这些标准?毕竟,社会主义是另一种社会秩序,资本主义本身也是一种社会秩序。只不过,社会主义是一个更加高级、更具进步性的历史阶段。但是,这种社会形态的等级排序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杰拉斯认为,马克思的确是在谴责资本主义社会,说它是不公正的。但是既然资本主义的正义原则不具有评价的正当性,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本身的进步性也需要提供价值说明,那么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正义原则就必定是超越历史的,不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正义原则不能说明它,相反,它是可以包括并说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正义原则的,即观点F(2)。这一原则,在杰拉斯看来,就是具有广义普遍性的所谓“对一定社会收益与负担进行安排的分配正义”。同时,由于这种超历史的正义原则不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束缚,它将有助于批判那些在历史必然性上大做文章的专制政体(如斯大林主义政权),因而具有普遍的评价功能[4]。这是观点F(7)。
三、非道德善与道德善
无论是体现阶级利益的正义原则,还是超历史的正义标准,或是“司法性”的正义概念,布坎南都一概拒绝。在他看来,伍德的观点A(7)(即正义只是一种“司法”概念)过于狭隘,只是着眼于概念的“描述性”特征,和马克思的本意不相符合。而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超历史的正义原则在马克思那里也是不存在的。布坎南认为,正义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只能被看作深层问题的表面征兆,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当务之急就是揭示这些深层问题。一旦这些问题通过更为理性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得到解决,那么休谟和罗尔斯所说的“正义的环境”将自然消失。而马克思所理解的“正义的环境”是“富足”(即“财富的涌流”)与“和谐”(即“自由人的联合”)。所以,马克思的那句话,即“从根据每个人的能力,到根据每个人的需要”,根本就不是一种正义原则,而毋宁说是在“深层问题”解决之后自然产生的一种结果,即观点A(8)。相反,恰恰是“需要的满足”左右了马克思评价一定社会制度优劣程度的标准,而不是正义原则。布坎南指出,那些试图用传统或当代的政治理论去刻画马克思的做法是完全无效的,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理论是对两种主要的政治哲学的批判:(1)批判以正义作为社会制度第一美德的政治哲学主题(如罗尔斯);(2)批判以尊重权利所有者的个体权利为第一美德的政治哲学主题(如诺齐克)。所以,在马克思那里是没有正义理论的,即没有一种正义理论可以给后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充分的规范性制度结构。[5]
如果布坎南是正确的,即马克思的确是把“需要的满足”作为评价一定社会制度优劣的标准,那么,作为“非道德善”的需要,它的满足可能会有两种情形:一是最大化非道德善,二是以相应的权利限制非道德善的最大化。第一种情形必须有前提,正如埃尔斯特(Jon Elster)所言,需要的满足有两个条件:一是生产力水平很高,二是人们相应地减少自己的需要。因为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要似乎是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第二种情形存在的原因是,一些人需要的满足不能以另一些人需要的损失为代价。因此,必要的权利限制是不可避免的。许多学者认为,第一种情形根本无法讨论,因为马克思显然不会在最大化非道德善的立场上更加热衷于“相应地减少各自的需要”,他很明显地是在期待不断增长的社会生产力。如果“乐观地估计生产力水平”这一条件是充分的,那么最大化非道德善就是有可能的。然而,生产力水平究竟能有多高似乎是个未知数,讨论它毫无意义。于是,主要问题集中在第二种情形上。埃尔斯特的观点F(8)认为,“劳动贡献原则”是一个“以劳动获得等额回报的平等原则”,而马克思所提出的“需要原则”是一个更加真实或更好的平等原则。因为马克思在谴责贡献原则的“缺陷”时本质上指的是:它产生了没有道理的各种不平等。不平等的回报建立在个人能力差异的基础上,而这种能力差异没有道德相关性。因此,马克思在贡献原则的替代物中所预见到的是:平等不是一种以等量劳动获得等值回报的权利,因而也不是每个人对同样的事物或一定社会福利份额具有同等的权利。毋宁说,它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平等,即每个人作为“种存在”(Species-Being)平等地通过自己的方式自我实现的权利。[6]
四、在道德改良主义与道德现实主义之间
根据布坎南和伍德的立场,他们显然不会同意埃尔斯特及其他一些学者以这种方式理解马克思对正义的看法。让我们再次回到《哥达纲领批判》中,回到马克思对那些“正义”和“权利”概念的批判和声讨中。众所周知,马克思批判《哥达纲领》的政治立场是直接针对拉萨尔派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十分明显地拒绝“通过一天公平的劳动,获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拉萨尔主义的社会主义口号。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不仅反对道德化的批判,也反对道德化的改良,即观点A(2)。理由很简单,从观点A(4)来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正义和权利只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造物,它不是工人阶级可以用来进行革命的手段,相反,它恰恰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虚假的意识形态,是用来欺骗和麻痹工人阶级的精神鸦片,即观点A(3)。于是,布坎南认为,关注分配正义,在另一种意义上就是改良主义的。它放弃了马克思所追求的具有真实革命趋势的唯物主义事业,即推翻资本主义的秩序,取而代之的却是道德启蒙和法律改革的方案。它会使工人阶级“直接关心那些使人困惑的抽象的正义理念而远离具体的革命目标”。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形式。它相信历史的进步可以在人们有关道德的或司法的观念中得到更好的改变。但以观点A(5)来看,这种改变是次要的,它只不过是社会生产关系变革中的派生物[7]。或者如伍德所说,对于一个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来说,以正义的名义批判资本主义就是一种退却——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想要把自己装扮成革命的、坚定的、富有激情的自以为是的人(如果可以是的话),从而可以“在下一届民主大会上发表政治性的演说”[1](244-282)。
但是有些学者认为,把“正义”和“权利”的分配原则带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活动,非但不是一种道德改良主义,恰恰是马克思所提倡的一种“道德现实主义”。在范德威尔(D.van de Veer)看来,马克思分配正义原则的含义要更加广泛。因为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在那些公认的反分配倾向的措辞中,马克思显然很关心自由时间的分配、机会的分配,关心那些令人厌恶的工作的分配,关心更普遍的社会福利分配,总之,关心社会的、经济的利益与负担的分配,而且马克思特别关心这些分配的生产资源的分配。因此,从观点F(5)来看,马克思最关注的就是生产资料的现实分配问题,正是这一问题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使命,即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卓越的革命[8]。不仅如此,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的“道德现实主义”在“卓越的革命”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在瑞恩(Cheyney C.Ryan)的观点F(6)看来,就马克思而言,如果道德化的批判是唯一自足的,那么它的确应该遭到反对。然而,当革命的手段或冲动显然还不充分的时候,道德的批判就决不会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即通往革命的真实历史趋势)相矛盾。并且,结合这种分析,伴随着工人反对资本家的真实斗争和运动,伴随着这些斗争所带来的社会的或经济的变革,规范化的道德批判就是完全恰当的,它是对经济主义的一种拒绝。伴随着现实活动过程,道德的规范性批判必将有助于革命的人类行动,有助于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9]
五、一种辩证的理解方式
塞耶斯在《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中对上述两种立场都提出了批判。他指出,“近来对马克思社会批判学说的分析和说明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思路。一方面有些人试图把马克思置于功利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传统中。他们坚持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基于某种普遍人性的观念,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将更好地促进人类的丰富性和满足人的利益(Lukes; Wood)。另一方面,有些人则坚持认为,马克思是基于正义和公正的普遍性标准而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和不平等的(Geras; Cohen; Elster)。这两者都是自由主义的启蒙道德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思路。人们常常认为这两种思路是绝对排斥的,其实不然: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哲学都同时包含了这两个方面”[10]。
与较早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道德》相似,塞耶斯认为,应坚持以辩证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与道德的关系,同时要认真对待黑格尔在这方面对马克思的影响以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在塞耶斯看来,马克思的辩证的历史理论为批判资本主义、倡导社会主义提供了基础。他总是把二者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予以关注。马克思并不试图在普遍原则的基础上去批判现实,也不是要阐明一种超越历史的未来理想社会应该是什么。他的批判并不诉诸超验标准,它是内在的和相对的。因此,从观点A(6)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对真实历史活动过程的揭示无需所谓超验的、超历史的道德标准作为历史“向导”。同时,塞耶斯强调,在理解道德价值的历史性和相对性的同时,也要警惕堕入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危险中。在马克思那里,道德价值建立在社会理论基础之上,这种理论不是纯粹的乌托邦和道德论,而是拥有坚固的、客观的和科学的基础(即历史唯物主义)。[11]所以,“不同的社会关系要求不同的正义原则,这些原则随着特定的条件出现,对于它们的时代来说是必然的和正确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新的社会秩序得以产生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先前的原则就会失去必然性和正确性”。于是,从观点F(4)来看,塞耶斯以为,“正义和公正原则都是社会历史现象,一定要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非正义的批判”[10]。
六、几点简评
限于篇幅,本文只从争论背景、西学立场和观点总结三个方面作些简单的评论。
1.对于为什么“正义原则”会成为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英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最富争议的焦点这一问题,绝大多数学者都语焉不详或避而不谈。本文以为,自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招致了许多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而社会失范症结首当其冲。所谓社会失范,也即社会缺乏引导和规约(无论是制度上的,还是价值精神上的),其潜台词则是呼唤“良序社会”。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正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是一部立志于“建功立业”的学术指南。但这与马克思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在我看来,尽管马克思的确是“正义”主题下所热议的焦点人物,但实质上却并不是“马克思需要正义”,恰恰相反,是“正义需要马克思”,是在“社会收益和负担的再分配问题上”、在“批判现存社会继而为新的良序社会扫除障碍的问题上”需要马克思的批判精神。这么说并无意于抹杀相当一部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立场和理论贡献,问题是,尽管我们可以在英美学者的学术争鸣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甚至是地道的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理解,可最终的结果还是,罗尔斯出了名著《正义论》,但却在性质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2.总体上看,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态度是一分为二的。他们一方面折服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深刻而犀利的社会分析,另一方面又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批判力有余,而建构力不足;是解释力过剩,而改造力贫乏。一如麦克莱伦在梳理了近半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史后曾这样说到:“马克思的理智威力就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他的工作的理性思路表明,它明显无力应对具有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在各类研究领域,马克思和由他所赋予灵感的思路仍会具有革新精神和洞察力。但这种思路仍会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请马克思恩准我的不同看法),在解释世界的时候要比它在改造世界的时候更为有效。”[12]正是心中存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此番理解,才会出现英美学者在“重建”马克思主义规范理论(正义原则是构建这种规范理论的主要价值来源之一)上的乐此不疲。但若仔细考察他们对这种规范理论建构的解释路径(或者具体地说,对正义原则的解释路径),就不难发现,大多数理论立场都来自于目的论(后果论)、契约论、道义论(混合道义论)、境遇论等。虽然我们不能说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或马克思主义的规范理论和这些解释路径都不沾边,但可以肯定地说,若要依循上述任一解释路径作为理论立场,那么也就无需“多此一举”地在这些原则和规范理论前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的定语了。
3.塞耶斯对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理解是中肯的。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言:“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13]正义价值就是要在这种“新社会因素”中去寻找来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法权形式中其实就客观存在着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出现的正义原则之社会基础和价值来源。不过,这一立场和观点其实已不算新鲜,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大都深谙其中的道理。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潜能尚未耗尽之前,正义价值自身能在“新社会因素”中找到多大程度上的发展空间;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充分厘清生产关系并发掘作为主导的“新社会因素”潜能的基础上,如何创制出一套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正义理论及其实现方式。总之,一如其他任何的道德价值,正义原则既不能被鄙为伸缩自如的附庸,也不能被视为绝对至上的神谕。就前者而言,如果正义不能被“板上钉钉”在社会制度的行动框架内,那么,垮塌散架或行将就木便会是该社会的未来征兆;就后者而言,应该铭记的是,当人们在正义的感召下热血沸腾、热泪盈眶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有时却是利益的一记耳光。
注释:
①布坎南曾在1982年出版的一部批判性著作中提到:“在过去的几年里,分析哲学家们兴起了研究马克思的学术兴趣。同时,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也使正义问题备受关注。此两种学术复兴的发展贯穿在马克思与正义的相互批判之中。”Allen E.Buchanan,Marx and Justice:Th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Preface,Methuen,1982,p.6.
②杰拉斯的“两个战略性问题”是指:(1)为什么马克思在著述中经常用“掠夺”、“盗窃”、“侵占”等词汇表述资本家的剥削?事实上,以资本主义的标准衡量,资本主义的剥削并不是盗窃,而是与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原则和贸易原则相适应的;(2)如果不诉诸某种超历史的正义原则,何种标准能够用来衡量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优于资本主义社会和各阶级社会的分配方式?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中,这一分配方式能够以人的自我实现为目的,使生产资源、自由、机会得到合理分配,从而使社会成员的获利与失利得到普遍的协调?Norman Geras,Bringing Marx to Justice:An Addendum and Rejoinder,New Left Review,195,1992,pp.37-69.
③杰拉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词典》的“正义”条目中,划出了“马克思反对正义”和“马克思赞成正义”两派,并就此罗列了绝大部分主要观点。本文参考了该条目,但对大部分条目做了简化处理并增补了部分内容。Norman Geras,Justice,in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edited by Tom Bottomore,Blackwell Reference,1991.
④如“F(1)”表示“马克思赞成正义”立场中的第一种观点,“A(1)”表示“马克思反对正义”立场上的第一种观点。
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道德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哥达纲领批判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经济论文; 道德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生产方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