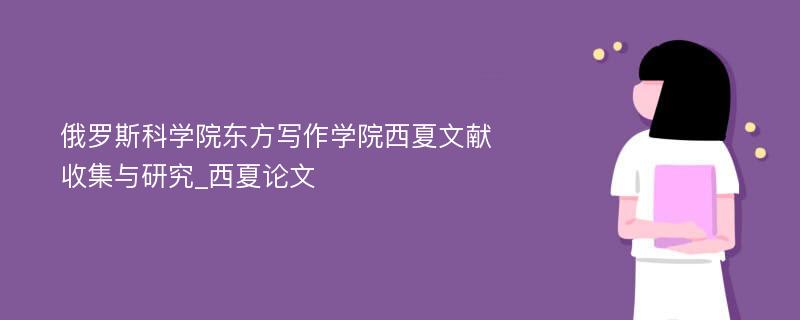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西夏文文献之收藏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写本论文,俄罗斯论文,科学院论文,文献论文,研究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前身为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的西夏文文献来自于被蒙古人称为哈拉浩特的“死城”,汉语称之为黑水城,西夏人称作额济纳。黑水城遗址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大约40公里处。
当俄国探险家们游经内蒙古戈壁滩以南阿拉善以北地区的时候,常常听到有关沙湮“死城”的传说。1886年,波塔宁(Г.Н.Потанин)探险队曾经沿额济纳河顺流而下,穿越黑水城。波塔宁没有从当地卫拉特人和土尔扈特人那里得到黑水城的确切位置,唯闻有人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古城遗址中挖掘出了各种物品,甚至银器,并获悉那里没有水,只有沙石。
关于“死城”的消息传至沙俄皇家地理学会,引起大家的兴趣。著名旅行家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获此消息兴奋异常,后来他回忆道:当时他在梦境中看到了掩埋在流沙中的神秘黑水城。他好不容易才设法获得许可和资金,于1907-1909年组建了蒙古—四川探险队。“死城”便是他在沙俄皇家地理学会支持下从事探险活动的目标之一。
1907年5月,当科兹洛夫正在为“死城”探险作准备时,布里雅特哥萨克人巴特玛扎波夫(Ц.Г.Бадмажапов)找到了“死城”城址。巴特玛扎波夫曾参与过科兹洛夫的探险队,当时作为俄罗斯贸易代表团的成员,在中国甘肃工作,受遣而前往戈壁南部边缘地区,向蒙古贵族收账。他会不会是从蒙古人那里得悉“死城”之方位呢?于史无证,不得而知,而巴特玛扎波夫提交地理学会的报告书中也不曾提及。但是,巴特玛扎波夫意识到他所发现的正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死城”。我们没有书面材料证实地理学会决定隐瞒巴特玛扎波夫的报告甚至不予公布“死城”照片之事。不过可以断定,当科兹洛夫于1907年底离开恰克图越过俄罗斯和大清国的边界时,就知道了“死城”被找到的消息。他与巴特玛扎波夫在乌兰巴托(Urga)的会见就是间接的证明。他们此次会谈的主题不得而知,但巴特玛扎波夫随后协同考察,并安排当地蒙古人与役其事,开始了对黑水城遗址的考察。[1]
俄历1908年3月19日(公元1908年4月1日),探险队抵达了黑水城。科兹洛夫在他的日记中深情地写道:“我们的激情在黑水城到了顶点,越过沙漠我们首先看到佛塔堡垒似的尖顶……然后是古城墙的一角。在紧张地度过了另外半小时后,我们翻过沙丘,来到了西边的石头平地,在这里,古城的全景便近距离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以它的财富强烈地吸引着我们……”[2]26至此,通过俄国科学家们的努力,黑水城被发现了。
这的确是20世纪初最有意义的科学发现之一!
俄国探险家终于梦想成真:科兹洛夫漫步在黑水城——这座淹没在戈壁沙漠被誉为“亚洲庞贝城”的古城街道上。一些建筑物几乎被埋在了地下,而另一些却依然挺立。人们曾在这里居住、工作、祈祷,经历痛苦,享受快乐,而今,这里却渺无人烟,甚至连城市的名字也被遗忘。哈拉浩特的意思是“黑色的城”,而不是城市的名字。
这座坚固的城池为380米×450米的矩形,其长边为东西走向,就像中国的许多城堡一样。土坯城墙高达6米~8米,墙基厚4米~6米。城内被划分为有规则的几个区域,东西城墙各有城门,但城门并不对称。两条主要街道之侧是小土屋,以茅草和硬黏土覆盖屋顶。有使用武器而留下的痕迹,但不多,与之相反,佛塔、寺庙及墓地随处可见。科兹洛夫决定住在古城中——在一座几乎被夷为平地的寺庙废墟里安营扎寨。随后,挖掘工作开始,这一工作使这位俄罗斯地理学家声名远扬。
科兹洛夫首先在城堡西南角佛塔内发现了一批刊本和手抄本文献,该佛塔用“A塔”标示。在蒙古王公与圣彼得堡公正友好的协作下,第一批发掘文物被运到俄国地理学会。其中附函一封,要求收件人携带这批文物面晤奥登堡(С.Ф.Ольденбург)院士和波波夫(П.С.Попов)教授,令其知晓。
俄历1908年10月15日(公元1908年10月28日),奥登堡、汉学家伊凤阁(А.И.Иванов)以及蒙古学家科特维奇(В.Л.Котвич)三人撰写了黑水城出土文物报告。他们盛赞科兹洛夫的发现,断定黑水城属于西夏王国,并指出从该城出土的写本除一些用汉文书写外,“还用一种未知的语言书写——至少无人能读这种语言,尽管文字字形早已为人所知”[2]31。
为了进一步的研究,科兹洛夫奉命返回黑水城,途次西藏东北部的贵德,在那里度过了冬季,于1909年5月抵达黑水城。随后,再次挖掘城墙,却一无所获。于是便决定发掘距西城墙约400米处的一座佛塔,从中发掘出大量的佛像和文献。科兹洛夫在日记里写道:“佛塔的屋顶坍塌可能压倒了佛像,或者这些佛像原先就同书籍、手卷和画像置于一起。”[2]34
科兹洛夫俄历6月2日(公元6月15日)的日记中继续写道:“塔的上部已完全清出,四周摆放着黏土和木头制成的佛像,中央摆放着书籍和文卷。书有大有小,有的装订,有的套装,有的分册,有的成卷。”[2]35在佛塔中央的底部,有一根立柱,在它的四周摆放佛像,“面朝内部,好像僧侣们朝着面前垒放的那些数百份西夏写本祈祷”[2]35。
俄历1909年6月7日(公元1909年6月20日),发掘佛塔的工作结束。黑水城木版画及写本的发现与收藏,是1908年3月到5月,以及1909年6月开始的挖掘与考古工作之伟大成效。这些文献为西夏文、汉文、藏文和蒙古文,绝大多数为西夏文。1910年6月,科兹洛夫将收集品中的写本文献交给俄罗斯科学院亚洲研究所保存和研究,是为俄国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藏西夏文写本之由来。
伊凤阁和科特维奇教授花费大量时间研究黑水城文献,仍不能完全解读它们。现存西夏文石刻有二,其一为凉州(今天甘肃省的武威)《感通塔碑》,其二为北京附近居庸关过街塔铭。伟烈(A.Wylie)、戴维理亚(J.G.Devéria)以及布谢尔(S.W.Bushell)曾试图进行解读。此外,在八国联军于北京镇压义和团运动时,法国人发现了《妙法莲华经》,一位佚名中国译码员为之提供了与之对义或对音的西夏字。毛利瑟(G.Morisse)比较研究了一些汉文和西夏文写本后,识别出部分西夏字,于1904年发表[3]。至此,可以确定这未知的文字是西夏文,并且印证了比丘林(Н.Я.Бичуриным)于1833年出版的《西藏与青海史(История Тибета и Хухунора)》一书中有关夏国(982-1227)历史的记载。
伊凤阁和科特维奇(具体不知道是他们两人中的何人、何时)在科兹洛夫的探险队带回的写本中发现了一本名为《番汉合时掌中珠》的书籍,木刻本,刊于1190年。这是一本编制精巧的西夏文和汉文双解字典。自左向右看,是汉文西夏文注音;自右向左看,则为西夏文汉字注音。这部书收字数千,它的发现为西夏文献的逐一解读开辟了道路。
伊凤阁发表了许多关于西夏文文献的论文,其中包括一篇概述性论文《西夏文文献(Памятники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письма)》(1918年)。文中总结了他在西夏文文献方面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有关《同音》《文海》《杂字》方面的信息[4]。经过多年研究,伊凤阁编成《西夏文字典(Словарьтангутского письма)》,遗憾的是,从1919年到1922年,这部书稿一直被科学院出版社束之高阁,未予出版。1935年,伊凤阁致信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院士,写道:“遗憾的是聂历山(Н.А.Невский)不知道我的手稿,从1919年到1922年,一直放在科学院。我取回此稿时,就决定不再写什么了,带有收稿和退稿标记的手稿还在我处。”[2]78可见,词典书稿直到1937年夏,伊凤阁被捕时才毁于一旦。
众所周知,伊凤阁和阿列克谢耶夫的不和是在伊凤阁对阿列克谢耶夫所著《司空图诗品(Стансы Сыкун Ту)》作出负面评价之后。20世纪20年代后期,阿列克谢耶夫在列宁格勒完全主导着汉学研究,而伊凤阁却在辞去中国外交工作后,未能继续从事西夏学研究,甚至不能回到列宁格勒。20世纪20年代末,龙果夫(А.А.Драгунов)从事了一段时间的西夏文文献整理工作,但聂历山从日本回到列宁格勒后,他也放弃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伊凤阁曾是聂历山的大学老师,曾指导聂历山在日本见习期间对平安文学的研究。1925年师徒在北京相遇,伊凤阁建议聂历山从事西夏学研究,聂历山接受之。阿列克谢耶夫也是聂历山的大学老师,曾帮助聂历山返回列宁格勒,全身心地投入西夏文文献之研究。在短短7年间,聂历山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出西夏文文献的详目,对亚洲博物馆来说,可谓滥觞之作,此前无人编写这样的目录。亚洲博物馆藏的西夏文文献大部分只是简单地按大小分类编号。聂历山停下手边一切活计,悉心投入目录编写工作,将佛教文献和非佛教文献进行了分类汇编。这项工作耗时而复杂,除自己的辛勤与天分外,还得益于他人的研究,如俄罗斯的伊凤阁和龙果夫,中国的罗福苌、罗福成兄弟,以及著有《西夏研究》的王静如,还有曾与聂历山携手工作过数年的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
1935年3月20日,聂历山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作了《西夏文文献及其收藏(Тангугская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ееФонды)》的报告,第一次全面、公正地对科兹洛夫从黑水城带回的文献作了评述,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报告中,他还提出了今后西夏文文献研究的四项任务。在这方面,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决定听起来令人鼓舞:“苏联科学院选载的1935年3月21日东方学研究所会议纪要如下:……倾听了聂历山《西夏文文献及其收藏》的报告。决定:1.鉴于聂历山的深入研究对中亚研究极为重要,有必要要求科学院主席团将聂历山的西夏研究论文优先且及时地发表。2.很有必要将聂历山派往东方学研究所专门从事西夏文文献研究。”[2]110
这是一个胜利,允许一位学者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最喜爱的工作当中。在东方学研究所全体会议上,聂历山被提名为科学院通讯院士。然而,不久后的结果却出人意外,而且极为不幸:他被投票否决了。1937年10月,聂历山被捕入狱。
聂历山不仅是西夏学家,还是杰出的日本学家。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期间曾教授日语;在研究所时,参与了日俄词典的编写工作,是此课题的权威之一。人很年轻,精力充沛,凡事都能游刃有余,原本计划要在1937年完成《基于西夏字典和碑文的西夏语音研究(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роизношения тангутских идеорафов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тангутских словарей икраткихФонетических таблиц)》一书的撰写。直到1962年,聂历山被追授列宁勋章,作为西夏学者,至此方为俄罗斯人所识。然而在日本,他作为语言学家和民俗专家而为人熟知,研究过日语方言和阿伊努民间文学,而且为日本南部的方言——宫古语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宫古岛平良镇,有一条街道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并立有纪念碑。
聂历山在列宁格勒克格勃总部消失后,西夏文文献便无人问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东方学研究所委派龙果夫继续为西夏文文献编目。战争期间,列宁格勒曾被围困,西夏收集品,以及其他来自东方学研究所的珍贵写本,都存放于设在科学院图书馆的东方学研究所里。列宁格勒遭受狂轰滥炸,幸运的是,坐落其中的图书馆却幸免于难,因此,所藏书籍和写本都得以完好保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方学研究所因战争而疏散的全体员工都相继返回,龙果夫继续从事西夏文文献的整理和编目工作,挑选有标题和比较完整的材料进行汇编,尤其是《般若经》,他几乎查阅了所有的相关文献,有些文献甚至查阅了两次。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一名杰出的语言学家,龙果夫没有钻研这些文献——至少没有迹象表明他做过这方面的工作。1950年,东方学研究所迁往莫斯科,在列宁格勒留下其分所。龙果夫随研究所的其他成员一起到了首都,1955年在那里仙逝。
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戈尔芭切娃(З.И.Горбачевщй)担负起西夏文文献的整理和编目工作,并发表了数篇关于聂历山及档案整理方面的论文。当时分所决定吸纳年轻的东方学学者从事西夏文文献的研究。1954年,分所得到招收两名西夏学研究生的许可。佐格拉芙(И.Т.Зограф)(精通汉语)和什考利亚(С.А.Щколяр)(研究西夏)前来应考。她们都通过了考试,但是位于莫斯科的研究所却招入了他们自己的候选人。佐格拉芙为了能进入研究所而再一次开始准备,1954年、1955年之交的冬天,她提前通过了必要的学位考试。什考利亚则决定不再参加研究生考试。1955年春天,列宁格勒大学东方语系推荐本年度毕业生中的四位学子继续攻读西夏学硕士学位。克恰诺夫(E.И.Кычанов)就是其中的幸运儿。1959年底,他奉命去完成西夏文文献的编目工作,到1962年末,他完成了这项工作;基于此,1963年,在康拉德(И.И.Конрад)(1891-1970)院士的支持与赞助下,第一个西夏文文献总目——《西夏文写本及木刻本——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西夏文已考订写本及刊本目录(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ксилографы.Список отождествленных и орпеделенных тангутских русописей иксилографов коллелции Института народов Азии АН СССР)》出版了,作为编纂者的戈尔芭切娃和克恰诺夫,也获得盛誉。
在该目录的前言中,康拉德院士给予了客观的评价,他将之与1960年出版的聂历山撰两卷本《西夏文献学(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相提并论:“我们第一研究阶段的成果,旨在创造重要的条件,使新加入到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能够进一步深入研究……目录的刊布将有助于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即西夏学作为东方学研究新分支的发展。”[5]5
1963年的目录仅列出了西夏文佛教文献。1999年,日本京都大学出版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的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①。除了那些字迹潦草、漫漶不清的社会经济文书外,书中几乎将所有的西夏文文献悉数介绍给了国际学术界。
目前,东方写本研究所藏西夏文文献中,九成以上是写本或木刻本。木刻本印于11世纪晚期至12世纪,也有13世纪头25年间的印品。其中以西夏文居多,其次为汉文和藏文。一些书籍可确定是用活字版印制的,有的在跋中有所反映。西夏王国制造了不同种类的优质纸张,令人不解的是,这些优质纸张何以始终未能引起今天造纸厂的注意。印度墨水(这可能也很值得专家研究),经历时间的考验,益发显示出其经久耐用的特性。由是以观,具有印刷业里程碑性质的西夏文印本,有待于专家深入的研究。
西夏佛经的印制,即使按照今天的标准看,数量也是惊人的:西夏的历代皇帝动辄印经上万,甚至达二万册。刊印佛经被视作功德,用于私人馈赠或者公开订购,一般情况下都无偿布施给官员和普通百姓。
从外观和形状看,西夏书籍的装帧以同时代的汉文书籍为蓝本,有写本双蝴蝶装②、蝴蝶装、卷轴装、折叠装和梵夹装。根据克恰诺夫与戈尔芭切娃合编的目录,西夏文文献可分为以下六类:
1.西夏文原著。
2.西夏文字典及语音表。
3.历法和医学著作。
4.律令及法律文书。
5.汉文典籍夏译本。
6.佛教典籍。其中既有汉文和藏文佛教典籍译本,也有西夏佛教徒自撰的著作。
西夏文原著中,最有价值的当数《大诗》,刊刻题记称:“乾祐乙巳十六年(1185)刻字司刻本”。这部西夏文诗歌集几乎不能翻译也很难理解,书中记录了大量的神话和对同时代要事的映射。书中部分内容由克恰诺夫和克平(К.Ь.Кепинг,1937-2002)翻译,但准确性尚不能完全保证。③
另一部有价值的文献是《新集锦合辞》,木刻本,刊印时间不详。该书是西夏谚语产生的例证。内容包括西夏原始谚语和一些从汉语借鉴的联句。中国出版了由陈炳应翻译的《新集锦合辞》,该版与克恰诺夫译本差异不大。克恰诺夫所译的俄文版也译成了中文④。
西夏之语言学家们从汉语言中汲取了很多的养分,尤其是汉语辞典编撰学对他们影响至深,留给后人多种反映其母语的辞书,堪称无价之宝。上文曾述及的木刻本《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文汉文对照辞典,刊于1190年,西夏骨勒茂才编撰。如果没有这部辞书,那么,西夏文文字的解读还会推迟很长一段时间。该辞书已在中国[6]和中国台湾地区[7]出版,成为当今西夏文辞书研究的案头必备书。
西夏文字典的破译是西夏文研究的前提,不仅有利于词汇量的扩展,还有助于从中找到例句以研读难以理解的段落甚至整个文本。应该指出的是,11世纪30年代初,夏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的西夏文音节书写规则,至1036年即已在全国推行,其书写规则在使用过程中经过小幅改进,至13世纪初基本确立。这就是当今研究者偶尔会遇到完全陌生西夏字的原因。
西夏文重要辞书《文海》成书于1124-1131年,仿汉语韵书《广韵》之体例编纂,词汇按韵和字形编排,释义和注音借助于汉文反切法,不能按韵编排的词汇则归入《文海杂类》,按声母分组编排。该辞书已翻译成俄文[8]和中文[9]出版。
另一本辞书名为《同音》,将西夏字同音字按声母分为九品,每个字符后都有注释,或用同义词,或注明词性,或用它的反义词释义。这本辞书在中国由李范文整理出版[10]。
《文海杂类三才字杂》采用的是传统分类法,将文字分为天、地、人三大类,之下再分小类。成书于1223-1227年。此辞书由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和索夫罗诺夫出版。⑤
《同义》是一部关于同义词的字典,成书于1189年,按照发音的清浊,巧妙地进行分类汇编。字典中的词汇表由李范文整理[11]。
《五音切韵》之第一部分按汉语习惯将辅音分为九品;第二部分则自上而下,无中间音节;下面是西夏语特有的带中间音的音节。该文献刊于1173年,分别由聂历山[12]132-139和索夫罗诺夫[13]82-84进行整理与研究。
对以上辞书、语音表以及西夏文汉、藏文转写文献的研究,为西夏语重构与拟音奠定了基础。承担此项工作的学者有西田龙雄、史金波、白滨、黄振华和龚煌城,但他们所作拟音各有千秋,且很难统一。
还有一些西夏历书残页,尚待研究。西夏历法与中国宋代历法基本一致,那个时代有这样的规则:即任何承认中国宗主权的国家都要接受中原王朝所赐的历书。很有意思的是,在西夏文佛历上发现了一些如何选择时间以趋利避害的内容。
西夏医药文献为数不多,未受重视,但续有出土,例如《治疗恶疮要论》,有点像祈雨的咒语。此外,《官阶封号表》也具有代表性,残卷以表格形式罗列出西夏王朝的行政组织的统属关系和职司品级。[14]180-196
在该所收藏的文献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律令和法律文书。前揭聂历山报告《西夏文文献及其收藏》的最后几行写道:“在未来……研究工作重心要围绕着……西夏的政治和经济,为此,西夏的法典研究应放在首要位置。”[15]94
东方写本研究所收藏的与这些内容相关的西夏文文献不少,主要有:
1.《贞观玉镜统》(1101-1113年间制定),译为德语[16]、俄语[17]5-34和汉语[18]出版。
2.《天盛年改旧新定律令》,共20章。保存不完整,文本第15章全部遗失。文献摘要由克恰诺夫翻译为俄文⑥。有中文译本出版[19]。2003年,日本律师岛田正郎利用中文译本,撰写了《西夏法典初探》一文[20]。
3.《新法》或曰《猪年新法》,是西夏法典的主要增补本,制定于12世纪晚期至13世纪第一季。克恰诺夫准备翻译出版。
还有一些西夏文文书书写潦草,只有很少的文本被克恰诺夫[21]193-203和史金波[22]406-446翻译。大多尚待复原与研究,特别需要那些具有破译西夏文草书能力的学者。
汉文典籍之西夏文译本亦应值得注意,两相对照进行研究,有利于探索西夏语的构词法特点,并扩大西夏语的词汇量。汉文典籍之夏译本较多,代表性著作有《孝经》《论语》和《孟子》。
1.《孝经》西夏译本,成书于1095年,由吕惠卿译注,刊布在《汉文经典西夏文译本》(克罗科洛夫和克恰诺夫合著)[23]135-211和格林斯坦德(E.D.Grinstead)的专著《西夏文文字分析》[24]300-376一书中。
2.《论语》,残存第5、11、15、19章,部分注释。刊布在《汉文经典西夏文译本》[23]135-211。吴其昱教授在他的论文末尾提到,在中国福建省发现的《论语》中,据说有相似的注释⑦。
3.《孟子》译本,残存两件,第4~6章和第8章。第8章包含不明身份之作家所作的注释,刊布在《汉文经典西夏文译本》[23]3-49。
4.无题,汉文经典语录西夏文译本。未出版。
西夏文文献中包括以下汉文军事专著译本[5]35:
1.《孙子兵法三家注》,曹操、李荃和杜牧所注,只存二、三部分。由克平整理出版,在她的西夏语法研究论文中有所增补[25]。
2.《六韬》卷一、卷二,无注释,未出版。
3.《黄石公三略》卷一,有注释,未出版。
其他汉文西夏文译本:
1.《类林》卷三至卷十。文献摘录的刊布及翻译来自克平释读的版本⑧。
2.《新集慈孝记》,节选译自《司马光·家范》。由克平译为俄文,并对文本进行了研究⑨。
3.《十二国》卷一、卷二,记载春秋十二国的各种历史事件。由索罗宁译为俄文出版[25]。
4.唐代吴兢撰《贞观政要》卷四、卷五,未刊布,克恰诺夫有一篇相关的研究论文。
5.《德行集》,曹道安编,由聂鸿音汉译出版[26]。
一些文本很难确认是否译自汉文,更像是某种汉文著述的汇编,如《圣立义海》卷一、卷二、卷五就堪为例证。克恰诺夫译之为俄文出版[27]228-329,再由罗矛昆译为汉文刊行[2 8]46-94。
因此,西夏文文献中还有儒家思想对周边民族产生影响的例子,不仅体现在周边民族对儒家经典的翻译上,而且反映在生活方式上,上至国家体制,下到寻常百姓的家庭生活。毫无疑问,额济纳的精英和官员们,喜欢阅读和学习这些著作。大约在12世纪末,全部佛教典籍已经被译成西夏文,在日本、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保存有蒙元时代,尤其是忽必烈执政(13世纪下半叶)时期的西夏文佛教典籍,遗憾的是我们却没有。可以断言,东方写本研究所收藏的西夏文佛教经典都是西夏立国以后的文献。前面提到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涉及的西夏文佛经总数达370种。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将其归入宝积、般若、华严、涅槃诸部,这些均属大乘佛教,此外还有阿含部经典、律部经典,以及显教和密教经典[29]86-90。
索罗宁考释和研究了华严禅经典之文本,指出西夏佛教文献中有极少一部分是西夏僧人自己撰写的[30]。
西夏文佛教文献数量可观,其中不乏大部头的经典,如《大般若经》《大般涅槃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大宝积经》《金刚般若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这些经典常常有数种不同的手抄本。佛教典籍在西夏文文献中占75%~80%,而这些大部头的经典又占到全部佛教典籍数量的75%。有消息称,在20世纪50年代末,西夏文《大般若经》之抄本曾赠送给了中国,尽管有中国学者(白滨)提及,但至今没有发现移交公文。一些西夏文文献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位于兰州、银川的西夏研究中心出版。
大多数佛教文献的题跋已得到研究,可参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可以确定,其中一部分佛教文献不是由外地传入的,而是抄写或刻印于额济纳和其他西夏行政管辖地区。
西夏佛教文献中还有版画。其中一幅为连环画性质的插图,很独特,仅此一见。所述故事的内容是男主人公为女儿的婚宴屠宰了很多羊,死后面临阎罗王判决,作为被宽恕和还阳的条件,要求他要大量抄写《金光明经》,并广为散发⑩。这些版画有可能来自中国的寺学或印度的那烂陀寺,透彻的研究还有待来日。
至此,除一些草书文献和少部分写本外,大部分西夏文文献都已得到甄别。文献需要修复,储藏条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除了辨识出的文本外,还有大量难以辨认的残片——这些残片原藏佛塔中,在发掘时即已散落,后在长途搬运或移动过程中,势必还会有散落。多数残页现在能够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进行识别,最近即有中国学者辨识出了一些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藏品。
至于西夏文文献中的草书,对其进一步研究无疑会带来有价值的成果。原始文本的书写标准肯定会遵循某些规则,一旦发现其规则,那么,研究人员就可以尽可能使用计算机把西夏文草书体转换为楷体。
西夏文文献还会给研究者带来一些新的发现吗?一定会的。
译者按:本文原文用俄、英两种文字发表,原题作“Танутский фонд Институтавосточных рукопис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 его изучение(The Tangut Colle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History and Studies)”,原刊波波娃(I.F.Popova)编《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之中亚探察(Российс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о в концеХIХ-начале ХХ века=Russian Expeditions to Central Asia at the Turn of the 20 the Century)》,圣彼得堡,2008年,第130~146页。本译文以英文本为依据,唯注释部分所引用参考文献,凡俄文著述,均依俄文原题,以便读者检索、利用。本文作者克恰诺夫(E.I.Kychanov),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教授、著名西夏学专家。
注释:
①克恰诺夫编著:《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京都,1999年。附有西田龙雄之前言,由荒川慎太郎编辑。
②译者按:应即晚唐、五代时期出现的一种装帧形式——缝缋装。
③克恰诺夫译注:《圣立义海(Море значений,установленных святыми)》(内容包括:木刻本摹本、文献刊布、简介、翻译、注释和增补),圣彼得堡,1997年,第217~225页;克平(К.Ь.Кепинг):《最新论文及文献(Последние статьи и документы)》,圣彼得堡,2003年,第97~110、116~136、196~201页。
④克恰诺夫译注:《新集锦合辞(Вновь собранные драгоценные парные изречения)》(内容包括:木刻本摹本、文献刊布、翻译、介绍和注释),莫斯科,1974年;陈炳应:《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太原,1993年。
⑤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索夫罗诺夫(М.В.СоФронова)译注:《文海杂类三才字杂(Смешанные знаки[треx частей мироздания])》。其中,绪论、西夏文俄译由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承担,而文献复原、序言、研究和注释工作由索夫罗诺夫完成,莫斯科,2002年。
⑥克恰诺夫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Измененный и заново угвержденный кодекс девизацарствования Небесное процветание 1129-1169)》(共4册,包括文献刊布、翻译、研究),莫斯科,1988-1989年。
⑦吴其昱口述。
⑧克平:《遗失的汉文类书〈类林〉的西夏文译本(〈Лес катeгорий〉.Утраченн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лэйшу в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内容包括:木刻本摹本、文献刊布、简介、翻译、注释和索引),莫斯科,1983年。
⑨克平:《新集慈孝记(末卷)(Вновь собранные записи о любви к младщим и почтении к старшим.Последняя цзюань)》(内容包括:手抄本摹本,文献刊布、序言、翻译和注释),莫斯科,1990年,第20~35、154~186页。
⑩译者按:即《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有关汉文写本在敦煌多有发现,今所知的抄本几达三十件,分别庋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地的图书馆及私人收藏,见郑阿财:《敦煌写卷〈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初探》,《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581~601页;杨宝玉:《〈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校考》,《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28~338页。此外还有回鹘文译本,见杨富学:《回鹘文〈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研究》,《敦煌学》第26期,台北: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编印,2005年,第29~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