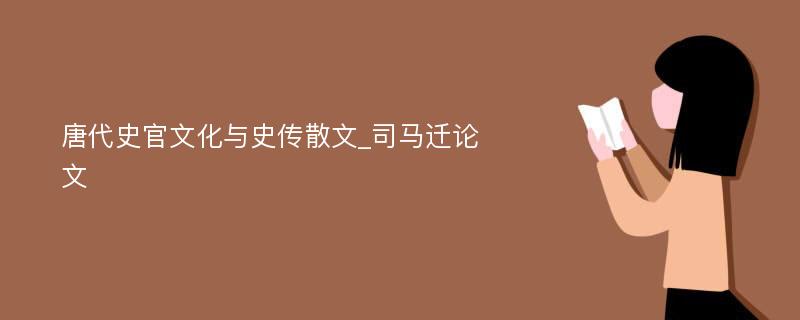
史官文化与唐前史传散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官论文,文化与论文,散文论文,唐前史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I207.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93(1999)03-0109-07
唐前史传散文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唐前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联的。从思想渊源来说,史官文化无疑是史传散文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所谓史官文化,是指上古三代到秦汉时期以史官为代表的知识阶层所创造的文化。这种文化从巫文化发展而来,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以人伦关系为本位,注重“隆礼”、“敬德”,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史官文化入手,探讨唐前史传散文的产生及其特征。
一、史官与史官文化
中国古代史官建置是很早的。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云:“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马端临《文献通考》卷51亦云:“史官肇自黄帝有之,自后显者,夏太史终古,商太史高势。”这些说法大都根据传说加以推测,不大可信。依现代学者的研究,最早的史官是沟通天人的巫官(天官),史官文化源于巫文化。[1]
早期的巫官就是史官,由巫到史,古人也早已注意到了。《国语·楚语下》云: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兴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
这条资料清楚地说明:一、巫的产生乃是为了沟通天地、人神之间的关系;二、巫者必须具有某种非凡能力,是人类中的精英;三、颛顼之时,命重司天、黎司地,天地、人神之路隔断,重、黎氏世叙天地;四、西周时,原来的天官、地官“失其官守”,成为司马氏。
再看《史记·太史公自序》: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
一般把这段话看成司马家族的历史,实际上它何尝不是史官文化的发展历史呢?由天官到史官,线索分明。这与上引《国语》的一段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这两条资料可以看出,西周时期是史官文化的一个转折点,此前的原始先民时期,巫掌管着沟通天人的职能,地位十分重要,即使殷商时期,虽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但史官的天官职能未有变化。西周时期史官的职能向人事逼近了一步。这样的变化还可以从其他文献得到印证。《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甲骨卜辞卜问的内容以有关自然神祗与祖先的祭祀为最多。卜辞中的史官有尹、多尹、卜某、多卜、工、多工、我工、史、北史、吏、大吏等,这些史官大都履行司天祭祖的天官职能。西周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礼记·表记》云:“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史官才有了记事之职,即许慎所说“史,记事者也。”《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当时的史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礼记·玉藻》还有“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的说法。周代的史官,从前期的巫分流而来,因而不可能完全割断与巫的联系,但总体上向人事逼近,以关注现实为主要特征。
史官文化替代巫文化,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此时,不仅王室有史官,各诸侯国也有史官。墨子《明鬼》篇就说“吾见百国春秋”,孟子《离娄下》也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从时代氛围来说,“天道远,人道迩”[2](《左传·昭公十八年》)、“国将兴, 听于民;将亡,听于神”[2](《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的呼声日益高涨,人们的思想从神的禁锢中解脱出来,注意到了人本身的价值。从春秋末到战国时代出现的“百家争鸣”局面,进一步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此期的史官,仍有祭天祀地之职,《左传》就是典型例子。但如果把“司天”、“司鬼神”、“司灾祥”、“司卜筮”的情况同《左传》整部书所记载的历史相比,不难看出,这些成分并不占主导地位。何况这些内容也并没有完全脱离人事。《左传·成公十三年》也明确地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总体来看,《左传》注重的是“戎”,也就是注重人的活动。
春秋战国时期史官文化替代巫文化,有两大明显的特征,一是把神话历史化。神话作为巫文化中的重要一部分,被历史家加以改造,成为历史。孔子把“黄帝四面”的形象解释为圣人垂听四方[3], 又将“夔一足”曲解为夔这样的贤臣有一个就够了[4]。这样的改造, 固然使神话失去了地位,但也反映出史官文化的特征。这“不同于原始人那样盲目地崇信超自然的因素,却企图将天命和神力纳入其实用理性的思想范畴之中,倾全力于建设起一个面向人伦日用的政权体制来,也就无需乎对神灵世界大肆渲染了。”[5] 《左传》中也将上古时三皇五帝的传说加以改造,成为历史。还有各国先君先祖的有关传说,也都已经历史化了。史官文化将人的视线由幻想的天国引入到现实的人间,无疑有其进步的意义。
史官文化对巫文化的替代,另一重要标志是史官文化具有了劝善惩恶的作用。如前所述,西周时的史官开始具有记事的职责,但这种文字记录不具备道德目的。从春秋开始,劝善惩恶的道德色彩进入史官文化之中。既然史官文化关注的是现实中的人,那么,人的本性中有善有恶,自然也应予以关注,史官文化就承担起劝善惩恶的责任了。春秋后期孔子编纂《春秋》,则使这种功能达到极致,如《左传·成公十四年》所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孟子·滕文公下》也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记事十分简略,往往一句话记载一件事情,但它却具有强大的力量,能使乱臣贼子畏惧,主要还是来自于它的道德评判。《春秋》一字褒贬,在历史记载之外,担当了道德评判的“法官”。如果说,西周时期是史官文化的变革、实现了由神到人第一步转变的话,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史官文化的变革,则使史官文化压倒了巫文化。当然,巫文化不可能从史官文化中彻底消失,史官到汉代仍有一定的天官职能。《史记·太史公自序》:“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后汉书·百官志》司马彪注曰:“太史公,掌天时、星历”。直到东汉明帝时代,史官才以修史为专职,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正式建立起史馆制度。
综上所述,在上古时代,巫官就是史官,地位十分显赫,乃至于参与政治,根据天象变化给人君提供治理天下的依据。此后,职能逐渐变化。由于史官始终与“天”有密切联系,因此,探求天人关系就成为史官文化的核心问题。早期的史官,看不到人的真正价值,往往将社会的变化归于“天”意,这种史官文化与宗教文化密切相连。西周以后,情况发生变化,史官们看出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于是,史官文化成为以人为本位的文化,把社会的发展变化看作人的活动的结果。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观念表现得更为突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直接从先秦史官文化发展而来,也是对先秦史官文化的最好总结,史官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线索:一是外在形态线索,即用天文术数等知识解释自然现象,大都体现于史书之中;二是在理论精神方面,把天文与人文结合起来,探求社会的发展,像《周易》、《易传》等,就是其中的的代表作。而《春秋》及其三传等,则是用历史变化来体现这种理论精神。尽管史官地位由上古到秦汉,经过了由尊到卑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但没有阻碍史官文化的发展,反而使史官文化在理论形态方面愈来愈丰富、愈来愈深厚。
二、史官文化对唐前史传散文的影响
史官文化对唐前史传散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史官文化的发展,经过了由巫到史、即由神到人的过程,作为史官文化一部分的唐前史传散文,它的发展也经历了由神到人的过程。恩格斯指出:“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6](P457)。 但有历史并不等于有史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还不能用文字来记录历史、记载人物。对于历史的认识,是处于混沌状态;对于自身价值的认识,几乎等于零。人们“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7](P113)。于是, 巫文化的形态之一——神话产生了,神是作为被描述的对象,如补天的女娲、追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治水的大禹等,把人的力量集中在这些神的身上,表达了人们战胜自然的愿望。文字的产生,表明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中国最早的文字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刻甲骨的贞人就是最初的史官,其职责是沟通神与王的意志,这是一种宗教活动。史传是随着人的自身价值的被认识、被肯定而产生的,而此时,人是神的附庸,神支配着人的一切行动,甲骨卜辞仅是历史记载的萌芽,还没有成为记载人的生命活动的传记。
殷商时出现的金文,记事也都很简单。到西周时逐渐有了较长的文字,记事较为完整,如大盂鼎铭文291字,散氏盘铭文350字,毛公鼎铭文497字。青铜器铭文目的在于显扬先祖,教育后代, 与甲骨文中的宗教意识有了不同。殷商时期的历史记载最重要的就是《尚书》中的《商书》、《周书》。它们以记言为主,包括誓、命、训、诰等,属政府文告性质。《商书》表现的是殷商时期的神权统治思想,天和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这与甲骨卜辞是一致的。《周书》则是西周王朝“敬天保民”(或“敬德保民”)思想的体现,标志着由神到人的转变,史传散文也由此逐渐向人的方面靠拢。
春秋战国时代,是人们价值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是史官文化替代巫文化的时代,史传散文随之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实现了由神到人的转变过程,而且人的类型由上层向各个阶层扩展。《左传》首先在写人方面取得成就,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给予很高评价:“左丘可谓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也,又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左传》已经刻画了许多鲜明的人物形象,如晋文公、秦穆公、楚灵王、郑子产、晏婴等,这在史传散文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此后的《战国策》,又把史传散文向前推进了一步,人物的类型更丰富,小人物也更多,尤为重要的是,巫文化的色彩愈来愈少。
《史记》继承了《左传》、《战国策》的长处,开创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己任,这是一种新的历史意识。“究天人之际”,就是探讨“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司马迁通过3000年历史,证明社会的发展是由人推动而非天的推动。“通古今之变”,就是要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探讨治乱兴衰之因,已经超越了单纯记事的职责,使历史由“史料学”发展为“历史学”;“成一家之言”,表明他对历史的记载、对人物的评论具有鲜明的个性、独特的思想,不受传统思想的限制。《史记》的出现,是史官文化的又一次飞跃,也是史传散文的一大转折,由此,史传散文迈开了新的步伐,以“人”为核心,展现历史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后来的《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等著作,都采用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它们各有特色,给史传散文的发展注入了一定的新的活力。
(二)由于史官文化是为统治政权服务,因而,史传散文也有明显的依附皇权的倾向。
首先是维护正统。欧阳修《原正统论》云:“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对“正统”进行了明确的解释。这种观念由来已久,《春秋》及其“三传”,都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就是明显的例证。为了维护和体现“正统”,史传在体例编排上都有固定的形式。天子雄居榜首,进入本纪,表示是天下之主。诸侯贵族是天子的辅臣,在《史记》中进入“世家”,如司马迁在《自序》中所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汉书》开始,将诸侯贵族放入列传一体,这是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汉家一统天下,不像西周、春秋时期诸侯林立,也不像汉初那样分封诸侯。不管怎样安排,都是为天子一统天下而服务,都体现出封建等级秩序。列传一般是先皇室宗亲,再是各等臣子。皇室宗亲虽无“世家”之名,但作用与“世家”相同。“正统”还体现在对前朝政权的认定与排斥,对分裂王朝更是如此。西晋代魏而统一天下,因此,陈寿的《三国志》只好以魏为正统,进入本纪,而蜀、吴只能进入列传,这是时代所迫,也是时代的需要。但陈寿对蜀、吴历史的记载还是比较公允的。南北朝时期,北魏、北齐等政权在北朝无疑是正统,而南朝的《宋书》等则斥之为“索虏”;同样,刘宋、萧齐诸朝在南朝被视为正统,而北朝的《魏书》等则斥之为“岛夷”。
其次是为尊者讳。刘知几《史通·曲笔》云:“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春秋》已开曲笔先河,如“践土之会”,明明是欲霸天下的晋文公召见周天子,而孔子鉴于“以臣召君,不可以训”,就在《春秋》中写成“天王狩于河阳”。此后的的史传,大都具有这种倾向,尤其是涉及改朝换代事迹时,避讳更为突出。《三国志》为西晋王朝服务,因而对魏晋交替之际司马氏所作所为多加回护。如司马师废魏齐王曹芳之事,《三少帝纪》说是出于太后之命,并极言齐王不孝,以显其当废,而据鱼豢《魏略》,是大将军司马师逼齐王让位,太后事先并不知废齐王之事。又如高贵乡公曹髦之死,据《汉晋春秋》、《魏氏春秋》及《世语》、《魏末传》等,司马昭实为弑帝之首。而《三国志·三少帝纪》只说“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接着载太后之令,言高贵乡公之当诛,欲以庶人礼葬之。对于《三国志》的这种做法,刘知几在《史通·曲笔》中以“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大加斥责,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专设“《三国志》多回护”条,予以批评。又如《宋书》,在晋宋革易之际,常常为刘宋回护;而当涉及宋、齐革易之处时,由于沈约本人是萧齐时代人,所以又为萧齐回护。再如《南齐书》作者萧子显,是齐高帝萧道成之孙、豫章王萧嶷之子,因而为亲者讳的倾向更为突出。当然,也有一些史传作家能够冲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束缚,大胆揭露当朝皇帝的丑行,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司马迁就是突出一例。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互见法”自从《史记》创立以来,一直被人认为是刻画人物的有效方法。最早对这种方法加以阐释的是宋代的苏洵,他在《史记》中认为《史记》的特点之一是“隐而彰”:“迁之传廉颇也,议救阏与之失载焉,见之赵奢传;传郦食其也,谋挠楚权之缪不载焉,见之留侯传。夫颇、食其皆功十而过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后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颇,辩如郦食其,而十功不能赎一过。’则将苦其难而怠矣。是故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则其与善也,不亦隐而彰乎!”“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这是互见法的一种形式。史传文学对功十而过一的人物,往往采取这种方法。尽管“互见法”在写人方面有它的长处,但这种方法无疑也起到了“为尊者讳”的作用。将某人的弱点过失不写入本传,而分散在其他传中,从作者来说,是出于对人物的偏爱,不愿以小失大;从读者来说,如果不读分散在其他传中的材料,就无法全部了解这个人物,但实际上,由于各种原因,读者不一定能读分散的材料,加之已有本传材料先入为主,往往对人物的全貌不能如实把握。因此,对于史传中的“互见法”,我们要正确看待。
再次是思想上为统治阶级服务。这在官修或者奉旨私撰的史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奉旨,就是反映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图,以统治者的思想为标准来选择人物和评价人物。班固《典引》记载,汉明帝有一次对他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实际上是给班固敲了一个警钟。正由于这样的干涉,班固《汉书》表现出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宣扬天命论、王权神授。《高帝纪》说刘氏政权“汉承尧运”、“自然之应”,得之于“正统”。再看《南齐书》,极力为维护王权服务,宣扬天命,把皇权转移说成是先天安排的,不是争夺来的。这些都体现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由于史传具有留名青史的功能,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对这块舆论阵地愈来愈重视,从东汉后期开始,朝廷都专门设立史官,编纂历史。官方的介入,使史传逐渐失去了自己应有的个性,而变成了统治者的舆论工具。
史传为统治者服务,这从体例安排、人物选择等方面也明显表现出来。司马迁创立纪传体通史,上下三千年,各种人物登台亮相。班固之所以要改通史为断代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史记》把汉家天子“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汉之列”,不能体现当朝的权威,不能突出当朝的利益,于是,他变“通”为“断”,使当朝君王居于榜首。正因为断代史有这样的功用,所以,后代史传大都采用这种形式,很少有人编纂通史。就史传选人物而言,如果说《史记》中还出现了各种下层人物,像商贾、占卜、俳优、游侠、刺客等,那么,愈往后,史传对下层人物愈不重视,甚至于一些有名的科学家也不见于史传。尤为突出的是,农民起义是封建时代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而且是新王朝建立的催化剂,但史传中除《史记》将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写入“世家”、并予以称赞外,从《汉书》开始,大都对农民起义采取敌视态度,以“贼”、“寇”来歪曲农民起义,甚至根本不把农民起义写入史传。史传中的这种倾向,无疑是皇权思想的体现,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三)史官文化讲究德、礼等人伦,强调劝善惩恶,史传散文也不例外。史传是一杆秤,秤星就是道德评价。刘知几《史通·人物》篇说:“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可见,史传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劝善惩恶。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也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这不仅是对《春秋》的评价,而且也是司马迁个人的追求。“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就是把史传纳入道德评判的轨道。善与恶是一种道德伦理观念,在阶级社会里,这种观念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阶级对立的关系,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善恶标准、观念,如对于农民起义,司马迁予以称赞,而后代统治者则视为“寇”;对于游侠,司马迁予以歌颂,而班固则予以斥责。但另一方面,由于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淀,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又有共同的善恶标准、观念,如对于统一天下的国君、爱国的忠臣、保持高尚节操的义士乃至于为国捐躯的将士,人们都予以高度称赞,相反,对那些昏庸的国君、卖国的奸臣、丧失人格、为个人谋私利的官僚,人们都投以卑视的目光。史传散文也就是通过这种善或恶的榜样,给后人树立一个警惕牌。对此,汉代王充《论衡·佚文篇》也明确指出:
天文人文,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
史传对人物的道德的评判,一般体现在传记的字里行间。这种形式,从《春秋》开端,后来的史传作家大都继承了这种传统,但总体上道德评判由隐而显。如《史记》,司马迁基本上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去表现人物的性格,其中寄寓着作者的评价。清人顾炎武《日知录》卷26指出:“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李将军列传》写李广一生的坎坷遭遇,字里行间渗透着司马迁对李广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愤慨之情;《项羽本记》写项羽一生由微到盛、由盛到衰、由衰到亡的全过程,寄寓着同情,也寄寓着批判,如此等等。这种手法,在“前四史”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当然,有时作者在记叙中也夹杂着评论,形成夹叙夹议的特点,如《史记》中的《伯夷列传》、《屈原列传》等。
最能体现史传道德评判力量的当是这些史传的论赞,作者在开头或结尾对人物进行直接评论。这种形式在《左传》、《战国策》中以“君子曰”的形式出现,史传作者假托“君子”对人物进行评论,自己还没有直接站出来,而且这种形式还不够系统化,不是每篇都有。直到司马迁的《史记》,才使这种形式系统化,并且直接以“太史公曰”对人物进行评论。后代的史传家也纷纷响应,刘知几《史通·论赞篇》归纳说:“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论,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在“前四史”中,范晔《后汉书》的史论颇有特色,据《宋书·范晔传》,他曾自负地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说:“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史传直接对人物进行评论,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给人们树立一个“善”或“恶”的典范,以起警戒作用。
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史传作家对人物的道德评判也有偏颇。尤其是对封建帝王,史传往往以褒为主,对于帝王的弱点则避而不论。就是对其他人物的评论而言,由于各人好恶不同,思想立场不同,褒贬难免有失当之处。司马迁对人物的评论,基本上是公允的,但也有失误之处,如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之人”,评晁错时说:“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像司马迁这样的史传家尚且如此,史识不如他的史传家就更不言而喻了。有些史传家人品极差,评价人物时以个人爱好为标准,如魏收:“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这样的史传家,还有什么道德标准可言呢?
(四)由于史官文化源于巫文化,此后巫史虽然分离,甚至史官文化替代巫文化,但巫文化并没有彻底消除,因此,史传文学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志怪、传奇色彩。比如《左传》,清人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认为:“千古文字之妙,无过《左传》,最喜叙怪异事,予尝以之作小说看。”《史记》是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作品,但其中也记载了许多神话传说故事,如《五帝本纪》等,还有《日者列传》、《龟策列传》专门记载卜筮者的活动,在《历书》、《天官书》中还记载了有关军事、灾异、风雨等的星占、兆应,《封禅书》写了许多巫祝活动。《汉书》中的《郊祀志》、《五行志》等,巫的成分更多,在其他一些人物传记中也有明显表现。如《萧望之传》、《谷永杜邺传》,大谈灾异。特别是《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专为五行家立传。《后汉书·范式传》写张劭给范式托梦,《方术传》写方士费长房的缩地之术,左慈的羊鸣之法等。刘知几《史通·书事》篇评此说:“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玉之暇,白圭之玷。”此外,《东夷列传》、《南蛮西南夷列传》、《西羌传》、《西域传》、《南匈奴传》等,对于一些巫祝之事也多有记载。其他史传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巫文化的影子。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另文论述。
综上所述,唐前史传散文与史官文化有密切关系。它作为史官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许多方面是受史官文化整体约束、限制,它所表现出的某些特征,与史官文化有其一致性。但是,史传散文又不完全等同于史官文化,它又有自己一些独特的个性,具有形象性、艺术性,以表现人的性格特征为中心任务,这就跨越了史学的门槛,迈向了文学的殿堂,成为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
收稿日期:1998—09—15
标签:司马迁论文; 儒家论文; 文化论文; 散文论文; 三国志论文; 汉书论文; 读书论文; 春秋论文; 史记论文; 战国策论文; 国学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左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