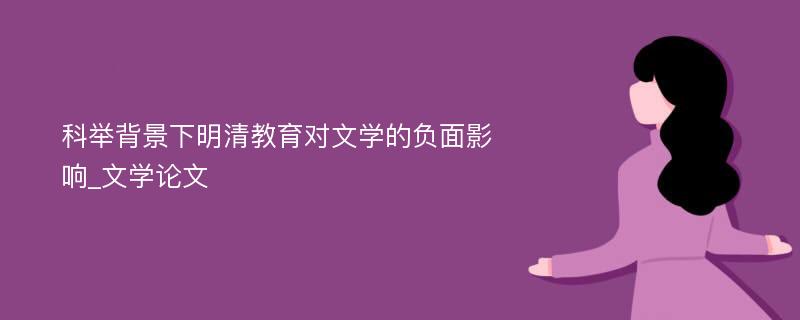
科举背景下的明清教育对文学的负面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明清论文,负面影响论文,背景下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6522(2008)04-0136-06
一、明清科举考试的去文学化倾向
科举考试是要选拔封建统治所需要的政治人才,原本并不是为文学而设;但是,唐宋进士科皆以诗赋为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文学考察为中心的科举传统。其间,宋代虽然一度兼考论策,但并没有在根本上取代诗赋的地位。宋神宗熙宁四年诏令“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1]278但这个诏令到钦宗靖康元年被废止,“复以诗赋取士”。[1]427而且神宗的“罢诗赋及明经诸科”,并不是将诗赋内容加以取消,而只是将它与经义的考试分别开来,析为两科:“神宗始罢诸科,而分经义、诗赋以取士,其后遵行,未之有改。”[1]2604南迁之后,经义、诗赋两科时分时合,到建炎三十一年始以两科分试为定制。如建炎二年,“命参酌元祐科举条制,立诗赋、经义分试法”;[1]456建炎十五年,“分经义、诗赋为两科取士”;[1]562建炎三十一年,“礼部侍郎金安节言:‘熙宁、元丰以来,经义诗赋,废兴离合,随时更革,初无定制。近合科以来,通经者苦赋体雕刻,习赋者病经旨渊微,心有弗精,智难兼济。又其甚者,论既并场,策问太寡,议论器识,无以尽人。士守传注,史学尽废,此后进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请复立两科,永为成宪。’从之。于是士始有定向,而得专所习矣”。[1]3631可见,宋代仍然延续着唐代以诗赋取士的传统;终宋之世,诗赋与经义或分或合,或此消彼长,但一直是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
明朝立国未久,朱元璋就颠覆了唐宋以来相沿已久的以文学考察为中心的科举传统。洪武三年,明太祖下诏说:“汉、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文学,而不求德艺之全。”[2]1695于是,“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2]1693由此看来,朱元璋对“试士之法”所进行的这次革新是针对前代“但贵文学”这一传统而展开的。也就是说,他的本意就是要扭转“但贵文学”的倾向,使科举考试从“文学”的笼罩中摆脱出来。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考试的内容上,用“经义”取代“文学”;二是在考试的形式上,用“八股”取代“诗赋”。唐宋之世,并非不考经义,然而经义作为其中一科(明经),与文学并行,并没有取代文学。彻底取消文学,从而使经义成为试士的唯一核心内容,是从明代开始的。正如顾炎武所云:“当时以诗赋取者谓之进士,以经义取者谓之明经。今罢诗赋而用经义,则今之进士,乃唐之明经也。”[3]715也就是说,明清时期已不存在唐宋意义上的进士科;明清的进士,实际上是唐代的明经。以文学取士的进士科在明清时期已经名存实亡。
与唐宋科举的文学内容相比,“经义”的非文学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要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一点,尚须注意明清科举背景下有关“经义”的以下几个事实。第一,“经义”主要指“四书文”。据黄尊素《宋科目考》(黄宗羲《明文授读》卷十二),明清科举考三场,然而“主司去留止以初场,馀束不观”。又据顾炎武《日知录》,“乡会试虽曰三场,实止一场,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3]734可见,三场考试,只重第一场,而第一场所考的八股文,题目不过由四书而来:“八股文考题限制在《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四书’内,所以称为四书文。……在绝大部分时间内,明清两代县、府、院试以及乡试、会试都以‘四书’题的八股文为重。”[4]第二,“经义”限于官方指定的解释。明代的《四书五经大全》,“编自永乐,颁于学宫,而诸书皆废”;[3]811清代的《钦定四书文》成于乾隆时期,也对经义的理解作了官方的限定。这就对考生的才气与识见造成了极大的束缚,使科举考试成为一种对既有成说的重复和变相抄袭。黄宗羲曾经沉痛地指出:“今日科举之法,所以破坏天下之人才,唯恐不力。经史,才之薮泽也,片语不得搀入,限以一先生之言,非是则为离经叛道,而古今之书,无所用之。”[5]254在这样的限制下,考生不能有所发挥,只能人云亦云,不得不沦落为“节抄盗窃之人”。[3]734第三,经义必须“代圣人立言”。所谓“代”就是揣摩圣人的意图,模仿圣人的口气写作,不得以第三者的语气加以客观评述;所谓“立”就是正面论证圣人之言的合理性,绝不能对它作批判性的解读。按照明人的理解,“作文是替圣贤说话,必知圣贤之心,然后能发圣贤之心,有一毫不与圣贤之意相肖者,非文也。譬之传神然,眉目须发有一毫不逼真者,非为良工也”(武之望《举业卮言》卷三)。文学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而上述这些限定都与文学格格不入,因而以“经义”取代“诗赋”,本质上就是对文学的放逐。
从形式上来看,用来阐明“经义”的“八股文”,也不具有文学性。与唐宋诗赋相比,明清“八股文”对考生的限制更为严格和僵化。顾炎武说:“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3]739同时又指出:“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为之,故日趋而下。”[3]741近体诗和律赋本来就有严格的格律规范,考试时提出格律的要求本与文学并不相妨,而散文本无格律和套式,明清八股文格式的形成,必然会在更大程度上妨碍其文学性。
总之,朱元璋以经义取士的本意就是要颠覆唐宋“但贵文学”的原有格局;同时,经义的内容限于四书,这些内容的解释又限于官方的规定,解释的口气须是“代言”,代言的宗旨只能“立言”,而其写作的形式又只能是“八股”。所有这些都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对文学性造成了无法逾越的限制,乃至在根本上取消了文学成分在科举考试中的存在。乾隆十二年以后虽然一度在考试中加入“试帖诗”,但这并没有改变重头场、重“八股”的基本格局,可以说明代的科举考试在清代得到了有力的延续。我们认为,明清两代彻底改变了唐宋以来以文学为考试中心的科举传统;核心考试内容从诗赋到经义的置换,直接引发了明清科举考试的去文学化倾向;这个倾向在明清教育中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排斥文学。
二、明清教育对科举考试的回应
科举背景下的明清教育是一种以科举为最终指向的应试教育,它对于以去文学化为特征的科举考试的回应便是排斥文学。考试是教育的指挥棒,科举考试既然重经义而去文学,那么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之下,教育的内容自然也以经义为核心,而对于文学,则采取了排斥的态度。
明清教育对文学的排斥表现在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在文学与举业的关系问题上,长期流行着“文学妨业”的观念。所谓“文学妨业”,就是学习文学妨碍举业。徐渭在嘉靖时所作的《黄潭先生文集序》一文中说:“近世以科条束士,士群趋而人习之,以急于售而试其用,其视古人之文则见以为妨己之业也,遂相与弃去不讲。”[6]嘉靖四十四年,詹仰庇《文章指南序》云:“文一而已矣,后世科举之学兴,始歧而二焉。学者遂谓古文之妨于时文也。”万历三年,武之望《举业卮言》云:“自举业起而经生视古文若异道。”天启七年,陆符《四六法海序》则说:“我国家以制举业登进天下士,士驰骛科举之利,规摹时好,视古文辞不啻若赘疣。”(王志坚《四六法海》)康熙四十年,吴昌祺在《删订唐诗解序》中也说:“胜国时,士子专治举业,以诗古文为揣摩家蟊贼,故吾乡虽有诗窠之名,载于郡志而习者实寡。”所有这些都说明以经义为考试中心的明代科举对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排斥作用,“文学妨业”的观念很流行。乾隆三十年,王锡侯《国朝诗观》之“诗例”云:“村师谓学诗有妨制艺。”可见,这一观念至少在清代的私塾教育中仍然很有市场。
如果从教育实践上考察,清代教育对文学的排斥似乎又甚于明代。顾炎武回忆说:“余少时见有一二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谯呵,以为必不得颛业于帖括,而将为坎坷不利之人。”[3]728顾氏生于万历四十一年,明亡时已三十二岁,上文所忆的“少时”当为晚明时期;那时对于“通旁经而涉古书”的好学者,“父师”则采取“交相谯呵”的激烈态度,只允许他们一意专心帖括之学。吴昌祺《删订唐诗解序》又云:“予年十三,与宋子楚鸿同砚席,其尊人秋士先生喜作诗,和唐人几遍。予亦窃习焉,为七律绝数首。先严怒,禁勿许,俾专治制义小品,为应试地。比年十九,补博士第子,禁稍驰,复从事于吟讽。”他十三岁时偷偷地学写诗,结果为其父所禁止,直到十九岁,才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吟讽”的自由,接续少年的文学爱好。父亲对儿子的态度如此,塾师对学生的态度也大抵如此。如闻人倓在其《古诗笺序》中说:“忆余年方舞象勺,已喜读八代诗。塾师以为妨帖括也,则扃巨箧中。夜分启錀,胪列泛览,往往至鸡唱就枕。”道光五年,许梿在其《六朝文洁序》中云:“往余齿舞勺,辄喜绎徐、庾诸家文,塾师禁弗与,夜篝灯窃记之。”道光时期,扬州的一个学堂条约规定:“馆中所用只是书仿笔墨砚,凡一切闲书,有妨正业,俱不许带入。……淫词艳曲、小说、俚唱最分心害事,总不许入目。诗词乃文人名成寄兴之事,少年习学,正业必踈。”(石平士《童蒙急务》)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的教育者和教育机构严禁学生从事文学阅读和文学创作活动,这些被禁止的内容既包括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也包括诗文等雅文学。其理由则是这些“闲书”“有妨正业”,也就是说,这些文学活动对于以经义为内容的科举考试没有用处,正如钱钟义《集古文英序》所云:“湘离之骚非不油然忠爱,而聱牙沉晦之辞,非应时制科所急。”总之,在这种功利主义的观念和实践笼罩下,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活动采取了排斥乃至封杀的态度。
更为严重的是,受教育者在功利主义的催动之下,自觉接受了父师的训诲,一心一意地专攻时文,对于前代文人必读的典籍,则束书不观。家长、塾师禁止受教育者从事文学活动的情况已如上述,但是如果这些受教育者能够认真学习《四书》、《五经》等基本典籍,也能为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一定的基础。这些典籍虽然并不都是文学,它们与文学的关系也有远近之分,但作为前代文人常读的书目,其对中国文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黄宗羲所云:“昔之为诗者,一生经史子集之学,夫经史子集何与于诗,然必如此而后工。”[5]357但是,明清时期,特别是明末清初,受教育者却往往不去读这些经典原著,而是怀着速成的投机心理去研摩时文,或干脆请人代为拟题。顾炎武云:“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悉。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誉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成于剿袭,得于假借,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3]735既然可以请人提前拟好文章,考试时只须择其近似者抄在试卷上,就可能考中,那么谁还去辛辛苦苦地去读原著呢?因而,即使是《四书》、《五经》这样的必读书,也是可以不读的。这就形成了“党塾之师,以时文章句为教”的风气。[3]789顾氏又云:“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舍圣人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7]23此风大抵起于万历,“万历以前,八股之文可传于世者,不过二三百篇耳,其间却无一字无来处”;[7]58“正、嘉以还,以剿袭传讹相师,而士以通经为迂。万历之季,以缪妄无稽相夸,而士以读书为讳”。[8]晚明时期,则又如张以忠《古今文统自序》所云:“帖括炽兴,渐忘古典,卑靡之气,盈于宇宙。”
直到晚清,“以时文为教”的风气依然盛行:“每当大比之后,必有一素擅文誉者选各省新墨而汇刻之,颜曰:某科直省乡墨。此风不知始于何年,先君子设帐,家塾常取书坊之新出墨,裁择其尤雅正者授门徒为程式。”(吕相燮《科场异闻录》)可以看出,对于取得科举的成功而言,钻研时文似乎比研读籍典更为便捷和高效,于是以功利为第一目标的受教育者每日“抱兔园寒陋十数册故书”,纷纷走上了“专工时文”的捷径。[5]401明清时期普遍存在的排斥文学、专工时文的教育风气给明清文学,特别是明清诗文,带来了诸多负面的影响。
三、明清教育对文学的负面影响
明清文学的作者是在明清教育格局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创作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教育的影响。科举背景下的明清教育既以排斥文学为突出特征,其对文学的影响就主要是负面的。
明清之前的中国教育,特别是启蒙教育,实际上十分重视文学教育。明清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由诗赋转为经义之后,明清教育也相应的颠覆了重视文学教育的传统,转而对文学采取排斥的态度,其中尤以启蒙教育最为突出。可以说,明清的启蒙教育不是从文学开始,而是从理学开始的。明人杨瞿崃在其《岭南文献规范补遗序》中说:“崃舞象时受业于先大人,每举我朝陈文恭、王文成、蔡文庄数先生之业以为课督。”清人李光地《榕村授读序》也说:“吾家子弟辈授诸经毕,即令稍诵近世儒先说理之文。”这种在启蒙阶段就以理学家的举业文字或深奥的理学专论为教学内容的做法超出了儿童的接受能力。其直接后果就是受教育者缺乏足量的文学积累,其知识框架主要由单一的理学成分所构成。知识的储备是思维形成的物质前提,一个缺乏文学储备的头脑同时也缺乏文学思维。可以说,明清时期的启蒙教育用理学内容置换了唐宋时期的文学内容,这一置换在根本上弱化了明清文学的基础,从而导致了明清雅文学的衰落。
从表面上看,明清时期从事诗文创作的群体十分庞大,而实际上真正专力于此并取得较高成就的,往往限于摆脱了科举制约的两个群体:一是“早得一第”者,二是“穷老自放”者。前者是由于年龄不很大就中了进士,有条件尽早从科举的流俗中摆脱出来,专力从事于文学的阅读和创作,如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袁宏道、王士禛等;后者是由于意外原因被取消了考试的资格,或者自愿放弃了科举入仕的道路,从而得以在文学的天地中寄情悦性、恣情放浪,如徐渭、唐寅等。关于上述第一个群体,清人徐嘉炎在其《野香亭集序》中曾做过这样的论断:“唐以诗取士,四声八病之学,童而习之,人人而能之,能者既多,工者亦不乏。中世数百年,学宫令甲专以经义为得失,而言诗之学遂衰,间有能者,亦复不得工。盖其自首咿唔,止此经生章句,必待一第,始得弃举子业,以从事于诗;迨从事焉,而其气已衰,且其章句之习墨守膏肓,未能澄汰以入古人之堂奥。此虽欲稍工不可得,况求其几于古人乎?是故今之能诗者必有高世之才,而士大夫之能诗者必早得一第,朝气犹新新者,乃能自拔于流俗,而外此则难矣。”按照徐氏的理解,唐代“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带来了“人人而能之”的群众性文学风尚;而“中世”之后,“经生章句”成为考试的唯一核心内容,因而这种群众性的文学风尚不复存在。士人只有在“弃举子业”之后,才从事文学活动,而此时天真渐失,意气枵散,科举思维盘桓胸中,结果“虽欲稍工不可得”。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明清科举背景下,人们要在文学方面有所建树,必须“早得一第”。得第不早,则“朝气”不新,即使可以放下举业,从事于文学,也无法有所建树。关于第二个群体,清人徐芳云:“天下埋首帖括之业数百年矣,有告以古文辞者,群然咍笑,以为杂学。其得专意于此道者,非科名既辍,则穷老自放之人也。”(周亮工《赖古堂文选》)在功利主义的应试教育背景之下,从事文学活动的“古文辞者”已经成为全社会“咍笑”的对象,而文学则已成为“杂学”,真正专力于文学的只有那些“科名既辍”或“穷老自放”的人。然而,就明清作家群的实际构成而言,这两个群体毕竟只占少数,这就是明清科举背景下雅文学生存的真实图景。由此看来,明清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从文学向经义的转变,使文学成为科举的异己成分,只有那些摆脱了科举束缚的少数人才肯专力于此,这就在根本上中断了唐宋时期群众性参与的文学格局。
诚如黄宗羲《明文案序》(上)所言,在排斥文学的教育格局影响之下,明清士人“专注于场屋之业,割其馀以为古文”,在文学上不仅用力不专,而且起步很晚,结果既无基础,又乏才情,于是出现了大量学殖不足的文学作品。对于这样的情况,清人王企埥说:“(予)方习举业之文,惟帖括是务,不暇言诗,先中丞亦不以诗教,故风雅一道,至今未窥其堂奥也。壬戌下第,中丞亦以是岁见背。悲惨之深,推敲俱废。既而成进士,入西清,迍邅十年,恒郁郁地冷署,诗兴既阻,诗律更踈。其后陟台班,登卿贰,黾勉职事,孜孜奉公,何敢分心于风雅;每于稠人广座中有称诗者,辄嗫嚅不敢出一词。此埥之于诗所以老大而靡所成就也。”(王企埥《明诗百卅名家集钞》)从王氏的情况来看,他早年“惟贴括是务,不暇言诗”,其父亲“亦不以诗教”,因而压根儿就没有足量的文学储备;入仕之后,既乏“诗兴”,又不敢“分心”从事文学活动,因而老大无成。明清士人之于文学,大抵如此:虽中进士,而文学不通者大有人在。即使是袁宏道这样的大家,也有文学学殖不足的缺陷。《明文授读》收了袁宏道的《抱瓮亭记》一文,文后有黄宗羲的一段评论:“天才骏发,一洗陈腐之气。其自拟苏子瞻,亦几几相近,但无其学问耳。”文学储备的不足必然影响文学才能的发挥,导致文学思维的俭薄。在他看来,袁中道的“天才”实与苏轼“几几相近”,却并没有取得苏轼那样的文学成就,其原因就是他没有苏轼的“学问”;换言之,袁宏道的学殖不足对其文学才情造成了限制;袁宏道早年提倡与闻见知识相对立的性灵,未必不是颇为自知的藏拙之举。
还要指出的是,明清时期以科举为目标的应试教育导致了“以时文为教”的教育风气,在此影响下,教育者对文学加以排斥,受教育者则对文学赖以生成的古代典籍“束书不观”,这样的风气从反面激成了明清时期的文学复古运动。有识之士往往以“复古”相号召,想以此来改变“游谈无根”的恶劣风气,而在“代圣人立言”的科举思维束缚之下,剿袭的风气已经成为士习的一大痼疾。在这种背景下,明清文学便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挥之不去的复古癖;然而与唐宋文学复古运动相比,它没有从复古走向创新,而是从复古走向了剿袭,这正是“代言”思维在复古问题上的反映。不论是明代中叶的秦汉派、唐宋派,还是晚清的宋诗派,无不带有复古的色彩,而它们又无不具有学步有余而创新不足的共同缺陷。不仅如此,八股思维的定式还惯性地渗入到作家的创作活动之中,使其审美心理无法摆脱某种完足而精巧的套式,因而其创作在形式上往往精巧有余,而美大不足,缺少撼人心魄的物质力量。即使像徐渭这样的天才作家,其散文也有“法度”有余而“美大”不足的时代局限。钟惺为晚明大家,在黄宗羲看来,他的文章“好为清转,以纠结见长,而无经术本领,求新求异,反堕时文蹊径”(俱见《明文授读》黄宗羲评语)。钟氏虽然力纠时弊,倡为新风,而在文章的结构方面也留下了“时文”的痕迹。可见,科举背景下明清教育对明清文学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深重的,即使是文学大家,亦不能幸免。
当然,诚如华淑《明诗选自序》所云:“制科能奔走天下之学,究不能奔走天下之豪杰。”一些豪杰之士对科举的本质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种负面影响的冲击。或者像王阳明一样把它看作敲门砖,或者像黄宗羲一样能够自觉地保持着对科举的批判态度,从而取得同时代人所不能企及的成就。然而,这样的成就于学术为多,于文学为少;明清时期未为科举所牢笼的“豪杰”大都不是文学家。如王阳明“才情振拔,少年颇擅风雅。自讲学后,多作学究语”,其文学创作的后劲不大;黄宗羲的诗则“枯瘠芜秽”、“不足挂齿”。[9]王、黄二人皆能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与科举的距离,然而皆不以文学名世。另一方面,明清教育的发生与展开所际遇的历史背景,就其原生的实际状况而言,是多层的,也是复杂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侧重也是不同的,因而这些不同的历史背景,或者说历史语境,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例如,除以上所论的科举语境之外,至少还有载道语境和文学语境,而本文所及限于科举语境中的明清教育与文学;至于其他方面,只能另文论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