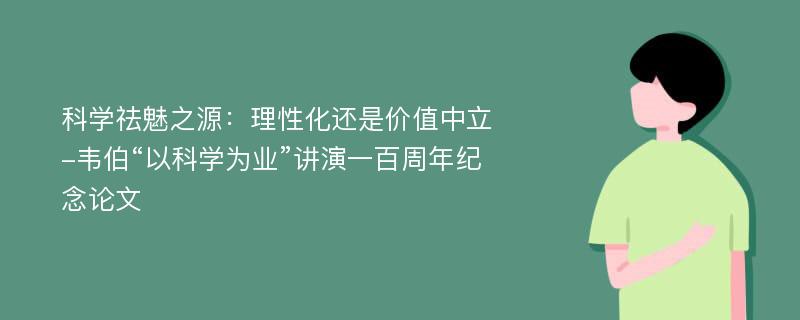
科学祛魅之源:理性化还是价值中立 ——韦伯“以科学为业”讲演一百周年纪念
刘清平1,2
(1.复旦大学 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上海 200433;2.武汉传媒学院 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5)
〔摘 要〕 韦伯虽然提出了“科学祛魅”和“现代化即理性化”的原创性理念,但由于笼统地运用理性概念以及恪守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架构,结果不仅错误地把科学的祛魅效应单纯归因于理性化却忽视了他倡导的“价值中立”的决定性作用,而且也很难解释价值中立的科学祛魅何以能够促成价值负载的现代化进程,甚至还否定了科学祛魅通过价值重载的转型所具有的积极现实意义。他也因此在三个理念的关系问题上陷入了自败的悖论,尤其没有意识到单凭理性化并不足以实现科学的祛魅,只有价值中立才能确保达成这一目的。
〔关键词〕 韦伯;科学;祛魅;理性化;现代化;价值中立
一、两个标志性的理念
马克斯·韦伯可以说是一位能以社会学家的身份进入顶级思想史的罕见人物了,因为他提出的某些原创性理念具有如此深刻的思想内涵,足以让人们不仅在过去的一百年、而且在未来的几百年都必须认真思索却没法绕过去,其中尤其值得严肃对待的就是“科学祛魅”和“现代化即理性化”两大洞见。这两个对他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理念之间也存在若干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有鉴于此,我们对这次著名讲演发表一百周年的最好纪念,或许就是努力澄清韦伯是由于什么缘故才让这两个凝结着他的创新心血的深度理念陷入了逻辑上不自洽、实践中会自败的窘境,然后再通过克服其悖论、发扬其精华的途径,使他凭借这两个理念做出的原创性贡献能够不被磨灭地与人类同在。
本来,在德国诗人席勒那里,所谓“祛魅”的原初内涵主要是指,在西方文化中,自从基督宗教里作为唯一神的上帝出现之后,古希腊神话里焕发着爱与美之魅惑的众神便逐渐隐退了,生气勃勃、充满欢乐的世界变得黯然失色、灰暗冷漠。〔1〕韦伯则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对于文学艺术中这个原创性的炫美意象做出了新的解读,一方面让科学承担起了“为世界祛魅”的头号使命,另一方面又让在席勒那里作为祛魅主体的基督宗教也变成了科学祛魅的重要对象(虽然他并不否认基督宗教尤其新教也有祛除巫术魅惑的功能),结果赋予了“祛魅”概念以新的语义,不仅把它说成是人类历史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型的标志性特征,而且还因此让它构成了自己试图阐释现代化进程何以会在西方世界率先展开的社会学理论的核心理念之一。
进一步看,在韦伯的具体阐释中,“祛魅”概念又是通过“科学”概念与“理性化”或“理智化”的概念密切相关的。众所周知,在1920年亦即去世那一年撰写的一篇总结性的导论里,韦伯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为什么只有西方文明才能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问题,然后紧接着就把答案归结到了只有在西方历史上才得到了长足发展的理性化科学那里(其中既包括了自然科学,也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亦即韦伯说的“文化科学”),一方面指出非西方科学缺乏西方科学的那种理性化的概念体系,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了理性化的科学精神通过种种渠道对于西方社会的高等教育、法律规章、宗教信仰乃至音乐建筑的全方位渗透,最终得出结论说:“在以上所有情况中,涉及到的都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问题。”〔2〕而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发表于1904—1905年间的久负盛名的代表作里,韦伯也在分析基督新教理性化伦理观与现代化经济生活的复杂关联时以类似的口吻声称:“宗教发展的这种把巫术魅惑从世界中清除出去的伟大进程, 开端于古老的希伯来先知们,然后又与希腊人的科学思想相结合,把所有以魔法手段追求拯救的做法都当成了迷信和罪恶加以摒弃,在此达到了它的逻辑终点。”〔3〕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显然有理由说,韦伯的“现代化即理性化”理念其实是从“科学祛魅”的理念那里合乎逻辑地推演出来的,因为他把“理性化”看成是“科学”能够通过“祛魅”效应促使人类历史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主要就是由于这一缘故,今天人们在解读韦伯的这两个标志性理念时,也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把“祛魅”的主体从“科学”转换成了“理性”,甚至干脆将它直接理解为“理性祛除魅惑”,以致“科学”这个原初的主体反倒在鹊巢鸠占中变得隐而不显了。〔4〕
喜姑与香娭毑的不同之处在于,香娭毑的山水,是嫁到白家湾以后慢慢显露出来的,而喜姑则是嫁到白家湾就显露出山水了,喜姑的山水当然是山歌。
毫不奇怪,韦伯在去世前一年发表“以科学为业”的著名讲演时,很自然地把自己的这两个原创性理念一以贯之地和盘托出了:“科学进步是理智化进程的一小部分,但同时也是它的最重要部分。……人们再也不用像那些相信这类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世界或祈求神灵去诉诸巫术了。技术和计算取代了它们为我们效力,而这实际上也就是理智化对于我们的首要意义。”〔5〕不难看出,韦伯在此一方面清晰地指出了科学进步只是理智化进程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又同样清晰地主张:现代科学具有的祛除魅惑、促成现代化的“最重要”功能,应当首先归功于它的理智化特征。于是,足以与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相媲美,韦伯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语也精辟地展现了科学知识推动人类历史进入现代发展阶段的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大学生创业初衷可能只是有一个“金点子”或单纯为实现理想。国家为鼓励大学生进行创业尝试,投入了大量资金完善基础设施条件,使创业项目在温室里茁壮生长,从未体验过社会的艰辛。创业项目想要脱离校园,就必然要与社会资金构建一个共担风险的共同体。许多大学创业以失败结束,常见问题主要是在“死亡谷”时期资金断裂。创业道路十分坎坷,许多项目拥有良好前景但做不成功。在把创业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要保持大学生的素质水平,不对困难轻言放弃,在创业过程中养成企业家风范。
当然,部分地由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部分地由于当时流行的对于科学价值的消极评判,韦伯在这场讲演里又试图“辩证”地指出这种理性化的科学祛魅给人类世界带来的负面效应:“由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性化、理智化、特别是为世界祛魅的特征,它的宿命就是那些最高贵的终极价值从公共生活里逐渐销声匿迹了,或是遁入了神秘生活的隐晦领域,或是转化为个体交往的直接友爱。”〔6〕无需细说,这段话以及相关的论证同样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韦伯十几年前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尾处谈到的那个经由“现代化即理性化”的祛魅机制打造出来的机械麻木僵化、匮乏人际情感、没有心灵魅力、缺失终极关怀的冷冰冰“铁笼”,〔7〕从而再次体现出这位思想家在基本观点上的前后一致。
综上所述,在韦伯那里,“科学祛魅”和“现代化即理性化”的理念不仅是合乎逻辑地联结在一起的,而且还内在统一地贯穿于整个思想体系,构成了并肩托起他的理论大厦的两根基本支柱,因此可以说远比他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冗长琐碎分析更富于思想史的深度意义。
二、理性化的纠结效应
不过,倘若我们抱着于无疑处生疑的批判精神,深入分析韦伯在阐发这两个标志性理念时运用的“理性”概念,却会隐约发现一个理论漏洞:所谓“理性”真的能使“科学”发挥“祛魅”的效应,乃至把整个人类历史也“化”到“现代”里去吗?下面我们会看到,正是这个不大不小的理论漏洞,一步步将韦伯貌似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带进了没法自圆其说的重重矛盾之中。
中外都有学者指出,韦伯运用“理性”概念的频繁程度几乎到了随处可见的地步;但与此同时,他运用这个概念的随意任性也几乎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不仅赋予了它至少16种不同的含义,而且可以说“在描写西方的一切东西时,极为自由地使用‘理性’这一密码”〔8〕。其实,他在描写非西方现象的时候同样如此,甚至更为笼统模糊。例如,在讨论中国的儒家(儒教)时,韦伯就从“理性”是“某种智识—理论立场或实践—伦理立场的逻辑的或目的论的一贯性”的宽泛定义出发,先是凭借儒家在实践—伦理立场上拥有目的论一贯性的理据,得出了一个结论:“儒教是如此理性,同时,在没有和抛弃了一切非功利主义标准的意义上是如此清醒,以至于除了边沁的伦理系统以外,还没有一个伦理系统能与之相比”;然后又笔锋一转指出:“但是,它与边沁的和一切实际理性主义的西方类型完全不同,尽管人们不停地将它与它们做着实的与虚的类比。”〔9〕结果,韦伯好像没有意识到,这里他自己其实也是在以某种脑筋急转弯的突兀方式,做着某种虚实无定、不明所以的奇妙类比,一会儿宣布儒家的伦理系统十分“理性”,一会儿断言儒家理性的伦理系统与西方理性主义的伦理系统“完全不同”。不难想象,韦伯这种“极为自由地使用理性密码”的做法,很容易导致他有关“现代化即理性化”的原创性理念落入大打折扣的自败泥潭:要是儒家同样如此“理性”,它岂不是也完全有可能把人类历史“化”进“现代”阶段,从而让“只有西方文明才能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韦伯式命题一触即溃吗?
能让韦伯摆脱这种尴尬处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小心谨慎地澄清“理性”概念的核心语义。这一点也不难做到,因为如果将西方现代哲学强调的“reason”“rational”“rationality”等回溯到它们在古希腊哲学的源头“逻各斯(logos)”和“努斯(nous)”那里,就会发现它们首先是指人们从事概念界定、判断推理、逻辑思维等认知活动的能力和过程,并且因此主要与感觉、知觉、情感、欲望这类“感性”的因素相对而言。〔10〕不错,从古希腊起,哲学家们就逐步将这种位于认知维度上的理性(又叫“认知理性”“纯粹理性”)运用到了道德、实利(功利)、信仰、炫美(审美)等非认知的维度上,从而生成了所谓的“实践理性”“道德理性”以及韦伯自己在讨论社会行为时强调的“工具—目的理性”“价值理性”等等。但与此同时,倘若我们遵守形式逻辑的同一律而拒绝偷换概念的话,便不得不承认:只有以认知维度上的理性因素为基础,这些能在非认知维度上发挥作用的理性因素才有资格名之曰“某某理性”。就此而言,韦伯说的“工具—目的理性”“价值理性”自然也不应当单纯是指任何“实践—伦理立场上的目的论一贯性”了,而只能是指那些以“智识—理论立场上的逻辑一贯性”为前提的“实践—伦理立场上的目的论一贯性”。换言之,在缺失了“智识—理论立场上的逻辑一贯性”这种“认知理性”的必要基础的情况下,亦即在“尚未领悟逻辑、定义、推理的威力”“缺乏自然科学思维”的情况下,单凭“实践—伦理立场上的目的论一贯性”自身并不足以让某种文化思潮一蹴而就地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实践理性”“道德理性”,因为这种目的论的一贯性也有可能是“实践情理”“道德情理”意义上的目的论一贯性。〔11〕
本文在分析国内外关于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影响要素基础上,参考Aaker(2004)[10]、沈鹏熠(2012)[12]、胡晓云(2013)[6]、李德立(2013)[13]相关研究,构建了新疆农产品品牌竞争力八要素模型,如图1所示,并以模型八要素对新疆区域品牌竞争力的影响提出假设:
就此而言,尽管认知需要与理性能力在科学祛魅的过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发挥的具体作用还是有着实质性差异的,只有价值中立的认知需要才是科学祛魅的唯一源泉,因为倘若认知需要背离了价值中立而与非认知需要混杂起来了,就会让科学自身也沾染上非认知魅惑,变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了,哪里还谈得上发挥祛魅的效应。相比之下,理性能力只是科学在单纯基于认知需要追求真理知识的过程中运用的逻辑思维工具,虽然也有助于科学祛除魅惑,却不足以将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严格分离开来,因而也并非科学祛魅的决定性因素。更有甚者,倘若理性能力变成了满足人们非认知需要的手段,它还有可能妨碍人们的认知成为科学,导致扭曲真相的非认知魅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祛魅的关键原因只能是在价值中立中构成了科学唯一动机的认知需要,而不是仅仅作为科学运用的重要工具之一的理性能力,当且仅当人们在认知活动中把各种非认知需要统统悬置起来,纯粹基于好奇心去描述和分析各种事实的存在状态以及价值属性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让这些认知活动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最终通过祛除魅惑以获得真知、拒斥错谬。所以,如果说韦伯将科学祛魅仅仅归结为理性化是难以成立的,当前国内外学术界的流行观念进一步把祛魅的主体从科学转换成了理性,宣称“理性祛除魅惑”,就更是以讹传讹错上加错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祛魅”的话头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但在揭示它怎样才能得以实现的内在奥秘方面却几乎没有什么进展,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在于,在韦伯有关说法的误导下,人们总以为科学祛魅的头号因素在于理性化或理智化,而不是在于他倡导的价值中立,结果面对经过理性化却依然充满非认知魅惑的神学理论这类反面的例证束手无措,于是只好停留在“理性祛除魅惑”的空洞口号上,却无力深究这种祛除魅惑何以可能的基本机制。
国内许多学者研究表明,使用语法隐喻可以更加有效地实现科技英语这类文本的文体特征。这种相互转化使得语言描述客观化,符合动物学科语言的行文简练正式、陈述客观、结构严密的文体特征。例如,
澄清了“理性”概念的核心语义,韦伯指认的“科学”与“理性化”或“理智化”的密切关联也就一目了然了。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科学理论之所以出现在古希腊,主要就是因为在各个文明古国中,只有那里的哲学家率先彰显了人们在认知维度上从事逻辑思维的理性能力,甚至把它说成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从而促使人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将自己有关世界的认知成果以概念体系的逻辑形式呈现出来,结晶成了最早的科学理论。值得指出的是,韦伯在讲演里谈到“科学的职业是什么”的问题时,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首先重述了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有关洞穴的著名寓言,然后就点明了这个寓言的深层内涵:“当时正是苏格拉底自觉发现了‘概念’这种获得所有科学知识的最伟大工具的重要意义。……在古希腊,人们第一次掌握了这种工具,运用它可以将某人置于逻辑的强大压力下,迫使他要么承认自己一无所知,要么承认这就是不会消逝的永恒真理。”〔12〕换句话说,在韦伯看来,正是由于自觉掌握了概念判断的逻辑推理这种“伟大的工具”,古希腊人才达成了追求真理知识、建立科学体系的目的。
不幸的是,由于恪守二元对立架构,韦伯不仅没有发现科学祛魅的关键原因在于价值中立的认知需要,而且在阐发现代化即理性化的理念时还陷入了另一个绵延而来的内在悖论:假如事实与价值真像他说的那样断为两截,以价值中立为底线的科学怎么可能在非认知价值领域发挥祛魅的效应,乃至促使充满非认知价值负载的整个人类社会展开现代化的历史转型呢?
美国成为独立国家后,国会建议全国人民每年庆祝感恩节。乔治·华盛顿建议把11月26日的这天定为感恩节。1863年,在漫长而血腥的内战结束时,亚伯拉罕·林肯要求所有的美国人把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作为感恩节。
通过式(5)综合评价函数计算天津地铁1号线各站的综合评价值,将综合评价指标值最大的营口道站的数据定为1,对其他车站的综合评价值进行同比例处理,得到评价相对值,如图2所示。
只有澄清了“需要”把事实与价值联结起来的枢纽作用及其包含的“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的内在分类,我们才能揭示价值中立为什么对于所有科学研究来说都不仅可能、而且必要的基本理据:当某个事实有助于人们满足某种需要的时候,它就会在这方面对人们具有善好的价值,反之则会具有坏恶的价值。进一步看,所涉及的需要种类不同,事实对人具有的价值种类也会不同。〔16〕韦伯在讨论后来被某些论者把玩良久以致变得玄乎其玄的“诸神之战”时提到的“真”“善”“神”“美”等“终极”价值,要是再补充一个可能有些俗气因而不被他看重的“利”,便分别来自人生在世的五种基本需要:认知、道德、信仰、炫美(审美)、实利(功利)。〔17〕其中的认知需要更是独树一帜,不仅能把事实变成价值——推动人们从事认知行为把握各种事实,以获得具有“真值”(亦即韦伯说的“科学价值”)的正确知识,而且还能把价值也变成事实——推动人们在韦伯说的“文化科学”亦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把人生在世的种种价值也当成被认知的事实来描述和分析。
于是,我们就能从中发现某种前后抵触的自相矛盾了:一方面,韦伯不仅承认某些有着宗教倾向的科学家会努力在理性化的科学研究中寻找通向上帝之路,而且还指出神学就是把人们的信仰体验加以理性化或理智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在他看来,科学祛魅的矛头所向首先又是对准了充满神秘体验的信仰领域,以致理性化的科学不仅与非理性的宗教彼此对立,而且似乎也与理性化的神学相互冲突。这样一来,韦伯的两个原创性理念便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了:如果说理性化本身就是科学祛魅导致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为什么他提到的那些凭借逻辑思维的理智工具建立起来的理性化神学在祛除了魔法巫术的种种魅惑之后,非但没有促进、反倒还在许多情况下阻碍了相关文化传统走向现代化?比方说,中世纪晚期基督教的神学理论在汲取了古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后实现的高度逻辑化、理智化和体系化,为什么非但没有祛除,反倒还强化了这种唯一神信仰对于人们的诱惑魅力,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如果像韦伯所说,科学与神学在具有高度理性化和理智化的逻辑结构方面具有无可否认的形式共通之处,那么,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实质性内容首先在它们之间,然后又进一步在认知与信仰这两个价值领域之间生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对立,以致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性化科学祛魅注定了会迫使某些宗教方面的终极价值销声匿迹而遁入隐晦领域呢?毋庸讳言,这个问题不解决,韦伯的两个标志性理念之间就同样摆脱不了无法消解的内在张力,以至于它们在人类思想史上做出的原创性贡献也不得不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三、价值中立的认知需要
解铃还须系铃人。可能连韦伯也没有意识到的是,能够帮他走出这座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的理论迷宫的,是他自己在这篇讲演里点到为止地阐发的另一个虽然也有标志性意义,却不像前两个理念那样受到高度关注,甚至还常常受到种种质疑的深刻理念:“价值中立”。
韦伯是在谈到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时倡导价值中立的,认为“文化科学”的研究主体虽然可以针对研究对象持有或赞成或反对的价值评判态度,但在学术研究中却应当像自然科学的研究主体一样,“只能要求自己保持理智上的诚实整一,清晰地认识到下面两件事的差异:确认事实、数学或逻辑状态、文化价值的内在结构是一回事,回答文化及其具体内容有什么价值、人们在文化共同体和政治社团中应当如何行事的问题是另一回事。这是两个完全异质的问题……科学家给出自己的价值评判之时,就是他对事实的充分理解终结之时。”〔15〕不难看出,如同其他许多问题一样,韦伯的这些微言大义再次陷入了逻辑上不自洽、实践中会自败的窘境,集中表现在由于恪守事实与价值不共戴天的二元对立架构,他始终未能令人信服地回答下面的问题,以致直到今天人们还对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能否保持价值中立充满了疑虑:如果说“科学”本身也像他提到的那样构成了与信仰、炫美、实利、道德等并列的一个“价值领域”,人们怎么可能在学术研究中维系“价值中立”呢?如果说“给出价值评判之时就是理解事实的终结之时”,文化科学的研究主体又该怎样把充满价值负载的“文化价值的内在结构”也当成了与“数学或逻辑状态”乃至日月山川相类似的“事实”来描述和分析呢?由此可见,将韦伯定位于“矛盾重重的思想家”的确是所言不虚:他虽然大力提倡价值中立,却又说不清楚其内在机制,反倒还陷入了种种悖论。
在讲演里强调古希腊科学运用逻辑思维的理性工具追求永恒真理之后不久,韦伯曾引用了17世纪荷兰博物学家斯瓦姆默丹的一句话:“我解剖跳蚤,向你们证明上帝的神力”,并对此评论说:“各位可以看到,当时的科学研究在新教和清教的间接影响下把什么当成了自己的使命:找到通向上帝之路。……但科学这种与上帝疏离的力量怎么能够成为通向上帝之路呢?今天已经没有人会在内心深处怀疑科学对上帝的疏离了,无论他们是否乐意承认这一点。摆脱科学的理性主义和理智主义,是与上帝同在的生命的基本前提——这已经成为当下那些有着宗教倾向或寻求宗教体验的年轻人的口号了。”〔13〕而在讲演快结束讨论理性化的神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时,他也坦诚指出:虽然神学作为“在理智上针对宗教拯救体验的理性化”存在于许多宗教传统之中,由于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影响甚至还在基督宗教那里呈现出了高度的体系化,但他们的假设却“超出了‘科学’的界限,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知识’……正是由于神学的缘故,‘科学’与神性这两个价值领域之间的张力才是无法消解的”〔14〕。
明白了这个关键点,我们就可以补上韦伯在科学祛魅与理性化关系问题上留下的那个漏洞了:从根本上决定了科学具有祛魅效应的,并非被科学仅仅当成了工具来运用的理性因素,而是能在价值中立中与非认知需要分离开来,构成了科学产生的唯一动机的认知需要。本来,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会出于认知需要描述各种事实的存在状态及其是否能够满足自己非认知需要的价值属性;但在这类情况下,人们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将两类不同的需要混杂在一起,甚至倾向于用非认知需要引导和约束认知需要,结果导致认知行为不是如其所是地揭示了事实真相,而是在非认知需要的干扰下扭曲甚至遮蔽了事实真相,诸如把雷鸣电闪说成是上天发怒,把风调雨顺说成是神灵眷顾,把邻居患病遭灾说成是恶魔附体,把家人健康平安说成是祖先显灵等等。不难看出,韦伯指认的科学旨在祛除的那些“魅惑”,无一例外地都是因为两类需要的纠结缠绕才生成的,尤其会在非认知需要的牵强附会下给各种事实涂上高深莫测的神秘色彩,所以才会由于貌似既能满足认知需要,又能满足非认知需要的缘故,对人们形成难以抗拒的非认知诱惑魅力。更严重的是,哪怕人们已经能够自觉熟练地运用逻辑思维的理智能力了,也不足以单靠这种理性的工具就将两类不同的需要严格分离开来而祛除魅惑,反倒有可能在非认知需要的强力诱导下,将认知维度上的理性能力也变成了助长非认知魅惑的有效手段。韦伯在前面引用的那段论述里语焉不详地提到的神学的假设“超出了‘科学’的界限”,说穿了其实就是指,尽管神学也拥有自己的理性化或理智化概念体系,但它们却不像科学的理性化或理智化概念体系那样纯粹是基于认知需要建构起来的,而主要是基于信仰方面的非认知需要建构起来的,所以“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知识’”,反倒不可避免地包含着灵性生活中的种种非认知魅惑。
从这个角度看,韦伯主要是由于既不了解需要的枢纽作用,也没有区分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的缘故,所以一直未能证成在所有科学领域(尤其在拥有厚重价值负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实现价值中立的可能性问题:首先,价值中立原则并不是主张研究主体不应当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追求正确的真值知识、拒斥错谬的假值知识,而只是要求人们将自己本来拥有的非认知需要暂且悬置起来,不去评判或诉求研究对象在实利、道德、炫美、信仰等方面的任何非认知价值,仅仅基于认知需要去描述和分析它们作为存在之事实的本来面目。换句话说,价值中立只是要求科学研究对于非认知价值保持中立,并没有(也不可能)要求科学研究对于认知价值同样保持中立。其次,只要把非认知需要悬置起来而单纯基于认知需要,即便对于那些本身充满了非认知价值关联的“文化价值的内在结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主体也完全可以把它们当成存在的“事实”来描述和分析,并且像自然科学那样得出如实揭示“真相”、符合“科学”标准的正确结论。
电热鼓风干燥箱(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电子天平[AL104,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司];智能温度控制器(TY-300A,常州澳华仪器有限公司);数显电动搅拌器(RW 20 D S25型,德国IKA实验设备有限公司);变频高速搅拌机(GJD-B12K,青岛百瑞达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由于类似的原因,我们也不能再像韦伯以及流行的观念那样,仅仅把科学的产生归功于古希腊哲学重视逻辑和概念的理性精神了。毋宁说,科学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在于韦伯虽然已经提到、却没有自觉辨析的柏拉图洞穴寓言隐含的有关“(基于认知需要的)真理”与“(基于非认知需要的)意见”的鲜明区分,尤其在于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的“闲暇”与“好奇心”的内在关联,“人们研究科学只是为了求知,没有任何实用的目的,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得到证明:人们总是在获得了几乎全部的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娱乐品之后才会从事这类研究。所以很明显,我们追求知识不是为了其他任何利益。”〔18〕遗憾的是,韦伯尽管也谈到了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方面的重大贡献,却未能察觉到他这段名言已经涵盖了自己倡导的价值中立原则的全部要点了。进一步看,韦伯谈到的文艺复兴运动发现的科学研究的另一个伟大工具“旨在可靠地控制经验的理性实验”,也是由于纯粹基于求知欲的缘故,才实质性地有别于古印度的瑜伽实验、古希腊的军事实验、中世纪的采矿实验以及炼金术实验等,并且最终让现代经验科学成为可能。〔19〕就此而言,无论理性思维还是感性实验,只有在纯粹基于认知需要的基础上加以运用,才能构成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反果为因地把它们说成是科学之为科学的决定因素,却遗忘了价值中立的认知需要这个可以说是“一票否决”的底线根据。
综上所述,无论科学的产生发展、还是科学的祛魅效应,归根结底都不在于韦伯青睐的理性化或理智化,而是在于价值中立的好奇心或求知欲。韦伯虽然提出了价值中立的理念,并把它说成是“科学自我节制的基本职责和防止愚蠢错谬的唯一方法”〔20〕,却又在事实与价值二元对立架构的误导下忽视了需要的枢纽作用以及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的内在区分,结果没有把这个标志性理念与另外两个标志性理念联系起来考察,最终错失了走出迷宫、找到谜底的良机。
四、科学的价值重载与现代化
所以,考虑到古希腊哲学理性精神对于科学诞生的这种促成效应,同时也考虑到科学发展对于理性工具的须臾不可离开的自觉运用,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否定理性化或理智化在科学祛魅以及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首先,正如韦伯提到的那样,人们的确会在合乎逻辑的理性思维的强大压力下,放弃那些有关自然万物、人类社会和自身存在的虽然充满种种诱惑魅力、却又虚幻扭曲地遮蔽了事实真相的错谬认知,转而接受那些虽然简单平实抽象枯燥、却又如其所是地揭示了事实真相的正确认知。其次,进入现代历史阶段后,我们也的确可以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现科学理性的弥漫性支撑作用,因为假如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法律规章、企业经营等等没有经历过韦伯描述的那种理性化或理智化过程,人类历史的现代化发展就不可能呈现出我们今天见到的这副模样。但尽管如此,连韦伯自己都没有否认的一个简单事实,却同样迫使我们在合乎逻辑的理性思维的强大压力下提出下面的质疑:科学祛魅以及现代化是不是真的能像他所说的那样,以单线条的因果决定方式最终归结为所谓的理性化或理智化呢?
问题在于,虽然韦伯自己经常在理论研究中将“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联系起来,并且承认科学研究能够扮演“工具理性”的角色,帮助人们找到达成既定目标的有效手段,但恰恰由于以“给出价值评判之时就是理解事实的终结之时”的非此即彼方式将事实与价值割裂开来了,他在讲演里要求科学保持价值中立的同时,又断然否定了科学能对价值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既然“各种价值体系之间存在无法消解的冲突……某种东西虽然不美、不神、不善,却可以为真”,那么,“在实践中为价值意见做出‘科学证成’就是不可能的了”〔21〕。不难看出,这位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思想家在此好像又遗忘了一点:倘若人们根本不可能在实践中为非认知价值意见做出科学的证成,他反复指认的科学祛魅便只能在认知领域内勉强发挥某种抽象苍白的空对空作用了,却没法起到他特别强调的那种把处于各种非认知价值关联之中的人类历史也给现代化了的实打实效应。于是,韦伯在此面临的自败式进退两难十分明显,要么转而承认价值中立的科学认知能够通过非认知价值重载对于人们的价值意见或价值体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要么根本放弃他自己原创的“现代化即理性化”口号。
其实,倘若我们放弃了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架构,承认科学认知能够证成非认知价值体系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既然价值只能经由需要的枢纽从事实中推出来,那么,如实描述事实的科学知识当然就不会像理性能力本身那样,仅仅发挥某种从属性的工具效应了;毋宁说,它们首先能够帮助各种应然性的价值体系找到自己立足其上的实然性事实基础。毕竟,无论在真的认知价值与利美神善的非认知价值之间存在怎样的张力对抗,后者如果缺乏稳固的事实基础,很容易沦为根底不牢、一触即溃的海市蜃楼。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证成过程中,只能凭借价值中立形成的科学知识还会给自己重新加上非认知价值的负载,从而不仅能在认知维度上发挥祛魅的效应,而且也能在非认知维度上对于实践活动发挥指导的作用。这一点也很容易理解:既然人们追求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原本就往往是与各种非认知需要纠结在一起的,仅仅出于避免生成魅惑、维系科学底线的考虑才让它们分离开来,那么,在获得了如实揭示真相的科学知识后,人们自然就不必再将这些科学知识束之高阁了,而完全可以把它们重新嵌入到这样那样的非认知价值关联之中,充分发挥它们指导自己达成各种非认知价值目的的实践行为的积极意义。
事实上,稍加分析就能发现,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谈到的科学精神对于西方社会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法律规章、企业经营、记账核算、宗教信仰乃至音乐建筑的全方位渗透,无一不是以“知识就是力量”的价值重载方式发挥出它把历史加以现代化的强大作用的。这里需要补充的只有一点,“知识”在此能够转化成实践中的“力量”,主要不是因为它们是逻辑思维的理性化产物。相反,正如它成为能够祛魅的“科学”靠的不是认知维度上的理性能力,而是意志维度上的好奇心或求知欲一样,它现在转化成实践中的“力量”靠的也不是认知维度上的理性能力,而是意志维度上种种非认知需要作为人们行为动机的基本效应,人们为了在实然性的事实基础上达成自己意欲的应然性价值目的,所以才基于意志维度上的非认知需要,把科学认知变成了指导自己的实践行为获得成功的强大力量。〔22〕与之对照,非科学知识之所以无从发挥这种把历史加以现代化的重要效应,也不是因为它们的理性化程度不够高,而首先是因为它们在本质上背离了价值中立、充满了非认知魅惑、扭曲了事实真相,结果常常把人们的实践行为不知引到什么地方去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如同“科学祛魅”的理念一样,韦伯有关“现代化就是理性化”的理念也有必要加以修正,因为严格说来,现代化的首要特征在于人类社会中各种非认知价值领域的“科学化”“祛魅化”,而不是仅仅在于这些领域的“理性化”“理智化”——尽管后者作为“科学化”“祛魅化”的助推手段,对于现代化的历史转型的确也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更不幸的是,韦伯思想的内在悖论到此还没有完结。如前所述,他虽然不仅要求科学研究保持价值中立,而且主张科学知识具有祛魅效应,乃至将人类历史的现代化也归因于科学祛魅的理性化,却又着力渲染了科学祛魅的现代化进程窒息某些“最高贵终极价值”、制造冷冰冰“铁笼”的负面效应,以致在讲演的结尾处声称:那些没法接受这种时代命运的人们可以静静地回归古老教堂的慈悲怀抱,而他们为了无条件献身于宗教做出的“理智牺牲”也不必受到批评,〔23〕由此呈现出了从指认“科学祛魅”变成赞同“信仰复魅”的复杂倾向。换言之,在这场探讨“以科学为业有什么意义”的讲演里,韦伯一方面主张科学知识无法证成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又宣布它作为真值知识的祛魅效应会消解善、神、美的高贵价值,妨碍人们找到通向真正的存在、艺术、自然、幸福之路,结果可以说几乎不认为按照他的要求应当努力保持价值中立、发挥祛魅作用的科学真理能够具有多少积极的人生意义,反倒更倾向于指责它们主要是在现实中扮演了添乱作怪的反面角色。于是从中又生出了若干韦伯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逻辑矛盾:第一,如果科学知识无法证成价值体系,那它如何可能通过祛魅效应消解终极价值?第二,如果凭借诚实的理智德性得到的科学知识能够揭示“真相”、具有“真值”、属于“真理”,那它怎么又会堵塞通向“真正”的存在、艺术、自然、幸福之路?第三,即便科学祛魅的现代化的确在非认知价值领域具有某些负面效应,难道这些负面效应不是应当首先归咎于那些在转型过程中重新加载于科学知识之上的非认知需要,而不能张冠李戴地归咎于韦伯自己强调的属于价值中立的科学知识本身?遗憾的是,部分地由于韦伯最后一个悖论的误导,当下国内外的科学哲学研究才往往陷入了某种无的放矢的错谬境地,把目前人类面临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道德失范等严重后果偏颇性地归罪于科学知识本身,而不是归罪于人们运用这些科学知识为自己服务的非认知需要。
本文旨在纪念韦伯的讲演发表一百周年,却既没有讴歌他的见解深邃隽永,也没有赞美他的用词文采飞扬,反倒四处挑毛病找漏洞,可能让人感到奇怪。但如前所述,鉴于历史上许多顶级思想家的标志性理念都同时伴随着内在悖论,这样做或许才是我们在科学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学术宿命。归根结底,只有以这种揭露悖论、还原真相的方式展开批评,我们才有可能把韦伯思想的深度内涵敞开出来,让他在倡导“价值中立”“科学祛魅”“现代化即理性化”三大理念方面对于人类思想史做出的原创性贡献发扬光大,从而实现我们在过了一个世纪之后依然还要来纪念这场著名讲演的真正目的。
注释:
〔1〕〔德〕席勒:《希腊的群神》,《席勒文集》第1卷,张玉书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8-44页。
在Amos 24.0中输出标准化路径系数图,结果显示,免费开放感知对公园满意度、地方依赖以及地方认同有正向影响,公园满意度对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有正向影响,但是“免费开放→地方认同”和“满意度→地方认同”的路径系数太小,地方依赖对地方认同有正向影响且路径系数最大,与预测测量模型大致相同.在研究后对模型进行修改,将“满意度→地方认同”以及“免费开放→地方认同”这两条路径删除,得到现模型(图3)以及变量相互之间的关系(表3),并进行拟合度检验,所有指标都达到标准水平(表4).
依据OSI七层模型,按照由下向上,层层相扣,逐渐加大难度,与理论知识紧密结合的原则,设计六组实验,如表1所示。设计思路是:新实验内容会涉及做过的实验所搭建的模型,通过使用前面的实验作为踏板进一步理解将要学习的内容。通过前面对网络性能的分析,也有助于后面综合网络性能的分析。通过对运行网络模拟环境所得图像分析,让学生了解影响网络运行的因素,找出解决和改进的方法,并通过报告得出希望的结果。
〔2〕〔3〕〔7〕〔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年,第4-16、79、143页。出于行文统一的考虑,本文在引用西方译著时会依据英文本或英译本略有改动,以下不再注明。
〔4〕任剑涛:《祛魅、复魅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试验所用的膨润土为河南省巩义市龙鑫净水材料有限公司提供的商业膨润土,其天然含水率为17.3%,其他基本特性见表1;其XRD衍射图,如图2所示。
〔5〕〔6〕〔12〕〔13〕〔14〕〔15〕〔19〕〔21〕〔23〕〔德〕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8-29、48、31、32-33、46-47、37-38、31-32、39-44、48-49页。
〔8〕〔英〕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刘东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4页;张德胜等:《论中庸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沟通理性之外》,《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
〔9〕〔德〕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03、32-33页。
〔10〕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239页。
〔11〕刘清平:《“理性”抑或“情理”?——读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博览群书》2003年第12期。
〔16〕刘清平:《怎样从事实推出价值?——是与应当之谜新解》,《伦理学研究》2016年第1期;《需要概念在人生哲学中的原点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17〕参见刘清平:《时尚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2页;〔德〕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9-40页。
〔1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页。
〔20〕〔德〕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5页。
〔22〕刘清平:《认知能够凌驾于意志和情感之上吗?——“知情意”排序的解构与重构》,《社会科学家》2017年第1期。
既往研究认为,JME难以治愈,即使癫痫长时间内得到控制,绝大多数病人也需要终生服药。近年来有些长期随访研究提示,在一些JME患者中,并不需要终身服用抗癫痫药物,停药数年后仍可保持发作终止,预后良好,有望治愈[28-29]。JME预后与发作类型、确诊时间、用药情况、脑电图表现等诸多因素有关,早期正确诊断,特别是赶在GCTS出现之前给予及时合理治疗,预后会更好,因此,更多的临床医生加强对此病的认识和判断,非常有意义。
作者简介: 刘清平,哲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武汉传媒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比较、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美学。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4.003
〔责任编辑:汪家耀〕
标签:韦伯论文; 科学论文; 祛魅论文; 理性化论文; 现代化论文; 价值中立论文;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论文; 武汉传媒学院人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