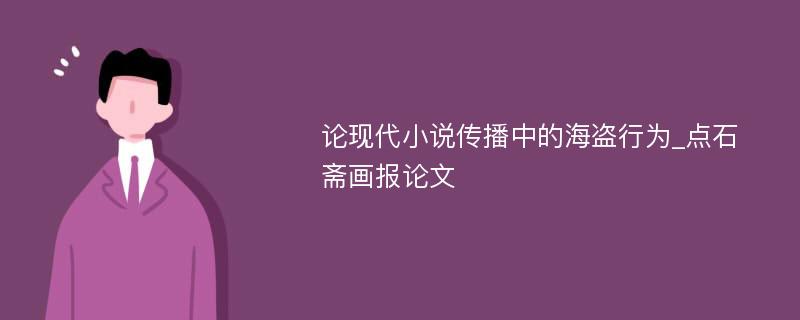
论近代小说传播中的盗版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小说是衔接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过渡环节,无论是出版的技术与速度、读者的层次与规模,还是作家的多寡及其创作理念、小说地位的高低以及官方的态度,古代与现代都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在近代,小说发展系统中各要素都应时代潮流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使古代与现代这两种落差巨大的小说状态相连接。在小说发展系统各要素中,传播环节最先发生变化。它以引入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与设备,以及报刊出版为标志,鲜明地体现出历史步入近代后的时代色彩。它造成小说史上从未有过的庞大读者群,这也意味着巨大利润空间的形成。社会处于变化动荡之中,出版业在迅速发展,但人们对有关出版的各种观念却没有相应地进入近代,更遑论相关的法律法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的诱惑使盗版一度成为小说传播环节中的突出现象。在这期间,盗版曾是新法印刷冲击传统出版业的方式之一,但更多地是不正当竞争的手段,同时它也刺激了人们版权意识逐渐树立,而由于盗版在某些方面也显示了读者对具体作品的好恶,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创作与翻译。 在古代,传统的印刷方式制约了出版规模,那时人们也不甚讲究版权概念。诚然,经济利益受损害的书坊主对盗版会深恶痛疾,但这一般并不被视为恶行,它在法律上更未被禁止。有的作者认为,作品被翻版正说明自己的才华受到众人赏识,他们甚至对这种扩大作品影响之举心存感激。在进入近代后的很长时间里,情形依然如此。道光年间,梁恭辰著成《劝戒近录》,他在《序》中写道,辛苦著成后,“尤不愿人束之高阁”,于是便自费刻印,“分送远近”。梁恭辰并无牟利算计,而只是怕读者不多,传播不广。后来他得到书被盗版的消息,认为是值得高兴的好事,而将它写入《劝戒续录》的《序》中:“不数月,而吴门遂有翻刻袖珍本出。”那本《劝戒续录》行世不久也被人翻刻,梁恭辰在《劝戒三录》的《序》中又郑重记载:“岭西亦已有翻本。”梁恭辰接连著录书被翻刻事,意在证明大家都欣赏自己的著述,“如是人情固不甚相远哉”。叙述时所用“不胫而走”四字,很能显示他的沾沾自喜。在道光年间,像梁恭辰这样的注重名声而忽略金钱的士大夫还不少,其实就是到了光绪年间,仍有些人专意于创作或翻译,脑中根本没有权益保护的概念。林纾与王寿昌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是借以抒发丧妻之痛,译成后也只是自费刻印一些送同人欣赏而已。当昌言报馆向他收购版权时,林纾大为惶恐,担心收下钱会妨碍自己的名声。昌言报馆根据林纾的要求在报上刊载广告:“拟以巨资酬译者。承某君高义,将原板寄来,既不受酬资,又将本馆所偿板价捐入福州蚕桑公学,特此声明,并志谢忱。”①后来林纾小说翻译得多了,对出版界情况也渐了解,受环境影响的他开始注意保护自己的版权,对稿酬的要求也毫不客气,不过这已是光绪末年的事了。 近代的版权观念是随着西方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而传入中国,因为它导致了印刷规模的骤然扩增,所涉及的经济利益比以往不知要大多少倍。到了光绪二十年左右,上海地区基本完成了印刷业近代化的改造,但其他地区却仍暂时在传统印刷方式的掌控之下,人们的意识一仍其旧,有些人出版了书籍还是不反对乃至欢迎别人翻刻。光绪十六年(1890),“文光楼主人”刊刻了《三侠五义》的续书《小五义》,其友“知非子”在《序》中写道,这位书坊主宣称“有乐意翻刻者,则幸甚,祈及早翻刻”,理由是“此《小五义》一书,皆忠烈侠义之事,并附以节孝戒淫戒赌诸则,原为劝人,非专网利”。倘若众人翻刻,“庶广传一世,岂非一大快事哉”。一位书坊主为了道德追求,难道愿意放弃应得的利润?这有可能是真心话,由此也可得知,在当时许多人看来,翻刻并非是应受道德谴责,更别说法律追究的行径。其实,《小五义》一旦售行于世,别人是否翻刻已经完全不由“文光楼主人”所能控制。声明不许翻刻、但翻刻本遍行的例子比比皆是,原刻者徒唤奈何几成通例。既然如此,还不如高调标榜为维护忠孝节义所作的贡献,同时原刻本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小五义》原刻本刷印了五千余部,这在当时可是个相当大的数字,所得利润也将颇为可观。 《小五义》果然被翻刻了,仅仅只过四个月,申报馆翻刻本就已行销于世,而且要使“文光楼主人”气塞的是,该本绝口不提文光楼,只是含糊地称“本馆觅得都中善本”。能无顾忌地隐去原刻者,前提自然是当地读者并不知情,而翻刻本行世后,文光楼本更是几无进入南方市场的可能。“文光楼主人”依据传统习惯,强调忠烈侠义等劝善惩恶内容,翻刻本遵循市场法则行事,注重迎合读者喜好,只宣传“事迹新奇,笔情天矫,空前绝后,生面别开”②。申报馆得意地宣称其印本“早已不胫而走,寰宇风行”③,可见收益相当丰厚。不久,文光楼又推出《续小五义》,这次不再有欢迎翻刻之语,但尝到甜头的申报馆还是立即翻刻。十个月后,申报馆宣布《小五义》与《续小五义》业已售罄,再次翻刻,并减价销售:“兹又续印成书,成本较前稍减,是以格外从廉出售,以飨阅者之心。”④两书均减一角五分,约是七折销售。减价的理由冠冕堂皇,但只要了解当时翻刻情形,就不难明白其用心。其时有多家翻刻,有的售价甚至高到每种八角,申报馆显然是想用低廉价格击垮竞争对手。翻刻诸家中,上海书局等采用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善成堂等则采用传统的印刷方式。这固然是一场围绕《小五义》销售的竞争,同时也使人感受到新、旧印刷方式的竞争,而在版权观念未树立的当时,竞争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居然竟是盗版!这种竞争的结局毫无悬念,更何况当时申报馆已认定以新法出版小说是其重要财源之一,并有计划地添置设备以瞄准小说市场。上海地区其他拥有先进印刷设备与技术的出版机构也不甘落后,传统的小说出版根本无法抵御这股来势汹汹的浪潮。新法击败传统的小说出版的另一典型例证,是《野叟曝言》的出版遭遇。这部乾隆间的长篇小说首次由汇珍楼搜得秘本出版,售价每部六元,但当时并无注册版权的意识与法律环境,于是没多久《沪报》就在报上连载该书,不仅是新法印刷,而且运用了新的小说传播方式。接着便是申报馆版的《野叟曝言》行世,它每部仅售一元。书价差距如此之大,充分体现出了先进印刷技术的压倒优势,于是后来只见申报馆版的再版,而汇珍楼版在市场上则是销声匿迹了。 近代著名文学家王韬两本小说集的遭遇,很能说明当时版权意识在作家以及出版机构心目中的地位。光绪元年,应申报馆请求,王韬将小说集《遁窟谰言》交其出版,谁知“刊布未几,而翻版者四出”。王韬亲眼在书肆中看到一本《闲谈消夏录》,竟是将《遁窟谰言》与朱翊清《埋忧集》“编撮成书,借以弋利”⑤。眼见别人拿自己的作品“弋利”,自己一无所知且一无所得,王韬自然很不高兴,但他光绪六年时又将此书交与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出版,在今天看来,此举已构成对申报馆版权的侵犯。不过此事似未被追究,王韬与申报馆也一直维持着较好关系,由此推断,版权究竟归于作者还是出版者,同一部书稿是否可交与不同的书局出版,当时似乎都未有共同的规范。 光绪十年,到申报馆任职的王韬带来了小说集《淞隐漫录》,议定先连载,后出版单行本。《点石斋画报》从第六号开始刊载了三年多,正当连载即将结束时,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的《申报》上刊载了《石印〈后聊斋志异图说〉初集》的销售广告: 长洲天南遁叟,文坛健将,墨海闲人。是书为渠极得意之作,用笔仿乎《聊斋》,命意等于说怪。以数十年之阅历,数万里之遨游,所见闻之侠女高人、灵狐老怪以至青楼妙妓、白屋书生,凡有可惊可愕可敬可喜之事,无不曲意描摹,正所谓长篇不嫌长,短章不嫌短者。兹特不惜工本,抄成工楷,复请吴友如先生逐节绘图,同付石印,七月望日成书。吾知此书一出,实可与《前聊斋志》后先媲美矣。每部用红木夹板,洋二元,在上海棋盘街宝文阁,并各书坊发售。味闲庐启。这部《后聊斋志异》,就是《淞隐漫录》中已被连载的内容。当初“尊闻阁主人”一再索讨,花了大价钱方得到《淞隐漫录》书稿,《点石斋画报》又花费许多精力财力,如请著名画家吴友如逐节绘图。可是按广告所言,读者都会误认为从索稿到插图纯为味闲庐的精心安排。申报馆计划先连载,保证《点石斋画报》的销售,然后再结集出版,再获取一次利润,如今凭空冒出一个味闲庐横刀夺爱,强抢它计划中的利润,这如何忍得?可是申报馆所能做出的最强烈反制措施,也只是先由王韬发表声明,责以大义:“是书乃由点石斋主人出重价购来,以后或照印,或排纂,或付剞劂氏,惟点石斋主人可为,即天南遁叟亦不得擅自刊售”,因“已受书价故也”,即申报馆的权益不应遭到侵犯。王韬又责问道:“乃今者既不商之点石斋主人,又不下询之余,绝不一言,毅然竟为,抑何巧取豪夺一至于此。”⑥由王韬的声明可知,实际的纠纷,已迫使当时一部分人开始思考版权问题。可是,味闲庐第二日在《申报》的回应却表示,它根本不承认申报馆拥有什么权益,自己唯一可感到“歉愧”的,只是事先未与王韬打招呼,但这也有原因:“本拟预先陈明,只缘向未识荆,不敢造次。”对于擅自出版他人作品则理由十足:“文章为天下之公器”,看不上的我们还不印呢!⑦这也等于在暗示,它压根没考虑过要给王韬什么报酬。味闲庐并非首开先例者,也无任何法规明言禁止。申报馆实际上是认同,至少是不想公开反驳味闲庐的理由,因此它并不出面,只是利用自己的便利,在味闲庐的启事旁刊载《新书出售》广告,宣布正版《淞隐漫录》即将出版。作此宣布后,又在其旁再刊一则广告,预告《点石斋画报》即将连载的《淞隐续录》,届时也将结集出版,同时又批评味闲庐所为“殊非雅道”:“特不思同是一书,同在一地,彼既为捷足之先登,我遂不觉瞠乎其在后;我则劳而无获,彼则安享厥成,言利则诚有得矣,揆之于理,窃未安也。”⑧味闲庐窃取了申报馆的成果,但它毫无羞愧,甚至同在《申报》上振振有词地申辩,可见在当时人心目中,盗版并不受禁止,最多只是受点非议,而申报馆也不强调版权,只是批评“殊非雅道”而已。在健全的秩序未建立前,大家都寻觅机会打混战。实际上申报馆也在翻刻他人之书,三年后它翻印文光楼的《小五义》、《续小五义》的举动,在本质上与味闲庐又有何差别? 以“文章为天下之公器”为由擅自出版他人作品,这正反映了当时上海地区出版已基本完成近代化改造,但人们维护出版秩序的思想却未及时跟上的情形。先进印刷设备与技术的引入使出版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突飞猛进,读者群不断扩大,书价的下降又促进了这一趋势。利润空间也在快速扩张,而约束获取利润手段与途径的机制却未相应形成。大家都怀着“文章为天下之公器”的念头,只要有利可图,看到别家的书籍销路甚好便拿来照印。生产的近代化与维护正常秩序机制未形成的脱节,使小说发展第一次遇上了盗版频仍的局面。 由于开埠、列强设立租界、资金与人口以及各类文化精华因战乱大批流入、率先引入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等各种历史条件的汇集,上海从光绪初年开始逐渐成为全国小说创作与出版的中心。出版的规模与速度都远超以往,利益的驱动使小说盗版很快在这里成为较突出的问题。报上常见盗版者堂而皇之的推销广告,而就在这类广告旁,又时载出版者反击的告示。上海新闻业起步早,发展快,通过那些报纸上各种广告、告白,可梳理出当时小说盗版的大致情况,以及出版者不得已的应对措施。整个出版业在动荡中快速发展,出版无序的乱象也随之滋蔓。“罂湖居士”序《玉如意》时写道,此时说部书籍虽是“枚不胜举”,但“类皆重印翻刻”,有的作品甚至是“日下翻印甚多,原本无几”⑨。此时无法从法律乃至道德层面借助力量约束盗版,被盗版者反而是孤立无援,只得自行设法维护权益,有时想出的应对之举十分笨拙甚至可笑。改七芗的《红楼梦图咏》出版仅两个月,翻刻本已在流行。出版者只好刊载广告提醒读者:“近有翻刻本,虽依样葫芦,而丰姿大减,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明眼人自能辨别也。”如何“辨别”呢?方法是“现用书面加‘孙溪逸士过眼’印章,以别原刻、翻刻鱼豕之混”⑩。这最多只是给盗版者增添些小麻烦,仿其样加盖印章又有何难?当时采用此法者还不止一家。洗红馆委托点石斋石印了绘图《列国志》,因销路不错,“无耻之徒累用原书照印,以图影戤射利”,“另有铅板将原图石印混充者”。由于书已销完,洗红馆不甘利润全被翻刻者占有,便又委托点石斋重印,并且“书面加‘光绪二十年秋七月重印’,另盖‘双悟书屋鉴定’印章,末页盖‘原图原书,翻印雷殛火焚’一戳”,“如无此二章记,即系赝鼎”(11)。可是盗版者似乎并不在乎“雷殛火焚”的恐吓,两年后洗红馆再次重印宣传时,反盗版便是重点内容,眼见加盖印章作用不大,于是又想出个笨招:“惟本斋全书共五百二十八页,计绣像四十八个,绘图二百十六个,如有缺数,即非原底。”(12)据此推测,盗版书可能为节缩纸版删去了部分图像,可是读者购书时还要分类点数验明正版,指望此招奏效恐怕太不靠谱。 应对翻刻的第二法是刊登广告讽刺或痛斥,稍泄胸中恶气,同时也借此告诉读者,自己所出的正版书质量才最为可靠。光绪二十六年,江南书局在上海代销香港中华印务总局的《中东大战演义》,它还来不及广为宣传,盗版书即已行世。理文轩在当年二月二十八日《申报》上刊载广告,售价六角。广告中将全书三十三回回目悉数开列,占了不小的版面,可谓是不惜工本。二十天后,江南书局在《新闻报》上反击:“近闻申江有店乱将无用浮文、淫污伪书改名,登报高价惑世者,较本局何啻霄壤,识者自能区别。”此广告之右列又强调“新出全图《中东大战演义》四本一角五”。此列用大字排列,以示醒目。三天后,江南书局又专为此书在《新闻报》上刊载广告:“近闻某书号用铅板宋体翻照,字迹模糊,登报骗世,竟有阅报者被迷,化洋六角买回,岂非大受诳骗。”接下来,便是对理文轩的挖苦嘲笑:“想该号贪利如此,竟不要做下次生意。哈哈!”相比之下,点石斋对味闲庐的嘲讽,使人感到有点像赌气:“嗣后若有蹈此弊者,则本斋所印数千部,尽当奉让,请给价值。”理文轩与文宜书局几乎同时出版《大明奇侠传》,其实都是翻刻道光间《云钟雁三闹太平庄》,但它们都自视为正版,两家在光绪二十年七月十六日与十七日的《申报》上互相对骂。理文轩斥责文宜书局版内容不全,“殊觉可恶”,文宜书局则干脆开骂:“你头虽未伸出,谅你眼亦瞎矣。你之铅板错字甚多也,火油气味也,数月走油变为黄色也。”对盗版者的挖苦、嘲笑、痛斥甚至谩骂尽可以尽情,但这怎能使他们因此而垂手止步呢? 降价是反击盗版的第三种措施。味闲庐盗印《淞隐漫录》售价二元,申报馆则宣布自己的正版只售一元。同文分局代广百宋斋石印的《廿四史演义》因遭翻刻,只好减价每部仅售一元(13)。降价意味着经济上蒙受损失,而且还未必就能将盗版者逼出市场,因为后者也可降价,而且它本来就成本低廉,光绪十二年同文书局的《图咏聊斋》便是一例。同文书局为这套书的出版投入相当可观,不仅广请名家,“每幅画成一图,题以七绝一首”,而且“书用端楷抄成,并将吕氏原注移系逐句之下”,又精心校对,“不但无一差字,即破体俗字亦皆悉心勘正”(14)。这部书未能逃脱凡畅销必遭盗版的命运,同文书局不得已宣布“情愿减价售出。每部码洋四元”(15),后来由于仍然敌不过盗版书,只好再次降价至一元二角,并恳请读者“细辨墨色纸张”,购买正版(16)。广百宋斋在光绪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的《申报》诉苦道,它出版的绘图《西游记》被人缩小翻印,只好减价到一元二角,这已是“仅收工本洋”,再降就亏本了。盗版书尽管被批评为“字迹糊涂,纸墨恶劣,图像不清”,但它只售五角,据说是“核算仍称厚利”,竞争力仍强于正版。总之,降价导致经济损失,却未必能击垮盗版者。 广百宋斋在《申报》上刊载的那则广告题为《查究翻书》,除诉苦外还发出了警告:“俟访确翻印奸商名号,再当送县究办,以儆刁风而安商业。”可是究竟怎么“访”,又如何“究”的,后来都没了下文。在广百宋斋之前,也偶尔有人提出类似的主张。光绪五年《红楼梦图咏》问世时,九月十七日《申报》上的广告就宣称:“深虑翻刻翻印,转失名人本来面目,现以存案。已蒙中外官宪批准存案备查,不准别处翻本。”可是后来该书盗版本照样在市面上出售。光绪二十五年,昌言报馆合印《巴黎茶花女遗事》等作时,于三月十五日与四月十七日分别在《中外日报》与《新闻报》上郑重声明“现本馆特向译书之人用巨资购得”,“书经存案,翻刻必究”。在光绪二十八年前,目前所见请求官府保护小说版权的资料也只有这零星三则。这都是在警示可能的盗版者,但书却仍被翻刻,官府也没出面干预。原因很简单:盗版书市面泛滥,但盗版者却不知为何人,无头官司不会被受理。而且,诉讼又是件很麻烦的事,不仅费时费力,经济上也须付出代价。所以在二十多年里,尽管盗版已渐渐在舆论上成为大家痛恨、不齿的行径,但未见有人选择司法解决的途径。 庚子国变后,无论是作者、译者或读者,人数都急剧增加,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后,小说阅读市场与相应利润空间更是空前扩大,同时盗版现象快速滋蔓,出版者遭受的经济损失也远多于以往。文宝书局曾埋怨说,那些盗版者“但知见有消(销)路,不知消(销)路从何故而来也”,其余不论,该局每年仅用于报上刊载书籍出版广告的费用,就“足有一千元之费”(17)。巨额的经济损失使正常出版者忍无可忍,被逼无奈的他们最后只有诉诸法律,请求官府干预。市场要从无序整饬为有序,这其实也是唯一有效的途径,而此时西方保护版权的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土,于是从法律层面制裁盗版更是成了势在必行之事。 最先大张旗鼓寻求法律保护的是维新派创办的广智书局,该局当时出版了大量包括小说在内的各种书籍。梁启超等人比较了解西方保护版权情况,身处流亡之中的他们要继续宣传维新主张,也迫切需要经费上的支持,对此尤为上心。书局经理冯镜如是香港人,故向英国领事馆提出申请,领事馆旋向苏松太兵备道发出照会,后者除颁发禁令外,又要求下属各县照办。于是上海地区道、县两级都为广智书局颁发了“嗣后不准将广智书局刊译各种新书翻刻出售。如敢故违,定干查究”(18)一类的禁令。文明书局“诚恐书贾射利,易名翻印”,它在创办时便向官府申请版权保护。上海道六天后即颁发禁令“示仰书贾人等,须知文明印书局编译各种书籍,均系该职商等苦心经营而成,尔等不得私易书名,改换面目,翻印渔利。倘敢故违,一经该职商等查知,许即指名具禀,本道立即提案不贷”;又“函致租界领袖、美总领事暨分行县廨一体立案示禁”(19)。嗣后,众书局与报刊纷纷效仿。留日学生组建的译书汇编社远在东京,因“上海各地书贾恶习,往往将他人善本翻印射利”而向上海道申请立案,后者“除分行县廨一体立案外”,并颁发禁令:“为此示仰书贾人知悉,毋得将该社立案各书翻印渔利,致干查究。”(20)其时上海有各国租界,许多出版或盗版活动就发生在这里,因此同时也要请租界当局出面保护。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六日,通社在《时报》上刊载《声明版权》:“所有通社出版各种书籍,前曾禀请道宪及英、法廨,出示禁止翻刻在案。”即它同时向上海道以及英、法租界提出申请。也有的是向上海道呈交申请,再由上海道照会各国租界,小说林社就得到上海道的“札饬县廨,一体禁示,并照会租界领袖总领事馆立案,以重板权”的批示(21)。这类广告一时颇多,商务印书馆还直接向中央政府的商部暨京师学务处立案,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得到“禁止翻印”的批示后,便通过《中外日报》、《大公报》广而告之,而它出版的《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鲁滨孙漂流记》与《澳洲历险记》等小说,还同时被选为“学部审定宣讲用书”向全国推行,这更是它津津乐道的事。文明书局也曾向北京学部申请保护版权,并得到批复:“嗣后文明书局所出各书,无论编辑译述,准其随时送候审定,由本大学堂加盖审定图章,分别咨行,严禁翻印。”大学堂事务大臣兼吏部尚书张百熙对“书贾之谋毁版权,心最巧诈”极为痛恨,他曾拟定过“暂定应用书目”,“咨发各省翻刻印行”,结果被解释为允许翻刻书目,使他“殊堪痛恨”。张百熙批复文明书局呈文时又提及此事:“此等市侩设想,断非士类所为。因答该司员来呈,纵言及之,亦以见牟利者之何所不至也。”(22) 同时,出版界内部的版权关系也开始梳理,特别是报刊连载小说较普遍时,何人有权出版单行本的问题尤为人关注。《新小说》连载《离魂病》完毕时,特地声明“特将版权售与上海广智书局,归其另印单行本出售。经已存案,翻印必究”(23)。此举表明,作品一旦发表,版权即归刊物所有,与著译者已不相干。相反的做法也有,《中外日报》刊载《日本军神广濑武夫传》与《七日奇缘》时,于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一日刊载《本馆特别广告》:“本馆所译印之小说,其板权已议定归诸译人,外间书肆不得翻印。如违,定当控究,谨告各书肆幸勿尝试为要。”不过,该馆一年半后即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九日又宣布:它请人“译得《海卫包探案》数种”,连载结束后,“由本馆改印单行本出售。藉告各书肆,勿得翻印,以致究诘”。由此语推断,版权已归报馆。其时多数书局或报刊,似乎都认为作品发表后,自己就是版权拥有者。小说林社曾专为此发布通告:各类稿件“由本社总撰述选定付印,版权归于本社”(24)。新世界小说社亦是如此:“入选小说,板权概归本社。”(25)《月月小说》创刊号就刊载《声明版权》,厘清版权归属:“本社所登各小说,均得有著者版权,他日印刷告全后,其版权均归上海棋盘街乐群书局所有,他人不得翻刻。”这是因为乐群书局是《月月小说》的经营者。一个月后,《月月小说》的《本社紧要广告》再次重申:“本报内所载各种撰稿,均由巨金购来,取有版权。”创刊方满月就要重申,似是已发现盗版迹象。该刊第十号上《特告》再次强调“本社刊登各部小说,著作板权均为本社所有,他人概不得翻刻重印。如经查出,定即禀究”,可佐证此推测。该刊第二年第二期的《紧要广告》,不仅重申版权,而且明确宣布:“即原撰译之人,亦不得擅自转售刊发。”显然已发生这样的事,《月月小说》才会如此反应。当年王韬责问味闲庐时,说《淞隐漫录》连载后出版单行本,“惟点石斋主人可为,即天南遁叟亦不得擅自刊售”,也正是这个意思。如今《月月小说》说得如此理直气壮,可见已是出版界的共识。 版权观念已经树立,书局报刊为保护自己权益作了许多努力,官府也发布了警告盗版者的告示,现在,就等着一桩官司来印证出版者努力的成效与官府的承诺了。 近代小说史上最出名的反盗版案例,是围绕着当时畅销于世的《官场现形记》而展开。作者李伯元其时为《世界繁华报》主笔,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作品开始在该报连载,四个多月后,已连载的十二回结集为初编由世界繁华报馆出版,其后也是十二回为一单元,以边连载边出单行本的方式连续滚动,同时又在各大报刊载广告造势。此作一面世,立即引起读者关注。国人已意识到官场的腐败与黑暗,但只是较朦胧的感觉,此作则形象地提供了立体景观的官场百丑图。国人欢迎这部小说,对官场更为愤恨与鄙视;而“官场中人无不喜读此书”(26),因为可借此揣摩上司或同僚心思,寻觅进身之途。这些现象都被李伯元写入宣传广告,更为其行销推波助澜。 身为报人兼小说家的李伯元很清楚盗版者的无孔不入,他自七月二十日到十月初不断在各报刊载广告,在《中外日报》上就至少刊载了十九次:“禀准捕房查办翻刻,各书庄幸勿误收被累。”可是小说三编出版才三个月,盗版书就已公然销售,编排与书价全同原作。盗版者是日本东京金港堂,运往中国代销的是朝日洋行知新社,自光绪三十年九月初七日开始,它在报上公然连续广告“现今在领事衙门备案,准本社出售,并禁止他人冒牌仿造”,“查出即禀提究不贷”(27)。盗版者时有,但在报上公开亮出名号,还禁止人家盗它的版,这种现象倒是首次出现。明目张胆,气焰嚣张,说穿了就是因为日本领事馆在撑腰。连续有好几天,这则广告竟与李伯元“各书庄幸勿误收被累”的告诫同时在报上刊载。日商在广告中玩了个诡辩,他申请禁止的是“假冒本社牌号仿造洋装式样”,与世界繁华报馆版《官场现形记》并不相干。 李伯元不能容忍自己心血任人肆意掠夺,其后的二十多天里,他做了两件事。一是与日本领事馆交涉,日本领事允诺“谕令停卖”;同时又向租界会审公廨起诉,因为世界繁华报馆与朝日洋行都设于英租界,而会审公廨已经受理,决定将“将托销之席粹甫传案严讯”(28)。这则广告在《新闻报》、《中外日报》上也是连续刊载。到了十月十一日,李伯元在《时报》上的广告又说:“近有席粹甫以翻刻本出售,已蒙会审公堂允准出票提拘。”所谓“出票提拘”,意味着席粹甫根本不理会传唤,拒不到堂。不仅如此,十月十五日,盗版者又刊载广告,其中三点尤可注意:首先,盗版《官场现形记》照卖不误,日本领事的“谕令停卖”只是骗人的话。其次,需批发者可与“本社经理人席粹甫接洽”,表明席粹甫仍在打理经营,被会审公堂列为被告事不必在意。最后,以往广告都署“朝日洋行”,这次却是“知新社主人弼本氏”(29),即日商亲自出面表明主角身份,言下之意是该找我论理,怎么却与我的代理人打官司? 这正是日本人的狡猾之处,因为起诉弼本氏,按不平等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案件应由日本领事审理,这意味着李伯元的官司必输无疑。李伯元之所以向会审公堂报案,而且是以“经理人席粹甫”为被告,目的也正是不让裁判权落入日本领事手中,何况租界当局曾批准过李伯元保护版权的申请。就在弼本氏刊载广告的当日,即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五日,会审公堂拘提抗传不到的席粹甫,李伯元终于赢得了这场官司。第二日,李伯元不惜工本用大字在《新闻报》、《时报》、《中外日报》等大报刊载《特别告白》醒目广告通报审判结果: 翻刻《官场现形记》者看,看,看!出售翻刻《官场现形记》之席粹甫前因抗传不到,经公堂出票拘提,昨日解讯,奉会审宪判席粹甫先枷三天。特此布告,各书坊、宝号幸勿误售受累。是盼。李伯元喜迎胜诉,枷号三日的处罚也不算轻,但由于国家主权丧失与领事裁判权作祟,受处罚的只是“经理人席粹甫”。但不管怎样,这毕竟是近代小说史上捍卫版权的重大胜利,而它又是围绕名重一时的《官场现形记》展开,故而更受人关注。后来不少书局都向官府备案保护版权,其中应有受此影响的因素。 李伯元胜诉只是个案,其后人们仍为屡遭侵权费神不已,因为要官府受理,前提是须知谁在盗版,这可是大不易。当时有部描写海上名妓女故事的《胡宝玉》,“初版三千部,未及二月已告罄”。销路红火必有翻刻,恼火的乐群书局所能做的也只是刊载广告警告:“如再私行翻印,查出定必究办。”(30)可是不知私行翻刻人何在,“究办”二字只是空话。眼见利润不断流失,书局权衡得失,决心悬赏侦探踪迹诡秘的盗版者。广智书局似最先行动,宣布对提供线索者奖二十元;“能亲自带到该翻刻之所指证者,即谢花红洋二百大元”。它还指出“在东西各文明国,以此等事为侵人权利治之,与盗贼同罪”,这是对中国尚无相关法律的遗憾(31)。文明书局也登报悬赏:“如有人确知翻印之家、能代扣留全书、来本局密告者,本局查确后,当以二百元奉酬,并将所获翻印之书,全数奉送,决不食言。”(32)当时还有些书局也都曾登报悬赏。向官府报案,同时为获取线索重金悬赏,这或可视为书局已摆开架势向盗版者宣战,其身后则有官府一定程度的支持,社会舆论已完全倒向反盗版一边。 此时,人们更迫切要求国家颁布相应法律。光绪二十九年,严复上书学部大臣张百熙,陈述版权立法必要性:“是故国无版权之法者,其出书必希,往往而绝。希且绝之害于教育,不待智者而可知矣”;若再不保护版权,“将从此输入无由,民智之开,希望都绝”(33)。学界与出版界对此也十分关注,上海书业商会出版《日本出版法》、《著作权法》等书,视其为“学界、出版界最要问题”(34),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介绍欧美版权立法的《版权考》。中国迟迟未就版权立法,学部大臣张百熙是主要反对者之一。他清楚国内呼声的强烈,也曾痛斥“书贾之谋毁版权,心最巧诈”,但基于全局的考虑表示反对。当时中国迫切需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各类书籍的翻译层出不穷,新式学堂课本也多采用译本。西方诸国强硬要求中国保护外国书籍的版权,一旦版权立法,这方面的经济支出将是不小的负担。面对列强的不断逼迫,国内学界与出版界又不断吁请,清政府终于在宣统二年十一月十六日颁布《大清著作权律》,涉及到著作权概念、侵权与处罚等各个方面。其第四十条规定,对盗版者“科以四十元以上四百元以下之罚金”,而且“知情代为出售者,罚与假冒同”;第四十一条又规定:“因假冒而侵损他人之著作权时,除照前条科罚外,应将被损者所失之利益,责令假冒者赔偿,且将印本刻版及专供假冒使用之器具,没收入官。”从此盗版不仅违法,而且一旦查实,损失将比投入大得多。 其实进入宣统朝后,由于出版界维权意识加强,明目张胆地盗印小说已较少见。新出盗版书往往玩弄一些花招,尽可能抹去明显痕迹。改良小说社曾宣告它出的小说,“中缝及封面等处,均刊有‘改良小说社印行’七字”(35)。这是预防性告知,并非有特指的作品。但该社确曾遭人盗版,它的《幻梦奇冤》被中国小说社易名为《血指印》出版,虽保留原有署名,但版权页上却是“翻译者东平太郎,著述者中国小说社”,书首另增“支那保黄人”的《歌词》,读者很容易误以为新作。其实,改良小说社也在干类似的事。它的《美人兵》实为新世界小说社的《冷国复仇记》,只是换了个香艳书名,因销路不错后来还再版。章福记书局的《改良新聊斋》初集所载为振亚书庄《新聊斋》的内容,只是原书序的题署“光绪三十四年菊月,茂苑省非子识”,被改为“宣统二年仲夏之吉,古盐补留生志于逍闲轩”。不过振亚书庄也无法较真,因为它是在翻刻光绪三十三年的醉经堂本。“补留生”此类事不止干过一次,他将洪兴全的《说倭传》删改为二十回的《中东大战演义全集》行世,将原书的自序改题为“宣统庚戌年孟秋月,补留生志于退思轩”。其时改头换面的手法还有各种,似乎就可以自辩为并非盗版。不过,这类勾当也很快被认定是违法。《大清著作权律》第三十四条规定,未经“原主允许者”,“就原著加以割裂、改窜及变匿姓名或更换名目发行”都属于侵损他人著作权应受惩处。不过法律的颁布并不意味着盗版现象就会绝迹,只要有利润,总有人会甘冒风险,只是行为将更隐蔽。 尽管国家已经立法,但有些盗版行为因人们不甚重视,仍然畅行于世,报刊上的小说转载便是突出的现象。对于这种侵权行为,《月月小说》比较宽容:“报界诸君如蒙不弃,愿为转载,亦须注明出处,仍存原著原译之人姓氏以昭公道,幸勿任意转录而隐去撰译者姓名,致蹈采美之嫌。”(36)《小说林》的态度就较严厉:“本社所有小说,无论长篇短著,皆购有版权,早经存案,不许翻印转载。”并警告擅载的“□□报馆”:“除由本社派人直接交涉外,如有不顾体面,再行转载者,定行送官,照章罚办,毋得自取其辱。”(37)吴趼人等是传统作家,而徐念慈、曾朴等人受欧美影响较深,这或许是他们对转载态度不同的原因。可作佐证的是,在英国殖民地香港,《东方报》连载《虚无弹》时篇题下注明:“版权所有,翻刻必究。”(38)可是不管同意还是反对,各报刊频繁转载却是客观的现实。 从光绪朝末年开始,“以小说附报者,比比皆是”(39),因为这“实能助读者诸君清兴”,有“定购新闻者已渐渐增加”(40)之效。然而报刊对小说的需求量相当大,作者较为集中的上海等地尚可维持,但在其他地区,却是颇使办刊者头疼的难题,四川的《广益丛报》、《重庆商会公报》等报刊几乎就离不开转载,更遑论海外的《中西日报》等报刊。其实就是在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中外日报》等大报也都在转载小说。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六十五家转载过别家小说(41),被转载作品有四百四十篇,鉴于近代报刊散佚不少,实际情况肯定更严重。当时转载不署名是常事,注明出处者更少,有时甚至擅改篇名。如《台湾日日新报》曾连载小说《人怪》,《星洲晨报》改题为《电贼杀人记》转载(42),《中西日报》连载时篇名又改为《人妖记》(43),都未注明作者。转载者还常任意删改原作,宣统元年《中兴日报》、《中西日报》、《神州日报》与《星洲晨报》都转载了《奇贼》,唯有《星洲晨报》保留作者署名,以及篇末“闻者曰”以下近百字(44)。前三家可能限于篇幅而删节,作者名则是有意抹去。当时转载如此普遍且随意,似可说明大家对这种侵权行为并不很在意。其实即使在意也无法可想。《时报》曾刊载包天笑的《藏枪案》,篇名下特注“不准转载”,可是仅过二十多天,就被同在上海的《通学报》转载,而且连“不准转载”四字也照样印上(45)。国家立法后,小说转载仍很普遍且随意,而且谁也不愿耗费精力财力,为一篇短短的作品诉诸官府。这个问题的解决只能有待时日了。 《大清著作权律》的颁布,是小说盗版问题解决告一段落的标志,回顾其历程,此问题受到关注是始于出版传播系统原有平衡被打破的光绪初年。先进的印刷技术与设备开始逐渐普及以及报刊等新型传播方式出现,打破了数百年来小说阅读市场常态化的平静。小说创作因甲午战争与庚子国变等事件的刺激出现转向,作品数量开始呈现增长态势,“小说界革命”后更是跳跃式递增。书局林立,报刊普及,物质生产层面刚完成的改造虽可支撑小说的迅速增长,但内部关系尚未调整,而此时作者陡然剧增,翻译小说也开始大量涌现。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十多年里,混乱在所难免。既有小说系统置身于一个较陌生的环境,因不适应而出现的混乱,也有为获利而不择手段的人为制造的混乱。后者的出现有必然性,而即使前者,其中也闪动着“利”的身影。对“利”的追逐导致了混乱,而整饬混乱,使无序走向有序也同样是迫于“利”的巨大力量。“利”还可细析,有有道之利与不义之利之分,也有大利与小利之别,同时还有眼前之利与长远之利的差异。就小说阅读市场中各博弈方而言,书局之“利”、作者之“利”与读者之“利”各不相同,即各群体内部也非一致,它们的纠结与抗衡,组成了犬牙交错、盘根错节且其中可始终看到势力消长的“利”网。当三大群体之“利”的交集很小甚至几无时,混乱就必然降临;反之,当其趋向较为一致或接近时,就形成了整饬混乱的巨大力量。 当旧有平衡状态被打破时,混乱不可避免,而身处动荡之中,人心思定也属必然,这是三大群体之“利”的交集出现并逐渐扩大的社会环境。弃不义而趋有道,这是社会尊崇的伦理道德的基本原理之一,它对人们决策与行动的制约力始终存在,大家痛恨混乱之弊时,这种认同感会越发强烈,于是混乱会受到道德与舆论层面的干预,如有的报刊在征集稿件时,就明确声明“不可剽窃他人著作”(46),或“并无陈旧抄袭之弊者”(47),甚至明确声明不得一稿多投,“总以本人得自有著作权且未在他处刊布者为限”(48)。就操作层面而言,除短视与无力规划战略者,人们都懂得舍小取大,以及眼前行为须顾及将来的道理,这其实也是在混乱中立足并图长期发展的最佳策略,惟有如此,方能经受优胜劣汰的竞争,那几家脱颖而出、行为较规范的书局,是稳定小说市场的重要力量,随其实力增强,影响力也相应增大,这更有助于市场的逐步规范。在另一方面,中国锁国状态被打破后,出版与传播界也必然与各国发生一定的联系,列强为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与中国的交涉,也成了规范市场的约束力之一。尽管在法律层面禁止盗版之后,这类现象不可能完全绝迹,但小说市场经过三十年的震荡终于进入较稳定状态,这也意味着新的出版传播系统已经确立。 (本文作者注:在匿名评审中有对本文的批评意见,经反复审核,笔者认为文中的那些论点与表述还是得坚持。对批评者的意见,笔者谨致衷心的谢忱。) 注释: ①“《茶花女遗事》告白”,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七日《中外日报》。 ②申报馆主人《新印〈小五义〉出售》,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申报》。 ③申报馆《新印〈续小五义〉出售》,光绪十七年六月二十日《申报》。 ④申报馆主人《新书减价》,光绪十八年五月初三日《申报》。 ⑤王韬《重刻〈遁窟谰言〉书后》,见《遁窟谰言》,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光绪六年版。 ⑥王韬《声明》,光绪十三年七月初五日《申报》。 ⑦味闲庐主《声明即请天南遁叟赐览》,光绪十三年七月初六日《申报》。 ⑧点石斋主人《拟印〈淞隐续录〉》,光绪十三年七月初五日《申报》。 ⑨同文书局《同文原印〈图咏聊斋〉》,光绪十六年九月初一日《申报》。 ⑩《真原刻〈红楼图咏〉声明》,光绪十年二月初一日《申报》。 (11)点石斋《原底绘图〈列国〉出书并申明翻印》,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申报》。 (12)点石斋《原底绘图〈列国〉出书告白》,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申报》。 (13)广百宋斋《〈廿四史演义〉减价》,光绪十四年四月初六日《申报》。 (14)同文书局《详注〈聊斋志异图咏〉》,光绪十二年三月三十日《申报》。 (15)新泰《〈聊斋图咏〉减价》,光绪十四年二月初六日《申报》。 (16)新泰《同文原印〈图咏聊斋〉》,光绪十六年九月初一日《申报》。 (17)裴锡彬《广告翻书混名者》,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四日《中外日报》。 (18)道、县所出告示载《极乐世界》版权页背面,广智书局光绪二十九年三月版。 (19)该告示载《利俾瑟战血余腥记》版权页前,文明书局光绪三十年正月版。 (20)该告示载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政法学报》第一期首页。 (21)该告示载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小说林社《秘密海岛》之附页,该社所出各书及《小说林》也多刊印此告示。 (22)该批示载《滑铁庐战血余腥记》版权页,文明书局光绪三十年四月版。 (23)新小说社《侦探小说〈离魂病〉全一册,定价二角五分》,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新小说》第六号。 (24)小说林社《广告著译小说诸君》,《秘密海岛》书末附载,小说林社光绪三十一年四月版。 (25)《新世界小说社敬告著译新小说诸君》,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新世界小说社报》第一期。 (26)世界繁华报馆《繁华报馆出版小说》,光绪三十年六月初四日《新闻报》。 (27)知新社《洋装〈官场现形记〉》,光绪三十年九月初七日《中外日报》。 (28)世界繁华报馆《南亭所著〈官场现形记〉初、二、三三编》,光绪三十年十月初二日《新闻报》。 (29)弼本氏《洋装〈官场现形记〉每编一元》,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五日《中外日报》。 (30)乐群书局《最新社会小说〈胡宝玉〉(一名〈三十年上海北里之怪历史〉),“老上海”著,再版广告》,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三号。 (31)广智书局《严查翻刻赏格告白》,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新民丛报》第二十四号。 (32)文明书局《买〈黑奴吁天录〉者,须看四大本的,封面有“文明书局出版”字样》,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初七日《时报》。 (33)严复《与管学大臣论版权书》,转引自周林、李明山主编之《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 (34)书业商会《〈图书月报〉出版广告》,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时报》。 (35)改良小说社《购阅改良小说者注意》,宣统元年四月初二日《民呼日报》。 (36)月月小说社《本社紧要广告》,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二号。 (37)小说林社《特别广告》,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小说林》第三期。 (38)见《虚无弹》,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九日《东方报》。 (39)吕粹声《跋》,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月月小说》第一年第十二号。 (40)《本报特别告白》,宣统元年四月十一日《中兴日报》。 (41)有些报刊虽先行刊载,但并无法确定为原载,这类报刊数并未统计在内。 (42)见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初九日《星洲晨报》。 (43)见宣统二年六月初八日至初九日《中西日报》。 (44)参见《奇贼》篇末,宣统元年十一月初四日《星洲晨报》。 (45)参见《藏枪案》,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初九日《通学报》第三卷第二、三合册。 (46)《本报投稿规定》,宣统元年二月《女报》第一卷第二号。 (47)《本馆征求小说》,宣统元年六月十六日《舆论时事报》。 (48)《东方杂志社悬赏征文略例》,宣统三年二月初三日《神州日报》。标签:点石斋画报论文; 小说论文; 官场现形记论文; 文学论文; 月月小说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小五义论文; 申报论文; 淞隐漫录论文; 新闻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