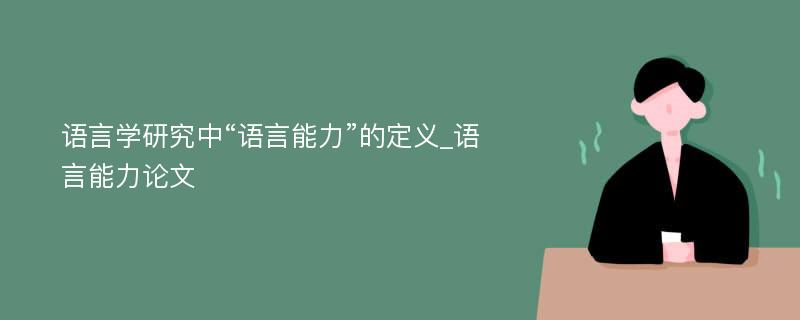
语言学研究中“语言能力”的界定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能力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引言
在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中,“语言能力”(competence)这一关键术语使用非常之广,内涵极其丰富。理论家出于构建自己理论框架的需要,通常对其重新审视和定义。目前,“语言能力”不再具有精确的意义(Taylor,1988)。定义的混乱给理论与应用研究带来了许多争议,一般研究者在使用该术语时选择自己赞成的其他学者的定义,或无所适从地交叉使用,造成前后矛盾,或一知半解地评论修正一番。
中介语语言能力的定义问题亦非常突出,语言能力到底是知识还是运用,是状态还是过程,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是天赋的还是习得的,等等一系列性质问题使研究者伤透脑筋,同时它们本身又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从审视语言能力的经典定义出发逐步论述它的内涵,指出它在不同语言研究领域里地位上的差异,特别是中介语语言能力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定位。
2.关于语言能力的经典论述
Chomsky语言能力观在语言学研究中影响甚广。语言理论的中心任务是解释语言能力,为了便于研究,他将语言能力理想化,将它定义为理想化的说/听者关于语言的潜在知识。乔氏在其经典著作《句法理论要略》(1965)中明确指出:
(1)“语言理论主要涉及理想说/听者,在完全同质的言语社团里理想说/听者完全知道其语言,在语言实际运用中应用语言知识时不受与语法无关的条件诸如记忆限度、干扰、注意与兴趣的转变、(杂乱或有特点的)误差等的影响。”
(2)“因此我们从根本上区分语言能力(说/听者的语言知识)和语言运用(performance),即具体情况下语言的实际运用。”
从乔氏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把知识和运用截然分开。此外,乔氏(Chomsky,1975,1980)在后来的著作中把知识(语言能力)与运用知识的能力(ability)分开,他认为从理论上讲人有可能具有语言知识的认知结构而没有使用该结构的能力(capacity),知识处于比能力(capacity)更抽象的层次。他进而指出知道语言等于处于一种心理状态,处于这种心理状态等于具有某种由规则和原则构成的心理结构。他把知识描写成一种“稳定的状态”(steady state)或“获得的状态”(attained state),又把语言知识与语法知识等同起来,语言能力即语法知识。乔氏还认为语言能力的发展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语言间具有普遍性(Smith and Wilson,1983)。他认为存在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由一套适合所有语法的通用原则和参数构成。语法又分为核心语法和周边语法(coregrammar and peripheral grammar),儿童的语言习得主要是由于普遍语法受环境的激发发展成成人的语言知识,同时儿童还得学会不遵循普遍语法的周边语言内容(Cook,1985)。
总之,乔氏理论中的语言能力指的是同质的语言知识或语法知识,是心理状态、心理器官或认知结构,是天赋的、绝对的心理特征;语言能力不是怎样使用语言知识的能力,不是过程或实际运用。
对于乔氏的语言能力观,自然有人不以为然。反对者中的代表人物首推社会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Hymes。Hymes(1971)以《论交际语言能力》为题撰写了一篇理论性很强的长篇论文,针锋相对地提出并阐述交际语言能力。海氏指出乔氏的语言能力观犹如伊甸园,忽略了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将人的语言生活切成两半,一半是语法能力——理想的天赋能力;另一半是语言运用——犹如吃苹果一样的突变,把完美的说/听者抛向尘世。”而事实上“社会生活不但影响外在语言运用,而且也影响内在语言能力”,例如有的人操单语言,而有的操多种语言。其次,海氏认为乔氏的语言运用概念似乎有几种意思混在一起。一方面,它指可以观察的行为,语言学通过语言运用资料研究潜在的规则系统,通过语言运用资料和其他因素(如内省资料)确定语言能力,从这种意义上讲,语言运用即潜在语言能力的“实际”(actual)体现,在构建语言运用模式用于解释语言资料并且用资料检验模式时,语言运用本身又是语言资料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可设想可以用语言运用的文体规则解释语法理论尚未解释的常见语序。海氏指出乔氏归入语言运用的东西有些是系统的,可以用规则描述,因而也可以看作某种形式的语言能力(Taylor,1988);乔氏(1980)后来也承认这一点,在语法能力的基础上加上了语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为各种目的恰当运用语言的条件和方式的知识,也就是运用语法知识的潜在能力。这样的修正有一定道理,因为语言知识不只有语法。海氏说,语法规则不利用某些其他规则就会毫无用处,就像句法规则制约音位、语义规则可能制约句法一样,言语行为规则是整体语言形式的一个制约因素。
海氏在评论乔氏语言能力定义后提出了自己的“交际语言能力”概念,他把乔氏划为语言运用的内容也归入语言能力名下。交际语言能力由四个部分组成:语法知识(形式上可能)、心理语言知识(操作上可行)、社会文化知识(语境中合适)和实际存在的知识(实际运用)。有些可能、可行、合适的语句并未真正出现。海氏几乎把语言的一切运用情况都划归交际能力范围,认为它们都可能用规则系统地阐述。这样一来,表面上他在扩充语言能力概念,而事实上他把语言能力做了微妙的改变(Taylor,1988)。语言能力包括从语法能力到社会语言能力的一切听和说的能力(capabilities),语法能力纯粹是个体的,是形式和状态,社会语言能力主要是社会的,是功能和过程。海氏认为语言能力依赖潜在的知识和使用知识的能力(ability for use)。结果,把运用知识的能力看作语言能力就得承认动机等非认知因素有部分决定语言能力的作用(Munby,1978)。
总而言之,海氏的交际语言能力概念比乔氏的语言能力概念意义更广更大,它包括大部分乔氏定为语言运用范畴的东西。他把众多的内容纳入语言能力范围,致使其意义含混不清(Taylor,1988)。虽然他还保留了语言运用(performance)概念,但它被削减成实际运用和实际结果(actual use and actual events)而已。
功能派语言学家Halliday从社会角度研究语言运用的情况,以解释言语实现的语言功能。他不承认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之分,认为没有必要将理想化的知识和实际运用分开,二分法无非把我们已经能够描写的和没有描写的分开,而在其他阐述中还起误导作用(Munby,1978)。Halliday(1971,1972)采用社会语义方式研究语言和说话者的语言运用,该方法的核心是他定义语言的“语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概念,语义潜势是说/听者可利用的一个个语义选择集,它将行为潜势和词汇语法潜势联系起来。他还指出语义潜势概念和乔氏的语言能力概念不同,说话者能做的不同于他所知道的,他又说自己的语义潜势与海氏的交际语言能力没有什么不同,而实际上海氏交际语言能力与语义潜势是有区别的,因为海氏虽然扩大了语言能力的范围,将乔氏划为语言运用的某些方面纳入交际语言能力,但是他依然接受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二分法。
与乔氏观点不同的学者除了Hymes和Halliday以外,还有Habermas(1970),Campell和Wales(1970),Greene(1972)等。但可惜他们对乔氏语言能力概念或多或少有些误解。
Habermas接受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之分,但是认为乔氏的语言能力是独白式能力(monological capability),不足以建立普遍语义学,不能阐述交际中的语义方面。Habermas认为,说话者为了参与正常的会话,除了具有语言能力外,还必须具备基本的言语和符号交际的资格条件。他把这些统称为交际语言能力。他的交际语言能力与海氏的不同,指的是对理想化言语情景的熟练掌握,由实现交际的普遍语言特征知识构成。
Campell和Wales也曾试图扩大语言能力概念范围,他们指出乔氏的语言能力忽略了最重要的语言方面的能力(the most important linguistic ability),即产生和理解不太合语法但符合语境的语句的能力。他们将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实际能力(capacity or ability)等同起来,把语言方面的能力(linguistic abilities)和作为这些能力的基础的知识(knowledge underlying abilities)混同起来。因而他们的论述是混乱的。(Taylor,1988)
Greene在评价乔氏的语言能力观时误以为乔氏的语言能力概念可分为强弱两种。乔氏说过一个人习得语言就是习得一套声音和意义以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规则系统,也就是习得某种用于产生和理解言语的能力;他又声称语法规则内化于说话人的脑中,是理解语言关系的基础。Greene划分的弱式语言能力概念(aweak version of competence)指规则系统的知识,完全是描写性的,Greene认为这种描写说明不了语言运用者用于产生输出的实际规则或操作,充分描述说话者直觉的规则与直觉的实际操作不一定有联系。如果直觉知识被一套规则充分描述,则这套规则必定以某种方式体现在大脑中,尽管说话者可能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Greene错误地以为乔氏语言能力概念由知识转向了如何运用知识的能力,而实际上,无论乔氏使用的术语是语言知识、语法能力、规则系统,还是认知结构,指的是抽象的心理状态,而非心理过程。
3.应用语言学关于语言能力的论述
在理论语言学家对语言能力的内涵还未达成共识之时,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者将这个有争议的术语引入中介语研究。第一语言能力与第二语言明显存在的差异使这个术语的定义更加复杂化。
Canale和Swain(1980)在他们的长篇论文《第二语言交际法教学与测试的理论基础》中指出语法规则如果没有语言运用规则是无用的,同理,语言运用规则如果没有语法规则也是无用的。他们用交际语言能力指语法能力(语法规则知识)和社会语言能力(语言运用规则知识)之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他们的交际语言能力包括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和策略能力。他们没有把运用能力(ability for use)纳入交际语言能力,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运用能力”概念不是交际语言能力研究中探讨的问题,任何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恐难充分阐述它。可以看出Canale和Swain的观点与乔氏的部分观点接近,两者的语法能力概念相同。他们的社会语言能力相当于乔氏后来提出的语用能力。但是,他们增加的“策略能力”使问题复杂化了。他们的策略能力指学习者用于交际而需要掌握的知识和能力(ability),因而自相矛盾地把运用能力纳入交际语言能力,此外,他们又没有指出本族语者和非本族语者的策略共性与差异。
众所周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是描写和解释中介语语言能力的形成。对于中介语系统(或称中介语规则系统、中介语语法)的性质,学者们看法不一。Corder(1981)用过渡性语言能力(transitional competence)描写中介语知识,他强调学习者具有不断变化的语言知识体系,虽然Corder声称自己借用乔氏的“语言能力”术语,但是他的过渡性语言能力与乔氏绝对意义的语言能力相差甚远。此外,把中介语看成可变动态系统的代表人物还有Ellis(1984,1985,1990)等。Ellis(1984)提出可变语言能力模式(Variable Competence Model),承认学习者的语言知识系统存在内在的变化性,这个模式强调语言运用,认为运用是第二语言赖以发展的机制。
另一位学者Krashen(1980,1981,1985)将学习者的中介语语言系统一分为二,一个是通过潜意识过程习得的系统,另一个是通过有意识注意形式和规则学得的系统,前者启动流利、自发的输出,后者监控前者的输出,尽管Krashen试图用表面上与普遍语法观一致的“自然习得顺序”论证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共性,但他的语言系统二分法无可避免地承认了个体语言能力的发展变化,与乔氏的绝对的静态的语言能力背道而驰。
Stern(1983)的“语言能力”范围也很广。他指出,第二语言学习者在不同时期的第二语言能力或水平(competence or proficiency)呈从零到近似本族语者的变化,语言能力是积极、动态的而不是机械、静态的,他把能力与水平等同起来,把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连在一起。他的语言能力概念包括语言知识、社会语言知识和运用这些知识的技能。他还指出,知道一门语言,即第一或第二语言的语言能力或水平,是从直觉上掌握语言形式和语言形式表达的语言的、认知的、情感的及社会文化方面的意义,最大限度注意交际、最小限度注意形式的情况下运用语言的能力(capability),也是创造性运用语言的能力。可见Stern认为,语言能力等于语言水平,也等于知识,语言运用技能是语言能力的构成成分。这种无所不包的“语言能力”把乔氏的语言运用也包括在内,语言能力之外只剩下语言运用的结果,即书面和口头材料。
Bialystok和Sharwood-Smith(1985)关于中介语的论述颇有见地地分析了Selinker(1972),Adjemian(1976)和Tarone(1982)三种中介语系统模式,认为它们都不合适。他们仿照乔氏的语法能力和语用能力之分,把中介语知识分为中介语语法知识(能力)和中介语语用知识(能力)。但又认为,两种知识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控制,两方面的知识合在一起,经过控制程序才产生输出;语言能力或水平(language ability of proficiency)包括语言知识系统和对知识系统的控制,换言之,中介语既包含有系统、有组织的目的语知识的心理表象,又包含在适当情况下有效取用目的语知识的程序;中介语既非一定的语言形式,又非学习者具体的能力(或无能),而是包含语法知识和控制程序具体值的成分系统。学习者的中介语语言能力或知识在量、自然性和知识分析性方面随时间变化,且大多数变化向目的语靠拢。最后,他们的中介语概念由开始的知识系统变成了包含一套过程的系统,它既不仅仅是一个产物(aparticular product),也不仅仅是心理过程和心理状态,而是心理活动的结果,是第二语言习得者没有充分获得本族语者一样的语言知识和语言处理控制(control of processing)水平时的系统性语言运用。由此可以看出Bialystok和Sharwood-Smith的中介语概念涉及从语言知识控制程序再到语言运用的一切中介语现象。
4.界定差异透视
本文的2、3两节简要介绍了国外语言学家关于语言能力、交际语言能力和中介语语言能力的观点。他们在理论分析中引入一套不很明确的术语:语言能力、语言知识、语法规则(系统)、语言运用、运用能力、交际语言能力、语言水平、社会语言能力、语用能力、语篇能力、策略能力、心理状态、心理过程、认知结构、心理结构、心理表象、中介语语言能力、可变语言能力等,试图用新的术语(含义可能更不精确)解释旧的术语,有的对等互换,有的包容其他,有的相互排斥,但是这些关系在实际论述中有时被暂时打破,导致自相矛盾的观点。我们认为,在研究对象、方法、目的不同的情况下,任何取得共识的企图已被证明、还将被证明是徒劳的。
Chomsky以天赋思想为指导,以构建人类语言普遍语法为目的,以第一语言为对象勾勒理想化的说/听者的语言能力。他不得不将研究对象理想化,也不能以一般的口头和书面材料(即语言运用的结果)为研究材料,否则有可能退回到描写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虽然描写和解释理想的语言能力给他及其追随者的语言学研究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因为他们可以任意造出合格或不合格的句子以便检验某规则),但是语言学家无法证明其理论的心理现实性;相反有实验表明语言运用者组织语言的方式与生成语法的深层到表层的转换方式无直接联系(Sharwood-Smith,1986)。Chomsky声称语法能力是静态的知识系统,但他及其追随者研究的生成语法论述的是语句转换生成的过程,规则是静态的知识,而它们有序的组合是动态的,D结构到S结构是变化的。所以,他研究的不是完全静态的语言能力,更没有理由认为研究静态比研究动态过程高明。此外,语言学家的直觉和本能是否真实全面地反映语言能力也有疑问。如果一般人的语言运用受情感等因素的影响不能正确反映语言能力,那么语言学家在进行直觉判断时能否成为不受情感等人性因素影响的“超人”呢?Lennon(1991)关于本族语者用直觉判断错误的研究表明,对语言的直觉判断不一定可靠。
人是社会的成员,语言行为受社会的制约,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人类祖先没有组成社会,那么个体的语言是否会形成呢?答案不言自明。人类的语言和机体一道经历了数百万年的进化才成为目前的样子。“其发展速度一定会受到文化发展与人口密度增长的很大影响。”(王士元,1987)从这种意义上讲,Hymes和Halliday的社会语言观更具现实意义。交际语言能力超越单纯的语法能力,是高出生物人的社会人具有的语言能力。考虑社会因素就得考虑功能和过程,也必然引入语言运用。Taylor(1988)在评述“交际语言能力”时说,当我们谈论语言教学中的交际语言能力时,我们实质上在谈论交际语言运用,在第二语言教学中,交际语言能力似乎通常是指用第二语言行事或交际的能力(ability),特别是当我们确定教学目的时主要感兴趣的还是语言运用。于是,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的界限模糊了,术语的含义也难以确定了。Halliday干脆不承认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之分,这一观点也为他省了不少术语上纠缠不清的麻烦。
第二语言习得领域的语言能力研究在本质上受语言、社会、教育等因素制约。第二语言能力与第一语言能力存在差异的事实、社会对第二语言水平的要求、教学活动与教学效果等现实问题把应用语言学家赶出了理想化的纯语言研究的象牙塔。我们要关心的不仅是学习者大脑中有什么样的语言知识系统,更重要的是如何获得这种知识,如何促进第二语言的习得,如何培养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衡量学习者语言能力的手段是用分析语言运用的结果(口头和书面的),而不是凭直觉推断出他可能具有的潜在能力。
从以上角度出发,应用语言学研究没有必要也不应该采用与理论语言学同样的方法,研究同样的对象,提出同样的理论,解决同样的问题。现有的中介语研究涉及的内容既有语言系统也有语言系统的形成过程,或者说既有静态的规则知识又有动态的规则形成。在中介语研究中将学习者理想化是荒唐的、有害的,因为理想化的学习者习得的第二语言从理论上讲和本族语者的语言相等,研究它将失去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教育学意义。
5.结论
语言能力的界定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Chomsky的语言能力是一个有限的、狭义的、表状态的概念(Taylor,1988),虽然它可能适合于解释人类共有的语言知识,但它无法应付语言系统的发展变化现象。当我们将它的意义扩展,把规则、形式、功能、过程和语言输出包含在内时问题就产生了,它的定义不明确或者超出了理想说/听者时混乱就出现了。但从理论语言学到应用语言学,从第一语言习得研究到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它们在根本上是不矛盾的,理论语言学家研究语言规则系统,心理语言学家研究语言习得和语言运用过程,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者既探讨规则系统又研究语言习得和语言运用过程。前者无多大教学意义,而后者直接影响语言教学。在后者的研究中,前者经典的“语言能力”概念只能起参照作用。第二语言习得者运用的不是理想完美的中介语知识,因而他们的语言也是不完美的,他们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通常称之为语言水平。Taylor(1988)精辟地提出语言能力(competence)、语言水平(proficiency)和语言运用三分法,前者是知识,中者是运用知识的能力,后者是运用语言水平的产物。他还指出,交际语言能力同样不如改成交际语言水平(communicative proficiency)。三分法为语言能力(知识)和语言运用架起了一座桥梁,在状态与结果之间加上过程,可以使语言现象得以适当的解释。在中介语研究中我们似乎也可以用类似的划分标出中介语语言能力(知识)、中介语水平(运用知识的能力或过程)和中介语输出。然后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框架上明确地探讨中介语的三个方面,研究中介语语言能力可知其与目标有多大距离,研究中介语水平可知有多大的表达能力,研究语言输出可推断前面两者。
鉴于语言学各领域的研究目的和对象不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用不同的概念表示各自研究的范围,而根本没有必要都把某一语言能力定义当作绝对标准,造成诸如此类的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