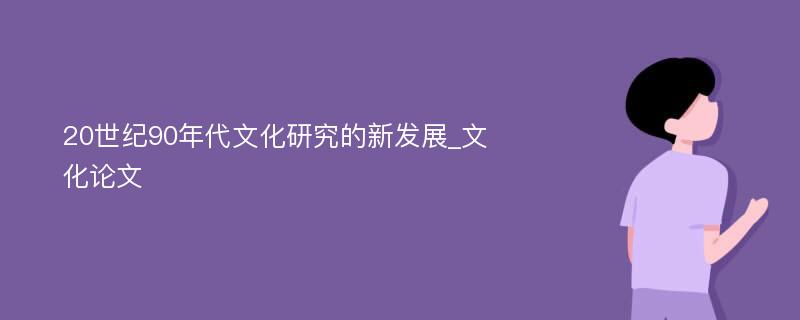
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发展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后期,随着后结构主义理论大潮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界的衰落,作为战后西方文化思想界和文学艺术界人们谈论最多的一个热门话题的后现代主义也逐渐大势已去。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崛起曾迅速地占领过批评理论的鳌头,但很快便显示出衰落的迹象。进入90年代初以来,西方文化界和文论界出现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浪潮,把后现代时期的一切边缘话语统统纳入其保护伞之下,这尤其对传统的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致使一些学者惊呼,在这股文化研究大潮面前,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及其经典的价值是否受到了怀疑?而另一些观念较为开放并致力于扩大研究视野的学者则对之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并主张将基于传统观念之上的狭窄的文学研究置于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之下,并且把目光移向西方世界以外的地区,通过与那里的学者的直接接触,达到东西方文化学术交流和对话的目的。显然,对之抱担心的态度,或厌恶的态度,或欢迎的态度,都从某个方面反映了一个客观的事实:文化研究已经占领了学术研究的中心地带,并在近几年内有了长足的发展,它已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理论现象,因此对之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本文正是继续笔者以往的研究,探讨90年代后期以来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最新发展以及一些相关的理论课题。
一、文化研究的历史及现状
我们一般很容易将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相提并论,这当然不足为奇,因为当今的不少欧美学者(尤其是反对文化研究者)都在这样做。但仔细追溯其各自的历史作用和当代形态,我们就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界定也迥然相异:前者主要指涉对文学的文化视角的批评和研究,这种批评模式早在19世纪后期的马修·阿诺德那里就已有之,只是在本世纪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语言学和形式主义批评占主导地位而被“边缘化”了,而在本世纪后半叶文学批评走出形式主义囚笼的呼声日益高涨时又重新得到了强调;后者的范围则大大超出了文学研究的领地,进入到了对人类一切精神文化现象的考察研究之境地,甚至以往被具有鲜明的精英意识的文学研究者所不屑的那些“亚文化”以及消费文化和大众传播媒介都被囊括了进来。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之下,文学研究被束之高阁,并且被限定在一个极其狭窄的圈子里。因而难免有精英意识较强的学者惊叹,文学研究有可能被淹没在文化研究的汪洋大海之中。
既然是一种边缘话语,并且有着鲜明的“非精英”意识和批判精神,那么,文化研究的“非边缘化”、“非领地化”和“消解中心”的特征便是十分明显的。学者们一般认为,文化研究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以研究后殖民写作/话语为主的种族研究,其中涉及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斯皮瓦克的第三世界批评和巴巴的对殖民话语的戏拟和混杂;以研究女性批评和写作话语为主的性别研究,这在当今时代主要涉及女性批评话语的建构和女性同性恋研究;以指向东方和第三世界政治、经济、历史等多学科和多领域综合考察为主的区域研究,如当前十分诱惑人的课题就包括“亚太地区研究”和“太平洋世纪研究”等。此外还应当加上考究影视传媒生产和消费的大众传媒研究,尤其当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文化研究的传媒特征越来越明显,它几乎与传媒现象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与文学研究的距离则越来越远。这也许正是文学研究者对文化研究抱恐惧甚至反感态度的部分原因。
文化研究虽在当今时代的英语世界声势浩大,但在较为保守的欧洲学术界却颇遭非议,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正如有些介入文化研究的学者所承认的那样,“它并非一门学科,而且它本身并没有一个界定明确的方法论,也没有一个界线清晰的研究领地。文化研究自然是对文化的研究,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是对当代文化的研究”。(Simon During:Cultural Studies Reader,1st ed,1 ~2,London and New york,Rouledge,1993.)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已经与其本来的宽泛含义有了差别,对于当今的文化研究者来说,“‘文化’并不是那种被认为具着超越时空界线的永恒价值的‘高雅文化’的缩略词”,(同上书,第1~2页。)而是那些在现代主义的精英意识占统治地位时被当作“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化或亚文学文类或甚至大众传播媒介。这说明,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理论基本上从后现代主义理论那里借鉴而来,并应用于更为宽泛的范围和更为广阔的疆域,它同时在西方帝国的中心话语地带——英美和原先的殖民地或称现在的后殖民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发挥作用。
从历史的发展线索来追溯,我们不难发现,早先的文化研究出现于50年代的英国学术界,其立论基点是文学,以理查德·霍加特的专著《有文化的用处》(The Uses of Literacy)和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年》(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为标志:前者作为一本个人色彩较为强烈的专著,通过作者自身的经历,描述了战后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的变化,作者试图表明这些变化是如何影响个人的整体生活方式的,在他看来,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范畴,有助于人们认识到一种生活实践(如阅读)不可能从诸多生活实践(如体力劳动、性要求、家庭生活等)组成的大网中摆脱出来;后者则批判了文化与社会的分离以及“高雅文化”与“作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分离带来的直接后果。因此早期的文化研究有着这样两个特征:其一是强调“主体性”,也即研究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从而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之模式;其二则是一种“介入性的分析形式”,其特征是致力于对各种文化现象的批判性分析。这两个特征奠定了当代文化研究的基础。
如果说,当今的文化研究确实识自文学研究,并且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始于50年代的英国的话,那么它至今也已有了四十多年的历史。它的创始人是利维斯(F.R.Leavis),他所开创的那种文学研究形式又称作“利维斯主义”, 其意在重新分布法国社会学者皮尔·布尔丢(Pierre Bourdieu)所谓的“文化资本”。 利维斯试图通过教育体制来更为广泛地传播文学知识,使之为更多的人欣赏。他论证道,需要有一种严格选取的文学经典,这一经典的核心——“伟大的传统”应当包括简·奥斯汀、亚历山大·蒲柏、乔治·爱略特等这样一些能够培养一批有着敏感的道德意识的读者的大作家,而一些致力于带有个人色彩的艺术实验的现代主义作家,如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芙则应被排斥在这一“经典”或“传统”之外,因为这些带有强烈的先锋实验意识的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并未经受历史的考验,因而其价值并未得到人们的公认,将他们的作品纳入文学经典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在他看来,阅读上述这些“伟大的经典”作品有助于以一种具体的平衡的生活观来造就一些成熟的个人,而对之构成的一个威胁则是所谓的“大众文化”。由此可见,利维斯的文化研究概念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与现在西方学术界风行的文化研究已明显地脱了节,但它却往往被认为是当代文化研究应当超越的对象或至少说一个早期的阶段。而后来的文化研究则是在走出了利维斯主义,通过霍加特和威廉斯这两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家的中介才逐步进入社区和知识界的,首先进入了中等学校和专科学院的课程,其后又对大学文学课程中所涉及的关于文学经典的构成问题形成了挑战。上述两位学者在实践利维斯的崇尚经典理论的同时也对之进行了必要的扬弃,在他们看来,文学经典的丰富文化内涵显然远远胜过大众文化,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利维斯主义至少抹去或并未直接接触自己所身处其中的社区生活形式,这无疑使得利维斯的文化研究理论与大众文化格格不入。在这方面,霍加特的研究实际上超出了利维斯的经典模式,扩大了文化研究的内涵,使之直接深入到战后英国的社会、经济、就业等工人阶级所经历的一系列文化问题。
随着工人阶级社区生活的裂变和趋向多极化,文化研究也依循着霍加特的专著《有文化的用处》中所指明的新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文化研究理论家们开始严肃地探讨文化自身的政治功能,试图对社会民主的权力集团进行批判,因为这一集团正在逐步将权力拉入国家体制中,在这方面,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A.Gramsci)的霸权概念无疑对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致使文化研究理论家们得以对文化本身的霸权作用进行批判和削弱;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兴趣的转向也导致研究者对旧有的范式进行了修正,从而使得文化越来越与政治相分离,对文化形式的研究也从注重文学经典逐步转向其他文化形式,包括影视制作、文化生产、音乐、广播、爵士乐等通俗文化艺术甚或消费文化。
文化研究除去其文学研究的资源外,还从另几个方面得到帮助和启迪: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使文化研究得以进行社会问题的批判;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使文化研究者得以从语言的层面切入,探讨文学和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习俗;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史学理论使论者们得以剖析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中权力的主导作用以及话语的中介作用;而文化人类学理论则使研究者得以探讨艺术的起源等问题,并且对当今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人类学转折”有着推进作用。可以说,在经过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冲击后,文化研究的范围更加扩大了,探讨的问题也从地方社区的生活扩展到对整个大众文化艺术市场的运作,从解构主义的先锋性语言文化批评扩展到对当代大众传播媒介甚至消费文化的研究,等等。原先戒备森严的等级制度被打破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人为界线被消除了,殖民主义宗主国和后殖民地的文学和理论批评都被纳入同一(文化)语境之下来探讨分析。这样,“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文化研究最有兴趣探讨的莫过于那些最没有权力的社群实际上是如何发展其阅读和使用文化产品的,不管是出于娱乐、抵制还是明确表明自己的认同”,(同上书,第7页。 )而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理论论争而来的“全球化”大趋势更使得“亚文化和工人阶级在早先的文化研究中所担当的角色逐步为西方世界以外的社群或其内部(或散居的)移民社群所取代并转变了”。(同上书,第17页。)这一点正符合当今西方理论界的“非边缘化”和“消解中心”之趋势,从而使得文化研究也能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得到回应。近几年来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日益风行就说明了这一点。
进入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逐步上升到理论话语的主导地位,并且越来越具有当代的现实性和包容性,并且和人们的文化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英语世界,文化研究虽然起源于英国,但它迅速进入了美国学术界,并且受到一大批在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领域内颇有影响的著名学者的关注,其中包括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爱德华·赛义德、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拉尔夫·科恩、希利斯·米勒、汉斯·岗布莱希特、保尔·鲍维、汤姆·米彻尔等,大量研究后殖民文学、传媒文化和其他非精英文化现象的论文频繁地出现在曾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称的著名学术刊物,包括《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和《疆界2》(boundary 2)等, 逐步涉及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并介入了对全球化现象的思考和研究。显然,当代文化研究的特征在于,它不断地改变研究的兴趣,使之适应变动不居的社会文化情势,它不屈从于权威的意志,不崇尚等级制度,甚至对权力构成了有力的解构和削弱作用,它可以为不同层次的文化欣赏者、消费者和研究者提供知识和活动空间,使上述各社群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活动空间。此外,文化研究还致力于探讨研究当代人的“日常生活”,这也许正是文化研究为什么得以在西方世界以及一些东方国家和地区(例如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如此风行的原因所在。总之,在文化研究这面旗帜下,许多第一流的学者和理论家走出了知识的象牙塔,和人民大众进行了沟通和对话,同时,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学者也能够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和对话,从而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共识。
二、文化研究在英国的发展
文化研究既然有着学科界限的不确定性,那么它在欧美国家也就有着不同的形态。我们经常所说的“西方”这个概念应当说是极不准确的,即使就同样操持英语的国家英美两国而言,在文化研究方面也有着很大的差别。而它们与欧陆学术界的差别就更大了。就欧洲大陆的观念保守之特征而言,尽管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奠基者身处欧陆,但他们的理论只是被介绍到美国之后才得到最热烈的响应,而在欧陆,他们的理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受到相对沉默的礼遇。与另一些当代新理论在英国所受到的“礼遇”不同的是,文化研究在现当代英国却得到了空前的弘扬,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众所周知,英国曾是本世纪英语文学批评界最有影响的批评流派“新批评派”的发源地和重要的实验场所,当年,诗人兼批评家T.S.艾略特(1888~1965)和I.A.理查滋(1893~1980)、燕卜孙(1906 ~1984)曾在这里提出新批评的美学原则和批评标准, 对后来的整整一代批评家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活跃在战后的重要批评家F.R.利维斯、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等都在自己各自的批评领域里对新批评的影响作了有力的反应或反拨,对于英国当代文学批评走出以形式主义的“文本中心”之狭隘领地,把文学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下来考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应该说,战后英国的文学批评的发展实际就是从现代文评的精英意识经由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批评的短暂中介迅速过渡到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过程,在这方面,下列三位批评家的贡献值得一提。
利维斯作为当代英国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先驱者和早期的主要代表,他的批评理论和实践都表现出强烈的精英意识和对高雅文学经典的崇尚,这也表明了英国的文化研究传统是植根于精英文学的土壤中的。早在1930年,他就发表了《大众文明和少数人的文化》一文,提出了自己的颇具精英思想的文化批评观点。在新批评风靡大学文学讲坛时,他也主张文学的内在研究和“细读式”批评。他甚至认为,对作品的价值判断与“书页上文字的特殊安排”都是一致的。他反对把文学研究扩展到社会历史的语境,认为文化既然为少数精英分子所拥有,因此他们实际上在人民大众面前扮演的角色就是启蒙者,要想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知识素养,惟有让他们开列一份经典文学书目,通过对这些经典文学书目的阅读和鉴赏来实现对广大读者的启蒙。在判断什么样的作品才算作经典方面,利维斯同样表现出传统的保守思想。应该承认,当代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英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的崛起,与利维斯早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正是超越并走出了利维斯主义的狭隘领地,文化批评才在英国得到长足发展的。
如果说,英国的文化批评在利维斯主义占统治地位时仍是精英主义的,那么这种精英意识便受到后来的另两位出身贫寒的左翼批评家的挑战。理查德·霍加特最有影响的著作是《有文化的用处》,在这部著作中,他一反利维斯的精英主义文化批评思想,主张当代批评家应把批评和研究的触角指向一个长期不为人们注意,但实际上却很有活力和影响的文化现象:大众文化和文学。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对文学阅读和欣赏的日益强烈的需求。他指出,既然大众文学是为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大众创作的,那么它就应当涉及并表现大众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其价值观念。作家们应当走出精英文学的象牙塔,深入到大众的社区生活,这样,他们的创作题材才不会衰竭。在当今文化研究日益具有冲击力和影响的情势下,霍加特仍不断地为批评家和学者们引证和研究。
另一位对利维斯的精英文学思想提出挑战的是当代英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他一方面投身英国的左翼文化运动和政治斗争,为在英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奔波,其中一大成就就是帮助斯图亚特·霍尔创办了左翼刊物《新左派评论》,使之成为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讨论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阵地。威廉斯对英国当代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卓越贡献体现在,他首先通过把研究的触角指向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而实现了对利维斯的精英文化思想的超越和批判;其次,作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威廉斯很早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在30年代就开始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对话,他反对当时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机械地照搬、教条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作法,试图在自己的一系列著述中建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再者,他通过《新左派评论》的中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有了正确的了解,经过多年的独立思考和探索,他终于于70年代推出了自己建构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这种文化唯物主义与传统的以基础/上层建筑为理论出发点的唯物主义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更重视语言的重要作用,与结构主义的不同之处则在于,文化唯物主义强调“有活力的语言”和“语言的发展历史”,注重语言的实际社会运用和意义的历史变化,从而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理论。应该承认,当前在英语文学和文化界风行的“文化研究”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维廉斯等理论家的努力。
60年代以后,工人阶级社区生活的逐步趋向多极化越来越受到文化研究者的注意,而这时的文化研究则开始在英国的学术体制内得到初步的确立,其中的一个征兆就是霍加特于1964年在伯明翰大学创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霍加特和霍尔曾先后担任该中心的主任。中心的研究方向从一开始就依循霍加特所规定的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严肃地探讨文化自身的政治功能,以便对社会民主的权力集团进行批判;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兴趣的转向也导致研究者对其旧有的范式进行了修正,从而使文化研究越来越与政治相分离,越来越朝着其审美的一面发展,对文化形式的研究也从注重文学经典逐步转向其他文化形式,其中包括影视制作、文化工业、音乐、广播、爵士乐、服饰等通俗文化艺术甚或消费文化。可以说,英国的后现代文学从一开始的带有精英意识的先锋派的智力反叛转向与大众文化和文学的合流、与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分不开的。
毫无疑问,继雷蒙德·威廉斯之后当代英国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推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他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在新形势下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从而使之成为当代西方批评理论中的重要一支立下了汗马功劳。伊格尔顿的主要文学观点体现在,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同时它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作家和文学艺术生产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扮演的是雇佣劳动者的角色,而文学艺术在后工业后现代时期则是一种制造业,艺术产品在某种程度上说来也可算作是商品。艺术生产的维系取决于特定的生产技术,而艺术生产方式则是艺术形式的决定因素。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反映论持不同看法,认为文学反映现实的提法实际上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简单地理解为被动的和机械适应的关系,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因此在伊格尔顿看来,不顾文学创作的规律,一味在文学作品中搜索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内容,表明了一种对文学的幼稚态度,这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于批评实践的正确态度,而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方法。他主张把结构主义的某些因素揉合进马克思主义中,从而创立一种新的综合“话语理论”,这种话语用于文学研究,则可吸收当代各种批评理论的积极方面,以便对文学进行多角度和全方位的考察研究。应该承认,由于伊格尔顿的努力,英国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带有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色彩。
伊格尔顿从7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的观点主要体现在《文学理论导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这两部著作中。前者是作者向英语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系统地介绍自20世纪初以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演变脉络,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尤其是在对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以及精神分析学等批评流派作了批判性评介之后,作者总结道,文学理论具有无可非议的政治倾向性,所谓“纯文学理论”只能是一种学术神话,作为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意义的文学理论决不应当因其政治性而受到责备。这就相当旗帜鲜明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和特征。后者是作者进入90年代以来出版的第一部有着重大意义和广泛影响的力著,在这里,伊格尔顿把审美看作是一种关于身体的话语,认为在当代文化中,审美价值与其他价值的分裂表现了社会关系的复杂多变性和矛盾性。作者继续了以往的研究,把分析对象集中在19世纪后期以来的德国美学,认为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是现代文化中最伟大的美学思想家,他们的理论为现代西方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基本范式。作为一位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的文化批评理论家,伊格尔顿曾在80年代介入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对后现代主义的表演性和怀疑一切的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予以了批判。同样,对于当今风行于后现代主义大潮衰退之后占据西方文化理论界的“文化研究”,他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但在承认其合法性的同时则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角度予以了冷静分析。在1997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的论文中,他甚至针对西方国家以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后现代热和文化热发表了不同意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文化主义加大了有关人类生活所建构和破译并属于习俗的东西的重要性……历史主义往往强调历史的可变性、相对性和非连续性特征,而不是保持那种大规模不变的甚至令人沮丧的一贯性特征。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在我们这里——属于先进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但现在似乎却日益进口到中国以及其他一些‘新崛起的’社会”。因此,在他看来,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不必把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特定文化现象统统引进自己的国家,否则便会丧失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他的这篇论文于1995年在中国大连举行的“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上首次宣读时引起了与会中外学者的强烈反响。然而,与威廉斯等人不同的是,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受到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他只能算作一位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学院”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英国的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左翼马克思主义理论密切相关,一些著名的文化批评家和研究者大都有着自己的独特文学研究和批评背景。近几年来,随着文化研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英国的文化研究也较为注意性别研究、种族研究和传媒研究。与英国的文化研究相似的是,美国的文化研究者队伍也有着一大批素有文学造诣和理论影响的学者,并掌握了一些很有影响的学术理论刊物,但这批人所主张的是将文学置于广阔的文化语境下来考察,而更多的来自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和传媒学界的学者则走得更远,他们把文化研究推到了另一个极致,使其远离精英文学和文化,专注跨学科的区域研究以及大众文化和传媒研究。相比之下,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些有着殖民地背景的国家,文化研究主要关注的对象则是后殖民问题和后殖民地写作/话语,这些地方的旧有文学历史并不悠久, 传统的势力也远没有英国那么强大,因而文化研究在这些国家便有着相当长足的发展,其势头之强大甚至引起了比较文学和英语文学研究者的恐惧,但对文化研究究竟与文学关系呈何种关系,现在还难以做出定论,但可以预言,任何将文化研究推向极端的作法都只能加速它成为学术理论界的匆匆过客。
三、结论
毫无疑问,文化研究在中国已经成了继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之后学术理论界的又一个热门话题,或者说又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继1995年中美两国学者合作在大连举办“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以来,这方面的论著、译著和论文也逐渐多起来了,在中国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也逐年增多。一大批曾经活跃在文学理论批评界、比较文学界和传媒研究界的学者受到这一颇有诱惑力的理论课题的吸引,他们,包括我本人在内,一方面紧紧跟踪西方学术理论界在文化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不时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则将这一引进的学术理论话语应用于中国的文化实践,这样便推进了中国文学的文化批评、大众文化研究和传媒研究的理论化和国际化,使之早日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安地看到,令不少人感到困惑的是,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纯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将有无出路?文化研究打破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天然界限,属于高雅文化范畴的文学是否仍有生存的空间?要回答这些问题,仅以本文的有限篇幅显然是不够的。我这里仅想指出,文化研究纵然有种种局限,但至少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即当文化研究打破了东西方文化的截然对立之后,文化相对主义这一曾在历史打上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印记的观念被重新赋于了新的意义,从而使得东方文化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东方文化及其高雅形式文学再度被西方人所重视,跨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谈。我认为,尽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我们在很多方面是无法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的,但在文化研究的诸种课题和层面上,这样的对话却是可能的,并且有可能率先取得突破。对此我们应当抱乐观的态度:21世纪的世界文化既不可能被西方文化主宰,也不可能被东方文化主宰,而是东西方文化经过冲突、磨合之后在新的层面上的融合,因而产生的就是一种新的兼具东西方各自特色的文化,因为文化应当是全人类共有的。
标签: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大众文化论文; 精英文化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艺术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读书论文; 九十年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