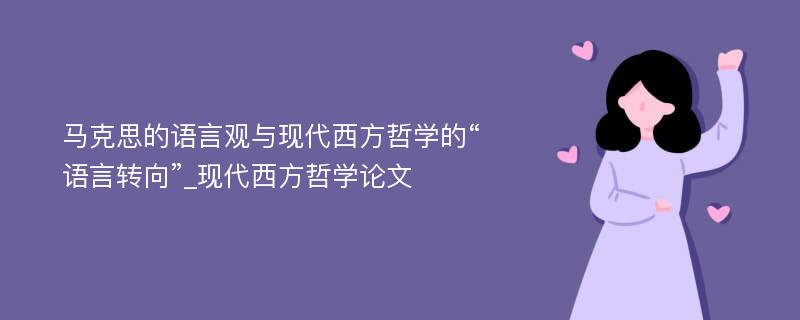
马克思的语言观与现代西方哲学“语言的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语言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语言的转向”之实质
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的转向(linguisticturn)”,这几乎已是众所周知的论断,亦是人云亦云的定论。与此相对应,众多学者认为西方哲学经历了从古代的存在论向近代的认识论、由近代的认识论向现代的语言哲学的两次转向。在我看来,这两次转向的实质在于它表征了西方哲学的知识主义倾向的演变。所谓知识主义是指这样一种传统,即把世界、人、精神以及诸如此类的存在者作为知识的对象,以理性论辩的方式进行探究。从思想成果来说,它以知识为中心,包含了对知识之基础与发生的思考,从思想方式来说,它以理性为原则,涵盖了对理性的历史考量。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从西方哲学史来看,古代哲学作为哲学的童年,思考的对象是存在者本身,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最普遍、最高的问题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为何物;关于存在之基础的知识的研究构成了存在论(ontology),其中核心部分是实体论(ousiaology)。这样一种研究企图的结果必然是晚期古希腊哲学独断论与怀疑论之争。怀疑论既有认识论的依据,也有存在论的依据,其特色是只作探究,不作判断,它的最终发展实际上取消甚至瓦解了知识,并贬抑甚至戕害了理性能力。
中世纪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限制信仰而为理性留地盘。其结果是,随着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兴起,科学精神也开始成熟了,人的理性能力开始恢复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关于事物的真知识问题又一次成为争论的中心。于是近代哲学在意气风发之余又面临着同样的遭遇:独断论与怀疑论之争。问题不再是关于存在之基础的知识,而是关于知识之基础的原则,因为前者依赖于后者对知识本身的说明。因而,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确认作为知识之基础的形而上学的实体存在,以及真知识如何可能。这一争论的路向大致有两条:1.从思维的自我出发进行关于实体和知识的论辩,其成果是在认识论意义上确立了主体性原则;2.从实体出发确立了形而上学意义上有关理性和真知识的原则。在这里,存在论和认识论往往是纠缠不清的,只是到了休谟那里才将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原则严格地贯彻到底,以温和的怀疑论和自然主义终结了以往的争论,为康德扫清了道路。
康德以知性的建构功能和理性的范导功能宣布人为自然立法,解决了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一方案一方面把知识之基础归结为主体的能力,另一方面把知识限制在现象界之内,排除在物自体之外,从而使存在独立于知识,道德独立于知识,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严厉打击了知识主义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哥白尼式的革命之意义与其说是倒转知识所以可能的中心,倒不如说是取消了知识主义传统在“未来形而上学”中的中心地位。
黑格尔则不然。他和费希持、谢林一样试图消解康德哲学中不能成为知识对象的物自体,最终成为知识主义传统的代言人(尽管他的最高原则也许是非理性或神秘主义的)。他通过“实体即主体”的理性原则展开了“否定的辩证法”,实现了存在论、认识论与逻辑学的统一,即存在、知识、本质在绝对精神的历史展开中的统一。至此,西方哲学史上的理性主义和知识主义巅峰形成了。
海德格尔认为,是马克思首次翻转了柏拉图主义。通常的看法是,柏拉图主义正是西方哲学中知识主义传统的代表,因此,马克思无疑是哲学家中的革命派,其革命性主要表现在:1.从人类的实践活动出发去解释人类史和人类社会的诸种现象;2.对人类历史和社会生活采取实证的理论态度;3.设定“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人学目的论的价值取向。这三个方面贯穿在马克思的整个理论生涯中,构成了他的方法论基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写道:“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1卷,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一思想也许可以看作是“拒斥形而上学”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先驱。所谓“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乃是要求对事物进行经验的刻画,摆脱诸种意识形态的束缚和遮蔽,展现“庐山真面目”;所谓“(按照)产生根源”乃是要求对发生史进行经验研究,剔除任何神秘或先验的阴影。马克思对语言的思考也是以此为基础的。
二、马克思的语言观
马克思并没有专门论述语言的著作,相关的讨论散见于各种著作中,但他对语言问题还是极为关注的。当代西方哲学家普遍认为,“语言在哲学中始终占据着荣耀的地位,因为人对自己及其世界的理解是在语言中形成和表达的,这一点甚至从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和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篇》的时代以来就为人们所承认了”。(P·利科主编:《当代哲学主要趋向》,中文1版,3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这一点并不与马克思的观点相悖,因为“理解在语言中如何形成和表达”与“理解如何通过实践活动在语言中形成和表达”不是同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理解”是指已经自觉地认识到或反思到的话,它必须在语言中获得。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文1版,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这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实践活动本身就包括着对世界的“理解”,但同时应注意到,这种“理解”只有进入语言,因而成为思想中的被把握的对象,才能成为真正的理解。因为简单地说,理解是意识份内的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虚幻性以及圣布鲁诺、圣麦克斯等人的语言戏法令马克思深恶痛绝,他感到有必要澄清语言问题。这里可以分三个方面来分析。
1.语言的物质性。为了反抗黑格尔式的德国唯心主义对语言的神秘化,马克思特意强调了语言的物质性。他不无讽刺地写道:“‘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1页。)如果离开当时的语境,这一点其实卑之无甚高论。马克思语言观的精彩之处在于:2.强调语言的实践性、社会性、交往性,即把它作为一种实践方式和社会产物来理解,因而与其说马克思在讨论语言,不如说是在讨论“语言活动”;3.并由此出发讨论语言与意识、观念、思想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说:“语言与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同上书,第81页。)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比如说,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活动方式使我们根据经验区分外物并命名,从而逐渐产生了语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405~4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因此,语言是人们的社会产物,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他的,而且他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或者说,语言本身一定是共同体的产物,正像从另一方面来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一样。而许多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的发展,这是根本不可思议的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489、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马克思有句被广泛引用的名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此前,他把语言称作“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6页。)马克思还写道:“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9页。)这无疑是说,语言是思想或观念的存在方式,我们可以而且只能通过语言来研究思想和观念。因为所谓“现实”,就意味着思想实现了自己的存在可能性,把语言作为载体;而所谓“直接”就意味着不通过其他中介,思想也就不能隐藏在某种实体背后来发号施令了。这样,语言就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外壳,而是直接与思想同一。否则的话,思想或观念有可能成为超验的所指,而独立于能指这一差异系统,仿佛外面是物质实体,而内核是精神实体;但实际情况可能如同玉葱层层剥揭,内蕴核心,了不可觅。M·福柯在其《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一文中指出,从古希腊到现代的诸多解释方法总是怀疑语言背后有一个完全脱离语言的实体,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弗洛伊德的《释梦》、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和《道德的谱系》开辟了现代解释学,他们的解释方法实际上否定了通常所谓的“深层意义”或“真理”。
既然语言是社会关系、交往形式的产物,又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那么可以获得两个重要结论:1.思想、观念、精神不可能有任何神秘性或实体性(如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2.我们可以揭穿某种“语言共同体”(姑妄称之)的秘密,由此批判各种虚假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写道:“我们看到,从思维过渡到现实,也就是从语言过渡到生活的整个问题,只存在于哲学幻想中,也就是说,只有在那种不会明白自已在想象中脱离生活的性质和根源的哲学意识看来才是合理的。这是个大问题,由于它总是闪现在我们这些思想家的头脑中,当然最终一定会迫使这些游侠骑士中的一个人出发去寻找这样一个词,这个词作为词构成可寻觅的过渡,这个词作为词不再单纯是词了,这个词用神秘的超语言的方式指出从语言走到它所标示的现实客体的道路,简而言之,这个词在一切词中起一种和救世主一圣子在人们中起的基督教幻想的作用一样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8~529页。)
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德国唯心主义或唯灵论的思考方式:将思想、观念、精神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实体化、客观化、神秘化,使之具有独立于生活世界,甚至创造外在世界的力量;进而把它们诉诸具有可操作性的语言,使之获得充分的表现(包括采取各种语言戏法,如借助于对词源的考察、一词多义现象等);然后又把语词超语言化,使之具有创世和救世的力量,从而可以用来演奏他们的“狂想曲”。例如,黑格尔常自夸德语优于其他近世语言,且适于思辨,“碰到这样的字,遇到对立物的统一,已经以素朴的形式,作为有相反意义的字出现于字典里,这对于思维是一种乐趣”。(黑格尔:《逻辑学》上卷,中文1版,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
马克思从他们的阵营中走出来之后,反戈一击,一针见血地指出:“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5页。)可见,马克思能够独具慧眼的原因就在于他把自己的理论定位(orientation)贯彻到底:不是思想领域、理论世界,更不是某种意识形态,而是生活实践、现实生活。从这一点出发,也许可以说,你想知道生命是什么,人性是什么,甚至语言是什么,你就必须去看现实的人的生命表现,去看一部关于人的实际的自然史,去看语言在生活中的实际运用;而不能只在书斋里玄想或演绎出某种理论体系,并且不得不去寻找哲人之石、方圆法和长生不老药,寻找一种本身能够从语言和思维的王国引到现实生活上去的具有神奇力量的“词”。
对德意志唯心主义的“语言共同体”来说,“哲学语言的秘密”就在于:“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一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是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同上书,第525页。)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来说,德国哲学是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结果,但它却试图成为关于世界的一般性理论,因此,这种“语言共同体”只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因而其意识形态也是虚假的。只有从现实的交往形式出发,才能揭露其虚伪性;只有揭露了其虚伪性,才可能获得对人类史、人类社会的真实的认识。由语言批判转向意识形态批判是马克思的一大创见,它对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启示极为巨大。
三、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
马克思语言观的基本宗旨是“去蔽”——去思想之蔽,解思想之困,也是“治疗”——治疗哲学因误解语言与生活而发作的“精神狂想症”。这些思想与现代哲学的很多著名观点不谋而合——这恰恰证明了马克思语言观的合理性和现代性,或者说,正是从生活实践出发考察语言的合理性造就了这种不约而同。
维持根斯坦是公认的语言哲学大师,其后期语言批判思想的核心概念是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说:“必须接受的东西、给予我们的东西,乃是——人们可以说——生活形式。”(L·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文1版,3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在他看来:第一,生活形式是怀疑的界限。因为“怀疑总有个终点”,(同上书,第274页。)“怀疑的游戏本身以确定性为前提”,而“现在我想把这种确定性不是看作某种类似于轻率、表面的东西,而是看作生活形式”。(L·维特根斯坦:《论确定性》,英文版,115、358页,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9。)第二,生活形式是语言的界限。因为“语言的述说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想像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像一种生活形式”。(L·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17、12页。)但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可以说生活形式是语言批判的基础,又必须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因为前者是看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的;后者是想出来的,却没有看清。维特根斯坦强调:“再说一遍,不要去想,而是要去看!”(同上书,第47页。)那么我们看到的生活形式是什么?是我们完整的生活——置身于人类继承下来的共同的文化背景中,它表现为人类的行为和活动,表达出人类的情境(如习惯和制度),构成了一部人类自然史。因此,生活形式并非外在于、独立于言语行为的东西,毋宁说语言是具体而微的生活形式。
既然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就是它在生活形式中的使用——各种语言游戏中的使用,那么语言批判就是思想批判,“当我用语言来思想时,除了该表达式以外并没有什么‘意义’呈现在我的心灵之中:语言自身就是思想的载体”。(同上书,第160页。)承认这一点,不仅意味着我们只想能通过语言来研究思想,通过澄清语言表达来为思想解困,而且意味着,“我在思想/我是思想的主体”这些句子是无意义的。
既然“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同上书,第31页。)那么实指定义(ostensive definition)就是不可能的。维持根斯坦用了很大篇幅反驳实指定义的可能性,意在批判把意义规定为所指或指示关系的理论。在他看来,哲学不是知识,知识是一种说明,说明总需有预设,但“我们不会提出任何一种理论。在我们的考察中必须没有任何假设性的东西。我们必须抛弃一切说明,而仅仅代之以描述”。(同上书,第71页。)“哲学……最终只能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述”。(同上书,第75页。)由于以往的哲学命题是对语言的实际使用(用法)的误解,所以这种描述就是治病。因此哲学不是发现什么,而是去掉什么——去病、去蔽。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都是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柏拉图主义传统的终结者。值得考虑的是,这两种转向的发生机制是不同的:从价值目的上说,马克思是在为全人类谋福利,而维特根斯坦则试图从一种悲剧性的人生苦闷中解脱出来;从理论哲学上说,马克思要求对人类历史进行实践性的理解和经验性的刻画,以此来瓦解唯心主义的思辨根基,建立一种新的世界观,而维特根斯坦则试图从思辨哲学的可能性基础上进行颠覆,重新理解哲学的价值。因此,语言观对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来说是从属性的,是以他的新世界观为依托的;面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则是基础性和根本性的,他正是从这个角度入手,逐步揭露传统哲学在立足点上的似是而非和武断虚妄。这些方面决定了他们的价值取向不同,语言观也有所差异。
不过,就终结西方哲学传统而言,两人的语言观是有殊途同归之处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从生活实践、生活形式出发理解语言和思想,而不是相反,这样就消除了语言的神秘性和思想的实体性,在理论上取消了唯心主义的合理性。例如,维特根斯坦把奠基于生活形式之上的语言游戏作为自明的出发点,在他看来,语言游戏是一个真正而平凡的哲学概念,它强调的是作为言语行为的实践性的语言,它使我们对语言的哲学研究独立于理论语言学、神经生理心理学和认识心理学等经验科学,并使我们放弃了对语言的本质的形而上学探讨,代之以对语言游戏本身的描述;语言是人的语言,而不是大脑的、发声系统的语言;语言是生活中的语言,生活中的语言并没有表现出规则演算或谓词演算的特征——许多现代分析哲学家却致力于构造这些演算系统;人的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和创造性。这样一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马克思的基本思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