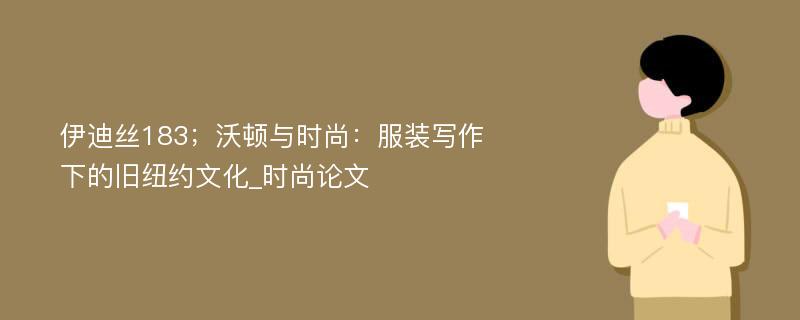
伊迪丝#183;华顿与时尚——服饰书写下的老纽约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纽约论文,服饰论文,文化论文,时尚论文,伊迪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尚,通常“指流行的着装方式”。①在日常生活中,虽然时尚并不是绝对的决定人们每天穿戴什么的标准来,但它的风向标仍然引领着都市街头不断变换的色调和翻新的风格。这似乎在宣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时尚已经在我们的社会里坚定地扎下了根。
“早在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时期,时装就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巴特20)它是体现我们自身社会行为的一种标志,而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对服饰的言语转换和对服饰的符号读解,我们能看到服饰与现实极不普通的关联。一般来说,我们既可以从服装风格上大体判断着装者所处的年代,也可以通过着装习惯的细微差别判断着装者所处的阶层。同样,在小说作品中服装与现实的关联通过文字的描述往往被具体化,由此,以服饰书写所划定的时空界线也更加清楚明了,因为它孕载着文化,体现着功用、价值、美感甚至道德和情感。它的重点不仅是服饰的实体、颜色、触感、硬度或者亮度,也是服饰特征背后的隐喻,是细枝末节所关联的阶级、性别和个性特征,是与此相联系的情境(包括时间和空间的)差别。
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1862-1937)是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后最出色的风俗小说家之一。她的作品多以19世纪末期纽约的上流社会生活为背景。在她的笔下,众多衣着光鲜、举止优雅的绅士、淑女们在季节的更替和世态的变迁中“被时尚之风吹得到处飘荡”(华顿1993:327)。在《欢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1905)和《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1920)这两部描写维多利亚美国的风俗小说中,细致的服饰书写更是成为作品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老纽约的时尚原则
一百年前的纽约同样受时尚的风气左右。19世纪末20世纪初,老纽约居民对时尚的要求更是繁多细致:除了日常生活和特殊场合必备的服装外,“一个人到乡下做客,打高尔夫球、滑冰,需要各式各样的衣服,还有艾肯式和晚礼服”(华顿1993:173)。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中,幼年的伊迪丝·华顿也希望长大后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成为“纽约穿得最好的女士”。在文学创作没能给她足够信心的时候,她也依赖时尚获得勇气。在成名之前,华顿曾有两次机会与当时蜚声文坛的亨利·詹姆斯见面。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她不过二十四、五岁年纪,“我穿上了新的杜塞裙,尽量让自己看上去最漂亮……那是一直教育我长大的原则”(Wharton 172)。但尽管有着最新款式的杜塞裙壮胆,她也不敢上去和詹姆斯交谈;一、两年后,他们在威尼斯同时收到朋友的邀请,同赴另一场晚宴,她选择了“一顶漂亮、崭新的帽子”!可惜这顶帽子最终也没能引起詹姆斯的注意。
借助服饰来帮助定义自己,并增加自身影响的思维习惯显然曾是华顿生活的一个基本原则。她“将女性时尚看作重要的标记之一来追踪19世纪最后几十年和20世纪头30年里小说人物专事的社会常态的变化”(Banta 52),因此,服饰书写几乎成为她的作品组成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尽管她并没有像研究室内装潢一样对服饰做系统的了解,但长期冷静观察包裹在华服中的上流社会给了她理解时尚的第一手资料。“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沙砾和花朵渺小地对应着世界与生活,华顿笔下的一纱一线也将帮助她深入世事,揭示时尚所隐蔽的社会现象,传达出个性对公众和社会习俗的遵从与反抗。
华顿小说的服饰书写多而精确,常带给读者以实在感。在《欢乐之家》和《纯真年代》这两部小说中更是如此。在她笔下,老纽约的绅士淑女们凭借不断变化的时尚把自己和其他阶层明显区分开来,建立起界限,培养独特的优越感。服饰选择成为阶级属性和阶级差别的标志,正如西美尔(Georg Simmel)在《时尚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Fashion")一文里谈到的那样:“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相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作用”,它“意味着相同阶层的联合,意味着一个以它为特征的社会圈子的共同性”(西美尔72—3)。在一部写实小说的服饰书写中,最为明显的服饰的隐喻是服装所对应的阶级差别。对于华顿来说,她的人物绝对不会穿错衣服:打杂女工戴旧的无边帽,围披肩;黝黑面孔的西西里女佣“戴着花哨的围巾”;英国来的公爵“穿的晚礼服是那样蹩脚,那样寒酸”(华顿2002:54—9)。这不仅仅因为风俗小说要求她的人物遵从因袭的一切常规,还因为,于老纽约而言时尚也是等级制度下的一种秩序,“他们从根源上将它(时尚)看做是贵族的”,“具有贵族和大量财富的特许”(Hoganson 72)。只有合乎身份与地位的穿着和打扮才是正确、合理、可行的,他们“穿得像欧洲贵族既是为了显示与社会精英的紧密联系,也是为了表现他们与社会较低等级的距离”(Hoganson 80)。
老纽约的阵线联盟在长期的磨合与振荡中已经将时尚划为了自身传统的一部分,它和家装布置、家具陈设、晚宴以及舞会一样,成为上流社会的一条锁链,把其中的每个成员时刻捆绑在一起。女人们“对衣着……(有着)詹尼那种病态的兴趣”(华顿2002:169),男人们则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他们从巴黎订制大量高档服装,并恪守着装规范的种种细节。他们鄙视那些没有教养、穿猎装就餐的“外国”客人,并对女士穿“晚餐便装”露出手腕还是肘部斤斤计较。“‘时新’(stylishness)是纽约人最看重的东西”,但即便如此“穿最新的时装(仍)被认为很粗俗”(华顿2002:53,225)。这一独特、保守的习惯仿佛违反时尚的常理,和他人追逐潮流的习惯大相径庭,但却将老纽约和他人彻底地区分开来,成为一种划分等级的观念。其实,服饰隐语的背后也是历史。“穿最新的时装被认为很粗俗”的观念并不是自古不变或延续至今的法则,这是19世纪70年代以前流行在波士顿、纽约等城市资产阶级中上层的一种习俗,要求女士们把巴黎订制回来的服装压上两季再穿,后来,炫耀财富和尽情享乐的风气盛行,于是暴发户们摒弃了这种保守的习惯。
对于这个似乎矛盾冲突的时尚观念有着以下两种解释:一、它代表了欧洲文化在美国的影响,欧洲成为老纽约一切有意义的行为和生活之源。“纽约向来就是个商业社会”(华顿2002:42),华顿借阿切尔太太之口告诉读者,和欧洲的上流社会不同,组成老纽约的名门望族并不是拥有贵族血统的皇室贵胄,他们多在殖民地早期从英国和荷兰移民而来,通过数代人诚实、辛劳的经营累积起财富,成为纽约金字塔尖的权贵人物。因此,他们“还不太确定美国人到底是什么,他们模仿欧洲,特别是法国文化,显示出一种不确定性”(Wikipedia:Victorian America)。文雅的谈吐、华丽的着装、细致的礼仪、丰富的娱乐——这种源自欧洲的享乐主义的风气成为美国上流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旨在标榜其与普通民众辛苦劳作有明显差距的有闲和富裕;二、它也代表了一种清教伦理。早期开拓者们崇尚朴素和节约,他们深受伦理道德约束的清教思想流传了下来,制约了后辈们显著消费的欲望。两者的冲突和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价值观并行不悖的老纽约传统,这也表现在着装上。他们紧紧追随欧洲的脚步,同时受清教思想影响,由此养成了含而不露的矜持。所以“把巴黎的服装压上两季再穿”不仅是与阶级观念相关的时尚风潮,也是与历史背景相关的文化理念。
时尚是善变的。每一年,每一季,我们都看得到它在人的身体上发生的些许改变。其实,这也是历史和文化催生的观念的变化。19世纪80年代,随着缝纫机发明的完善和成衣工业的发展,时装开始有了“正式”的分工:茶会裙(tea gowns)、晚礼服(evening gowns)、舞会裙(ball gowns)、社交裙(casino gowns)、游艇装(yachting costumes)、戏水装(watering-place costumes)等等,美国人的时尚要求开始得以实现。1889年《女士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的一位时尚作家写道:“穿着得体的普遍愿望本质上是女性气质的,是自然的”(Hoganson 71)。这位作者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掉了服饰的阶级性,强调时尚所象征的无差别的统一。它其实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想法,特别是新出现的百万富翁们。他们打破了老纽约所设置的时尚的障碍,大批订购巴黎的最新装束,不会受到“把巴黎的衣服压上两季再穿”的制约。在他们那里,高价就是美,“在服装上为了夸耀而进行的花费,情况总是格外显著,风气也总是格外普遍”(凡勃伦122)。这一点在华顿的小说中刻画得格外明显,(正在/刚刚)设法挤进上流社会的人们都怀揣着野心披上了炫耀性的装束:《纯真年代》中穿白色栗鼠皮衣服的博福特夫妇、《欢乐之家》中由时髦的伦敦服装“装潢”的罗斯戴尔、靠有“艺术风格”的礼服制造效果的伯莎·道塞特……与莉莉·巴特相比,《里维埃拉通讯》报的记者小达布罕更愿意注意到塞特太太,不是因为伯莎更漂亮、优雅或聪敏,而是因为她“新奇纤巧”的衣服是金钱堆积的明证。在一个金钱的社会里,时髦是女人对丈夫财产履行的潇洒、豁达的代理消费。伯莎成功地理解并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和经济上捉襟见肘的莉莉交手中总是立于不败之地。
时尚的物化:个人与大众的矛盾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服饰的显著消费所带来的影响。1902年8月《纽约世界》(New York World)刊登了一篇对英国艺术家菲利普·伯恩—琼斯爵士(Sir Philip Burne-Jones)的专访,针对美国社交界女性服饰的炫耀,他评论到:
奢侈在其他地方从没上升成为一种标准。炫耀从没有如此富有生机和纯粹……它就像一场辉煌的、野蛮人梦中的盛会。……他们的服饰是那样强烈、大胆、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他们的灵魂也许在底下什么地方包裹着、隐匿着、埋葬着,但人们不能轻易地看见。要找到他们真实的自我很难,因为他们的衣服——他们华丽炫目的衣服。(Montgomery 125)
从伯恩—琼斯的批评来看,服饰的显著消费带来的问题主要是关于人性的。由奢侈引导的时尚埋没了人的本真性格。服饰也是一种伪饰,它把自己的特征转嫁到个人身上,使他/她具有变化的特质。有的时候,它甚至成为异化自我的标志,把一些与个人不同的性质强加到他们身上,这是外在物质条件对人的物化。从时尚来说,它对人的物化主要表现在它要求一种形式甚至价值观念上的“趋同”,即个人受潮流束缚,不得不追随其变化而变化,或者至少“在外在性上作出牺牲,即在外在性上受一般大众的支配,以达到保存内在自由的目的”(西美尔83)。华顿的服饰书写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一方面个人受时尚支配,模仿他人,将自我建构融入社会整体中;另一方面,个人听从自我要求,保持独立,拒绝物化。这两者的矛盾始终在斗争和屈服中反复,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对此,《欢乐之家》中的莉莉·巴特可谓深有感触。这位出类拔萃的女性总有着偿还不尽的债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需要付给裁缝和时装店的,因为,在她生活的圈子里“邀请女人要看她本人,同时还要看她的穿着。衣服是背景,或者就得算基础。衣服本身不能取得成功,却是成功的组成部分”(华顿1993:12)。由此,代表着美国精英的老纽约赋予了时尚更多的社会隐喻,它与豪宅、汽车、珠宝等其他物质基础形成的象征驱使着人们将其作为一项成功的标准得到广泛的认同。
这种认同在上流社会及其追捧者中间内化为一种自身需求的假象,成为个人品位的佐证,迫使人为此努力和奋斗。正是这种“服装=成功”论的内化作用断绝了莉莉理解生活内涵的真正途径,根植下错误的成功观念,让她把寒碜的衣着与粗鄙低下联系到一起,最简单地类化了富有、时髦、美丽和高雅以及贫穷、丑陋、粗俗和狭隘;它和老纽约各种光辉夺目的规范一起,形成一股奇特的向心力,否定他们观念范畴外的一切。
莉莉在上流社会追求“成功”的过程实际上是自我异化过程,她的服装也参与其中,成为自我异化的一大因素。“在她寻找配偶的本能的盲目行动里”(同上327),她常常按照每次行动的目的装扮起来,在周围形成“合适”的氛围,比如她有一个计划来吸引富有但羞涩、保守的《美国史书》拥有者格莱斯先生。“为实现她的目的,她甚至比平时起得要早。她想,自己身穿虔诚的灰色长外衣,那引人注目的长睫毛对着祈祷书垂下,这样一副神采将使征服格莱斯的事业臻于完美”(同上54)。这里,莉莉配合服装的暗示,穿什么就是什么。灰色长外衣被赋予了人格特征,并将“虔诚”的特质转嫁给她,让她具有与服装相同的气质,做出背离“自我”的事情。
不过,莉莉本人对物欲社会的逃离和反叛是犹豫和反复的。她是“屈服于庸俗需求的理想主义者”,“私下里……对金钱那种赤裸裸的欲望感到羞耻”(同上259,35)。她本性中高尚、善良的部分总是促使她摆脱上流社会的向心力。“她心里看不起她自己努力争取的东西”(同上193)才总是错过世人眼中绝好的婚姻机缘。不过,即使在最糟糕的状态中,漂亮的衣服仍是莉莉的安慰,它们是她“光辉历程的残留物……留下的衣服虽然已经不新,却仍然长期保留着原封不动的轮廓,富有大艺术家的笔触神韵。她把衣服摊在床上,它们穿在身上时的那些场面又历历浮现在她的眼前。每一个褶痕都埋藏着联想,每一个花边的下摆,每一道刺绣的闪光——都像记录她过去的文字。她发现旧日生活的气氛如此浓重地包围着她,不禁大吃一惊”(同上325)。
其实,莉莉对衣服和旧日生活的联想是符合常理的。在消费社会中,流行服饰具有的社会隐喻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必须突出其声誉根源,即贵族模式……(它)以一种愉悦的方式,通过把内在世事的功能转化为符号(工作、运动、度假、季节、庆祝会)”(巴特322),构成与奢华景象相关联的行为模式,它必定等同于丰富多彩、悠闲舒适的生活,与劳苦、奔波没有联系。它创造了一种群体成员感,也暗示了下层阶级的不安全感和极力要变动的心理。因此,寄人篱下的莉莉以及像她一样的女性才被流行服饰愉悦的构想引领着,孜孜不倦地追求这种构想所象征的上流社会的生活,在主流社会圈内形成样板,并吸引其他阶层做类似的模仿,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风气。
在这样的前提下,报纸和杂志也成为时尚传播的媒介。1890年前后,印刷业的发展和大众读者的崛起促使报纸和杂志担负起了娱乐与教化的双重责任。大量的报纸和家庭杂志开始针对女性读者的需求花大量篇幅打造“新女性”的形象:家庭、女性气质成为传媒宣传的重点。然而对多数以盈利为目的的报纸杂志来说,曲解女性气质的抽象定义,将它与“时尚”混为一谈是一种更简单易行的操作。著名的流行杂志《女王》(Queen)便把“(女性)可视的躯体定义为女性气质和由‘时尚’代表的财富”(Beetham 103)。华顿小说中的媒体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星期日增刊》(Sunday Supplements)、《里维埃拉通讯》(Riviera Notes)等报纸都开辟了专栏,把社交场合的各个画面转化为文字,为大众提供流行的娱乐资讯同时教导他们模仿名人的着装方式和举止。
于是在莉莉身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女性们努力地效仿时髦人士,从舞台、报纸、流行杂志处获得华而不实的爱好。尼斯的一家“餐馆里挤满了人,他们大部分是为了观光聚拢来的,而且事前准确地得悉了他们来看的名流和模样”,小报记者们也不失时机地混入其中,“除了注意太太们漂亮的晚礼服,便无所事事”(华顿1993:221)。在帽饰作坊里,女工们除了准确了解社交界名媛淑女在社会中的地位,还贪婪、好奇地对她们品头论足。而曾经接受莉莉资助的打字员内蒂·斯特拉瑟也对她说,“我们常常在报纸上注意你的名字,我们常常谈论你在做什么”,并且“阅读对你穿的衣服所做的描述”(同上322)。
以社交界为谈资是贴近流行风尚的一种普遍的做法,因为“较低的阶层几乎没有时尚,即使有的话也往往不是他们特有的”(西美尔75)。时尚这一由上而下的特性对中产阶级及以下民众的吸引造就了大众文化的明星,莉莉以及和她同阶层的女士们便是如此,她们广受关注,获得敬畏、羡慕和崇拜。她们用不断变化的服装所制造的新奇的视觉效果在普通人所承受的购买力制约中显现出财富特殊的魅力。这加强了“物化”的效果,同时也破坏了前消费社会中“长久”、“永恒”所代表的老的价值观念。在媒体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价值观念的“趋同”将个体的内部世界塑造成受制于时尚的扭曲的状态,在与大众差异性的斗争中丧失了活力,它决定了在大众意识中单一物品寿命短暂的必然和作为概念的“物”的广泛的胜利。
时尚与女性
像莉莉一样的年轻女性成为流行服饰的俘虏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在现实中,我们的确发现男性对时尚的免疫力仿佛要强得多,在大多数文学作品中间亦是如此。以《欢乐之家》为例,和服装相关的篇幅多是描写女性角色的:莉莉、和莉莉同阶层的朋友们以及制帽女工和女打字员……从巴特(Roland Barthes)的《流行体系》(The Fashion System,1967)来看,通常受时尚行为模式影响的也几乎都是女性,“绝对年轻,具有强烈同一性,同时又不失与之矛盾的个性”(290)。为什么女性与时尚的关系会如此紧密?为什么女性在服装风格、品位上表现出的差异虽大,却似乎都不能摆脱它的束缚呢?
华顿借人物之口一语道破真谛:“这(服饰)是她们的盔甲,是她们对陌生人的防范,也是对他们的挑衅”(华顿2002:172)。时尚总是对的,不管与美的绝对标准相差多远,穿着流行的服饰即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作为巨大社会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只要不脱离这个机器就不会一无是处。莉莉·巴特十分认同这一点,她深谙服饰的社会功用,明白女性——特别是富有家庭中的女性“出名的方式在于家庭关系和社交成功。这一社会定位的方式从根本上稳固了对巴黎时尚的供奉……女人们将巴黎的服装视为国民重视的社会资本的信用。比起生产来,她们更看重消费”(Hoganson 103)。基于对以上信念的清楚认识,莉莉从不在穿着上自惭形秽,“不让实用的服饰和皱巴巴的帽子表露出对命运的默认”(华顿1993:91)。就像当年还未成名的华顿一样,她需要靠穿着来营造一种社交优势,这是弱势的一种表现,也是对自身不足的弥补。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弱小感,害怕被排斥和牺牲,处于社会弱势的女性似乎更愿意接纳公众所提倡的品位和习惯,把自己融入传统,顺从包括时尚在内的各种普遍形式,在跟潮效应、认同效应和示范效应下成为流行趋势的附庸者。
每一个阶级,确切地,也许是每一个人,都存在着一定量的个性化冲动与融入整体之间的关系,以至于这些冲动中的某一个如果在某个社会领域得不到满足,就会寻找另外的社会领域,直到获得它所要求的满足为止。因此,当女性表现自我、追求个性的满足在别的领域无法实现时,时尚好像是阀门,为女性找到了实现这种满足的出口。
在14、15世纪,个性在德国社会中获得了充分发展。个人自由大大突破了中世纪的集体约束。但这种个人主义的发展并没有给女性带来更大的生存空间和个人行为的自由,她们的自我提升也得不到支持。出于补偿,她们在穿着上表现出过度的、夸张的时尚。(西美尔81—2)
和中世纪后期的德国相似,维多利亚的美国并没有为女性提供太多自由的选择。传统的家庭责任仍然是阻碍女性个体发展的借口。从整体来看,女性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依附地位,即使是由女性力量掌控的第五大街(时尚的窗口)也不能违背华尔街(由股票、金融代表的男性权力)的规矩来运作。此时,尽管女权运动正在酝酿之中,等待掀起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浪潮,但两性平等、政治、经济权力甚至公民权都依然遥不可及。在纽约资产阶级的中上层,女性在老纽约众多习俗和“责任”的限制下,想要获得个性发展和行动自由更是不大可能。《纯真年代》当中,艾伦·奥兰斯卡的离婚诉求便招来了家族甚至整个上流社会的集体反对;而她的表妹梅则把自己摆在妇道的祭坛上,成为“传统与崇尚的守护之神”(华顿2002:171)。在这样的环境下,她们要么意识到自己被奴役者的身份,在反抗中被放逐或抹杀,要么把被奴役的观念内化为一种完全自觉的行为和根深蒂固的传统。除此以外,她们还要受到时代带来的新的囿限。“消费文化的发展迅速地推动女性进入公众领域,其间,如要想符合最新的时尚,便需要不断更新女性有闲阶级的身份。……新女性成为公众展示物,屈从于媒体、熟人和其他居民的审视,被迫通过她的服饰和举止展示她的非生产性角色”(Gair 273)。女性的命运终究是社会铸就的,在将女性变为时尚达人的过程中,经济、文化、政治、性等诸多因素参与其中形塑了一位在男性社会中的耀眼、光亮、积极却又被动的原型。她的身体被注视和参观,而她也只能允许自己被有闲和奢侈商品化。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一直以来由于在教育、工作、生活和娱乐等各个领域受到太多的局限,缺乏发挥自我个性和才能的渠道,因此(一旦经济允许)她们往往只好以时尚消费获得满足,促发经济、思想和艺术交互作用下的一股文化意识潮流。
《巨变:美国的变形1900-1950》(The Big Change:America Transforms Itself 1900-1950,1952)的作者弗里德里克·路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说:1900年前后每个走在美国大街上的人都会对女性的裙子发出感慨。
因为每个城里的成年女性都穿着裙摆几乎及地的服装;实际上如果衣物的主人不懂得提裙,那它们会不时扫着地面,污损了裙裾。从女士裙装的整体来看,1900年的女性从头到脚都包裹在物质之中。(肯定的是,对这种包裹有专制的限定。时髦女士的晚礼服低领露肩,和50年代电视明星的差不多。但穿这样的衣服也要训练,着装者必须在跳舞的时候尽量提好裙子。)即使是乡间的装束,实际上即使是高尔夫球装或网球装,裙子也必须只离地两、三英寸,还有帽子——一般是硬的水手帽——几乎是必须强制戴上的。(8)
按照艾伦的说法,这样的时尚无异于“个人牢房”——穿着时髦衣裙的女性绝对无法按照她们的想法自由活动,去她们想去的地方。因此,时尚限制了女性的生存空间,是对女性身体的束缚。而这种束缚,成为正常劳作和运动的一大障碍,为女性沦落为性的牺牲品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它来自于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传统,将女性视为置于男性羽翼保护下的、柔弱的尤物,这和维多利亚时期天真、不经世事的女性“天使”形象相吻合,成为一种心理的束缚。它使女性的意识空间里只能容纳“穿着贵重的衣服并保持极度闲适、优雅”(华顿2002:7)的着装原则,忽视个体本真的表露与追求,将自我建构的自由意志禁锢在男性的视觉享受中间。
华顿抓住服饰书写的功用,将其充分地发挥在文学作品当中,将上个世纪末的流行动态生动、细致地表现出来,就像人类学家在远古的祭祀活动中捕捉人类社会发展的细节一样,小说再现的真实将商业和消费发展最初的维多利亚美国带回到人们眼前。老纽约再也不复存在,这一群体和他们绚亮的服饰、辉煌的历史一起被湮没在新兴商业时代虚假的繁荣和大众无尽的想象之中。新世纪即将到来,它所象征的由中产阶级造就的大众文明将取代维多利亚的斯文传统,但老纽约服饰文化的本质特征——“时尚”的观念却保留下来,大家都坦然接受。因为人们对“流行于饶有古风的有闲阶级中的那些生活、观念、理想和消费时间与物品的方式加以官场的欣赏得来的享乐和意向,同对于现代社会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知识和志趣等方面的熟悉以及从这种熟悉中得到的结果比起来,人们总觉得前者是‘高一级的’、‘比较高尚的’、‘比较有价值的’”(凡勃伦279)。在一百多年来与大众文明的折中和平衡中,时尚已经成为了通俗文化的范例,不管它暗指的是庸俗化的高雅还是中、上阶层的平民化,总之它的存在已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吸引了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在服饰选择所代表的文化选择中淘得或真实的抑或是不真实的“自我”。
注释:
①Wikipedia:"fashion" describes the popular clothing style.
标签:时尚论文; 女性服饰论文; 着装礼仪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纯真年代论文; 欢乐之家论文; 服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