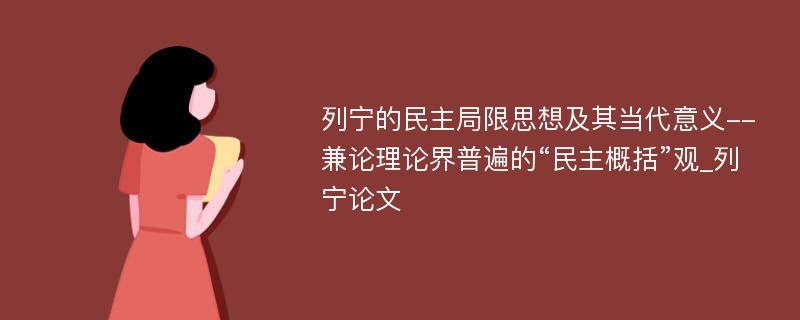
列宁关于民主限度的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兼驳理论界“民主泛化”的流行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理论界论文,列宁论文,限度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14)10-0128-005 所谓“民主泛化”,集中表现为夸大民主的作用和适用范围,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超阶级的、纯粹的民主。戈尔巴乔夫时期极端民主化的改革就是“民主泛化”的典型表现,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民主化”和“公开性”,而置社会和民众的承受能力于不顾。事实上,列宁对“纯粹民主”等论调持批判的态度,认为民主是有限度的。当前条件下,学习列宁关于民主限度的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民主、避免陷入理论误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列宁关于民主限度的思想 列宁从未一般地否认“民主化”的合理性,相反把民主作为自己孜孜以求的目标,但列宁坚决反对脱离具体实际去谈论“广泛民主原则”,[1](P417)强调民主的发展是有限度的。列宁关于民主限度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超阶级的、纯粹的民主 列宁反对抽象地谈论“纯粹民主”,认为民主具有阶级性。针对考茨基等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推崇“纯粹民主”,“彻底民主”,“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阶级的民主”[2](P721)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做法,列宁指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超阶级的、纯粹的民主。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强调:“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附带说一下,‘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无知之谈,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历史上有代替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有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2](P600-601)基于此,列宁认为,考茨基等人高谈“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企图欺骗群众,掩盖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2](P683)构建民主与专政之间的二元对立,进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可以说,民主是具体的,民主具有阶级属性,是列宁对民主概念的深刻解读。考茨基等人的错误不在于对民主的重视与强调,而是在于鼓吹一个超阶级的、纯粹的“彻底民主”。因为“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它向我们指出,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人的认识的一种狭隘性、片面性,表明人的认识不能彻底把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3](P483)基于这样的认识,列宁在《论“民主”和专政》一文中批驳道:“这时候高谈什么纯粹民主、一般民主、平等、自由、全民性,就是嘲弄被剥削的劳动者,就是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2](P684)因此,列宁警告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资产阶级“超阶级的民主”、“纯粹民主”的论调保持清醒的认识。即“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谈一般‘民主’是很自然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决不会忘记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对哪个阶级的民主?’”[2](P593)在这里,列宁强调了民主是有限度的,即民主具有阶级局限性。 2.民主的发展程度受到经济、文化、阶级斗争等条件的制约 在列宁看来,民主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民主权利实现到什么样的程度,都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对此,列宁曾鲜明地指出:“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的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4](P405)由于受到经济、文化、阶级斗争等条件的制约,民主的发展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首先,民主的发展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俄国是经济极其落后的小农国家,这种半农奴制的小农经济像一把沉重的枷锁套在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身上,“阻碍着一切等级和一切阶级的政治思想的发展”。[4](P72)因此,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执掌政权以后,在积极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同时,大力恢复与发展经济,为民主的发展和建设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即便列宁在晚年之际,他还是担忧,经济落后的现实国情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制约,当然也包括对民主建设的制约。因为在他看来:“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制度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共同存在’的,它也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受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2](P181) 其次,民主的发展还受到文化条件的制约。关于这一点,列宁有一句经典名言,即“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4](P590)俄国极其落后的文化水平致使民众参政议政的意识淡薄,同时也不具备管理国家事务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对此,列宁指出:“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作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2](P766)本来,列宁设想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在俄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使得全体劳动者都参与到管理国家事务中来,但列宁很快发现,这种民主形式与俄国极其落后的文化水平不匹配,不得不转而采取由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代之管理的间接民主。同时,列宁指出,虽然我们的法律有助于实行高度的民主,“但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大量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这不能用法律迅速办到,这需要进行长期的巨大的努力”。[2](P766) 此外,民主的发展还受到阶级斗争条件的制约。如同列宁所讲,任何仇视社会主义的反对势力,“它一定会打着自由的旗号来反对我们”。[2](P811)同时他们还会宣扬其资产阶级民主的纯粹性和超阶级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此,列宁指出,资产阶级鼓吹其制度是最自由的制度,“现在法、英这些西欧文明国家和美国都打着这面旗帜,‘为了自由’而反对布尔什维克”。[2](P811)某种程度上,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更是为了反对仇视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列宁强调民主的发展是有限度的。 3.党内民主是有限度的,必须以维护党的纪律为前提 党内民主是指党员是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党员具有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参与和决定党内事务的权利和资格。就此而言,党员权利从实质上讲就是一种自由。这种自由表现在诸多方面,如党内讨论的自由、党内批评的自由、党内表决的自由等。但是如同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一样,党员的自由也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集中表现为党的纪律。对此,列宁强调发展党内民主要适度,必须以维护党的纪律为前提,不能破坏党的纪律。对此,列宁给党的集中制纪律下定义为“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5](P341)在列宁看来,在党的最终决定作出之前,党员进行自由批评与讨论是完全允许的,因为只有根据自由批评的原则,“党才能很好地解决一切争执和一切误会”,[6](P129)但列宁同时也指出,在党的决定完全作出之后,就“表明不容许有任何破坏或者妨害党既定行动的一致的批评”。[6](P129)列宁在这里强调的是,发扬党内民主必须以维护党的纪律为前提,如果党员在行使自由批评与讨论等民主权利时毫不顾及党的纪律,党内就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党也就很难形成统一的意见,作出最后的决定,那么,党也就难以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与重任。 二、戈尔巴乔夫时期极端民主化改革的失败教训 列宁对超阶级的、纯粹的民主的批判以及对民主限度的强调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政治事态发展就不可辩驳地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时期极端民主化改革就是“民主泛化”的典型表现,盲目地强调“公开性”与“民主化”而不顾具体实际,从而突破了“社会稳定、政局稳定、人心稳定”的基本前提,终落得玩火自焚、亡党亡国的境地。 1.片面强调民主化,弱化党的集中制纪律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了要对党自身进行彻底改革的思想,主张党内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作报告时指出,列宁为党制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培养了“军营式的职位等级纪律”,形成了官僚专制、行政命令,是一种官僚主义的强权。因此,为了更好地“坚持民主原则”,苏共就要“坚决放弃在行政命令体制条件下形成的那种硬性集中的民主集中制”。[7](P129)此外,戈尔巴乔夫还认为“少数服从多数”和“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极大地限制和侵犯了个人自由。于是,他坚称:“如果一些党员对某些问题持有不同于多数党员立场的观点,他们可以自由讨论和宣传自己的观点,甚至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这些观点。”[7](P45)这样,在苏共党内顿时涌现出了诸多个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围绕着改革的方针、政策以及目标,甚至围绕着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以及合法性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之后,愈演愈烈,党内批评与讨论的自由逐渐超出了党的纪律和党的原则范围,致使党在组织上出现极大的混乱,党内派别林立,党内意见分歧也逐渐演化为党的分裂。 2.追求无条件的民主,忽略了民主的阶级属性 随着改革的深入,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逐步偏离了苏共实际。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戈尔巴乔夫极力推崇不分阶级的、全民的民主,抛开社会主义原则和法制去抽象地倡导“超阶级的民主”,声称苏联共产党是全体人民的党。甚至在1988年的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追求“无条件的民主”。这不仅削弱了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降低了党的决策的权威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无政府主义和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一时之间,“民主”一词充斥着官方文件、党的报刊杂志、舆论媒体,并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涵义。而各个政治反对派别则借机鼓吹西方民主的纯粹性与普世性,将“民主化”与“公开性”作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工具,歪曲与诋毁苏共的历史。 3.民主化改革走向极端,放弃党的领导 戈尔巴乔夫民主化改革主张放弃苏共的执政地位,这使得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彻底走向了极端。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阶级对全体人民的专制,苏共一党执政就是对国家权力的垄断与制裁。因此,要实现政治民主化,苏共必须结束一党专政,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在多党竞选中谋求自己的执政地位。他说,“民主国家的必由之路是实行多党制。我国在逐渐建立各种不同的政党。同时,苏共也必然要进行根本性的革新。……我确信,大多数普通党员会把党的前途依托于民主派的”。[7](P459)这也就意味着,戈尔巴乔夫要把苏共变成组织议会和总统选举的议会党,放弃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综上所述,戈尔巴乔夫的极端民主化改革给弊病百出的苏共以致命一击。从提出“民主化”口号到取消民主集中制原则,不限制党员在辩论过程中按纲领进行联合,再到追求“无条件的民主”,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到最后取消党的领导地位,转而实行多党制。这一系列极端民主化的改革彻底摧毁了苏共的领导体制,消解了苏共执政的基石,也瓦解了苏共。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不在于强调“民主化”和“公开性”,我们也很难指出民主化和公开性这两个概念本身存在着什么样的缺陷,毕竟这两个概念列宁也曾强调过,并将之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在于他对“民主化”和“公开性”的过度迷恋,推崇超阶级的、纯粹的民主,不仅忽视了民主的阶级属性,也忽视了民主由于受到经济、文化、阶级斗争等条件的制约而具有渐进性。在苏共改革频频出现失误之际,在党内出现反党集团的情况下,甚至不顾西方仇视社会主义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离开社会主义谈民主,离开法制和纪律谈民主,势必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混乱。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戈尔巴乔夫忘记了列宁关于民主是有限度的谆谆教导,其主导的改革走向了民主化的极端,导致了苏共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处于节节败退的境地。 三、对理论界“民主泛化”论调的认识与思考 近些年来,国内理论界出现了一种“民主泛化”的论调,这种论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脱离具体实际,抽象地谈民主,把民主的作用绝对化,似乎民主可以解决中国在发展阶段中出现的一切问题;其二,推崇西方的民主形式,认为西方民主是纯粹的、彻底的民主,因而具有普世性。这种论调与第二国际时期考茨基等修正主义者的“超阶级的民主”、“全民的民主”,以及与戈尔巴乔夫时期所力主的“无条件的民主”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事实上,“民主泛化”的论调并不是一种新生事物。早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就曾出现过鼓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思潮。这种思潮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社会主义,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认同所谓超阶级的、抽象的民主理论,在政治上主张“多元化”、“多党制”等。近几年来,这种思潮在中国仍然有着一定的市场。正如邓小平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8](P211)只不过是,在当今条件下,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更为隐性化,即持“纯粹民主”、“普世民主”、“民主泛化”观点的论者,大多已经不是仇视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更多的要么是被西方的民主形式蒙蔽了双眼,盲目地跟从这股“洋风”,人云亦云、不明就里,要么是为了标新立异,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认为马克思主义应当包括对“普世民主”、“纯粹民主”的价值追求等。持这种论调者,虽然没有公然高举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但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为仇视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呐喊助威的作用。 在一球两制的背景下,必然会存在着两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只要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总会有西方仇视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不断宣扬其“民主”、“自由”的理念,也总会有被“西化了”的学者鼓吹西方民主的纯粹性与普世性来混淆视听。因此,我们学习列宁关于民主限度的思想,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在党内民主的问题上,要坚持党内民主与党的纪律的辩证统一。民主集中制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因此,不能机械地把民主与集中割裂开来,更不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简单地认为党的集中制纪律是对党内民主的侵犯。尤其是,在“言必称民主”的今天,切忌把“一般民主”、“纯粹民主”的概念在党内无限放大,走向极端。对此,列宁曾严明地指出,民主集中制“所表明的正是充分的普遍的批评自由,只要不因此而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的一致”。[6](P129)在这里,列宁强调了党内民主是有限度的,即党员民主权利的行使不能突破党的纪律和党的原则范围。 其次,列宁早就警告过,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纯粹的、超阶级的民主,有的只是具体的、阶级的民主。所谓“一般民主”、“纯粹民主”等,都是资产阶级“以便回避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2](P601)借以愚弄群众和推销自己的价值体系以及发展模式,从而促使社会主义社会发生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转变。同时,在民主的问题上,作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应该像列宁那样持着批判的态度,提出质疑:“这是对哪个阶级的民主?”[2](P593)而不能忽略民主的阶级属性,站在所谓“超然的”立场上,突破民主的限度,陷入“民主泛化”的理论误区。 最后,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民主的发展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不顾具体实际,急速地转向民主,势必会导致走上“民主泛化”的道路。戈尔巴乔夫时期极端民主化的改革就是如此,即从高度的集中急速地转到极端的民主上面,从而忽视了民主发展的渐进性和有序性。因此,在民主建设的问题上,不能操之过急,不能幻想一夜之间实现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样显然不符合列宁关于民主限度的思想。任何民主与权利的诉求,都必须贴合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因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9](P305)对此,邓小平也曾告诫道:“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8](P284)标签:列宁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理论界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时政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