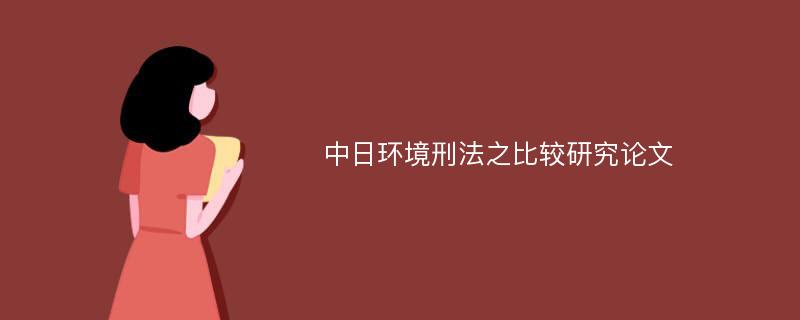
中日环境刑法之比较研究
郭 佳
(周口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1)
摘 要: 日本的环境刑法采取的是以单行刑法为主加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未来中国环境刑法在立法模式上应坚持以刑法典为主,为应对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未来也要尝试在环境行政法规定刑罚条款。中日两国基本上都在环境犯罪主体问题上采取双罚制,中国环境刑法未来应继续维持目前的自然人和单位双罚制;通过比较,中国未来应明确以人类中心主义的法益观作为环境刑法立法、司法的指导理念,以危险犯作为环境犯罪的基本行为方式。
关键词: 环境刑法;环境犯罪;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
全球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环境问题,这些环境问题反过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对人类的生命、健康,甚至人类的生存产生了威胁。根据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18年共起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42 195人,同比上升21%。单从这项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环境问题依然严峻。可以说,环境问题是世界各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换言之,同样的问题在其他国家存在,或者是曾经存在过。作为以保护法益为任务的刑法当然也成为各国不可或缺的环境问题治理手段,比较其他国家的环境刑法可以为我国提供一定的参考或对照。
我国刑法在环境保护中该发挥怎么样的功能呢?1997年刑法专门增设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来应对环境问题,至今经过十个刑法修正案,目前我国刑法分则涉及环境犯罪的规定,在第6章第6节共9个条文15个罪名。一般认为,该节第388条、第399条规定的污染环境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3个罪名属于污染环境型犯罪,其余12个罪名则属于破坏自然资源型犯罪。
与此相对,日本则是以《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为主,加上附属在行政法中的刑罚规定所组成的环境刑法体系。不过,刑法典中的一些犯罪也被认为是环境刑法(如以环境为媒介时的业务过失致死伤罪)。本文拟就中国与日本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保护法益、犯罪主体、犯罪行为方式等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在比较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刑法。
一、中日环境刑法之立法模式比较
所谓的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指的是规范环境犯罪的相关法律所采取的立法形式。各国根据自己国家的法律文化、法律体系、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采取不同的立法模式。有学者认为,各国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主要有综合式、法典式和行政刑法式。第一种以日本为代表,即在刑法典和有关保护环境与自然资源的行政性法律中均有惩治环境犯罪的立法规定,而且还以特别法的形式专门制定了惩治环境犯罪的特别刑事立法;第二种以德国、俄罗斯和中国为代表,即在刑法典中系统地规定环境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一般是采用专章或者专节集中规定的形式;第三种以英美法系国家为代表,即在有关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的单行行政性法律中直接规定环境犯罪的刑事条款,并且有相应的具体刑事责任的规定, 对有关环境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直接依照相应的行政法律定罪判刑即可[1]。从世界各国的现行的立法体系和实践来看,这三种立法模式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行政刑法的分类在概念使用上容易混淆。因为,行政刑法所规定的是行政犯,而与之相对的则是自然犯。但是,在行政法中有很多犯罪到目前已经很难说是行政犯了,如污染环境犯罪。因此,本文认为,环境立法模式应分为:(1)法典式。在刑法典中规定环境犯罪,代表性的是我国刑法。(2)综合式。不仅规定了单行环境刑法,也在其他行政法中规定刑罚条款,甚至刑法典中某些条款也被认为是环境刑法,如日本。(3)附属刑法式。该类主要在行政法中规定刑罚条款。
如前所述,日本采取的是综合式的环境刑法立法模式。该国最引人注目的是制定了单行的环境刑法,即《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该法属于刑法典之外的直接规定犯罪和刑罚的单行刑法或者特别刑法,制定于1970年,至今仍然有效。该法全部仅有7条。第1条规定了立法目的,规定该法的目的是防止与人类健康相关的公害;第2条规定了故意犯,即在事业活动中排放有害物质,对公众的生命或者身体产生危险的行为为处罚对象;第3条规定了过失犯,即怠慢业务上必要的注意,在事业活动中排放有害物质,对公众的生命或者身体产生危险的行为为处罚对象;第4条设置两罚规定,即同时处罚实施前两条行为的自然人与法人;第5条规定了因果关系推定制度;第6条和第7条规定的是时效和诉讼制度。此外,日本还在大量的行政法中规定了刑罚条款。环境污染型行政法如《大气污染防止法》《水质污浊防止法》《噪音规制法》等。生态保护型行政法如《自然环境保全法》《关于鸟兽保护及管理与狩猎合法化的法律》《温泉法》等。
与日本不同的是,我国1997年刑法专节规定了环境犯罪,分别为污染环境型犯罪与破坏自然资源型犯罪。前者如污染环境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等,后者如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等,中国至今还维持着这样的模式。在这一点上与德国较为类似。
从以上论述看,中国与日本的环境刑法在立法上存在共同点,两者既有以人类中心为标准的环境犯罪,也有不以人类为中心标准的环境犯罪。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中国与日本的环境刑法在保护法益的问题上,都有体现人类中心主义的条款和体现生态中心主义的刑法规范。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两国都采取的是生态、人类中心法益观呢?在本文看来,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本文认为,应当从实质的角度来理解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不能仅仅根据法条上或者说构成要件上是否联系到以人类为判断标准。本文的基本立场是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至少就中国而言,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都应当是人类中心主义,从这个立场解释环境刑法也更为合理。例如,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表面上看起来保护的是动物,但是该法条保护的是特定的野生动物,并非全部的野生动物。那么,这里的特定的野生动物是如何选择的呢?很显然这里所保护的都是一些可能灭绝的野生动物,而这些动物的灭绝对人类可能带来危害。这表现的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污染环境型犯罪同样如此。例如,污染环境罪要求“严重污染环境”,换言之,一般的污染环境行为并不受该条款规制。此外,司法解释规定该罪的入罪行为方式之一的“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可以看出只在饮用水水源排放特定的物质才符合本规定,这里显然也是以人类中心为标准的。事实上,从法律实际运行的角度也可以证明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应当是人类中心主义。因为,要打击环境犯罪,保护法益仅仅颁布法律是不够的,“徒法不足以自行”,还需要各种机关的相互配合,也意味着需要庞大的财政资源支撑。在现代国家中虽然经济发展迅速,但是财政资源还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这些资源只能用在与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领域。换言之,在使用财政时不能离开国民的利益考虑。所以,环境刑法立法阶段,从财政资源的角度也必须要以人类为中心作为基准。
二、中日环境刑法之保护法益比较
与此相对,中国刑法专节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如前所述,可以分为污染型环境犯罪和破坏自然资源型环境犯罪。那么,中国的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到底体现的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呢?对此学者们的看法也不一样。有学者认为,中国环境刑法保护的法益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指出“我国现行刑法基本采取的是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之立场,尤其是此后饱受诟病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可谓这一标准的集中体现”[8]。也有学者认为体现了“生态中心主义”[9]。仅从法条规定和司法解释来看,两种观点可能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如污染环境罪,在之前是以损害人身财产为成立条件的,《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其中的人身财产损害的要件,只要求严重污染环境,表面上似乎法益保护观发现了变化。但是,2017年实施的司法解释将其细化为17种行为方式(另加1项兜底条款)。其中很多项都以是否造成人身或者财产损害为标准的,可以说,体现的就是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另一方面,破坏自然资源型环境犯罪,从法律条文和司法实践来看,更接近于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论的主张。例如,刑法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在构成要件上很难看出其与人类的联系,实践中判断是否成立这些犯罪不需要联系到具体的人,其保护的就是动物本身。
与此相对,中国刑法基本上肯定单位(法人)作为犯罪主体,在总则第31条中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刑法分则规定了大量的单位犯罪处罚条款,有的犯罪主体甚至只能是单位,例如第387条规定的单位受贿罪。在环境刑法方面,根据刑法第346条规定,刑法典第6章第6节所规定的环境犯罪全部采取两罚规定,既处罚单位也处罚自然人。也就意味着中国所有的环境刑法之犯罪主体都可以是单位。究其原因,不外乎在环境犯罪中,特别是污染型环境犯罪,通常是在企业的生产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规定单位的刑事责任可以更好地发挥刑法效果。
一方面,从前述日本《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来看,第1条规定的立法目的是防止与人类健康相关的公害,第2条和第3条规定的犯罪都是与人类的生命或者身体健康相关的,似乎属于人类中心法益论立场。另一方面,日本还在大量行政法中规定了刑罚条款,这些条款不全是与人类直接相关的又接近生态中心法益论。
一般认为,刑法的目的或者说任务是保护法益。法益,简单来说,就是立法者通过规范特定的行为以保护特定的利益。在解释或者说理解刑法规范时都不离开法益概念,环境刑法作为规范环境犯罪行为的法律自然也不例外。“关于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存在如下两种对立观点:一是在人的利益(含子孙后代在内的人的生命、身体安全等)中探求保护法益的见解(人类中心主义);一是从环境自身(含生态系统在内的环境本身)更为广泛地把握保护法益的见解(生态中心主义)。”[3]一般来说,第一种观点主张环境刑法存在的理由就在于保护人们的生命、身体机能等。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或者说基础,对环境的危害只有达到实际侵害或者对人类生命、身体、财产或公共安全有危险的相关的程度时,才会作为犯罪处理。第二种观点认为,处罚环境犯罪的目的,主要在于使人们对环境保护的伦理感有所觉醒并加以维持,因此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是生态系统本身。不过,也有国家的环境刑法既有人类中心主义同时又有体现生态中心主义的条款,有的学者认为德国就是这类国家。“在这种既要生存又要发展的两难选择中,德国环境刑法目前采取了结合‘人类环境’和‘生态环境’两方面利益作为自己保护的法益的立场。”[4]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是法秩序都是为了调整个人相互之间的利益和公共利益。因此,不管是怎么样的法规范其本质在于与人类的关系。环境也不例外,其只有作为人类现在以及未来的生活基础才是重要的”[5]。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环境刑法“一是为了保护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存在;二是为了保护环境大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总起来说,就是保护环境大生态,因而这种意义上的环境刑法就是生态本位的环境刑法,这相对于传统环境刑法的人类本位(社会本位与国家本位的统一)而言,这种革新实际上是要求环境刑法回归其应然的生态本位”[6]。
根据是否以结果为标准犯罪分为结果犯与危险犯,危险犯又可分为具体的危险犯和抽象的危险犯。在环境刑法中,环境犯罪到底属于危险犯还是结果犯,除上述标准外,对法益概念的理解不同也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破坏自然资源型环境犯罪中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在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的立场,其保护的法益就是特定动物本身,因此属于结果犯;相反,如果采取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该罪属于破坏生态平衡间接损害人类的利益,则属于抽象的危险犯。在污染型环境犯罪中由于对法益概念理解的不同,对环境犯罪属于危险犯还是结果犯的认定也有一定的影响。
未来中国的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该如何发展呢?是坚持目前的体系还是借鉴他国有益经验?具体来说,日本可以为我国提供哪些借鉴呢?在本文看来,首先,不能完全照搬日本的单行刑法的立法模式,该立法虽然简便,但是,有的日本学者就指出,上述单行刑法在实践中,“国民所期待的对公害犯罪积极的处罚机能被限定的话,当初所预想的效果几乎没有发挥”[2]。换言之,该法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很难发挥刑法的报应和预防犯罪的功能。此外,单行刑法目前也不符合我国刑事立法习惯。即便如此,日本单行刑法中规定的因果关系的推定制度却是值得我国借鉴的,因为这种制度减少了实践中认定的难题。其次,单纯的附属刑法模式具有操作性强的优点,但鉴于我国已经在刑法典中专门规定了环境犯罪,不宜另行规定,而且目前对于附属刑法的研究还相对薄弱,单纯的附属刑法模式似乎也不应是中国环境刑法的发展方向。这样看来坚持目前的刑法典模式是中国环境刑法立法模式最好的选择。但是,在社会进一步发展,制定附属刑法条件成熟时,以刑法典为中心,在环境行政法中也规定刑罚条款,可以同时兼顾附属刑法的优点。
干预前,两组患者对上消化道出血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知识的掌握分值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犯罪主体,是指实施刑法所规定构成要件行为的主体。不管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大陆法系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之下,还是中国通说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之下,犯罪主体都是不可或缺的。换言之,任何一个犯罪的成立都少不了犯罪主体的要素。一般来说,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国外称为法人),在环境犯罪中,自然人作为犯罪主体似乎在世界各国都没有争议。但是,法人是否可以作为环境犯罪的主体,中国与日本存在不同之处。中国刑法明确规定单位可以作为环境犯罪的主体,理论上对此争议不大。日本也在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规定了法人的两罚制,但是刑法典中没有规定法人犯罪主体。
三、中日环境刑法之犯罪主体比较
本文是从森林资源资产价值核算的角度提出的旅游生态补偿机制方案。其方法对近熟、成熟、过熟林木资源价值评估比较适用。但由于生态补偿的对象、范围、类别的差异,在核算时应综合运用多种方法确定旅游生态补偿的标准,以满足各类利益诉求在不同影响因素条件下生态补偿的需要。
日本在刑法典没有规定法人作为犯罪主体,因此被一些学者归类为环境刑法的以环境为媒介的业务过失致死罪只处罚自然人而不能处罚法人。但是,在作为单行环境刑法的《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中规定了法人的两罚规定。该法第4条规定:“法人的代表人或法人、其他人的代理人、使用人及其他从业人员犯第2、3条之罪是与法人或者其他人之业务相关的,除处罚行为人之外,对法人或其他人科处各条所规定之罚金。”还有一些其他环境行政法规定了两罚规则。污染型环境犯罪,如《大气污染防止法》第36条、《水质污浊防止法》第34条、《噪音规制法》第32条分别规定了法人两罚规则;破坏自然资源型环境犯罪,如《自然环境保全法》第57条、《关于鸟兽保护及管理与狩猎合法化的法律》第88条也规定了法人两罚规则。从这些条款可以看出,日本虽然在刑法典中排斥法人犯罪主体,但是在环境刑法中却未采取积极的态度。
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三峡旅游空间游客流动的网络结构特征进行研究,考虑到三峡沿岸景点非常多,且传统三峡游线固定,部分景点为必经景点,游客具有自主选择权利,为拓宽研究的范围,深入广大三峡腹地景区,本文选择以3A及以上景区为节点,以三峡游轮旅游方式为例,游客上岸进入景区即被视为实际流动发生。节点结构特征主要通过程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结构洞指标来反映;整体网络特征以网络规模、密度以及凝聚子群进行分析[9]。
如前所述,日本采取的是综合式的环境刑法立法模式,既有单行环境刑法,也在环境行政法中规定刑罚条款。在日本,关于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学界看法不一,受到日本学者关注的并具有代表性的见解,大概有如下几种:(1)纯粹生态学的法益论。该说将生态学的环境本身(水、土壤、空气)和其他环境利益(动物、植物)作为保护法益。(2)纯粹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该说主张环境本身不是保护法益,被环境危险化所危害的人类的生命、身体、健康才是保护法益。还有主张间接保护说的观点。(3)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论。如前所述,该观点来源于德国通说,在日本也有学者持类似观点。(4)未来世代生命、人类共同财产法益论。该观点主张环境犯罪是对未来世代生命的抽象危险犯,同时也是对人类共同财产的犯罪。因此,环境刑法的法益是未来世代的生命和作为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环境财产之人类共同财产。(5)健康论。该说主张健康是环境刑法直接保护的法益。(6)宪法的价值原则论[7]。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中国刑法规定环境犯罪主体,在单位犯罪主体问题上比日本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日本刑法没有规定单位犯罪,仅仅在刑法典以外的法律规定单位犯罪。
四、中日环境刑法之犯罪行为方式比较
“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这是2016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的殷殷嘱托。江西全力打响脱贫攻坚战。2017年底,井冈山市、吉安县顺利脱贫摘帽,全省实现53万人脱贫、1000个贫困村退出、6个贫困县达到摘帽条件,贫困人口减至87.54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2.37%,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发生显著变化。江西2017年扶贫开发和易地扶贫搬迁两项工作双双获国务院通报表彰。
日本刑法规定的业务过失致死伤罪,如果是以环境为媒介实施的可以说是典型的结果犯。而《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第2条第1款、第3条第1款均使用了“对公众的生命、身体产生危险”,属于具体的危险犯;第2条第2款、第3条第2款规定的致死伤罪则属于结果犯。此外,对违反《大气污染防止法》第13条规定的一定排放标准的行为,该法第33条之二设置了直罚规定,不需要另外造成其他结果,属于典型的抽象危险犯。环境行政法还存在违反行政命令的刑罚条款。
与此相对,学界对中国环境刑法中最具代表性的污染环境罪之行为方式则存在争议。有的学者主张该条中既有结果犯也存在危险犯[10]。该观点主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对污染环境罪中的“严重污染环境”做出的解释,其中,“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的规定属于抽象危险犯,“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的规定则属于结果犯。但是,在本文看来,这种观点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同一个法条中的概念,既理解为危险犯又理解为结果犯是存在矛盾的。换言之,该罪要么是结果犯,要么是危险犯,不可能两者同时存在。司法解释中规定的类似“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的规定表面上看起来属于结果,但是,司法解释属于对法条的具体化,不能超越法条本身的语义,也就是说,该规定只不过是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属于“严重污染环境”。最终,该罪的成立标准还是“严重污染环境”,仍然属于危险犯。破坏自然资源型环境犯罪,根据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均属于危险犯。
根据南山终端中水系统试运行期间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对工艺系统进行了优化改造,改进转水方式、采用硝化与反硝化同步工艺,采取多项措施降低系统的耗电量及淡水消耗量,并优化系统的运行管理方式,中水回收率高,产水水质合格,解决了系统运行不稳定、氨氮含量偏高、回收率低、运行成本偏高等问题。措施可操作性较强,系统运行经济性强,实现了生活污水零排放,既是南山终端持续推进低碳、清洁生产的手段,也是油气田降本增效的一项重要措施。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日本环境刑法既有结果犯也有危险犯。而中国环境刑法则是以危险犯为主,司法解释有类似结果犯的规定(本文持否定态度)。基于环境犯罪的法益侵害的严重性和认定的困难性,未来我国环境刑法应在人类中心法益观的指导下,以危险犯作为环境刑法的核心内容。
五、结语
环境问题是中日两国都面临的问题。通过比较研究,未来中国环境刑法在立法模式上应坚持以刑法典为主,为应对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未来也要尝试在环境行政法中规定刑罚条款。应维持目前的自然人和单位双罚制,明确以人类中心主义的法益观作为环境刑法立法、司法的指导理念,以危险犯作为环境犯罪的基本行为方式。
备用调度监控中心应能在主监控中心的调度自动化系统处于事故或灾难,不能继续运行时,保证电力调度人员在备用调度监控中心能继续有效地监控本地区的电网运行,并能有效地与其他系统进行数据互通。维护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参考文献:
[1]王明远,赵明.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探讨[J].中国环境法治,2008(1):265-269.
[2]三枝有.環境刑法と原発規制[C]//信州大学法学論集.2014:1-25.
[3]今井猛嘉.环境犯罪[J].李立众,译.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2010(1):7-14.
[4]王世洲.德国环境刑法中污染概念的研究[J].比较法研究,2001(2):53-64.
[5]Hans Joachim Hirsch.新しい犯罪形態克服のための手段としての刑法[J].上田健二,川口浩一,译.同志社法学,47(2):246-270.
[6]张光君.环境刑法的生态本位论纲[J].时代法学,2008(1):77-82.
[7]中山研一など.環境刑法概説[M].东京:成文堂,2003:11-17.
[8]刘艳红.环境犯罪刑事治理早期化之反对[J].政治与法律,2015(7):2-13.
[9]汪维才.污染环境罪主客观要件问题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J].法学杂志,2011(8):71-74.
[10]苏永生.刑法解释的限度到底是什么:由一个司法解释引发的思考[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9-75.
Comparison of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GUO Jia
( School of Political and Law, Zhoukou Normal University, Zhoukou 466001, China)
Abstract: The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in Japan is single- line criminal law plus accessory criminal law.In the future, the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in China will also insist on criminal code, in order to settle the complex environmental problem, at the same time, China will attempt to provide penalty clause in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law.In a all, China and Japan generally adopt double pubnish system on the environmental criminal problem and China’ s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will always keep current double penalty system for natural persons and units in the future.By comparison, In the future, China should clearly take the anthropocentrism concept of legal interests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legislation and judica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and take the dangerous criminal active as the basic behavior of environmtal crime.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environmental crime; anthropocentrism; ecocentrism
收稿日期: 2019-05-16;修回日期: 2019-05-24
作者简介: 郭 佳(1993-),女,河南周口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刑法。
中图分类号: D924.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76(2019)04-0084-05
DOI :10.13450/j.cnki.jzknu.2019.04.18
【责任编辑:孙廷然】
标签:环境刑法论文; 环境犯罪论文; 人类中心主义论文; 生态中心主义论文; 周口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