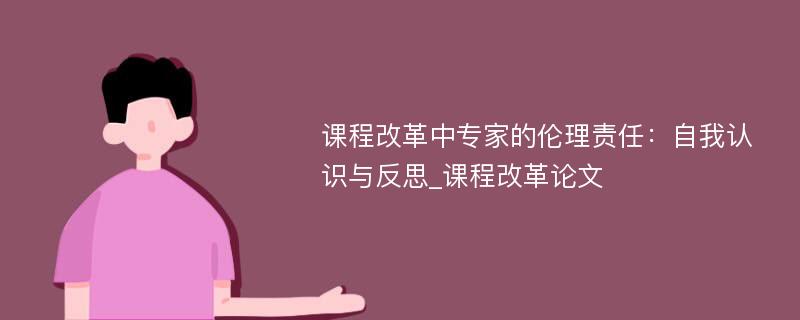
课程改革中的专家伦理职责:自识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课程改革论文,伦理论文,职责论文,专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培根曾经说过,即使有很多人喝彩,改革仍然是很危难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关涉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成长和发展,需要热情和激情,更需要智慧和理性。因此,社会公众的深刻理解和广泛支持不可或缺,课程专家的作用更不容忽视。
也许正因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复杂和艰难,人们对课程专家的期望就更高,课程专家的影响就容易凸显出来。事实上,多种的社会牵制力量和多元的教师评价标准,已经使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身处其中的教师陷入一种不确定状态,正是这种不确定状态为课程专家提供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舞台,从而使课程专家承担了课程改革引领者的角色。一位课程专家倘若真切地感受时代的脉搏,看到时代的问题,就会产生一种切肤之痛,内心有种责任感驱使他去作艰苦的探索,积极的思考。他的努力如果对课程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就会感到精神上有所寄寓,情感上得到升华,于是就体验到人生真正的乐趣,真正的价值。应该说,课程改革的专家引领是时代使然,而对课程专家自身来说,同时也是一种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但是,经过这些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践,我们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任何明智和聪颖的课程专家都不可能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身处其中的教师从现实困境和决断的不确定性中一劳永逸地解脱出来。因此,课程专家必须具有探明自我不完美和局限的勇气,消除黑格尔式的乐观和自负,克服“启蒙者”居高临下的心态。
课程改革需要坚实的课程研究为基础,可是我们在很多课程的根本问题上,目前甚至还没有得到哪怕是稍微可靠一点的结论,甚至连“课程的改进能够提高教育质量”这个很为人们接受的命题,至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科学地加以证明。如此,对课程及其改革的理性的种种鄙视便有了一个可以言明的理由。自知者,智也。人必须认识自己,如果这不能有助于发现真理,至少这将有助于规范自己的生活,还有别的比这更为正确的吗?每一个课程专家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也许不是因为你拥有的那点狭窄的有待确证的知识而是因为并不一定合理的社会分工和你隶属的群体才赢得了人们的些许尊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课程专家更需要谨慎从事,不能为自己的随意而行而开脱自己应负有的社会职责。即使是写作,也不能仅仅视为纯粹文本和思想的任意表达,而应该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批判、自我改造的个人伦理行为。我们知道,单纯的以言表意难以产生行为约束或行为规范,以言行事才能约己束人,以言取效才能真正影响社会公众并产生非正式的约束或相应的制度。记得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表达了对纯粹的哲学写作的讨厌和过一种哲学的生活的希望,他是这样反思自己的:我的论文进行得不错,它们不可能变得更好了,但它们产生了什么效果?我能帮助别人吗?如果不能,这比我是个为他们表演的著名悲剧演员高明不到哪里去,他们学习的东西不值得学习,而且我制造的个人印象并未给他们带来什么。我认为,维氏的表达很值得我们课程专家思忖和玩味。课程专家必须把批判的注意力与创造的想像力不仅指向他自己的观念,也要指向他自己的具体行为和生活经验,每时每刻,一跬一步,必须将其所思所言与其所做进行比较,真正做到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否则,课程专家就失去了自教的品格和能力,如果不能自教、无力自教,其创造知识的路子就会浅而窄,其中必真伪难辨,善恶不分,美丑不明,又何以充当课程改革的引领者?教人须先自教,育人须先育己,正己以育人,永远都应该是知识分子的必备品格和应有风范。今天,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这些年来我们的许多所谓的课程专家常常自弊而欺人,“不会玩牌倒是很能洗牌”,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可以找到他们忙碌的踪影,成了一无所能却能明辨是非的人,直接影响了课程专家的声誉,亵渎了课程及其改革的基本理性。
伴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具有不同学科背景和学术个性的专家卷入到课程的研究中来,课程专家的队伍因而不断壮大。这些专家的参与,使课程理论的建设突破了教育界的狭小圈子,为跨学科的合作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带来了难以沟通而导致的混乱。大家都知道,专家本身的角色就是个矛盾,因为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知识只会作为个人的知识而存在,所谓整个社会的知识,常常只是一种比喻而已。所有个人的知识的确存在,但却是以分散的、不完全的、有时甚至是彼此冲突的信念的形式散存于个人之间的,因此如何能够做到人人都从此知识中获益,便成为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大问题。既然如此,为了课程改革的顺利进行这一共同目标,每一位课程专家都应该在基于个人知识的前提下有超越个人知识的胸怀,探明自己的局限以便掌握课程研究所需要的维度和方向。我们不能不承认,一旦超出了专业化的小圈子,专家的思想也很一般,而且常常还是最空泛、最没有内容的符号运算。面对复杂的课程改革,我们需要的不是一般的课程知识,而是具有概括意义的课程思想。只有具有概括意义的课程思想才能启迪我们建立认识现实课程的战略和艺术。也就是说,具有概括意义的课程思想才可以昭示我们一种方法,在出现不能确定的课程问题和矛盾时,这种方法能与复杂的课程现实联系起来,而不是无视乃至否认课程现实,停滞不前。遗憾的是,我们尚缺乏真正可以称为课程专家的专家,我们更缺乏探明自我不完美和局限的勇气,以至课程专家之间志趣相左,价值取向歧异,甚至相互攻讦,似乎五位拍卖师的叫卖声比莫扎特的一曲五重奏还动听,不能说不影响着课程改革引领的有效性。
即使课程专家克服“各持己见”的局面,形成了真正的“专业共同体”,但还必须时刻警惕杜威所说的由专家的“特权”所制造出来的“认识的扭曲”——专家阶层容易脱离共同兴趣,以便成为一个拥有私人兴趣和私人知识的阶层,而这在社会事务方面根本不是知识,因为它无法了解社会其他部分的经验和兴趣,而且所有的特权都会使那些拥有它的人的视野变窄。其实,这并不是否定而恰恰是因为专家所有的专业知识。如果我们承认课程改革的复杂性、创造性和社会性,那么我们就应该自觉地认识到,课程改革决然不是某些课程专家所拥有的一些课程知识的简单应用过程。布鲁纳曾颇有感慨地指出,不顾教育过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来论述教育理论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是自甘浅薄,势必在社会上和教室里受到蔑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依靠自己个人以往的经验树立起一种世界观,知识从一开始便是群体生活的合作过程,个人的知识是群体的共同命运、共同活动以及克服共同困难的产物。实际上,只有当课程知识不再是一种单纯解决课程专家的问题的手段,而成为由课程专家培养出来的、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时,课程知识才能够真正发挥其功能,体现其价值。我们处在一个平等的时代,课程专家既然是课程改革的引领者,也就是民主社会当然的推动者。那种将课程知识从广大的现实课程实践领域孤立出来使之成为少数课程专家似乎无利害游戏的做法,实际上已经隐含了巩固课程专家特权和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的利害考虑。所以,课程专家共同体不应退却到自鸣得意的、经院式的专业主义,而应抱有知识社会学的宏阔视野,掌握知识社会学的分析和批判方法,放弃将自己视为天经地义的傲慢态度,直面具有不同社会背景团体或个人的攻击,扩大具有不同观点的人的接触范围,寻求并形成对话的基础,共同解决课程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只有通过参与共同的智慧,分享共同的目的,为共同的利益而努力,课程专家才能不断扩展、丰富和完善自身,既引领课程改革,又与课程改革一起成长。
苏格拉底在谈及哲学家的使命时,曾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自述:国家就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可是由于太大,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蟒叮叮它,使它的精神焕发起来,我就是神赐给这个国家的牛蟒,随时随地紧跟着你们,鼓励你们,说服你们,责备你们。今天,为了保证课程改革的顺利进行,捍卫课程改革的基本理性,课程专家还必须有苏格拉底所说的牛蟒精神。我认为,正是这种精神表征着课程专家的一种反省批判的姿态与目光,也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使课程专家自身及其引领的课程改革抵制种种蓄意的歪曲和任意的背离,免于在非理性因素干扰之中沉沦,并能不断超越,创造更高远的境界。如果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那么课程专家就不仅仅是课程知识的生产者、课程改革的引领者和推动者,更应是课程改革的良知。守望良知,这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课程专家的天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