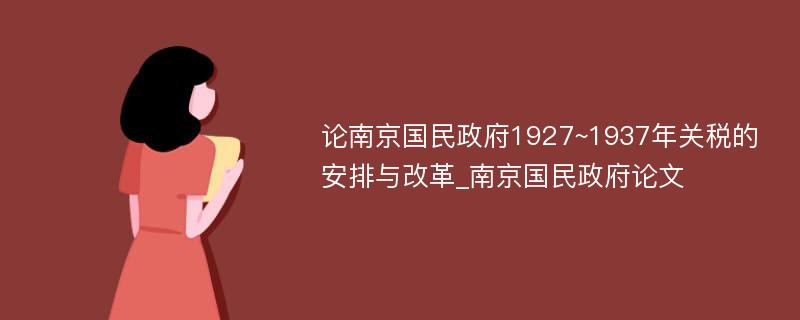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关税的整理与改革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南京论文,关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巩固国家政权,南京国民政府在建立之初即进行财政的管理与改革。在近10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以关税、盐税和统税三税为核心的税收体系,而关税收入又于三税收入中高居首位。本文拟就南京国民政府整理改革关税的经过、意义以及关税的性质进行探讨,以请教于方家。
一、南京国民政府关税自主的经过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将中国关税税率协定为值百抽五,子口税税率为值百抽二点五。协定关税率和海关自主权的丧失,有利于列强掠夺中国的工业原料和向中国倾销商品,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民族市场,摧残了中国的民族经济,同时也大大削弱了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摆脱协定关税的束缚,增加财政收入,巩固其统治,于1927年7月20 日发表了“关税自主”的布告(注:《关税自主之经过》,第7—8页,载江恒源《中国关税史料》,中华书局1931年2 月版。),宣告于9月1日裁撤厘金,实现关税自主,并组织国定税则委员会,以示决心。1928年7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修约宣言》,宣称:“(一)中华民国与各国间条约已届期满,当然废除,另订新约;(二)其尚未满期者,国民政府即以相当之手续解除而重订立;(三)其条约已期满而新约尚未订立者,应由国民政府另订适当临时办法,处理一切。”(注: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2辑,台北1977年9月版,第294~295页。)同年7月,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照会各列强驻华公使,要求进行废止旧约、重订新约的外交谈判,但遭到驻华外交使团的阻挠。对此,南京国民政府指出,“此次国府对废约态度极为坚决,非达到不可”,“若各国对此不了解,乃以种种方法阻挠,则国府为达其目的计,已另有办法”。(注:《申报》,1928年 7月19日。)此后,又针对个别国家,表示“虽致绝交亦所不惜”。(注:《申报》,1928年7月27日。)接着, 南京国民政府寻求同列强的个别谈判,想方设法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美国出于种种考虑,率先同意与中国订立新约。1928年7月25日, 《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在北平签订。该约规定,以往对于剥夺中国关税自主的一切条款都应立即作废,而应适用国家关税完全自主的原则。中美新约对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鼓舞,而对其他列强却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注:《东方杂志》第25卷第16号,第5页。)。不久,南京国民政府相继同德国、挪威、比利时、 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瑞典、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签订了关税新约。这些条约有两个共同特点:其一,都承认中国应适用“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其二,均要求保持“应与其他国享受之待遇无区别”的最惠国待遇(注:参见江恒源《中国关税史料》所载《关税自主之经过》。)。根据最惠国待遇,如果有一国不承认关税自主,则其他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国家也可不承认,因此,直到1930年5月6日《中日关税协定》签订后,南京国民政府谋求关税自主权的努力才算真正有了收获。但由于《中日关税协定》的附件中有三年内不能增加某些既定税率的规定,所以,1931年的国定税则还是不能完全自主。直到1933年《中日关税协定》三年期满后,南京国民政府又公布了1933年的国定税则,至此才真正取得了关税自主权。
关税自主是整理与改革关税的前提,南京国民政府谋求关税自主权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可能性。
首先,严重的财政困难是南京国民政府争取关税自主权、进行关税整理与改革的直接动因。关税作为近代中国财政的最主要来源而为列强所控制,南京国民政府“为巩固它的政治军事地位,不得不付出重大代价,因此迫切需用巨款。关税收入在偿还外债之后剩下的余款,自然是政府所急于得到的”(注:[美]扬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如果能够掌握自主关税,那当然更是其意中的想法。
其次,南京国民政府争取关税自主权,既是当时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又是其阶级意志的体现。辛亥革命以后,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近代国货运动兴起并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到20年代这一运动已具有了全国性规模,关税自主的呼声随之日益高涨。北洋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和自身财政危机的背景里,曾多次对外交涉,要求修改关税税则,争取关税自主。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一切不平等条约……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902页。 )武汉国民政府针对当时的北京关税会议指出:“说到关税问题,只有完全无条件的关税自主才能应付中国政治的经济的需要,同时列强……也应当顺应中国国民普遍的一致要求,把关税自主权完全交还。”(注:《关税自主之经过》,第7—8页,载江恒源《中国关税史料》,中华书局1931年2月版。)1927年2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人民支持下,无条件地收回了汉口、九江两地英租界。这大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这种形势下,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废约和收回关税自主权是顺理成章的。而对于帝国主义列强而言,为维护其在华根本利益,在适当时机作出一定让步也是可能的。
第三,国内政治局势的相对稳定是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关税自主权的一个重要砝码。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北伐, 打败北洋军阀,同年12月东北易帜,全国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也就是在这一年里,关税自主问题有了重大转机。
二、南京国民政府“国定税则”的制订
中国关税税则自南京条约以后,一直是协定税则,实质上是列强强加给中国的片面税则,中国政府不能自由修订。据协定关税,中国关税实行的是单一税制,规定了值百抽五的固定税率。其后虽经过几次修订,但都没有超过这一固定税率。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的变迁,关税税率实际上已经达不到这一定率的标准了。南京国民政府为谋求自主关税,于1928年“设立国定税则委员会,专司其事,将历年施行之进出口税则,统筹修订”(注: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3辑,台北1977年9月版, 第188页。)。
首先,国定进口税则有四个,其税率都由均一税率改为差等税率。
第一,1929年国定进口税则。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12月7 日公布了第一次修订的国定进口税则。该税则将进口货物分为14类, 718目,其税率有七级,从7.5%到27.5%不等,平均税率为8.5%,并规定凡税则中所没有载明的货物都按12.5%的税率征收进口税。税则于1929 年2月1日施行,期限为一年。该税则税率是将5%的正税税率与北京关税会议上英美日专门委员会所提出的七级附加税率以及对卷烟煤油所增加的2.5%附税税率综合而成的。1929年国定进口税则的施行, 因为尚未得到日本对中国关税自主的支持,所以在规定实施期满后并没有订出新的税则,其有效期延续了近二年。我国进口税则向以关平银为计税单位,自1929年下半年世界金价暴涨,银价跌落,而中国支付的外债本息则是按金价计算的,这样南京国民政府在偿讨外债、将关平银兑换成海关金单位的过程中即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有鉴于此,南京国民政府“爰议决海关进口税改用金本位征收……自民国19年2月1日实行”(注: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3辑,台北1977年9月版,第1—2页。)。 进口税改用金单位征收保证了关税收入的稳定和实质性增收。
第二,1931年国定进口税则。1930年5月6日,中日关税协定正式缔结,至此中国关税自主的要求才得到所有缔约国的同意。于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定税则委员会重新拟订出新的进口税则,并于1930年12月29日公布,次年1月1日施行。该税则把进口货物分为16类,647目, 税率分为12级,从最低5%到最高50%不等,平均税率为15%, 从价税与从量税并用。综计全部税则货物,与按金价征收的1929年税则相比较,税率增高者有451项,税率减低者有150项,税率未变动者有232项。 该税则受1930年5月中日关税协定的约束,片面优惠于日本。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不仅占据了东北的关税,而且还在华北一带大肆走私,该税则被搅得面目全非。南京国民政府于“1932—1933年期间,进而大量增加了进口税”(注:[美]扬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用来弥补失去的东北关税收入。
第三,1933年国定进口税则。1933年5月6日是中日关税协定附件中对日本的主要货物三年内不得加税的限期届满之日,1931年国定进口税则中许多片面税率需要更订;日本把东北变为其殖民地,攫取了东北海关,中国关税收入骤减。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应急,临时变更了许多税率。1931年国定进口税则实际已名存实亡。1933年5月22 日实施新的进口税则。该税则税率分为14级,从5%到80%不等,平均税率为20%; 进口货物共分为16类,672目,综计全部税则货物,较之于1931 年国定进口税则,增高税率者有385项,减低税率者有92项,照旧不变者有433项。同年12月16日,对输入的洋米征收进口税。很多项目的税率都大为提高,明显的是棉货、海产品和纸张,这些都是曾对日本实行特惠税率的货物。1933年税则的加税情况引起了日本的反对,“日本政府曾于5 月31日对中国采取新关税税率,令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向中国国民政府提出抗议,……日本外务省方面再事抗议”(注:《大公报》,1933年6月7日。)。随着在华北的扩大侵略,日本在中国沿海和内地进行大规模走私,日本商人也不肯照章纳税。这些都影响了1993年国定进口税则的实施。
第四,1934年国定进口税则。1934年7月实施新的国定进口税则, 该税则的分类及税目仍沿用1933年税则,但税率有一些变动。综计全部税则货物的税率,较之于1933年税则,增高者有388项,减低者有66 项,照旧不变者有470项,平均税率为25%。 该税则把日本所关心的进口税项目,主要是棉货、海产品和纸张的税率都降低了。
其次,国定出口税则有两个。
第一,1931年国定出口税则。于1931年6月1日开始实行。该税则税目共分270种,税率规定从量税5%,至于若干品项,则体察贸易情形,不便增加税率者,仍依当时征收正税的原额(约为 3%)规定其税率;从价税部分订为7.5%。并规定对茶、绸缎、漆器等30 项货物免征出口税。在该税则的实施过程中,又陆续免征了对丝及丝织品、米谷、小麦、杂粮等货物的出口税。并明确规定,海关仅对出国货物征收出口税,而对运往国内另一通商口岸的货物不再征收出口税。
第二,1934年国定出口税则。于1934年6月实行的这个出口税则, 较之于1931年税则,其税目和税率并没有变动,但对减免税的货物项目却增多了。减免税所遵循的原则如下:“在财政许可范围以内,对于原料品及食品在国外市场推销最感困难者,酌量减税免税;在财政许可范围以内,对于工艺制品宜予奖励输出者,酌量免税。”(注:贾德怀:《民国财政简史》(上),商务印书馆出版,第81页。)本此原则,税率减低者有蛋品、豆类、花生、花生油、烟叶等35项,新增免税品有糖、酒、小麦粉、杂粮粉等44项。
另外,南京国民政府还实现了海陆边境进出口税则的划一,鸦片战争以后,俄国通过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陆路边境关税的特惠税率。接着,英、法、日等国也相继与中国政府订立通商条约,获得陆路关税的减免特权。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顾维钧建议“现在适用于陆路输入或输出各货物之减收关税制度应即废除”,(注:[英]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三联书店1958年8月版,第434页。)但因为列强的阻挠而搁浅。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关注这个问题,在中英、中法关税条约的附件中都有划一海陆边境进出口税则的规定。1929年1月19日, 南京国民政府因为新税则实行在即,下令取消中东路及越缅边境减税办法,并按照进口税则征收进口税。其后,中国与俄及英法所属殖民地半殖民国家的边境,都如期取消减税办法。1930年中日关税协定最终规定了陆路与沿海关税平等待遇。至此,华盛顿会议关于划一海陆各边界征收关税的原则,才得以实现。(注:贾德怀:《民国财政简史》(上),商务印书馆出版,第81—82页。)
三、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前10年关税整改的简要评析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1937年对关税的整理与改革,与争取关税自主权的活动相结合,这一过程本身即具有积极意义。而整理与改革所带来的直接结果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整理与改革增加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据有关材料表明,整理与改革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收入基本上是逐年增加的,在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关税的大幅度增收,不仅较大程度地满足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迫切的财政需要,而且促进了南京国民政府整理改革税收制度的步伐。例如,关税收入的增加使南京国民政府能够将善后借款本息改由关税担保,不再用盐税收入偿付,于是盐税行政权完全收回,“设立了盐务署,统辖全国盐政,主持税收”(注:吴兆莘:《中国税制史》(下),上海书店1984 年版, 第278 页。),着手整理混乱的盐税体系。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政策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的,因此其关税主要属于财政性关税。
其次,整理与改革削弱了列强对中国关税的控制,体现出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保护与鼓励,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南京条约以后,我国关税即逐渐为列强所控制,从关税的行政到税款的征收保存,无不体现出列强的干预与操纵。列强通过对中国关税关政日益全面的控制,左右中国政局,干涉中国革命,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南京国民政府经过关税自主活动,制订国定关税税则,将海关税务司纳入财政部的管辖范围内,并且“自1932年3月1日起,关税税款全部集中存在中央银行”(注:[美]扬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从此,关税关政80年为列强控制的局面基本结束,其殖民地程度有了明显的降低(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不在此列)。南京国民政府整理与改革关税,争取关税收入的同时,也有发展国内产业的意图。1933年2月,对向来免税的进口米谷小麦、 杂粮征征进口税,同时提高麦粉进口税。“中国政府实难同意法国政府关于完全取消大米进口税的要求,因为中国农民的处境很不好,他们大多依靠稻谷为生,因此中国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来保护他们的利益,或者倒不如说是减轻他们的负担。”(注:《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 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5页。)结果,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最后几年内小麦、稻谷和棉花的进口数额减少,”(注:[美]扬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2页。)同时, 中国农业产品总值也有所提高,以1933年价格为基数,以国币10亿元为单位,1931年为18.79,1932年为19.66,1933年为19.34,1934年为17.11,1935年为18.79,1936年19.89,平均每年增长1.5%(注:[美] 扬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1页。)。1934 年国定进口税则规定:“为补助财政及维持实业起见,对于若干进口货品,酌加税率。”(注:贾德怀:《民国财政简史》(上),商务印书馆出版,第77—78页。)这对外国商品的倾销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保护了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两个国定出口税则中关于减征或免征出口税的规定也含有保护贸易、奖励实业的意义。
由此可见南京国民政府对关税的整理与改革的过程与结果都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必须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特点也导致南京国民政府关税整改的局限性。南京国民政府为了顺利地进行关税的整理与改革,对帝国主义列强作了妥协退让。反映到国定税则的制订上,1929年国定进口税则的税率就没有超出北京关税会议上英美日七级税率规定的范围,1931年固定进口税则则受中日关税协定的制约。同时,沿袭旧例,南京国民政府海关的总税务司仍然由外国人担任,1929年还聘请了甘末尔设计委员会,协助其财政政策的制订和行政的管理。西方资本主义财政理论及其经验固然能为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改革提供帮助,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洋员们与其各自的政府相联系,所关心的仍是他们各自国家的利益。1933年国定进口税则就充分照顾到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对关税进行整理与改革的过程以及整理与改革后的关税并没有彻底改变其半殖民地的性质。
标签:南京国民政府论文; 关税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出口税论文; 进口税论文; 海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