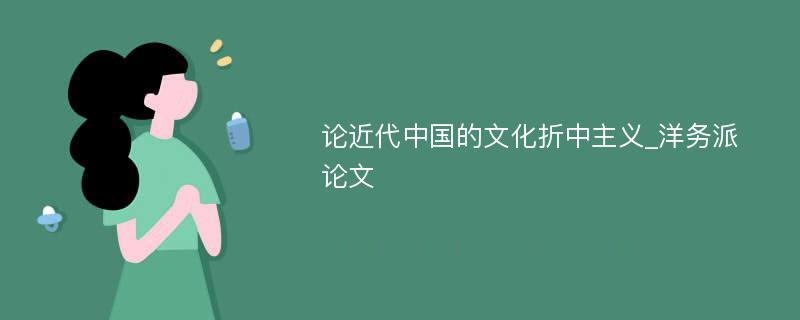
论近代中国的文化折衷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折衷主义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折衷主义在近代中国盛行一时,且影响深远。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中体西用”,可以说是19世纪后半期的一种重要文化思潮。“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从闭拒(文化传统主义)到融合汇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反映了西方文化在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嬗变轨迹。对这一思潮进行剖析,对理解中国文化在近代的演变以及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无疑具有学术理论和现实借鉴的双重意义。
一
在近代,明确使用“中体西用”概念者是戊戍时期的孙家鼐。他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说:“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人之舍己芸人,尽弃其易学西法。今中国京师并办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架中学,此是立学宗旨。”〔1〕然而, “中体西用”作为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一种反应模式,它所表达的文化折衷主义的内涵,它所代表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则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时期。
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失败,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进步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信奉的“天朝至尊至上”的观念发生了动摇。通过鸦片战争的切身体会,他们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所代表的军事技术的先进性,为此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分析这一时期向西方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军事技术与近代的工业技术。魏源明确界定的“夷之长技”有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2 〕同时,魏源还认为诸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火轮机、自来火、自转碓、千金秤之类“凡有益于民用者”都应当学习。虽然后期魏源曾对西方的议会政治有所介绍并流露出一定的赞赏之情,但这并不是魏源思想的主流,也不是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主流。而且,魏源没有也不可能对封建的政治制度提出任何疑议。所以说,鸦片战争时期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所表达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可以看作是“中体西用”的思想渊源,而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工业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正是这一时期“中体西用”的实际内涵。
19世纪60年代,“中体西用”论开始成为一种广泛流传的社会文化思潮,而比较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他在这本书中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了初步的比较。比较的结果,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学)有六个方面不如西方文化(西学)。即:“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3〕。 这种明确承认中国文化“不如夷”的思想,较之于林、魏要更全面和深刻一些。在中西对比的基础上,冯桂芬提出了“中体西用”的主张。他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岂不更善之善哉?”〔4 〕冯桂芬的议论,基本上界定了“中体西用”的特定内涵。
洋务运动实际上是“中体西用”的政治实践。伴随洋务运动的展开,“中体西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十分盛行。这一时期阐发“中体西用”思想的主要是洋务派官僚和初期的维新派人士。
“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官僚的洋务实践的纲领和规范。洋务派官僚大都是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起家,或者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与西方列强较多地打过交道的朝廷内外大臣。他们在这些活动中亲身体验了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工业技术的优越之处,所以他们感到固守“夷夏之辩”的古义是无助于改变中国极弱的局面的,因而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等“自强之术”。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中是得益于洋枪洋炮最多的,故他早就提出要“师夷智以造炮制船”〔5〕, 认为“欲求自强之道,莫如制器械”。李鸿章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师夷之长四字,尤为今日所当知也”〔6〕,所以必须“取外人之长技, 以成中国之长技”〔7〕。
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之长,他们所理解的“夷之长技”是什么呢?主要是西方的军事技术和近代工业、科技。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可以看作是林、魏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如果说林、魏在中西文化接触的最初阶段提出的具有“中体西用”涵义的思想,还有其时代的局限的话,那么,洋务派官僚的“中体西用”则是出于有意识的对西方文化抗拒。洋务派官僚在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就规范了它的内涵与外延。这就是:西方的文化只能用来维护封建的统治,西方的文化也只有军事技术、工业、科技等器物层面的东西可以学,至于制度教化,只有中国的优越。曾国藩说:“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者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8〕就是这个意思。 李鸿章就说得更明确了,他认为,“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狉獉之俗,所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9〕他还认为, 治国经邦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所谓“根本”、“全体”,便是中国的文物制度、伦常名教,至于西学,只论是“偏端”、末叶。所谓“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10〕。如果“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11〕
由此可见,洋务派官僚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内涵,乃是以西方的物质文明来挽救或弥补中国封建的文化基础——文物制度、纲常名教,尤其是以专制主义为特征的政治制度。从情理上来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封建统治支柱的洋务派官僚,当然是不能提出改变其根本制度的主张,虽然他们中的个别人也曾对西方政制发表过褒扬的评价,但并不代表其主流。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乃是当时文化折衷主义思潮的主要内涵。
二
进入七八十年代,“中体西用”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就是以早期维新思想家为代表的文化主张。早期维新思想家最初虽然也从属于洋务派群体,但他们是洋务自强运动的“言者”,而不是“行者”,故而所论较为放达,也少有拘束。他们也认为“中国教化最好,民物最殷”〔12〕,主张在学西方时,“不必尽改旧章,专行西法”〔13〕,而须“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14〕,也就是郑观应明确主张的:“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5〕。但是,早期维新派还是与洋务派官僚有分歧的,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体”(或“本”)与“用”(或“末”)的内涵与外延不同,较之于洋务派官僚更进了一步。
在洋务派官僚看来,能够学的“西学”只有军事、工业、科技,至于政治制度、文物教化是绝对不能学的。而早期的维新思想家主张学习的“西学”是相当广泛的,不但包括了西方的军事、工业、科技、教育等,更包括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君主立宪。郑观应对此有准确的解释,这就是他在《盛世危言自序》中引用张树声一的段话,他说:
“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至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16〕
郑观应主张,必须在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教育诸方面学习西方。他认为,“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脊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收,保商务,使物畅其流。”〔17〕这基本上反映了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西用”的看法。由此可见,早期缴新思想家对“西用”规范与外延已经较洋务派官僚大大扩张了。
那么,早期维新派所主张的“本”、“道”、“体”是什么呢?这就是孔孟儒学所代表的“纲常名教”。郑观应说:“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所变者,富强之术,而非孔孟之常经也。”〔18〕王韬说:“孔孟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所以,“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19〕陈炽也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修道之谓教,自黄帝孔子而以至于今,未尝废也,是天人之极致,性命之大源,亘千万世而不容或变者也。”〔20〕显然,在早期维新思想家看来,孔孟的纲常名教才是“本”、“体”或“道”,是不可改变的。“西学为用”,就是“取西人器教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21〕。
从这些内容来看,洋务派官僚与早期维新思想家主张的“中体西用”,在内容上还是有所区别的。这就是后者所坚持的“中体”比前者已经大大缩小,而“西用”的内涵与外延扩大了。但是,从文化思潮或文化模式来看,早期维新思想家们仍然是属于“中体西用”这一范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器观、本末观仍然是支配早期维新思想家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选择的价值模式。不过,他们二者之间在“西用”内容上的分歧,也显示出中西文化冲突与整合过程正在向新的更高层面上发展。到19世纪的90年代,伴随着西方文化传播的深入和民族危机的加深,早期维新思潮进一步发展,成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变法维新思潮,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等社会政治学说开始传播,成为批判孔孟学说的思想武器了,而洋务派官僚仍然固守于“中体西用”的模式,甚至把它发展到绝对的程度,张之洞便是其重要的代表。
张之洞的《劝学篇》可以说是把“中体西用”赋予理论的形式,进行了系统的阐发和发挥。他在《劝学篇》中是这样概括“中体西用”的: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22〕
“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可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夫所谓道、术者,三纲四维是也,……著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诚变法之非者哉?”〔23〕
与他的前辈相比,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与早期维新思想家略为接近,他不把“西用”拘泥于“器械”的层次,也认为“法制”即体制也属于“器”、“用”的范畴,是可以改变的,不能变者,是“道”即孔孟“圣道”。他认为这是维系人心学术的根本,不能改变。尽管有了这种变化,但他仍然是落后于时代的。因为在19世纪末期,以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来批判封建的纲常名教,已经是社会的潮流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时代的先进人物已经以自由、民权的学说对封建道德和思想意识展开了全面的批判,要求在中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新社会。所以说,张之洞的《劝学篇》尽管也超越了早期的洋务派官僚,但远远落后于社会潮流,他的“中体西用”从现实来看,只不过是反对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之洞是“中体西用”论的理论概括和阐述者,也是“中体西用”论的终结者。在张之洞之后,主张“中体西用”论者不乏其人,但毕竟已成不了社会的主流。伴随着维新思潮特别是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广泛传播,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逐步取代了封建的纲常名教而渐入人心,“中体西用”论成为了历史的遗产。
三
“中体西用”作为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一种最初的整合模式,盛行于19世纪的后半期。它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的最初环节。从60年代初期起,“中体西用”不仅是洋务派官僚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以早期维新派人士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所普遍认同的一种文化模式。它所反映的是中国人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初期的一种价值判断和文化选择。
“道”与“器”、“体”与“用”以及“本”与“末”,是传统中国文化哲学中最基本的范畴。“道”、“体”、“本”表达的是根本、绝对的概念,而“器”、“用”、“末”表达的是枝叶、相对和可变的涵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是绝对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最基本的命题。“中体西用”的模式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这种规范,体现了前者对后者的一种抗拒心理。这种心理表现的是中国文化“中心”、“优越”的观念在西方文化不可抗拒的优越性的冲击下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防御机制。这种防御,不但是一种保守的政治传统的需要,也是中西文化接触初期的一种必然表现。所以说,它所反映的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一种粗浅程度的认识。
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过程是一个漫长、缓慢的过程。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冲突。由于西方文化是伴随着西方的军事侵略而进入中国的,所以国人首先目睹的“西学”便是“坚船利炮及其之后的军事技术与近代工业科技,这就使中国人感到所谓“西学”不过如此。从这一层面来认识,所以“中国人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来反省中国文化,而认为中国之败于西方,非“人心”,非“圣道”,只是“器械”不如人。因此,人们便认为只要学习西方的近代工业、科技便可重新打败“夷狄”了。所谓“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的说法,正反映了这种认识。因此,“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与社会背景下出现的文化反应与选择。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模式体现的是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过程中的最低层次,是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必然环节。从文化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对于一种文化特别是异域文化的认识,必然是遵循从有形到无形、从浅表到深层结构这种认识规律的。西方近代文化最初是以大炮、轮船、商品等反映其文化的外显层次的形式冲击着中国的,这也是中国人接触西方文化的最初因素。同时,因其不直接反映它的深层文化结构,也不具备威胁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性,因而能够为具备传统文化认知结构的中国士大夫们接受。这种现象,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最初认识,也表现了他们对西方文化冲击的最初反映。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必然的反映。
“中体西用”论打破了传统文化中心的观念,因而在近代中国文化变迁中具有进步的意义。在中国,文化传统主义的“华夏中心”观念是相当深厚的。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独特的文化传统使中国人形成了一种自我中心的文化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和文化的中心,只有中国文化才是优越的,其他各国都是“夷狄”蛮邦,没有文明可言。所以,历代统治者都认为所谓“内圣外王”是天经地义的,“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因此,传统中国士大夫是拒绝承认中国以外的文明的,认为“夷狄”远远低于“天朝上国”,没有什么“教化”可言,所以他们拒绝了解外部世界,也不愿为外部世界所了解。所以,当西方势力杀来时,他们的无知就显得相当可笑。他们仍然以传统的眼光来看待外部世界,把西方的近代国家当作古代的“蛮夷”,采取所谓“柔远”、“羁糜”之类的政策,寻找所谓“驭夷”、“制夷”之法,其结果是徒然破灭了“天朝”的幻梦。正是震惊于这种惨痛的教训,有识之士才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作出了“中体西用”的回应。
“中体西用”的反应是对上述文化自我中心论的最初否定。不论是林则徐、魏源,还是洋务派官僚,抑或是早期的维新思想家,虽然他们拒绝承认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或纲常名教的任何缺陷,毫无例外地把这些当作是根本之道,但是他们毕竟开始承认了在中国文化之外的西方文化尚有可取之处,至少可以当作“富强之术”加以吸收。这种观念在今天当然只是一种常识,然而在150多年前, 在充斥了“天朝无所不有”的文化保守氛围中,这确实是了不起的进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正体现了从文化保守主义到接纳、整合中西文化的新的步幅。如果说,鸦片战争以后的林则徐和魏源的“师夷之长技”还带有“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羁縻之类的传统痕迹的话,那么,在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这里,“西学为用”的“西学”则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富强之术”了。这其间,就已明显地显露出一种文化反应与选择的清晰轨迹了。从排斥一切外来的文化、拒绝一切西方的事物,到承认西方也有先进的东西,进而主张可以并且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事物,这正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在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历程中由封闭到开放的过程,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体西用”有其积极的意义。
四
在肯定“中体西用”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它毕竟只是近代中西文化整合过程中的最初步的形式,是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最浅层次的认识基础作出的一种反应和选择,因而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考察,“中体西用”论并不是中西文化融合与会通的科学选择。这是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并不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科学分析和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而是一种调和中西、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文化折衷主义思潮的典型表现。因而它在理论和实践的角度,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矛盾与误区。
“中体西用”的矛盾之一,是它割裂了文化的整体性。“中体西用”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中国的精神文明是优越于其他各国的,而只有物质文明不如人。如李鸿章所说的:“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中体西用”论者才以“中体”与“西用”的概念来规范和界定中西文化,从而割裂了作为独立的两种文化的“体”与“用”之间的联系和统一。在“中体西用”论者看来,中国文化的“体”即它的文物制度、纲常伦理、意识形态是可取的,只是它的“用”即器物的层面不可取;而西方文化正与之相反,其“体”不可取,其“用”可以接纳。而这正是“中体西用”论者在文化整体关系上的矛盾所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总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是受制于一定时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因而所谓文化的“体”与“用”其实是不可割裂的,即使从大文化的角度(即把文化理解为一种包括经济、制度、意识、心理等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来理解,所谓“体”与“用”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彼此制约的,一定的精神文明正是受制于一定的物质文明。“三纲五常”的封建意识形态乃是小农经济、专制制度、等级社会的产物,而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则需相应的自由、平等、民权等观念意识来维护。因而文化的“体”与“用”是不能分割的,也不存在只有“体”或“用”的文化形态。其实,即使是洋务派官僚或早期维新派人士,随着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更深入的了解,他们也开始意识到用“体”“用”关系来涵括中西文化是不确切的,认识到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样,是有着不可分割的“本末”与“体用”的完整的文化体系。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西用”范围的放大和对“中体”内涵的收缩,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已经意识到这种“中体”与“西用”之分的内在矛盾,并试图加以解决的思路。然而他们既囿于“体”、“用”的框架,就无法突破这一范围。
曾经走出国门的郭嵩焘在亲历了西方文化的氛围之后,认识就大大提高了。他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24〕郭氏还将西方思想家“巴夫子”(柏拉图)、“亚夫子”(亚里斯多德)、“琐夫子”(苏格拉底)和“比耕”(培根)与被中国士大夫视为圣人的孔子、孟子相比较,说明西方文化也有其发展源流,有其历史传统,并成为近代西方文化的“本源”。这种认识,是朝着冲破“中体西用”的框架迈进了一步。杰出的维新思想家郑观应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1884年就写道:“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而效其用,所以事多扦格,难臻富强。”〔25〕因此可以说,“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模式存在的矛盾,乃在于它对文化整体性的割裂,也是它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
“中体西用”论的矛盾之二,是它违背了文化整合的规律。两种不同的文化在接触过程中,总是经历从冲突到整合的过程,这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所谓文化整合,乃是不同的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调合而趋于一体化(即互相容纳、有机结合)的过程。它实际上是不同文化因素的重新组合,原来不同源流、不同性质以及不同目标取向、价值取向的文化,在整合过程中渐渐融合,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并组成新的文化体系〔26〕。然而,文化整合并不是各种文化机械地组合,更不是人为地割裂文化整体,各取所需,而是在交流的过程中相互吸收、融化的自然过程(当然这并不排斥文化控制的可能,但文化控制也必须是一种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调节、组织的机制)。“中体西用”论者的矛盾与误区在于,他们人为地割裂了文化整体的各个部分或因素的有机联系,以主观的需要来取舍中国文化和西方的某些构成或因素,从而导致了违反文化所反映的社会时代性质的不同性质的文化的主观组合,也导致了它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所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西方近代文化则受制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两者反映的社会时代性质是基本不同的。同时,以近代社会发展的趋势而言,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又是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但是,“中体西用”论者企图在保存封建的“文物制度”(洋务派官僚)或“伦理纲常”(早期维新派)的基础上,引进西方的器物文化层面,并用以维护封建的基础——换言之,即以西方文化的“用”来嫁接于传统文化的“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洋务运动之收效甚微,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虽然建立了较为先进的机器、武器工业体系,但管理制度、思想观念乃至于整个社会机制都是陈旧的,这就很难发挥作用。戊戍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思想家和改革家进一步从制度的层面来思考中国文化的问题,正是在对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体西用”论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正说明了“中体西用”论所代表的文化价值判断和文化选择模式所存在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此,“中体西用”也不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整合的理性反应模式和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文化价值选择,它必然为新的文化选择所代替。
注释: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戍变法》,(二)第426页。
〔2〕《海国图志》,卷二,“议战”。
〔3〕〔4〕《校枬庐抗议》,“制洋器议”;“采西学议”。
〔5〕《洋务运动》,(二),第286页。
〔6〕《李文忠公尺牍》,第八册。
〔7〕《洋务运动》,(五),第119页。
〔8〕《术厥斋日记类钞》,卷上,页五十五。
〔9〕《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页三十五。
〔1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页九。
〔11〕《李文忠公全集·明僚函稿》,卷三。
〔12〕〔13〕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第147页; 第138页。
〔14〕〔15〕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
〔16〕〔17〕〔18〕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
〔19〕王韬:《易言·跋》。
〔20〕陈炽:《庸书·自强》。
〔21〕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
〔22〕《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23〕《劝学篇·外篇·变法第七》。
〔24〕郭嵩焘:《条陈海防事宜》,《养知书尾文集》,卷3。
〔25〕郑观应:《南游日记》。
〔26〕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3 月版,第384~386页。
标签:洋务派论文; 折衷主义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劝学篇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中体西用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