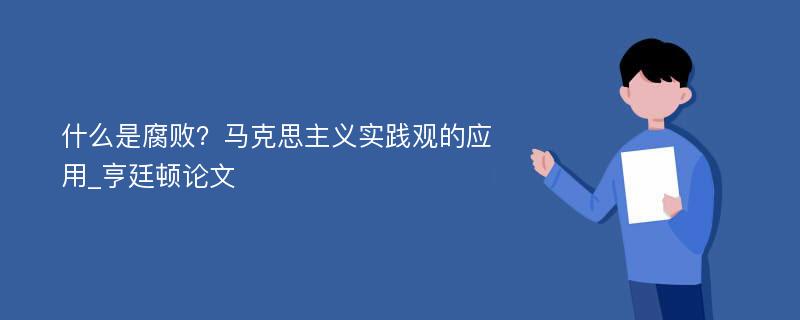
什么是腐败行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一个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腐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亨廷顿的腐败定义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对腐败行为提出下述定义:腐败行为是“公职人员违背公认规范,谋取私利的行为”。这个定义指出了腐败行为的两大要素:一是违规使用权力,二是图谋私利,与人们的常识中的“以权谋私”大致相符,因而广为接受。然而,该定义有严重缺点,以致会在实践上导致许多有害的结果。
首先,这个定义只把腐败行为者界定在公职人员范围内,而把行贿与其他腐蚀官员的行为排除在腐败行为之外。其实,那些贿赂性的腐败行为,不仅是由受贿者构成的,而是由行贿、介绍行贿与受贿行为联合在一起构成的。[①]行贿者与贿赂介绍者对腐败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他们排除在腐败行为之外,是不合理的。
其次,这个定义只把腐败行为的主观动机定义在个人私利上,从而忽视了腐败行为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为小集团利益与地方利益而损害国家与社会的利益。这些影响相当恶劣的行为,由于似乎不是出于私利,而有可能被堂而皇之地排除在腐败行为之外,或者至少得到同情与理解。
其三,按照亨廷顿定义,一个行为是否腐败行为,其核心判据是行为者的主观动机(私利),以及其所采用的手段(违背公认规范使用权力),而不是该行为的客观后果。这是该定义最严重的缺点,由此导致一系列理论上与实践上的混乱。
理论上的混乱的突出表现,即所谓的“腐败行为正功能论”。按照亨廷顿定义,一个行为只要包括某种私利目的,再加上对权力的违章使用,便一定构成腐败,而不论其所引起的社会后果如何。然而,不存在抽象的权力使用“公认规范”,只存在某一社会发展阶段中某一特殊社会环境下的权力使用规范;这种规范不可能是某种普适于全人类的尽善尽美的绝对真理,而只是某个时代某个国家具体规定的规范,其包含着许多局限与错误。所以,违背所谓“公认规范”的行为,即使是出于行为者的私利,也未必就是如何对社会发展有害的行为,有时甚至可能对社会发展有利,自身具有直接正功能(而不是克服它们所引发的正功能)。按照亨廷顿定义,这些行为也应当包括在腐败范围之内。正是由于这种概念上的错误,导致从60年代起,国外一些学者开始研究所谓腐败的“正功能”,认为腐败行为本身(而不是腐败行为引起的反腐败斗争)可以对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②]国外学者的这些观点,在我国会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有人据此认为腐败是搞活经济的“润滑剂”,是改革开放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极大地干扰着我们反腐败的决心。实际上,并不是腐败本身有什么正功能,而是由于按照流行的关于腐败行为的概念,把一些具有正功能的非腐败行为,被错误地划归腐败行为范围内所致。
对客观现实的求事求是的分析研究表明,在那些按照亨廷顿定义,可以划归为“腐败”的行为中,的确有一部分(为了与真正的腐败行为相区别,本文将这一部分行为称之为“特殊的权力越轨行为”)可能具有以下正功能:
第一,这种“特殊的权力越轨行为”,是打破束缚经济发展的官僚主义的有效手段。用正常的权力使用方式,很难以致无法在有效期间内打破各级政府的官僚主义对经济发展的束缚,于是经济发展的活力有可能被官僚主义窒息。这时适当地使用一些润滑剂,可以使权力得到灵活使用,从而以较小的成本克服官僚主义障碍,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否则,要等官僚主义自己得到克服以后,经济发展才能松绑,必然坐失良机。
第二,这种“特殊的权力越轨行为”,能够有助于打破行业垄断,打破现有经济体系的“循环流转”,给技术创新开辟道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比特说过,社会经济常常形成一种“循环流转”格局和垄断格局,各种生产要素与产品按照既有途径流通。技术创新作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必须打破这种垄断格局与循环流转格局,开辟新的流通渠道。而当原格局十分牢固时,适当地使用一些润滑手段,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打破原有格局,开辟新的流通渠道。
第三,这种“特殊的权力越轨行为”,能够冲破由政府决策失误造成的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禁区,从而减少这种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政府的决策的失误总会发生,在我国,就曾经“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错误,即使在改革开放期间,各级地方政府也有不少束缚经济发展的清规戒律。它们会扼杀或阻碍一些有发展前途的新生事物的生长。全面地纠正这些政策失误,当然最好,但这需要花费时日,付出巨大的代价。这时,如果采用某种灵活手段,能在某些时候松动政策界限,使新生事物得到生存与发展的机会。
总之,在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下,采用一些灵活手段,使权力得到非规范性使用,可以在某些局部事件上,克服僵化,给技术创新与其它新生事物得到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从而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些“特殊的权力越轨行为”,在具有上述正功能的同时,也具有种种负功能,主要是纪律上的不良示范作用,可能造成在一定程度上的失控。然而,正负功能相比,正功能有可能占主导方面。这些行为,按照亨廷顿定义,它们的确是腐败行为。然而,在社会革新时期,又非要如此不可,否则新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得不到发展机会,社会政治经济格局会处于十分僵化的状态,从而严重地束缚社会经济的发展。
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叶剑英元帅曾经说过:“大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按照当时的政治路线,一些好人不一定能够得到提拔任用,以至需要一些“开后门”之类的违章小动作,来避免林彪、“四人帮”之流的干扰。再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成份基本上不存在,国民经济全部被计划经济体系所完全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能够生产较高质量产品、富有经济活力的乡镇企业,为了打破行业垄断,打破当时经济领域中的“循环流转”格局,不得不使用所谓各种“灵活经营”手段,来突破当时计划经济的僵局,争取到一点生存机会。正因如此,人们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而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打破僵化的经济格局的必须付出的代价,否则,在当时的僵化的国民经济格局中,就不可能有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再例如,在对外贸易中,我们遇到的是强大的既有的国际经贸格局,还会遇到各种政治上的麻烦与各国政府的官僚主义等等。如果我们不采用某种灵活的经营策略,只是一味地指望通过斗争来建立有利于我们的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等到新格局形成后,再“冠冕堂皇”地打入国际市场,那将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其结果只能是窒息我国民族工业的国际生存空间。所以,在上述各种情况下,使用这些“特殊的权力越轨行为”,可能是必要的。当然,一个理想的、完善的政治经济体系,自身应当具有克服官僚主义、打破行业垄断、纠正决策失误、协调各方利益的正常的合法渠道,而不应通过“权力越轨行为”来做到它们。然而,现实的政治经济体系不可能是如此理想,总有些不完善的地方,以至缺乏这种合法渠道。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更不用说,即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也不可能时时处处都如此理想。在这种情况下,轻微的“灵活经营”,作为克服这些弊端,使社会经济得到发展的权宜之计,有其存在的理由。
凡是对社会发展具有正功能,因而具有存在理由的事物,一定是必然出现的事物,具有不可遏止的发生趋势。因此,只要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具有僵化的不合理的成份,我们要搞活经济,上述种种“特殊的权力越轨行为”就不可避免。这是社会自身为了克服政治经济体系的僵化与不合理成份的必然的补偿机制。如果将这些行为都确定为腐败行为,那么,只可能出现下述两种结果:如果我们坚持反腐败斗争,那么就必须严厉禁止这种“特殊的权力越轨行为”出现,使经济“一抓就死”;如果我们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容许上述对经济快速发展有正功能的“特殊的权力越轨行为”出现,又承认它们是腐败行为,于是会产生“腐败有功”的错误观念,放弃反腐败斗争,导致我国经济就会“一放就乱”。要避免这两种局面的出现,就必须既要坚持反腐败斗争,又要解放思想,使经济迅速发展,必须把上述“特殊的权力越轨行为”与真正的祸国殃民的腐败行为区别开来。
再把非腐败行为划为腐败行为的同时,亨廷顿定义还会把一些真正的腐败行为排除在外。实际上,不仅不合当时规范的权力行为未必是腐败行为,那些合乎当时规范的权力行为,也未必是非腐败行为。例如,在昔日的封建社会,那些被后世称为“昏君”“暴君”的帝王的专横拔扈、为非作歹的行为,无不合乎当时的权力规范,因为这种规范规定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其的确是地地道道的腐败行为。在文化革命期间内,有些行为合乎当时权力规范,如残酷地整革命干部和专家学者、在经济上“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这些行为如果出于私利目的,如趁机徇私报复、争名夺利等等,同样构成腐败行为。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我们在法律上与政策上有各种漏洞,一些人出于私利钻空子,进行各种危害国家、社会与人民的利益的权力活动,这些活动并没有直接违背权力使用规范,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我们不能不认为它们是腐败行为。而我们按照亨廷顿定义,就不能把它们划归腐败行为,造成其滋生泛滥。
亨廷顿定义之所以有上述错误,其根本缺点在于只从抽象观念上给腐败行为下定义,未从行为的实践结果上来定义,不是关于腐败行为的功能性定义。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看,一种行为的性质,不是看其抽象的道德意义,而在于看其实践后果。为了真正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保护改革开放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而不是从抽象的伦理角度,来进行反腐败斗争,就应当突破亨廷顿定义,将上述“特殊的权力越轨行为”与真正的腐败行为严格区分开来,把真正的腐败行为包罗进去,对腐败行为进行真正科学的判定。
腐败行为的功能性定义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看来,对任何社会行为的完整定义,应当由各有关方面主观动机、手段与客观后果三个要素构成,其中实践的客观后果是核心。衡量一个行为是否腐败行为,也必须分析这三个要素,其具体含义如下:
1、主观动机因素。真正的腐败行为,总是为了谋取某种私利,特别是那些不可告人的私利,或者地方与小集团的利益。按照我国著名政治学家王沪宁教授的意见,腐败行为者的主观动机可分为拜金型、拜物型、聚宝型、享受型、徇私型、徇情型、贪色型七类。[③]笔者认为,腐败者的主观动机,可具体地分为三大类:1、图谋各种物质利益:如谋取钱财、贪图享受和贪恋女色等等;2、图谋心理满足:如追求权力与名位;徇私情,讲私人关系;3、追求小集团和地方利益。这些主观动机构成腐败行为的出发点。
2、客观手段因素,即使用权力。腐败行为与其它犯罪行为的区别,在于它是通过使用权力来实现的。这里讲的“使用权力”,既包括合乎当时权力规范的行为,也包括违背当时的权力使用规范的行为,二者都可能成为腐败行为实现其目的的手段。我们已经指出,合乎当时权力使用规范的行为未必一定不是腐败行为,许多腐败行为都是在合法权力程序的外衣下进行的。不然,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国家大政方针正确,法制日益健全,所发生的腐败行为,将越来越通过对权力的违章使用而形成。这些违章行为,表现为四大类:第一是积极性违章,即给不允许办的事开红灯,扩大规定的职权范围;第二是消极性违章,即故意设立关卡,当办不办,或人为拖延,以显示其权力;第三是在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对既可办也可不办的事,根据私利来裁定。这种行为表面看来并不违章,是腐败行为最通常使用的形式。第四是公职人员利用非正式权力与影响力,来谋取私下利益。
3、客观后果因素,即腐败行为给社会和他人造成的严重的直接危害。由腐败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可以分为直接后果与间接后果,其中直接后果是判断是否腐败以及腐败程度的大小的最重要的客观根据。间接后果也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它具有长期性与不确定性,有时往往带有某种逻辑推论性质,所以,为了不致将腐败行为扩大化,我们应当将腐败行为的判据限制在直接损害范围内。腐败之所以必须根除,最重要的是其给社会与他人造成严重的直接危害。
上述三者中,主观动机不能作为腐败行为的核心判据。亚当·斯密说过:在市场经济下,人们“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③]这是市场经济的最根本的行为基础。所以,要搞市场经济,使用“看不见的手”配置社会资源,就必须允许人们追求私利,承认这种利益驱动的合法性,不能将其作为腐败的核心判据。当然,我们在道德上有比此更高的要求,提倡人们公而忘私,但不能将此要求视为是否腐败的判据,不能认为不是孔繁森就一定是王宝森。所以,如果把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主观动机,说成是腐败行为,都在反对之列,必然把市场经济下人们的正常行为混同于腐败行为,只能起到保护真正的腐败行为的作用,这当然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对权力的非规范性使用也不能作为腐败行为的核心判据。如上所述,腐败行为以使用权力为手段,既包括符合规范地使用权力,也包括不合规范使用权力。我们已经指出,合乎权力规范的行为未必不是腐败行为,例如各种合法的封建特权,以及钻改革开放时期法规政策上的漏洞等等。而违背当时权力规范的行为也未必一定是腐败行为,因为权力规范本身也可能具有各种扼杀新生事物与阻碍经济发展的缺点。当然,这并不是说,腐败行为与权力使用是否违章毫无关系。同样的腐败行为,其中违章行为要更加严重与恶劣,因为它缺乏“社会批准”的理由,而必须全部由行为者个人来承担。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看来,上述三要素中,只有对社会和他人造成严重的直接损害,才能作为腐败行为的最核心的判据。腐败行为不是一般追求私利的行为,也不是一般的违纪行为,而是犯罪行为。任何犯罪行为必须是对社会或他人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一个行为如果没有构成对社会与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算不上犯罪,当然也就谈不上是腐败。这类行为的动机与做法不论怎样不妥,只能是纪律上的不妥或道德上的不高尚,而不能作为腐败行为来处置。所以,腐败行为的必要条件,是其必须是造成对社会与他人的严重损害的犯罪行为。而这些犯罪行为分为两类,一是非权力犯罪,如抢劫偷窃等等;二是权力犯罪。在权力犯罪中,又有多种形式,如失职和腐败。所谓腐败,指的是那些出于各种利益驱动并通过权力使用过程造成的犯罪。
这样,综合以上三个因素,我们应当给腐败行为作如下的界定:腐败行为是行为者为实现私人、小集团与地方利益(特别是不可告人的私利),通过使用权力(特别是以违背当时的权力规范的方式使用权力),从而给社会造成严重的直接损害的行为。简单地说,腐败就是以权谋私或以权谋取地方或小集团利益,从而造成对社会的严重损害的行为。这是以行为的客观后果,即其社会功能所下的定义,所以,我们称之为对腐败的“功能性定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对腐败问题的分析上的体现。
这个定义的含义,关键在于对腐败行为的对社会与他人所造成的直接危害,作出明确的界定。总的来说,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权力过程可能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有以下几个方面,它们成为我们判断一个权力行为是否腐败行为的核心判据:
1、给国家、集体与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的严重损害。这是可以定量计算的直接经济损失与对人的生命与健康的损失。直接经济损失有时等于腐败者所侵吞和收受的财产,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远远大于这个数目。现在对行为腐败程度的判定,往往以其直接侵吞与收受的财产为据,我认为是不妥当的。一个因为收受一台彩电而进口200万元设备的人,与一个进口同样设备而收受10台彩电的人相比,所犯罪行是一样的,甚至更加恶劣;因为此人如果收受10台彩电的话,很可能要国家赔上2000万元的损失。
2、所导致的对市场秩序的破坏。例如,由于收受贿赂,导致市场上“优汰劣胜”,伪劣产品泛滥,构成对消费者生命财产的坑害,给生产优质产品的厂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等等。这些损失,基本上也是可以定量计算的。
3、导致公害与人为事故。由于腐败而导致的进口洋垃圾和毒品、环境污染、放松计划生育管理、各种责任事故等等。
4、直接的政治性损失。由腐败行为导致的党和国家的机密的泄露;对党和政府形象的直接歪曲,等等。
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危害。当然,腐败的危害性绝对不止于此,其最根本的危害性在于阻碍改革开放进程,破坏现代化事业,威胁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等等。但这些属于间接性危害,带有推论性质,一般不作为腐败行为的直接判据。
由于行为的上述后果可以明确界定,所以,这个对于腐败行为的功能性定义,具有很强的客观性与可操作性,既可严格地定性判断某一行为是否腐败行为,也可对其腐败程度进行定量判定。其判断的优先次序应当如下:首先应根据对社会与他人的损害程度,对该行为是否腐败及其腐败程度作基本的确定。在这种损害相同的情况下,再视其权力使用过程是否违章,以进一步确定其腐败程度的大小。最后,在根据行为者的主观目的——是“阳光下的目的”,还是不可告人的目的,对腐败程度作进一步的判定。
功能性定义的意义
这个功能性定义,是关于腐败行为的最科学、最有用的定义。
首先,这个定义是能解放思想。它把那些做法看来有问题,但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作用的“特殊的权力越轨行为”,与腐败行为区别开来。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的越轨行为的确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对权力的使用规范并非尽善尽美的,有时对它的越轨,反而可以给僵化的政策与体制带来一些松动,给新事物的发展创造一些机会。这个功能性定义,把人们的视线从行为的动机与行为方式上,转移到行为的后果上。“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不管动机如何(如亚当·斯密所言)和行为怎样,“只要能够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是允许的行为,就不能将其划成腐败,尽管我们可以不提倡这些行为。这样一来,人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看准了的符合“三个有利”的,就大胆去做,而不必畏首畏尾,裹足不前。
另一方面,这个定义又是严格的。它要求当权者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在一切情况下,都严厉禁止任何会给社会与他人带来严重危害的行为,不管行为者的行为是否能够穿上合法性外衣。我们已经指出,由于我们法制与政策上的不健全,有时会给各种严重危害国家、社会与他人的行为提供漏洞。这个功能性定义要求在此情况下的行为者,不要挖空心思钻权力规范上的漏洞,给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披上合法性外衣,趁机大捞一把,做危害社会与他人的事情,而把责任完全推给当时的权力体系。正象“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一样,不管白鼠黑鼠,偷吃粮食就是坏鼠。行为者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的权力程序,只要造成对社会与他人的严重损害,都必须对由此而产生的后果负责。如果是出于私利,就一定是腐败分子。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要求权力行为者把国家、社会与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都有理由禁止那些危害社会的权力行为。一旦这个目的得到实现,反腐败的目的便完全达到,整个社会就会蒸蒸日上,不断发展。
因此,按照这个功能性定义来作为腐败行为的判据,就能够使反腐败斗争与改革开放齐步并进,健康发展,而不致一搞反腐败斗争,就不敢闯,不敢冒,停止改革开放的步伐,陷于“一抓就死”;而一搞改革开放,就忘乎所以,为了私利与小范围利益,可以钻权力规范的空子,不惜牺牲他人与全社会的利益,陷入“一放就乱”。
这个功能性定义之所以有如此意义,说到底,是因为它的理论基础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按照这个定义来界定腐败行为,实质上就是按照邓小平同志重视实践效果的一贯思想风格,按照他的“三有利”的标准,来指导反腐败斗争。如果我们按照这一功能性定义确定反腐败斗争的各种方式与政策,将大大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建立健康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注释:
[①][③]童星:《世纪末的挑战——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10—411页。
[②]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75—76页。
[③]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