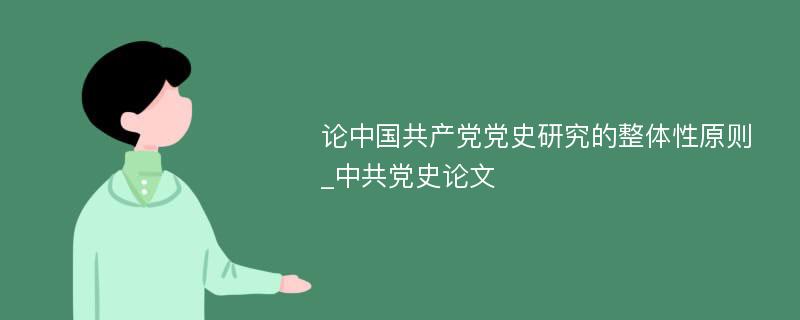
论中共党史研究的整体性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整体性论文,党史论文,中共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5)03-0004-09 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历史性阐释或规律性探讨,是党史工作者一贯秉持的准则。近年来,受西方以“解构”为特征的理论、方法的冲击,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党史研究中所建构的学术秩序,趋向于对细节问题的挖掘或考证工作。这样的细化研究对具体问题的梳理或情景再现有所裨益,却由于研究者往往缺乏相关的系统理论知识或宽广的“研究视域”,无法恰当处理宏观背景与微观个案的关系,也引发一些“碎片化”问题的出现。值得注意的是,有人以“反思历史”为名,诋毁和否定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历史合理性,或者抓住党的历史上的个别失误大肆渲染,借此否定党史的主流和主线,出现了一些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这些问题的出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研究者缺乏整体性科学思维。因此,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提倡和贯彻整体性原则有着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并应当成为党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中共党史研究整体性概念的基本内涵和范畴 所谓整体性,通常是指事物内在的连贯性、有机性或系统性。就史学研究而言,整体性概念内涵主要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全面性,终极目标是为了解历史整体框架下的所有内容,尽可能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地了解历史面相。虽然这样的全面性难以实现,但正如历史“求真”一样,也不能否定“求全”的准则和精神。二是联系性,它要求把研究对象看作一个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而非一个片段或孤立的内容。联系性还体现在“以小见大”,即具体的研究要与宏观研究形成有机对接,彰显出大历史的实践轨迹。三是宏观性,这是整体性研究的最高境界。它不但重视综合、全局的考察,更注重对影响和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问题、脉络问题或主流问题等宏观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人类历史本质规律的概括和总结。也就是重视对历史逻辑、历史法则或历史哲学的思考,其意义最大,研究难度也最高。整体性概念内涵的这三个层次构成统一的整体性研究思维,其中任何一个层次都具有学术价值。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都提倡从整体上去分析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不同要素间相互作用的有机的系统整体,“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①,不能孤立、片面地观察和解释个别社会现象和问题。法国年鉴学派则提出了“总体的历史学”,认为只有综合地、广泛地、全面地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才能真正地认识过去,所谓“整体史”、“总体史”的概念正由此而来,但整体观念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是在历史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在我国古代,整体性是传统哲学的重要思维方式之一。如庄子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②即体现了宇宙万物普遍联系和“天人合一”的和谐整体观。散耗结构创始人普里戈金指出,“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和”,并预言西方科学和中国文化对整体性、协和性理解得很好的结合,将“导致新的自然哲学和自然观。”③西方哲学也十分重视事物的整体性,从巴门尼德提出作为整体的存在不生不灭④,到赫拉克利特把世界看作有规律可循的整体⑤,再到亚里士多德提出整体并不是其部分的总和的著名命题⑥,及至黑格尔以辩证思维首次提出“整体性”范畴⑦,他们对于整体性问题的表述至今仍富有启迪性。到了20世纪,在自然科学领域,系统论、散耗结构理论、复杂学等一系列具有浓厚哲学色彩的整体性方法论也开始出现,都在努力寻找某种具有普遍性、超越学科界限的整体性方法。所有这一切,至少说明对复杂事物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的全局思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贝塔朗菲所指出的,“不管怎样,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这就意味着科学思维基本方向的转变。”⑧ 在学术研究中,整体性问题已经引起我国学界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即有学者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对整体性原则进行了系统性论述,并呼吁在科学研究和社会改革实践中重视这一科学思维方式⑨。整体性问题在学术研究领域得到凸显,是伴随着近几十年来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系统论热的兴起⑩。在系统的整体性概念的知识体系和原理方法的基础上,社会科学各领域积极进行新的思考,实现了一系列新的突破。如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整体性已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和热点问题,不少学者围绕整体性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论述(11)。社会学、文学、管理学、决策学、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也都不同程度地尝试运用整体原理解决学科中的问题,并取得了进展。在史学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也有不少学者尝试运用系统论研究历史,以改变传统单一的研究思维模式(12)。但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史学领域对整体性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分析“碎片化”问题和社会史研究视角时述及。他们指出,要克服当前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整体史观(13),而以“无所不包”自称的社会史,其内涵在本质上就是“整体历史”,或者说“整体史的社会史”(14)。也有学者提出以“大历史”(15)的方法来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发展,把国史放在现代化进程和中国与世界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中考察其成败得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从整体上研究党史的必要性和意义(16)。这些讨论对于党史领域的“整体性”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就中共党史研究来看,其整体性概念范畴至少应包含以下三个理解视角。其一是“问题”的整体性。中共党史作为研究对象,其本身是一个完整的、具有内在逻辑的统一体。科学地研究中共党史的关键,是从整体上把握中共历史,而不是人为地切割为几个互不联系的历史时期或部分,更不能随意抽取中共在某一历史时期的错误而歪曲甚至全盘否定党的历史。其二是“方法”的整体性。“问题”的整体性要求在方法论上必须运用整体性原则进行研究。一方面,党史研究者必须把党史作为一个有机的联系整体进行考察,既从纵向上考察历史现象的前后联系和长期发展演变,又从横向上对一定历史阶段的众多方面进行通盘考察,以历史主义原则探寻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另一方面,中共党史本身的性质和内涵丰富、外延广博的特点,决定了应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吸收中国传统史学、西方史学以及相关学科如抽象、概括、综合、比较、系统、结构等具体的研究方法,以完整深刻地认识和反映党的历史。但在方法运用上必须要得当,否则势必会影响党史研究的整体性,甚至导致党史的扭曲和虚无。其三是“学科”的整体性。整体性是认识和确定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基本点。从当前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整体性集中体现在学科对象的整体性、学科结构的整体性和学科功能的整体性上。在学科对象上,党史研究应当包括党建研究,党的自身建设的历史本身就是党的历史的一部分;在学科结构上,中共党史应由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党史学史、文献学和史料学、编纂学,以及主体学组成它的完整体系(17);在学科功能上,作为一门科学性与党性、学术性与政治性高度统一的学科,它应当在发挥其传承文明功效的同时,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发挥其资政育人的作用。中共党史学科也必须在各板块整体性发展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统一规划,统筹安排,提高党史研究的整体化水平,并最终建立大党史的工作格局和实现学科的整合。 二、运用整体性原则指导中共党史研究的必要性 以整体性原则研究中共党史,无论对于转换研究思路、指导工作,还是解决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中共的历史是一个整体,只有坚持整体性原则才能反映其主题和主线。中共90余年来的发展历程是一个由各个时期组成前后连续的整体历史。在这一历史长时段中,中共始终围绕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进行长期不懈的奋斗,这是中共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要反映中共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准确地把握中共历史活动的主要轨迹和脉络,就必须把中共各时期的历史放到90年的历史长河中,甚至放到中国近两三个世纪的历史中进行考察。但在当前的党史研究中,存在着整体肢解和误解的现象:或是把中共历史分割为革命和建设两个孤立部分,无视中共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或是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割裂开来,相互否定;或是对中共在某一时期的错误进行片面的、过度的甚至歪曲性的阐释,破坏了中共历史的整体性和真实性。强调中共历史是一个整体,并不意味着要回避和遮盖中共在历史上所犯过的错误。应当承认,中共历史同样包含着失误和曲折的历史要素,如中共的路线在各个时期并不都是正确的,有的时期甚至错误的路线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总体来看这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胡绳坚持从整体上评价中共的历史,他认为,“讲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是就党的全部历史来说的,不必将哪个时期例外。……如果‘声明’一下,说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要将30年代前期除外,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除外,那样反而说不清楚了。对我们党,要看重内在的、整体的、长远起作用的因素。”(18)很显然,中共历史是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每一个时期相对于历史整体进程都带有“阶段性”的特征,只有建立在整体性的思考路径之上去把握中共历史,才能深化对党史主流和本质的认识,也才能对中共作出正确的评价。 其次,坚持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对整体性的阐述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社会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客观世界看成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整体,进而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统一体进行把握,强调社会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19)。其中又包括三层内涵:一是将人类社会这个大的社会整体,概括为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构成的社会有机形态,这是面向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二是将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并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三是对具体社会事物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把社会生产方式看作是一个由各个独立要素构成的整体。这三个层面,马克思主义都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并常以“系统”、“有机整体”、“统一体”、“总体”、“过程集合体”等术语来表述(20)。第二个方面是整体和部分。在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确立了整体并不是其组成部分机械相加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这一复杂事物进行研究,是从厘清其构成因素入手的,但最终目的在于说明社会形态的演进,揭示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这就需要具有整体史观。第三个方面是普遍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再强调,一切事物和过程乃至整个世界都是普遍联系的,并因此形成一个统一整体,普遍联系也因此成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马克思指出,唯物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灭方面去考察的。”(21)任何事物只有置于历史发展过程中和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之中,才能得到正确的说明。这就揭示了客观世界的普遍联系原理。以上三个方面说明,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的一条基本线索和基本要求。不从整体上认识人类社会,就不可能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党史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当然包括整体性原则的指导。 再次,坚持整体性是反对“碎片化”、特别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迫切要求。史学研究领域中的“碎片化”问题已经引起学者的高度关注。2012年《近代史研究》编辑部曾召集章开沅、郑师渠等学者针对“碎片化”问题作过集中式的笔谈(22)。所谓“碎片化”,即是指那种割裂整体、过于细化的研究取向。作为一个源自西方的概念,其产生主要受西方国家一些社会思潮如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影响,并与我国社会史发生的区域转向、“中国中心观”和新文化史的兴起有直接关联。中共党史作为中国现代史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同样面临“碎片化”倾向。目前,在一些总体性、综合性和基本理论等重大问题尚未得到厘清之时,不少党史研究者却纠缠于那些琐碎冷僻、无关宏旨的一事之考、一字之辨,这固然与当今学术考评机制有关,也显示出研究者在追寻党史内在脉络上问题意识和整体意识的缺失。克服“碎片化”问题,从结构和整体上重建中共党史,是当前党史学界面临的最急迫的使命之一。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同样需要我们在研究中坚持整体性。有学者指出,历史虚无主义者研究历史,往往把现象当本质,把支流当主流,将历史上的某些失误抽象化,并片面地、孤立地放大、渲染,从而达到歪曲历史的目的(23)。他们进行学术研究,不是在对历史资料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去把握历史发展的进程,而是通过隔断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联系,来否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抑或撇开现实历史条件,以主观愿望假设或预设历史的进程,再从历史资料中择取有利于论证自己观点所需要的部分并加以涂抹。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科学的整体性和客观性原则。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否定中共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合理性;二是夸大中共领袖的错误,试图通过抹黑中共领袖和对中共历史的否定,达到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三是渲染中共历史上的个别失误,借此否定中共党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这些做法都是严重背离整体性原则的错误行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24) 最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和中共历史学功能的发挥需要坚持整体性原则。中共党史学科体系目前已基本确立,但要建构一个成熟的党史学科体系仍存在不少困难。就这门学科的基本理论来看,很多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答,有些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水平;从研究成果看,数量虽然不少,但理论概括往往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共党史学科的整体建设。这种学理上的困境导致中共党史与其它学科相较,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党史学科存在被弱化和边缘化的危险。因此,新世纪的中共党史要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就必须从更广阔的研究视域中回答有关的重大问题,同时加强在党史编纂学、文献学、目录学等相关的辅助性门类方面的配套性综合研究,保证党史学科建设的完整性。 中共历史学功能的发挥同样离不开整体性研究。党史学科功能包含着学术功能和政治功能两个层面。党史学科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党史研究不可能离开现实政治而抽象地谈它的学术性,其学术功能与政治功能是一个辩证统一体。在学术上,整体性原则要求党史研究要采取客观、严谨的态度和方法,尽可能地反映客观真实,而不能预先存有某种价值倾向随意割裂和歪曲历史,这也是其社会功能得以发挥的重要基础;在政治上,必须注意总结中共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现实社会作出科学分析并为现实提供借鉴,真正发挥党史学科“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这就需要党史研究者具有面向现实的“问题意识”,不仅要勇于批判社会上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颂扬中共的历史功绩,还要加强理论建设,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不断增强理论自信和历史自信。 三、中共党史研究中如何运用整体性原则? 整体性作为一种统揽全局的思维方式或分析框架,在党史研究中贯彻落实,既要有理论指导,也要有方法借鉴,更要重视处理好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坚持正确的历史观 史学的核心问题是历史观。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有着不同的历史观,就会对客观历史现象作出不同的评价和判断。中共党史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确保党史研究的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等基本原理,由此向人们提供了科学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武器。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两个最伟大发现之一,它使“整个世界历史观上实现了变革”(25)。列宁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说而是科学证明了的原理……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26) 中共党史研究不仅是一门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揭示近现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还是一门具有鲜明党性和阶级性的科学。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才能真正实现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才能增强政治敏锐度和政治洞察力。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各种各样的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向我们涌来,于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告别革命论”、“侵略有功论”,以及“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等诸多错误言论,其命题都涉及中国究竟应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些错误思潮甚至以标新立异为要,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恶搞”。在它们的歪曲和攻击下,雷锋精神的本质被归结为“愚民”精神,董存瑞和黄继光的英雄行为都被改写成“被迫之举”,这显然是对中国人文精神内在传承意义的否定。在本质上,这些都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虽然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历史时花样百出,手法多样,缺乏严格的逻辑和理论证明,但是,在这背后却隐藏着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格格不入的理论前提和方法。”(27)这就需要党史研究者学会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去揭示其错误本质。 (二)开阔研究视野 整体性原则和方法要求党史研究的视野要开阔,除了对中共历史本身要从整体上去把握外,更重要的是要把中共历史置于民族复兴、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中去考察。也就是说,党史研究不能拘泥于自身,不能就党史言党史,需要有“大历史”的研究视野。只有跳出党史看党史,才能认识“庐山真面目”,对党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才能获得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28)。要开阔党史研究视野,需要重视纵观与横观两个维度。 纵观即是要在时间上了解中共党史的整个发展过程,并将其置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可以说,一部中共党史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欧阳淞指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实现,为中华民族复兴创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而新中国的成立,又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29)。对党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有一个时代主题上的总体了解和认识,才能在研究某些党史课题时避免对历史主题的忽视,也才能正确阐释党的历史在中华民族复兴中的地位。 横观是就空间而言,即党史不仅要研究党、政、军的活动,还要研究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不仅要研究中共的历史,还要研究与革命发展有关联的其他党派的历史。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党史研究还要具有世界的眼光。一方面,中共党史本身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一部分,只有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总体上去进行考察,党史研究才能全面、深入;另一方面,要把中共历史放到世界范围内进行考察,在宏观比较中展现党史的独特内涵。同时,应主动了解海外中共党史的研究动态,既要重视进口和翻译外文书刊,密切注意海外中共党史的研究动态,还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他们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澄清或批判,同时向全世界传播党的光辉历史。 纵观与横观这两个观察和分析问题的维度,共同构成党史研究的历史坐标。纵观表明纵坐标上人类历史发展的持续性和顺序性,横观表明横坐标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广延性,在实际研究运用中二者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密切相联。司马迁提出治史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钱穆称要“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30),都旨在说明只有在纵向和横向上同时开阔视野,会通古今中外,才能探求史实背后的规律和意义。 (三)研究方法要得当 整体性研究不是抽象的思辨,而是通过多种多样的具体研究方法进行的。有论者指出,方法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主要承担着三项基本任务:一是全面地把握历史事实;二是深刻地分析历史现象;三是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31)。而每一项基本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整体性原则:要全面地把握历史事实,就要把历史的过去与现在,前进与曲折,正面与反面,敌人与朋友,领袖与群众,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理解;挖掘历史现象的深层本质,同样离不开在横向与纵向上对事物的诸多因果联系,以及不同层次问题进行非线性的立体考察;要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发现社会和政党运动的规律,就尤其需要运用整体性思维。在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法国年鉴学派的作用无疑具有先锋性。在研究方法上,年鉴学派主张广泛应用历史学以外的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计量方法和比较方法,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并倡导用“问题史学”代替传统纯客观的“叙述史学”,强调历史学与现实的联系。党史研究除了要借鉴年鉴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外,还需要注重和把握以下几种具体研究方法。 一是比较研究法。党史研究要克服狭隘性,尤其需要具有大跨度、长时段、大时空的比较视野。毛泽东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运用比较研究法研究党史的典范。他指出,“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套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32)比较研究的实质是“同中求异,异中求同”,从而全面、深入地认识事物的面貌和本质。目前的党史研究成果,大都对于敌方在革命进程中的活动反映不多,难以展现革命斗争的复杂过程;就中外政党的对比研究来看,大部分学者缺乏对国外中共党史或研究情况的系统了解,使其研究无法与之产生交流。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共党史学要真正面向世界,就必须具有恢弘的世界意识,及时了解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信息和成果,以加强中外中共历史学的比较研究(33)。 二是系统研究法。系统研究法是一种提倡整体观和综合观的科学方法,它立足于整体论,讲求从多时空、多侧面的复杂网络交叉结构中认识事物,补充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联系和因果关系的唯物辩证法,对于帮助我们从整体上考察党史中复杂多变的历史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使我们从信息、因果、反馈、控制、顺序和网络等多角度加以探讨,改变传统的“分析——综合”的线性思维方式,树立“综合——分析——综合”的新思维方式;其次,它为我们提供了党史研究数量化的中介环节,便于作出严格的逻辑证明,以及促进国家对党史研究规划管理的科学化;最后,从全球化的角度看,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为我们观察和研究党史,提供了开放性思路和世界性眼光,成为我们开展科学研究之必需(34)。可见,运用系统分析法研究党史,可以完善中共历史学方法论体系,有助于解决党史研究中一些新的问题。 三是跨学科研究法。中共历史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学科,它需要党史研究突破自身的知识边界和学科壁垒,融合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为一体。正如年鉴学派所称,历史的综合作用表现在历史学科应改变与其他学科的分裂状态,把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语言学等吸收到自己的学科中来,使他们成为研究历史的辅助学科(35)。有学者指出,党史这门学科要成为枝繁叶茂的长青之树,而不是一棵被剥得净光的树杆,需要党史工作者从学科本身的封闭状态中走出来与其他学科“通气”,进行多学科、多层次的综合研究(36)。但跨学科研究并不能采取“拿来主义”,在运用时需要注意其“有效性”和“有限性”。前者主要是针对一些学者在新概念或新术语的运用上给人“生搬硬套”、“食而不化”的印象而言;后者则要求注意到某种单一方法的有限性,坚持“有限使用”的原则(37)。也就是要求党史工作者在运用跨学科方法时不能盲目套用,而应将经验事实与概念体系灵活衔接。 (四)正确处理学理上的两个关系 运用整体性框架研究中共党史,需要正确处理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整体性研究与个案研究的关系。尽管整体性研究与个案研究在观察问题的角度和研究范围方面存在差异,但二者之间并不是黑白对立的,而是具有相对的统一性。一方面,个案研究是整体性研究的基础。个案研究所记录或确定的局部现象,可以为深入研究整体结构提供帮助,与宏观历史研究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并成为整体史的组成部分或者观察总体历史的一个视角和途径。个案研究所冲击和挑战的主要是“不当”的宏大叙事,而不是宏观研究本身(38)。另一方面,个案研究须“微中见著”,其最终建设目标应回归到整体史层面。也就是要求个案研究者要有一个关照宏观的问题意识或学术自觉,否则只能使其研究陷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尴尬境地。正如彼得·伯克所说:“微观历史研究若想规避回报递减法则,那么其实践者应多关注更大范围的文化,并展示小社区和大历史趋势之间的关联。”(39)因此,整体性研究所反对的也恰是过于细化的“碎片化”研究,而不是碎片本身。 二是学科整体发展与深化专题研究的关系。二者之间实质上是党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的关系问题。中共党史研究的整体发展不能建立在“大而空”的基础上,要求实现与各个领域的专题研究的辩证发展。党史学科的整体发展是靠深入的专题研究来推动或作为基础的。毛泽东指出,要综合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40)。只有研究好中国社会诸领域的特点及变化,以及每一领域内的多个层次问题,才能为整体史的研究提供基础性的、全面的资料,从总体上了解党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党史只有对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演化和变革进行分析,突破政治、经济、文化三足鼎立的著述格局,才能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原因,说明社会整体的历史全貌和历史发展趋向(41)。反观之,整体史又为深入研究社会生活诸方面的专史打下基础。研究任何一门专史,必须具有整体观念。布洛赫指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42)换句话说,只有通过众“领域”的协作,才能接近整体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党史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决定了党史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一条线或一个面,而是要具有多维的“立体空间”。对于这些空间领域,我们可以从总体上把握,并具体分析各个领域内的问题对历史整体发展带来的影响和推动,以便最终从一个新高度去总结历史经验。 总之,整体性是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一种思维方式。它以系统、动态的视角和思维,打破了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线性和静态的视野局限,弥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对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坚持整体性,要求在党史研究中坚持全面性,反对片面性;坚持客观性,反对主观性;坚持科学性,反对随意性。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②《庄子·齐物论》。 ③普里戈金:《从存在到演化》,《自然杂志》1980年第1期。 ④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页。 ⑤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页。 ⑥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63页。 ⑦[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82页。 ⑧[美]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林康义、魏宏森译,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⑨如吕国忱:《整体性原则·方法及应用》,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⑩贝塔朗菲指出,“一般系统论是关于‘整体’的一门科学。”也就是说,一般系统论在实质上是对“整体”和“整体性”的科学探索。参见[美]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林康义、魏宏森译,第34页。 (11)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房广顺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韩庆祥等:《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上、下,《哲学研究》2012年第8、9期等;张雷声:《从整体性角度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学术界》2010年第6期;梁树发:《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的实质》,《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8期。 (12)如金观涛:《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贵阳师范学院学报》第1~2期;李怀义:《中共党史研究的系统论视角》,《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年第3期;丁卫平:《系统科学方法与中共党史研究》,《长白学刊》1989年第1期;陆云彬:《毛泽东的系统论思想初探》,《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陈日增:《系统方法在党史研究中的应用试探》,《福建党史月刊》1990年第9期;齐卫平、宋瑞:《试析系统论思想与党的建设科学化》,《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等。 (13)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学典、郭震旦:《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行龙:《克服碎片化,回归总体史》,《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李金铮:《整体史:历史研究的“三位一体”》,《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14)如周积明、宋德金主编的《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乔志强的《深化中国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5)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2007年版)一书中,倡导“大历史”的研究视角,主张不以道德论史,不以考据为文,而利用归纳法在纵横捭阖中梳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也就是注重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勒和对历史特质的书写。 (16)程美东:《从大历史的视角来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发展》,《兰州学刊》2012年第1期。 (17)郭德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新进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2期。 (18)胡绳:《从党的历史看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5期。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 (20)孙国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系统观》,《齐鲁学刊》1993年第6期。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 (22)《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上、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5期。 (23)梁柱、龚书铎:《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24)《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4页。 (26)《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27)许恒兵:《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演进、危害及其批判》,《思想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28)杨凤城:《党史研究的规范、视野和多层互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29)欧阳淞:《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0期。 (30)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第11页。 (31)高树森、孟国祥:《论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32)《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页。 (33)由梁怡、李向前主编的《海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是建国以来首次综合述评近50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状况和著述的专项成果,代表了国内党史学界一些学者在该方面的努力。 (34)李怀义:《中共党史研究的系统论视角》,《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年第3期。 (35)吴泽主编:《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页。 (36)陈浮:《中共党史研究的困惑与希望》,《求索》1988年第4期。 (37)侯松涛:《中共党史研究: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审视》,《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1期。 (38)张海荣:《中共党史学个案研究的若干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5期。 (39)[英]彼得·伯克:《历史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40)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60页。 (41)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42)[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家辩护》,张和声、程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标签:中共党史论文; 历史虚无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认识错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