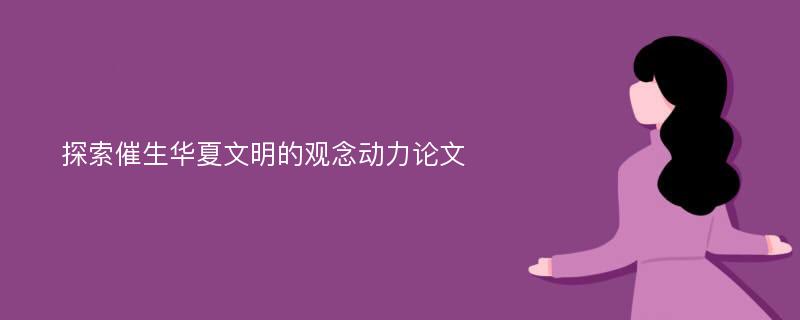
探索催生华夏文明的观念动力
叶舒宪1,2
(1.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200240;2.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摘 要: 探索文明发生的观念动力,是国际社会科学的前沿课题。文章从玉石神话信仰方面,通过解析三个文学故事,从中探究催生华夏文明的观念动力,并提出有关华夏文明发生的新理论建构的三个条件:一是其知识视野必须超越汉字文献的限制,真正做到能够贯穿到五千年上下的历史深度;二是能够得到本土的系统的新材料的支持;三是能够兼顾该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物质。
关键词: 玉石神话信仰;华夏文明;价值观;观念动力
一、聚焦催生文明的观念动力
一个文明古国是怎样产生的?常见的解说策略在于陈述其发生的历史过程。对于一切生活在中国通史之父司马迁之后的古人来说,理解这样的问题也较为简单,没有多项选择和思考的必要,只需看首部国家通史《史记》的第一篇章《五帝本纪》,就有西汉官方权威学者给出的现成标准答案:华夏国家以黄帝炎帝为始祖,黄帝之孙为颛顼,其后三帝为尧舜禹。知道了这五帝的传承谱系,也就相当于理解了华夏文明的发生。对于古代知识人来说,信仰观念驱动的问题似乎并不存在。
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文献史学的正统性、权威性都受到强烈的挑战。先有新文化运动要彻底打倒孔家店的过激要求,随后又有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要否认以三皇五帝为首的国史开端谱系。直到20世纪后期,大量的新材料出现,终于迎来走出疑古派的阴云笼罩状态,重建中国古史脉络的学术追求。不论是20世纪末期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是21世纪初再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都体现着国家意志支配下,要重新认清华夏文明由来的当代学术诉求。
从学界目前进展情况看,无论是给最早的三个朝代确定精确的年表断代,还是在先于夏代的史前期寻找都城遗址和文明国家的象征物,学界主要关注点聚焦在华夏文明出现的时间和空间坐标方面,很少有人去思考:驱动一个文明发生的核心要素和动力是什么。换言之,在文明起源研究现状中最缺乏的短板方面,是文明发生的动力学视角和相关的理论阐释。这方面首先需要一个因果关系层面的问题澄清:是什么因素在驱动着史前各地的各自为政的部落社会,终于走向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巨大范围内的统一文明国家的?这样的质问,就会将研究者思考的方向,引向国族的文化认同问题。这显然要比年表和时空考证更有难度。
笔者为此撰写“玉成中国”三部曲① 参见拙著《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著述,遵循知识社会学的系统研究思路,尝试从“神话—观念—行为—文化特质”这样一种系列因果链条的解释系统中,透视华夏古文明特质的由来,而不再停留在泛泛而论或主次不分的文化时空描述方面。希望在文明发生的时空展开过程中透视到具有驱动作用的主因素线索,即有关玉石被神圣化的一整套神话信仰观念。
观念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能动性要素作用,是自现代社会学奠基人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两位大师以来,以及阐释人类学派的领军人物克里福德·格尔茨以来,国际社会科学界关注的前沿问题。新教伦理观念如何驱动资本主义兴起,全球化观念与地球村的构成等,成为一时之焦点。而国内学界则因为受制于僵化理解下的唯物主义,较少有学者用心于这方面的思考和探索。
漕河渡槽位于河北省满城县西北9km处,交叉断面以上流域面积588km2,是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上的一座大型交叉建筑物。漕河渡槽全长2300m,建筑物级别为1级,地震设计烈度6°。
本文从启发本土文化自觉的意义上,将围绕三个典型性的中国故事而展开,意在凸显神话观念所铸就的文化潜规则,如何在暗中支配着国人的言论和行为取向,从而塑造着十足带有“中国性”的因果叙事模型。三个故事皆来自文学方面。一个是以往曾引用过的,另外两个则分别取自作家创作和民间传承:其中的《红楼梦》一个案例,属于尽人皆知的小说名著;另外一个则出自罕为人知的云南少数民族的民间口传文学。三个故事要来源不同,空间跨度覆盖北方和南方,却足以说明同一个道理:是什么样的核心物质和核心精神要素,暗中支配国人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一旦能够找到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华夏文明大国就可以找出一种文明发生动力学阐释的基本理论架构。
到宝岛台湾旅游必看台北故宫的珍宝,其中最著名的清代玉器叫做作“翠玉白菜”。只因为“白菜”谐音“百财”,这就给这件古玉带来极高的人气。窃以为,能使得翠玉白菜这样的古代文物重新被激活的最佳方案,出自文学人类学方面所指称的“第三重证据”,即作为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头传说。下面即链接一下南方民族白族流传的《玉白菜》原文:
真核生物通常分为植物、动物、真菌和被称为原生生物的微小多细胞生物4个界,涵盖了地球上找到的几乎所有真核生物。但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达尔豪斯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日在英国《自然》网站上发文称,他们发现了生命之树上的新分支——一种以前未知的新型真核生物,或许应该使其所在的“门”升级为新的“界”。研究人员将新发现的生物称为Hemimastix Kukwesjijk。从外观上看,新生物拥有一个椭圆形的身体,周围是成排的线状鞭毛。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3D放大观察,这种生物有点类似毛状南瓜种子。
二、从三个故事看华夏文明价值观
第一个故事是曹雪芹《红楼梦》的“通灵宝玉”叙事。小说人物塑造根据二元对应原理,构思出男女主人公的三角关系:一个是“宝玉对黛玉”的关系,另一个则是“宝玉对金锁”的关系。前者充分显现文化大传统的根深叶茂,以玉为至高价值;后者则突出文化小传统中后来的贵金属崇拜。大、小传统对接之后,玉和金两种物质成为一种绝配,用老子的话说就是“金玉满堂”,由此成为人间财富追求的一种理想。此后,玉原来独享的神话性和神秘性蕴含,也就相应地移植或嫁接到了金银铜等稀有金属上面。世俗社会以为金玉组合乃是天命注定的,于是就催生出了“金玉良缘”和“金童玉女”等各种匹配组合性的成语。
由此看,《红楼梦》描写贾宝玉自降生到人间的一刻,就口含通灵宝玉。此一细节预示这个男孩天命就有“玉”的注定。不过周围的人们还是觉得不可思议般的奇特。玉毕竟是稀罕的好东西,贾母则据此判断,这位含玉而生的孙子,日后长大成人一定不会是凡夫俗子。因此把这个孙子当成受宠若惊的宝贝儿,使得小小的他,就在大观园的红粉国中获得众星拱月般的独特地位。
在曹雪芹的描述中,贾宝玉的玉自然是天赐神物一样的东西。贾府内外的人都知道这位公子生来就口含神玉。但是玉佩上所写着的字样内容,就不是贾府内外的一般亲朋好友所能够知晓的。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代表个人命运的珍宝,一般也都是秘不示人的。尤其是命运相关的神秘性,更不会随便让他人所熟知。不过,宝玉这孩子自己起初对这玉的态度并不明确,当他知道别人都无玉,惟有自己有玉。便对这样的特殊性感到不自在。当远方的亲戚妹妹黛玉进入贾府,宝玉就忍不住好奇地向她发问:妹妹你也有玉吗?黛玉只能如实招来,说:那玉是稀罕东西,岂能人人都有。谁知宝玉听说和自己一样名字中有“玉”的黛玉,其实没有玉,就好像被名字所欺骗了一般,立刻丧失常态,发狂般地要摔掉自己的佩玉。贾母只好命人立刻捡起那块玉,再小心翼翼地给宝玉戴上。还要骗宝玉说,林妹妹原来也有玉,只不过她将那佩玉给母亲陪葬用了。宝玉的精神状态这才恢复正常。晚间宝玉的丫头袭人见黛玉还不睡,过来探望。黛玉和袭人也谈到那块神奇的佩玉。黛玉表示以后有机会再设法仔细看个究竟。
中国人的圣物想象有其深远的文化根源,这种想象越是古老越是单一,而且对后世产生难以磨灭的深远影响。作为说明,下面引出第二个故事——满族民间故事《细玉棍》:
清代社会继承了传统观念中的金玉良缘说,这通过贾府上上下下的舆论氛围,给黛玉脆弱的心灵带来更大的压力。她只能自叹命运不济和生不逢时。黛玉的名字里没有金,身上也有没有与生俱来的佩玉。虽说名叫黛玉,也只能暗喻着一种上古时期曾经流行的墨色玉。而在崇尚“白玉为堂”的清朝现实中,能够欣赏墨色玉的人,可谓是凤毛麟角吧。生不逢时的黛玉,如何能够同自己的情场对手薛宝钗展开竞争呢?宝钗作为豪门巨富之家的千金小姐,佩戴这豪华雕饰的金锁,这也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作者特意还在那件金锁上安排八个篆字,居然和通灵宝玉上的八个篆字是完全匹配对应的。
曹雪芹让宝钗自己不说金玉匹配的话,而是将这个点题一般的说法安排到宝钗的丫鬟莺儿口中说出来:金锁上的八个字和通灵宝玉上的八个字是对起来的呀!金玉成对啊!林姑娘听了莺儿的话,十分懊恼,却有口难言。白先勇对这一段金玉匹配的情节特别看重,他分析说:
金子是最世俗的东西,但真金不怕火炼,也是最坚强的东西。玉还可能碎掉金子不怕炼。别忘了,最后贾府要靠宝钗撑大局。贾府衰败,王熙凤死了,贾探春远嫁,撑起贾府就靠薛宝钗。难怪薛宝钗步步为营,一举一动都合乎儒家那一套宗法社会的规矩。……如果往大处看,也只有她能撑,那两块玉——宝玉、黛玉,都撑不起来的。只有这把金锁能够撑大局。所以金跟玉这么两个人一比,就比出一段很重要的姻缘。① 白先勇:《白先勇细说红楼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6-107页。
预应力张拉过程中,应注意以下问题:(1)预应力筋放张时混凝土强度、弹性模量和龄期应符合设计要求,放张之前应将限制构件位移的模板拆除;(2)预应力筋的放张顺序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无要求时,应分阶段、对称、相互交错地放张;(3)预应力筋的放张速度不宜过快;(5)放张后预应力筋的切断顺序,应由放张端开始,逐次切向另一端。此外,在预紧张拉过程中,要确保钢绞线高度的绷紧性,并避免钢绞线出现错位问题。因此,对于预紧力的大小这一问题,必须要予以高度重视,防止钢绞线出现缠绕现象。
要说作家创作给民间玉宝故事增添了什么要素,那就是玉石神话与文字神话相结合的生动例证。《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含玉而生的那块玉,其正面横向刻写的四个汉字“通灵宝玉”,一般都当作文学家子虚乌有般的虚构想象。比较神话学视角则可确认,那是来自华夏史前石器时代古老玉石信仰的回音。以玉为“宝”的观念不用远求,就潜藏在汉字“宝”从玉从贝的造字建构中。换言之,离了玉字,就没有宝字(详细的“宝”字词语分析,参看拙著《玉石里的中国》第九章)。后起的金银等贵金属虽也被视为珍宝,但是古人早有“黄金有价玉无价”的古训。至于“通灵”的解读,需要认识到自先秦时代“灵”字即指神灵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指出:灵与神灵、灵与巫师,以及祭仪上代表神灵的尸具有一致性。常宗豪引用王国维观点对《楚辞》中的灵巫通神现象做出系统研究。参看氏著:《楚辞——灵巫与九歌》,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第33-63页。 ;“通灵”即通神。
水利施工现场由于具备显著的复杂性,因此亟待对此予以综合性的施工管理。通过推行现场施工监管的举措,应当能在根源上消除某些潜在隐患或者其他施工风险,确保水利建筑物应有的安全性并且杜绝某些额外的水利建设成本耗费。由此可见,施工现场管理举措应当能够渗透在全过程的水利施工中,其中包含了如下的施工现场管理关键技术:
宝玉的佩玉虽说是块顽石,只因为僧道的神奇变化,这块石头被点化出了灵性。故曰“通灵”。玉石上既有字样说明功能,也有可穿绳系挂的孔洞,其表面还泛着红色,纹理中透露粗暗暗的花纹,而且象酥般光润。
看了下面讲的民间玉宝的故事,再去对照《红楼梦》中的“通灵宝玉”,可知作家曹雪芹的文学想象与民间故事想象具有惊人的一致性。那就是将玉这种物质当作超自然的神意之象征:美玉乃由天神降下人世间,作为体现神灵意志及各种美好价值的某种神秘符号。
和方差(SSE)为3.838,确定系数(R-square)为0.962 1,调整后确定系数(Adjusted R-square)为0.957 4,均方根(RMSE)为0.399 9。
山、臻摄的字也有读作[ŋ]尾的,如:摊 thaŋ1;前~后 sεŋ2;殿 tεŋ6;锦 keŋ3。咸、深摄也有读作[ŋ]尾的,如:蚕 tshεŋ2。
熟悉上古史的人,都知道秦始皇开创传国玉玺制度,一看就知道通灵宝玉上的文字之出处。至少后四个字是曹雪芹照抄来的。金锁上的后四个字,也和前面两个意思相同。只是表示祝福的对象不是男性,而希望女性小姐能长寿的意思。宝钗一家进京的目的是待选、作生意销账、躲避人命官司。但是宝钗一家长期住在贾府。莫非是为了这个姻缘匹配?
如果宝钗对宝玉没有喜爱?她为何能念出玉上的字?并且念两遍。她应该只看不出声。这样她的金锁自然也就没人看了。
金锁上的字怎么来的?宝钗父母故意编造的。为什么?要和王夫人结成娃娃亲。具体表现就是让双方的儿女带上彼此合成一对的物件。只是宝玉的玉是天生的。宝钗的锁是父母人为打造出来的。贾政、贾母他们对此都不知情。不然,黛玉也会有八个字的物件带在身上吧。
他惊叹外表其貌不扬的孔家庙,却有着宏大的格局。整个孔庙坐北朝南,分东西中三条轴线,中轴线上有孔庙大门、大成门、甬道、大成殿、东西庑等建筑,东线排列着孔塾、崇圣门、崇圣祠、圣泽楼;而西轴线上五支祠、袭封祠、六代公爵祠、思鲁阁等建筑保留着宋以来的形制。
宝钗的锁怎么来的?丫头莺儿对宝玉说,是一个癞头和尚给的八个字。这种说法和宝钗的说法出入比较小。宝钗没说是谁给的字。薛姨妈的说法是癞头和尚给的金锁。自然锁上的字也是原来就有的。宝钗的哥哥说法是:薛姨妈说了妹妹宝钗将来的婚姻必须和有玉的公子相配。现成的证据就是,宝钗替宝玉说话。这就把宝钗、薛姨妈都气哭了。宝钗哭了一夜。第二天。薛蟠向妹妹、母亲赔罪!但是他没说昨天他说的是自己瞎编的。只是说了一些迷信话。
从表3看出,不管是春季还是秋季,蚕蛹中谷氨酸、天门冬氨酸稳居氨基酸含量的前2位,相对含量最高;赖氨酸、亮氨酸、组氨酸、酪氨酸等4种氨基酸在第3~6位,位次相对稳定。而胱氨酸、蛋氨酸和异亮氨酸相对含量最低。赖氨酸、精氨酸、苯丙氨酸、丝氨酸的位次变化较大。该结果与陈义安等[7,12]的研究较为一致。
宝玉的玉是神奇的。玉上的字让人更神奇。我们知道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上面有八个篆字是丞相李斯镌刻上去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通灵宝玉上的字是什么呢?书中直到描写宝玉正式和宝钗见面才向读者揭示出来。那玉上的字通过宝钗的眼。宝钗的嘴里反复两次念出来。“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宝钗的丫头莺儿听到玉上的字。立刻说和姑娘宝钗锁上的字是一对。这样宝玉便觉得很好奇,一定要亲自验证一下。宝钗说不过是别人给的吉利话儿。她嫌金子沉甸甸的没趣儿。所以錾上了字。无奈在宝玉的执意要求下,宝钗让宝玉看了金锁。这件长命锁确实不是特别稀罕的奇珍异宝。但是锁上写明的那八个字,确实在让宝玉感到非常神奇。那八个字是:“不离不弃,芳龄永继。”这一回的故事题为“比通灵金莺微露意”。二宝看完彼此的宝贝。黛玉就闻讯来了。她没看见二宝的行为。不然,非把黛玉的醋坛子打碎不可。
从信仰角度看,玉之所以为宝物,原本就在其通神的宗教法器功能。佩戴美玉能够保佑佩玉者的信念,在华夏传统中至少流行了近万年。贾宝玉的通灵宝玉背面还镌刻着十二字,分别道出玉石神话的三项基本原理:辟邪除祟,治疗疾病和预知祸福。这三点都是史前巫医和占卜师一类神职人员的职司,因为他们才是圣俗两界和神人之间的沟通中介者。玉石神话的起源,当然离不开巫师贞人一类社会宗教领袖。国内玉学界新近认识到的“巫玉”之说② 杨伯达:《巫—玉—神泛论》,见《巫玉之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27-256页。 ,为今人以“同情之理解”的方式重新进入玉石神话时代,在地质矿物学和考古学以外,标示出宗教学和神话学的思考路径。用宗教学家马利亚苏塞·达瓦马尼的说法:“对于神灵的信仰通常包含着一种需要与之交流以保障其驱邪避祸,财运亨通的意义。”③ [意]马利亚苏塞·达瓦马尼:《宗教现象学》,高秉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4页。 玉石神话观的普遍意义就在于,史前初民以为玉石宝石就是充当神灵载体作用的实物符号,因而具有特殊的通神通灵和庇护保佑作用,魔法石和护身符的流行观念即由此而来。
黛玉和宝玉,就这样以玉结缘,开始了几年时间的青梅竹马和两小无猜的生活。有一天,宝玉的姨表姐薛宝钗来到贾府,并长住下来。“钗”字从金,按照古人的观念金是玉的绝配。曹雪芹就这样让安排人物关系,让和宝玉同名的黛玉,渐渐意识到自己的情敌更具竞争优势。而且宝钗在性格上雍容大度,知书达理,显然比惯于使性子的自己更得人心。黛玉觉得宝钗在各个方面都比自己胜出一筹。于是就对宝钗心生妒忌。每看到宝玉亲近宝钗,都会增加醋意,心态终于失衡,陷入精神的漩涡。其实还是作者曹雪芹有意不让她解脱情债。就这样,黛玉和宝玉的好日子走到尽头,接踵而来的是不断的猜忌、斗气和争吵。两小无猜的纯真状态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一个老头有三个儿子。老大两口子贪心,老二两口子奸诈,老三两口子憨厚。因为老三愿意周济别人,老头总想将他撵出去过。一天,他把三个儿子叫来,每人给了三百两银子,让他们出去找事干,三年后将银子翻九番来见他,拿不回来的赶出家门。老大在外面开酒馆,在酒里兑水,得到高利息。老二开了个山货铺,低买高卖,钱挣无数。老三为照顾在路上遇见的一个病老头,整整伺候了三年,只得了一根玉棍留作纪念。当他们哥仨回家时,由于老三没挣到钱被赶出家门。正在他们走投无路时,细玉棍显灵为他们变出了水晶宫一样的房子和热腾腾的饭菜。当老头和另外二个儿子知道后,千方百计要得到这个宝物。最后,他们用全部财产换得了玉棍,住上了老三的漂亮房子。但是宝物在他们手里怎么都不管用。水晶宫样的四合院也缩到了地里。他们只好冻在田野里。这个故事流传辽宁岫岩满族自治县。由于这个县以产“岫岩玉”闻名,故事更增添了几分地方色彩。① 季永海,赵志忠:《满族民间文学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版社1991年,第66页。
这一则来自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满族的民间故事,将一根细玉棍作为来到人间的神灵化身,并作为对三兄弟中德性最好的老三所行善事的报答物。故事遵循一般的神秘宝物的情节,充分体现出将玉石神圣化的普遍性信仰。细玉棍的存在,成为老天爷或神灵赏罚善恶的意志之象征,正所谓“天眼恢恢疏而不漏。”换言之,神灵不直接出面,而是幻化成圣物出现。细玉棍虽不及金银财宝那样耀眼醒目,却能够帮助善人心想事成,脱贫致富;同时也能够鉴别和惩罚恶人,让他们遭到报应,倾家荡产。可以说出自满族民间幻想的这件细玉棍,要比贾宝玉的通灵宝玉更有伦理道德原则,更体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社会性正义诉求。由于玉棍充当神的化身,所以故事中也就无需佛教僧人或道教道人出来捧场或表演了。玉棍即是潜在的玉教信仰的现身说法者。
救死扶伤,再加上生命永恒,这就是白族民间故事想象的玉白菜之文化功能。对照基督教的《新约圣经》,不难看出,在西方社会行使着扶危济困和治病救人作用的是救世主耶稣基督;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玉石便可以替代神佛,行使同样的功能。
这种新理论需要满足如下三个条件:一是其知识视野必须超越汉字和汉字文献的限制,真正做到能够贯穿到五千年上下的历史深度。二是能够得到本土的系统的新材料的支持。三是能够兼顾该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物质。
很久很久以前,在苍山脚下,一个村庄里住着一户姓俞的人家,只有母子二人,母亲七十几岁了,人称俞大娘,儿子俞大香,依靠上山砍柴和卖柴维持生计。一年春天,母亲患病,病情日渐加重。儿子忙得东奔西走求医问药,但仍不见效。一天夜里,守候在母亲身边的儿子恍惚入梦,升高到苍山之巅。遇到一位白胡子老人从天而降,对他说:“在苍山中和峰脚下有一口红龙井。井底有石门,只要轻扣三下门环,石门即自动打开。进入石门后拐三个弯就到了玉白菜生长的地方。有四条红色蛟龙守护。你对它们说你只要去掐一小块玉白菜的叶子,就可以了。带回去放在母亲嘴里含着。含一天,百病全消;含两天,恢复健康;含三天,白发转黑,落齿重生。”俞大香听着听着,不觉一觉醒来,按照白胡子老人说的话,去找玉白菜。他下到红龙井底,摸到石门,惊喜地来到玉白菜面前,向四条红蛟龙说明来意,得到准许,掐下一小块玉白菜叶片,带回家给要母亲口含。到家后取出玉白菜叶片一看,已经不是白色的,变成碧绿的一块玉石。他顾不得思量,立马放进母亲嘴里。母亲当天就痊愈,次日恢复健康如初。第三天,白发转黑,落齿重生。这样的奇迹事件传扬开来,远近的人们都来请求一睹玉白菜的芳容,或请求借给病患者入口一含。消息传到南诏国都城,国王立刻派人把俞大香传入宫中,让他拿出玉白菜叶片为身患重病的王太后治病。果然玉石入口就获得药到病除之效。国王高兴不已,封赏俞大香为“进宝状元”,并赐金银财宝,骑着大马衣锦还乡。都城里的富豪贾家藻看到这场景,一心要将玉白菜据为己有。于是他奔向苍山中和峰下的红龙井,来到四条红蛟龙守护的玉白菜前,谎称自己的母亲患病需要治疗,索要一小片玉白菜的叶子作为灵丹妙药。四龙也同意了他的请求,谁知他贪婪本性不改,双手拉住一片玉白菜的叶子猛烈摇晃,叶子被拉倒在地,引发地震。四条蛟龙勃然大怒,闪电般就奔过来将贾家藻杀死。据说,一直到现在,那棵玉白菜依然在大理城中心的五华楼下,支撑着整个大理坝子。但是自那片叶子被拉倒以后,大理就常常发生地震了。② 以上引文为笔者根据《玉白菜》文本压缩改写,原文:1979年洱源城石音口述,李中迪记录。《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云南·大理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引自杨海涛主编《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云南卷》送审稿,2018年9月,第93-95页。
白族的《玉白菜》故事非常生动地表现出玉石所蕴含的正能量,玉石不仅具有通神通灵的效应,而且直接表现为救死扶伤和拯救生命的奇幻功能。这不能不说是东亚洲特有的深厚无比的万年玉文化发展的最大精神动力所在。
玉白菜这个叙述母题,直接将作为无机物的玉石和作为生物种的白菜组合成为一个神话意象,并让它承载着世间最神奇的正能量,能够让一切生命体得以生生不息。来自民间口传文化的第三重证据,给古代传世文献《山海经·中山经》中基本无解的黄帝播种玉石的叙事,也能一下子获得重新激活的现实语境,变得容易被今人所理解和接受。玉荣、琼花、琼枝玉叶、玉树临风,球琳琅玕,金枝玉叶,所有这些古汉语成语都不是哪个文人随意创作出来的,而是植根于万年玉文化的想象中的。植物也好,动物也好,作为生物体的生命之始源,都可以被华夏神话思维追溯到承载着神力和正能量的玉石。换言之,文化符号的编码是分层级展开的:先有昆仑山和田玉的实物,催生出昆仑瑶池的仙界想象,再有人格化的掌握不死秘方的西王母想象,最后才有西王母蟠桃会的想象。总之都指向一个神话理想:生命的永生不死性。
第三个故事是中国南方云南白族民间故事《玉白菜》。
三、华夏文明奇观之金缕玉衣
华夏文明以其持久不断的巨大生命力而著称。历朝历代更替不断,革命加战乱,本土造反加外族入主,但华夏文明的主脉却始终不绝如缕,能够在历经各种磨难之后,不断自我修复,其最持久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凝聚力是怎样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一类挂在国人嘴边的超级流行的国粹措辞,其实已经将某种深层的华夏文化价值观和盘托出了。
物质的玉石与精神之弘毅之间的固定联想,自儒家以来也有两千多年的积淀,这绝不会是任何个人作家或诗人所能够发明出来的。在此充分体现出来的,是以潜规则形式而存在的文化文本的规定性作用,而不是个人独创性的作用。玉文化发展在两汉时代迎来前所未有的局面:一方面是汉武帝通西域后,将国家海关设定在河西走廊西端链接新疆的玉门关,使得优质和田玉源源不断输入中原,给玉器生产带来空前的大繁荣;另一方面,以玉代表天和永生的神话观念为基础,在汉代刘姓诸侯王家族里流行金缕玉衣这样奢侈至极的帝王级丧葬制度,给万年玉文化长河留下空前绝后的一道别样风景。
前几年国内文物收藏界轰动一时的大事件,便是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模拟汉代金缕玉衣的赝品大案,造假者居然能够凭借金缕玉衣的巨大声誉,直接从银行骗得贷款数以亿计。甚至连故宫的玉器研究专家也被卷入此案,因为收受红包而给赝品金缕玉衣开假证明。
古代金缕玉衣的制作,遵循着什么样的设计理念呢?在拜金主义盛行的当下市场社会,很容易理解为皇室贵族死后的炫富行为。其实并不尽然。金缕玉衣,乃华夏古老的玉石神话信仰在汉代催生的新神话现象。其当初设计理念虽没有留下说明,却能从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的对照中,得到神话学的认识。汉代顶级殓服用玉衣,因等级不同,分为金缕、银缕、铜缕、丝缕几种。几种玉衣在考古发现中都有实物。自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出土两套金缕玉衣,迄今已发现的玉衣不下四五十件。其中完整无缺的玉衣仅有四件,除满城的两件之外,还有广州南越王赵眛墓出土丝缕玉衣一套,徐州火山刘和墓的银缕玉衣一套。较完整的还有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一件,河北定县西汉刘修墓一件,后者作为国宝级文物,进京到国家博物馆展出。
金缕玉衣的出现,堪称世界工艺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观。玉衣一般采用来自新疆和田玉料,先制作出两千多件方形玉片,四角钻孔后用金丝编缀而成。不论是所耗费的珍稀玉材还是大量工时,都让人感到匪夷所思。早在汉末三国时期的战乱中,这些神秘的玉衣就已被大量盗掘,并记于史书,称为“玉匣(柙)”。如《三国志·魏志·文帝纪》云:“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说的是盗墓者为了获取黄金,不惜用火烧熔化黄金的方式处理玉衣,连玉衣内的尸骨都烧尽了。如今在各地的古玩市场上,常有零散的玉衣片出售,这里面有真有假,眼力好的收藏者不难淘到一些真的玉衣片。只要玉质好,盘玩之后还会变色、出油、通透,带来更多的遐想空间。
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土壤破坏日益严重、作物品质难以提高的现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使“土壤修复改良”成为农资行业一个崭新的风口。一时间,市面上的有机肥和微生物菌剂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虽然当前有机肥市场上鱼龙混杂,产品质量良莠不齐,但仍有很多企业凭借优秀的品牌文化、过硬的产品质量,打开了市场,赢得了口碑,金沂蒙就是其中之一。
玉衣葬俗的观念动机为何?其实在殷纣王的临终举动中,已经多少透露出一些观念的端倪来:以宝玉缠绕在自己身体上,然后点火自焚。只要知道火苗是能够克服万有引力定律,熊熊地向上方运动的,则殷纣王的借火儿升天之梦想,也就不难体会了。试问,如果没有宝玉缠身的细节,殷纣王还能顺利完成他的升天梦吗?本书第三章“万岁的中国”里给出两个五千年前的墓葬景观,都是借助玉礼器是力量祈祝死者魂归天国的极好例子。参看之下,原理不变,而汉代玉衣的制作技术集大成性,则显得尤为突出。在殷纣王那里,众多的宝玉平时都深藏在宫中,并不当衣服穿;只是在临终之际拿出来当成临时上身的“玉衣”。这临时裹身的“玉衣”虽然毕生只穿这一次,而这一次就意味着升天的永恒。
比“玉匣”更早一些的称呼叫作“含珠鳞施”,见于秦汉之书《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这个比喻性名称透露出神话的仿生学观念:玉衣的构成之所以用数以千计的片状拼接为一体,是为了让死者模拟性的变化成鳞介类的水生动物。相传象征不死的千金之珠藏在龙口之中。而鱼鳖一类的鳞介动物,在神话中普遍视为能够长寿或死而复活的神物。
从比较文明史的视野看,金缕玉衣的制作和古埃及金字塔的设计理念一样,都是出于统治者死后灵魂升天的信仰观念和神话想象。只不过升天的方式和凭借物质不同而已。中国先秦的冥界神话将地下死者之国称为“黄泉”,汉以后又称“九泉”或“黄垆”等,指黑暗的大水围绕的状态。死者下黄泉之旅,要模拟鱼龙之类的水生动物,也就顺理成章。《吕氏春秋·节丧》云:“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高诱注:“鳞施,施玉于死者之体如鱼鳞也。”章炳麟《信史下》解释说:“古之葬者,含珠鳞施。鳞施者,玉柙是也。”越过秦汉时代,再向上溯源,商周以来的以玉鱼铜鱼饰棺现象,当为汉代王侯玉衣葬制的雏形。再向史前史的大传统溯源,则有红山文化的玉龙玉龟和良渚文化玉鱼开启穿越三界的神话想象之先河。
那时的江边特别凉快,可一直坐至日暮,忽地想起什么似的,一个激灵,迅速把一篮碗筷送回家,再扛一个拖把出来,在江水里上下捣捣,大力往水泥石阶上掼,一派空荡荡的回声,响彻久远。家里木地板刷着红漆,快被我拖至发白,已然看得见木质纹理。若是趁势跳一跳,所有家具都会剧烈晃动……
银杏树有国树之谓,但凡古老村落总有银杏庄重身姿如影随形。尝闻中国有九大银杏林,分别在浙江湖州、富阳和终南山、广东南雄、云南腾冲、广西桂林、贵州妥东、丹东及湖北安陆。随州人指出,此说有偏颇,随州大洪山一对千年古银杏举世无双。此言亦不虚,不过,独木不成林,双木亦未成林。
本文从华夏文化的特有的崇拜观念出发,探寻对文化成员思想和行为有支配作用的文化规则,通过以上三故事的分析,加上对中国文化独有文物奇观金缕玉衣的神话解析,说明为什么是玉石神话信仰及其汇聚而成的观念要素,最终成为本土文明发生发展的一种驱动力量。
Exploring the Conceptual Motivation Behind the Birth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YE Shuxian1,2
(1.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200240;2.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732,China)
Abstract: Exploring the conceptual motivation behind the birth of civilization is the front topic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ade myt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ree literary stories,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ceptual motivation behind the birth of Chinese civilization,and proposes three condi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heori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First,its knowledge horizon must transcend the limita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ruly reach the historical depth of 5,000 years;second,it can get support from the new materials of the local system;third,it can balance the core values and core materials of th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belief in jade mythology;Chinese civilization;values;conceptual motivation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233(2019)04-0001-07
收稿日期: 2019-6-20
基金项目: 上海市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基地“中华创世神话研究”和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资助。
作者简介: 叶舒宪(1954~),男,北京人,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文学人类学。
【责任编辑:黄 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