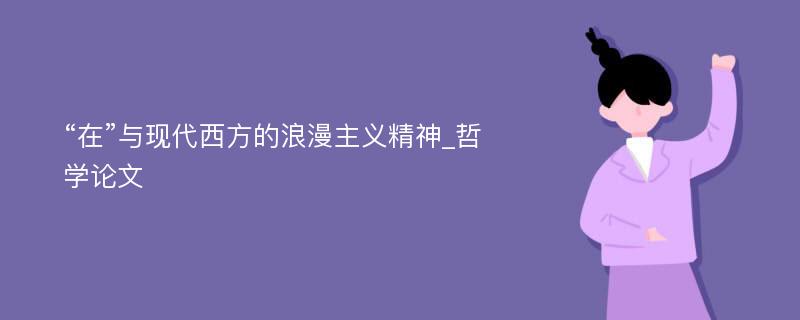
“在”与现代西方浪漫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论文,浪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西方浪漫哲学和浪漫美学中,“在”(Sein)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本体论概念。通过这个概念,浪漫哲学和浪漫美学不仅对人类存在的终极状况作了现代性、根本性的反思,而且这种反思始终充满浪漫超然的诗学精神。“在”的本体论关注人的存在困境,重视人的诗性生命,积极探讨人的审美生存的可能性,因而,它是诗的本体论,也是本体论的诗。它虽然最终指向的是审美超验和乌托邦,但却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一、“在”的本体论规定
本体论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理论。所谓本体,指的是“终极的存在”。 (注:陈宣良:《法国本体论哲学的演进》,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P2。)讨论本体问题,也就是对“终极的存在”的追问,而这正是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哲学家常用各种本质范畴来探讨本体。如世界的本质是“物质”,这个“物质”范畴就是探讨世界本体的范畴。本体与本质范畴必须具有同一性,通过一定的本质范畴才能探讨本体。因此,本体论哲学最关键的就是建立存在与本质的同一性。古今中外许多哲学家都在寻找这种同一性,从而产生了种种哲学本体论。如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因”、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笛卡尔的“自我”、斯宾诺莎的“实体”、黑格尔的“理念”、马克思的“物质”、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海德格尔的“在”、老子的“道”、宋明理学的“理”等。人们不禁要问,他们在追问什么?回答是追问本体。什么是本体?老子说本体即“道”。什么是“道”?老子又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常无名”。就是说,“道”是用来说明本体的。“道”就是“道”,它的本质要靠本体自身作出证明,而“道”又是用来证明本体的。显然这是一个悖论。也许哲学家就是在这样的悖论中艰难前进的。他可提出新的本体论来超越旧的本体论,但他却永远不能回避本体问题,也即人类自身面对的终极存在问题。与其说人类是在追问存在(本体),不如说是在追问自身,因为只有人类才会有这样的追问,追问自身生存的意义,追问自身的终极存在。
西方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建构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上的。亚里士多德用形而上学和逻辑学推论出“第一因”作为本体论范畴;柏拉图则用“理念”来规范本体,他们都视之为一成不变的东西,人类通过一定的逻辑范畴便可把握它。然而,这种统治了二千多年的哲学体系,不过是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的,作为终极存在的人类自身也是被先验的逻辑规定好了的,人类作为自身的存在反倒忘却了。
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兴起,叔本华、尼采第一次对传统哲学展开猛烈冲击。尼采塑造了查拉图斯特拉这一叛逆者形象,高喊“上帝死了”,把被异化了的人类自我意识(上帝),从高高的宝座上拉了下来,重新提出了人类自身存在的问题,这就是“权力意志”。马尔库塞就认为,尼采哲学超越了本体论传统,指控逻各斯压抑和歪曲了权力意志。“尼采是以一个与西方文明的现实原则根本对立的现实原则立论的。据对作为自在目的的存在、作为欢乐和享受的存在的经验,他抛弃了理性的传统形式。”(注: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P87。)
随后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也向传统哲学本体论宣战。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因”和柏拉图的“理念”,都不是真正的本体论,他们追问的不过是逻辑的先验的东西,他们都忘却了真正的“在”,而这个“在”就隐藏在逻辑的背后。于是他提出“基础本体论”,目的是希望找到这个隐藏在逻辑背后被二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所忘却的“在”,克服旧的形而上学,为人类重新找到新的居所。在他看来,真正的本体论,应该关心人的存在,是“在”的本体论。
什么是“在”?海德格尔解释说:“但是在——什么是在?它是它自身。将来的思维、将来的思想,必须学会体验这个在并且言说它。在——不是上帝,也不是世界的根据或最终的地狱。在既比一切存在更远离于人,又比一切现存物(essents)更接近于人,不管它们是岩石、 动物、艺术作品、机器还是天使或上帝。在最接近于人。但是这个最接近性仍然最远离他。”(注:斯坦纳:《海德格尔》,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P77注。)
对于“在”,海德格尔认为,人只能体验并言说它,而不能加以逻辑判断。“它是它自身”,既“远离”于人又“接近”于人。这个“在”,恰似老子的“道”,存在与本质范畴之间的同一性又是一个非常玄奥的问题。海德格尔同样要面对本体悖论问题(在就是在)。但他与旧哲学家不同,他的哲学的姿态是对“在”的惊奇而非证明,因为在他看来,真正的“在”是无法用逻辑推论的,形而上学和科学理性最终导致的只有“在”的忘却,导致二十世纪人的普遍异化和“无家可归”状态。因此,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应该“听”,而非逻辑判断,唯有“听”才能感应“在”;本体论哲学不应追寻某种实体物,追求功利主义,而应使“在”还乡。最终,他把自己的哲学的基点定在人的生存的根基上,认为“在”的解释恰恰必须从人的生存开始。
“在”的本体论规定,表明哲学最终指向的实在就是人类存在的终极境况。在存在主义哲学家看来,传统本体论必须回到人类存在的终极状况的问题上,回到死亡、机遇、罪恶、世界的不确定性和精神的失落等问题上。哲学不能回避这些问题。雅斯贝尔斯指出:“在各种终极境况中,人类将摆脱或超越一切瞬间的世间所在,它或者知觉到虚无,或者感觉到真实存在。就事实而言,即使绝望只能存在于世间,但它所指向的却超乎世间之外。”(注: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P13。)
二、“在”的美学态度
海德格尔那部近乎神喻的巨著《在与时间》,通篇探讨了人类存在的基本困境:生之不确定性(被抛)与死的必然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决定着统摄人生的基本态度,就是一种超越的态度。在他看来,哲学就应把握这种态度。所谓指向逻辑背后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种超越。然而,正如所有存在主义哲学家一样,这种超越的限界只能是“超乎世间之外”,指向的是精神的实在和永恒。在他们看来,倘若人类能够达到这种限界,那么生与死也就没有分别了。死是一种超越,是“精神脱离肉体转向自我本身的世界”(注:今道友信等:《存在主义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73、75。); 而精神的本性也是一种超越,超越现象的世界,从时间世界趋势向永恒世界,“完全地复归于自我本身”(注:今道友信等:《存在主义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73、75。)。死与精神具有相同的哲学本性, 真正的死也即真正精神的永垂。“在精神中,可以看到由于死产生的不死的可能性。死无非是作为精神从肉体的完全解脱的脱自(extasis )”(注:今道友信等:《存在主义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P73、75。)。作为超越的限界,死与精神都是向存在本身的升华。因而,死、精神、永恒的回归与现实之间,也就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裂痕,为艺术的生存提供了可能性。存在主义哲学最终为人类存在的终极困境找到了一条升华之路,这就是美和艺术。而超越作为统摄人生的基本态度,也最终演变为一种美学态度。
在西方,美和艺术的结合,并作为一种感性的美学形态存在于传统哲学体系中,还只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美学只是哲学体系中的一位婢女,而艺术自柏拉图开始,也纯粹是作为一种认识论工具。在柏拉图看来,艺术所认识到的不过是一些皮毛表面的东西,诗人的摹仿只得到影像,而不能抓住真理。柏拉图所规定的存在本体是“理念”,而诗人想通过摹仿来认识这个“理念”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认为,对存在本体的“理念”认识,与诗人借摹仿的感性认识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属于观念认识,是完整的认识,是对“体”的认识;后者属于感性认识,是不完整的认识,是对“相”的认识。最终他将艺术(感性认识)从存在本体(观念认识)的领域中清除出去,并给诗人扣上了扯谎罪状的帽子。这可以说是古代哲学法庭审判艺术的冤案。
然而,感性认识被视为一种低级认识的偏见(到十八世纪上半叶德国占统治地位的沃尔夫的逻辑学也还只是研究高级认识)最终改变过来,哲学中存在本体论与艺术认识的分离自十八世纪下半叶得到了复合。沃尔夫的门徒鲍姆嘉通为弥补传统哲学的缺憾,创立了一门新的作为感性认识和自由艺术理论的新科学,这就是美学。他说:“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完善感性认识)。而这完善也就是美。”(注:鲍姆嘉滕:《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P18。)从此, 美学作为一门新科学从哲学王国中独立出来,也替艺术翻了案。曾被柏拉图置于高高在上地位的观念认识,最终与感性认识结合起来。哲学中的观念本体论也不再被抽去感性存在的根基,人作为存在的本体的主体地位得到强调,人的感觉、想象力等感性认识能力也从理性哲学的窒息中解放出来。美学作为它最初的本性不过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然而这种思维方式对后世的影响是多么巨大。“美学作为近代基本思维方式——形而上学的一种产物,在审美现象的一切领域,明显或含而不露地规定着当今我们的根本思想。”(注:鲍姆嘉滕:《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P77。)
这种以美学的思维方式替代传统理性逻辑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并以此去寻找哲学最关心的存在本体问题,正是近现代浪漫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雅斯贝尔斯在谈到当代人的精神处境时指出:“他必须提升自己到极限,并在那里瞻仰他的超越者,要不然就会陷入与世俗之事纠缠不清的自我幻灭之中。”又说:“由于危机剥夺了人的世界,人必须以他所能处置的资料的预设,从头开始重建世界。自由终极的可能性是朝着他开放的,纵使在面对极不可能的情况下,他也得以全力去把握自由,否则就只有沦入虚无之中。”(注:雅斯培:《当代的精神处境》,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版,P158—159。)
虚无是可怕的,恐惧虚无之际也就是自由觉醒之时。理性的破损,精神的创伤,幸福的指望,这一切都昭示着人类的天堂必须重建。如何重建?席勒老早就说过:“美学是必由之路,因为正是美导向自由。”(注: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P137。)自由终极的可能性正是美和艺术的可能性。于是,一切浪漫哲学都决然转向美学和艺术,浪漫哲学也是浪漫美学,浪漫哲学的本体论也是审美生存的本体论。
三、“在”的诗性之思
浪漫哲学是诗化的哲学。海德格尔的哲学就是地道的诗化哲学,因为他对“在”的本体的追问,用的是诗的方式。海德格尔强调了哲学本性与诗的本性的一致,最终超越了形而上学。因为诗正是人的生存的具体表现。哲学家通常被人认为居住在人与上帝之间,哲学的理性与诗的神性之间的鸿沟是无法逾越的。然而,这在海德格尔看来,却是一种误解。他在《在与时间》中的命题,便是在品达和荷尔德林的诗中找到灵感,精奥的哲理融会着浪漫的诗思。荷氏有《还乡》、《漫游》等诗,海德格尔也把诗人说成是“返回家园的徘徊者”(注:恰特基:《哲学与诗》,《深圳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增刊。)。
海德格尔在荷氏的诗里更发现了“在”的原真意义。在《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中,他认为荷氏才是真正的诗人之诗人,因为荷氏在其诗中找到了人的此在的根基:“人的此在的根基从根本上说是‘诗意的’。”(注:伍蠡甫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P574—589。)荷氏有句名言:“充满才德的人类,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大地。”(注:伍蠡甫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P574—589。)海德尔格认为,“诗意地栖居”就是置身于神祗的现在之中,进入一切存在物的亲近处。诗人正是尽可能地去“神思”这种神祗的现在和一切存在物的亲近处,这不是回报,而是赠予。诗的本质就是,“诗是给存在的第一次命名,是一切存在物的第一次命名”。(注:伍蠡甫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P574—589。 )人正是“在诗中神思存在”。(注:伍蠡甫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P574—589。)
诗人拿什么来命名、来神思呢?海德格尔说拿语言。“诗的活动领域是语言。”(注:伍蠡甫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P574—589。)他认为, 诗是历史的人的源初语言,语言的本质必得通过诗的本质来理解。同样,诗的本质也必须通过语言的本质去理解。在诗中,人重新与自己的此在相结合,就好象确信自己到了家一样,人在诗意中找到了此在的根基。但人的此在的基础是“交谈”,只有在“交谈”中语言才是真正现实的。可以这样说,人是在交谈中相识的,这也等于说人是在语言中相识的,“语言乃是存在的家园”(注: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中译“代序”,三联书店1988年版,P19。)。
但海德格尔又把语言看成是人类所拥有的“最危险的东西”:“它之为所有危险物中的危险物乃是因为它最早造成了危险的可能性。危险就是存在者对存在的威胁。人被开启而明晓自己作为存在者得为自己的此在而苦恼、焦虑,作为一个非存在者又使自己失望和不满,这正是语言的功劳。正是语言最先造成了威胁、扰乱存在的明显条件,从而造成了丧失存在的可能性,因此说语言是危险物。”(注:伍蠡甫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P574 —589。)在他看来, 人类是拥有了语言才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与非存在的。因而,导致今天人类存在的失落也是语言的罪过,而要找回这个失落也必得从语言开始。他从古希腊哲学的“逻各斯”概念中找回了被人们误作逻辑判断系动词“是”(Being)的存在意义。
诗与哲学的汇通,语言并非必然的中介,它们在原初就是汇通的,只是后来才失落了。今天看来,它们的默契好似有一种不可言谈的神秘:“那不可言说的神秘是通过自然之书,通过人自身的内在力量,包括通过那每一个用语言思考的人都十分熟悉的心灵凝聚而成的。”(注:恰特基:《哲学与诗》,《深圳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增刊。 )而这部“自然之书”,正是人类源初的诗性的历史。维柯在其名著《新科学》中,就把远古人类历史看作是诗性的历史。因此,诗与哲学的汇通并不像狄尔泰所说的:“哲学呈现出它完成了的概念及其一定类型的人生观。它俘虏诗——危险地然而不可避免地俘虏了诗。”(注:伍蠡甫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P574—589。)哲学和诗决不是谁俘虏谁的问题, 因为哲学的本性就是诗, 哲学的极致也是诗的极致,它们本来就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孪生姐妹。
海德格尔采取诗的方式追问“在”,这正如我国古代的屈原和庄子。屈原《天问》,与其说是追问宇宙本体,倒不如说是放纵人类的想象力去追问人类生存自身。而这正是“在”,一个诗和哲学的极致和终极精神。庄子以其哲学喻语揭示诗的意义,在古代哲学家中更是无与伦比。面对“在”之本体,他采取的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听”的审美观照态度。他的散文是哲学,这种哲学也是美学。庄子所要追求的美学本体(即所谓的“至人”、“真人”、“神人”、“大宗师”)都不过是一种理想的人格,本体论在这里成为一种人格本体论(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P186。)。庄子召唤理想人格的出现,正是庄子面对人被异化的社会现实、人的“在”被忘却的文化所作出的抗议。
四、结语:“在”的反思意义
西方现代浪漫哲学和美学,由于其用一种现代性的、反传统的姿态,站在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对立面,强调破坏、抵抗、否定、超越,作为其本体论哲学和美学的出发点,同时又崇尚美和艺术的诗性力量,崇尚美学与人生的完美结合,因而其所探讨的普遍自我意识、命运、上帝、自然、绝对精神、逻各斯,最终都落实到人的自身存在的根基上。这是西方哲学和美学对导致人类生存危机的社会现实所作出的根本性的反思。尤其是西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使人普遍体验到了作为生存的岌岌可危。因此,现代浪漫哲学和浪漫美学其实也体现了人类自我反思的深刻精神。
就浪漫本体论而言,现代哲学和美学对“在”的根本性反思,无疑充满乌托邦色彩。乌托邦的意义也许不在于它能实现与否,而在于它与现实的对立,在于它对现实的批判意义。“意识形态告诉人们: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乌托邦则表示:存在的是必须改变的。乌托邦的死亡就是社会的死亡。一个没有乌托邦的社会是一个死去的社会。因为它不会再有目标,不会再有前景和希望。”(注:张汝伦:《坚持理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218。)
胡塞尔在一篇题为《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的演讲稿中指出,欧洲最大的危险是困倦,如果欧洲人都有勇气来与这个危险作战,那么,“一种新的内在精神生活的不死鸟将站立起来支撑人类伟大而遥远的未来”(注:胡塞尔:《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P175。)。如果我们借用胡塞尔所说的这个“不死鸟”,也许可以说,贯穿于西方现代哲学和美学精神生活中的那个“不死鸟”,正是浪漫超然的乌托邦思想。
标签:哲学论文; 本体论论文; 美学论文;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本体感觉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现象学论文; 伍蠡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