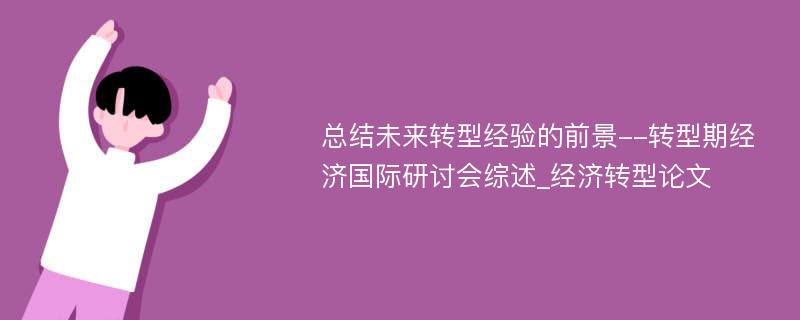
转轨经验的总结 未来前景的展望——转型经济国际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景论文,国际研讨会论文,未来论文,经验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和中国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共同主办的“转型经济国际研讨会”于2004年6月11~13日在南开大学隆重举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立群教授主持会议并宣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致会议的贺信,南开大学副校长逄锦聚教授致欢迎词,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邢广程教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A.B.奥斯特洛夫斯基教授分别致辞。会议邀请了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波兰前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G.W.科勒德克教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O.T.博戈莫洛夫教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A.B.奥斯特洛夫斯基教授,并就会议主题进行学术演讲。中国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罗肇鸿教授,中国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南开大学张仁德教授,中国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副会长、辽宁大学校长程伟教授等专家学者与会并发言。来自中国、俄罗斯、波兰、日本等国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一 对中国、俄罗斯、东欧经济转轨的总体评价
中国自1979年以来开始了渐进式改革;苏东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激进式转轨,在这场历史性转型中,最重要的政策实践问题是采取休克式转型还是渐进式转型。不同的转型方式带来了不同的转型效果。时至今日,对不同国家转型效果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是非常必要的。与会代表从不同角度评价了中国、俄罗斯和东欧经济转轨的效果。
科勒德克教授在题为《从休克到治疗:后共产主义国家转型的经验教训》的演讲中高度赞扬了中国的经济转轨和体制改革。他指出,波兰在经济发展最快的三年里GDP共增长了28%,而中国却在20年里一直保持了GDP每年9%左右的增长速度,“中国是渐进式经济转型的典范”。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实行渐进为主、激进为辅的转型方式,其经济或多或少、或快或慢地都得到了一定发展。而俄罗斯采取的休克疗法这一激进方式不仅没有在短期内完成转型,反而为此付出了高通货膨胀、高失业、负增长等高昂代价,也为现任总统普京遗留下了大量难以解决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是胜者,波兰居于中间,而俄罗斯和某些东欧国家则是败者。
在转轨的总体评价上,博戈莫洛夫院士同科勒德克教授有相同的看法。他指出,俄罗斯社会改革遭受了巨大痛苦,没有成功,中东欧这个进程却迅速和顺利得多。而形成更加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经济成就。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虽然也有一些问题,如“三农”问题、国有企业职工下岗问题等,俄罗斯激进式的改革虽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但却发生了更加严重的问题。2003年GDP总量仍然低于改革前的1990年水平的20%,而工业产值低35%,基本建设投资低65%。社会收入分配严重不公,最富的10%居民和最穷的10%居民平均收入之间的差距,官方统计确定为14倍,而根据许多学者和专家的计算,包括收入和其他因素差距应为30~40倍。如果注意到货币积累、有价资产、住房质量、可享受的高质量医疗和休养条件,那么,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还要更深。在欧盟各国,其差距仅4~7倍。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中国是转轨国家中最成功的一个。奥斯特洛夫斯基教授从所有制改革、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转型进程加以比较分析,充分肯定了中国经济转型取得的成绩。他指出,在1990年中国的GDP大约是俄罗斯的60%,而14年后的今天,俄罗斯的GDP则是中国的60%,中国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所马蔚云博士从效率与公平的角度对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进行了评价。他认为,俄罗斯自1992年实行激进式改革以来,收入分配机制从保障性分配转向效率性分配,在效率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已经很严重。
与上述对苏东国家激进改革持批评态度的观点不同,一些学者认为,激进式改革至少在某些方面是优于渐进式改革的。程伟教授认为,俄罗斯实行的是激进转轨,中国实行的是渐进转轨。俄罗斯从改良到转轨,中间没有改革,破旧在先,立新在后;中国是从改革到转轨,破旧兼顾立新。选择激进式改革未必就是错误,俄罗斯实现了改革的不可逆转,实现政治动荡后的基本稳定,实现复苏之后的稳定增长。他认为,俄罗斯经济增长面临很多有利的因素,如国内政局进一步稳定、国际环境空前有利、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总体上趋于弱化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林跃勤博士认为,俄罗斯经济转型虽然付出了较大代价,但其新型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基本建立,经济调控机制实现了由政府调节向市场调节、法制调节的根本转变,市场经济框架日益完善,正在走向成功;中国近25年的改革一直避重就轻,至今体制转轨远未完成,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营模式、调控方式等均远不能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中国改革尚需提速。
还有的代表认为,中俄转轨各有利弊,很难说孰优孰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孙振远教授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实行了不同的转轨模式,都有各自的问题需要解决。中国模式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但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如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问题,俄罗斯已经被认为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再如,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俄罗斯解决得比中国要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孔田平研究员对波兰实行的休克疗法做出了不同的评价。他认为,转型前波兰由于外债高筑、货币定值过高以及预算赤字货币化等因素的存在,导致波兰宏观经济中不稳定因素较多,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价格自由化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是有效果的,波兰休克疗法为波兰持续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波兰经济成功的标志是:短缺经济不复存在,控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国有经济主导转变为私有经济主导,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波兰的休克疗法并非像科勒德克教授所说的那样“只有休克、没有治疗”。同时与匈牙利等国家相比,波兰经济的衰退时间是比较短的,转型付出的代价也没有科勒德克教授所说的那样大。
为了更好地对转轨国家进行总体评价,在本次研讨会上张仁德教授和他的博士研究生张淑惠提出,应当构建一套转轨度指标体系来反映转型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体制建设水平。这套指标体系由市场体制建设指数、国民自由权利保障指数和政治体制指数三个方面构成。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分析各国之间转轨度的差异,才能从量的测度上做出准确评价,也才有助于划分转型的阶段、时期,寻找和分析影响转轨度的敏感因素。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生导师、中国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景维民教授和他的学生杨晓猛在提交的一份书面发言中认为,产业结构变动与调整状况的测度是衡量转轨国家相对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指标,甚至是第一指标。他们通过设置模型对9个转型国家在1991~2003年的三次产业变动进行分析,结论是总体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新纪元的前期各国相对市场化程度在排序上变化很大,中国和俄罗斯的排名由前4位跌至后4位;塔吉克斯坦由末位上升到前两位;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由后5位上升到前4位以内;哈萨克斯坦以第5位为轴线起伏波动;只有摩尔多瓦和阿塞拜疆仍位居前4位;白俄罗斯仍位于后两位。
此外,上海城市管理学院上海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王子奇还从经济转型的代价角度评价了中国、俄罗斯、东欧经济转轨的效果。
二 俄罗斯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经验和教训
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剧变不仅带来了政治上的地震,更重要的是许多中东欧国家经济陷入泥潭,经济增长乏力,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探讨俄罗斯和某些东欧国家转轨失败的深层原因,吸取其失败的教训,使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引以为戒,少走弯路是非常有必要的。与会专家学者普遍将其转轨失败的教训归结为:过于迷信西方资本主义和忽视制度建设。
科勒德克教授指出,中国的经验告诉世界,应该朝正确方向推动渐进式发展,仅有市场经济是不够的,转型需要强有力的引导而不是幻觉,还需要好的理论构建有效的制度。经济社会转型应该包括三个同时进行的过程:自由化与稳定政策、微观机制重构、制度建设。除此之外,国家政策也非常重要。波兰等国的改革经验证明:政策不仅受经济理论的指导,更受政治冲突的影响,是利益集团冲突、妥协及合作的结果。中东欧和原苏联国家经济社会转轨最深刻的一条经验教训是,不能忽视促进发展的经济政策,而只寄希望于“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的自发调节。私有化不是目标而是手段,比私有化和自由化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建设,而中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将手段与目标相混淆,忽视了制度的建设。
博戈莫洛夫教授指出,俄罗斯市场化改革没有获得成功有多种解释。改革的设计师们断言,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错误归咎于我们过去的沉重遗产和俄罗斯现实的特殊性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其实,根源就在于改革政策本身的有害性,以及忽视国家在这一过程中重要组织者的作用。俄罗斯改革的悲剧在于领导人的错误路线,原苏联的精英们无论就其道德水准、政治上的成熟、起码的诚实和良心,还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的理解,都绝对不能适应历史转折的召唤。他们的改革不是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是完全恢复资本主义。特别是走了一条完全简单化的道路,走了一条最坏的道路。资本主义不仅仅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好处,在实际生活中也有很多缺点。私有制并不必然比国有制更有效率。目前,俄罗斯石油、冶金行业的效率都低于过去。不能采用休克疗法,改革是分阶段、分步骤的一个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博士生导师许新教授认为,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实行了12年,休克疗法的神话变成了冷酷的现实。脱离国情的药方使玻利维亚奇迹变成了俄罗斯失败;不符合俄罗斯经济特点的目标模式和违反经济转轨规律的过渡方式,使期望的自由市场经济变形成为“资本原始积累”式的野蛮的市场经济;经济政策的内在矛盾和在经济学上犯忌导致经济形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一直处于衰退性危机之中,并最后演变成以金融危机为尖锐表现的社会经济的全面危机。这一切都源于政治目的和理论误区:崇拜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经济体制上迷信市场万能,反对国家干预;奉行现代货币主义政策,在反危机上片面抑制需求,忽视增加供给;把转轨的成败建立在依赖大量外援的基础上,幻想靠外援解决休克疗法造成的各种尖锐问题,渡过各种危机交织的难关。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何自力教授认为,转型方式的选择一定要适合本国的国情,西方议会民主制与中国文化存在不适应性。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分裂统一、统一分裂,说明中国是适应集权的。过去25年改革证明,渐进方法是成功的,未来也将证明渐进是成功的,而激进是不成功的。坚持共产党领导就是渐进的,而多党制是激进的。中国选择了适合自己的改革道路,所以中国成功了;而苏东许多国家选择了不适合自己的道路,因而遭到重创。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秘书长田春生认为,中东欧国家在转轨过程中过多偏重华盛顿共识,而实际上华盛顿共识的内涵与中东欧国家的现实相差悬殊,这就造成了中东欧国家改革过程中对目标和手段的认识都是混乱的,政策是误导性的。她指出,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机制确实非常重要,但它却不是万能的。因此,转型国家必须善于找到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战略。中国市场学会理事长、中国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副会长高铁生教授认为,在转型过程中,各国应该立足实际,计划经济的一套办法不适用了,发达市场经济中规范市场秩序的办法也不宜照搬照抄。
三 俄罗斯的转轨前景和其应用中国经验的可能性
俄罗斯目前实现了剧变之后的经济复苏,经济复苏能否继续保持以至给俄罗斯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很多学者关注的问题。本次研讨会也对俄罗斯经济发展前景展开了讨论。有些与会学者认为,俄罗斯目前经济复苏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价格的提高,经济增长仍然缺乏坚实的基础,对其经济增长前景不十分看好。
博戈莫洛夫教授认为,普京执政后的第一个四年经济实现了增长,但并没有恢复到改革以前的水平。近年来引起乐观主义倾向的原因,主要不是由于改革带来的经济健康化发展,而是由于一系列有利的、同时又是暂时的因素在起作用。如世界市场上石油、天然气的价格提高及卢布的贬值,俄罗斯经济增长仍然缺乏坚实的基础,经济增长还没有足够的持久性保证。它绝没有扭转社会恶化的进程,其表现是:人口寿命和数量的下降,居民保健状况的恶化,吸毒和心理疾患的蔓延,大量贫困和儿童流浪现象的存在等。
奥斯特洛夫斯基教授认为,俄罗斯最重要的优势就是自然资源丰富,俄罗斯最大的问题就是宏观调控体系的不健全,导致了俄罗斯存在一系列问题,如税收过多,商业银行太多,利率过高,国债过多。而中央财政收入不够,很难实现科学决策。这就导致俄罗斯科学教育投资不多,使俄罗斯经济发展前景堪忧。
东北财经大学郭连成教授指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应该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在这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并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俄罗斯经济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协调甚至脱节现象。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是以不合理经济结构为前提的,以增长质量不高为代价的,以缺乏竞争力为特征的。这是造成俄罗斯在经济快速增长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副会长陆南泉教授认为,俄罗斯在发展经济方面具有以下一些有利条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承接了原苏联大部分智力资源,尽管由于人才大量外流而遭到严重破坏,但仍有相当大的实力;存在很大的经济发展空间,如现存的大量闲置生产设备可利用,扩大投资与增加需求的潜力很大。但同时要看到,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从各种情况分析来看,目前与今后一个时期,制约俄罗斯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有:投资短缺是俄罗斯经济难以快速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短期内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很难改变以出口为主导的模式,经济原材料化趋势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难以改变;扩大内需乏力;外债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仍不可忽视;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因此,俄罗斯实现普京提出的加速经济增长速度,201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存在着比较大的困难。
如果俄罗斯也走渐进式改革道路,是否能够避免十几年的经济低迷,如同中国经济一样获得持续快速的增长?与会代表还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博戈莫洛夫院士认为,总的来看,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如果俄罗斯也走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很可能也会取得巨大的成绩。俄罗斯本来也可以走上渐进式改革之路的,当时俄罗斯实际存在不同的改革方案,大体可分为激进式和渐进式两类。叶利钦政权之所以选择激进方案,其原因是:第一,渐进的改革需要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政权自上而下地加以贯彻,而这种政权体系在俄罗斯实际已不存在;第二,民主派认为,激进的改革虽然会带来经济下降,但下降将是短暂的,长痛不如短痛。这也就是叶利钦所说的:两年实现稳定,三年有所改善。作为当时社会主流意识的代表,民主派天真地以为,只要照搬西方的自由市场模式,就能够在短时间(比如说“500天”)内摆脱苏联晚期形成的尖锐的经济危机,实现俄罗斯民族的快速振兴。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当时选择激进改革方案的重要原因。博戈莫洛夫院士强调指出,由于社会精英的素质低下,才使得俄罗斯偏离了走渐进式改革这样一条正确的道路。奥斯特洛夫斯基教授指出,中国是渐进的改革,而俄罗斯是激进的转型。渐进的改革比激进的转型成效要好。他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在俄罗斯是适用的,只是偶然因素使得俄罗斯没有走上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如果俄罗斯走渐进式的道路,代价不会这么大,效果也会好得多。如何稳定市场、控制经济,俄罗斯在这方面应该吸取中国的经验。
与原苏东国家的学者相反,我国部分学者则认为,俄罗斯选择激进式的道路有其客观必然性。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周冰教授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综合决定论,即转型方式是由体制结构、外部环境、改革时机和改革策略集共同决定的。由于俄罗斯决定体制改革的因素与中国不同,因此,不可能采取同样的转型方式。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刘文革教授和南开大学靳涛博士对经济转型模式进行了划分:刘文革将转型方式划分为突变式制度变迁和演进式制度变迁两种;靳涛则认为,转型应当包括文明的转型、社会的转型即宪政转型和经济体制的转型三个层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俄罗斯东欧史室研究员黄立茀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从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引起的利益冲突的视角,分析了经济改革陷入困境的原因;同时借鉴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理,以中国改革道路为参照物,从经济结构对改革道路制约的角度,剖析了苏联转向政治改革的深层客观制约因素。她认为,选择激进式的道路在原苏联是有客观原因的。
在研讨会上罗肇鸿教授、张仁德教授做了总结性发言。他们对这次大会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且对转轨经济的研究、原计划经济国家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总之,作为国际转型经济学界的一次盛会,此次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对繁荣转轨经济研究,对扩大中国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学术交流,对中国、俄罗斯和东欧的改革与深化必将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