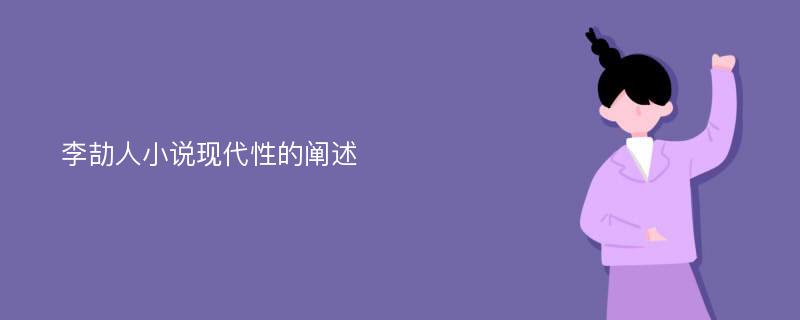
王亚玲[1]2012年在《论李劼人前期短篇小说的“现代性”追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李劼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许多学者认为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具有现代性的开拓价值,是中国历史小说现代模式的完成者。笔者结合前辈学者的观点,认为除了“大河叁部曲”外,李劼人的前期短篇小说创作,也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因此本篇论文主要考察了李劼人前期短篇小说的“现代性”追求,对其小说的创作内容与艺术手法的影响,进而论述其前期短篇小说创作的意义与价值。本文以李劼人前期短篇小说创作中,体现出的“现代性”为论文的立论基础。认为他的前期短篇小说将“人性关怀”作为一条中心线索,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手法上,都体现了清晰的“现代性”追求。内容上,他的前期短篇小说,考察了阻碍社会与人现代化的惰性文化传统,所造成的悖谬性的人生困境与对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残,并批判了产生于此种文化负面因子下的国民劣根性;同时他关心女性命运,反思了处于军阀混战与启蒙话语中女性的解放问题,体现出“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双重追求。人物塑造上,他的前期短篇小说打破传统小说以情节为结构中心的窠臼,实现了“人物大于情节”的现代转化,以写实的笔法,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与潜意识分析,描写人的成长史,刻画圆形人物形象。叙事手法上,通过倒叙与插叙打破传统小说线性的叙述时间桎梏,注重通过生活的横断面反应人生;呈现了一条从全知视角向限知视角转化的线索。本篇论文将文献研究与文本细读、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相统一,结合李劼人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以及生活的时代,来探讨其前期短篇小说的思想成就与艺术价值。
王永兵[2]2001年在《李劼人小说现代性的阐述》文中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李劼人是一个独异性的作家,这种独异性不仅表现为他始终游离于众多的文学社团流派之外,而且还体现为他具有浓厚的现代意识。李劼人现代意识的形成是中西文化的双重熏陶以及他所处的时代环境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强烈的爱国情怀促成李劼人一生中不倦的追求现代化之旅,也令他象许多人一样将文学由目的化为手段。本文将李劼人小说的现代性作为研究的主旨,以此来认识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人物。 李劼人小说的现代性由内容与形式两个维度上展开。首先,在思想内容方面主要表现为对“人”和人的命运的关注,开放、自由的妇女观和婚恋观,科学辨证的思维方式;在艺术形式方面主要体现为对新的小说类型的探索、以心理分析方法为主的现代艺术手法的运用等,由于个人、时代等因素的局限,李劼人小说带有明显的过度性,留下一些缺憾。
包中华[3]2018年在《论李劼人小说对晚清“现代性”的延续》文中研究说明李劼人的小说创作(1912—1937年)源头上主要受晚清小说和林译小说的影响,他早期的小说创作和现代文学发展的主流观念存在思想和技艺上的差距,是晚清文学"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延续;另外,李劼人的长篇小说虽然借鉴了晚清小说的描写和叙事,但是在19世纪法国文学的影响下,已完全具有了现代小说的形式和精神结构。李劼人的长篇小说创作是在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表现"人",突破了现代文学中"人的文学"表现的狭小的时间和空间维度。
高明[4]2014年在《历史的“空间化”》文中认为李劼人凭借其“大河小说”的历史成就,便可以跻身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家之林,原因在于其创作素材的独特选取、影响其创作的文化因子,最重要的是其独特的书写历史的方式——突出日常生活在观照历史过程中的作用。他将为世人还原历史原貌为出发点,发觉被精英历史所掩盖的民众历史,尽可能的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本文尝试着从“小历史”这一角度研究李劼人在“大河小说”中的书写姿态,希望能有所收获。文章共分为叁章,彼此是有合理的内在联系的,我们要了解李劼人书写历史的观念,历史在他笔下是如何呈现的及他想成这种观念的原因:第一章,研究李劼人笔下“小历史”的建构。这部分内容首先弄清“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区别,阐明自己认为李劼人历史书写的姿态,并分析产生的原因。然后研究这样一种独特的书写姿态对其笔下历史的呈现有着怎样的影响。第二章,研究“大河小说”重要的叁个组成因素,空间、历史和人。这部分由两部分组成:其一,以茶馆、民间庆典为切入点研究这些主要的公共空间是怎样反映时代变迁的;其二,以女性个体成长、婆媳关系、夫妻关系为切入点研究私人空间是怎样反映历史变化的。第叁章,研究李劼人独特历史书写姿态的原因,主要就是以巴蜀文化和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入手。结语中,简单地介绍历史转折对李劼人的影响,这样一位书写历史的人,其实也逃不出“被历史”的圈子。
何平辉[5]2008年在《中西文化交汇中的李劼人》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现代文坛,李劼人以长河式的长篇历史小说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景象和人物风貌,表现了作者丰富的历史文化素养和深厚的艺术底蕴,奠定了他作品“史诗”的地位。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部分展开:一,描绘李劼人小说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环境,展示中西文化交汇碰撞下社会的激烈动荡变革,以及人们在现代体验中的观念意识和心理结构的变化。二、具体从李劼人建构的“巴蜀世界”来阐释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并分析其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价值及意义。叁,深入剖析李劼人小说最典型、最辉煌、最美丽的女性,解释李劼人建立的“女性神话”,把握她们在巴蜀淳风中的“异样情调”。四,分别从语言艺术、心理描写艺术和史诗性及结构艺术叁个方面展现李劼人多彩的艺术风采,显示其不朽的价值。
蒋林欣, 张叹凤[6]2013年在《“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英语世界的李劼人研究成果与现象》文中研究表明近30年来李劫人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与研究已取得初步成就,《中国文学》杂志及"熊猫丛书"是最早的译介,司昆仑、陈小眉、吴国坤等学者对李动人的历史观、异域体验、地缘诗学等作了宏观视域里的精微阐释,司昆仑、王笛、路康乐、戴英聪等"以诗证史",将李劼人笔下的晚清成都社会万象作为史料文献征引入学术专着;马悦然、英丽华、王德威等将李劼人作品编入中国文学"手册"、"辞典"和"文学史"。地方色彩、历史叙事、社会史料等是汉学家特别关注的重点,因跨文化、跨学科的学术背景,这些英语世界中的李劼人研究学术视野开阔,立论高远,解读精细科学,自成一派。在今天多元共生的文学评价环境里,李劫人文学地方书写的价值日益凸显,相关研究渐行丰富,必将呈现出新气象、新格局。
王学东[7]2013年在《“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李劼人文学思想》文中研究指明关于巴蜀地域文化与四川现代作家的小说创作,已有诸多的研究,产生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在巴蜀文化视野之下,四川现代作家文学观念的形成,则是一个相对缺少的研究领域。我们知道,区域文学有其独特的地方性,指导作家进行创作的文学思想又怎么不带有区域色彩呢?这里从"文学地理学"的视野来思考李劼人的创作,特别是探讨区域文化之下李劼人的文学思想,以及这种文学思想所蕴含的独特价值。
李先宇[8]2011年在《李劼人小说与“城市”书写》文中指出李劼人有着强烈的史志意识,他一方面扎根于蜀文化的土壤中,另一方面努力吸收外来文学艺术的营养,使得他的“城市”书写有着浓重的中西合璧的影子。他为保留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意义尤为深远。李劼人是一位具有自觉的区域文化追求意识的知识分子,他把成都及其近郊作为灵魂的栖居地,把自我融入民间,把千年古都纳入近代向现代的转变之中,使成都在这一历史性的转型中,既展现出它美丽阴柔享乐的一面,又暴露出它貌似强悍后的虚弱与浮躁,他笔下的成都意象拥有浓郁的巴蜀地域特征,把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成了一整体,在这个过程中,成都及周边乡镇构成了一个区域,它由乡村与城市共同构成一个事实上更本质化了的乡土世界。在不断的冲击碰撞中,成都精神得以扬弃。李劼人带着他强烈的民间立场,以自由之笔、自由人格和对历史与现实的独立思考而赋于其作品独特的民间意味。其民间意味主要体现在民众丰富的日常生活体验中和独有的语言与表达方式上。他幽默乐观、隐藏作者、秉笔直书,追求一种史的厚重与大器和诗的灵巧与智慧,用心去描绘成都这座城市和它的子民,通过欲望叙事和暴力叙事的方式把人性与历史很好的融合起来,完成了蜀文化影响下成都形象的书写,实现了自己的美学追求。
詹玲[9]2010年在《现代成都文学茶馆叙事中的“现代性”考察——以李劼人、沙汀小说为材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文学场景地图中,茶馆作为叙事空间多出现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江浙小城镇与动荡政局中相对平和、保持传统的城市地带背景中。与充满西化的开埠都市类比,这些地区有着更加坚韧的传统根子;而相较内陆偏远地带的贫困乡村,它们又更多地感
冯琪[10]2017年在《自然人性的关照与升华》文中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系列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群体成为小说家们争相刻画的对象。匪盗小说所具有的精神内蕴在中国人的群体意识中深深铭刻,亦逐步进入到现代文学的叙事里。对匪盗的书写是现代文学体系中的一部分,正如饕餮盛宴中的一道“野味”,滋味别具一格。现代文学各个区域的匪盗叙事在描写对象、创作风格和表现效果上各具特色,以一个个极富地域文化符号的故事共同构成了现代文学匪盗叙事流,其中,极具巴蜀地域文化特征的袍哥群体是巴蜀本土作家们在匪盗书写上的自觉选择。较为重要的有巴金、艾芜、沙汀、马识途,此外,对这一群体更具细腻独到和全面客观表现的作家,则是李劼人。李劼人对袍哥的描写,集中体现在“大河叁部曲”中,其中尤以《死水微澜》和《大波》为典型。李劼人的人物形象没有英雄和小丑般的泾渭区分,而是一个个具有复杂人格的交织体,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这些真实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对本真历史的记录与描摹。就读者接受层面来看,李劼人笔下这些不够完美的保路运动参与者反倒有了被欣赏或议论的必要,读者们反而发现了其中跨越时代、阶级语境的价值。当小说过滤掉多余的写作者情感,剥离掉道德评价和伦理准则,呈现出来的正是人性中最为真实、鲜活的状态。《死水微澜》是李劼人袍哥叙事最为典型的一部。《死水微澜》因其具有典型特色的人物形象,紧凑而充满戏剧化的故事情节,加上在一定程度上去政治化的表述效果,使得辛亥革命的政治背景对于整部小说来讲更像是一层单薄的外衣,其内在实则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民间化、世俗化气息。在《死水微澜》之外,还有一位与罗歪嘴具有相似气质和人格的袍哥,他就是曾活跃在巴蜀政治、军事历史舞台上的范绍增。袍哥的“义气”与“邪气”给了范绍增特立独行的行事、作战风格,军旅生活的种种规约又逐渐驯化了他身上的江湖气。袍哥气质与军人风范在范绍增身上交织为一体,造就了范绍增极具争议又传奇的一生。而范绍增与罗歪嘴的相似,又令他的存在如同对罗歪嘴的续写。至于李劼人袍哥叙事所受到的影响,主要有叁方面。首先是李劼人对写实的追求;其次则离不开巴蜀地区的风物、文化,这是李劼人袍哥叙事的本土资源,涉及巴蜀封闭、野蛮、恃强力为王、享乐的地域文化氛围;另外则是法国文学的影响,左拉一派的自然主义文学观深深影响和塑造了李劼人的文学创作,其中包含了作家对法国文学的吸收,也包含了他对自然主义文学弊端的克服。
参考文献:
[1]. 论李劼人前期短篇小说的“现代性”追求[D]. 王亚玲. 西南民族大学. 2012
[2]. 李劼人小说现代性的阐述[D]. 王永兵. 扬州大学. 2001
[3]. 论李劼人小说对晚清“现代性”的延续[J]. 包中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8
[4]. 历史的“空间化”[D]. 高明. 沈阳师范大学. 2014
[5]. 中西文化交汇中的李劼人[D]. 何平辉. 江西师范大学. 2008
[6]. “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英语世界的李劼人研究成果与现象[J]. 蒋林欣, 张叹凤. 中外文化与文论. 2013
[7]. “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李劼人文学思想[J]. 王学东.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8]. 李劼人小说与“城市”书写[D]. 李先宇. 重庆师范大学. 2011
[9]. 现代成都文学茶馆叙事中的“现代性”考察——以李劼人、沙汀小说为材料[C]. 詹玲.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届年会论文摘要汇编. 2010
[10]. 自然人性的关照与升华[D]. 冯琪. 重庆大学. 2017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李劼人论文; 现代性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短篇小说论文; 读书论文; 死水微澜论文; 范绍增论文; 袍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