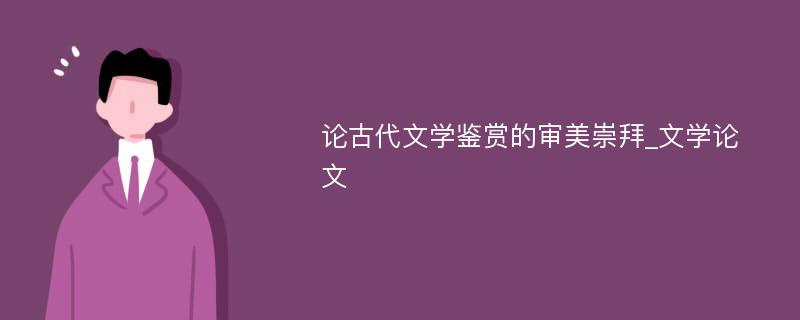
论古代文学鉴赏的审美崇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古代长期的文学鉴赏活动中,虽然因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级阶层,不同地域空间、不同个性特征等原因,人们的审美要求、审美趣味、审美标准不尽相同。人们审美判断的千差万别,系社会的客观存在,我们不仅不要求它整齐划一,而且还主张发展具有个性的审美趋求。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长期稳定的民族群体,形成一种共同的民族审美心理。这种心理往往成为“集体无意识”,甚而是一种集约式的心理定势。这就形成了审美差异性和同一性的统一。也就是说在共同民族心理的支配、制约、熏陶下,会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传统习惯的审美崇尚。
审美崇尚是审美趣味、审美态度,审美标准的综合体现。我国古代文学鉴赏由于社会的、历史的以及文学创作和鉴赏的诸多原因,其共同的传统的崇尚择要而言,有如下几方面。
重自然轻雕饰 文学鉴赏中崇尚的自然,指创作时自然胎脱,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同时指作品浑然天成,不矫不饰;也指那种不施粉黛,扭捏作态的风格。南朝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这些已作了较充分的阐释。“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古斑字)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原道》)“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定势》)创作完全按自然之趣,自然之势进行。钟嵘《诗品·总论》举出徐干《室思》中“思君如流水”,曹植《杂诗》起句“高台多悲风”谢灵运《岁暮》之诗句“明月照积雪”等,认为这些诗句成为“古今胜语”,就在于得“自然英旨”,“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鲍照鉴赏谢灵运和颜延之的作品,认为谢的五言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而颜诗则如“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失却自然本色。(见《南史·颜延之传》)这种贵自然的鉴赏观,到晚唐司空图的《诗品》在二十四诗品中将“自然”列为第二,并作了高度概括,为当时和后世立圭作则,也就成了公认的传统。司空图的概括是:“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苹。薄言情语,悠悠天钧。”此后或评人、或自谓,都以自然为尚。李白曾说:“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太守良宰》)并斥责绮丽、雕琢诗风:“绮丽不足珍”、“雕虫丧天真”(《古风》)宋代欧阳修主张诗文都要“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转引欧阳修诫王安石语)苏轼把这种自然美比作海棠花:“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定惠院海棠》)他主张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姜夔论诗有四种高妙说:“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而且“非奇非怪,剥落文彩,知其高妙而不知其所以高妙”的自然之妙为最高。(《白石道人诗说》)陆游主张“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文章》)认为“琢雕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大巧谢雕琢”。金人无好问有两句名言:“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三十首》第四)明代谢榛也认为“自然妙者为上,精工者次之。”(《四溟诗话》)清代沈祥龙论词,亦谓“以自然为尚。自然者,不雕琢,不假借,不著色相,不落言诠也。”(《论词随 笔》)近代人王国维《人间词话》痛诋梦窗(吴文英),玉田(张炎),也就是认为他们砌字、垒句、雕琢、敷衍,“归于浅薄”。他还自填一首《蝶恋花》:“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视“天然”为最高境界。纵观历代文学创作论。鉴赏论,崇尚自然之说绵延不绝。而且多采芙蓉为喻,或称“初发芙蓉”(鲍照语),或谓“初日芙蓉”(汤惠休语),或言“秋水芙蓉”(李白语),这正如宋代叶梦得的解说:“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外。”(《石林诗话》)
崇尚自然的审美观源发于道家的自然妙道说,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认为道如同自然物一样是自在之理,本身是“无为”的,不带任何功利目的,道“化生万物”也不是外力使然,人工造就。庄子进一步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知北游》)一切顺乎自然的就美。“自然”具有符合客观规律的丰富内涵,切合人们的审美心理。笔者曾将道家的自然妙道美学观归纳为:自然之本在真,自然之貌在朴,自然之魂在淡,自然之理在悟。(参阅拙作《道家的自然妙道与山水文学》,见《武陵学刊》1993年第2期)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主观情态,外观质朴,内在冲谈,不假斧凿,谢绝粉黛,确是一种上乘的境界。
厚含蓄薄浅露 以含蓄蕴藉为上,反对直言迳说的作品,也是传统鉴赏的审美要求。以含蓄为美,反映了一种普遍的艺术规律,体现了文学的基本特征。我国古代很早就发现“言”与“意”的对立统一关系,言要逮意,又要赅意,同时又有意在言外、意丰言简的现象。文学作品的表意功能,更要求以少驭多,由浅见深,言在此而意在彼。《周易·系辞下》就提出:“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这虽然是指《易》的表达方法,可是却最早道出了语言含蓄美的一般规律。而后直接指称文学作品的司马迁说屈原赋“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到梁的刘勰,更有专论,其《隐秀》篇中说:“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傍通,伏彩潜发。”所谓“隐”即为含蓄。“文外之重旨”、“隐以复意为工”、“义生文外”,都是说文学作品要言简意赅、文约意丰,使读者欣赏时能“秘响傍通,伏彩潜发”,可联想翩翩,味之无尽。钟嵘在《诗品序》中也提出诗要“使味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推崇含蓄美。唐代以后一直以含蓄为诗家之能,刘禹锡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里。工于诗者能之。”(《董氏武陵集记》)司空图《诗品》中更提出了为人乐道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说。“浅深聚散,万取一收”。张联奎在《司空图诗品解说》中予以阐释:“纯用烘托,无一字道着正事,即‘不著一字’,非无字也。”“万取,取一于万,即‘不著一字’,一收,收万于一,即‘尽得风流’。”司空图还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出“愚以为辨于味,是要寻绎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宋代欧阳修认为诗家“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六一诗话》)姜夔说“语贵含蓄”,“若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白石道人诗说》)严羽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声,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诗辨》)到了明代,仍然一脉相承,李东阳说:“诗贵意,意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浓而近者易识,淡而远者难知。”(《簏堂诗话》)谢榛主张要有“辞后意”,清代沈德潜“恐露”说,都以含蓄为旨归。
含蓄成为古代文学鉴赏的审美崇尚,一方面是语言要求,能以少总多,精炼地、概括地准确地表达内容,即用语少含意丰。另一方面是篇章要求,即通篇的表现艺术,以一写十,以点写面,以小写大,以此写彼,以显写隐等,使人得篇外意,味外味,能拓展人的思维空间,激荡人的感情湖面。含蓄和浅露相对立,而含蓄又不是晦涩,和寄托也不同。晦涩,隐晦艰涩,使人费解。含蓄使人能思而得之;晦涩,则叫人百思不解。寄托,言在此而意在彼,和含蓄的意在言外相近,相关,而却是另一类型的艺术手段。
贵传神贱描形 我国古代文学创作论和鉴赏论中,都关注到艺术形象的神形问题,要求神形兼备,以传神为主。文学艺术上的形神论,源于哲学、美学上的形神论。道家把抽象的形而上的“道”看得高于一切,贬低和否定具体的形而下的“物”。庄子在《德充符》中讲了个“恶骇天下”的哀骀它,其人形貌丑极,可是人人喜欢他,男人见了离不开他,女人见了愿意做他的小妾,国君甚至想要“授以国”。说这是因为“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成玄英疏:“使其形者,精神也。”说明哀骀它虽然形貌丑陋,但内在精神是美的,因而大家喜欢他。庄子虽然许多地方讲得有点极端化,可是其强调“神”对后世鉴赏审美影响却很大。到西汉刘安主编《淮南子》就比较辩证地谈了神形关系,重视神,还要借形传神。《说山训》云:“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画吴越美女西施的面貌,战国时勇士孟贲的眼睛,如果缺少“君形者”,不能够传神,那显不出美与威武。嗣后,六朝时受玄学和品藻人物之风的影响,使传神之说逐步成了鉴赏中的审美崇尚。魏晋时品评人物的神气、神情、神姿、神隽、神韵、风神等,移植到文学艺术上来了。最精彩的例子就是大家熟知的顾恺之画人:“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 ,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赏誉》)顾恺之为裴楷画像,颊上添了三笔,“益三毛如有神明”,后来苏轼在《传神记》中就顾恺之的实践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说明,要找出事物的典型特征予以传神。
描形往往只得外在形貌,传神则透出内在的精神,唐代张九龄在《宋使君写真图赞并序》中主张“意得神传,笔精形似”。苏轼更有一为人乐道的名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与苏轼同时的晁说之较苏轼说得更公允些:“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传画中态。”(见杨慎《升庵诗话》)诗贵传神,因而鉴赏中出现了神气、神韵、神妙等概念。关于“传神”、“神似”的问题,可参阅拙作《论古代文学鉴赏范畴的中国特色》中有关部分,(见《阴山学刊》1993年第4期)
崇意境卑模写 意境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也是一个特殊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鉴赏要求。虽然对意境、境界的涵义学术界还有争议,可是王国维所说的“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自成高格。”(《人间词话》)却是历代的共识。意境,注意到意与境、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先秦时《易传》的“立象尽意”,庄子的“言不尽意”说,“诗六义”有比、兴。汉魏六朝时期,陆机、刘勰、钟嵘论述情与物的关系,“意象”、“滋味”、“风骨”、“神韵”等概念,对意境说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佛教传入,提倡象教、境界,对意境说的形成更有直接的作用。意境作为审美范畴,当推唐代王昌龄的《诗格》,皎然的《诗式》为最早标示,宋代范晞文曾以具体诗句阐述意境中情与景的关系:“老杜诗‘天高云去尽,江迥月来迟。衰谢多扶病,招邀屡有期。’上联景,下联情。‘身无却少壮,迹有但羁栖。江水流城郭,春风入鼓鼙。’上联情,下联景。‘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景中之情也,‘卷帘唯白水,隐几亦青山。’情中之景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情景相触而莫分也。‘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凉。高风下木叶,永夜揽貂裘。’一句情,一句景也。固知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对床夜语》)明代谢榛概括地说:“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浩无涯矣。”(《四溟诗话》)清代王夫之并进而讲情与景的融合:“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姜斋诗话》)近代王国维还指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人间词话》)古人对触界生情、情景交融讲得很多,吴功正同志以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和我国“无人合一”的哲学观,提出了意境的建构理论,认为“建构是以主体为本位的体认活动,在自然山水审美中‘境’是被‘意’的主体功能所建构起来的。它不是对象本身,而是主体同化机制。”(《中国文学美学》第161页)把“境”视为一种建构现象,有别于传统的把“境”看成仅仅是客体的见解。吴功正将山水诗分为四种建构的类别:道德伦理的山水建构,情感心态的山水建构,哲学意识的山水建构,历史意识的山水建构。这是就山水诗而言的,而我国传统的审美崇尚的意境,其涵盖面很广,其意指也不拘执一端,因而王国维才说“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以“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揭出了文学作品能感人的重要原因。历代鉴赏家所推崇的意境高妙之作,实际上乃指其味隽永,其神灵动,其势飞扬,其情诚挚,其语精纯之作。崇尚意境,自然以那些模写物象的作品为卑下,布颜图认为“笔、境兼夺为上”:“笔既精工,墨既焕形,而境界无情,何以畅观者之怀?境界入情,而笔墨庸弱,何以供高雅之赏鉴?”(《画学心法问答》)可见意境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
主创新反因袭 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文学创作上也要求不断创新。人们审美心理上也是追奇逐新,厌恶陈陈相因。魏晋时期,对文学创新尤为强调。陆机说:“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文赋》)意谓已经开过的花就应当舍弃,而努力促使那些未开的花及早开放。钟嵘对当时“文章殆同书钞”的因袭作风表示极端愤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通变》、《时序》专门谈了这方面问题。“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通变》)客观事物日新月异,“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时序》)人情文事自然也因时变而变,“故知文变染乎世情,而兴废系于时序”,刘勰比较辩证地讲了通与变的关系,也就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奇制,参古定法。”(《通变》)”文学鉴赏上,也一直以新颖独创为优。既要求立意上的新,也要求艺术手段、语言形式上的新。唐代杜甫自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宋代欧阳修说:“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六一诗话》)南宋杨万里曾作诗云:“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清代刘熙载说:“词要清新,切忌拾人牙慧。盖古人为清新者,袭之即腐烂也。拾得珠玉,化为灰尘,岂不重可鄙笑!”(《艺概·词曲概》)清代赵翼的《论诗绝句》:“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王夫之说“好驴马不随队后”,都是讲力求意新语新。不管诗词、小说、戏剧、鉴赏者都肯定其新,欣赏新鲜美。
我国古代文学鉴赏的审美崇尚是多方面的,上述仅是举其要而言之。其他如动静结合,虚实相生、浓淡互用、雅俗共赏、奇正变化等等。即就是上列五项,相比较而言是重自然、厚含蓄、贵传神、崇意境、主创新,但也不绝对地排斥适当的藻饰,必要的浅白,高妙的描形,忠实的摹写,传统的继承。文学美本身就具有丰富性的特点,鉴赏者的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具有差异性的性质,使审美崇尚呈现出多样性、变化性。我们只是就整个民族、长期历史所表现出的具有共同的崇尚倾向而已。
我国古代文学鉴赏审美崇尚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和我国长期的文化淀积、审美心理建构,民族气质等密切相关。
审美崇尚是文化淀积的结果 对我国人民思想性格形成的文化因素,在古代主要是儒、道、释三家。孔子主张情信辞巧,也就是表达要顺乎自然,自然而然,不要矫揉造作、华词丽藻。他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要有文采,但不是藻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以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和前文所述道家的自然说互补互用,也就逐步形成了“重自然轻雕饰”的崇尚。同样,孔子“温柔敦厚”的诗教,和道家关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说,佛家的禅悟说,形成“厚含蓄薄浅露”的崇尚。《礼记·经解》记载孔子的话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即所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这一方面是中和的感情,另一方面也是要求含蓄的表达。同时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使人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教化目的,都不主张径情直说,而要委婉曲达。佛家叫人悟道,回避直道其详,要人感而悟之。三者异途同归,合力同构,使含蓄不仅成为被推崇的艺术手段,而且成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人们说中国人是“热水瓶”性格──外冷内热。不轻易表情,即就是言情也含而不露,蓄而不泄。这种民族性格自然导致他的崇尚。“贵传神贱描形”,系佛教传入后,促使了六朝绘画的发展,由画论引入诗论、文论。总之,古代文学鉴赏的审美崇尚,不是单一因子的发展,也非一时的作用所致。长期文化淀积使之孕育成熟,潜入人们的意识之中,结果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又是普遍的审美要求与标准。
审美崇尚是心理建构的产物 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并非机械的镜子式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造成审美崇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审美心理结构存在着差异。某种审美崇尚,也是某种审美心理定势的体现。民族生活的特殊性对个体成员审美活动心理定势的形成具有强有力的作用,而这种心理定势的共性,就形成了特定民族的审美心理结构。德国美学家约·埃·史富格尔在一篇讨论民主戏剧的文章中指出:“每一民族,都是按照自己的不同风尚和不同规则,创造它所喜欢的戏剧”。其实,风尚和规则促成了不同民族成员的个性心理特征,这种心理特征制约着全民族的艺术美的创造和欣赏。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以及封建社会长期的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封闭的伦理观念的统治,在这样的土壤上滋生出的风尚和规则,陶治着民族性格,甚而造成民族审美思维方式的差异。我国古代仍停留在整体思维阶段,与讲究分析、注重普遍、偏于抽象的西方思维方式不同,比较注重具体的直观把握,因而审美崇尚自然、含蓄、传神、意境等,注重在“表现”上的美感,而非“再现”上的准确。中国被称为“诗的国度”,不仅因有大量的灿烂的诗篇,长期的诗歌历史,而且有着诗的心灵和诗的思维。
审美崇尚是民族气质的表现 上述已经触及到民族气质问题。民族气质关系着民族审美心理。各民族的与生存相关的自然条件和该民族自己所造就的社会条件,长期作用于民族的群体,形成有别于他民族的特有气质。古代认为我国处于“四海之内”,“风调雨顺”的环境,农耕为主的生产,滋生出“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于是对自然山水先秦的“比德”说,六朝的“娱情”说,唐以后的“情景融合”说,都没有把自然视为对立物、征服对象。人与自然的亲和感、和温柔敦厚、含而不露的民族气质关系很大。我国古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等造就的民族气质,使中华民族成为礼义之邦,自我感觉地灵人杰,在和谐的环境中品味赏韵。古代文学鉴赏中的审美崇尚和这种民族的气质互为表里。
综上述可见,自然的、社会的因素造就了中国古代人的民族性,民族性的心理素质表现为它的审美崇尚。审美崇尚导致文学创作上的倾向,并引导文学鉴赏上的审美标准、审美判断。创作和鉴赏又互为作用,创作促进鉴赏,鉴赏又反作用于创作。这两者之间都受审美崇尚的制约和推动。如此反复循环,使共同的审美崇尚更加鲜明,更趋稳定。这又汇成一个使大家信守的文化氛围,从而陶冶着人们的心灵。就是这种多重因果关系、互逆反应,使我国古代文学呈现出中国特色的风格和流派。
今天我们探讨古代文学鉴赏审美崇尚的特点与形成,不仅可以把握古代文学鉴赏一向推崇什么,贬斥什么,而且能够缘此明了文学史上多次思潮斗争的一方面的原因。同时,这也便于总结古代文学鉴赏的经验、源流以及不足之处,从而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鉴赏古代文学作品,并进而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古代文学鉴赏学,有既保持民族传统的,又具有时代精神的审美崇尚,推动新时期文学事业的发展。
